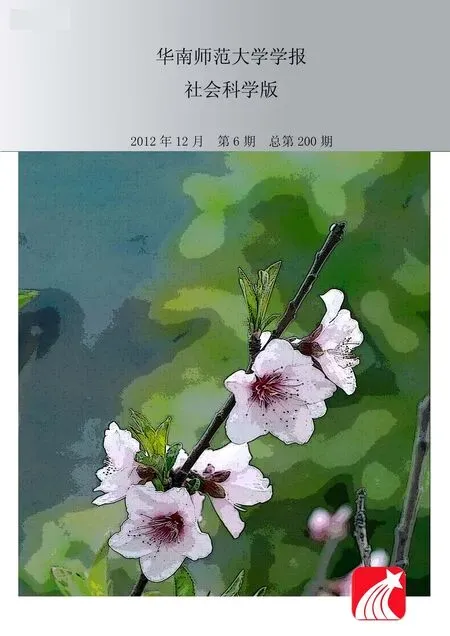独创性与超越性:莫言的启示
郭 杰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无论对获奖者本人,对中国文学界,还是对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融合,都是一件包含深刻启示、具有广泛意义的事件,值得人们认真思索。
一、莫言获奖的里程碑意义
自1901年首次颁发以来,在一个多世纪的岁月里,诺贝尔文学奖已经颁给了一百多位具有高度成就和广泛影响的各国作家。[注]1914年、1918年、1935年、1940年、1941年、1942年、1943年未颁奖;1904年、1917年、1966年、1974年由二人共同获奖。虽然对这份名单上某些作家的上榜理由、水平和成就,人们不可避免地还会存有一些争议,但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世界文学的最高荣誉,则是举世公认、无可置疑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截至2012年10月11日,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蜚声国际的文学荣誉,却一直与中国作家无缘。[注]在获奖者中,有以英文写作、反映中国内容的非中国籍作家(如赛珍珠,即珀尔·巴克,美国,1938年获奖),也有以中文写作、反映中国内容的非中国籍作家(如高行健,法国,2000年获奖),但却没有以中文写作的中国籍作家。这与中国近百年来新文学传统的发展成就是不相符合的,但却真实反映了外部世界对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的认知程度,对双方来说,这都是一种令人沮丧而又无法超越的隔膜。这一状况,由于瑞典文学院2012年10月11日宣布中国作家莫言的获奖,已经得到了相当的改变。这是随着时代推移而产生的历史性变化,因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恩隆德,在宣布获奖者姓名及其获奖理由时说,中国作家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瑞典文学院新闻公报中说:“从历史和社会的视角,莫言用现实和梦幻的融合在作品中创造了一个令人联想的感观世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瑞典汉学家马悦然接受专访时说,莫言是一位很好的作家,他的作品十分有想象力和幽默感,他很善于讲故事。此次莫言获奖将会进一步把中国文学介绍给世界。[注]据新华网2012年10月11日消息。
当我们说莫言的获奖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时,我们理所当然地首先是从文学上看待这种意义。
莫言是活跃于当代文坛上的一位勤奋的、多产的、富于个性化的、具有强烈独创性和想象力的中国作家。自1985年发表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这一成名作以来,二十多年时间里,莫言陆续发表了《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食草家族》、《丰乳肥臀》、《红树林》、《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蛙》等十多部长篇小说,以及一些中篇和短篇小说。如此众多的作品,足以证明这是一位极为勤奋的作家。而其作品中一以贯之的鲜明个性、强烈的独创性和奇幻诡异的想象力,即所谓“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也让他在为数众多的中国当代作家中名列前茅,获得了中国文学的最高荣誉——茅盾文学奖以及其他许多重要奖项;不仅如此,他的作品还通过二十多种语言的翻译,在世界各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由此看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实在是当之无愧的。
应该指出的是,尽管可能很多人(包括获奖者和评审人)都强调,诺贝尔文学奖只是基于文学的理由颁给作家本人的奖项,我们却不能不看到,莫言的获奖,实际上也是近百年来中国新文学传统发展演进的题中应有之义。在这个意义上,它才更加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当1901年首次颁发的诺贝尔文学奖迎来112个年头的时候,正值发端于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国新文学传统将要完成一个世纪的蜕变和再生。新文学传统的本质,就是运用自古以来具有悠久传统的白话文体,融会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文化成果,而以真实深刻地表现当下社会生活中人们的精神轨迹和心灵状态为旨归。由于“救亡”与“启蒙”主题的相互交织,重视伦常教化、讲求社会功利的传统文学观念,亦即强调现实性功能的观念,在新文学传统深层意识中,一直保持着颇为强大的影响力,这就在积极干预和推进社会生活的同时,也若隐若现地忽视了文学的超越性功能。而不绝如缕的超越性的线索,终于在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的时代氛围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个性化、独创性、想象力等文学创作的本质精神特性,在一个宽容和鼓励的环境下,正在蓬勃地繁荣和发展起来。法国艺术史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说过,只有处在同时代众多艺术家所构成的时代精神的森林里,伟大艺术家犹如一棵巨树拔地而起的辉煌成就才会成为可能。莫言的成功,是时代整体的精神氛围的个体性化呈现,其中凝聚着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精神追求,大而言之,它以个案的形式,展现了新文学传统经过百年发展而自然形成的格局和结果。这当然不是莫言获奖之后才引发的意义,但他的获奖却提醒人们更深入地关注和思考这一问题。
在全球化的时代浪潮下,在中国崛起的历史进程中,莫言的获奖,一方面将有助于增强中国作家的信心,唤起中国社会对文学更普遍的关注,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学(文化)与世界之间日益加深的交流,另一方面也将有力地拉近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作家和普通中国人之间的距离,使这一世界性的文学荣誉,由于十三亿中国人的广泛关注而更富于活力。
二、情节诡异、想象奇幻:莫言创作的独创性
莫言是一位成功的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他成功的结果,而不是成功的原因。那么,作为主要依靠十多部长篇小说的创作而取得成功的作家,莫言的制胜之道是什么?
在带有艺术宣言性质的《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一文中,莫言这样写道:“长度、密度和厚度,是长篇小说的标志,也是这伟大文体的尊严。”“所谓长度,自然是指小说的篇幅。”“一个作家能够写出并且能够写好长篇小说,关键的是要具有‘长篇胸怀’。大苦闷、大悲悯、大抱负、天马行空般的大精神、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大感悟——这些都是‘长篇胸怀’之内涵也。”“长篇小说的密度,是指密集的事件,密集的人物,密集的思想。”“长篇小说的难度,是指艺术上的原创性,原创的总是陌生的……难也是指结构上的难,语言上的难,思想上的难。”他这些话,不同于一般的理论家或批评家,不是仅仅基于逻辑思辨的理论构建,而是从自身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心得体会,是其丰富创作经验的艺术审美升华。验之莫言的主要作品,这些观点都是贯穿始终、若合符契的。这是经验之谈、实践之果,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莫言关于小说创作成功的夫子自道。
具体而言,首先聚焦长度、密度、难度三者,因而也成为莫言小说创作的制胜之道的,莫过于其中与众不同、而又不可重复的艺术的独创性。独创性,这是莫言创作的重要启示之一。莫言自己曾说:“我一向认为,好的作家必须具有独创性,好的小说当然也要有独创性。”[注]莫言:《我为什么要写〈红高粱家族〉》,见莫言:《红高粱》,第150页,花城出版社2011年版。而莫言小说的独创性,是通过其中精心结撰的奇幻诡异的情节(故事)体现出来的。马悦然曾经感叹,莫言“很善于讲故事”。他的几乎每一部小说,都具有离奇、独特、奇幻、诡怪的情节(故事),仿佛蒙上一层诡异多变的迷雾,神龙见首不见尾,永远是那样出人意表、令人不可思议,实现了现实与幻想的完满融合,所以被称为“魔幻现实主义”。而这一切,离开了独特的、奇幻的、超现实的、富于个性化的想象力,无疑是难以实现的。正如黑格尔在《美学》中所说:“如果谈到本领,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象。”[注]黑格尔:《美学》,第一卷,第375页,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最大限度地赋予想象力以广阔空间和无限可能,从而创造出奇幻诡异、离奇多变、仿佛蒙上神秘面纱的情节(故事),让人永远无法预测其过程和结局,只能揣着一颗焦急而好奇的心,一步一步随着情节的发展,窥测各种变化的可能。在此过程中,读者由于焦虑和好奇,也在不知不觉中张开自己的想象的双翼,从而完成了艺术的再创造的活动。正如莫言自己所说:“讲故事的能力就是想象力。有的人可以讲一个活灵活现的故事,就因为他有想象力。”[注]莫言:《与〈文艺报〉记者刘颋对谈》,见莫言:《红高粱》,第171页,花城出版社2011年版。
例如,曾改编成电影、并获第38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的中篇小说《红高梁》,从一个孩子的视角,交织描写土匪头“我爷爷”率部伏击日军车队,以及“我爷爷”与“我奶奶”之间的离奇情爱,两条线索错综交织,情节诡异,场面悲壮,叙述角度富于变化,成功运用意识流的表现手法,尤其注重人物主观的感觉和感受的叙述。而当这连串涌现的极富动态感和画面感的感觉,出自一个农村孩子的视角,就更具有了成年人、城里人所无法抵达、而又深感新奇甚至神秘的特殊境界。由此形成了莫言一贯的独特艺术风格。到了晚近出版的作品中,这一风格表现更为突出,并达于极致。200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蛙》,曾于2011年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小说由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五封书信、四部长篇叙事、一部话剧剧本融合为一体,不仅有力地开拓了小说艺术的表现空间,同时也实现了新文学史上一次重要的文体创新和革命。没有独特奇幻的原创性和想象力,这显然是难以办到的。因此可以说,富于鲜明独特性和奇幻想象力的离奇诡异的情节(故事),是莫言小说创作的制胜之道,是他取得艺术成功的法宝。
三、跳出表象、俯瞰人性:莫言创作的超越性
跳出现实功利性的有限格局的约束,摆脱流于简单化的善恶二元论,着力从深层次发掘复杂而矛盾的人性内涵,进而实现艺术的超越性,这是莫言小说创作取得成功的又一制胜之道。莫言自己曾说: “只有正视人类之恶,只有认识到自我之丑,只有描写了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才是真正的悲剧,才可能具有‘拷问灵魂’的深度和力度,才是真正的大悲悯。”[注]莫言:《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载《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1期。事实上,他笔下的人物,都是善恶杂糅、处于各种命运的制约下、具有复杂人性内涵(即所谓“大悲悯”)的形象,不是依靠简单的道德评判,而是依靠深邃的人性发掘,给读者带来强烈的震撼。
例如,2003年出版的《丰乳肥臀》,是莫言早期创作的一个高峰,被称为“民间史诗性书写的成功试验”。小说中主人公上官金童,是母亲和一个瑞典牧师的私生子,是一个懦弱无能的恋乳癖者,永远只能依偎在女性哺乳下,永远不能自立。而他的母亲,因为丈夫的生理无能,一生所生育的八个子女中,竟没有一个是与自己丈夫共同的孩子。整个情节离奇古怪,犹如天方夜谭;而婚外私通的情形,更为古今中外的伦理所不容。这一切,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实为前所未有。人们不禁要问,这样一部小说,究竟有何意义呢?仔细想来,它借助夸张性的象征,表现了深邃的人性意义。所谓“丰乳肥臀”,本身就是极具想象力、富有隐喻性的艺术象征:“肥臀”象征生育,“丰乳”象征哺养。这是女性所独具的最伟大的人性——母爱的象征。每个人,无论男女老幼,既然都是物质的存在,都有生理性需要,以及由此而来的七情六欲,那么善恶美丑,也一定错综交织,呈现人性的复杂内涵。恩格斯曾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第15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而从人性的角度来说,在“人类自身的生产,种的繁衍”的过程中,更能产生出人类最深邃的感情,即人性最美好的方面,这既体现为男女两性之间的爱(即爱情),也体现为父母对子女的爱(特别是母爱)。古往今来,爱情和母爱,永远是文学表现的主题。而《丰乳肥臀》,就深刻表现了无私而伟大的母爱这一永恒主题。
基于跳出表象、俯瞰人生的超越性,莫言作品中往往呈现出以下特征:一是象征性,即通过具体可感的物象,象征某种深邃的人生体验,深化作品的人性内涵;二是距离感,即通过黑色幽默式的调侃或讽刺,让人从外在的角度观察人类生存的状态,感受生活的无奈和辛酸;三是多变性,即叙述的视角可以不断变化,从一种视角转换到另一种视角,不受约束地展开描写。这一切,与莫言所始终保持的赤子般的纯真天性密不可分。莫言在《檀香刑》中这样描写女主人公:“孙眉娘从小跟着戏班子野,舞枪弄棒翻筋斗,根本没有受三从四德的教育,基本上是个野孩子。”从写作的角度来说,这也是农家出身的作家莫言的自我写照。作为山东高密的一个农家子弟,莫言一直保持着农民的朴野和聪慧,内心自由,不受礼法和各种成规的约束,天然成就一种极为丰富的、无拘无束的想象力,在道德上也较少陈腐教条的羁绊,能以调侃幽默的态度看待生活。虽然没有过于抽象的哲理性寻究,和把自己也折磨得痛苦不堪的终极性拷问,但却始终不失天真纯朴,而于心灵的放纵自由中,超越凡俗,自成格调,终于开创出前所未有的境界。可以说,超越性是莫言小说创作取得成功的又一制胜之道,是他带给我们的又一重要启示。
四、文学的使命:人性复杂内涵的深层次追究
莫言小说创作的成功,并非偶然。事实上,由于数量众多的作品的出版、在世界各的广泛的翻译和多次获奖,莫言早已引起海内外的高度关注和广泛认同。例如,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 1994年12月7日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感言中,谈到自己所继承的文学传统及其形象系统时,就对莫言做出了高度评价。他说:“正是这些形象系统,使我得以植根于我置身的边缘的日本乃至更为边缘的土地,同时开拓出一条到达和表现普遍性的道路。不久后,这些系统还把我同韩国的金芝河、中国的莫言等结合在了一起。这种结合的基础,是亚洲这块土地上一直存续着的某种暗示——自古以来就似曾相识的感觉。”[注]大江健三郎1994年12月7日在瑞典文学院发表的获奖感言,题为《我在暧昧的日本》。见大江健三郎:《我在暧昧的日本》,第89-97页,王中枕 、庄焰译,南海出版社2005年版。这位富有良知的日本作家所谓“某种暗示——自古以来就似曾相识的感觉”,应该就是这种坚韧不拔的超越性。大江还曾于2006年9月9日发表题为《始自于绝望的希望》的演讲时,做出明确预言:“我坚信中国很快会有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莫言先生就是强有力的竞争者。”他的预言,在六年之后的今天,终于变成了令人欣慰的现实。
当然,一个作家,即便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也不可能像鲤鱼跳龙门那样,即刻化为巨龙,骤然腾空而去,成为超凡脱俗的圣贤,必然取得不朽的历史地位。事实上,也确有一些获奖作家已经被历史所遗忘。甚至就莫言本身而言,恐怕也还不能说已经达到完美无缺、无懈可击的艺术极境。他对艺术语言的把握,似乎就略显平淡,神韵稍感不足。这里,不妨重温一下钱钟书的一席谈话,以期让我们更加理性地看待诺贝尔文学奖的意义。他说:“萧伯纳说过,诺贝尔设立奖金比他发明炸药对人类危害更大。当然,萧伯纳自己后来也领取这个奖的。其实咱们对这个奖,不必过于重视。”在谈到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因拿不到诺贝尔文学奖而耿耿于怀一事,钱钟书说:“这表示他对自己缺乏信念,而对评奖委员似乎又太看重了。”[注]《钱钟书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看法》,载《文艺报》,1986-04-05。应该说,钱钟书的淡定和自信是令人钦佩的。在中国人没有拿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应该如此;在中国人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同样应该如此。钱钟书的充满了人生智慧的话语,无疑是发人深省的重要启迪。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应该承认,无论诺贝尔文学奖设立的宗旨,还是其百余年来的评奖实践,都令人信服地表明,一个作家获此殊荣,绝非等闲之事,一般来说,必有其值得表彰的根基性理由。考察诺贝尔文学奖,有助于我们沉思文学的意义。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它借助于语言的媒介,进行艺术的创造,给人带来新奇的审美体验,进而产生感动和震撼。优秀的文学作品能达到艺术上的创造,而伟大的文学作品,则不仅能达到艺术的创造,还带来关于人性复杂内涵的深层次追寻——它并不给出现成的答案,而是触动和升华读者的精神和情感,从而产生心灵深处的强烈共鸣。而在此过程中,独特性和超越性显然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当莫言得知自己获奖后曾说:“我的文学表现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表现了中国独特的文化和民族的东西,同时我的小说也描写了广泛意义上的人,我一直是站在人的角度上,立足于写人,我想这样的东西超越了地区和种族。”[注]谢正宜等:《忠于对人的描写是自己获奖的主要原因》,载《新闻晚报》,2012-10-12。以独创性的艺术方法,以超越性的人生态度,努力探究人性的复杂内涵,为理解人类心灵提供一把钥匙,为人与人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的精神交流建立一座桥梁,文学的创作理应承载如此崇高的使命——这是莫言创作带给我们的启示,或许也是当年诺贝尔设立文学奖的初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