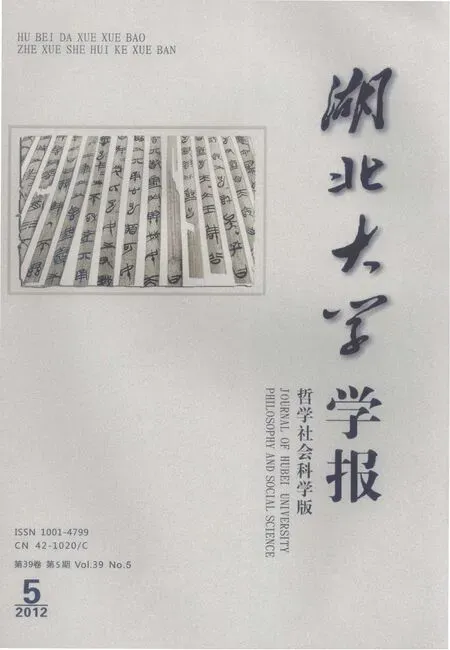论西方怪诞审美观念的多元变奏
宋雄华
(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西方的怪诞一词,最早来自意大利语中的La grottesca和grottesco,它是为称呼15世纪末在罗马发掘出的一种装饰风格而专门创造出的一个新词。但是,“怪诞这一现象比我们分配给它的名字更古老。一部全面的怪诞史,需要研究中国的、伊特拉斯坎的、阿兹台克的、古日耳曼的艺术,希腊(阿里斯托芬)和其他民族的文学”[1]201。“怪诞的形象观念类型最为古老:在所有民族的神话和古风时期的艺术中,当然也包括古希腊人和罗马人在前古典时期的艺术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类型”[2]37。实际上,早在“怪诞”这个词汇产生之前很久远的人类各民族的早期艺术中,怪诞艺术就产生了并不断发展着。约出现于公元前2550年的古埃及雕塑狮身人面像,一般被认为是怪诞在现存较早期的造型艺术中的最杰出代表之一。
虽然古希腊艺术的主要精神是追求优美、和谐,但古希腊文艺中也有怪诞的传统。怪诞的埃及雕塑狮身人面像后来就传到了古希腊,虽然其中的人面由原来的男性变成了女性,而且加上了翅膀,其意义也发生了变化,但其怪诞的性质并没有变化。在希腊人的眼里,怪诞的狮身人面像是一个伟大之谜,“代表古希腊人对此宇宙神秘的一种象征表现”[3]276~277。“希腊人尽管生活在理想之中,还是有他们的百手怪、独眼巨人、长有马尾马耳的森林之神、合用一眼一牙的三姊妹、女鬼、鸟身人面的女妖,以及狮头、羊身、龙尾的吐火兽”[4]516。另外,古希腊神话传说中也塑造了许多怪诞的艺术形象,如百眼怪物、九头蛇、龙、蛇发女怪美杜莎、蛇尾羊身狮首的喷火女妖、长着双翼的神马、上身是女人腰部以下是鱼的美人鱼,以及大量半人半兽、神人互变、神兽互变等形式各异的怪诞形象。总体上看,古希腊人描绘的怪诞艺术还处于幼稚阶段,这时的怪诞①雨果《克伦威尔·序》中有个法文词grotesque,柳鸣九1961年在《世界文学》第3期上将它译成“滑稽丑怪”。刘法民认为,根据国际惯例,grotesque应当译为“怪诞”。参见刘法民《雨果的“grotesque”理论名曰“怪诞”而非“滑稽丑怪”》,《外国文学》2005年第一期。“还是怯生生的,并且总想躲躲闪闪。可以看出它还没有正式上台,因为它在当时还没有充分显示其本性”[5]32。
但是,怪诞艺术一经产生,就以其独特的魅力引发了一些理论家的思考。西方的怪诞审美观念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并因为出现于不同历史时期产生于不同国度和不同理论家之手,而呈现出异彩纷呈的面貌。下面我们拟对这些形形色色的怪诞审美观念进行一次比较全面的梳理,以期对其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理解。
一、怪诞的审美形态:奇怪与反常
尽管怪诞艺术在原始艺术中就已出现,但就现有的资料看,直到古罗马时期,怪诞艺术才进入西方理论家的视野。怪诞一进入古罗马学者的视野,就被视为反常的,遭到了猛烈的批评与贬斥。古罗马学者的怪诞观,主要以建筑学家维特鲁威和文艺理论家贺拉斯对怪诞的看法为代表。公元前1世纪,古罗马建筑学家维特鲁威论述了当时建筑壁画中新出现的一种风格。首先,维特鲁威描述了这种建筑壁画的具体表现:“在墙面上画出的是奇奇怪怪的东西……或在柱子之处攀援起来藤萝;或画出有卷叶和涡卷的条沟纹样而取代人字顶;或又画出支承着小神庙模型的烛台,而在其人字顶之上有许多柔软的细茎和涡卷一起从根生长出来,在其中甚至没有意义地坐着一尊小像。此外,这些细茎常常是一些有着人头半身像,另一些有着兽头半身像。”其次,维特鲁威分析了这种建筑壁画产生的原因是:“从真实的东西取其形象的绘画在今天由于不适意的情趣还没有被承认下来”,当时的人们“心灵被不健全的判断所蒙蔽,竟不能以威信与适合原理来验证实际可能存在的东西”。再次,维特鲁威指出,这种建筑壁画“现今既不存在,也是不可能存在的,或从来就未曾存在过”。最后,维特鲁威还谈到了他形成这些看法的理由:“不模仿真实存在的东西的绘画是不能承认的。又即使在技艺上绘制得精美,但是根据上述的道理,如果没有不可驳辩的理由来加以证明,还不能认为是正确的。”[6]164~165从维特鲁威的具体描述和相关评论来看,他提到的这种建筑壁画就是一种怪诞绘画。与维特鲁威同时代的古罗马文艺理论家贺拉斯,也曾论述过类似的怪诞绘画。贺拉斯描述了一幅由美女的头和马颈、各种动物的四肢、鸟的羽毛以及鱼的尾巴等不同动物身上的器官“拼凑”而成的怪诞画,并批评说:“画家和诗人都有向一切事物挑战的特权。……并且既要求具有这样的特权,但是又不能过了头,以致于把温顺和野蛮结合在一起,让蛇与鸟同体、绵羊与猛虎联姻。”[7]137
从古罗马学者维特鲁威和贺拉斯对怪诞绘画的批评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之所以贬斥怪诞的艺术风格,是因为他们基于艺术是模仿生活和再现现实的古典主义的美学理论,要求艺术“模仿真实存在的东西”,“从真实的东西取其形象”,不理解怪诞这种不符合他们追求规范、规则、秩序、和谐与理性等古典主义艺术原则的新兴艺术形式。古罗马学者维特鲁威和贺拉斯虽然都是当时各自领域中的权威人物,但怪诞绘画这种新的艺术样式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反对和贬斥而止步不前,反而以旺盛的生命力不断成长壮大起来,甚至因为他们的反对而引起了更加广泛的关注。维特鲁威和贺拉斯所批评的那种怪诞绘画,在文艺复兴时期被意大利画家广泛模仿,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但是,文艺复兴时期怪诞艺术的蓬勃发展,丝毫没有阻挡住德国理性主义美学家们继续对怪诞艺术进行批判的步伐。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批评家高特雪特从他的理性主义立场出发,将怪诞贬低成笨拙的艺术家的梦幻或“想入非非”[1]15。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艺术史家温克尔曼认为,不能用理性来解读的怪诞艺术,应该接受“理智的浸渍”[8]33~34。德国古典美学的奠基者康德把理性视作“检查、衡量”[9]62一切事物的标准,在论述崇高(高贵)、冒险、怪诞三者之间的关系时,指出了怪诞与不自然的、古怪的、颠倒的、荒唐的、废物、神话故事[10]10~12等元素具有不解之缘。在谈到不同民族的民族性时,康德指出了怪诞与宗教、违反自然、奇怪的、不自然的、颠倒混乱的[10]59~60等因素的密切联系。德国古典美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认为,怪诞艺术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第一,将不同领域里的事物反自然地拼凑和混合在一起,形成怪诞艺术。印度艺术就是“人与自然这两个因素的怪诞的混合”[11]54。第二,以离奇的想象将对象歪曲和颠倒,造成怪诞艺术。怪诞艺术是想象的“晕头转向的狂乱跳舞”,想象力往往凭歪曲“把个别的形象推到它们本来的界限以外,加以夸张,把它们改变成为无定性的,漫无边际的,支离破碎的”[11]45~46。第三,将同功能的事物无限夸大、扩大、增殖,创造出多头多肢的怪诞艺术形象。为了表达意义的广度和普遍性,印度艺术或“依靠形象的漫无边际性”,让形象“被扩大成为光怪陆离的庞然大物”,或“采用最浪费的夸大手法”,或“按倍数去扩大同一定性或因素,例如一座像可以有许多身体或许多手”[11]50。
从高特雪特、温克尔曼、康德和黑格尔等人对怪诞的描述和批评中,可以看出,他们认为怪诞艺术是古怪、荒唐、可笑、杂乱无章、想入非非、畸形的东西,是胡乱拼凑、随意歪曲的结果,是混乱、颠倒、违背自然形态的反常形态,并对怪诞表现出愕然、厌恶与贬斥的敌视态度。他们之所以贬斥怪诞,是因为他们是以理性主义为标准来衡量怪诞的,怪诞艺术不符合他们追求规范与秩序的艺术观。
二、怪诞的审美心理:恐怖与滑稽
随着人们在艺术实践中对怪诞的广泛运用,同时,经过德国浪漫派的非理性思潮的冲击,西方学者的怪诞观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到18世纪下半叶,西方学界对怪诞风格开始“有了比较深刻和广泛的理解”[2]39,许多学者对怪诞作出了新的富有创造性和建设性的阐释。法国学者雨果认为,怪诞不但不是混乱和反常的,而且是指向现实的,甚至是反映人性的,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广泛的社会作用。雨果指出,怪诞是近代社会产生的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在近代人的思想里,怪诞“具有广泛的作用。它无处不在:一方面,它创造了畸形与可怕;另一方面,创造了可笑与滑稽”[5]33。他还指出:“人也是二元的,在他身上,有兽性,也有灵性。”[5]26在新的诗歌中,崇高优美将表现灵魂经过基督教道德净化后的真实状态,这种典型将拥有一切魅力、风韵和美丽;而怪诞则将表现人类的兽性,这种典型则将“收揽一切可笑、畸形和丑陋”[5]37。雨果还从生活和艺术辩证法的高度提出了他的著名理论:“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的背后,美与恶并存,光明与黑暗相共。”[5]30这就肯定了怪诞与优美、崇高的血肉联系,大大提升了怪诞的艺术价值和美学地位。
英国学者约翰·罗斯金指出,怪诞的作品虽然有时因荒唐的成分占主导地位而成为可笑的怪诞,有时因恐惧的因素占主导地位而成为可怕的怪诞,但几乎所有的怪诞作品都同时包含了荒唐与恐惧这两种因素,是可怕与可笑的统一体。“所有这类作品都无不在一定程度上同时具有这两种成分,没有哪幅怪诞画只是一味地追求滑稽可笑而不含有恐惧的色彩;也很少有一幅让人恐惧的怪诞画不具有逗乐取悦的意图”[12]282。美国现代艺术理论家简·布洛克指出,西方评论家在解释某些大型的“怪物”面具时往往会上当,譬如塞拉利昂的曼德·贡古里,有夸张的大鼻子、大耳朵、大眼睛,张开的大口中有巨齿突出在外。西方评论家认为“它的审美特征是凶残的和恐怖的”,但当地人认为它是“幽默的”。这是“因为夸张的巨大面具器官在审美上究竟是幽默还是恐怖,本身就含混不清,即使在我们西方文化中也是如此”[13]177。面对同一幅怪诞面具,西方评论家和当地非洲人的审美感受之所以出现那么大的反差,就是因为这幅怪诞面具本身就具有双重性,它既给人带来恐怖,又让人感到可笑。
托马斯·克莱默认为,“怪诞乃是被推向极端的滑稽所唤起的焦虑感”,反过来,“面对不可解释的事物,怪诞依靠滑稽战胜了焦虑感”[14]83。这就是说,怪诞的滑稽感既能引发焦虑感,又能消除焦虑感,怪诞是滑稽与焦虑的统一体。在此基础上,迈克尔·斯泰格从心理学角度这样定义怪诞:“怪诞乃是滑稽对怪怖的驾驭”,“怪诞的这两个极端类型(恐怖占主导地位的和滑稽占主导地位的)……都使我们回到幼年,——一个试图从恐惧中获得解放,而另一个则试图从压抑中获得解放。”[14]83~84这样,斯泰格就从心理接受机制上,为我们阐释了怪诞既消除焦虑又制造焦虑的悖论性质。
以上理论家对怪诞的论述,主要揭示了怪诞审美心理的双重性:怪诞既是恐怖的,因其可怕的内容会引起我们的恐惧;怪诞又是可笑的,它能带给我们一些轻松的感觉,因其往往以滑稽的形式表现出来。
三、怪诞的审美功能:狂欢与创造
18世纪德国文学家默泽尔认为,怪诞是一个特殊的“幻想世界”,“即把各种异类因素结合在一起的世界”,它存在“对自然比例的打破(夸张性)、漫画和戏仿因素”,这样的怪诞风格具有“出自人类心灵追求愉悦和快活的一种需求”的“诙谐因素”[2]42。18世纪末德国的歌德指出,古代的怪诞原是处于正统地位的迷人的艺术风格,是文学的“原始形式”和所有伟大艺术的基础。他在梵蒂冈敞廊观赏拉斐尔创作的浮雕时,面对那些花卉漩涡中的丘比特头像、鹰头狮身带翼的怪兽等怪诞装饰图案,极力推崇拉斐尔那不竭的创造力和对古代装饰风格的复兴,并对作品中表现出的“欢乐、轻快的气氛和丰富的想象”[1]10十分欣赏。
19世纪的F.菲舍尔指出,动物形式与人类形象、有生命的物质与无生命的物质混为一体的怪诞形象,“往往带有一种长久不衰的幽默情调,而这种幽默情调是怪诞的决定性因素,而怪诞的产生是与荒谬和滑稽的贡献分不开的”[1]106~107。在这种古怪的幽默中,菲舍尔仍然感觉到一种“奇特的、不祥的、深不可测的品质。他反复谈到‘疯狂’,正是这种因素混淆了不同种属的事物,把事物本身‘固有的轮廓’搅得乱七八糟。不过,他还是如往常一样把‘欢快’和‘疯狂’联系起来,从而去掉了后一词非理性的、不祥的属性”[1]107。. 美国学者桑塔耶纳充分肯定了怪诞的创造性。他认为,怪诞不是胡拼乱凑,而是一种重新创造,是“改变一个理想典型,夸大它的某一因素,或者使它同其他典型结合起来所产生的一种有趣的效果”。它的优点“在于重新创造,造成一件自然所没有但想必可以产生的新事物”。它虽然背离了自然的可能性,但没有背离内在的可能性,这正是怪诞的创造性的真正魅力。因此,“正如出色的机智是新的真理,出色的怪诞也是新的美”[15]175~176。苏珊·科利(Susan Corey)指出,怪诞“通过夸张、扭曲、矛盾、不协调和震惊的作用,打破常规的感观方式,激发新的联想,发掘新的意义”[16]。这就肯定了怪诞在打破常规、创造新的意义上的重要价值。
苏联学者巴赫金在评价古罗马的怪诞艺术时,就认识到了怪诞是快活的、欢乐的、自由的创造。他说:“新发现的这种罗马装饰图案以其植物、动物和人的形体的奇异、荒诞和自由的组合变化而使当时的人们震惊,这些形体相互转化,仿佛相互产生似的。……在这种装饰图案的组合变化中,可以感觉到艺术想象力的异常自由和轻灵,而且这种自由使人感觉到是一种快活的、几近嬉笑的随心所欲。”[2]38巴赫金在《拉伯雷研究》中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思想,他不但批评了凯泽尔关于怪诞世界“总的阴暗、恐怖和可怕的音调”,主要的是“某种敌对的、陌生的和非人的东西”,“就是变得陌生的世界”[2]56等观念,而且从怪诞与民间诙谐文化、狂欢化话语的紧密联系出发,认为怪诞可以从笑的角度来理解,但怪诞的笑具有双重性:“它既是欢乐的、兴奋的,同时也是讥笑的、冷嘲热讽的,它既否定又肯定,既埋葬又再生。”[2]14巴赫金还强调,怪诞并不恐怖,在那种只是一味强调恐惧因素的怪诞观里,“诙谐的欢快、解放和再生的因素,即创造的因素不见了”[2]60。而且,在怪诞世界中我们总能感觉到思想和想象的“快活的自由”。怪诞的基础是诙谐因素和狂欢节世界的感受,它不但能打破现存秩序的严肃性和一切对超时间价值以及对必然性的追求,“解放人的意识、思想和想象”[2]58,给我们提供一个自由追求的想象空间,而且给我们指出了超越现实世界的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怪诞“揭示的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另一种世界秩序、另一种生活制度的可能性。它超越现存世界虚幻的(虚假的)唯一性、不可争议性、不可动摇性”[2]57。在这种怪诞的世界中,洋溢着一种欢快的、解放的、再生的、向可能和无限无穷开放的自由创造的精神。
怪诞的狂欢与创造说给怪诞赋予了一种明朗、欢快的色调,使它具有了丰富的感情色彩和人情味,让我们感到怪诞不但不阴森可怖,而且轻松、亲切、自由。
四、怪诞的社会成因:陌生与异化
德国早期浪漫派理论家弗·施莱格尔认为,怪诞的基本成分主要包括:不同种属的因素的混合、混乱、幻想,甚至是“世界在某种程度上的异化”,还有对世界通常的秩序和现成制度的打破,而怪诞险恶恐怖的一面揭示了“存在”最深处的奥妙[1]46。
德国艺术理论家凯泽尔指出,在怪诞艺术光怪陆离的表层下,蕴涵着独特的结构模式,即怪诞是由滑稽可笑与丑恶恐怖两种因素组成的。但在这两者中,他更强调的是怪诞的恐怖因素,他认为怪诞乃是我们面对疏离、异化的生活世界时所产生的一种陌生感和恐惧感。“我们之所以感到震惊和恐惧是因为我们的世界已变得不可靠,我们不可能生存在这个面目全非的世界里。怪诞所倾注的毋宁说是对死亡的恐惧,还不如说是对生活的恐惧”[1]196。在对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文学艺术中怪诞现象的广泛考察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凯泽尔指出:“怪诞是异化的世界。”[1]195凯泽尔还指出:“潜藏和埋伏在我们的世界里的黑暗势力使世界异化,给人们带来绝望和恐怖。尽管如此,真正的艺术描绘暗中产生了解放的效果。黑幕揭开了,凶恶的魔鬼暴露了,不可理解的势力受到了挑战。就这样,我们完成了对怪诞的最后解释:一种唤出并克服世界中的凶恶性质的尝试。”[1]199这就是凯泽尔关于怪诞的最后定义。这个怪诞的定义从研究怪诞艺术给人带来恐怖和绝望的心理反映中,挖掘出怪诞艺术背后隐含的广阔的社会生活的本质,反映了凯泽尔怪诞观的深刻性。在20世纪这个充满黑暗和异化的世界中,只有这种独特的怪诞艺术才能达到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把握,我们正需要怪诞艺术来揭示和批判这种异化的世界,以引起人们对它的警惕、批判和超越。在这种怪诞对异化的揭示中,我们不仅更清晰地理解了这种恐怖和异化的生活,而且好像超越了它,在精神上获得了一种解放的快感,从而达到对异化的克服。
20世纪法国结构主义文论家托多洛夫在《论恐怖类型中的怪诞》中指出,怪诞的核心是:“在这个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真切的世界上,我们知道,没有魔鬼、气精、吸血鬼;但是,这里所发生的事件也不能用这个我们熟悉的世界中的法则去解释清楚。经验到这一事件的人必须从两个可能的结论中选择其一:在一个有规律运行的世界上,它是一个感受幻觉的欺骗,一种想象性的结果;或者,这一事件确实发生了,它本就是现实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这一现实是由一种我们所不知道的规律控制着的。无论魔鬼是一种幻觉,一种想象性存在,还是确实存在着,犹如其他生命存在一样的真切,在这一预定中,我们会偶尔地与之相遇。……在这种不确定的持续中,怪诞占据了我们。一旦我们选择了这种或那种回答,我们就给怪诞留下了一个相似的类型:离奇或惊异。怪诞就是这样一个人体验到的犹豫,他只知道自然法则,却遭遇到一种超自然的事件。”[17]155卡斯达克斯在其《法国怪诞》中写道:“当一种神秘的东西粗暴地插进现实生命的环境中……就构成了怪诞的特征。”[17]156路易斯·范克斯在其《怪诞文学之艺术》中说:“一般而言,怪诞叙述把人写成与我们相似,生活在现实的世界里,却突然遭遇到不可解释之事。”[17]156罗根·卡罗斯在其《怪诞教程》中说:“怪诞总是对现实秩序的一种打破,是对不变的日常法则的异常侵入。”[17]156以上这些理论家的主张比较接近,都认为怪诞产生于我们对异化世界的陌生感受,具有离奇性、神秘性、不可解释性、超自然性等特征。
综上可见,西方学者论述怪诞的侧重点各不相同,大体上涉及到了怪诞的各个方面,我们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怪诞的审美形态是奇怪和反常,以古罗马学者维特鲁威、贺拉斯和德国理性主义美学家黑格尔为主要代表;第二,怪诞的审美心理是恐怖与滑稽的统一体,以法国学者雨果为主要代表;第三,怪诞的审美功能是狂欢与创造,以苏联学者巴赫金为主要代表;第四,怪诞的成因是陌生与异化,以德国学者凯泽尔为主要代表。总体上看,随着历史的进步和艺术实践的发展,人们对怪诞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从反感、谴责到逐渐接受、理解甚至欣赏、追求。这既是怪诞艺术在整个艺术大家庭中不断发展壮大的结果,也反映出人类的审美观念在不断走向宽容和开放。尽管我们看到,不同的理论家对怪诞的理解具有较大的差异性,有的观点甚至是对立的,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寻绎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我们发现,西方学者所论及的怪诞主要有以下几种构成方式:第一,以迷狂的想象混淆不同领域的事物的界限,将人、植物、动物不加区别地拼凑组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非理性超自然的怪诞形象;第二,通过极度的夸张创造出超现实的怪诞形象;第三,通过极端的扭曲和大胆的变形创造出怪诞的形象;第四,通过功能的增加和数量的重复来创造怪诞的形象。
[1] 沃尔夫冈·凯泽尔.美人和野兽——文学艺术中的怪诞[M].曾忠禄,等,译.西安:华岳文艺出版社,1987.
[2]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六卷[M].李兆林,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3] 姚一苇.美的范畴论[M].台北:台湾开明书店,1997.
[4] 鲍桑葵.美学史[M].张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5] 雨果.克伦威尔·序[M]//论文学.柳鸣九,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6] 维特鲁威.建筑十书[M].高履泰,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
[7] 贺拉斯.诗艺[M].杨周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8] 温克尔曼.希腊人的艺术[M].邵大箴,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9] 蒋孔阳.德国古典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0] 康德.论优美感和崇高感[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11] 黑格尔.美学:第二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12] 贡布里希.秩序感——装饰艺术的心理学研究[M].范景中,等,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
[13] 简·布洛克.原始艺术哲学[M].沈波,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14] 菲利普·汤姆森.论怪诞[M].孙乃修,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92.
[15] 乔治·桑塔耶纳.美感——美学大纲[M].缪灵珠,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16] Susan Corey.Toward the Limits of Mystery:The Grotesque in Toni Morrison’s Beloved[M]//The Aesthetics of Toni Morrison:Speaking the Unspeakable.Edited by Marc C.Conner,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2000.
[17] 张法.美学读本[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