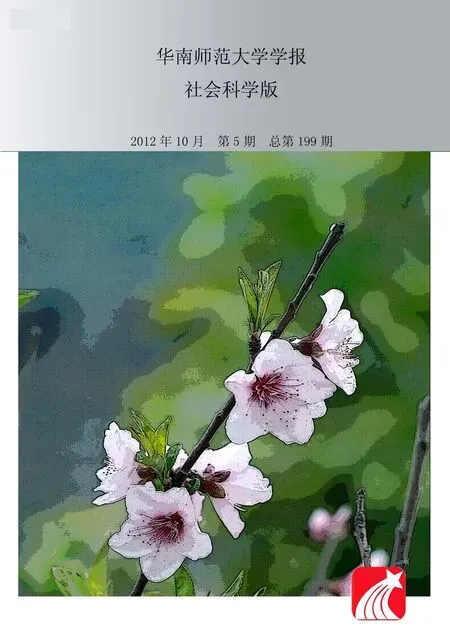论中国古代文章学中的“反言”笔法
余祖坤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中国古代文章学非常讲究文章的寓意深刻、层次丰富,讲究表达的委婉曲折、层出不穷,以千变万化、神鬼莫测为文章的最高境界,最忌平铺直叙、一览无余。所以,中国古代文章作家往往通过虚实、宾主、顺逆、开阖、正反等艺术辩证法的巧妙搭配,尽量避免直话直说和浅白平弱;高明的作家,甚至有意隐藏自己的真实意旨,刻意营造一种隐微曲折的效果。正如清代文章理论家王又朴所说:“昔人作文,主意惟恐人易知,今人作文,主意惟恐人不知,此古人文字所以绝非后人所能及者也。”①(清)王又朴:《史记七篇读法》卷一,第14页,清乾隆诗礼堂刻本。在中国古代的隐微写作中,“反言”是一种比较重要的笔法。
一、“反言”笔法的内涵
韩愈之文,如神龙出没,穷极文章之变。他的有些文章,如《送石处士序》、《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意蕴奥渺,其主旨是褒是讽,曾使人们产生了截然相反的理解。②霍松林:《韩文阐释献疑》,载《文学遗产》2000年第1期。误解产生的原因之一,是读者忽视了这样一点:韩愈之文,好以反言见意。这是晚清古文理论家吴铤明确提出来的:“退之好以反言见意:樊绍述文最坚涩,而退之以为文从字顺;郑权在南海,积珍宝以遗朝士,而退之以为贵而能贫,为仁者不富之效。”③(清)吴铤:《文翼》卷二,第14页,道光十六年刊本。那么,究竟何谓“反言”呢?先看吴铤所举的两个例子。樊宗师之文以僻涩著称,而韩愈却在《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中称赞他的文章“文从字顺”④(唐)韩愈:《韩昌黎文集注释》卷七,第290页,阎琦校注,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对此,李淦指出:“铭谓‘文从事顺,各识职则’,宗师之文不从、字不顺者多矣,亦微有不满意。”⑤(元)李淦:《文章精义》,见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2册,第1172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在《送郑尚书序》中,韩愈称郑权家属有百人之多,没有足够的住所,以至不得不租房居住,“可谓贵而能贫,为仁者不富之效也”⑥《韩昌黎文集注释》卷四,第432页。。而据《旧唐书》记载,郑权以家人数多,俸入不足,于是通过宦官疏通关节,出任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到任后,肆意积聚财货,贿赂宦官,“大为朝市所嗤”⑦(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六二,第13册,第4246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所以朱熹在《昌黎先生集考异》中指出郑权多姬妾、性豪奢,而韩愈之所以称他“贵而能贫”,乃是讥刺之语。⑧(宋)朱熹:《昌黎先生集考异》卷六,第1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从吴铤所举之例来看,所谓“反言”,就是指文章不以正面、明确、肯定的方式表达思想或情感,而是以说反话的方式进行隐藏和暗示的一种隐微笔法。
“反言”是韩愈非常擅长的一种笔法。除了吴铤所举二例之外,《送董邵南序》也是比较突出的一个例子。董邵南很有才华,且中了进士,但在京城一再碰壁,不得已,于是打算投奔河北藩镇。而在中唐时期,藩镇拥兵割据的形势对中央政权构成了严重威胁,削弱了中央政权的威信和统治;韩愈一贯主张维护国家的大一统,反对藩镇的割据局面。所以韩愈此文,表面上句句是送别之语,实则句句有挽留之意。“反言”笔法的运用,使文章产生了含而不露、耐人寻味的韵致。
《进学解》也是韩愈运用“反言”笔法的一篇杰作。该文由作者与假想的学生之间的往复问答组成。文章以说反话的方式含蓄地批判了当权者埋没人才,用人不公,抒发了自己长期不受重用、反而遭受贬斥的愤懑之情。比如:“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拔去凶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盖有幸而获选,孰云多而不扬?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①《韩昌黎文集注释》卷一,第66页。这表面上是赞颂当权者唯才是举,公正无私,实则是明褒暗贬,反话正说。下文中对孟子和荀子的一番评论,则又转为正话反说。孟子和荀子无疑是历史上的两位大儒。韩愈表面上是说孟子和荀子不合时宜,不符合当权者的用人标准,因而导致了悲剧命运,实则是明贬暗褒,暗含了对两位大儒人生际遇的同情以及对当权者是非不分、用人不公的愤慨。
从以上所举例文可以看出,“反言”笔法,有反话正说和正话反说两种表现形态。所谓反话正说,就是以肯定的语句暗示否定的观点和态度;正话反说,则是指以否定的语句暗示肯定的观点和态度。
那么,“反言”何以能够“见意”?从“反言”的表层意义来看,它必定蕴含着一个假判断。假判断是不能表达人们对客观事物情况的断定的,但在特定语境的作用下,这个假判断被转换成为真判断,从而能够有效地表达对客观事物的观点和态度。由此可见,特定语境是“反言”笔法的一个核心要素。离开特定的语境,“反言”笔法是不可能奏效的。“反言”笔法之所以成立的语境是丰富多样的,其中最普遍的一种,是中国古代伦理型、政治型的文化特点。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对伦理和礼仪的强调,人们在不同对象面前或者在不同场合之中,都必须有其相应的言说方式。这样,在不便直言的情况下,“反言”的表达方式也就应运而生了。除文化传统的原因外,作家的思想个性、作品的创作背景、作品内部的深层结构以及作品与作品之间的互文关系等,也都是“反言”笔法的生成条件。在中国古代的文章创作中,有些作品运用“反言”的笔法十分隐微,要敏锐地捕捉它,必须全面和准确把握其之所以成立的特定语境。
“反言”笔法与现代修辞学中的“反语”很接近,有时很难分别;但从总体上说,二者还是有较大的差异。反语一般运用在语句的修辞中,意思相对较为明朗,读者通过上下文即能理解其正面之意。比如林黛玉对贾宝玉说:“真真你就是我命中的天魔星。”②(清)曹雪芹、高鹗:《红楼梦》第十九回,第27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天魔星”一看就知是反语。而“反言”笔法则具有更大的隐蔽性,往往要在文本的整个结构设置、甚至是文本之外的特定语境中才能体现出来。换言之,反语是一种局部的修辞手法,而“反言”笔法则涉及整篇文章的立意构思和结构安排。反语的表达目的,是为了获得幽默、滑稽或讽刺的效果,而“反言”笔法则是为了使文章产生更加新奇、更加隐微、更加深邃的境界。
另外,“反言”笔法与古代文章批评中的“反笔”概念也有不同。那么何谓“反笔”呢?清人何家琪举例说,在《史记·李斯列传》的论赞中,“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一句,就运用了反笔。③(清)何家琪:《古文方》,见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6册,第6047页。可见,反笔的逻辑是先正面陈述,再以否定句式说反面情形。“无正不切实,无反不醒豁。”④陈仲星:《作文指南》卷一,第1册,第3页,民国二十三年中华书局铅印本。正反结合,目的是从正反两个方面将一个意思说得深透。反笔与正言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关系。“反言”笔法则往往无须通过正言,而是通过说反话来隐藏、暗示真实的思想和感情。
二、“反言”笔法的历史考察
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反言”笔法至少在春秋时期就已出现。由于中国史学自《春秋》开始就形成了暗寓褒贬、惩恶劝善的传统,所以在史传文学中,“反言”笔法比较常见。
比如,《左传·隐公元年》描述郑庄公对其兄弟的步步退让,表面上显示了他的宽宏大度,实则暗示了他的阴险和老谋深算。文中说:“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①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册,第15、76页,中华书局1990年版。这表面是赞庄公之孝,实则是借颍考叔之孝反衬郑庄公之不孝,是典型的“反言”笔法。
又如《隐公十一年》记载,是年七月,郑庄公与鲁隐公、齐僖公联合伐许,结果很快占领许国都城,许庄公逃往卫国。之后,郑庄公说了一番冠冕堂皇的话掩饰自己的侵略行为,仿佛郑国攻入许国是为了拯救许国百姓。接着文章评论道:“郑庄公于是乎有礼。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许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也。”然而文章马上笔锋陡转,批评他既无德政又无威刑:“郑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鸡,以诅射颍考叔者。君子谓:‘郑庄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即无德政,又无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诅之,将何益矣!’”②杨伯 峻:《春 秋左 传注 》, 第1册 ,第15、76页 ,中 华书 局1990年版。这一褒一贬,前后变化何其之快!实际上,《左传》称赞郑庄公“知礼”,是以“反言”的笔法反话正说,借以讽刺他的贪婪和伪善。正如《左绣》所指出的,《左传》“有虚美实刺之法,如郑庄贪许,方才赞他知礼,即刻便讥其失政刑,有此一刺,连美处都认真不得”③(清)李骅、陆浩辑:《左绣·读左巵言》,见《四库f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141册,第140页,齐鲁书社1997年版。。
秦汉时期,由于专制集权的建立和强化,臣子向君主的上书或讽谏之辞,为了避免冒犯君权,往往采用“反言”的方法。李斯的《狱中上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篇文章是李斯遭赵高陷害而被下狱之后给秦二世的上书。文章表面上是历数自己的七大罪状,而这七宗“罪”实则无一不是自己为秦王朝立下的的赫赫功勋:“胁韩弱魏,破燕、赵,夷齐、楚,卒兼六国,虏其王,立秦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广,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见秦之强,罪二矣”④(秦)李斯:《狱中上书》,见(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册,第23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等等,皆为正话反说,其目的是以一种卑恭可怜的语气,乞求秦二世的同情和赦免。
《史记》中“反言”笔法的例子就更多了。《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隐然以孔子修《春秋》作为自己修史的楷模。而壶遂诘问道:“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⑤(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三○,第10册,第3299、3299-3230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司马迁为了回避时忌,故意先把汉朝的功德颂扬了一番,继而说:“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⑥(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三○,第10册,第3299、3299-3230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这显然是情非得已的反话,而这恰恰透露了司马迁内心的雄伟抱负,其欲吐还吞、曲折迂回的语言,令人叫绝。再如《秦楚之际月表序》,文章开头就感叹,自陈涉起义、项羽灭秦,到汉高祖平定海内,“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⑦《史记》卷一六,第3册,第759、760页。。这似乎在歌颂刘邦的盖世功勋。然而紧接着,文章以浓墨重彩,极力强调前代的圣明之世,如虞、夏、汤、武等,无不是经过数十年乃至几代人的修行仁义,最后者才继承大统的。其言外之意无非是说:在短暂时间内继承大统的刘邦,不是通过修行仁义实现统一的;刘邦不是一位仁义之君。既然如此,那为何偏偏是他统一了天下呢?对此,作者感叹道:“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⑧《史记》卷一六,第3册 ,第759、760页。这表面上是在歌颂刘邦是“大圣”,并称其之所以统一天下乃是顺应了天命,但实际上这只不过是司马迁在专制强权的压力下,出于万般无奈而发出的言不由衷的赞叹。“反言”的笔法将作者的真实意图掩藏起来,使文章如云中之龙,虽只显露一麟半爪,但更见其神奇莫测之姿。又如《外戚世家》记载,汉武帝晚年欲立少子,于是杀了少子之母钩弋夫人。接着文中写道:“诸为武帝生子者,无男女,其母无不遣死,岂可谓非贤圣哉!昭然远见,为后世计虑,固非浅闻愚儒之所及也。谥为‘武’,岂虚哉!”⑨《史记》卷四九,第6册,第1986页。这表面是极力赞美汉武帝的深谋远虑,实则也是反话,是对汉武帝残酷无情的辛辣讽刺。此类例子在《史记》中还有很多,《万石张叔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酷吏列传》、《滑稽列传》等,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反言”的笔法,收到了明褒暗贬的效果。
《汉书》中也不乏“反言”的笔法。如《武帝纪》的论赞说:“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①(汉)班固:《汉书》卷六,第1册,第212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评价之高,可以说无以复加。但实际上,武帝朝一改前朝休养生息之策,以致于外则战争频仍,内则骨肉相残,海内凋耗,几至大乱。班固在文中不厌其烦地罗列灾异和人祸、记载战争和叛乱,表明他内心对武帝是有批评意味的;而他在赞语中称武帝“不改文景之恭俭”,乃是违背事实的反话正说。因为班固所载武帝的任何事迹,都与“恭俭”二字沾不上边。一个作家如果故意犯下常识性错误,那么他肯定是别有用意的。正如凌稚隆所言:“此赞率多褒语,而其所不满于帝者,都包括于‘不改文景之恭俭’一句,微婉委曲,深得史臣之体。”②(明)凌稚隆辑:《汉书评林》卷六,第30页,光绪辛卯刻本。文中所有关于天灾、星象和祸乱的繁琐记载,原来都是为了与“不改文景之恭俭”一句形成反照。这就像高手下棋,看似不经意的一着,却顿时使全局皆活。
《史记》、《汉书》之后,“反言”一直是中国古代文章创作中的一种独特笔法。当作者为了避开某种忌讳或者为了达到讽刺的目的时,“反言”笔法就成了他们的一种明智选择。比如《全唐文》卷四三二所载仆固怀恩的《陈情书》中,“臣实不欺天地,不负神明,夙夜三思,臣罪有六”③(唐)仆固怀恩:《陈情书》,见(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四三二,第5册,第4396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云云,明为认罪,实为表功,其“反言”的笔法,与李斯《狱中上书》如出一辙。
再如,据新旧《唐书》记载,“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仓皇逃到蜀地。太子李亨在玄宗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即皇帝位,是为肃宗。后来二京收复后,玄宗回朝,李亨恐玄宗生变收回皇权,于是对其父长期实行武力监控。对此,颜真卿在其《天下放生池碑铭并序》中进行了委婉的讽谏:“迎上皇于西蜀,申子道于中京。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问安视膳,不改家人之礼。”④(唐)颜真卿:《颜鲁公集》卷四,第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肃宗擅自即位,并对其父玄宗实行武力监控,哪有什么孝道可言?哪有什么“家人之礼”?颜真卿之所以表面赞颂肃宗之孝,其实是以“反言”这一隐微笔法对肃宗进行旁敲侧击。
晚唐小品作家罗隐,擅长讽刺,其《书马嵬驿》一文也巧妙地运用了“反言”的笔法。文中写道:“夫水旱兵革,天之数也,必出圣人之代,以其上渎社稷,下困黎民,非圣人不足以当其数。故尧之水、汤之旱,而玄宗也革焉。”⑤(唐)罗隐:《罗隐集校注》,第460页,潘慧惠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作者表面上是说,“安史之乱”与尧舜时期的水灾和旱灾一样,都是天数运行的结果;而这些灾害,往往出现在圣人的时代,因为“非圣人不足以当其数”。如果读者稍不留意,一定会以为这是一篇为玄宗荒淫误国而辩解开脱的翻案文章。实际上,这篇短文通过“反言”的笔法,对玄宗的荒淫误国进行了十分隐蔽的讽刺。这比直接、正面的谴责更加具有批判的力量和讽刺的意味。
又如欧阳修《与荆南乐秀才书》,表面上是奉劝乐秀才顺时以取荣誉于当世,但其弦外之音却是极力主张摆脱时俗,卓然自立。清人王元启评论此文时说:“欧公措辞微婉,不作伉直语,较为可味,而读者竟至无可捉摸,率意妄评,则亦良可悯矣。”⑥(清)王元启:《读欧记疑》卷二,第21页,湖北省图书馆馆藏刻本。
由于中国古代文章浩如烟海,所以“反言”笔法的例子恐怕是难以穷尽的。这就需要读者格外留心,不要为作者的反言所迷惑,否则就会得出与作者本意完全相反的理解。
明清时期,文章评点的风气十分兴盛。“反言”在明清的文章批评中经由批评家的反复运用,逐步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文章学概念。只不过有人称“反言”,有人称“反言见义”,有人称“反言见意”,其实含义是一致的。比如,《汉书·万石君传》中有“内史坐车中自如,固当”⑦《汉书》卷四六,第2196页。一句,顾炎武指出说:“反言之也,言贵而骄大,当如此乎!”⑧(清)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二四,下册,第1539页,黄汝成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韩愈《送陆歙州诗序》一文中说:“先一州而后天下,岂吾君与吾相之心哉?”⑨《韩昌黎文集注释》卷四,第346页。何焯指出:“按权文公《送陆公佐序》,当日似以直道不为时宰所容者,此言‘岂吾君吾相之心哉’,反言之也。”[10](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三二,中册,第562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方苞在《书淮阴侯列传后》一文的《自记》中说:“后论似果以信为叛逆者,盖其诬于传具之矣,故反言以见义,谓天下已集,非可以叛逆之时矣。若果谋此,虽族诛亦宜,然以信之智,而肯出此乎?”①(清)方苞:《望溪集》卷二,见《四库全书》,第1326册,第74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四库馆臣在《魏书》的提要中说:
收(引者案:指魏收)以是书为世诟厉,号为“秽史”。今以收传考之,如云:“收受尔朱荣子金,故减其恶。”其实荣之凶悖,收未尝不书于册。至论中所云:“若修德义之风,则韩、彭、伊、霍,夫何足数。”反言见意,正史家之微词。②(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五,上册,第407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到了道光年间,吴铤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将“反言”作为一个固定的术语,运用到自己的文章批评中,提出了“退之好以反言见意”的论断,标志着“反言”成为一个固定的文章笔法概念。当代学者钱锺书也曾使用过“反言”概念。他在《管锥编》中说:
李斯乃从狱中上书:“臣为丞相,治民三十馀年矣。……卒兼六国,虏其王,立秦为天子,罪一矣”云云,《考证》:“凌稚隆曰:‘按李斯所谓七罪,乃自侈其极忠,反言以激二世耳’”。按《滑稽列传》褚先生补郭舍人为汉武帝大乳母缓颊,“疾言骂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壮矣,宁尚须汝乳而活耶?尚何还顾?’”亦“反言以激”也。《全唐文》卷四三二仆固怀恩《陈情书》:“臣实不欺天也,不负神明,夙夜三思,臣罪有六”云云,全师李斯此书,假认罪以表功,所谓“反言”也。③钱锺书:《管锥编》,第1册,第536页,三联书店2008年版。
钱锺书在罗列例子之后的总结是:“所谓‘反言’也。”这明显表明他将“反言”视为一个专门的概念。而且,《管锥编》将“反言”作为一个小标题,更清楚地表明钱锺书是将“反言”作为一种专门的笔法来进行观照的。
通过上文的考察,可见“反言”(或称“反言见意”)概念是从中国古代的文章创作中抽象出来的,是在明清以降的文章批评中逐渐成形的。它既符合古代文章创作的实际,又具有较强的概括性,因此将它作为一个固定的文章笔法概念,是合情理的。
三、“反言”笔法的文化渊源
从文化渊源上来说,“反言”笔法与中国史书修撰中的“春秋书法”有很紧密的关联,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古人崇尚迂回的言说方式。
“春秋书法”原指《春秋》在记载史事中的书写原则和书写方式。根据《孟子》和《史记》的记载,孔子面对世道衰微、礼乐崩坏的社会现实,于是在鲁国旧史的基础上删改修订,著成《春秋》。《春秋》在记载史事时,通过一定的书写原则和方式,暗示了孔子对当时政治和伦理的评判,同时也寄托了他的政治理想和伦理观念。《左传》最早总结了《春秋》的书写特色:“《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④(周)左丘明传:《春秋左传正义》卷二七《成公十四年》,第765页,(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这表明,隐晦曲折、婉而成章的笔法是“春秋书法”的一个重要表现。“春秋书法”在中国古代的著述中产生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形成了一个悠久的传统。其中,“反言”笔法作为一种隐晦曲折的表达手法,成为古代史学修撰和文章创作中经常运用的一种笔法。《史记》作为一部杰出史学巨著和文学经典,继承和发扬了“春秋书法”,将“反言”的笔法运用得更加奇妙莫测。在《淮阴侯列传》的论赞部分,司马迁表面上说韩信谋反、罪有应得,而他在正文中却以大量笔墨详细记载了韩信的忠诚之举和知恩图报的品性,实际上是句句在说韩信未反,而且根本不可能反。司马迁曾被汉武帝残酷地施以宫刑,身心遭到了极度的摧残,人格受到了极大的污辱,因此他在揭露和批判汉统治者时,不得不避开专制政权的淫威,采取“反言”的笔法,隐晦曲折地表达他内心深处的不满和抨击。可见,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专制威逼和政治迫害是“春秋书法”得以长期盛行的外部原因,也是“反言”这种特殊笔法生成和存在的一个历史原因。面对专制威逼和政治迫害,古代作家往往通过“反言”的笔法,曲折隐微地表达内心的愤激不平。柳宗元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在被贬之后的文章,如《乞巧文》、《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入道序》、《与萧翰林俛书》等,都或多或少地运用了“反言”的笔法。
当然,专制政治不是全部的原因。中国古人偏好迂回曲折的言说方式,也是“反言”笔法的一个生成机制。法国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在其《迂回与进入》一书中,对中国古人偏好迂回曲折的言说方式进行了专门的论证。他指出:“中国表达法的本质(也是中国文章的特点)就是通过迂回保持言语‘从容委曲’:以与所指对象保持隐喻的距离的方式。”①[法]弗朗索瓦·于连:《迂回与进入》,第37页,杜小真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反言”笔法正是一条追求迂回的有效方式,古代作家在无法直言或者为了追求更加丰富的言外之意时,往往会采用“反言”的笔法。比如,黎、安二生是两位青年才俊,善古文,因乡人讥其迂阔,所以请曾巩作文为之辩驳。曾巩于是写下了著名的《赠黎安二生序》。文章表面说自己十分迂阔,只知志于古道,不知合乎时俗,然而实际用意,却是在勉励黎、安二生为文应当志于古道,不要流于时俗,更不必计较世俗的讥评。曾巩此文之妙,关键在于“反言”的笔法,使文章产生了含蓄委婉、意在言外的韵味。
四、“反言”笔法的表达效果
“反言”笔法通过反话正说或正话反说的形式,借助“言”与“意”之间的对立和张力,可以使文章产生陌生化、含蓄化和反讽的艺术效果。
(一)陌生化
任何文章的创作,都要遵循一定的形式逻辑和情感逻辑。一般来讲,形式逻辑属于理性思维,它所包含的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要求意思具有明确性和一贯性,不能模糊不清,更不能前后矛盾。但在文章创作中,如果情感逻辑与形式逻辑完全重合,那么文章的意味必然是确定的、直白的,不能使读者产生新奇的感受。相反,如果情感逻辑摆脱形式逻辑的束缚,超出人们思维的固定规律,那么文章的情感必然获得更加丰富、更加新奇的效果。这正是文章增强审美内涵的一个奥妙。接受美学的理论家姚斯指出,期待视野与作品间的距离,决定着文学作品的艺术特性。②[德]姚斯:《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见[德]H.R.姚斯、[美]R.C.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第 31页,周宁、金元浦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如果文章完全符合读者的期待视野,表明它的内容和形式流于陈旧的俗套;而只有打破读者的期待视野,才能出奇制胜,提升文章的新颖性、感染力和审美价值。
“反言”笔法使情感的表达超越了形式逻辑的一般思维规律,打破了读者的期待视野,增强了理解的难度,拉长了理解的时间长度,从而使文章产生陌生化的艺术效果。韩愈以继承孟子道统为己任,其应举求官的道路却十分坎坷;艰难进入仕途之后,又屡遭贬黜。《进学解》就是他在被贬为国子博士时所写的。在他经历种种坎坷和打击之后,心中难免愤愤不平。按照正常的形式逻辑来推,以韩愈刚毅果决的个性,他心中的不平,理应表现为对当权者的猛烈批判。然而事实上,他在文中摇身变为一个温文尔雅、安时处顺的国子先生,对当权者不仅没有批判,相反却大唱颂歌;不但没有发泄怨气,反而表示心满意足。这些都违反了形式逻辑的固定思维,从而使文章产生了鲜明的陌生化效果。
不过,“反言”笔法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是适用和有效的,而必须在它确实能丰富文章的内涵和深度、提升文章的陌生化程度时,才是必要的、有效的、新颖的。《文心雕龙·定势》篇曾指出:“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驭奇;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势流不反,则文体遂弊。”③(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义证》中册,第1139-1140页,詹瑛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在文章创作中,如果正说就能有效地达到很好的效果,就不应当刻意“反言”,文章不能脱离创作的规律而一味炫异争奇。反意见意的笔法,必须以确实能提升文章的陌生化程度、丰富文章的内涵为前提条件。
(二)含蓄化
中国古代的言说方式具有很强的暗示性和曲折性,因此,含而不露是古典文章的一种理想境界。刘大櫆说:“文贵远,远必含蓄。或句上有句,或句下有句,或句中有句,或句外有句,说出者少,不说出者多,乃可谓之远。”④(清)刘大櫆:《论文偶记》,第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反言”笔法由于采取正话反说或反话正说的方式,避免了直话直说和平铺直叙,从而使文章产生隐微曲折、含而不露的艺术效果。那些运用“反言”笔法的古文之所以容易被人所误解,就是因为“反言”笔法的运用,使文章的微情妙旨具有了很强的隐蔽性。比如汉武帝不惜劳民伤财,打算派兵通西南夷。司马相如于是写下著名的《难蜀父老》。文章借蜀中长老的责难之辞,引出了一大段回护和颂扬武帝的话。李兆洛认为此文“意虽寓规,实则颂也”⑤(清)李兆洛选辑:《骈体文钞》卷三,第56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然而事实上,文中假托蜀中长老的批评之词,就是作者自己的真实立场。至于文中大段冠冕堂皇的辩解和颂词,读者千万认真不得,那是为了顾及君臣大体而说的套话和反话。
(三)反讽效果
所谓“反讽”,就是指“语境对于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①[美]克林思·布鲁克斯:《反讽——一种结构原则》,见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第33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清)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见(明)施耐庵:《金圣叹批评本水浒传》,第10页,(清)金圣叹批评、陆林校点,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通俗地说,就是指在一定的语境下,一个表达的实际内涵与它的表面意义恰恰相反。“反言”笔法在特定的语境之下,有意通过反话正说或正话反说的方式,使文章的所言和所指之间形成尖锐的对立和巨大的张力,从而使文章产生强烈的反讽效果。“言”与“意”之间的张力越大,反讽的效果就越强。
《史记·淮阴侯列传》是一篇寓意深刻的传记。司马迁在论赞中说:“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②《史记》卷九二,第8册,第2630页。这段话了无痕迹地运用了“反言”笔法,不易被人察觉。司马迁表面上表达了对韩信的批评和惋惜,实际上通过巧妙剪裁事件和精心安排文本的结构,暗示了韩信根本没有反意的真相。王又朴指出,韩信的将才及其对天下大势的洞幽烛微,在当时实无有出其右者。“乃武涉说之,蒯通复说之,信不于此时反,迨天下已集,乃谋叛逆耶?是以于武涉、蒯通两段,皆备述无遗,而于赞内点明此意,曰‘不亦宜乎’,盖反言之耳。”③(清)王又朴:《史记七篇读法》卷二,第32-33、33-34页,清乾隆诗礼堂刻本。这就是说,在楚汉相争的过程中,以韩信之才,他完全可以拥兵自立,与项羽、刘邦成鼎足之势,但他没有这样做;而且当武涉、蒯通劝其叛汉时,他也没有动摇。既然韩信在手握重兵、刘邦势力尚弱或战事失利时都没有反叛,那么他怎么可能在协助刘邦统一天下之后谋反呢?王又朴还进一步指出:“前叙信寄食南昌亭长、漂母饭信及受辱于少年诸琐事。后叙信之相报,一一详写,不少遗者,正为信不反汉作证。见信一饭尚报,况遇我厚之汉王乎?以少年之辱己,尚不报其怨,又岂以汉王之厚己,反肯背其恩乎?此亦史公之微意也。”④(清)王 又朴:《 史记 七篇 读法 》 卷二 ,第32-33、33-34页, 清乾 隆诗 礼堂 刻本 。按照一般的解读模式来看,《史记》中的琐事和细节,都是为了刻画历史人物的鲜明性格,将人物写活。这样理解是有道理的,但还没有切中要害。王又朴却别具慧眼,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细节背后的微言大义。
司马迁为韩信功高盖世、却被无辜杀害的遭遇,感到深深的同情和不平,对高祖、吕后的刻薄寡恩、阴险毒辣感到极端愤慨。但在汉王朝残暴的统治之下,他无法直言,故而采取正话反说的方式:一方面在论赞中假装批评韩信居功自傲、反叛朝廷;一方面,却又在正文中细针密线地记叙韩信种种不反的事实。二者之间构成强烈的反讽,深刻揭示和讽刺了汉王朝的残暴无道,同时也暗含了作者对自身所受污辱的强烈控诉。他对韩信的“批判”越是郑重其事,其反讽的意味不是越强烈吗?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在“反言”的字里行间,司马迁隐藏着多么深刻的思想、多么沉郁的情感!何寄澎说得好:“‘文本’的研究,除了透过‘史料’推敲、掌握真相之外;‘文本’本身遣辞造句的精细解读也是‘发现’作者真意的重要途径——尤其中国史书撰写,自《春秋》以下即有‘曲笔’此一‘书法’传统在,后世读者更宜用心斟酌。”⑤何寄澎:《〈汉书〉李陵书写的深层意涵》,载《文学遗产》2010年第1期。
总之,在特定的语境下,“反言”笔法以其所产生的陌生化、含蓄化和反讽的艺术效果,有助于避免平铺直叙,有助于增强文章的审美意蕴和情感内涵的深度,有助于增强文章耐人寻味的韵致。
五、“反言”笔法的价值
自现代学术产生以来,关于古代文章的研究,就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薄弱环节,远不能与诗词、小说、戏曲等文类的研究相比。造成古代文章学研究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五四”以来,文学界和学术界割断了几千年的古代文章传统,将古代文章学中的概念、范畴、命题、理念几乎全盘抛弃,导致了今人对古代文章学的隔膜;加之缺乏一套有效的批评话语,最终导致研究只能停留在内容复述、主旨概括和风格判断的模式中,而不能深入剖析文章的形式技巧和结构肌理。今人对于一篇古文的阐释,大多先说:本文通过什么、表达了什么、揭示了什么,或者说抒发了什么样的情感,之后再加上一些似是而非的价值判断,比如“主旨明确”、“中心突出”、“叙事生动”、“形象鲜明”、“语言流畅”,等等。在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课堂上,如果就一篇古文的写作特点向学生提问,其问答一定不会超出这样一套思维模式。这套归纳模式,着眼点是文章的主旨大意,其突出弊端是遮蔽和遗漏了具体的行文技法。金圣叹曾说:“吾最恨人家子弟,凡遇读书,都不理会文字,只记得若干事迹,便算读过一部书了。”①[美]克林思·布鲁克斯:《反讽——一种结构原则》,见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第33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清)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见(明)施耐庵:《金圣叹批评本水浒传》,第10页,(清)金圣叹批评、陆林校点,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如果研究者对文章肌理本身没有透彻的理解,那么他对文章主旨和内容的理解也一定会产生偏差。“反言”笔法,难道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改变单纯注重归纳的方法,加强文本本身的细读,是今后古代文章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而为了进行有效的文本细读,首先必须要有一套批评的话语。所以,为了推进中国古代文章学的深入研究,当务之急是从中国古代文章作品和文话、评点等著作中,提炼、总结出中国古代文章学的范畴、概念、命题等,并对之进行深入阐释,明确其理论内涵,从而沟通古今,消除今人的隔膜,激发其理论活力,最终建构起一套切实可行的古代文章的批评话语体系。
“反言”这一概念,准确概括了中国古代文章创作中的一个悠久而又独特的笔法,简明精炼,富有理论概括力;而且事实上,明清以来的一些文章批评家在各自的批评活动中已经使用了这一概念。既然如此,那么当代学者完全可以使其成为中国古代文章批评话语中的一个概念,完全可以借用它来观照古代文章的创作。明确“反言”笔法的理论内涵、文化渊源及其蕴含的审美原则,有利于研究者透过“反言”的迷雾,准确把握文章的言外之意,对于深入细致的文本分析,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意义。
虽然当代散文创作所运用的白话与古代文言存在较大差异,但只要是运用汉语进行思维和交流,那么中华民族的根本审美原则就不会改变。当代作家必须摒弃那种强行将古与今、传统与现代进行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事实上,中国古代文章学中的一些创作理念和创作方法对当代散文的创作具有很大的借鉴价值。“反言”作为一种古文笔法,其反常合道的立意取向、含蓄隐微的审美原则、言此意彼的表达方式,对当代散文作家避免立意的直白和行文的平铺直叙,都具有丰富的启发意义。刘大櫆说:“文字只求千百世后一人两人知得,不求并世之人人人知得。”②(清)刘大櫆:《论文偶记》,第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这句话,应当引起当代散文作家的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