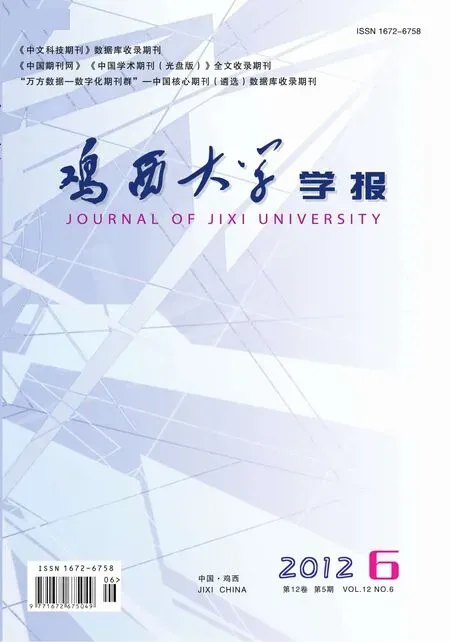论大化改新之前日本与朝鲜半岛的关系
潘 颖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论大化改新之前日本与朝鲜半岛的关系
潘 颖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大化改新之前,日本处于奴隶社会。此时,朝鲜半岛有三个国家,分别是高句丽、新罗、百济。日本与朝鲜半岛国家的交往,既有冲突又有往来。日朝的交往对日本、朝鲜半岛及中国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日朝在交往过程中伴随着任那的问题,而任那问题又影响着日朝的交往。
日朝关系;古代日本;高句丽;新罗;百济;任那
大化改新发生于645年,是日本①一次重要的社会政治改革运动。此次改新促进了国家统一,并形成了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国家。是日本进入封建社会的起点。笔者选择大化改新这一拐点,旨在探讨处于奴隶社会的日本与朝鲜半岛国家之间的关系。各国学者在研究日朝关系史时,视角各有不同,有从日本的角度出发,也有从朝鲜半岛的角度出发。笔者将站在日本的视角上,讨论它与朝鲜半岛的关系问题。
到目前为止,日朝关系史的研究虽是一个较大的命题,但是这方面的专著和论文比较少。专著有汪高鑫的《东亚三国古代关系史》等;论文有金锦子的《五至七世纪中叶朝鲜半岛三国纷争与东北亚政局》、李婷的《流入日本的百济、高句丽移民研究》、崔山玉的《试论六至七世纪中叶百济与倭关系》、金在善的《好太王碑文研究》、熊义民的《公元四至七世纪东北亚政治关系史研究》等等。笔者将从《日本书纪》《三国史记》《三国遗事》等史料中抽丝剥茧,探寻在大化改新之前日本和朝鲜半岛国家的关系。
一 背景条件
日本是位于亚洲大陆东岸外的太平洋岛国,是呈弧形的列岛。领土由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四大岛和3900多个小岛组成。日本在统一之前,岛上有众多的小国。其中最大的是大和国家,是位于日本大和(今奈良县)的地方古国。该国于公元3世纪形成,4世纪前半期其势力已达关东地方,中央政权通称“大和朝廷”。
朝鲜半岛在古代有三个并存的国家,分别是高句丽、新罗、百济,这一三国并立的时代史称“三国时代”。此前朝鲜半岛上出现过古朝鲜、魏满朝鲜、马韩、辰韩、卞韩等几个国家。《三国遗事》记载,“崔致远云:马韩,丽也;辰韩,罗也”;“致远云:卞韩,百济也”。在三国时代之前没有朝鲜半岛与日本交往的记载。本文主要阐述处于三国时代的朝鲜半岛与大化改新之前的日本的关系。
二 日朝关系
1.与新罗既有冲突又有友好往来。
(1)冲突与战争。
《三国史记》中关于日本与新罗交往的记载有很多,其中有一些是军事冲突。赫居世居西干②11年,“倭人行兵,欲犯边,闻始祖有神德,乃还。”③是关于日罗交往的首次记载。《三国史记》中的记载多带有神话色彩,大概是新罗的始祖军事才能很优秀,使倭人非常恐惧,倭人才退兵。《三国史记》中关于日罗关系的记载大多是倭人入侵新罗,后被新罗人逐出。从公元前47年到公元500年,涉及日本和新罗军事冲突的记载就有29条。其中也有反映新罗人战略智慧的,如奈勿尼师今④三十八年,“夏五月,倭人来围金城,五日不解,将士皆请出战,王曰:‘今贼弃舟深入,在于死地,锋不可当’。乃闭城门,贼无功而退,王先遣勇骑二百,遮其旧路,又遣歩卒一千,追于独山,夹击大败之,杀获其众”。③
日本一直对新罗虎视眈眈。新罗为了抵御日本的侵略,遂于“开元十年任戌十月,始筑关门于毛火郡,今毛火村,属庆州东南境,乃防日本塞垣也。”⑤日本王文庆听说新罗有万波息笛,“以金五十两,遣使请其笛。”⑤新罗婉言拒绝,文庆再次遣使,欲以一千两黄金换万波息笛,“寡人愿得见神物而还之矣”。元圣大王金敬信因得到祖传的万波息笛,“厚荷天恩,其德远辉”,所以日本想得到此笛,以此达到吞并新罗的目的。这反映了日本对新罗的野心。
(2)和平往来。
日罗除了军事冲突以外,还有和平的往来。其中派遣使者的情况比较多。如阿达罗尼师今二十年,“夏五月,倭女王卑弥呼遣使来聘”,基临尼师今三年,“春正月,与倭国交聘”。③另外还有请婚和派遣人质的记载。讫解尼师今三年,“春三月,倭国王遣使,为子求婚,以阿急利女送之。”不过也有拒绝请婚的时候。讫解尼师今三十五年,“春二月,倭国遣使请婚,辞以女既出嫁”。接下来便发生了一件事。讫解尼师今三十六年,“二月,倭王移书绝交”。或许是因为新罗王没有答应联姻,倭国就“移书绝交”。看来,日本与新罗联姻,是维护两国外交关系的一种重要方式。实圣尼师今元年,“三月,与倭国通好,以奈勿王子未斯欣为质”。以派遣王子为人质的方式,表明倭国比新罗强大,大概是新罗为了寻求保护,才这样做的。《三国史记》中还有倭人供职于新罗朝廷的记录。“瓠公者,未详其族姓,本倭人,初以瓠系腰,渡海而来,故称瓠公”。赫居世居西干三十八年,“遣瓠公聘于马韩”。瓠公的工作相当于外交官。瓠公面对马韩王的质疑,回应“我国自二圣肇兴,人事修,天时和,仓庚充实,人民敬让,自辰韩遗民,以至卞韩、乐浪、倭人,无不畏怀,而吾王谦虚,遣下臣,修聘,可谓过于礼矣,而大王赫怒,劫之以兵,是何意耶”。③从瓠公的工作和上述话语,可看出新罗的地位较高,能让倭人畏怀。并且日罗关系友好,竟然让瓠公从事外交事务。虽是个例,但日罗关系可见一斑。
《三国遗事》中有几篇记述了新罗与日本的交往。虽然其中有一些是具有神话色彩的传说,但能从侧面反映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延乌郎,细乌女》中,延乌和细乌都能乘岩“负归日本”。两人去了日本被立为王和贵妃,“是时新罗日月无光,日者奏云:‘日月之精,降在我国,今去日本,故致斯坚。’王遣使求二人。延乌曰:‘我到此国,天使然也。今何归乎?虽然,朕之妃有所织细绡,以此祭天可矣。’仍赐其绡。使人来奏,以其言而祭之,然后日月如旧。”⑤这个故事曲折地反映了新罗与日本的关系。太阳、月亮都是文明的象征。亚洲大陆的先进文化,大多都是通过古代朝鲜再传入日本的。
新罗曾以向日本朝贡的方式来维持两国的关系。《隋书·倭国传》提到“新罗、百济皆以倭为大国,多珍物,并敬仰之,恒通使往来。”⑥新罗或因为寻求日本的保护与支持,或因为惧怕日本的势力,向日本朝贡。神功皇后四十七年夏四月,新罗遣使来朝,皇太后和太子誉田别尊非常欢喜,群臣都潸然泪下。并且新罗带来了很多珍异的贡物。由此反映出一个重要的事实:新罗和日本都非常重视和对方的关系。日本书纪中也记载了“新罗不朝”的情况,如仁德天皇“五十三年,新罗不朝贡”。⑦日本因为新罗不朝贡,就派兵袭击新罗。“六十三年,新罗不朝,即年,谴袭津彦击新罗”。⑦
此外,还有新罗人归化的情况。“(垂仁天皇)三年春三月,新罗王子天日枪来归焉,来将物:羽太玉一个,足高玉一个,鹈鹿鹿赤石玉一个,出石小刀一口,出石桙一枝,日镜一面,熊神篱一具,总七物,则藏于但马国,常为神物也。”⑧又“闻日本国又圣皇,则以己国授弟知古而归化之。仍贡献物:叶细珠,足高珠,鹈鹿鹿赤石珠,出石刀子,出石枪,日镜,熊神篱,胆狭浅大刀,并八物。”天日枪娶但马出岛人太耳女麻多乌,在日本繁衍生息。很多人像天日枪这样移民日本,在日本定居,被称作“归化人”或“渡来人”。这些渡来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技术移民,为日本的生产活动作出了很多的贡献。“大和朝廷给予了他们‘氏’的身份,并赠与土地。据9世纪的《新撰姓氏录》记载,在1182个氏中,有373个氏(30%)是‘渡来人’的氏”。⑨《日本书纪》应神天皇纪记载,“廿八年……新罗王……乃遣能臣者,是猪名部等之始祖也。”⑩猪名部是从事木工的手工业奴隶集团。雄略天皇时,从新罗来了一个叫猪名部真根的木匠,雄略天皇任命他为猪名部的伴造,让他建楼阁。他使用中国式的规矩和准绳,把中国的建筑技术带到了日本。所以新罗又是向日本传播中华文明的中介。
2.与高句丽既有冲突又有友好往来。
(1)和平往来。
645年之前,高句丽本纪中没有与倭交往的记载,高句丽关于与日本的交往的记载仅见于高句丽的广开土王碑上。或许是因为高句丽不重视与日本交往。但笔者认为高句丽与日本交往不密切的原因是高句丽和日本距离较远。因为高句丽位于朝鲜半岛的北部,而西南部是百济,东南部是新罗。地理位置成为高句丽和日本交往的障碍。
吴廷璆在他写的《日本史》中提到:推古天皇二十六年八月一日,高句丽遣使于日;并且,《日本书纪》中也提到应神天皇五十八年“冬十月,吴国、高丽国,一并(到日本)朝贡”。⑦如果《日本书纪》中记载属实,那么笔者认为朝鲜半岛国家(特指高句丽、新罗、百济)与日本之间存在着朝贡体系。
高句丽对日本获得先进的技术和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例如,高句丽僧昙徵去了日本,制作出彩色和纸墨,使日本的绘画技术获得了很大进步。《岩波讲座》提到高句丽是中国北朝文化传入日本的重要媒介。“钦明天皇四十年,高句丽向日本派遣使者,日本和大陆之间结成的新的文化输入圈开通了。”有一段时期,日本和高句丽的关系比较友好。钦明天皇三十一年,高句丽遣使到倭,钦明天皇竟下诏“宣于山城国相乐郡起馆净治,厚相资养。”同两次扣留新罗使的行为截然相反,日本厚待高句丽君臣。招待异国君臣本来是涉外机构和负责礼仪的机构负责的。很明显,日本对改善两国关系寄予厚望,而高句丽国王对送他们回国的地位卑微的难波船人“以厚礼礼之”,同样看出高句丽也希望改善两国关系。
为日本的改革作出杰出贡献的圣德太子,他的老师就是慧慈。推古天皇三年(595)五月“高丽僧慧慈归化,则皇太子师之”推古三年,“此两僧(指慧慈和慧聪)弘演佛教,并为三宝之栋梁。”⑨并且于推古天皇四年冬十一月“法兴寺造竟,则以大臣善德臣拜寺司。是日慧慈、慧聪二僧始住于法兴寺。”⑨日本的考古学者发现法兴寺的伽蓝布局同位于平壤清岩里的高句丽时代的废寺有以八角塔为中心的相同布局。有学者认为,法兴寺的伽蓝布局有可能受到高句丽的影响。⑨当时的高句丽采取了“亲倭”的政策,因而两国关系比较友好。
(2)冲突与战争。
更引人注目的不是两国的友好交往,而是两国的战争。297年在遣使日本时,高句丽称“高丽王教日本国也”,应神天皇的太子菟道稚郎子厌恶高句丽咄咄逼人的态度,“怒之,责高丽之使,以表状无礼,则破其表”。⑦因此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高句丽没有向日本遣使。391年,日本与高句丽战,结果“高句丽大胜,大和国联军败退”。高句丽与日本的战争描述多见于414年建立的广开土王碑上。从碑文上可以看出当时日本向朝鲜半岛扩张势力,但高句丽的广开土王击败了日本的入侵,并驱逐了大和国在半岛的势力。因为碑文残破及被后人篡改,存在一些有争议的地方。“以六年丙申,王躬率水师讨百残国”高句丽攻打百济的原因尚且不明。一说是,百济和新罗是高句丽的属国,一直以来朝贡。但日本在391年侵略百济和新罗,逼迫百济和新罗成为自己的臣民。高句丽出于对自己利益的考虑,才攻打百济。或许是因为百济王勾结日本,作出对高句丽不利的事。百济王被围困,“献出男女生白(即生口)一千人,细布千匝。归王自誓:从今以后,永为奴客”。⑧但这个誓并没有维持多久。“九年己亥,百残违誓,与倭和通”。⑧而新罗称,“倭人满其国境,溃破城池,以奴客为民,归王请命”。高句丽答应新罗的请兵。于400年,“遣步骑五万,教往救新罗。从男居城,至新罗城,倭满其中。官兵方至,倭贼退。”日本并没有就此罢休。“十四年甲辰,倭不轨,侵入带方界。”高句丽再次出兵,才使得“倭寇溃败,杀无数。”雄略天皇二十三年(479年),日本“筑紫安致臣,马饲臣等,率船师以击高句丽。”高句丽和日本之间既有和平的往来,又有战争。总体来看交往不怎么密切。
3.与百济的关系亲密。
与高句丽相比,百济与日本的交往比较频繁。高句丽是朝鲜半岛上的霸主,新罗国力强大,百济略显弱小。五到七世纪中叶朝鲜半岛上三国纷争不断。百济为了和其它两国抗衡,遂与日本结盟。日本为了保有其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即任那加罗),因此和百济密切往来。
佛教就是从百济传入日本的。佛教是传入日本最早的宗教。钦明天皇十三年(552)冬十月,百济圣明王遣西部姬氏达率怒唎斯致契等,献释迦佛金铜像一躯,幡盖若干,经论若干卷。并称“此法能生无量无边福德果报,乃至成辨无上菩提”。⑧苏我大臣稻目宿弥支持崇佛,但物部大连尾舆和中臣连镰子称“我国家之王天下着,恒以天地社稷百八十神,春夏秋冬祭拜为事。方今改拜蕃神,恐致国神之怒。”⑧最终, 天皇答应引进佛教。有学者认为佛教进入日本后,立即展开崇佛废佛之争,中间夹杂着政治的较量。但坂本太郎认为佛教刚传来时,立即产生强烈的敌对意识,采取了排斥和打击的态度,并非事实。
百济不仅向日本传入了佛教,还传入一些文化和技术移民。百济人味摩之给日本带来了吴的伎乐舞,伎乐后来在寺院举行法会时演奏,有些伎乐用的面具一直延续至今。应神天皇十六年(285),五经博士王仁从百济至日本,献《论语》10卷和《千字文》1卷。之后,太子菟道稚郎子拜他为师,学习中国典籍。《岩波讲座》提到,《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在五世纪末记录了百济的技术民集中渡来的情况。《日本书纪》卷十记载,应神天皇十四年春二月,百济王贡缝衣工女,叫做真毛津,是来目衣缝的始祖。敏达六年(577)11月,百济向倭晋献了律师、禅师、比丘尼、咒禁师、造寺工六人。崇峻天皇元年(588)为营造法兴寺,百济向倭晋献了寺工、炉盘博士、瓦博士、画工等。因为日本得到百济的协助,法兴寺的建造于当年开始,历时八年建成。法兴寺用的瓦是是轩丸瓦,上有莲花图案,同百济都城扶余出土的瓦类似,从侧面证明法兴寺的建造有百济瓦工的参与。
日济以联姻的方式维系两国关系。《百济新撰》中记载,“己巳年,盖卤王立,天皇遣阿礼奴跪来索女郎。百济妆饰慕尼夫人女,曰适稽女郎,贡进于天皇”,应神天皇三十九年春二月,百济直支王派遣他的妹妹新齐都媛来归,并带来七个妇女。这说明日本和百济以联姻的方式加强两国的友好往来。
两国还经常互遣使节。《百济本纪》记载,阿莘王(402)五月,“遣使倭国求大珠”。“二十二年,春二月,倭国使者至,王迎劳之,特厚”。百济支王五年(409),“倭国遣使,送夜明珠,王优礼待之”。“十四年,夏,遣使倭国,送白绵十匹”。毗有王二年(428),“倭国使至,从者五十人”。③《百济本纪》中所有关于百济和倭的交往的记载全都是遣使,没有任何冲突。645年,百济遣王子翘岐入倭,延续了两国间传统的王族外交。《日本书纪》也曾多次记载百济派遣使者到日本。例如,神功皇后五十年春三月,“百济王遣亦久氏朝贡”。这些都可以看出百济和日本关系密切,且友好。
笔者认为当时百济是小国,需要依附于日本,获取日本的保护。有一件事说明百济恐惧日本的势力。应神天皇四十一年春三月,纪角宿弥被派遣到百济。当时,百济王的族酒君无礼。纪角宿弥竟然因此呵斥百济王,更惊讶的是百济王居然感到非常惊恐,用铁锁把族酒君绑起来,最后天皇赦免其罪行,此事才告结束。
在与高句丽的战争中,百济也依附日本参与其中。此外,当雄略天皇听说百济被高句丽所破,“以久麻那利赐汶州王,救兴其国。”百济还多次向日本请兵。544年,百济欲夺洛东江时,提出“吾欲据此修缮六城,谨请天皇三千兵士,每城充以五百”。钦明天皇十五年(554)正月,日本应百济的要求支援百济“军数一千,马一百匹,船卅只”。类似这样请兵的记载,多见于史料,由此可以得知,百济和日本是军事伙伴的关系,当然,这种关系并不是平等的。
百济个人因素也给日本带来一些变化。 百济僧观勒向日本传播了历法,并向大友村主高聪等传授天文地理知识、遁甲(一种占星术)和方术。推古天皇因一僧侣斧砍自己的祖父,要对非行的僧尼科刑,但观勒反对。于是推古天皇仿效朝鲜和中国的做法,建立僧正僧都制(即寺院自治),并命令观勒对寺院巡察。在各个方面,百济和日本都关系紧密,并且百济对日本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
4.任那问题。
(1)日本通过其在任那的机构间接控制半岛南部。
任那位于朝鲜半岛南部,距离日本最近,是加罗诸小国的统称。广开土王碑、《宋书》、《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文献上多次出现“任那”字样。《日本书纪》中首次出现“任那”的记载是崇神天皇六十五年秋七月,“任那国派遣苏那曷叱知朝贡。任那离筑紫国有二千余里。阻隔北海,在鸡林的西南”。⑦鸡林是新罗的国号。
日本学者关晃认为任那的正确称呼为“任那加罗”。任那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吴廷璆在《日本史》中称,“4世纪60年代大和朝廷出兵朝鲜……征服弁韩之地(庆尚南道),建立任那地方,设‘日本府’统治之”。日本学者多称存在“任那日本府”。《岩波讲座》中多次提到“任那日本府”。末松保和的《任那兴亡史》中也有相同的提法。日本学者的这种定论被认为是“皇国史观”,尤其受到韩朝两国学者的批判。全昌淑专门撰文《“任那日本府”真相——驳日本新历史教科书“任那据点说”》,抨击这种“皇国史观”。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学者金锡亨主张任那是朝鲜半岛三国移民集团在日本列岛上建立的分国。关于任那的争议颇多。日朝两国学者在第二期朝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上从学术角度正式取消了日本在古代统治朝鲜半岛南部的“任那日本府说”。
争议的源头之一就是高句丽时的广开土王碑。其中辛卯年条最有争议。在此列举周云台本,“百残新罗旧是属民由来朝贡而倭以辛卯年来渡海破百残□□□罗以为臣民”。学者们对“而倭”、“海”、“ □□□”所在位置内容的不同理解,造成了主张的不同。金在善在其文《好太王碑文研究》中认为,此段文字应理解为“百残新罗旧是属民由来朝贡亦叛以辛卯年来渡海破百残十城新罗以为臣民”。并认为倭只不过是高句丽征服百济、新罗的副次对象,而不是主角。因为有关倭的记事间断出现,而且又是退、追或是灭的对象。而高句丽对邻国的称呼各有不同。其他学者认为此段文字的主语不是高句丽,而是倭。因此对碑文的理解又有不同。
关于任那的地位。《日本书纪》称任那是日本的屯仓,是日本的官家(即附属国)。例如,钦明天皇下诏讨伐新罗时说,“新罗,西羌小丑,逆天无状,违我恩义,破我官家,毒害我黎民。”但朝鲜学者否认曾经存在“任那屯仓”和“任那官家”。《日本书纪》中还有“任那国司”的记载。雄略天皇七年(463),天皇任命吉备上道臣田狭为“任那国司”。说明任那有日本的势力。笔者认为日本不是直接统治任那,而是间接控制了这个地方。《岩波讲座》中有任那王向新罗、百济请兵的记载,说明任那是存在任那王的。钦明天皇五年(544)春正月“百济遣使召任那执事和日本府执事”。由此看出,任那和日本府不是一回事,不存在任那日本府。都是执事,应该互不统属。“召”字表明,任那的地位低于百济。任那的机构只是日本在朝鲜半岛南部处理与朝鲜半岛利益关系的机构。钦明天皇五年(544)二月,百济王要求“汝日本府卿、任那旱歧等,各宜发使,共我使人往听天皇所宣之诏”。这有命令的语气,为什么不是天皇直接召见日本府和任那的使者,或许任那有被百济管理的可能。
(2)任那问题牵涉多国势力。
此后,百济请求割让任那四县(在全罗南道西南部),大连大伴金村接受了百济的贿赂,就同意了此事。因为中间涉及到新罗的利益,新罗的势力就逐渐渗透到任那。532年,任那的一国金官国的国王金仇亥投降了新罗。钦明天皇二十三年(562),伽耶投降了新罗,标志着任那的灭亡。任那的灭亡宣告了日本在朝鲜半岛势力的消失。皇极天皇元年(642),百济从新罗手里夺去任那旧地的大半,改新政府第一次默认了新罗、百济侵略任那的事实。以“任那调”的名义在百济课税。此前,日本对被夺去任那一事愤愤不平。钦明天皇三十二年(571)三月,“遣坂田耳子郎君使与新罗,问任那灭由”。敏达天皇四年(575)二月“百济遣使进调,多益恒岁,天皇以新罗未建任那,诏皇子与大臣曰:‘莫懒懈于任那之事。’”591年8月,天皇召群臣说:“朕思欲建任那,卿等何如?”群臣奏言:“可建任那官家,皆同陛下所召”。“领二万余军,出居筑紫,遣吉士金于新罗,遣吉士木莲子于任那,问任那事。”推古朝为恢复在任那的势力,于600年和602年两次发兵新罗,“新罗与任那相攻,天皇欲救任那。”结果接连失败,只好作罢。
三 日朝关系变迁的原因分析
大化改新之前,日本视野中的外国只有中国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日本与朝鲜半岛开始互有往来。为了达到自己的利益,日朝双方既有军事冲突又有和平往来。朝鲜半岛三个国家:高句丽、新罗、百济,实力不平等。所以日本在交往中采取了不同的对策。百济在三国之中实力最弱,为与高句丽、新罗抗衡,则依附于日本,以此来获得日本的保护。“百济王与日本使节同坐于磐石上,发誓永称西藩,朝贡日本”。双方几乎没有矛盾。日本为扩大在朝鲜半岛的势力,不断向朝鲜半岛渗透,在半岛南部的任那建立机构,以此间接控制半岛南部,并与半岛上的三国角逐。日本觊觎新罗和高句丽的领土,多次入侵高句丽和新罗。奈解尼师今十三年“夏四月,倭人犯境,遣伊伐利音,将兵拒之”。③儒礼尼师今四年“夏四月,倭人袭一礼郡,纵火烧之,掳人一千而去”③等等。于是日本与高句丽、新罗屡次发生军事上的交锋。在战争之外,伴随着日朝之间的友好往来。
四 历史影响
1.对日本的影响。
(1)文化影响。
日朝关系对日本的影响有一些是文化上的影响。当时日本把从外国传来的音乐统称为“雅乐”,掌管雅乐的机构叫做雅乐寮。雅乐受到上层社会的欢迎,并用于宴会及寺院的法会。雅乐寮里面有高丽乐师、百济乐师、新罗乐师、舞师、伎乐师等。朝鲜半岛三国的音乐传到日本,颇受欢迎。“631年,倭与唐朝因‘高表仁争礼’事件而断绝来往,半岛国家就成为倭吸收先进文化的唯一途径”。朝鲜向日本传入的文化改变了日本人的文化,“于百济求得佛经,始有文字”。②
(2)经济影响。
从朝鲜传入的技术、劳动力、生产工具提高了日本的生产力水平。石刀和蛤刃石斧是朝鲜原有的农具,后传入日本。传入日本的陶瓷器以朝鲜陶瓷器为最多。日本主要依靠从朝鲜南部进口的铁材。日本须惠器和朝鲜的新罗烧相似,制法大致相同。须惠器大概来源于新罗烧。
日本与亚洲大陆联系的必经之地是朝鲜半岛。从朝鲜半岛到对马海峡的路线,对日本的影响最大,同时是大陆移民进入日本的主要路线。到日本的朝鲜移民中的一些人成为日本的官吏,为日本成为律令制国家奠定了基础。而且,日本的外交事务也由一些朝鲜移民来完成。
朝鲜移民中大多数是体力劳动者。“是岁,新罗人朝贡,则劳于役(指修茨田堤)”。还有,钦明天皇十七年,“冬十月,遣苏我大臣稻目宿弥等于倭国高市郡置韩人(指百济人)大身仓,高丽人小身狭屯仓,经国置海部屯仓”。而且,日本的部民中有很多朝鲜移民。他们为日本的繁荣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3)军事影响。
朝鲜半岛对日本的军事影响也很突出。高句丽、新罗、百济军事力量增强,日本为保存在朝鲜半岛南部既存的势力,遂派遣倭军向朝鲜半岛渗透,并扶植在南部的日本势力。在任那被新罗吞并后,日本失去了朝鲜方面的物质、技术、劳动来源。对日本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
2.对朝鲜半岛的影响。
(1)社会生活影响。
在朝鲜半岛发现了日本特有的前方后圆坟,并大量出土了日本产的翡翠制勾玉,表明当时在朝鲜半岛有大量的日本移民。朝鲜和日本的生活习性、服饰、饮食也有很多相同的地方,说明日朝的往来对朝鲜半岛的社会生活产生了一定影响。
(2)军事影响。
在朝鲜半岛三国时代,岛上三个国家纷争不断。再者有日本势力的渗入,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复杂。
“369年,应百济之请向半岛出兵,征讨新罗,平定了洛东江沿岸七国,西灭济州岛交给百济”。改变了百济的版图。为了自身利益,百济和日本结盟。但新罗和日本的关系不稳定。由于日本与百济的盟友关系,百济和新罗的关系一直紧张,争夺任那也使得济罗关系恶化。日本曾联合百济向朝鲜半岛扩张势力,百济与倭的联合对高句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但到好太王时,高句丽打败了倭济联军,百济也随之遭受重创。高句丽援助新罗驱逐了日本的入侵,使新罗依附于自己,成了半岛的霸主。百济和日本在伽耶的势力阻碍新罗在这一地区的扩张,导致罗济关系不协调。475年,高句丽趁日本在半岛势力衰退,攻陷百济首都汉城,百济被迫迁都熊津。日本因无力继续统治半岛南部,不得不答应百济索取任那四县的要求。百济最后得到了任那四县,扩张了势力。日本向半岛渗透势力的过程中,影响了三国之间的关系,并影响了半岛各国势力的此消彼长。
3.对中国的影响。
日朝关系对中国的对外交往影响较大。中国作为东亚文化圈的轴心,在东亚各国中有一定的权威。日本多次要求中国任命其王为“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⑥欲借中国的权威君临各国。中国不仅在与其他国家的朝贡等交往中扩大自己的影响,日本的这种做法也扩大了中国在东亚的影响。
日朝之间的通道是维系中日交流的桥梁。日朝交往密切,逐渐形成了文化交流的通道。中国文化、技术、劳动力也通过这个通道向东亚各国传播,扩大了中国的影响力。中国的稻作、冶炼术就是通过朝鲜传入日本的。5世纪,中国的医学、天文、历法也通过朝鲜人传入日本。623年惠日回国与632年唐朝派遣高表仁出使日本都是取道新罗。当时新罗和日本关系密切,中国人才能经过新罗到达日本,否则到达之日遥遥无期,有诸多不便和风险。因此,日朝关系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也影响中国与东亚各国的交流。
注释
①笔者题目中的“日本”指的是日本列岛,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日本。日本到大化时正式决定国号为日本,在此之前统称为倭国。在本文中,“日本”与“倭”通用.
②居西干,辰焉王,或云呼贵人之称。据[高丽] 金富轼,三国史记,[韩]乙酉文化社,1997:1.
③ [高丽] 金富轼,三国史记,[韩]乙酉文化社,1997:1,23,20,2,151,15,19
④尼师今,方言也,谓齿理。昔南解将死,谓男儒理,婿脱解曰:“吾死后,汝朴、昔二姓,年长而嗣位焉。”其后,金姓亦兴,三姓以齿长相嗣,称尼师今。据《三国史记》第4页。
⑤ [高丽] 一然,三国遗事,岳麓书社,2009:121,130,53.
⑥戴逸主编,简体字本二十六史·隋书,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1203.
⑦舎人親王,日本書記,東京:岩波書店,1994:268,506,272,214,304.
⑧王辑五选译,一六〇〇年以前的日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8,9,13.
⑨冯玮,日本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46-27,57.
⑩转引自李婷,流入日本的百济、高句丽遗民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8.
[1]舎人親王,日本書記[M].東京:岩波書店,1994.
[2]家永三郎,等.岩波講座[M].東京:岩波書店,1967.
[3]John Whitney Hall etc,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
[4] [日]坂本太郎,日本史[M].汪向荣,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5] [高丽] 金富轼.三国史记[M]. [韩]乙酉文化社,1997.
[6] [高丽] 一然,三国遗事[M]. [中]陈蒲清,[韩]权锡焕,译.长沙:岳麓书社,2009.
[7]吴廷璆,日本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
[8]戴逸.简体字本二十六史[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9]王辑五,选译.一六〇〇年以前的日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10]冯玮.日本通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
[11]朱旻暾.高句丽与日本的交往[J]. 社会科学战线,1995,5.
[12]熊义民.公元四至七世纪东北亚政治关系史研究[D].暨南大学, 2003.
[13]金锦子.五至七世纪中叶朝鲜半岛三国纷争与东北亚政局[D].延边大学,2007.
[14]崔山玉.试论六至七世纪中叶百济与倭关系[D].延边大学,2006.
[15]王明星.日本古代文化的朝鲜渊源[J]. 日本问题研究,1996,3.
[16]金在善.好太王碑文研究[J]. 宜宾学院学报,2003,2.
[17]李婷.流入日本的百济、高句丽遗民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08.
ClassNo.:K313.21DocumentMark:A
(责任编辑:郑英玲)
OnRelationshipBetweenJapanandKoreanPeninsulaBeforetheTaikaReform
Pan Ying
Japan has been in the slave society before Taika Reform. At that time, there are three countrie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y are Goguryeo, Baekje and Silla. Japan have had not only contacted with those countries but some conflicts . Exchanges between Japan and Korean countries had influenced on Japan, Korea and China. The rel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Korea was influenced by with Mimana and the Mimana problem has had impa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apan and Korea.
relationship between Japan and Korean peninsula;ancient Japan;Goguryeo;Silla;Baekje;Mimana
潘颖,硕士,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1672-6758(2012)06-0144-5
K313.21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