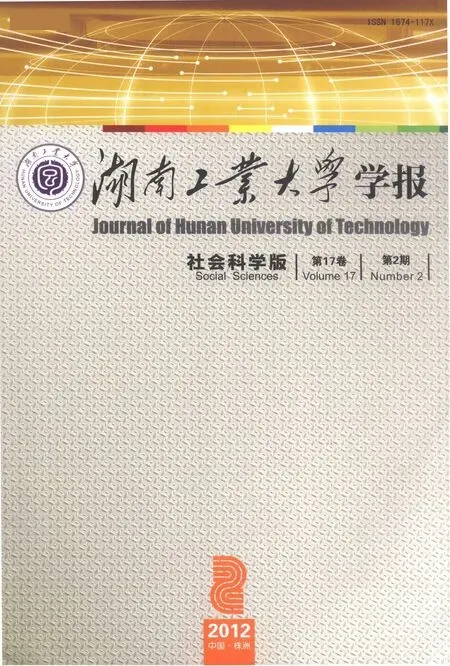施虐受虐循环中的悲剧女性
——苏童小说女性人物心理探析*
王钟屏
(宜宾广播电视大学,四川宜宾644002)
施虐受虐循环中的悲剧女性
——苏童小说女性人物心理探析*
王钟屏
(宜宾广播电视大学,四川宜宾644002)
苏童小说中的众多女性形象,饱受男权文化制度的压榨,其心理普遍带有强烈的社会受虐倾向,但在受虐的过程中,为了寻找精神平衡,其心理又具有强烈的施虐冲动。在施虐受虐的循环中,她们反复演绎着女性作为第二性的人性悲剧。
苏童小说;女性形象;父权制;施虐;受虐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提到“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1]有压迫的出现就有权力运作的空间。“几千年来,男权社会使女性长期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附属地位,身上压抑的枷锁越来越沉重。女性甚至成为男性赏玩的“物品”和“生产”的工具,被异化为非人,成为有价值的物。”[2]男权社会要求女人永远是男人身上的肋骨,永远依附于男人。苏童笔下的女人无论是《妇女生活》中的娴、芝、萧,《另一种妇女生活》中的杭素玉,简家姐妹,还是《红粉》中的秋仪和小萼,《妻妾成群》中的太太姨太太,面对男人的时候,永远是处于弱者和依附的一方,似乎女人的命运都是被男人安排的,男人既是女人痛苦的根源,又是女人的救星,而女人永远处于被动的、弱小的,需要扶持的一方,甘愿将自己的命运,交由别人主宰,将女性个体的未来寄托在男人身上。在苏童的笔下,描写的都是一个个日常生活中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女人,但是在这些“平凡”女人身上依然可以发现社会受虐倾向,而施虐的一方已经是“环境”、是“制度”,所有人都在这样的处境中生存并受着不同的残酷压榨,无法逃离。在看似个人悲剧的背后,无一不是由那些世俗的文化、社会的制度,周围的环境起着加剧作用。
一 男权文化的压榨
在苏童笔下,每一个女人都是一种悲剧,每一种悲剧就是一个女人的结局。而悲剧表面上都是由于或明或暗的男人而起,但实际上无一不是男权文化在背后起推动作用。在《红粉》中,秋仪和小萼虽然是被男性玩弄的妓女,是一件性商品,但是她们内心并不忌讳这样的身份,甚至乐于如此,当新身份(女工)到来的时候,她们害怕和抵触,拼命地抗拒。秋仪不惜性命从车上跳下,第一个去的地方是妓院,第一个要投靠的人是老主顾。然而她的生活并没有走回到过去,在被社会(妓院被勒令关门)、被男人(老浦)遗弃的时候,她依然不愿意接受新身份。最后因为自己的妓女身份,连出家都不行。没有了容身之所,她只好回家,开始她鄙夷家庭的寒酸,不愿回家,但却发现家里也因为她的身份不接受她。万般无奈下,将自己交给一个鸡胸驼背的男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婚姻是她得到供养的唯一方式,也是证明她生存之正当性的唯一理由。”[3]而小萼虽然接受了劳动改造,接受了女工的身份,却没有放下自己做妓女时候的心态。在一系列的展转当中,终于因为自己的拜金主义,害死了丈夫,最后为了跟另一个男人生活,遗弃了自己的孩子。
作品表面上描绘了一对被金钱腐蚀,贪图安逸,自甘堕落的女人应有的悲剧,但事实上,悲剧不是她们个人造成的,而是男权制度的产物。小萼的一句话道出了事实的真谛“我就不相信男人会不喜欢逛窑子。把我们撵散了,这世界就干净了吗?”的确,如果没有男人想要购买性商品,性交易就不会存在。在男人不断的寻找与购买中,这些本来出生贫寒的女子,在自己一无所长,无处安身,又不得不生存的时候,只能依靠出卖自己仅有的肉体了。然而这样的行为,既得不到男人的理解和真爱,连女人对她们也是一惯的鄙夷,不仅是正经家庭的女人(浦太太)、经历过革命的女干部、吃过苦的旧时代女工,就是自己的亲人(姑妈)、老板(老鸨),甚至讲求“众生平等”的佛门中人(尼姑庵里的尼姑)也瞧不起妓女这种职业。在她们眼中,妓女都是些好逸恶劳的寄生虫,是身体肮脏、道德败坏、品行低劣的女人,对女性这个群体来说是一种耻辱的象征,尤其是那些连改造都改不好的妓女,仿佛天生贱命,命该没有好下场。但实际上,让她们脱离了这个社会,只能以出卖肉体作为职业的根源,却正是这个男权社会本身。正如小萼,在她爹死之前,有两个女人依附在他的身上,但是他爹一死,娘攀附了别人,改了嫁,小萼也只能依靠出卖自己的肉体,继续依附在男人身上存活。对小萼而言,是男人让她如此悲惨,但是离开男人她又无法活在这个世上。她的命运始终在男人的手中被掌握着,被安排着。即使脱离了妓女的环境,也无法让她从妓女的身份中走出来。秋仪和小萼如此地在男权制度的淫威下受虐,却又无法醒悟到这一点,即使到了最后,秋仪看到悲夫在玩弄小萼留下的胭脂盒时,也将所有的问题归结于个人的性格,而看不出是制度对个体的残酷施虐。
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压迫成了女性“应有的”命运,带着受虐倾向的女性却对命运无条件臣服,甚至所有的反抗也是无济于事。这样的想法不仅仅在苏童的一部作品中体现,在其他作品中体现得更加明显。如果说《红粉》讲的是同一时代两个相同身份女人的故事,因为经历的相同而导致悲剧的相同,那么《妇女生活》讲的就是不同时代三个不同背景的女性,当她们并没有因为不同,而走向不同的生活。祖孙三代,仿佛总是在一念之间,毁掉了自己的一生,既而让后代也延续着自己的悲剧。甚至娴也在不同的年代,面对不同的人,为这件事情懊恼。但娴对于孟老板来说不过是众多被玩弄的女演员中的一个。她既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但是娴却无法明白是这个男人伤害了自己,而仅仅认为是因为自己不顺从而导致的悲剧,这就是受虐倾向的逻辑。她将自己的怨气发泄到女儿芝和母亲的身上,虽然母亲死时,她也认为“真不值得,为这个臭男人寻死,太不值得了”,但她却无法看到,孟老板利用手中的权力,让她甘心地顺从。受虐倾向掩盖了她反思自己的那一步了。
然而这样的悲剧在芝的身上又一次发生了。对比孟老板,邹杰出身贫苦,但是解放后的党员身份比解放前有权有势的有钱人更能征服一个软弱的女人。虽然身份从女演员到了女技术员,但是带着受虐倾向的女性那一面却并没有改变。从芝想要一个男孩的愿望可得知,她不喜欢女性这个身份,她已经觉察到女性这个身份让自己难受,但是这样的觉察却又朦朦胧胧,“一时也说不清楚”。知道自己不能生育的时候,芝觉得自己作为女人向社会提供孩子的权利丧失了,自己也就失去了结婚的意义。在芝的眼里,“一切都会变的,只有人的命运不会改变”。因为自己承担了母亲悲惨的命运,所以注定得不到“幸福和权利”,让芝轻生的正是她“不能改变的命运”。让自己婚姻摇摇欲坠的也正是自己不能生育的“命运”。芝的受虐倾向让她在“命运”下甘愿臣服。弃婴中全部是女婴的事实,不仅仅破碎了芝想要个男孩的愿望,也让我们发现只有女人才是被遗弃的对象。而萧的生活并没有因为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虽然萧的工作是卖肉的,表面上看起来终于可以宰割别人,但是放在社会砧板上被宰割的仍然是女人。养父对自己的行为使萧对那个家庭产生了淡漠的情绪,也对自己的性别产生了怀疑和厌嫌。小杜的出轨,对萧的冷漠,也是因为这一点。小杜的理直气壮仿佛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他没有看到养父对萧的伤害,只看到一个男人对属于另一个男人的“物品”的无理侵占,而错全在“物品”本身。这让萧恨透了小杜,并想到以结束性命的方式去对付小杜。从娴的顺从,到芝的觉察,到现在萧拿起菜刀反抗,虽然看似一种进步的过程,但是小杜最后的一句话,打碎了所有的挣扎:“一般来说,女人都敌不过男人。”这最后注脚一般的结语就是三代甚至四代女人的缩影。于是,受虐倾向在女性这个群体中扎根地更深,让女性更轻易地沉浸在这样的“事实”中。但这一切都仅仅是男人这个性别在压迫女人吗?
当男人退居到女人生活的暗处时,女人的悲剧并没有改变,相比《红粉》和《妇女生活》,《另一种妇女生活》中的男人们并不如此显眼,但也无所不在。楼上的简氏姐妹还是楼下的三个店员,没有一个逃脱“女人就是为男人而设”这样带着受虐倾向的观点。且不说因为通奸被杀的杭素玉、拼死抵触封闭了自己一辈子的简少贞,就连顾雅仙也认为没有男人陪伴的简少芬是不幸福的,粟美仙的脑子里也成天想着如何去抓杭素玉与孙汉周的把柄,用男人去打倒自己的敌人。所以在故事里退到次要位置的男人,丝毫没有减少他们对女人命运的影响。孙汉周与杭素玉的通奸,是导致她被杀的主要原因,而老宋这个拼命保护杭素玉的男人,到她对自己不忠时也露出残忍的一面,用私刑的方式,理直气壮处理了自己的爱人,并认为她死得活该。而章老师这个男人的出现,彻底打乱了简氏姐妹的生活,娶走了妹妹,让姐姐发疯,最后自杀。在故事中,总是男女之间的事情让这些女人和男人们疯狂。另一面,虽然我们没有看过简少贞的故事,但是从她对戏曲《碧玉簪》的态度,对它下的评语“严小姐是个蜡烛货,自轻自贱的蜡烛货。”我们就得知,她年轻的时候一定经历过什么事情,所以才会封闭自己的。姐姐想保护妹妹,所以才封闭妹妹,但是她的做法,也让妹妹陷入了另一种不幸福当中。她对妹妹的霸道、独占、全面的控制,让她身上的受虐倾向变得复杂,但我们也依然可以看到,她对妹妹过分地依赖,是她对爱的渴求,面对男性,她宁可用封闭自我的方式去逃避、躲闪,以为躲过了男人,生活就会像她想的那样,她彻底地隔离自我,放弃自我,以为无限地退让,男性就不会侵蚀到她的空间,但是最后章老师的出现并带走妹妹的事实,让她彻底地绝望。对姐姐来说,无路可退无路可让是绝望的,绝望到她要用死去面对。阿德勒曾经说过“每一个自杀案件都是一种谴责”。[4]但她至死也不明白,自己真正该谴责的对象不是顾雅仙不是章老师,不是自己的妹妹,而是整个男权社会。但是她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并且永远不会意识到了。
二 施虐受虐的循环
从对前三部作品中的女性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出,在权力的面前,她们身上所体现的社会受虐倾向并非仅是一种个体现象,而是社会文化对个体束缚这一现象的缩影。为了进一步分析苏童笔下的人物的受虐倾向中所反映的权力关系,笔者引入了一个概念,父权制。“父权制意识形态使女性置身于性别化的集体匿名凝视中,这一凝视内含了一系列父权制社会中有关女性道德和行为的评价模式,通过督促女性实践父权制意识形态标准来行使性别权力,”[5]也就是说男人凭借他们的性及与他人的血缘关系确立的男性统治,是以男尊女卑的意识形态确立和保护男性普遍优先权的性别关系秩序。“父权制并不意味着作为个体的男性是一个“统治者”,作为个体的“女性”是一个被‘统治者”,作为一种制度形式,女性像男性一样参与到这种男性统治中,男性也像女性一样受到这种统治的限制。这种统治的逻辑在于,所有的参与者不断加入到对统治制度的建设中,推进对其自身的统治,并自觉或不自觉地促使统治延续下去。”[6]于是,当社会对个体的束缚形成为制度之后,制度化的社会束缚会给社会(群体)成员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甚至是一种精神折磨。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体只有将社会束缚的形式内化为自身认同的形式(这也就是社会化过程)以后,才能通过这样一种“屈从”得到个体的解脱。当内化的制度表现在外显的行为时,它便反身强化了制度本身,这就形成了制度再生产。在这样的情况下,所有的社会(群体)成员都身陷其中,个人对制度中的他人而言,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集社会意义上的受虐和施虐于一身。但是整个人群相对于制度来说,又是带着强烈的社会受虐倾向。他们在受虐的过程中,一方面释放了自我,寻找精神平衡,使内心的苦闷和痛苦得到缓解,另一方面在这样缓解的过程中,却是一种变相的施虐过程,又塑造出新的受虐对象。在这样的循环下,人们的生活是死的,人在其中是死的,权力和制度却可以永生。
苏童的中篇小说《妻妾成群》中,陈家大院中的姨太太们,她们既是男权制度下的牺牲品,但又极力维护那些有形无形压抑她们的家规(制度化的权力)。她们的争夺行为,仅仅是为了获得一家之主(陈佐千)宠爱,为了能生下更多的后代(这也可以看成是制度的再生),并让自己在那个死气沉沉的家庭中获得更大的权力。她们这种欲望促成了她们之间的布满血腥的施虐甚至攸关性命的行为。
故事是从颂莲的家庭败落,父亲自杀于水池中开始,又从颂莲围着井边疯子般呓语结束。文章因为死而开始,又因为死而结束,但是陈家大院里人们的生活并没有为此而改变。一代又一代的陈家女眷因为同样的原因在那口井里被毁灭,而一代又一代的女人们又走入陈家大院的大门,复制着他人的命运。
陈佐千是陈家大院权力的代表,但是在颂莲的眼里,却是一个“形同仙鹤,干瘦细长,生殖器像弓一样绷紧着”的人,陈佐千的解释是“让她们掏的”。事实上,从他在梅珊屋里出来的表情,就可看出陈佐千对这样的生活并不是一味地享受。自身也在其中,走向枯槁。
大太太毓如信佛,但在陈佐千眼里,她不是“什么信佛,闲着没事干,滥竿充数罢了”。大太太进门的时候很风光,为陈佐千生儿育女,算得上家中地位第二的人。但是也摆脱不了自己人老珠黄,日渐失宠的命运。但是,大太太是不会甘心权力旁落的。颂莲第一次的拜访,她就没有给一个正眼,到后来烧树叶与颂莲的争执,在陈佐千的生日上对飞澜和忆容打翻花瓶时的惩罚,到最后因为颂莲与飞浦之间的吵架,处处都是以对他人的施虐来满足弥补自己年老而被陈佐千冷落的痕迹。
而几个姨太太之间的争斗也是心照不宣。颂莲在得知二太太帮着雁儿诅咒自己后,作为报复,在旁人以为偶然的情况下,用剪刀剪下卓云的半边耳朵,;而卓云为了能比梅珊早一点生下后代,并且能生个儿子,不惜设计下毒手残害梅珊。梅珊也为了争取陈佐千的宠爱,半夜闹病,将他从颂莲屋里叫走。在这样看似循环的因果报复中,为了实现自己控制他人、压制他人的权力欲望,三位姨太太既是悲剧,又是制造悲剧的主谋,既受虐又施虐。连被陈佐千摸过一把的雁儿也没有逃脱被压榨的命运,延续着在施虐与受虐的循环。她们一如前几部作品中的女性一样,在社会受虐倾向的影响下,她们看不见自己的悲剧的根源,只以为是姨太太太多,陈家男人好色,是因为别的女人,才让自己的地位下降,权力旁落。
在这样一个男人扭曲女人的制度,长者扭曲后辈,地位高的人扭曲地位低的男权制度之下,所有的人都带着强烈的受虐倾向,既受着制度的束缚,又自觉地裹紧了那些束缚,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甚至还乐在其中,认同这样的束缚并使之屈从于它,企图从中获得个体的解脱。但是他们的认可与屈从必然会使这一束缚变本加厉,使他们在权力的迷网上越陷越深,对自己的束缚也是越裹越紧,而且因为社会受虐倾向的作用,让她们更不知痛痒的活在其中。
陈家所有的人,都延续着代代相传的悲剧。在老佣人宋妈的口中,得知那井里死的三个女人是怎么死的,而在颂莲的眼里,梅珊的死仿佛是复现了那三个女人被投入井中的场景。制度的权力已经大到可以毁灭人本身的地步,令人恐惧又真实地存在于陈家大院里。既惩罚了死去的人,又震慑了活着的人。让那些想要跳出制度的人,惶惶而疯狂,正如在那井边自语的颂莲。另一面,飞浦作为陈家的大少爷,却害怕女人不敢靠近,也并没有逃脱制度对他的伤害。
在宋妈的眼中陈家一年不如一年的事实,让我们了解,终有一天,陈家也会像颂莲的家一样衰败,陈家的儿女们也会像颂莲一样,在失去父亲和男人支撑后,又会投入另一个男人组建的家庭,在刚跳出这个制度后,又跳进这个制度新的再生产中。人是会死的,家是会败的,但是这个让人在受虐的同时的施虐制度却是永生的,而这才是受虐者的真正的悲剧。
社会受虐倾向虽然在苏童笔下女性人物身上有着不同特征的表现,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男权文化的屈从。虽然有些女人做出些许反抗,但这样的反抗在父权制面前却显得弱不禁风,会被轻松化解。在那些看似荒诞和软弱行为的背后,正是带着受虐倾向的女人面对男权的生存智慧与求生手段,也是父权制、男权社会对女人无形管制的结果。“这种管制,是通过指定风俗习惯和法律制度来实施的,那些风俗习惯和法律制度旨在使人们变得‘会计算、讲秩序、一切行为都有一定的必要性’——简言之,旨在使人们驯服。”[7]
[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223.
[2]马藜,王美丽.妥协与反叛——《金粉世家》中女性命运与女性现代意识的分析[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56.
[3]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394.
[4]阿德勒.挑战自卑[M].李心明,译.北京:华龄出版社.2001:77.
[5]翟永明.成长·性别·父权制——兼论女性成长小说[J].理论与创作.2007(2):23-26.
[6]佟新.社会性别研究导论——两性不平等的社会机制分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5.
[7]詹姆斯·米勒.福柯的生死爱欲[M].高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96.
Tragic Females in the Cycle of Sadism and Masochism——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Female Characters in Su Tong's Novels
WANG Zhongping
(Yibin Radio and Television University,Yibin Sichuan,644002 China)
Most of the female images in Su Tong's novels are deeply exploited by patriarchal culture system and thus they have a strong mental tendency of social masochism.However,in order to find spiritual balance,they also have a strong psychological impulse of sadism during the process of masochism.In the cycle of sadism and masochism,they repeat the human tragedy of females as the second sex.
Su Tong's novels;emale images;Patriarchy,sadism,masochism
I207.67
A
1674-117X(2012)02-0128-04
10.3969/j.issn.1674-117X.2012.02.026
2011-11-08
王钟屏(1983-),女,四川宜宾人,宜宾广播电视大学讲师,硕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李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