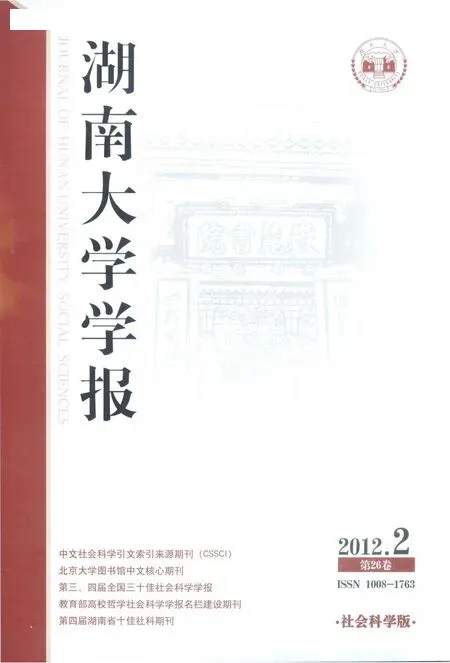浅谈20世纪初我国近代教育转型过程中的乡村文化生态危机*
邓运山
(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浅谈20世纪初我国近代教育转型过程中的乡村文化生态危机*
邓运山
(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在传统社会,我国乡村地区一直存在一个与封建小农经济相适应的,由乡村士绅、私塾或族学、宗族文化以及民间娱乐等要素构成的、相对质朴而又和谐的文化生态系统。但是,自清末民初“废科举、兴学堂”的近代教育转型过程中,这种传统的乡村文化生态开始出现了危机。其主要表现是:士绅精英的离乡进城使乡村社会失去了重要的文化载体和传播主体,乡村教育转型过程中呈现出“旧学难除,新学难布”的两难局面,传统社会凝聚人心的宗族文化遭到乡民的漠视,乡村社会日常娱乐活动的减少使乡民精神生活越来越贫乏。
20世纪初;近代教育转型;乡村文化生态危机
文化生态系统是指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某一相对独立而完整的社会区域内各种文化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方式和状态,是一定社会的区域文化和人们的行为习惯与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相互联系而组成的一个有机统一体。文化生态是一个比自然生态更为复杂的系统,它是一个民族长期历史积淀而形成的结果,对该民族个体素质的培养以及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的塑造等方面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影响。任何民族的文化生态既不可移植,也不能复制和再生。如果一个民族破坏了自己特有的文化生态系统,割断了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其后果也许不会像破坏自然生态那样直接和明显,但却会深远地影响自身历史的发展。
在我国传统社会,封建小农经济始终占绝对优势,与这种分散的小农经济相适应,“传统文化是城乡一体化,具有乡土性,中国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的……”[1]。正因如此,长期以来,在我国乡村社会一直存在一个相对质朴而又和谐的文化生态系统。这种文化生态系统是由乡村士绅知识精英、私塾或族学、宗族组织以及各具地方色彩的民间娱乐活动等要素构成的。不过,对这种乡村文化生态系统的维系起决定作用的是我国封建社会长期盛行的科举考试制度。作为传统社会统治阶级的治国方略,科举制度对于整个国家的政治、教育、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都起到重要的枢纽和调节作用。同时,作为一项教育和文化制度,它也维系了传统乡村社会教育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对乡村教育和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更是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可是,自清末民初“废科举、兴学堂”的近代教育改革启动以后,中国乡村社会这种千年如斯、长期稳定的文化生态系统开始出现了危机。
20世纪初,中华民族在屡遭西方列强的侵略之后,清政府不堪帝国的耻辱,终于痛下决心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化创制,其中,近代教育体制改革就是清末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1901年9月,清政府诏令停止八股取士制度,“所有书院,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2]。第二年,正式颁布《钦定学堂章程》,以小学、中学、高等学堂(大学预科)与大学三级学校为主干的近代学堂体制在中国开始确立。1905年,清政府最终宣布:“著即自丙午(光绪32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举考试亦停止”。[3]从此,我国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制度终于寿终正寝,使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式学堂教育体制最终得以确立。然而,这一划时代的诏文在宣告一项集政治、文化、教育等功能于一体的科举制度走向历史终结以后,却对整个国家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当然,也包括我国的乡村社会,尤其是对乡村文化生态系统的破坏和影响。
一 士绅精英的离乡进城使乡村社会失去了重要的文化载体和传播主体
相对于世界其他各国来说,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是人类前资本主义社会最具开放性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世家无百年之运”,故传统社会一直存在着这种相对频繁的阶层流动。通常,引导这种阶层流动主要是由科举考试制度来实现的。由于科举时代封建官僚的职数有限,只有那些取得较高“功名”的士子才有资格进入官僚阶层,因此,对于大多数的士绅阶层来说,他们只能以较低的“功名”和“身份”终生居住在乡村社会。据有学者不完全估计,这些“沉积”在乡间的士绅知识精英,事实上是一个“闲居”乡村的庞大精英集团,他们约占整个士绅阶层总数的96%以上。[4]于是,这些乡村士绅便成了传统社会乡村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主体,成了乡村政治和文化生活的组织和领导者。正如张仲礼先生所说,“乡村士绅作为一个在乡村社会居于领袖地位和享有各种特权的社会集团,他们视自己的家乡福利增进与利益保护为己任,承担许多的社会职责,诸如……此外,还组织地方治安、征税,弘扬儒学,兴建学校等农村社会生活的各项工作”。[5]由于这些乡村士绅受过良好的儒学教育,故他们在乡村社会往往能够自觉承担弘扬儒家文化及其价值观念的职责,不仅承担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任务,而且起到维系和平衡乡村文化生态系统的重要作用。另外,即使那些留住城市做官的少数士绅精英,当他们离任时,大多数人也会选择告老还乡。因此,在传统社会,乡村往往更容易成为士绅精英的汇集之地。
但是,自清末民初“废科举、兴学堂”以后,随着旧式科举教育体制的废除和新式学堂教育体制的确立,传统乡村士绅的“功名”和“身份”特权骤然之间就失去了制度保障。由于“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被堵死,昔日的乡村士绅失去了向上晋升的希望,断绝了通向上层统治阶层的路径。在此情况下,多数乡村士绅不得不另寻新的出路,尽快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位置。由于大多数近代化的新兴职业几乎都聚集在城市社会,使得一向安土重迁的乡村士绅们不得不离乡进城,于是就造成了大量乡村精英的急剧流失现象,使“农村中比较有志力的分子不断地向城市跑,外县的向省会跑,外省的向首都与通商大埠跑”。[6]另外,为了与近代工业化相适应,在清末教育改革过程中,新式学堂绝大多数设在城市,这又使得乡村读书人也纷纷离乡进城。可是,这些从乡村走出来的知识精英们在城里接受新式学堂教育,获得毕业文凭,取得较好的资格以后,一般人都会选择留在城市,再也不愿意回到乡村。正如费孝通所说的,“以前保留在地方上的人才被吸走了;原来应当回到地方上去发生作用的人,离乡背井,不回来了”。[7]因此,由于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的近代教育体制的转型,直接导致了清末民初乡村知识精英城市化的进程,从而使士绅阶层作为传统文化精英开始退出了乡村社会的历史舞台。
无论是传统乡村士绅,还是接受近代学堂教育的知识精英,他们都是乡村社会的文化载体,既是乡村文化的承载者,同时又是乡村文化的传播者。在清末民初“废科举、兴学堂”的近代教育转型过程中,当乡村知识精英不断离开乡村,涌向城市以后,无疑就像从原来的乡村文化生态体系中抽走了一根主心骨,导致乡村社会出现了人才的“真空”状况。旧时,诸如给刚出生的孩子起个显贵、高雅的名字,给终年在外混事的亲人写封信,乡邻之间订个契约、写份合同,逢年过节时写副对联,农村婚丧嫁娶时看个日子、择个时辰,甚至某家孩子养得不顺,半夜三更经常哭闹时,需要请人写张“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啼郎,行路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的帖子之类的事情,以前村子里不乏文化人,这样的事情很容易办。可是,现在当遇到这些事情时,要找个文化人来帮忙就难了。因此,随着乡村社会整体文化水平的陡然下降,过去曾经是传统文化生长的家园,如今却成为文化的荒漠之地。
二 乡村教育转型过程中呈现出“旧学难除,新学难布”的两难局面
在旧时科举时代,传统社会的教育基本上是一种城乡一体化模式,并且由于封建社会耕读传家的传统,整个社会的教育重心基本上还偏向于乡村社会。就传统的乡村教育来说,历来盛行的是一种乡村私学教学模式,由于各地私学分布极广,使那些已经取得“功名”和“身份”的乡村士绅都能成为乡村塾师,甚至一些只要参加过科举考试,能润笔作文的童生也可以吃上私塾先生这碗饭。传统乡村教育主要为蒙学教育,通常大多数适龄儿童都能接受。对于那些朴实乡村民众来说,他们让子弟读几年书也没别的太多想法,会识文断句,略通文理,算清账目,能在社会上做到不吃亏就行了。当然也有少数出身殷实之家、自身资质较好的童生士子怀抱“鲤鱼跳龙门”的梦想,或闭门苦读,或在私塾受业,“平日则习礼于庙,研经于斋,课艺于厅,校射于圃,旁及书算法律”,[8]只有当三年一度的科举考试来临时,他们才会定期汇聚城市来参加应试。另外,“中国之民素贫,而其识字之人所以尚不至绝无仅有者,则以读书之值之廉也。考试之法,人蓄《四书五经》、《诗韵》并房行墨卷等数种,即可终身以之,由是而作状元宰相不难。计其本,十金而已。以至少之数而挟至奢之望,故读书者多也”。[9]因此,由于教育投资不多,大多数贫穷乡民也能够应付,故乡村社会办学盛行,读书成风。但是,随着近代“废科举、兴学堂”教育近代化的转轨,各地乡村教育都开始呈现衰败迹象,于是,昔日乡村教育黄金时代的盛况一切都成了过去。
自清末新政宣布“废科举、兴学堂”以后,举国教育从中央到地方大肆“除旧布新”,然而,广大乡村教育改革现状却是“旧学难除,新学难布”。导致新式学堂教育在乡村很难推行的原因,首先是由于新式教育的办学成本较高,读书费用很大,使得兴办学堂教育面临一个资金严重短缺的瓶颈问题。由于近代新式学堂教育是与资本主义工业化相适应,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有限资金要重点保证城市学堂教育的大力推广和发展,于是,乡村社会的新学教育被严重忽略了。例如,在河南大部分乡村地区,乡村教育根本得不到重视,“各县以往教育当局,多偏重城市教育,以粉饰取荣;置乡村教育于不顾,竟使适龄儿童,多半失学”。[10]在河北,到1928年为止,整个全省大约还有四分之一的村社没有设立小学,有些县份如南皮、易县、东明、长垣等甚至高达70%以上。[11]根据当时全国乡村新学教育的发展状况,有人估计,如果清末民初整个中国共有12万个乡,100万个村,那么到1922年时,全国中小学校共178847所,平均每6村才有一所学校,即使到1931年以后,全国中小学校也才只有262889所,平均每4村才有一所学校。由此可见,在中国乡村社会,当时的新式学堂教育艰难推广的严重程度。
当然,在“废科举、兴学堂”的教育近代化转型过程中,乡村民众对新式教育的极力抵制也是导致新式学堂在乡村很难普及推广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近代“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传统文化尽管遭到西方文化的强劲冲击,但其顽强的生命力仍然在文化革新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展示着。[12]由于传统私塾教育是从农业社会的土壤里衍生出来的,它在教学形式、教学内容、教学效果、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很符合乡村民众的价值取向,因此,于乡土社会具有较强的亲和力。可是,新式学堂教育不但学费昂贵,让一般乡村民众难以承受,而且班级教学、团体授课的教学形式对于乡间儿童来说也很不适宜,同时教学内容也“不切于民生日用,使生徒毕业者举其所学,与社会不相入”[13],因此新式学堂教育很难得到乡村民众的认可。此外,自从“废科举、新学堂”以后,连以前乡村社会纯朴的学风都发生改变了。据民国《山阳县志》记载,自科举废除后,新式学堂大兴,乡村社会不再有比户弦诵之声,“礼教寖衰,竞争日起,缙绅子弟,无复恂恂,一得自矜,迂视耆老,甚至博塞嬉游,莫之惑禁,洵乎士风情法为转移也”。[14]正因如此,自近代学制改革以后,很长时间内,乡村民众还是“亲私塾、远学堂”。有人曾描述当时南方某县乡间新式学堂的办学情形:“亦尝贴广告于通衢,招人就学。乃待之许久,初无来校报名之人。校董不得已,则择其家有子弟、而其力又足使之就学者,亲往敦劝,许以不收学费。然犹应者十一,拒者十之九”。[15]
清末民初,一方面,新式学堂教育在乡村社会很难普及推广,而另一方面,政府大张旗鼓要求罢免的旧学塾馆却依然强劲地硬挺。于是,就出现了近代乡村教育的一种奇怪现象:“代表新文化的新式学校以政府为后盾,不断地向乡村社会渗入,而代表传统旧文化的私塾在百姓的支持下挣扎生存,并回击来自新学的‘挑战’,两者交锋对垒,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新旧并存的二元教育模式”[16],甚至在很多乡村地区,旧式塾馆比新式学堂还要多。据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曾对我国乡村教育构成进行的统计估算:直到抗日战争前,我国农村教育属于旧式的占65.1%,属于新式的仅占29.7%,属于新旧式学校,即改良私塾的占5.2%;华北农村旧式教育占53.9%,新式教育占44%,改良教育占2.1%;华南农村私塾发达,旧式教育占75.6%,新式教育占19.1%,改良私塾占5.3%。[17]可见,当年政府“废科举,兴学堂”在乡村社会推广之艰难。
三 传统社会凝聚人心的宗族文化遭到乡村民众的漠视
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宗族通常是指拥有共同祖先而形成的男性群体,主要以族长、族规、祠堂、族田和族学以及祖坟和族谱为主要特征。旧时乡村社会几乎每一个姓氏都有一个宗族,人们十分注重血缘亲情,家族宗族观念较强,宗族文化盛行。在宗族势力强盛的华南地区,大多数宗族自然村落都有两个标志性的建筑,即宗族神庙和宗族祠堂。宗族神庙起沟通族人与祖先神灵之间的情感交流作用,在乡村社会维系本宗族民众的精神世界。宗族祠堂则是一个宗族祭祖、正俗、教化等事务的圣地,它集宗教、伦理道德、法律于一身,也是宗族最高权利的象征,起着维系本宗族人际之间血缘亲情和伦理关系的作用。地方宗族组织是乡村社会日常生活和教育文化事业的重要组织和协调者,每个宗族都拥有相当数量的族田,办有族学。族田具有救济族人、救荒赈灾、助役应差、助学重教、敬宗奉祀等敬宗收族的一系列功能。而兴办族学就使相当一部分同宗族子弟不论贫富都能够通过就读本宗族学校,从而成为乡村社会的准文化人。通常年份,每个宗族都要定期举行一些祭祀活动,这些活动仪式自然成了宗族乡绅们的专利。因此传统乡村社会很多人迷醉于科举考试,求取“功名”和“身份”,这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出人头地,更重要的也是为了家族的地位和荣耀,为了光宗耀祖,显亲扬名。与传统宗族文化相适应,在思想和观念上,乡村民众表现出浓厚的传统伦理价值观念,重视血缘、地缘、家族和礼俗,人们习惯安于现状,安土重迁,乡土观念浓厚。
自“废科举、兴学堂”以后,传统乡村社会的宗族组织开始松动了,宗族文化也开始有所变化。首先,社会转型时期乡村精英的“土豪劣绅化”使宗族组织的凝聚力日趋减弱。过去,传统乡村士绅是乡村社会的文化载体,甚至个别士绅还是宗族灵魂人物,他们是一切宗族活动的召集和组织者,在乡村民众中享有较高的威信。但自从科举制度废除以后,乡村社会出现知识精英城市化的趋势,使得作为一个阶层的传统士绅在乡村社会开始消失了。在此情况下,宗族内部就很难找出原来这样深孚众望的道德人物来取代。尽管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乡村社会又出现一些“新士绅”取代原有的传统士绅,填补了乡村社会的暂时的权力“真空”,但由于这些人在才德和威望方面无法和传统士绅相比,在乡土社会不具有内在道德性权威和外在法理性权威,在宗族内部很难服众,因此,宗族组织的凝聚力日减,宗族活动的开展越来越不正常了。其次,随着“废科举、新学堂”的近代教育转型,乡村族学开始衰落,宗族组织的义田制和学田制走向瓦解。在传统社会,助学重教是乡村宗族组织的一个重要功能,它使一部分聪明好学而家庭贫困的儿童能通过宗族资助来完成学业,最后通过科举考试,获得较好的“功名”和“身份”,从而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但是,自从宗族义田制和学田制走向瓦解以后,宗族学堂开始停办,从而使一些贫寒子弟就与教育无缘了,于是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文盲率反而比传统社会更为上升。再次,宗族文化遭漠视,乡村民众的宗族观念和宗族感情开始淡化。在近代社会转型时期,随着乡村现代化的进程,商品经济的发展,现代文明的足迹也开始走进昔日封闭的乡村社会。人们开始观念更新,思想解放,“重利轻义”取代“重义轻利”,对敬宗收族的宗族组织的敬畏之情也开始弱化。据江西宜丰县方志记载,在传统社会,凡遇祭礼,“必肃衣冠入庙,间有不具靴者,人皆笑之”,而自“剪辫、改西装,率皆便服从事;头童然露顶,或戴帽,或毡笠,或瓜皮尖帽,或穿臂衣。遇雨,当献酬之时,东西两廊展齿声与鼓乐志嘈嘈相杂,神如有知,其不飨矣”。[18]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说:“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们,结对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爷们只好听他们的便”。[19]这些都表明:在乡村民众的心目中,以前传统的观念完全改过来了。
四 乡村社会日常娱乐活动的减少使乡民精神生活越来越贫乏
在传统乡村社会,一些民间戏剧、杂耍和说书等都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深受大家的喜欢。对朴实的乡民来说,“无论其他什么样的娱乐方式,没有一种能像戏曲那样,在闲暇时给人们带来如此大的欢娱”。[20]通常,人们观看戏剧最主要的形式是社戏,乡村社会举行社戏,大多的时候都是为了媚神的目的。但是,虽说名义是为了娱神,其实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娱人。由于乡村民众终年劳作,平时很少有什么娱乐活动,因此,每当乡里社会有戏剧演出时,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人们都会兴高采烈前去参加。于是,“开台锣鼓一打,只见场子上里三层、外三层挤得满满的都是人,外围的有的站在高凳上,有的桌子上放凳,凳子上再站人,顽皮的小孩大都猴在树上…”。[21]在乡里社会,一年中唱戏的机会很多,几乎逢年过节要唱戏,婚丧嫁娶要唱戏,集市庙会要唱戏,宗族祭祀要唱戏。清朝刘世英写有一段描绘乡下人看庙会戏的曲子:“逢庙会,人烟盛,堂客喜,碰碰碰,抱孩子,净发愣,《忆真妃》《梦中梦》。赶车的,更好胜,车骡俱净”。[22]除了戏剧之外,各地乡村娱乐活动还有一大看点就是村头杂艺表演,其形式主要有高跷、旱船、舞龙队、舞狮队、大头娃娃、威风锣鼓、挠搁、各种类型的秧歌等。民间说书也是一种很重要的乡村娱乐活动,它是由专门的说书人在乡村社会进行表演的一种艺术形式,大致可归为当今演艺节目中的曲艺类。此外,在夏日的晚上,皓月当空,乘凉的人们围着一个见多识广的人听故事,讲天下奇闻,讲英雄豪杰,讲狐仙鬼怪。常常,当讲到最恐怖的时候,小孩子们连回家睡觉都不敢了。这种情景也是传统乡村社会的一道独特的风景,让每个从乡村走出来的人无不感到记忆犹新。
可是,随着清末民初“废科举、兴学堂”近代社会的转型,以前丰富多彩的乡村文化娱乐活动越来越少了。[23]导致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首先是乡村士绅精英的城市化,使得一些乡村娱乐活动骤然之间少了重要的组织和发起人。在传统社会,这些乡村公益性的娱乐活动都是由威望较高的地方乡绅来牵头,一般乡民都很拥护和响应。而随着这些乡绅们离乡进城,这些活动的组织和发起人就很难找到适合的人选了。虽说传统乡绅阶层退出了乡村社会的历史舞台以后,又有新式乡绅来填补乡村社会暂时的权力“真空”,但由于这些新式乡绅们在乡民心目中缺乏应有的威望,再加上他们“私”字当头,往往以娱乐活动的名义,来达到谋求个人私利的目的,故由他们来牵头发起的民间娱乐活动,人们很少有人响应。于是,乡村社会像以前那样的娱乐活动就越来越少了。其次,随着近代社会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乡二元化结构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了,于是一些民间艺人也开始涌进城市社会,去寻找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致使乡村社会在必要的时候要找台戏班子有时都不容易。再次,自从乡村社会大量知识精英阶层离乡进城以后,在闲暇时间,人们更感到无聊、单调了。以前人们凑在一起时,还有个见多识广的文化人天南海北地给太多没有出过远门的村民讲讲故事,当百无聊赖的人们听起来时,也感到津津有味,兴趣盎然,现在乡间连这样讲故事的人也很难找了。
综上所述,在传统社会,乡村文化生态系统虽然少了些高雅的格调,但却不乏清新的气息;虽说略显单调,但也相对和谐。然而,传统乡村社会这种千年如斯、田园牧歌式的文化生态系统却因西方工业文明的近代化进逼,以清末民初“废科举、新学堂”为契机,开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于是,昔日那些“宽厚长者风范的乡绅、抑扬顿挫读古书的儒者、堂屋里优雅的瓷器与山水古轴、祖屋里静穆安详的观音法像、孩子们追逐的卖唱艺人和算命瞎子、郊外古刹里打坐的僧人、节日里迎神送神的欢乐气氛、甚至妇女们哭丧时那种哀婉悲伤的古调韵味都已被时代席卷而走”。[24]取而代之的却是:作为传统乡村文化载体的乡村文化精英的城市化,乡村社会教育转型中“旧学难除,新学难兴”的两难局面,旧时显得神秘的、凝聚人心的宗族文化的受人漠视,乡村社会日常生活中娱乐活动的日益减少。正如有学者所说的:“自新政以后,农村社会生态就已经开始破坏了,……农村丧失了原有的调节机制,无法完成固有的循环和运转。民国以来虽然乡村的风俗还在延续,但灵魂却已丧失,日见纷乱和无序,乡村的组织,从宗族到乡社,无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中国农村至少在文化层次上,已经陷入了现代化变革的深渊”。[25]总而言之,随着清末民初“废科举、兴学堂”的近代乡村教育的转型,传统社会的乡村文化生态开始出现了严重危机。
[1] 梁漱溟全集(第二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
[2] 朱寿明.光绪朝东华录(四)[M].北京:中华书局,1958.
[3] 朱寿明.光绪朝东华录(五)[M].北京:中华书局,1958.
[4] 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M].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5] 张仲礼.中国的绅士[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6] 潘光旦文集[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
[7]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8] 房山县志(卷四)[M].民国17年铅印本.
[9] 论废科举后补救之法[J].东方杂志,1905年第11期.
[10]河南省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第三次行政会议记录[R].1936-06.
[11]朱汉国,王印焕.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华北农村教育滞后问题及其对社会的影响[A].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二卷)[C].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
[12]李喜所.中外文化交流史(晚清卷)[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13]教育部整理教育方案草案[A].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3辑)[C],1914-12.
[14]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1860——1916)[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15]问天.述内地办学情形[J].教育杂志.第1年第7期(宣统元年六月),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
[16]郝锦花,王先明.论20世纪初叶中国乡间私塾的文化地位[J].杭州:浙江大学学报,2005,35(1):14-22.
[17]乔启明.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
[18]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中)[M].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
[19]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0] (英)麦高温.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M].朱涛,倪静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8.
[21]周燮初.吴文化资源研究与开发(第3辑)[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7.
[22]刘世英.陪都纪略·诸般伎艺门[M].长春:沈阳出版社,2009.
[23]荆惠兰,刘永伟.变革中的衰亡——清末新政再研究[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109-112.
[24]钱理群,刘铁芳.乡土中国与乡村教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25]张鸣.教育视野下的乡村世界——由“新政”谈起[J].浙江社会科学,2003,(3):41-52.
Discussion on Modern Education in China in the Process of Transition of the Early 20th Century Rural Cultural and Ecological Crisis
DENG Yun-shan
(Yuelu Academy,Hunan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2,China)
In traditional society,The had been a relatively simple and harmonious cultural ecosystem adapt to the feudal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by the country gentry,old-style private schools or family,clan and civil elements such as entertainment.However,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abolishing imperial examination,establishing education hall”modern education in transition since the crisis of rural cultural ecology of this tradition began to appear.Its main manifestation is:leaving the city to rural society of the gentry elite lose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culture and media;rural edu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transition constituted a dilemma with abolishing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establishing education hall;traditional patriarchal clan culture of the social cohesion were ignored by the villagers;rural society daily entertainment activities reduced local spiritual life more and more poverty.
The early 20th century;In the process of transition of modern education;Rural cultural and ecological crisis
K258
A
1008—1763(2012)02—0040—05
2011-05-10
邓运山(1969—),男,湖南耒阳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