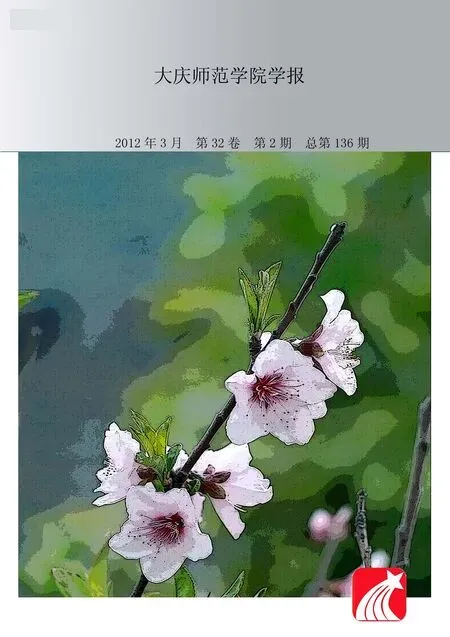从元杂剧的上场诗看元代的士子形象
刘小莉,熊贤勇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北碚 400715)
上场诗在元杂剧中非常常见,即在人物出场时,以自念上场诗的形式,让剧中人物“亮出自己行动的原因、目的、手段,甚至可将自己灵魂深处绝对不可告人的秘密,毫不隐讳地告诉观众”。在现存的一百一十六种元杂剧中,上场诗就有五百多首,平均每一种杂剧就有约四首上场诗,精彩地描写了元代社会中丰富多样的众生百相。在这一百多种杂剧中,写到元代士子的就有约五十种,几乎占了元杂剧的一半,而这五十多种杂剧中有士子的上场诗约有三十种,另外二十来种虽也是写士子,但没有他们的上场诗,且不论。元杂剧中大量关于士子的描写说明士子跟元杂剧的创作以及艺术特色有着深刻的联系。
一、 元杂剧上场诗中士子的类型化描写
元杂剧上场诗的内容,根据人物的身份、行业、年龄及剧情而有所不同。但几乎每一类型都各有几句照例的、公式化的句子, 甚至在不同的杂剧作品中字句完全相同, 呈现出鲜明的类型化特点。这个特点在士子的上场诗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
念上场诗:“黄卷青灯一腐儒,九经三史腹中居。学而第一当须记,养子休教不读书。”有如:《宋上皇御断金凤钗》、《鲁智深喜赏黄花峪》、《状元堂陈母教子》。将此诗稍作修改,从而形成照例的、公式化的句子如:
黄卷青灯一腐儒,九经三史腹中居。试看金榜标名姓,养子如何不读书。
黄卷青灯一腐儒,九经三史腹中居。寸阴当惜休轻放,治国齐家在此书。
(《晋陶母剪发待宾》)
黄卷青灯一腐儒,九经三史腹中居。他年金榜题名后,方信男儿要读书。
(《临江驿潇湘秋夜雨》)
黄卷青灯一腐儒,九经三史腹中居。世人只说文章贵,何事男儿不读书。
(《迷青琐倩女离魂》)
以上几组上场诗的字数、句式都相同,内容上只是将某些字词稍作修改,而意思却都一样。
感叹身世飘零悲苦、仕途失意无望的如:
惭愧微名落礼闱,飘零不异燕孤飞。连天大厦无栖处,来岁如今归未归。
(《陈季卿误上竹叶舟》)
坐守寒窗二十春,虀盐乐道不知贫。腹中晓尽古今事,命里不如天下人。
(《罗李郎大闹相国寺》)
流落天涯又几春,可怜辛苦客中身。怪来喜鹊迎头噪,济上如今有故人。
(《杜蕊娘智赏金线池》)
读尽缥缃万卷书,可怜贫煞马相如。汉庭一日承恩召,不说当垆说子虚。
(《感天动地窦娥冤》)
客里愁多不记春,闻莺始觉柳条新。年年下第东归去,羞见长安旧主人。
(《洞庭湖柳毅传书》)
一自离家赴选场,命中无分面君王。方信文齐福不至,锦衣何日早还乡。
(《王月英元夜留鞋记》)
刘蕡下第千年恨, 范丹守志一身贫; 料得苍天如有意, 断然不负读书人。
(《赵盼儿风月救风尘》)
以上几组上场诗也都表达了同一个主题,即士子在求学过程中的艰辛和漂泊之感。像此类感叹身世飘零的上场诗还有很多,此不赘述。
另外也有表现士子留恋风尘的上场诗,如:
本图平步上青云,直为红颜滞此身。老天生我多才思,风月场中肯让人?
(《钱大尹智宠谢天香》)
虽是文章出众前,若无风月也徒然。请君试把嫦娥问,何事偏生爱少年。
(《谢金莲诗酒红梨花》)
从上面几类例子可以看出,元杂剧中的上场诗有非常明显的重复现象,表现的士子形象也被类型化。可见,表现某类人物共同的生活感受和突出某类人物的共同特性是元杂剧上场诗的一个显著特征。
二、 元杂剧上场诗中士子的形象
元代的知识分子呈现出与前代明显不同的特点。魏晋的知识分子都是上层人士,他们虽然消极、避世,但他们身份高贵;唐代的知识分子是积极的、开朗的,虽然身份从世族阶层变成了平民阶层;“宋代知识分子的气质又与唐人不同,宋代的知识分子更带有学者的气质和修养。”那么,元代知识分子的现状和境遇又是怎样的呢?卑微的出身使得他们贫困潦倒;黑暗的社会背景和严峻的政治环境使得他们消极避世,还常常留恋风尘;科举的诱惑和宦游的艰辛又使得他们悲苦无望,平庸迂腐。而这些特征在元杂剧的上场诗中都有深刻的表现。
突出士子贫困潦倒的如刘君锡《庞居士误放来生债》中的李孝先:“心头一点痛,起坐要人扶。况是家贫窘,门前闻索逋。”他因:“自幼家贫,习儒不遂,于是去而为贾。只因本钱欠少,问本处庞居士借了两个银子做买卖,不幸本利双折,无钱还他。”后听说无力还钱者都要送衙门拷打,于是心生恐惧,忧而成疾,在家中染病。本是一介书生,因无钱读书,便去而经商,却不幸遭遇种种坎坷和波折,由此可见元代士子境遇的悲惨和贫苦。
又如范康《陈季卿误上竹叶舟》中的陈季卿:“惭愧微名落礼闱,飘零不异燕孤飞。连天大厦无栖处,来岁如今归未归。”他幼习儒业,颇有文名,只因时运未通,应举不第,流落不能归家。时值暮冬,雨雪交加,寒风凛冽,他却举目无亲,无家可归,于是无奈之下只好投奔终南山青龙寺,那里有个同乡的和尚肯救济他,他这才幸免于难,有了着落,可以继续读书考试。元杂剧中很多士子都和陈季卿的遭遇一样,他们饱读诗书,颇有抱负,怎奈“一自离家赴选场,命中无分面君王。方信文齐福不至,锦衣何日早还乡”。漂泊的他们虽然“腹中晓尽古今事”,却是“命里不如天下人”。知识分子的无奈和悲哀可见一斑。
突出士子消极避世、留恋风尘的,如关汉卿《杜蕊娘智赏金线池》中的韩辅臣:“流落天涯又几春,可怜辛苦客中身。怪来喜鹊迎头噪,济上如今有故人。”他“幼习经史,颇看诗书,学成满腹文章,争奈功名未遂”,本来是去上朝取应,路经济南府时,去拜访他的拜交哥哥,结果与妓女杜蕊娘相识,便与其相伴,一住就是半年以上,功名全抛之脑后,还说:“一生花柳幸多缘,自有嫦娥爱少年。留得黄金等身在,终须买断丽春园。”元杂剧中像这类的例子很多,又比如关汉卿《钱大尹智宠谢天香》里面的柳永,张寿卿《谢金莲诗酒红梨花》中的赵汝州,等等。这些士子在奔赴考场的途中多与妓女相遇相恋,然后贪图享乐,将功名抛之脑后,也有因为种种障碍而不能一起,最后发愤图强,一举及第的士子。
突出士子平庸迂腐的,如郑延玉《宋上皇御断金凤钗》中的赵鹗:“黄卷青灯一腐儒,九经三史腹中居。学而第一当须记,养子休教不读书。”士子上场很多都念这首上场诗,虽然表现了他们的勤奋和学识,但也突出了他们平庸、迂腐的一面。这个赵鹗仕途经历可谓一波三折,他在准备应试期间因没钱付住店的钱,于是他妻子要他休了她:“你也养活不的我,将休书来!”店小二也为难他:“将房钱来!”后来一举及第,其妻子马上变了嘴脸,店小二也改变了态度,还将其媳妇的裙子拿去换了酒来庆贺,谁曾想赵鹗在谢恩时当殿失仪落简,于是又被免了官。其遭遇变得更糟:“(旦云)你这等模样,还不与我休书?快将休书来!(俫儿云)爹爹,我肚里饥了也!我也不跟你了。(店小二云)还我房钱来。”世态炎凉可见一斑,然后他并无怨言,逆来顺受,任人宰割,毫无世情之心。像这样的士子形象在元杂剧中非常多,他们读“九经三史”只是为了有朝一日能金榜题名,他们不但自己要在科举这条路上越走越远,还要后代也沿着他们的路子走,尽管频频下第,他们仍然坚持,因为他们有一种希望,那就是“金榜一朝标姓名字,此时方显读书高”(《萧淑兰情寄菩萨蛮》),他们坚信:“今日一寒儒,明朝食天禄。”(《包待制智勘后庭花》)
三、 元杂剧上场诗中士子形象形成的原因
既然士子的活动和一切行为目标都是为了金榜题名,那么他们形象特征的形成原因必然也与科举有关。元代科举具有极大的历史特殊性,自隋至宋, 科举考试逐渐成为历代王朝选官取士的主要途径, 但到了元代,科举考试制度备受冷落, 呈现出不同于前代的许多特点。科举制度备受冷落成为元代士人形象特征的形成原因,主要体现在:
(一)元代统治者不重视科举制度
科举制作为中国封建时代的一种主要人才选拔制度之一, 创设于隋, 完善于唐, 发展于宋, 大盛于明清, 终结于清末。然而在元代,主要表现在:第一,科举制度曾一度被废除,其间虽然又恢复,但也只是断断续续地实行,且时间很短,从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1206年)到元朝被灭(1368年),共经历162年,其中科举制度仅实施了46年(1315—1336年,1342—1366年);第二,科举考试规模小,在总共施行的46次科举考试中,其中有15次所录取的人数皆不足原定之数,前后共录取进士1139人,每年平均录取24人,而唐代每年录取的进士约30人,明经100多人,这一数字与两宋相比,更是相差五六倍之巨。
元代之所以不重视科举考试,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是一个疆域辽阔的多民族融合的朝代,三次西征征服了广大中亚地区、东欧地区以及中东地区。忽必烈建立元朝后, 又将南宋政权消灭, 汉人最终成为蒙古人的属民。由此可见,蒙古人征服了无数民族,而汉人只是元代社会的一小部分,因此在统治方式上,蒙古人绝不可能仅仅因为汉人的文明和先进而以汉族政治制度来统治元朝。其次,蒙古民族崇尚实用主义。由于蒙古民族是个游牧民族,靠天吃饭的现实和环境培养了他们崇尚实用、民风简朴的民族风格, 这种朴实与汉族文化中的浮华形成强烈反差。而且蒙古统治者认识到,那些通过科举及第进入仕途的人,大多缺乏统筹全局以管理国家各种事务的能力,只会吟风弄月、贪图享受,或是为了个人利益和仕途升迁而苟且偷生,致使民生凋敝,国事日衰。他们对科举消极面的认识颇深,因此蔑视这种文人误国。
统治者对科举考试的态度,直接影响到士子的前途和利益。所以元杂剧中的士子要么郁郁不得志,要么悲观失望,因为他们进入仕途的道路受到了巨大的阻碍,而作为身份低下的普通文人,他们又不可能通过其他途径进入仕途,所以他们表现出这样的精神面貌也就不言而喻了。
(二)科举考试倾斜于蒙古人、色目人
蒙古统治者在科举考试的问题上, 对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实行了互不相干的两种机制。在每一阶段的选拔中, 蒙古、色目人经过两场考试就能见分晓, 而汉人、南人要进行三场考试才能有结果。另外, 在复习的范围和准备考试的形式等方面, 蒙古、色目榜与汉人、南人榜之间也有明显的差异。相对而言, 前者的复习范围略微小一些, 考试次数少一些, 而后者要参加古赋诏诰章表的考试。这种区别对待使得汉人和南人及第的几率就更小了。但这种政策并不是民族歧视的表现,以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来看,这还是一种比较合适的制度。因为蒙古族和汉族本身就存在着文化上的差异,如果要做到绝对公平,那么显然对蒙古族不利,而作为统治者的蒙古族,肯定要将本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要遏制汉族文化的滋生和蔓延,如此才能保证统一和和平。只是士子在这种充满重重阻碍的制度下,更加难以像唐宋时期的士子一样逍遥快活了,难怪他们要感叹“腹中晓尽天下事,命里不如天下人”。
(三)科举不是做官的主要途径
在科举施行之后,元朝绝大多数官员仍系由怯薛、恩荫及吏员出身,进士从未成为文官主流,科举出身的官员仅占全部官吏的百分之二十,而在唐宋时期,科举考试是最重要的做官途径之一,尤其对于下层文人来说,可以说科举是唯一的入仕途径。士人释褐后通常都从最小的九品官做起,但即使是最不起眼的校书郎、正字、县尉等九品官,其日后也可能飞黄腾达,甚至官至宰相。
综上所述,元代统治者对科举的冷落乃至废除,断绝了知识分子入仕的途径,他们从云端狠狠地摔了下来,地位沦落到娼妓之后。因此大批读书人沉溺下僚,既失去了经济上的依靠,也失去了政治上的希望,他们被抛向市井,不仅穷困潦倒,还孤独绝望,这不仅是元代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也是元杂剧中士子的真实写照。
[参考文献]
[1] 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2] 赖瑞和.唐代基层文官[M].北京:中华书局,2008.
[3]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0.
[4] 王季思.全元戏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5] 龚贤.元代科举制的文化阐释[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2).
[6] 徐黎丽.略论元代科举考试制度的特点[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3).
[7] 萧启庆.元代科举中的多族师生与同年[J].中华文史论丛,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