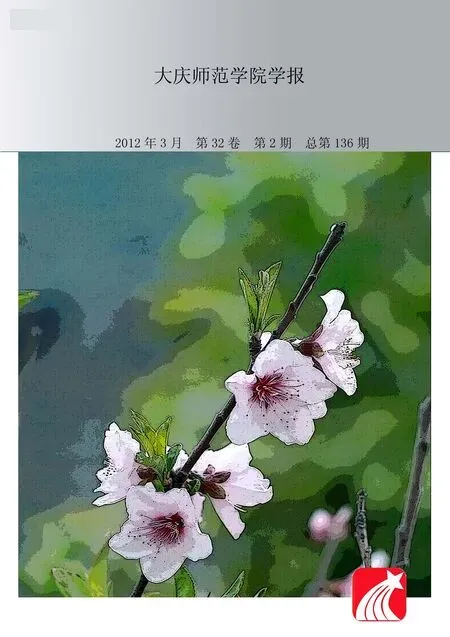可疑的与确定不疑的
——读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
梁 惟
(中共贺州市委党校,广西 贺州 542800)
笛卡尔是17世纪法国伟大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是西方近代哲学创始人之一,批判的怀疑是笛卡尔哲学的一大特色。他通过“怀疑”、“沉思”树立了理性的权威,突出了人的主体性,标志着西方哲学史上主体性哲学的开始。
一、笛卡尔“怀疑”产生的历史背景
笛卡尔怀疑哲学的产生是具有浓厚历史背景的。17世纪的西欧处于封建社会制度开始崩溃、新兴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正在萌芽的时代。这时的法国资产阶级在经济实力上不断壮大,对路易十四的封建专制统治很不满,渴望能改变社会现状以更快地发展资本主义,并使自己摆脱无权的地位而挤进统治阶级行列。但是,由于他们的力量还不是足够的强大,还不敢同封建势力公开决裂,幻想在封建王权的庇护下发展资本主义。这就表现出一种两面性:既有革命性又有妥协性。笛卡尔的以怀疑为特色的哲学就是当时法国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生动写照。
17世纪的西欧虽然经院哲学仍然控制着哲学及科学,但是自然科学已得到很大的发展,简单的机器不断被创造出来。伽利略制成了天文望远镜,进一步证实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开普勒发现了行星运动的三个定律,哈维提出了血液循环理论,笛卡尔本人则研究过数学、物理学、光学、天文学、机械学、医学、解剖学等。显然,宗教里的天启神学已经无法再解释自然科学的成果了,经院哲学旧的知识和认识方法已经成为自然科学发展的障碍,这使得哲学家们怀疑其真实性和作用。在此历史背景之下,笛卡尔的怀疑哲学产生了。
二、笛卡尔认为可疑的东西和确定不疑的东西
(一)最根本的怀疑对象是经院哲学旧的知识和认识方法
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深思集》(以下简称《沉思》)一开始就说:“由于很久以来我就感觉到我自从幼年时期就把一大堆错误的见解当作真实的接受了过来,而从那时以后我根据一些非常靠不住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东西都不能不是十分可疑的,不可靠的,因此我认为,如果我想要在科学上建立起某种坚定可靠、经久不变的东西的话,我就非在我有生之日认真地把我历来信以为真的一切见解统统清除出去,再从新开始不可。”[1]14由于笛卡尔从小就是在拉夫累舍的教会学校学习,一直学了八年多,[2]321学校里所讲述的当然是经院哲学。因此,笛卡尔上述所指的“自从幼年时期就把一大堆错误的见解”、“一些非常靠不住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东西”、“历来信以为真的一切见解”显然是针对经院哲学旧的知识和认识方法的。他主张人们在认识之前先要把一切过去接受的思想、观念都提到“理性”的面前来进行审查。显然经院哲学旧的知识和认识方法成了他怀疑的首要对象。
(二)怀疑感性认识而肯定理性认识
笛卡尔作为近代唯理论的代表人物,他是否定感性认识的,认为靠感觉获得的知识都是十分可疑的。在《沉思一》中,笛卡尔提到要认真地对全部见解进行一次总的清算,因为“直到现在,凡是我当作最真实、最可靠而接受过来的东西都是从感官或通过感官得来的。不过我有时觉得感官是骗人的,为了小心谨慎起见,对于一经骗过我们的东西就决不完全加以信任”[1]15。在《沉思二》中,他通过蜡块受热而改变性质和形状的例子说明人们不能凭借感官认识事物。在《沉思六》中,他通过论述“塔远看是圆,近看却方,塔顶上的巨大塑像从塔底下看却是小小的雕像”[1]81,从而得出结论:外部感官所下的判断是错误的。笛卡尔列举了上述丰富的例子,目标是明确的,那就是要极力贬低和否认感觉器官在认识中的作用,否认感性认识的可靠性和真实性。
在否认感性认识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同时,笛卡尔十分推崇理性认识,认为靠理性直观和演绎推导出来的知识是可靠无疑的。他说:“凡是我们领会得十分清楚、十分分明的东西都是真实的。”[1]35在他看来,理性直观是最根本的、最可靠的,然后以理性直观为依据进行演绎推理,从而推演出一切真实可靠的知识、建立起全部知识的大厦。他认为,理性直观和演绎推理是获得可靠的真理性认识的唯一正确的途径。
笛卡尔怀疑感性认识而相信理性认识,这一点还可以从他《论可以引起怀疑的事物》的后面结论中找到很好的证明。他说:“物理学、天文学、医学以及研究各种复合事物的其他一切科学都是可疑的、靠不住的;而算学、几何学以及类似这样性质的其他科学,由于他们所对待的都不过是一些非常简单的、非常一般的东西,不大考虑这些东西是否存在于自然界中,因而却都包含有某种确定无疑的东西。”[1]17为什么笛卡尔会得出这一结论呢?因为在他看来,前者是通过感觉和经验得来的,是感性认识,而感官是不可靠的,因此,前者是不可靠的;而后者不存在于自然界中,非经感觉得来,是一种“天赋观念”,靠感性直观、从理性之光中产生,因此是可靠无疑的。由以上所述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出笛卡尔哲学的唯理论特征。
(三)“我思故我在”被笛卡尔认为是首先的和最确定的知识
笛卡尔的怀疑是一种普遍的怀疑,或者可以说是一种彻底的怀疑,但也有他认为确定不疑的东西。在他看来,“我思故我在”就是他所探求的哲学的第一真理,是最清楚最明白的原理,并断定这条真理的可靠性和确实性是任何怀疑论者的所有最狂妄的假定都无法把它推翻的。
在笛卡尔哲学里,“我”并非是指人的身体,而是指脱离物质的心灵,思维是“我”的属性。笛卡尔认为,“我思维多长时间,就存在多长时间;假如我停止思维,也许我就同时停止了存在”[1]25,“我”并非是由肢体拼凑起来的人们称之为人体的东西,而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一个在怀疑,在领会,在肯定,在愿意,在不愿意,也在想象,在感觉的东西”[1]27。由上可以看出,思维就是“我”的属性,“我”就是一个实体,是独立于肉体的,因为有“我”,身体的存在才是靠得住的。这就是笛卡尔认为首先的且最为确定的知识。
三、笛卡尔“怀疑”的目的
从表面上看,笛卡尔“怀疑”的目的是为了得到最终确定不疑的知识。在《沉思一》中他提到想要在科学上建立起某种坚定可靠经久不变的东西,就要对全部旧的见解进行总的清算,而清算的方法就是普遍的彻底的怀疑。他通过普遍的彻底的怀疑,从而实现了对旧的见解的总清算,最后终于得到了这一“最清楚明白的原理”,这一“阿基米德支点”,即“我思故我在”。有了这一原理和支点,在他看来,就“有权抱远大的希望了”。即可以以此为前提和出发点,演绎推理出整个知识大厦,也就是可以像阿基米德所说的那样有了固定的支点就可以撬起地球。由此可见,笛卡尔的怀疑与传统的怀疑派不同,怀疑不是他的目的,怀疑是他用以扫除错误传统偏见的手段。他不是为了怀疑而怀疑,而是为了找到确切的知识而对旧的知识体系进行怀疑,即为了达到不怀疑而进行怀疑。这是笛卡尔显而易见的目的。
笛卡尔的“怀疑”有没有更深层的目的?
笛卡尔主张人们在认识之前先要把一切过去接受的思想、观念都提到“理性”的面前来进行审查,主张通过普遍怀疑来找到“最坚实可靠的出发点”,再由此用演绎推理的全部知识的大厦。稍加分析就可知,这实际上是在否定盲从宗教教条、否定教会的权威,是在反对经院哲学宣扬的信仰主义、蒙昧主义,要人们凭借理性独立思考。所以,笛卡尔怀疑的深层目的在于使人们摆脱陈腐的经院哲学的束缚,从而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扫清道路。
由此看来,出现后来的结果是不会令人意外的:笛卡尔的学说发表后即遭到众多神学家的反驳,甚至在1663年,教皇宣布他的书为禁书,[3]117他本人则被指责歪曲教义,被迫长期逃亡他国。而且应该说这个后果并非超出笛卡尔本人的意料,这可以从如下事实中得到证明:为了使自己的学说得以发表,或者说是为了寻求经院神学家的宽容和原谅,他做了不少工作。他首先致信巴黎神学院院长和圣师们,向他们说明写作此书的正当动机,即不是反对宗教神学,而是“有正当的理由把它置于你们的保护之下”[1]1,直至信的末尾说了不少恭维话。但是,笛卡尔这一做法不仅没有收到他所预期的效果,反而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此外,他还主动地来到神学法庭上,让一些有名的神学家们把他们对“沉思”的反驳意见提出来,并加以回答,然后把他们的反驳和自己的答辩与“沉思”发表。
笛卡尔的小心翼翼和神学家们的惶恐不安乃至气急败坏说明了笛卡尔“怀疑”的深层的、隐藏的目的在于使人们摆脱陈腐的经院哲学的束缚。
四、笛卡尔“怀疑”的影响
笛卡尔的“怀疑”、“沉思”对当时的哲学学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把西方哲学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其本人也因此被认为是近代哲学的创始人之一。
首先,实现了西方哲学由本体论向认识论转向。笛卡尔从其第一原则“我思故我在”推演出他的知识大厦,建立了他的哲学体系,使近代哲学从经院哲学的烦琐而神秘的形而上学中摆脱出来,并第一次从认识论的角度提出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研究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关系问题。
其次,确立了主体性原则,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笛卡尔通过“怀疑”、“沉思”第一次把人的思想对思想活动本身的肯定和认识当作哲学的出发点和第一原理,赋予人的思维和理性以至上的地位,为近代西方人的觉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人们树立了理性的权威,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也使人们相信用理性的方法就可获得对世界的真理性认识和把握。坚信理性力量后就会积极地发挥主体能动性去探索科学,去认识世界,因此,崇尚理性必然重视科学,也必然推动自然科学的发展。
第三,动摇了宗教神学,推动了人们思想的解放。笛卡尔以怀疑为武器,对经院哲学陈旧腐朽的知识和认识方法进行了总的清算,反对盲从宗教教条,从而动摇了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的神圣权威,使人们摆脱经院哲学的束缚,对当时人们的思想解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当然,笛卡尔的怀疑学说有其不足之处,他割裂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之间的内在联系。他推崇理性认识而极力贬低和否认感性认识,既否认了感觉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又否认了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他在创造出“我”即心灵这一实体之后,又提出另一实体:物质,从而创造出两个平行且彼此独立的实体,从而陷入了二元论。这些都不能不说是他的哲学思想的不足,但与其哲学思想的伟大意义比较起来,不足是次要的。
总而言之,笛卡尔的“怀疑”和“沉思”是哲学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一件大事,它对哲学的发展和人们思想的解放都产生了极其深远而有益的影响,笛卡尔也作为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而被永远载入史册。
[参考文献]
[1] 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M].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1986.
[2] 于凤梧,等.欧洲哲学史教程[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3] 杨寿堪.西方哲学十大名著导读[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