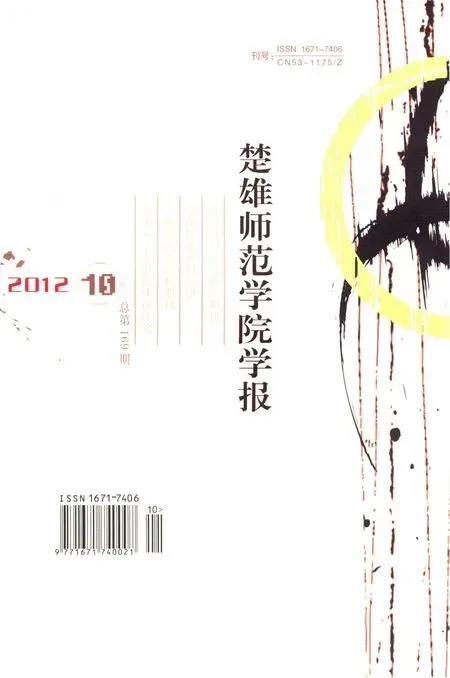试论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作品阅读教学*
王佳琴
(盐城师范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作为大学中文专业的重要基础课程,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正在面临严峻的挑战。人文环境的变异、大学教育的大众化形势、课时的大量缩减、学生学习态度的变化等,都为这门课程的教学提出了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目前,包括“教育、教学改革、学科的性质定位、教学专业性、文本阅读等”[1]在内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已经引起学界的关注和反思。其中“文本阅读”(作品阅读教学)更是难中之难,有学者指出:“阅读作品进而理解作品,是大学文学课程普遍存在的难点问题,现代文学也不例外”。[2]不少人注意到了在教学过程中,重视对文本的解读及对文本的微观分析,这对于回归文学教育的效果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此基础上,本文拟从作品阅读教学与文学史教学关系的处理、经典作品阅读的教学和作品阅读教学中“对话”方法的应用等角度,深化对这一教学问题的探讨。
一、作品阅读教学与文学史教学
以往的中文专业学生在大学期间,是先学一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在积累了一定的作品阅读数量和具备一定的鉴赏分析能力的基础上,再学习《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但是,随着教育环境的变化、课时的缩减,现在这门课程只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和文学史同时教学,对教师来说增加了难度。为此,怎样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同时也是教学过程中必须正视的重要问题。
感应着时代变迁,承载着几代知识分子的追求和梦想,中国现代文学已经走过了百年的历程。百年嬗变,积淀、淘洗了一批从内容到艺术表达形式都迥异于传统文学的现代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是构成百年文学史的基本元素,它们凝聚着作家的独特个性和思考,同时又是历史地存在于文学史的变迁、演化之中,可以说,它们是特殊和一般的结合体,正是由这些个别的“作品”才汇成了文学史的“过程”。如果说,那些浸染着作家生命体验的作品是明亮的夜星,那么文学史便是那灿烂的星空。没有第一层面的文学作品,文学史将失去存在的基础;没有第二层面的文学史过程,作品则杂散无章,更无法定位和评价,文学史也无法建立起来。
文学作品和文学史过程不能孤立存在,这决定了二者在教学中都不可偏废。笔者所在的学校在该课程的教学说明中有这样的表述:“教师主要讲授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作家和作品,使学生获得较多的文学评论和分析作品的知识,从而提高学生思考、欣赏和分析作品的能力;教师扼要讲授文艺运动、文艺思想论争的过程和特点,布置一些思考题让学生去思考、讨论,养成学生好学深思的学风”。可以看出,在次序上是先作品后文学史;在学时和用力上很重视作品阅读的教学,突出了新形势下阅读教学的首要地位。但是,怎样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贯彻、实现这一教学思想,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下文将从文学作品阅读的角度尝试做出一些思考。
必须重视重点作品的阅读教学。在现有的多数现当代文学教材中,在进入每个时期的学习之前都有一章专门介绍本时期的文学思潮,以期能够使学生从整体上把握和了解该时期的文学运动、文学论争等文学环境,为后面的学习打下基础。但是,实际的情况是学生往往对这部分学习心有畏惧,加之内容本身的复杂更使初学者一头雾水。一些从学术角度看来重要的文献,学生却对其毫无兴趣,更难理清头绪并记忆、掌握,如果一味地“硬”学,只能是事倍功半,更难达到重返历史场景的学习效果。因此,在总课时缩减的情况之下,应当尽量删减对文学思潮面面俱到的描述和讲析。而既要对某个时期的文学思潮有所了解,又要让学生容易接受,我们不妨通过一些重要的文学作品的学习来解决这一问题。即把对时代思潮的了解落实到具体可感的作品解读上,通过具体的作品达到对某个时代特征、时代转型的理解。这就要求在教学中选取一些能够代表一个时代思潮,表现某个时期时代精神的作品进行学习。通过对重点作品的深入解析,既容易进入,又能够以点带面,让学生了解某时期的文学信息,从而弥补了思潮评析的抽象和空泛,使叙述变得可感可知、血肉丰满。如在讲解十七年小说概述时,题材问题颇为重要,因为题材这一“写什么”的问题不再仅仅是一个材料的问题,题材的选取关系到文学的性质,周扬和何其芳在文论中都有相关的表述。比如周扬说:“知识分子一般地是作为整个人民解放事业中各方面的工作干部、作为与体力劳动者相结合的脑力劳动者被描写着。”可见,十七年小说中知识分子题材的创作有着严格的限制,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地位尤其是在与工农兵的对比之下更为渺小。这样的书写规范如果仅依靠文论、史料来介绍,学生较难理解,但是如果将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拿来解读分析,从知识分子丈夫和工农妻子之间的家庭细节到政治隐喻,再结合对它的批判,这个问题就变得非常具体可感了。
文学作品和文学史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通过优化二者的内部关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把握一个适当的度,从作品阅读教学入手,可以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从而实现教学目标。
二、“读经典作品总比不读好”——经典作品的阅读教学
重视作品阅读教学,尤其应当重视经典作品的阅读教学。20世纪,中国文学在一个世纪以来产生了数量庞大的文学作品,我们要阅读、学习所有的文学作品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但那些经过时间的淘洗和文学史检验的经典作品,依然是作品阅读教学的重中之重。2011年的现代文学年会也在关注这个命题,有学者指出:“现代文学经典阐释是本届年会的主要论题,也是最近十多年来现代文学界持续不断思考的问题,一方面体现了现代文学介入当代基础教育联系的动向,同时也体现了现代文学界力图介入当代社会文化建设的思路。”[3]在今天的语境中,强调经典作品的阅读教学,不仅因为这是课程教学的重要内容,而且因为经典作品是疗治某些文化痼疾的良药,是教育介入文化建设的方式之一。在当今浮躁的、充满功利色彩的社会,人文教师很难理直气壮地跟学生说,读这些书“可以”怎样。但如果非要给出一个理由的话,正如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所说的:“读经典作品总比不读好”。
人既是文化建设的主体,也是文化建设的对象。当今的大学生正是那些被命名为“90后”的青年,他们热衷于媒体、影视、网络,口头常用的是“杯具”、“坑爹”的网络用语,阅读的是短小的微博,能引起他们兴趣的是视图的冲击。研究表明:“经过网络阅读的熏陶之后,人们既失去了阅读大部头文学作品 (如《战争与和平》)的兴趣,也失去了专注与沉思的能力,因为思维总是呈现一种“碎读” (staccato)状态。”[4]面对“碎读”状态的90后,进行经典阅读教学就更有必要,不说其他,能够在大学期间耐住性子读几部长篇,如老舍的《离婚》、巴金的《寒夜》、钱钟书的《围城》等,这本身就是对他们思维能力的训练。
经典阅读教学有助于培养当代大学生的人文精神,塑造未来社会中的文化主体。当下的中国,文化思潮驳杂、中西兼具,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多元并存,在这样的语境中价值观尚未完全定型,还谈不上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当代大学生很容易目迷五色、随波逐流。随着对崇高的嘲弄、历史的戏说、意义的消解,一种后现代式的无序正在流行。如果说过去的教育包括中学语文教育过分看重承载的“意义”,使学生对经典失去真正敬畏的话,那么,今天的经典作品阅读教学应当回归其应有的人文指向。正如学者所言:“实际上,在对待经典的问题上,20世纪的中国已经经过了太多的“祛魅” (disenchantment)的过程,我们现在亟须要的是“返魅” (reenchantment),即让伪经典现出原形的同时,让真正的经典作品成为引导人们心灵世界的指路明灯,让人们对真正的经典作品拥有一种宗教般的情怀。”[5]现当代文学课程中的经典作品阅读教学,正是要担当这样的责任。
不仅如此,通过经典阅读教学,我们要找回英国评论家利维斯所说的“伟大的传统”,还要凸显现当代经典作品阅读教学的独特性。何为传统?当下对传统的理解过多地偏向于中国古典传统,如百家讲坛对孔子、庄子等的阐释曾获得大众热捧,幼儿在春晚上表演典籍吟诵而获得赞誉。先不论这种传统传承有无问题,但其对传统的理解仅仅局限于古典就是偏颇的。因为百年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也是知识分子以文学的方式参与民族精神重铸的过程,现代文学本身已经形成了传统,我们没有理由摈弃这样的传统。如鲁迅,他的作品就形成了伟大的现代传统,但是当代大学生对鲁迅的接受现状令人堪忧。如果说古典文学传统注重个人修养,齐家、治国、平天下那种家国一体的人生理想,那么,现代文学传统从鲁迅开始就在呼唤着独立思考的个人的出现。今天,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片面强调古典传统,难免成为夸耀“我们先前比你阔多了”的阿Q。我们重回现代经典作品的阅读教学,就是要彰显现代经典的独特之处,并使其养分在教育的血脉中得以传承。
三、“对话”——作品阅读教学的一种方法
作品阅读教学的实现最终要落实到具体的方法和途径上来。这是一个关乎教材的选取、方法的设计、考核的改革在内的系列工程,它既是一个理论的推进,更是一个实践的探索过程。不少名家、大家、老师和同行们对此已经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由于篇幅和能力所限,下面仅就作品阅读教学中的一个具体方法——对话试谈一二。
哲学上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将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称为轴心时代,此间人类文明同时在中国、印度、希腊等国家形成。这个时期的文化巨人通过“对话”产生了丰富的思想,对后来的东、西方文明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对话”是一种强调交互的知识生产方式。具体在作品阅读教学中,“对话”的运用首先是一种对作品的开放式解读。卡尔维诺曾说:“经典作品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好的文学作品在其产生之后的不同时代语境中,都在召唤一种开放的阅读,这个链条是没有穷尽的,作品阅读教学要鼓励学生投入到这种阅读中来。在课堂教学中,不要急于告诉学生文学史总结概括出来的一两条结论,而是要启发学生将自己的阅读感受与作者形成一种“对话”,从字里行间仔细品读作者心灵的喜痛,体悟作者对人生的哲思,形成心灵与心灵的“对话”,生命与生命的“对话”。
对话还是教学的一种直接形式。中西方都有以“对话”方式展开教育的先例,如《论语》中即有描写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各言其志的一章。其实,通过教师和学生之间问答的方式,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种教学方法的运用很多。具体在作品阅读教学中,这种“对话”形式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邀请他们加入阅读的队伍,抓住现当代文学作品与我们生活距离较近的优势,鼓励他们保存个人的阅读体验。在课堂上围绕作品中的一个人物、一个情节、一段描写谈出自己的感受和看法,在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和学生之间形成“对话”,往来之间加深印象、启人深思。因为不同解读者之间的这种“对话”可以扩大解读的可能和空间,同时也可以启发学生求证自己的观点。诗人王小妮在谈到自己的教学体验时曾说:“大学不能只是个技能培训所,总要有非功利的形而上的提领,而且不应是单向的,只由老师发出的提领,它必然是双向的。”[6]在作品阅读教学中较好地运用“对话”,就是在阅读中努力实现这种“双向”的提领。
[1]编者.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问题(笔谈)[J].江海学刊,2006,(3).
[2]刘勇、李春雨.现代文学大学课程教学的几项考察及思考[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3).
[3]曹万生.现代文学语言研究的突破与经典的当代阐释[J].文学评论,2011,(1).
[4]赵勇.消费快感与娱乐经济[J].文艺争鸣,2010,(11).
[5]赵勇.经典的祛魅与返魅——文化研究语境下的文学经典和文学教育[J].天涯,2006,(3).
[6]枝上花开又十年:女诗人王小妮谈〈上课记〉[EB/OL]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10-10/15/c_12663362_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