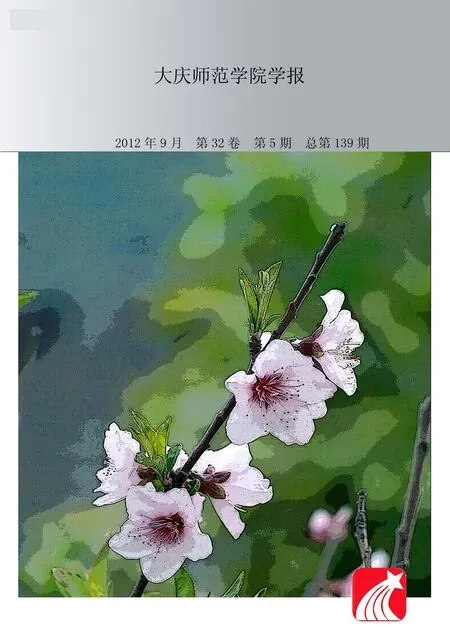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减法与加法
刘 阳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北京,100011)
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是事关我国城市化进程及成败的重要因素。针对目前农民工的基本流向集中于各个大中城市的趋势,如何让那些为城市建设付出巨大努力的老一辈农民工以及早已远离乡村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序流动,逐步融入城市生活,并避免许多国家出现的大量城市贫民窟的严重社会和经济问题,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新特点
农民工的城市流动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经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也是农民流动的三十年多年。[1]283经过三十多年的城乡互动,农民工城市融入展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第一,农民工的外在表现已经与城市人趋同。长期的城市就业与社区生活,使很多农民工的语言(甚至是方言)、着装、娱乐方式等社会符号已经与城市居民趋同而难以区分,现在已经很难简单地从言谈举止、衣着打扮上区分谁是城市人,谁是农村人。更有甚者,许多农民工对城市当地方言也学得颇为神似。比如在广东地区做小生意的农民工,在讨价还价时熟练使用粤语早已是人所皆知的,作者在上海的一次社会调研中,在与两位年纪四五十岁,来自四川一个小乡村的农民工交谈时,我们不但可以很顺畅地用普通话交流,更有意思的是,在他们的话语中还夹杂着明显的上海话尾音。
第二,部分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主动完成了心理融入。当前我国外出农民工有1.64亿人,其中约六成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中的大多数虽然户籍在农村,但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城市中度过的,土地已经远离了他们的生活,乡村生活对于他们早已不再熟悉。他们在社会文化积累、衣着、思想、业余生活等多方面,已经与城市青年人没有太多区别。上海一项针对农民工子弟学校学生的调研发现,绝大多数的小学生已经坚定地认为自己就是“城里人”。
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大多是因为单纯依靠土地收入不足以维持家用的被迫选择,城市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来说,在本质上与土地一样,是他们养家的手段或者场域,那么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城市就是自己的家,社会融入是他们自然生发的要求。
二、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推动力
需要明确的是,现阶段农民工城市融入新特点的显现,并不是一个一帆风顺的自然过程,而是经历了许多波折的曲折发展结果。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到21世纪之初,政府层面就出现了许多以限制农民工流动为主要指向的政策,甚至是歧视性的政策规定。[2]然而,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伴随政策导向的转移,农民工群体呈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城市融入的趋势,在城乡双方面都出现了许多有利于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社会环境和条件。
1.城市舆论更加成熟和宽容
近些年来,媒体对农民工群体的报道越来越显示出成熟和理性的特点。媒体中已经看不到把农民工视为城市异类的报道,更多的媒体人将农民工群体看做是需要保护的弱势群体而不断给予扶持和帮助。
很多城市的广播、电视等媒体,纷纷设立了以农民工为主要服务群体的专题节目,这些节目紧贴农民工日常生活的实际需要,在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宣传和保护作用。比如节目中的重要内容是教会农民工如何运用相关法律法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此外,媒体还通过自身社会影响力,在帮助农民工讨薪、帮助农民工子女入学入托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作者在杭州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在回答“如果自身权益遭到损害时,选择什么方式进行权益救济”的问题时,首选的是找老乡帮忙,第二就是找媒体曝光。由此可见,虽然地缘关系仍然是农民工日常生活的主要依托,但现代的城市媒体在农民工心目中已经有相当的影响力。以媒体为代表的城市舆论为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创造了相对宽松和良好的环境。
2.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互动更为频繁和谐
客观上讲,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盲目排斥基本绝迹。绝大多数城市居民已经不把身处城市看成是自己的优势,不会产生对农民工进入城市的排斥感。
前些年,由于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城乡生活质量上的差距,很多城市人在与农民工相处时展现出肤浅的优越感。他们会由于农民工对城市生活常识的缺乏、衣着打扮与城市主流明显脱节而表现出非常肤浅的歧视,并从言谈举止上对农民工有显而易见的轻慢。
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快,以学生毕业、工作调动等形式在大城市定居的新居民和外来者越来越多,纯粹的城里人和本地人所占比重越来越小,所谓的城市人对农民工自然也少了几分歧视,多了几分同情。尤其是当农民工的工作范围从建筑业扩展到家政、医护等与城市人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后,城市对于农民工接纳和认可程度的提高更为显著。
3.城市社区层面对农民工等外来群体的服务日趋务实
目前,在很多基层社区,面对农民工群体为城市建设的巨大付出,各地基层社区在工作中积极主动,开展了许多形式多样的服务农民工群体的活动。比如在天津市外来人口较为集中的尖山街道,多年来在工作中创造性地开展工作,通过“第二故乡教育服务基地”、“市民学校免收学费”、“农民工子女免费入托、入学”、“农民工子女夏令营”、“手拉手,与市民结对子”等系列活动,从实际出发,解决农民工群体的日常生活难题,为他们的城市融入创造条件。
而中央因势利导,在今年及时出台了《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意见》,首次从国家层面描绘了农民工参与社区生活的“路线图”,为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提供了制度依据和保障。这种政策环境的改善,有助于促进农民工顺利融入城市社区,拓宽农民工参与社区管理服务的制度渠道,不仅仅给农民工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便利,便于他们培养能力、适应社会,也为儿童的成长提供了很好的环境。
三、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新问题:核心矛盾凸显
城市内多年的共同生活,已经让城市人抛弃了那种盲目的优势和排斥,部分农民工已经从心理上做好了长期生活在城市的准备,农民工融入的社会环境和微观政策环境已经大大改善。但遗憾的是,在城市融入的道路上,一些制度性难题的存在,依然使得农民工群体无法真正实现城市化,并使得农民工群体展现出一些特有的二元性。
1.没有未来的人——教育不公平
学校教育对于一个青少年的未来成长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目前农民工子女在接受教育方面与城市孩子有很大的区别,而这种差异为未来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埋下了潜在的鸿沟。
从就读学校来讲,在绝大多数城市,公立学校并不接收户口不在本地的学生就读,即便有例外,也需要缴纳高额的借读费用,而这笔费用是远远超过普通农民工的收入水平的。所以,绝大多数的农民工子女就读于农民工子弟学校,而这样的学校虽然让孩子有书读,但从师资力量、教学资源、社会实践机会等方面,与公立学校的差异非常大,这是教育中起点的不公平。
从学生升学机会来讲,相对教育资源更为丰富的一些城市,农民工子女虽然能较为顺利地就读城市幼儿园、小学和中学,但一旦面对高考,严格的考试制度规定,学生必须在户口所在地报名参加考试。而由此带来的最大问题是,近年来由于教育改革的推进,全国各省在教育内容和教学重点上有很大差异,而高考考题也由地方做主。长期在城市生活的农民工子女,即便排除往返考试的种种不便,面对与学习内容存在较大差异的试卷,能拿到好分数的几率大打折扣。现实中,面对这种显而易见的考试结果,很多农民工子女只能把高中作为自己学生生涯的最后一站,而过早地进入社会。
从未来发展空间上讲,教育起点上的不公平以及教育关键环节的制度障碍,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工子女的未来发展。当他们还是学生的时候,由于没有高考的压力,他们的学习成绩对于学校的整体竞争实力没有影响,导致城市教师在教学中的差别待遇,以及学生对自己未来无望感下的自暴自弃。而城市学生的家长也难免担心这种消极的情绪感染到自己需要升学的孩子,进而对农民工子女与自己孩子的交往加以限制和干涉。这些因素由此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而身处怪圈中心的农民工子女在心理发展上也难免出现消极和悲观。即便农民工子女进入社会工作,由于知识储备的局限,让他们在职场的竞争中也处于劣势。在现实中最基本的表现就是频繁更换工作,但往往都是在底层游荡而没有上升的空间和通道。
由此,如果教育制度的壁垒不打破,将直接影响一代人,给新生代农民工带来难以想象的社会压力和负担。着眼长远我们应当明白,最根本的是保障新生代农民工或者在学校中求学的农民工子女尽可能少受到不公平的环境的影响,给学校中的孩子以城市学生同等的待遇和考学机会,使他们有一个灿烂的未来。
2.没有安全感的人——社会保障不完善
由于社会保障不完善,对农民工至少有两大影响。
第一,工伤保险的缺失让农民工遭遇到意外伤病时无所依。而一旦维权遇挫,会让原本发展很好的农民工生活一落千丈,在大多数情况下,可能只能是带着一身伤病回乡疗养。这种发展结果,受伤害的不仅仅是农民工的身体,同时连带受损的,还有农民对城市的信任、对生活的向往。
第二,养老机制的不健全让农民工始终存有“过客心态”。农民工绝大多数从事的还是一些技术要求较低、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作。而这些类型的工作对体力的要求很高。农民工在城市辛苦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一旦失去工作没有任何收入,必然无法在城市生活。农村或者土地才是他们最后的依靠。这种显而易见的政策缺失也造成农民工即便表象上融入了城市,也是暂时的、无根的。
对于城市社区或有城市户口的居民而言,他们也了解农民工群体由于种种制度的缺失,生活的质量会起伏巨大,而且,很可能今天是同事,明天一旦返乡,就再也不见。农民工群体的这种不可预见的移动或者被动移动的存在,妨碍城乡之间形成牢固的、长久的信任关系,由此成为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的障碍之一。
更值得关注的是,有学者相对尖锐地指出,比起第一代进城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稍高,因此职业期待也高,适应城市生活的能力也较强,一旦他们受到种种制度的制约而无法有效融入城市社区,势必对社会整体的协调发展有所阻碍。
四、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的“减法”与“加法”
从社会公平的视角分析,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实质上是对其劳动付出的合理回报,是不断提升农民工群体生活质量和水平的现实需求;从农民工群体的成长和发展视角分析,城市融入是生存方式变革的现实走向,是争取自身权益的必然要求。从政府的视角看,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每一个进步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调整,其中牵涉太多的利益调整和制度设计,需要全社会和政府的巨大努力。但不论从哪个角度分析,进一步促进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是中国未来顺利发展的必然要求。
但面对社会融入这个显然在短期内无法很好解决的问题,我们的思路应该是做“减法”而不是“加法”,找出那些现在真正能做的马上去做,为问题的真正解决“减负”。比如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融入就是社会融合中可以做“减法”的部分。
要指出的是,在社会生活中对农民工群体的不公正待遇依然很多,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并不是一个顺其自然的自发过程。我们之所以在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工作中采取“做减法”的态度,不是推卸责任和无视现实,之所以要减,根本目标是为了更好地分清楚根源,解决实质性问题。
1.城市融入程度的“减法”:融入状态不能理想化
加快城市融入目前看来的确是社会公平的必然需求,但是,需要明确的是,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需要认真考虑,什么样的融入程度才算我们的目标,笔者的意见是,对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期待不要脱离实际而过于理想化。
首先,对农民工心理融合程度应有宽泛的界定。关于心理融合的程度,从城市文化及乡村文化的不同视角去审视,是存在显而易见的区别的。从农民工相对熟悉的乡土文化来说,他们认为的融合更多是以乡村生活中的乡亲邻里关系为蓝本的,也就是只有深入了解对方生活的方方面面才算是融入,算是一个团体。这与乡村社会结构流动较小,本质上是熟人社会密切相关。但显然这种深层次的了解和融入,在社会流动较为迅速、生活节奏明显更快的城市社区,很大程度上是无法实现的。所以,对现阶段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心理考评,应该更宽松一些。
其次,就城市社区而言,需要进行心理融合的,绝不仅仅局限于农民工群体,社会各个阶层其实都面临这个问题。比如大学毕业生群体,他们在远离家乡的高校中完成了四年甚至更久的学习,从校园走向社会本身也面临融合的考验。目前在许多大城市周边村庄的蚁族,很大程度上就是部分大学生在社会融入中遇到困难,未完成融入的表现。即便另外一部分能力更强和更幸运的毕业生在城市找到了合适的工作,娶妻生子,安家立业,但当谈到家乡时,很大一部分人魂牵梦绕的,还是乡间的小道和妈妈的饭菜,很少有人说是高楼林立的大城市。所以,不建议在现实中过于突出农民工这个需要融合的群体,而更应当强调整合社会和全部阶层的融合。
2.政策主体的“减法”:杜绝城市新的二元化
正如前文强调,目前的城市文化已经足够宽容,虽然仍然存在对农民工群体的某种歧视,但其实质已经不是简单的身份排斥,而是整个收入较高群体对低收入群体,及其不是特别现代和科学的生活方式的排斥。歧视的核心是由于农民工群体整体经济水平较低,文化素质不高,在社会竞争中始终处于劣势地位。所以,消除对农民工群体的歧视,关键是提高他们整体生活水平和文化素养。授之以鱼的方式无法彻底解决农民工本身的成长问题,所以,应当给他们一个公平的机会和平台,在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条件下接受教育,共同在社会生活中成长。
针对这样的社会现实,在对待农民工群体融入问题时,地方政府应该以减法的思路推进,即将主要精力放在不断提升所辖范围内,所有低收入者的生活质量与水平上,而不要非常机械地再次划分为城市低收入群体与农民工群体分别处理,这样可以在城市内部杜绝新的二元化。在很多政策层面上,需要的是统一的政策,而不是差异化。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过多的针对性往往是一种对差异性的强化,是变相的歧视。而且,农民工群体的问题,在城市日常管理中,更多要按照城市低收入群体的标准来涵盖农民工的日常服务和管理工作。也就是说,政策出台是做减法,在城市部分弥合户口所有可能造成的城市新二元化。
淡化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促进融合。政策出发点上要平等,不要为了政绩凸显,人为划定城市的二元化,短平快见效益。这不仅仅是农民工群体的问题,而是全社会的问题,
3.发展中的“加法”:不断提升城市承载力
如前所述,即便有一个对农民工融入的理性认识,一旦政府真正把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融入视作自己应尽的责任,而在工作中淡化区别,服务于整个社会较低收入者群体后,可能最大的问题就是城市承载力的问题。面对突然多出的较低收入群体,对政府的社会服务和管理职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涉及教育资源、社会保障资金等具体问题时,更是如此。这就需要地方政府不断为自己的工作加码,如何在现有程度上统筹协调出更多资源,加强对用工企业的管理,扩大农民工的社会保险覆盖面,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这里的城市,既包括中心城市,也包括二线城市及城镇。农民工的未来发展只能伴随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才能真正解决。
所以,终归一句话,最根本的是不断提升城市承载力。而这里的城市,并不单单指中心城市,也指小城镇。只有在城市化过程中,不断发展小城镇,实现全面城市化,才是农民工完全融入的方法。
[参考文献]
[1] 赵树凯.农民的政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