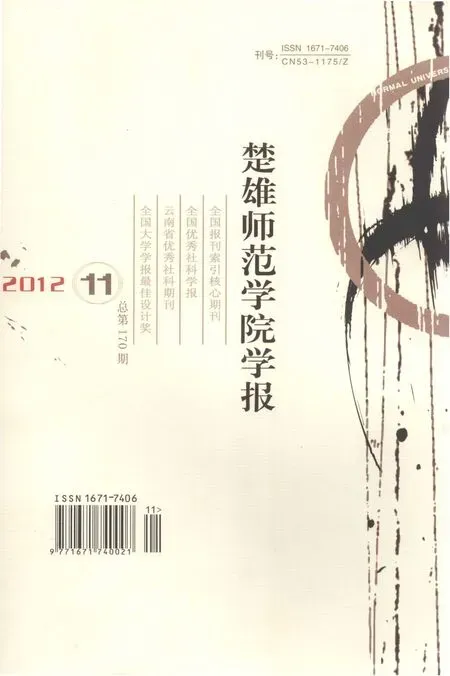李根源与崇谦*
杨朝芳
(云南大学,云南 昆明 650091)
李根源 (1879—1965年),字印泉,又字养谿、雪生,别署高黎贡山人,永昌府腾越厅九保 (今属梁河县)人。1898年永昌府试考中秀才,1903年考入云南高等学堂,1904年考取云南第三批日本留学生,入东京振武学校,四年后又进入日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1909年8月毕业,参与著名的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创办工作。他是云南辛亥革命的重要领导人,在昆明“重九起义”、云南军都督府建立、滇西问题的解决、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李根源与清廷楚雄府知府满人崇谦的交往,成为反映云南军都督府民族政策的有力例证,受到社会各界的称道。
一
崇谦 (1866—1935),字仲益,又字益三,号退葊,雅尔湖瓜尔佳氏,正红旗满洲荣泰佐领下人,[1](P642)自署长白①今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清末曾置长白府。见崇谦《楚雄县志序》,载崇谦、沈宗舜纂修《宣统楚雄县志述辑》,该志多处均署“长白”,见杨成彪主编《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楚雄卷下,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958页。有资料称崇谦为“长白山人”,似不尽准确。,山西蒲州协副将星舫次子。②宝铎《略历》,载崇谦《退葊诗稿》,1页,钞本,藏云南省图书馆。1866年 (同治五年)9月初十日生,③崇谦记,宝铎注《宦滇日记》(节录),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辑《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83页。1879年 (光绪五年)由文生员遵例报捐笔帖式,1881年 (光绪七年)12月选补礼部笔帖式,1885年 (光绪十一年)中式乙酉科文举人。1901年 (光绪二十七年)7月选授云南南安州 (今双柏县)知州,1902年 (光绪二十八年)到任,之后历任云南善后局收支文案、通海县知县、东川府知府、釐金局提调、盐井渡釐金督办、楚雄府知府等职,宦游云南10年,称为“威楚”(楚雄旧称“威楚”)公。“善诗文书画刻印,凡清篆篆书八分行草,无一不工。在滇关防,多出计划。所至均有墨迹。”①宝铎《略历》,载崇谦《退葊诗稿》,1页,钞本,藏云南省图书馆。“工诗、文、联语、书、画、清篆、刻印。”②宝铎《略历》,崇谦记,宝铎注《宦滇日记》(节录),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辑《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82页。“勤于民事,所至有声,尤长听讼。素慎取予,独标廉洁。”③邓之诚《滇语》卷四,人物,1页,1942年,稿本,载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日记》(外五种),第八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邓先生与崇谦之子宝铎交往甚深,自云《滇语·人物》“凡得五十二人,皆深知其人,或与之稔者。”其文笔“有略似六朝人处”。见邓之诚遗作,邓瑞整理《五石斋文史札记》(六),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2年4期,127页;《五石斋文史札记》(五),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2年3期,121页。著有《宦滇日记》46卷及《南安宪纲》、《东郡识略》等书,主持纂修宣统《楚雄县志》12卷。辛亥革命后改姓黄氏,入籍楚雄,任楚雄自治局名誉总理,闲居府署西院。1912年 (民国元年)10月回昆明,寓南门外南校场头道巷。1913年乘滇越铁路火车回到北京,冠汉姓关。之后寓居天津,开办公司,经营煤窑、煤铺等。1935年 (民国二十四年)因病去世,享年70岁。
云南辛亥革命爆发之初,由于消息隔阂,信息不通,“排满”传闻甚嚣尘上。新成立的云南军都督府民 (种)族政策并不明晰,军政府称“大汉云南军政府”,对外发布《滇军政府讨满洲檄》,④载上海《民立报》,1911年11月26日 (旧历十月初六日),见曾业英编《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87—90页。以1907年章太炎《讨满洲檄》⑤《民报》临时增刊《天讨》,1—8页,见《民报》合订本 (二),科学出版社影印,1957年。及武昌首义初期黎元洪发布的《中华民国军第十三章檄告天下文》[2](P625—632)为基础,略加删减改动而成,表现出了较为偏激的“排满”革命和狭隘“民族建国主义”思想。都督府大楼名“光复楼”,全省悬挂“汉”字白旗。军政府所发函电、告示、宣言、照会等,动辄以“誓灭胡虏”、“光复汉族”、“光复故土”、“人心思汉”为号召。原《云南日报》也改名为《大汉滇报》,成为军都督府的机关报,⑥民国元年 (1912年)2月改名为《云南政治公报》。“排满之说更烈”。⑦崇谦记,宝铎注《宦滇日记》(节录),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辑《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85页,88页。以下引自该文及宝铎注文的不再注明出处。云南布政使正白旗汉军世增 (益之)、顺宁府知府镶红旗满人琦璘等被杀。⑧《清史稿》“列传二百八十三”·“忠义十”有二人传记;吴庆坻修,金梁补《辛亥殉难记》亦有记载,民国二十四年刊本,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八十二辑,台北文海出版社。临安 (今建水县)新军第七十五标第第三营管带赵瑞寿是满人,赵复祥等发动起义时就不通知。后赵瑞寿等见大势已去,拔营来降,但“因籍隶满洲”,“未便收纳”,“赠以大洋千元而去”。[3](P448—449)省城内外出现了“身着军服,手持枪械,借搜索逃官、满人为名,任意闯入民居官宅,肆行骚扰者”,以刚入伍的学生为多。⑨《禁将士肆入民居官宅搜索骚扰告示》,1911年11月,载成都《大汉国民报》1911年12月24日,见曾业英编《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99页。
面对如此形势,身为满人的崇谦如坐针毡,可谓临渊履薄,朝不保夕。9月初九日,腾越 (今腾冲)起义消息传来,崇谦“闻之心惊”,感慨“天下纷纷多事,岌岌可危,曷堪设想”,尚能为清廷安危操心。此后因“腾情形甚迫,不胜惶惧”,省城兵变,“闻之涕零”,消息不佳,恐难见容,“拟以身殉”,完全陷入了如何保全身家性命的恐惧之中,笼罩着焦灼、惶急的阴霾。如“不胜焦灼,倘为世所不容,拟命玉琴 (崇谦侍姬)将六儿 (指‘六曾’,即宝铎)携逃命,夫妇偕殉。而六儿又不忍离,全家尽哭,是将全家同殉而已,伤哉!”“风声甚恶,心焦万状。”“是夜心颇焦灼。”“风声仍属不佳,阖家焦灼无已。”“全家坐守未眠,并预备署后逃避之路。”“焦闷万状”,等等。他压下了省城兵变的消息,仅宣布腾越兵变,决定以保护百姓和维持社会安定为主意。他赴议事会召集城内绅士,调集团兵,防守城池。9月12日,接到新成立的军都督府致各府、厅、州、县电稿,要求各地官吏照常办事。崇谦立即与大理方面联络,商量如何回复军政府。这一天,他还看到了军都督府致各道、镇的电文,声称“李制军 (指清廷云贵总督李经羲)已在议局率司道办事”,这对他无疑是一个较大的安慰。于是调团点团,抚辑营兵,成立保甲,宣布条规。但随后几天,消息更加隔阂,传闻蜂起,崇谦如坐针毡,担心革命军难以相容,于是召集士绅谈话,宣称要自杀殉清。士绅们议论纷纷,希望他保境安民,并提出如果时局长期不能解决,就请崇谦出面组织临时民主政府,并派士绅在崇谦出行时前后围护,保护他的安全。为了自救,保全身家性命,17日,崇谦以楚雄县议事会、劝学所的名义,致电省谘议局议员李子通,投石问路,“借探省城消息”,强调自己“深明大义,会绅竭力经营,……现在人心安定,即悬旗庆贺,全体欢欣,商学各界,均各照常。”几天后再以楚雄县议事会、劝学所暨绅商学界的名义,致电云南军都督府暨参议院,声称都督府电令崇谦等仍旧供职,“仰见兼容并包,钦佩无既。崇府亦仰体德意,会同绅等,昼夜宣勤,不辞劳瘁,以维公安。刻下人心大定,居民安堵,深赖崇府之力。窃念崇府到滇以来,历任南安、通海、东川各州县府,总以爱民为宗旨,故所至有声,口碑载道。莅楚三年,实心实政,七属绅民,无不感戴。此次闻省宣布独立,既表同情,毫无疑义,似此贤吏,虽在汉员中亦不可多得,谘议局员,均可询证,非绅等之私见也。在崇府部署后,即欲避位让贤,退归农牧,因绅民等再三泣留,故尔中止。现在省军西上招安,纪律严明,沿途称颂。维我楚民,知识浅陋,均以崇系满人,代为担忧,致生惊懼。绅等宣布我军政府大德优容,既蒙录用,自与同胞一体相待,解释群疑。然恐宵小狎侮,轻举暴动,累及治安,敢请我军都督府参议院,俯念地方重要,明白电示,以靖人心而慰民望。并请电告来楚官兵,到境晓谕安抚。”10月初四日,崇谦看到了军都督府新委任的楚雄府知府黄彝致楚雄自治局的电文,只好商量另找房屋居住,收拾行李衣箱,焚烧相关公文资料。初六日,得知顺宁府知府满人琦璘被杀,“兔死狐悲,深为惋惜”。楚雄地方也发生了佃户要求减免地租、军人宣言排满等事件。
18日,李根源临危受命,扶病以“云南陆军第二师长节制迤西一带文武官吏西防国民军总统”身份,率军前往大理,处理滇西问题。途经楚雄时,军队进入知府衙署,崇谦只好让眷属躲到轿夫老谭的破屋中。由于大量军队在衙署出入无忌,崇谦担心遇到“不测”,衙署后院及轿夫破屋均无法躲藏,只好出署逃往绅士左济生家,眷属逃往门生宋元德家。但左济生极为恐惧,不敢收留,并下了逐客令,宋元德住处的房主也不敢收留。崇谦无奈,逃往自治局,并将眷属也接到自治局安置,儿子宝铎由其老师倪谦吉带回家中躲藏。到了夜半,李根源副官蔡自煇因为父亲受过崇谦的照顾,带兵持枪,四处寻找崇谦表示感谢,为崇谦所误解。“势甚不测”,议事会副议长王建章与士绅张凤诰将他藏匿在自治局南厢房床下。蔡自煇等人走后,崇谦将眷属送往自治局局丁李万家,自己化装为团兵,随哨弁王维富及团丁四人,假装出外巡城,从东南城墙的缺口处爬出城外,打算逃往荷花村王维富家。半路上,因王维富有事回城,崇谦与团丁许光亮、许光前改往小东村许光亮家。“一路竭蹶而行,二许或牵或负,至时天犹未明,而心中忐忑,甚悔此行。”到后暂息于楼上草榻,“一夜未眠,奔彼虽疲,而万虑千愁,不能合眼。一经思及,中心如焚,前途如何?何堪设想。”许光亮与其父许学彦、兄长许光宣不断来陪伴安慰,但因有事在心,坐卧不宁,“每自言语,或绕楼徘徊,焦灼不堪言喻。又恐累及许家,拟明日定另逃避。然又思逃避无所,只好寻一自尽,回首妻儿不能相顾,日后如何归结?伤也何如?”可以说,崇谦的生命有如风中残烛,随风摇曳,岌岌可危。
二
但事情很快出现了转机,随着形势的发展,云南军都督府也在调整自己的民 (种)族政策。收到谦崇以楚雄县议事会、劝学所名义发来的电报后,9月23日,云南军都督府军政部回电:“来电悉。此次系政治革命,并非种族革命,不得妄生满汉意见。崇守、涂令(楚雄县令涂建章)均有政绩,理应力为保护,以为亲民者劝。除经电饬大理曲统领传谕所属军官,道经楚雄地面,妥为保护外。凡该属土著客籍亦应仰体德意,不得别生意见,致累贤良。电到仰该会即将电文印刷多张,遍为宣告。”①《致楚雄县议事会劝学所电》,载上海《神州日报》1911年12月11日,见曾业英编《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78页。崇谦记,宝铎注《宦滇日记》所载大致相同,惟文字稍异。同时通令全省,“满人琦守璘能识大义,首先赞同。自当以汉籍相待,一体任用。该处同胞,亦不得视为异族,胥泯猜虞。楚雄崇守谦,广南桂守福,若能来归,尤加优待。各属流寓满人,本军府亦必妥筹善法,以相安置,勿自惊扰。”②《军都督府等致各厅、州、县等电稿》,见《赵蕃遗稿》之一,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第十五辑,186页。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著《云南少数民族·满族》(修订本)引该电文,认为“重九起义”领导人能妥善对待满族官员和百姓,“没有发生民族间不幸流血事件。”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617—618页。同日致电大理陆军统领曲同丰,“此次反正,楚雄府崇守既表同情,且平日政声洋溢。希告我大汉军官凡经过楚雄地面,理应极力保护,不得别生意见。”军政部也致电崇谦,“该守莅楚,实心任事,本政府一视同仁,并无满、汉意见。已饬曲统领暨地方极力保护。该守仍当靖共尔位,勿生疑虑。”③以上两电载上海《神州日报》1911年12月11日,见曾业英编《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77页,79页。但崇谦似乎没有收到发给自己的电报,虽有曲同丰经过楚雄时对他进行了安慰,解释疑团,并向他借了300元钱后怱怱前往昆明。陆军方炳管带“见面颇为安慰”,并聚各队官兵演说,仍因种种事实与误会,发生了连夜逃亡事件。
李根源知道崇谦逃亡后,“甚不过意”,派士绅倪谦吉和王建章等找到许光亮家,宣布一定极力保护,并接他返回城内。这大大出乎崇谦的意料,“念及昨宵,伤定思痛”,“闻之心释,诚始愿不及此。”当晚,崇谦回到自治局,前往见李根源。李根源“甚道歉”,声称因其逃避乡间,一夜未曾安眠。于是颁布奖札,称“照得此次建义,拨乱反正,实以扫除专制,改造民国为职志。此固政治之革命,不杂种旋 (族)之问题,举凡汉回满蒙藏,以逮沿边苗夷诸族,其生息于中国者,皆中国人。方当共同组织,以建立我中国统一之民族国家。第为中国编民,义利必无偏畸,其各属官吏,身任地方,但当问其贤否,不当强生差别,果属循良之长,尤为崇奖所先。兹查楚雄府崇守谦虽出满洲,久官滇土,起家牧令,所主 (至)有声。迨守楚雄,尤多美政,绅耆黎庶,翕然称之,此在汉族之中,犹不数觏。方今整饬吏治,登进贤良,所宜首予旌奖,以示矜式。又查满蒙诸族之间,一切习尚,大抵与我同化,惟民族名籍,尚存别异,实畛域之未除者。前代编定谱牒,改易杂姓,所以泯种界之偏见,章同文之郅治。该守世长中土,服习礼教,应准改姓黄氏,取同为黄种之义,入籍楚雄,嫓昔人居颍之风。至该守在官,廉洁自持,民被其惠,为该属士绅所共认。兹既解任入籍,除由本总统呈请军都督府,从优奖给银五百两外,并由该属自治局公同酌议,拨送公产一区,为该守资生之具,以表我地方酬报之忱,用奖循良而劝来者。”同时颁布札令,任命黄崇谦为楚雄自治局名誉总理。新任楚雄府知府黄彝移文称:“遵即调查得大净室华严会寺产,坐落楚雄民东界大乌郎田一分,计二百七十工 (楚雄每三工为一亩),年收市榖租三十一石;又冷水阱新旧米康郎山地租,折银二十二两,应完楚雄县民赋秋粮二石五斗五升二合八勺;并坐落城内旧县街裁缺楚雄协专城汛署一所,以作卸任黄旧府尊资生之具。”云南军都督府军政部接报后转饬民政厅发给执照,出示晓谕,“阖省官绅士庶,即便一体遵照。”
这应是民国初年“五族共和”思想积极作用的表现,也是“五族共和”思想保护了部分满族官员和普通满人生命的例证。
由于政策的变化与明晰,濒临绝地的崇谦全家突然之间柳暗花明,死里逃生。李根源“不惟垂谅,而过誉余在楚声名美政。”心旌摇曳、死里逃生的崇谦不敢与人结怨,马上向闯入衙署的军人求情,甚至下跪。第二天,新任楚雄府知府黄彝到任,与黄崇谦联宗。黄彝原是崇谦旧友,相见甚欢。他接回眷属及儿子宝铎,暂居衙署西院。劫后余生,惊魂未定的崇谦病倒了,“左胁气痛”,“头昏气结、困倦思睡”,“连日气痛”,“又病”,“盖因自反正以后,忧伤惊懼,昼夜经营,劳顿太过之故。”闲居中的崇谦与当地士绅多有往来,并与黄彝过从甚密,受到黄的多方照拂。当士绅谢丹诰攻击崇谦入籍楚雄,“遍街肆骂,谓余非楚种,不认其入籍”,黄彝将李根源保护告示张贴,“如有造谣生事,即照军法从事。”稳定下来的崇谦开始关心清廷的命运并感慨万千,曾赋诗云:“莫问华清今日事,如今已是汉家朝”、“春色无情故,新年改故年。荣华今异路,爆竹好惊眠。……那堪至漂泊,天畔独潸然。”①崇谦《退葊诗稿》之《唾馀唫草》(选本),《无题口占》、《旧历辛亥除夕感怀》,4页,2页。他一面清算钱粮、税帐,移交各文册,一面与刚到楚雄的顺宁知府琦璘家人苑福交谈,了解到琦璘被杀及其家属现状甚惨,决定将其接到楚雄安置。当琦璘次子夔功 (乳名寿格)到达楚雄,“余阖家见寿格遭际异乡,均怆然泣下,怨人亦自怨耳。”之后琦璘夫人等到楚雄,住到次年6月下旬才离开。
崇谦的经历反映了民国初年云南军都督府民族政策的调整和演变历程,是“五族共和”思想积极作用的表现,也是“五族共和”思想保护了部分满族官员和普通满人生命的例证。
三
之后,李根源与崇谦的交往并未结束。
李根源到滇西后,南甸土司刀樾椿呈文请求改归原姓龚氏,“以复汉籍”,李根源“批准之,并为改樾椿名龚绶云。”②刀樾椿《南甸土司呈请改复龚姓文》,载李根源辑《永昌府文征》,文录,卷二十九,民十一,见杨文虎、陆卫先等《永昌府文征校注》三,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3012页。1912年10月,崇谦一家 (侍姬玉琴已去世)返回昆明,1913年乘滇越铁路火车回到北京。其子宝铎,约生于清光绪二十四年 (1898年),“当辛亥革命时,年十三岁”。因崇谦及胞兄吉甫两房中,“弟兄名之上一字均用宝字,小名均用曾字,上冠以排行。宝铎行六,故曰‘六曾’。”字振生,冠汉姓后名关振生。③宝铎为《退葊诗稿》所作《略历》,记崇谦“子宝铎,字振生”,则崇谦仅宝铎一子。云南省图书馆崇谦《退葊诗稿》卡片提要径署“关宝铎辑”。回京后事迹不详,惟可知与著名历史学家、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邓之诚先生交往甚深。据邓瑞先生整理之《邓之诚日记》,知关振生为邓先生家“抄书先生”。④邓之诚著,邓瑞点校注释《邓之诚日记》(1933年),载《民国档案》1998年1期,48页。《邓之诚日记》 (节录)1934年,载《民国档案》1998年2期;邓之诚遗作,邓瑞整理《五石斋文史札记》, (一)— (三十六),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2期至2010年3期。或即指邓之诚先生所养“为他编讲义、抄文稿兼陪他下围旗、聊天的‘清客’”。[4](P35)
邓之诚 (1887—1960),字文如,号明斋、五石斋。原籍江宁,生于四川成都,随父仕宦云南,“先后客滇十有八载”。在云南两级师范学堂读书时,与李根源先生是同学,“俱各年少气盛,豪迈不羁,咸抱经世致用之志,虽一文一武,而最称莫逆,至老而弥笃。”[5](P1326)曾任《滇报》社编辑、昆明第一中学教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李根源在北京任职时,当与崇谦、邓之诚、关振生等有所往还。1936年4月,崇谦去世逾半年后,关振生将崇谦所遗诗稿、集句辑校并附注,合为《退葊诗稿》。1954年4月,李根源为崇谦《退葊诗稿》题签,曰“崇太守遗稿”,①藏云南省图书馆未再提“黄氏”,亦不称“关氏”,殊堪玩味。1959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辑出版《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云南部分系经各方协助和李根源先生帮助找到的。”②《编者的话》,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辑《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ⅱ页。关振生将崇谦《宦滇日记》有关辛亥革命部分注释收入该书,当与李根源的帮助有关。
[1]秦国经主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七[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2]阳海清等编.辛亥革命稀见史料汇编[M].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7.
[3]谢本书等编.云南辛亥革命资料[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
[4]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5]陈清泉,苏双碧,李桂海,肖黎,葛增福编.中国史学家评传:下册[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