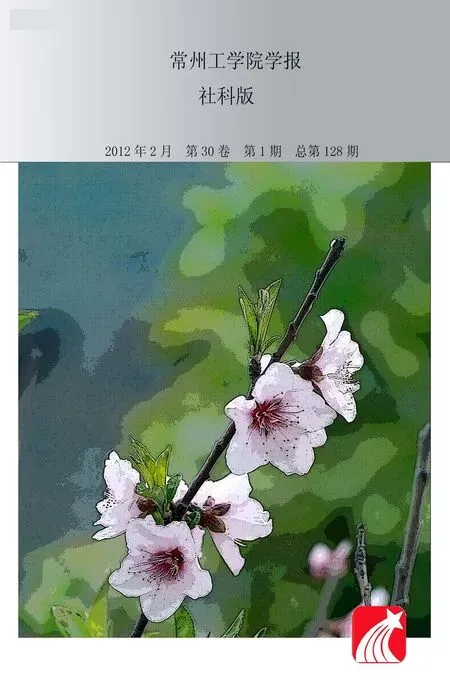典雅与风雅
——浅论士大夫与文人的不同雅化追求
李霞
(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北京 100075)
“雅”是我国传统士人的人生追求和审美理想。在我国浩瀚的词海中,以“雅”形成的词汇数不胜数,如:典雅、雅正、古雅、博雅、和雅、渊雅、风雅、文雅、高雅、逸雅、淡雅、闲雅、幽雅、安雅、骚雅等等。细分起来,如此多的“雅”有两种倾向:一是“典雅”倾向,讲求以修养和学识作为根基,是儒家审美观念和审美理想的产物,可以涵盖雅正、古雅、博雅、和雅、渊雅等;一是“风雅”倾向,不重人格的道德充实和内容形式的讲究,更多一种天赋自然气质,可以涵盖文雅、高雅、逸雅、淡雅、闲雅、幽雅、安雅、骚雅等。这两种不同的“雅化”追求是由士人的双重人格所导致的,士大夫追求的是“典雅”一格,文人追求的是“风雅”一格。
一、士大夫与文人:士人的双重人格
“文人士大夫”、“士大夫文人”,一直以来,“文人”和“士大夫”总是被连在一起使用,少有人加以区分,其内涵大体涵盖中国古代所有文化人、读书人。但是,笔者以为他们的内涵是有差异的,分别用来指称中国士人的两种不同人格。
士人阶层是我国传统的知识分子阶层,兴起于春秋战国那个动荡混乱的时代。特殊的时代背景,使其自产生之日起就具有“救世”与“自救”的双重追求。那些以“救世”为己任的士人在当时的存在状态是“游士”,他们无恒主、无恒产,游走于各诸侯国之间,朝秦暮楚。他们或为人臣,或为帝友,献计献策,辅佐各诸侯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救世”大志。而所谓士大夫则是士人的官僚化。秦王嬴政异军突起,统一六国,建立了崭新的中央集权大一统的政治制度。虽然,秦也建立了封建官僚体制的雏形,但是“秦帝需要的是一批称职的官吏”[1],而非以“救世”为己任的士人知识分子,且意图以焚书坑儒的专制手段结束“游士”时代,这使中国士人遭受了一次重创。继秦而起的汉朝,继承了秦的大部分体制,包括其官僚制度,但汉朝“察举、争辟”的取士方式,为中国士人“出仕”提供了机会,形成了所谓的“士大夫”[2]。中国士人的“救世”追求从此便以士大夫的形式得到了人格体现。因而,士大夫是一种政治伦理文化人格。
对于文人人格的形成需要从“文”开始探讨。“文”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文”之初是指人的一种侧重于道德伦理意义的行为态度。“对于行为说,德是发之于内,文是表之于外,提到‘文’是不能不联想到‘德’的。”[3]而文人要想脱离道德伦理的人格特征,首先有待于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的产生。“文学”之谓早已有之,但后世所谓之“文学”自汉始。钱穆《读文选》谓:“诗书以下迄于春秋乃及诸子百家言,文字特以供某种特定之使用,不得谓之纯文学。纯文学作品当自屈子离骚始。然屈原特以一政治家,忠爱之忱不得当于君国,始发愤而为此。在屈原固非有意欲为一文人,其作离骚,亦非有意欲创造一文学作品。”以钱穆先生之标准,既要非有意为之,又不能特以某种特定之使用,那汉赋称为纯文学应当之无愧,所以钱穆先生认为“汉代如枚乘司马相如诸人,始得谓之文人。其所为赋,亦可谓是一种纯文学”[4]。汉初裂土分疆,大封诸侯,梁孝王以其尊贵之位聚集了枚乘、邹阳、路乔如等一大批士人。他们清闲无事,优游自在,其所为赋,既非有意为之,又非特以供某种特定之使用,只为“游戏”,只为“自救”,当属“纯文学”。故他们身上已经具有了“文人”的质素,具有一种艺术审美文化人格。
二、典雅:士大夫之雅
“典雅”之谓出自《论衡·自纪》:“深覆典雅,指意难睹,唯赋颂耳。”曹丕评徐干:“辞义典雅,足传于后。”①刘勰在其《文心雕龙·体性》中把文章分为八种体格:“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其把“典雅”列为第一,最为推崇。他甚至主张“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沿根讨叶,思转自圆,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5]506。他还认为:“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5]505一语道破了“典雅”的思想根源,即士大夫的精神支撑——儒家思想。因而,“典雅”是儒家审美观念和审美理想的产物。
典雅之“典”,《尔雅》释曰:“典,经也。”郑注:“典,常也,经也,法也。”此正与“熔式经诰”相通。因此,“典雅”以修养和学识作为根基,与“古雅”“博雅”相近。朱熹《答巩仲至》认为“(作诗)亦须先识得透古今体制,雅俗向背”,要有“崇古”的追求。在儒学的观念当中,雅乐先声是先王所制。据《礼记·乐记》记载:“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乐而不流,使其文足论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所以,以“古”为雅,引得经,据得典,能模古拟古,古香古色,才称得“典雅”。“典雅”,要求品性高尚,学问渊博,即“诗难其雅也,有学问而后雅”[6]。“古雅之性质,既不存在于自然,而其判断亦但由于经验,于是艺术中古雅之部分不必尽俟天才而亦得以人力致之。苟其人格诚高,学问诚博,则虽无艺术上之天才者,其制作亦不失为古雅。”“虽中智以下之人不能制造优美及宏壮之物者,亦得由修养而有古雅之创造力。”[7]与其相反之“俗”为“近”,吴乔《围炉诗话》中“以唐、明言之,唐诗为雅,明诗为俗;以古体、唐体言之,古体为雅,唐体为俗;以绝句、律诗言之,绝句为雅,律诗为俗;以古律、唐诗言之,古律犹雅,唐诗为俗”,即以“以古为雅,以近为俗”作为自己区分雅俗的标准。
《诗大序》中谓“雅者,正也”。其“正”包括思想内容的“正”,而“正”又与“政”通,“言王政事,谓之雅”(《释名·释典》),也即“诗教”,所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②。“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③此为内容之“正”。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审美风格,“雅正”“和雅”等是以儒家审美观中的“中和”之美为根源的。“中和”之美源于儒家的“中庸”思想。所谓“中和”,即“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④,也即情感的表现要以理性加以控制,“要发乎情,止乎礼义”⑤。要适度,不能过,钟嵘批评嵇康“过为峻切,讦直露才,有伤渊雅之致”[8],意即要做到“温柔敦厚”⑥,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⑦。《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注“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言其和也”。另外,还要做到内容与形式的和谐一致,“文质彬彬”,要求文辞雅驯,“模经为式者,自得典雅之懿”[5]530,但又不可过于直白浅露和过于艰涩隐晦;审美价值与伦理价值要统一,要“尽善尽美”⑧,不可偏废,“中正则雅,多哇则郑”⑨。与其相反的“俗”乃是“过”,清代李清易《小蓬莱阁画鉴》:“学画须辨似是而非者,如甜赖之于恬静也,尖巧之于冷隽也,刻画之于精细也,枯窘之于苍秀也,滞钝之于质朴也,怪诞之于神奇也,臃肿之于滂沛也,薄弱之于简淡也。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学者其可忽视诸?”即说明了不可“过”,一过即变“雅”为“俗”矣。
因此,“典雅”讲求以修养和学识作为根基,有修养而有古雅之创造力;思想内容要“正”,“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符合中和之美,也即情感的表达要以理性加以控制,内容与形式要和谐一致,审美价值与伦理价值要统一。这正是以“救世”为己任的政治伦理化人格——士大夫人格的雅化追求。
三、风雅:文人之雅
风,本义指一种自然现象,如《庄子·齐物论》:“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号。”但在先秦的典籍中已有多种引申义,如“教化”之义,《尚书·商书·说命下》:“四海之内,咸仰朕德,时乃风。”如“风俗”之义,《礼记·王制》:“陈诗以观民风。”魏晋六朝之时,“风”用来指称名士风流,这是关于人的审美价值,《世说新语·赏誉》:“卫风韵虽不及卿,诸人倾倒处亦不近。”“戎子万子,有大成之风。”其他如“风采”、“风度”、“风姿”等都常见于六朝士人的人物品评中。这里的“风”均指人的某种内在气质的外在显现,审美色彩加强,伦理色彩减弱。刘勰《文心雕龙·风骨》:“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风”已属于审美范畴,乃是指诗文蕴含的情感所表达出来的艺术感染力,不同于儒家的伦理感染力。
唐代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有“典雅”一品:“玉壶买春,赏雨茆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荫,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杨振纲《诗品解》引《皋兰课业本原解》云:“此言典雅,非仅征材广博之谓。盖有高韵古色,如兰亭金谷,洛社香山,名士风流,宛然在目,是为典雅耳。”已经道出了司空图所谓“典雅”与刘勰之“熔式经诰,方轨儒门”的“典雅”之不同的特质:不同于儒士以正为雅的风范,其突出的是超凡脱俗、不染尘埃的审美境界。即如清人孙联奎所说:“壶有冰心,胸中那有俗气;胸无俗气,笔下那有尘氛。”[9]因而,司空图之所谓“典雅”已更倾向于“风雅”一格。
“风雅”根源于老庄道家,庄子因无人能够领会其“缪悠之说”而哀叹“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因“而今也以天下惑”而感叹“大声不入于里耳,折杨皇荂,则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于众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胜也”[10]。“名士风流”有别于儒士风范,其人格理想是:摒弃利禄,淡泊功名,脱俗超逸。与其相似的有“清雅”,《三国志·魏·徐宣传》:“尚书徐宣,体忠厚之行,秉直亮之性,清雅特立,不拘世俗。”“清”本指水的澄澈见底,也指空气的透明。《孟子·离娄上》记载楚《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经由老庄,“清”发展为指心灵的空虚澄明。《老子·十五章》:“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魏晋,“清”常用于人之品评,《世说新语》中比比皆是。曹丕《典论·论文》开始用于文学评论,其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故“其清脱之气出之,即具清雅之格”。明代胡应麟云:“格不清则凡,调不清则冗,思不清则俗。清者,超凡脱俗之谓。”[11]清代吴文溥《南野堂笔记》卷一记载:“不清则俗,俗则不可医。”《石涛画语录·脱俗章》云:“俗不溅则清,……俗除清至也。”其他还有“逸雅”,“逸”《说文》释为:“逸,失也。从辵兔,兔漫驰善逃也。”故“逸”有奔纵、隐遁、放逸、闲适等多种引申义。“逸”由全身远害、避世隐遁的社会学意义转变为不拘常法、超然放逸的审美意义,时间大致在东汉以后。魏晋品评,“逸”成为名士风度的重要内容,如曹丕《与吴质书》:“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后来用于品评艺术作品,其精神与魏晋品评人物的内涵一致,如王羲之:“望之惟逸,发之惟静。”⑩至唐,“逸”开始属于重要的审美范畴。至宋代黄休复,“逸”开始被视作最高的审美标准:“画之逸格,最难其俦。拙现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故目之曰逸格尔。”[12]这正是只为“自救”的艺术审美文化人格——文人人格的雅化追求。
总之,“风雅”正是以其超凡脱俗,飘逸纵恣吸引了无数文人,成为追求“自救”的艺术审美化人格文人的审美理想。与“典雅”相比,“风雅”不重人格的充实和内容形式的讲究,更多一种天赋自然气质,更具审美境界和审美趣味。正如徐复观所说:“其实乐的雅俗,在由其所透出之人生意境、精神,而绝不关系乐器的古今与中外,亦与歌词的体制无大关系。”[13]也正如张竹坡所说:“《红楼梦》与《金瓶梅》,同为通俗文学,但其境界不同,一具有诗化精神和雅的品格,一为一篇市井的文字。”[14]74-75与“风雅”相对之“俗”者大抵为仕途所扰,不能忘情于世务和功名利禄,不能做到如陶渊明之“悠然见南山”,不能远离尘嚣,精神境界不能达到超脱,如《带经堂诗话》:“汪钝翁(琬)尝问予:‘王孟齐名,何以孟不及王?’予曰:‘正以襄阳未能脱俗耳。’汪深然之。”[15]也即“王维经安史之乱的打击,险遭不测,之后虽身居高位,却‘俗’念已消,终日沉溺于佛经和山水之中。而孟浩然虽一生潦倒,却一直未能忘情于仕途”[14]50。没有“孤高”的个性,就不能达到超功利的审美观照。
注释:
①(三国魏)曹丕:《与吴质书》,见(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42,中华书局,1977年,第591页。
②⑤出自《诗大序》,见朱志荣:《中国古代文论名篇讲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页,第1页。
③(唐)白居易:《新乐府序》,见《白居易集》,中华书局,1979年,第52页。
④出自《中庸》,见韩路:《四书五经全注全译》,沈阳出版社,1997年,第35页。
⑥《礼记·经解》引孔子言:“温柔敦厚,诗教也。”
⑦孔子称赞《关雎》语,出自《论语·八佾》,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66页。
⑧出自《论语·八佾》:“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见(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八佾》,中华书局,1983年,第66页。
⑨出自《法言·吾子》,见李守奎:《扬子法言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9页。
⑩出自《记白云先生书诀》,见杨素芳、后东生:《中国书法理论经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页。
[参考文献]
[1]许倬云.秦汉知识分子[M]//许倬云.求古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2]于迎春.汉代文人与文学观念的演进[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
[3]季镇淮.“文”义探源[M]//季镇淮.来之文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26-28.
[4]钱穆.读文选[M]//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77:193.
[5](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注[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6](清)袁枚.随园诗话[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7]王国维.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M]//王国维文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8](南朝梁)钟嵘.诗品[M].张连第,笺释.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0.
[9](清)孙联奎.诗品臆说[M]//(清)孙联奎,杨廷之.诗品解说二种.孙昌熙,刘淦,校点.济南:齐鲁书社,1986.
[10](战国)庄周.庄子[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
[11](明)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2](宋)黄休复.益州名画录[M].何韫若,林孔翼,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13]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
[14]孙克强.雅俗之辨[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7.
[15](明)王士禛.带经堂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士大夫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