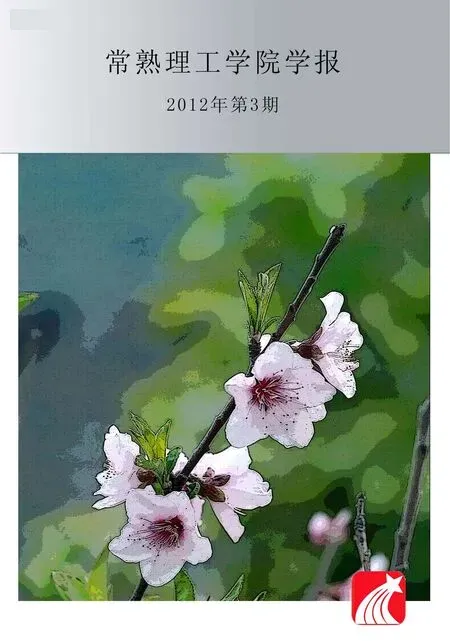从反事实条件句到绿蓝悖论——纳尔逊·古德曼科学认识论思想管窥
朱耀平
(苏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古德曼认为,哲学研究的第一步是区分什么是“有待澄清和解决的问题”,什么是“对问题的澄清和解决。”作为深受二十世纪上半叶盛极一时的逻辑经验主义思潮影响的哲学家,古德曼用于做出上述这种区分的标准是它们是否能够得到显明可见的经验事实的证实和支持。在古德曼看来,像“反事实”(counterfactual)、“倾向性”(disposition)以及“可能性”(possibility)之类的概念,在它们自身得到澄清之前,都不足以用来作为对它们之外的其它问题进行澄清的手段。其原因就在于在它们身上存在着太多的非经验的成分,在将它们背后隐藏着的形而上学幽灵赶走之前,是无法合理地把它们作为与实证科学的基本原则相容的科学概念来使用的。
一、“反事实条件句”的穷途末路
在以上提到的这几个概念中,与“倾向性”和“可能性”这两个概念相比,“反事实”这个概念的神秘色彩似乎更少一些。因此人们常常试图通过构造“反事实条件句”的方式来对“倾向性”或“可能性”的概念进行澄清。例如,我们可以将“物体K在时刻T是有弹性的”这样一个包含性质谓词的语句替换为下列这样一个反事实条件句:“如果物体K在时刻T受到一定的压力,那么它将会弯曲。”后面这个语句将前一个语句中的“弹性”这个具有神秘色彩的概念解释为“在受到一定的压力时会发生弯曲”这样一个可以通过经验直接观察到的现象。就此而言,它确实对前一个语句起到了澄清作用。
在古德曼看来,反事实条件句的这种表面上的成效,正是引起人们对反事实条件句产生浓厚兴趣的重要原因。人们期望能够仅仅通过把反事实条件句作为真值函项加以处理就能达到澄清某些困难问题的目的。然而,结果看来并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乐观。人们之所以在反事实条件句问题上倾注了巨大的热情,是希望它能帮助我们对象“某物K是否有弹性”之类的问题做出断定。具体方法是:在“如果物体K在时刻T受到一定的压力,那么它将会弯曲”这个语句为真的条件下,我们可以得出“物体K是有弹性的”这样一个结论;反之则说明物体K无弹性。但是,古德曼认为在这里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反事实条件句的后件并非单纯是由前件造成的,或者说,反事实条件句所断定的关系是否成立与前件没有提到的某些“初始条件”有关。例如,当我们说“如果那根火柴被刮擦,那么它将被点着”时,我们的意思是说,在那根火柴质量很好,很干燥,并且在它的周围有充足的氧气的情况下,从“那根火柴被刮擦”可以推导出“那根火柴被点着。”可见,严格来说,反事实条件句所断定的那种关系应该被看作存在于前件及其它描述初始条件的句子与后件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反事实条件句的初始条件进行界定,即对“有哪些句子必须与前件一起作为能够导致后件所说的那种结果的前提考虑进来”做出判断。
其次,就算导致结果的各种相关条件已经确定,反事实条件句所表达的前提与后果之间的关系也并非一种逻辑关系。例如,“如果那根火柴被刮擦,它就会被点着”这个反事实条件句表达的是这样一个物理学规律:“任何制作完好、足够干燥、处于充足的氧气之中的每一根火柴一旦被刮擦都会被点着。”但并非每个反事实条件句表达的普遍语句都是因果定律,而反事实条件句的真假则主要取决于它表达的普遍语句是否为具有普遍性的定律,于是我们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对定律语句与非定律语句进行区分。[1]38
古德曼认为这两个问题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
二、“倾向性”的流逝
古德曼认为,“反事实条件句”、“倾向性”与“可能性”等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对“反事实条件句”问题的探讨处处碰壁的情况下,不妨看看能否在“倾向性”或“可能性”的问题上取得突破。
表面看来,反事实条件句与表述事物的倾向性的语句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其实二者通常可以相互转换。假设W是一块木柴,我们通常认为“木柴W具有可燃性”与下列这样一个反事实条件句是等价的:“如果将木柴W加热到一定程度,那么它将会燃烧起来。”与后面这个反事实条件句相比,前面那个表述事物的倾向性的语句在形式上更加直接也更加简单,除此之外,看不出二者有什么不同。[1]59然而事实上表述事物倾向性的语句与相应的反事实条件句并不能完全等同。因为我们很容易找到一种关于事物的倾向性判断为真而相应的反事实条件句却为假的情况,例如在木柴W周围缺少氧气的情况下就是如此。[1]59为了消除二者间的不一致,我们不得不对原来的反事实条件句加上一定的限制性条件:“如果所有相关条件都有利,并且将这块木柴W加热到一定程度,那么它将燃烧起来。”事情变得复杂起来的原因在于,倾向性判断谈论的仅仅是木柴W本身的“内在性质”,而反事实条件句则还包含着对木柴W周围的情况的规定。必须看到的是,并不是只有像“弹性”、“可燃性”、“可溶性”等包含“性”字的词语才是性质谓词。象“坚硬”、“红”这样的词语虽然不包含“性”字,但同样也是性质谓词。只有像“发生弯曲”、“破碎”、“溶解”等对所发生的实际过程进行描述的谓词才被称为“明证谓词”。二者的不同在于,性质谓词谈论的是事物潜在的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明证谓词谈论的则是事物已经表现出来的可被直接观察到的情况。[1]61
但是,仅仅把性质谓词规定为潜在性或可能性是无济于事的,问题在于如何根据实际发生的过程对性质谓词做出解释。在这个问题上主要有以下两种不同的方案:
第一种方案是把性质谓词看作对某个事物的所经历的实际过程的某个方面的概述。例如说一个事物是“有弹性的”,就等于说“每当它承受一定的压力时,它就会弯曲。”但古德曼认为这种方案至少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缺陷:首先,这个方案会把“有弹性的”这个谓词指派给最坚硬的从来不处于能使它弯曲的压力之下的物体;其次,上述这个方案还忽视了如下这个事实,即某个处于一定压力下常常会弯曲的物体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不弯曲,例如当它的温度极低时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1]62另外一种方案的基本想法是,即使一个没有处于一定的压力之下的事物也能被称为“有弹性的”,只要它与那些已被证明是“有弹性的”事物是同类事物。换言之,如果在受到一定压力的事物中,属于且只属于K类的事物才会“伸缩”(即表现出弹性),那么,“有弹性的”这个性质谓词就对属于K类的事物都适用,不管它们事实上是否受到某种压力。古德曼认为这种方法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却并不容易。困难在于我们如何判定两个事物是否属于同一类别的事物?一方面任何两个事物都可以说是属于同一类别的事物;另一方面,没有任何两个事物是完全相同的,因此它们是否属于同一类别的事物始终是可疑的。[1]64
古德曼的结论是:想要用明证谓词来对具有神秘色彩的性质谓词进行说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甚至有可能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三、“可能性”的消失
与“倾向性”相比,“可能性”更加“不现实”。不过,幸运的是,“倾向性”与“可能性”可以相互转换。关于“倾向性”的谈论可以用关于“可能性”的谈论来代替,反之亦然。如前所述,与明证谓词谈论的是事物已经表现出来的可被直接观察到的情况不同的是,性质谓词谈论的是事物潜在的有可能发生的情况。这就是说,当我们说某物K在时间S是“有弹性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描述的是在时间S可能发生在K身上的一个虚构事件。
古德曼认为,上面这个说法反过来也是成立的:即任何一个有可能发生的虚构事件都可以用一个性质谓词来表示。如果物体K在时间S有可能会因为受到一定的压力而伸缩(即表现出弹性),我们就可以把物体 K 称为“有弹性的”。[1]72如果物体 L有可能因为着火而燃烧,我们就把物体L称为具有“可燃性”的物体,即我们可以把正在燃烧的物体和可能燃烧的物体统称为具有“可燃性”的物体。与“燃烧”这个明证谓词相比,“可燃性”这个性质谓词具有更大的适用范围,它不仅对正在燃烧的物体适用,而且也对目前没有燃烧但有可能发生燃烧的物体适用。看来,关于事物的可能性的谈论完全可以用关于事物的倾向性的谈论来代替。实际上,关于可能性的谈论并没有超出现实世界的范围,“通常被我们错误地当作现实世界的东西只不过是对它的一种具体描述,而被我们错误地当作可能世界的东西实际上只不过是用另外一套术语对现实世界所作的同样真实的描述。”[1]74因此,与莱布尼茨把现实世界看作是多个可能世界中的一个相反,古德曼认为所有可能世界都潜伏在现实世界之中。这样一来,长期以来困扰我们的“可能性的幽灵”总算被我们赶走了。[1]76
古德曼认为,“倾向性”和“可能性”的问题,说到底就是如何从明证谓词出发进行“投射”(project)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一个关于如何从象“燃烧”这样的明证谓词开始,定义一个象“可燃性”这样的性质谓词的问题。性质谓词与明证谓词的不同在于前者具有更大的适用范围,它既可以用来描述正在燃烧的物体,也可以用来描述未燃烧但有可能燃烧的物体。[1]75不难看出,从明证谓词出发进行投射的问题与从已知推出未知,或从过去推出未来的问题并没有实质的不同,“倾向性”问题与归纳问题看来是相同的问题。实际上它们不过是下面这样一个一般性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即如何从一个被给定的一系列事例中推出更广泛的事例。[1]75可能性的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因为向倾向性问题的转化而消失,因为倾向性问题与长期困扰我们的归纳问题或投射问题一样,都是有待解决的问题。
四、绿蓝悖论
归纳问题是“哲学家的老朋友和老敌手”,特别是自从休谟发表了对这个问题为人们所熟知的看法以来就更是如此。对于作为经验主义者的休谟来说,世界上只有两件事情是确实可靠的,一是“经验”,二是“逻辑”。而基于对已经发生的经验事实的归纳所做出的预测既不是对经验的表述,也不是经验的逻辑后果,因此它的正确性或可靠性始终是成问题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预测都是同等可靠或同等不可靠的。预测仍然有好的预测与不好的预测之分。根据休谟的看法,只有建立在事件的重复所造成的心灵习惯的基础上、并且与过去的规则性相符合的预测才是正确的。古德曼认为休谟在这个问题上的不足在于他没有看到这样一个事实:有些规则性现象能够形成那样一种习惯,有些则不能;建立在某些规律性现象之上的预测是正确的,而建立在另外一些规律性现象之上的预测则是错误的。因此,古德曼认为休谟并没有完全解决如何为归纳和预测进行辩护的问题。
古德曼认为,归纳的正确性来自它与归纳的一般规则的一致性,而一般规则的正确性则来自于它与被认可的归纳推理的一致性。“如果我们所作的预测符合归纳的一般原则,那么它就得到了辩护;反过来,如果归纳的一般原则与被认可的归纳实践符合一致,那么,它也就是正确的。”[1]82
就象演绎逻辑关心的主要是命题之间的关系,而与它们的真假无关一样,归纳推理关心的也主要是各个命题之间相对可证实的关系。因此,如果命题S1能够证实命题S2,那么问题就在于如何对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界定。根据我们目前的“证实”定义,如果两个相容的证据能够证实两个不同的假设,那么,这两个证据的合取应当能够对那两个假说的合取起证实作用。现在假定我们有E1和E2两个证据,证据E1是“事物B是黑的”,证据E2是“事物C是非黑的。”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我们目前对命题之间的证实关系的界定,E1能够证实“所有的事物都是黑的”这样一个假说,而E2则能够证实“所有的事物都不是黑的”假说。这样一来,两个相容的证据就证实了下来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假说:“任何事物都既是黑的又不是黑的。”这种荒谬的结果意味着需要对“证实”的定义进行彻底的修改。实际上,某个给定的证据所证实的,并不是把它作为孤立的子项加以普遍化所得到的假说,而是在考虑到所有证据的前提下所得到的假说。“证实”的定义应该根据这一点进行修改。
但是,不幸的是,即使经过这样的修改和完善,我们仍然没有摆脱“一切证实一切”的幽灵,古德曼所说的“绿蓝悖论”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绿蓝悖论可以表述如下:假定在某个时刻T之前,我们观察到的所有宝石都是绿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观察将支持下列这个假说H1:“所有的宝石都是绿的。”现在让我们引进一个新的颜色词“绿蓝”(grue)并将它界定为:某物X是绿蓝的,当且仅当,我们在时间T之前观察到X是绿的;或者我们在时间T之后观察到X是蓝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时间T之前观察到的宝石都是绿的这一事实可以同时用来支持假说H2“所有的宝石都是绿蓝的”。然而,当我们预测在T之后将被发现的某一块宝石的颜色时,根据H1得出的预测是:那块宝石是绿的;而根据H2得出的预测是:那块宝石是绿蓝的,因而是蓝的。显然,这两个预测是相互冲突的,因而 H1和 H2也是相互冲突的。[2]24这表明,从“描述同一观察证据的陈述”出发能得出两个相互冲突的假说。这就是古德曼所说的“绿蓝悖论”或“新归纳之谜”。[1]91
导致绿蓝悖论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迄今为止观察到的宝石都是绿的,并不能保证我们随后观察到的宝石也是绿的,我们观察到的下一块宝石也完全有可能是蓝的(或别的某种颜色)。
五、消解绿蓝悖论的思路
绿蓝悖论表明我们对命题之间的“证实”关系的界定有着根本的缺陷。古德曼认为这个缺陷就在于人们把证实关系仅仅看作是证据与假设这两个方面之间的关系,而忽略了大量相关的背景知识对证实关系的决定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过去实际进行过的预测及其结果的记录”[3]85。
古德曼把“归纳”和“预测”看作是“投射”(projection)这个更广泛的概念的具体类型。因此,他把他自己的归纳理论称为“投射理论”。[3]83相应地,如何区分有效的归纳推理与无效的归纳推理的这样一个“新归纳之谜”也就是区分可投射假设与不可投射假设的问题。古德曼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借助过去实际进行过的投射及其结果的记录。为此他引进了一个新的概念即“牢靠性”(entrenchment)。[3]95一个谓词的牢靠性取决于它过去实际被投射的多寡;一个假设的牢靠性除了与它所包含的谓词的牢靠性有关之外,还应根据下列规则进行确定:H与H′相比,在其前件的牢靠性并不更差的情况下,其后件的牢靠性更好;或在其前件的牢靠性更好的情况下,而其后件的牢靠性并不更差,那么,H比H′更牢靠。这一牢靠性的标准就是古德曼用于区分可投射的假设与不可投射的假设的主要依据。[3]101
古德曼强调指出,根据上述这个规则对两个假设的牢靠性进行比较的前提是它们均“被支持”(supported,指“有正面事例”),并且均“未被违反”(unviolated,指“无反面事例”),并且均“未穷尽”(unexhausted,指“有未被检测的事例”)。[3]90一个假设如果不具备这三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那么它就是不可投射的。但是,一个具备这三个条件的假设并不一定就是可投射的。古德曼所关心的正是如何在具备这三个条件的诸假设中区分“可投射的假设”与“不可投射的假设”的问题。
根据上述这个规则,绿蓝悖论中的H2“所有宝石都是绿蓝的”是不可投射的,因而应被拒斥。这是因为相对于给定的证据,即宝石E1,E2,……En是绿的,H1“所有的宝石都是绿的”与H2“所有宝石都是绿蓝的”均为“被支持的”、“未被违反的”和“未穷尽的”,但二者相互冲突,而前者比后者更为牢靠。说H1比H2更牢靠又是因为H1和H2前后件基本相同,但H1中的谓词“绿的”比H2使用的谓词“绿蓝的”更为牢靠。这样,绿蓝悖论就被消除了。[3]94
在笔者看来,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迄今为止观察到的宝石都是绿的”既为“所有的宝石都是绿的”提供了支持,也为“所有的宝石或者是绿的,或者不是绿的”提供了支持,从而也就为“我们观察到的下一块宝石将是蓝的”提供了支持。因此,古德曼实际上没有也不可能真正消除“绿蓝悖论”。这是由归纳推理不同于演绎推理的本性所决定的。
[1]纳尔逊·古德曼.事实、虚构与预测[M].刘华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2]陈晓平.新归纳之谜及其解决[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1(5).
[3]Nelson Goodman.Fact,Fiction and Forecast[M].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
——论胡好对逻辑谓词的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