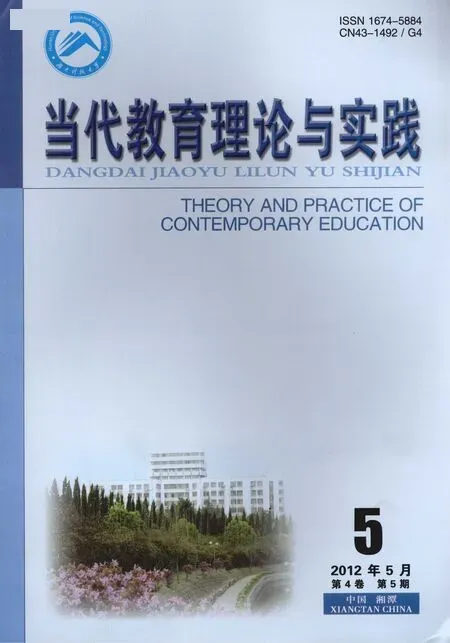论中西方古典爱情诗歌中的审美文化差异
曹文凌
(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湘潭411105)
论中西方古典爱情诗歌中的审美文化差异
曹文凌
(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湘潭411105)
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之一。有史以来,中外诗人们均为我们留下了无数歌咏爱情的美丽诗歌。由于中西方审美、语言乃至宗教等诸多文化上的差异,导致中西方古典爱情诗歌,无论从表现手法还是意象营造等各个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拟从比较中西方爱情诗歌的角度,简要分析其中反映出的中西方审美文化的差异。
中国古典爱情诗歌;西方古典爱情诗歌;审美文化;差异
爱情是人类最美好的情感,无论是在诗风尔雅的中国,还是情感热切的西方,爱情,始终是诗人永恒的主题。从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到莎翁笔下的十四行诗,都流露着中西方诗人丰富的爱情情感。而由于中西方审美、语言乃至宗教等诸多文化上的差异,导致中国的古典爱情诗歌同西方爱情诗歌相比,无论从意象营造与表现手法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等各个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拟从比较中西方古典爱情诗歌的角度,简要地分析其中反映出的中西方审美文化的差异。
一 中西方诗歌意象营造与表现手法的差异
中国古典艺术,从绘画到书法,均强调写意象征,突出深远的意境,诗歌也无例外。因此,中国古典诗歌始终追求并洋溢着一种含蓄朦胧的意境之美。这种含蓄朦胧的手法,早在《诗经》中就已屡见不鲜。如《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中那种“所谓伊人”的隐约,“宛在水中央”的朦胧,以及追求的具体内涵,都带有相当的不确定性,却又引人遐思,回味无穷。再如《静女》:“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诗歌描绘的是一位恬静美丽的女子,可是作品通篇都不见这位女子的真实形象,仅有“姝”“娈”二字,赋予读者无穷的的想象空间,让每位读者心中都可以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静女”的形象,营造出一种隐约美妙的意境。
至唐宋古典诗歌艺术高峰时期,文人士大夫在诗歌创作中吸收了诗经、乐府诗的精华,更是大量地通过运用典故来加重对诗歌含蓄朦胧意境的锤炼,强调以景抒情,爱情诗歌尤其如此。如李商隐之《无题·飒飒东风细雨来》:“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金蟾啮锁烧香入,玉虎牵丝汲井回。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诗人在此一连用了几个典故。开头一句“飒飒东风细雨来”采用了“梦雨”的典故,隐隐传出了生命萌动的春天气息,又烘托出女主人公正在萌发跃动的春心和难以表述的相思忧郁的心情;“芙蓉塘外有春雷”化用了司马相如《长门赋》中“雷殷殷而响起兮,声象君之车音。”纪昀说:“起二句妙有远神,可以意会。”所谓“远神”,即指这种富于暗示性的诗歌语言所构筑的渺远的艺术意境,一种难以言传的朦胧美;“贾氏窥帘韩掾少”则是晋朝贾充的女儿与韩寿的爱情故事;“宓妃留枕魏王才”则用了魏时甄后与曹植的爱情典故;诗最后感叹:“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将一种爱着想着却又极无奈的情感,淋漓尽致却又婉转曲折地表达出来,使诗歌具有一种动人心弦的悲剧美。即便风流潇洒如柳永,在与恋人分别时,也只是低叹一声:“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依依别情,凄凉秋景,正是情景交融的最佳佐证,其中典故来自欧阳修的“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相比之下,柳词之含蓄幽美,更是出神入化。
西方诗歌则恰恰相反。西方诗人更倾向于直率地把的所要表达的感情表现出来,直抒胸臆,毫无造作,言尽而意亦尽,回味的空间相对缩小了,但这样比较符合西方人的心理及思维特征。欧洲大陆面对大海,大海以其波涛汹涌,惊世骇俗而动人心魄,并赋予西方人开拓直露的民族性格。受其影响,直接地表达自己和赞美爱人成为西方文化中一种习惯。这种习惯表现在建筑中,就如人工喷泉,自下而上,一泄到底;表现在美术中,就像一幅幅古典油画,以精确造型,以光色现形。因此西方古典爱情诗歌也大都诗风浓郁而热烈。比如英国女诗人勃朗宁夫人的《请再说一遍我爱你》:
说了一遍,请再对我说一遍,
说“我爱你!”即使那样一遍遍的重复,
你会把它看成一支“布谷鸟的歌曲”;
记着,在那青山和绿林间,
在那山谷和田野中,如果她缺少了那串布谷鸟的音节,
纵使清新的春天披着满身的绿装降临,
也不算完美无缺,
爱,四周那么黑暗,耳边只听见
惊悸的心声,处于那痛苦的不安之中,
我嚷道:“再说一遍:我爱你!”
谁会嫌星星太多,每颗星星都在太空中转动;
谁会嫌鲜花太多,每一朵鲜花都洋溢着春意。
说,你爱我,你爱我,一声声敲着银钟!
只是要记住,还得用灵魂爱我,在默默里。
诗人用尽了“布谷鸟的歌曲,青山,绿林,山谷,田野,清新的春天,满身的绿装,鲜花,星星”等比喻来形容溢满心怀的爱意,而这一切都还不够,最后,她直接告诉对方:“还得用灵魂爱我”,这样的爱情,才是完美无缺。
再来看莎士比亚著名的十四行诗《你的长夏永不凋落》
我怎么能够把你比作夏日的一天?
你这个艺术品不仅比它可爱也比它温婉:
粗犷的风五月里把让人喜爱的花蕾摇撼,
夏天的赁期对日子来说又过于太短:
天堂般的眼睛常常闪耀着火辣的光芒,
使他金黄色的面容常常显得黯淡:
好看中的每一个好看该凋零都会凋零,
机缘和大自然会改变天然的过程,
但是你的永恒的长夏将永不会谢落,
你的好看的容颜也将永不会丧失,
死亡也不会夸口说你在他的影子里漂泊,
在不朽的诗行里时间与你一起生长。
只要人类还能呼吸,还有眼睛可以看见,
这首诗就将永生,并给你以生命。
诗人也在诗中运用了众多的比喻,直接将自己的爱人比作太阳、夏天等自然界中的美好事物,甚至这一切对形容她的美和表达他对她的爱意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这正是西方人热情、奔放、外露的表达感情的方式的体现:没有留白,却极具感染力,读来令人心胸为之豁然开朗。
当然,在中国爱情诗歌史上也有不少大胆吐露热情的作品。特别是一些乐府诗,如《乐府诗集·鼓吹曲辞一》的“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种热烈奔放的爱情宣言与西方诗歌有着神似之处。但在中国这种诗歌毕竟是少数,因为这种生死震撼的感觉不符合中国人的传统审美,含蓄蕴藉才是中国古典爱情诗歌的基本特征。
二 中西方诗歌人物形象的差异
爱情是人类社会最美好的感情,以爱情为主题的诗歌,必定要有爱人的形象。中西方古典时期的诗人均在诗中描写了众多女性的形象,她们都是动人的爱情故事的主角,诗人爱慕的对象。然而,他们在诗歌中所咏颂的女性形象,与他们营造的意境一样有着很大的差别。
在西方古典情诗中,诗人喜欢用《致……》作为诗的标题,而且歌颂的对象大都是真实的人物形象。如约翰·密尔顿的《致亡妻》就是写给自己的第二任妻子凯瑟琳·伍德科克,在这首诗中,作者把亡妻比作古希腊神话中的忠于自己的丈夫,自愿替自己的丈夫去死的阿尔刻提斯,表达自己对这位妻子深深爱意。诗人彭斯的诗歌《致约翰·安德森》中所描写的约翰·安德森就是诗人现实中的女友,彭斯采用一种完全写实的笔法,将诗中的主人公姓甚名谁、发色如何等一一道来,给人一种强烈的现实感,并用这种方式深深地打动了读者。
还有一类虽没有明确指向,但也实有所指。如彭斯的《一朵红红的玫瑰》描绘的就是前文所指诗人的女友约翰·安德森;叶芝的《当你老了》中的“你”就是诗人终生爱恋的一位激进的爱尔兰自治运动女领袖茅德·岗;拜伦的《雅典的少女》是一首热情奔放的爱情诗,诗人以动人的笔触描绘了雅典少女的美丽风姿,“无拘无束的鬈发”“墨玉镶边的眼睛”“野鹿似的眼睛”,这些比喻新颖独特,本已令人难忘,再加上一句贯穿全诗的“你是我的生命,我爱你”,直接而热烈地倾吐出对雅典少女浓郁的爱恋,具有强烈的震撼力,而这位雅典少女就是诗人第一次旅居雅典时结识的特蕾莎·居齐奥里伯爵夫人。
在这样些西方古典情诗中,诗人所描写所歌颂所爱恋的女性形象鲜明真实。也正是由于这种真实性和针对性,使西方女性在诗歌作品中整体呈现出一种浪漫热烈之态。
而中国古代的情诗蕴涵了很典型的中国东方古典文化的内涵,儒家文明的内敛和含蓄被看做是美德和修养的象征。严羽在《沧浪诗话诗法》中说,“言有尽,而意无穷”成为中国诗歌的语言的最高境界。因此,中国古代诗人都会在时间和空间上为含蓄留下很多空白点。他们并不直接描写赞美自己的爱恋的对象,却需要读者在言外去体味,思索,女性的形象寓于朦胧的诗意之中。对于诗人来说,形象的描述并不是重点,重要的是表述自己的某种情愫和隐射其中更深刻的含义。
以李清照《一剪梅》为例。词中沉溺在甜蜜爱情之中的女主人公思念着远方的丈夫,“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写出了夫妻二人的缱绻思绪浓浓情意,可是我们除了看到她“轻解罗裳,独上兰舟”的幽怨背影之外,对她的真实形象却一无所知;《诗经》里有着大量的情诗,其中《静女》《蒹葭》《关雎》等也都是典型的意象型情诗,这里作者或少年所爱慕追求的女性,都是模糊而朦胧的人物,没有具体的形象和鲜明的特征。
在西方,由于受宗教的影响,《圣经》的上帝造人、亚当夏娃的经典故事深入人心,人们将男欢女爱视为是正常而自然的现象,这就使诗人们放声大胆地颂扬爱情、炙热张扬地赞美恋人成为自然而然不足为怪的事。而在中国,由于受数千年孔孟文化的影响、男尊女卑思想的禁锢,妇女的卑微地位是不能登上“诗”这种大雅之堂的。加上儒家思想对“性”的桎梏,认为“性”是羞耻之事。因此中国诗人对爱情的抒发历来就比较委婉、含蓄、细腻而不张扬。
三 中西方诗歌审美观的差异
中西方审美意识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文学艺术和意识形态上。具体到文学、诗歌、戏剧、电影、舞蹈、绘画、雕塑、建筑,美育和价值观念等方面,都有太多的不同。
中国的哲学思想以中庸谦和为主,把天人合一,物我两忘推为至高。因此,中国的诗歌审美强调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静为美,而诗歌之美,就在于这种含蓄朦胧的静美之中,如中国园林中的泉声幽咽,迂回婉转,溪流潺潺;对于女性形象的描写,更多的则是将自己的意志隐喻其中,讲究个体形象与周围事物和环境的协调统一。诗人所描写的女子形象,往往与周围的景物融为一体,将诗人对伊人的爱恋和朦胧的景色交融在一起,亦如中国的水墨画,以写意抒情为主要目的,人物形象则是模糊遥远。
西方人的哲学态度却是物我对立。在对立思想的支配下,西方人很重视对事物的客观认识,重视物体本身的实体效果,在审美中更强调人为因素。“西方审美,曾经由‘理性、和谐、道德’的古典审美范式演变成‘唯艺术、唯情感、独立、个人主体性、自由’的浪漫审美范式。”这种浪漫主要表现在他们追求艺术、讲究艺术的执著,也表现在他们对人类情感的爱憎分明,特别是对男女之爱的推崇与乐此不疲。因此,西方古典爱情诗歌奔放激越,诗人会以高喊“你是我的太阳,爱情之火烧得我浑身焦灼”的方式直言不讳地表达心中强烈的情感。同时,西方诗歌审美也强调写实性,正如西方的油画一样,描写事物,要求惟妙惟肖,形象逼真地再现社会生活。因此,西方古典情诗对于女性形象的描写,通常也像油画一样,详细地刻画人物形象,而不渲染环境,体现人物的真实和感情的真切。
四 结 语
中西方的诗人们都以自己绝世才华创作出了优美的古典情诗,蕴涵了人类丰厚的情感,展现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语言魅力。中国诗歌讲求写意,追求风格上的和谐与统一;而西方诗歌讲求写实,追求情感上的热烈与奔放。中国人深沉,含蓄,以诗言志;西方人外露,热切,以诗言情。品读中西方爱情诗歌,不仅能够感受到中西方不同的爱情表达方式,更能体会到中西方在爱情审美上的差异,从而也能体会到中西方在整个文化审美观上的趣味异同。然而,总的来说,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不管是热情奔放抑或含蓄委婉,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爱情都是人类永不湮灭的文化主题,是闪耀着奇异光芒的永不凋谢的花朵。
[1]辜正坤.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2]黄杲炘.英国抒情诗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4]王佐良.英诗的境界[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91.
[5]向 熹.诗经词典[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6]伊丽莎白·朱.当代英美诗歌鉴赏指南[M].李力,余石屹,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7]寇鹏程.古典、浪漫与现代——西方审美范式的演变[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
[8]高 永.弥尔顿和他的三任妻子[J].世界文化,2007(2).
I06
A
1674-5884(2012)05-0151-03
2012-03-16
曹文凌(1969-),女,湖南益阳人,讲师,硕士生,主要从事中外文论与文学批评比较研究。
(责任编校 晏小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