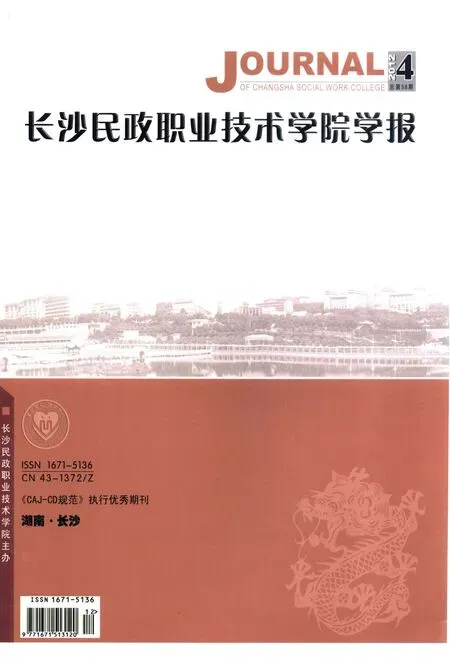论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
丁 杰
(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成功地实践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开创了一国之内不同社会制度、法律制度共存之先河,得到了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好评,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创造了宝贵的经验。1999年对澳门行使主权的恢复又是这一制度的有力实践。按照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的规定,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制度长期不变,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审判权。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成功实践表明,我国在特别行政区管理方面高瞻远瞩,进一步验证了不同社会制度下国家的统一、协调发展,为实现祖国的最终统一提供了有力依据,同时也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一、高度自治权的基本内容和特征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都在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这就是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自治的基本内容。从法理上讲,“高度自治”是一个相对范畴,尽管它描述的是特别行政区所享有的权力性质、范围和程度,但在单一制体制下,特别行政区的权力与中央的权力是一个有机整体,“高度自治”是相对于中央的权力来讲的,同时也映射了中央的权力。
(一)行政管理权
在传统的单一制体制下,中央政府通常掌握了大量的行政管理权,地方政府往往只是被动地执行中央的有关政策和命令。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根据“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原则,由中央人民政府授权享有行政管理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6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自行处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事务”。澳门特别行政区也有同样的规定。基本法没有采用列举的方法详细开列特别行政区享有哪些方面的行政事务管理权,这是因为行政事务的范围非常广泛,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很难列举清楚、列举完全的。然而政府对行政事务的管理又是不能有漏洞的,所以基本法在第16条中先概括地规定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事务管理权,这样就使得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出现新的社会事务时不至于由于基本法没有授权而无所作为、导致“权力真空”和社会混乱。
(二)立法权
特别行政区享有的立法权虽然在性质上也属于中国地方立法的一种,但是和上述中国内地一般地方立法十分不同。根据“一国两制”的原则,特别行政区保留原有的法律制度基本不变,全国性法律除非有明文规定,不在特别行政区实施,因而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权是实实在在的,是创新的,而不仅仅是执行性的。
与特别行政区享有的立法权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对于在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全国性法律,要由特别行政区在当地自行公布或者立法实施,而不是由中央直接在当地公布实施,这也是对特别行政区立法权的尊重。至于在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全国性法律,《基本法》在其附件三已有明确的列举。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征询其所属的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后,可以对附件三的法律作出增减,但所有列入附件三、在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全国性法律,都必须严格限制于国防、外交和其他不属于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的法律,因此这些法律在特别行政区的实施不会影响特别行政区立法权的行使。
(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特别行政区政府对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无管辖权,因此特别行政区法院对涉及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的法律事务也就不应有管辖权。香港、澳门基本法都对这种无权管辖的行为作了具体规定。
根据“一国两制”的方针,司法权属于特别行政区自治权的重要内容之一。《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9条规定的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中的“独立”的涵义不仅是指独立于特别行政区内的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而且更重要的是独立于中央和内地,即特别行政区成立后,中央不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司法,特别行政区法院除继续保持本地原有法律制度和原来对法院审判权所作的限制外,对特别行政区所有的案件均有管辖权。
独立司法权的一个重要内容和重要特征是特别行政区享有终审权。其实世界各国宪法都把司法终审权赋予本国的最高法院,这是一国司法统一的重要体现。即使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法院也从来没有享受过终审权,而澳门以前的司法对葡萄牙的依赖性更强。但是,中国恢复对香港和澳门地区行使主权、成立特别行政区后,并没有把司法终审权收归中央行使,而是授予特别行政区行使。可见,特别行政区的司法权是十分完整而独立的。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均设立了自己的终审法院来行使终审权,而特别行政区的其他一般法院则行使一般的司法权。需特别指出的是,司法权的独立还包括其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无隶属或业务关系。
(四)自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的权力
这也是特别行政区拥有的高度自治权的内容之一。香港和澳门地区是东西方文化荟萃交融的地方,两个地区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们是对全世界开放的社会,因此要维持其经济文化的繁荣和国际地位,就必须授权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以一定的自行处理对外事务的权利。为此,特别行政区有权依照《基本法》的规定或经中央人民政府授权自行处理有关经济文化等的对外交往事务,这是其自治权的一个重要方面。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我国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具有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高度自治权的授权性。香港和澳门基本法都是全国人大制定的,特别行政区地方国家机构因基本法的规定而享有有关职权。没有基本法的规定,特别行政区地方国家机构没有任何权力可言。第二,高度自治权的依法性。指特别行政区地方国家机构行使高度自治范围内的权力,必须在内容和程序上符合基本法和特别行政区的法律。第三,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相互制衡性。通过对权力的分类和分配,明确中央国家机关和特别行政区机关的职能和执掌,各司其职;同时,有关特别行政区的权力虽然含行政、立法、司法三类,但属于行政权的国防、外交等事务由中央管理,立法权又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权的约束,因此包含一定的权力的制衡关系。
二、高度自治权对我国单一制国家结构的影响
过去我们对单一制的理解十分片面,把它等同于中央高度集权制,认为单一制下中央必须尽可能多地把权力集中起来,这些权力不仅包括外交权、国防权、地方政府组织权、货币发行权等应该由中央政府统一行使的权力,而且包括一系列经济、文化、社会等十分具体的事务也要集中到中央统一管理。“一国两制”的提出与实施、特别行政区建置的设立、高度自治权的授予,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对单一制的理解,进一步充实了我国单一制的内容,使我国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更加丰富。
就高度的自治权而言,它的原始权力还是归于中央的,来源于中央的授权,它仍是一种地方权力的性质,它的合法性是来源于中央的。至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可以多种多样,地方权力的大小也是可以十分不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都在总则规定:“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这些规定明确了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表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处于国家的完全主权之下。正是如此,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权力虽大,甚至超过联邦制国的成员邦,但是它仍然没有改变中国的性质,没有改变我国国家结构形式,我国仍然是单一制的国家,总的国家结构并没有发生变化,只是更进一步发展完善了单一制的理论与实践,扩大了单一制的包容性,丰富了其内容。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实行单一制的国家中所没有的,由此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
三、我国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完善
(一)强化中央对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保障
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是中央授予的,中央不能也不会随意收回或限制,相反,中央为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实现,提供了多层次的保障。一是法律保障。宪法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作了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保障。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立法依据。基本法赋予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是我国政府在特别行政区贯彻和落实“一国两制”方针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央权力行使的基本界限,中央负责管理限于体现国家主权的事务。二是组织上的保障。全国人大在通过两部基本法的同时,决定在基本法实施时,分别设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基本法委员会的任务是就基本法中部分特殊法条的实施问题进行研究,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供咨询性意见,对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行使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三是人事上的保障。“港人治港”、“澳人治澳”是以“一国两制”方案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具体政策,是中央在香港问题上一贯奉行的基本立场。“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标准必须是以爱国者为主体的香港人、澳门人来治理香港。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的民族、诚心诚意地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澳门的主权、不损害香港、澳门的繁荣与稳定。“港人治港”、“澳人治澳”保证了中央授予的高度自治权掌握在香港永久性居民手中。因此在法律、组织、人事上加强保障,就能保证中央在基本法规定的范围内行使其职权,而不超越其规定,以及凡属高度自治范围内的事务,都由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自己管理,中央不加干预,即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自治权的“不受干预性”,同时,充分表明了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享有的高度自治权是真实的、可信的。
(二)完善中央对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监督
一是完善行政权的监督。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依照法律对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特别行政区政府的编制和提出的财政预算、决算案,以及特别行政区在外国设立经济和贸易机构,都须报中央人民政府备案。中央有权依照基本法的规定认定特别行政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超越了基本法的授权范围。
二是完善立法权的监督。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征询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后,如认为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不符合基本法关于中央管理的事务及中央和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可将有关法律发回,但不作修改。特别行政区对基本法提出的修改议案,须经特别行政区的全国人大代表2/3多数、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全体议员2/3多数和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同意后,交由特别行政区出席全国人大的代表团向全国人大提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如需修改,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法案、议案的表决程序如需修改,在特别行政区获得同意后,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三是完善司法权的监督。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判活动中所适用的法律,必须是基本法、不与基本法相抵触的香港、澳门地区原有法律和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中遇有涉及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的事实问题,应严格依照法律程序进行审理,其中对涉及基本法的法律解释必须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有关条款作出解释。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免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在中央人民政府的协助或授权下,特别行政区政府才可与外国就司法互助关系作出适当安排。总之,中央对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监督,是“一国两制”的必然要求。因此,完善监督,并不是对特别行政区行使高度自治权的妨碍,而恰恰是为了使其依照基本法的规定,更好地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基础上行使高度自治权。
[1]肖蔚云.论香港基本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王振民.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一种法制结构的解析[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3]周叶中.宪法[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4]张千帆.宪法学导论[M].法律出版社,2004.
[5]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6]潘敬国.试论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中的“港人治港”思想[J].党的文献,2004,(5):80-87.
[7]王景亮.从基本法的解释权配置上认识特区与中央政府的关系[J].法制与社会,2007,(5):505-506.
[8]李林.香港基本法规定的高度自治及其实践[J].四川统一战线,2007,(7):1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