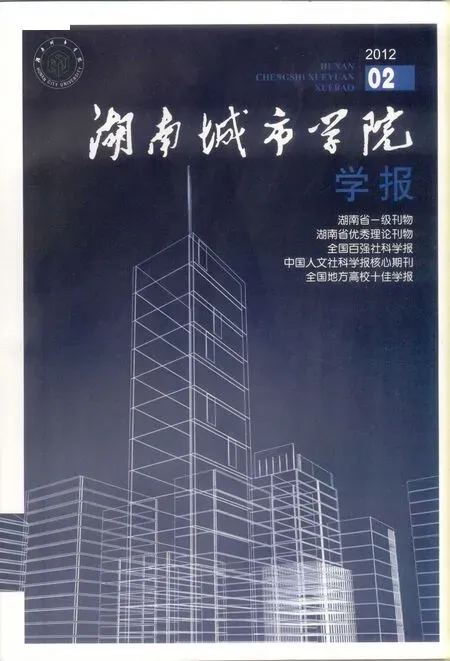杜夫海纳审美对象论中再现与表现的世界
杜志运,罗常军
杜夫海纳将审美对象和世界的关系问题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世界中的审美对象,它关涉空间(或空间的时间化)艺术和时间(或时间的空间化)艺术,一方面是审美对象的世界,它关涉再现和表现这两个世界。“世界”(world)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并非一项独立的课题,按照倪梁康的解释,“它意味着一个普全的(universal)现象,亦即普全描述的对象。”[1]511在胡塞尔那里,“世界”一方面涉及被感知事物的世界性结构问题,一方面涉及现象学还原的问题。前者适用于对意识的描述分析,因为世界提示一个知觉域,即此物总在其他事物为背景的前提下显现自身,某物直接或间接被给予都是作为世界中的经验,它的这种总体性视域使得部分与整体、在场与缺席等等这样的形式结构成为可能,同时,世界也不是静止在这样结构中,不是借这一结构为事物画上了边线,它配合时间和空间使知觉无限延展,使存在者自身的呈现被安置在世界之内,又使存在敞开。后者之所以关涉现象学还原是因为世界的原本性特征,即生活世界的现象学,生活世界作为与科学世界相对的原初被给予的世界,它是直接的、实在的、单纯的、非科学的、最值我们得信赖的世界,比如一个完美的圆,科学以生活世界为基础把圆理想化,而在生活世界中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经验,生活世界只是让意识发挥它应用的作用直接与这个世界相遇,杜夫海纳将审美对象的这种相遇归结为再现的和表现的两种方式。
一、再现的世界
普通对象显现总以世界为背景,它在世界中寻找它存在的根基,也就是说,普通对象又是生长在世界之中的独立,这种独立就不是完全的独立。审美对象不同于普通对象,它将“此在”(Dasein)纳入自身,即一种通过对“存在”(Sein)的领会而展开的存在方式,它自身带有一个世界。杜夫海纳认为艺术作品为自身开放,它即有赖于世界背景,又从中独立,它与自然发生关系,也与人类的普遍情感密不可分,它是一个再现的现实,同时又创造一个表现的现实,如同“道”,道化万物,创生自然,却又不干涉自然,周行不怠,独立不改,“审美对象并不为世界服务,它是自己特有的那个世界的本原。”[2]201
最先进入审美对象的世界是一个再现的世界。布洛克认为“在再现世界时,人类心灵活动——综合、组织、选择统一等——所作出的积极贡献,至少同感官从现实接受的被动印象同样重要。”[3]55在这里,再现至少不是一种机械的复制。在杜夫海纳的审美对象论中,再现的世界首先应当与作品的主题区分开来,艺术作品中的感性具有自身的统一性,这种统一致使形象得以完整再现,主题就是为作品提供统一性的契机。主题自身具有它的内在逻辑,它根据感性自身的规律和需求确定感性,并将其有秩序地呈现,这种呈现就是感性整体或再现世界的呈现,但主题的逻辑性并非审美对象把握的最终手段,毕竟审美对象不囿于逻辑,它是超越性的,再现的世界一旦把握到这种逻辑,认识到了主题,同时就又跳出主题,因为世界的本性是要求它自身的意义开放,走向表现的世界。
其次,再现的世界不同于实体性世界。作为实体性的作品世界类似于模仿,它一方面够不上现实的世界,一方面够不上再现的世界,作为实体性的作品世界是对现实世界的机械复制,必然丧失现实世界的活力,作为审美对象的再现世界虽然也在反应一个物的世界,但要使审美对象凸显就需要具备一种唤起自身存在的能力,即审美对象的再现世界需要突出物的重围,使自己周围的他物建立联系,通过这种扩张以使自身协调,不孤立,这样才能使再现的世界充实。也就是说,艺术作品中每一个被描绘的对象总是作为比自身更为丰富地存在着。
艺术家的工作在于删除和填补杂乱的表象,他以艺术地手法保留他认为可以保留的东西,使我们进入一个完整地可被接受地世界,对于审美对象再现的世界来讲,它里面还是包含有现实世界的诸多痕迹,有它的时间和空间。“再现的世界也以自己的方式拥有被感知世界的时空结构。”[2]206在杜夫海纳看来,再现世界的时空结构不仅能够展现世界,还能对世界进行客观的调配。时间和空间使再现世界对现实世界的模仿具备客观性,一位小说里主人公内心活动的开展是依据现实时间结构进行的,内在于作品的时间性和读者阅读的时间性一起出现,读者感受不到这两者有什么差别,因为读者在时间中阅读,小说的世界也在读者阅读的时间中被感知,作品中的因果关系和作品中意识自身地延续,都是对这种时间性的证明,正是因为审美对象时间的切身性才能使读者很容易进入作品,也使作品在时间中建立起再现世界的“厚度”。同时,再现世界中每一个对象都有背景,就空间而言,世界总是为对象设立一个定点,又布满了不定点,杜夫海纳特别以戏剧为例,认为戏剧作品的世界同时可以呈现于感官和精神,戏剧的背景勾勒出一个世界的“框架”,它由感官提示出来,并规划了它的意义范围,即保证了表演的确定性,又使对象具有世界,背景“它也总是某种方式的框架:它把它引出的这个世界限制在审美对象的范围,它既开放这个世界,又封闭这个世界。”[2]210
再现的世界是使审美对象出现的基础,由现实世界提供的审美对象的再现世界把背景推到后面,把对象拉到场地,目的就是不能像现实世界一样把所有的对象都淹没在世界之中,它只是从现实世界中抽出具有确定性的有意义的对象,再尽可能多地把再现隐匿,即使它具有现实世界的客观性,它也只是一个客观性的刻度,它不在数量和广度上与现实世界争抢,而在于再现上的非再现,即领入一个表现的世界,因而“在这个意义上讲,不是表现通过再现而表现,而是再现通过表现而再现,再现的对象通过表现的对象而出现。”[4]189再现的世界虽然具有一定的完整性和独立性,但审美对象仅仅拥有一个再现的世界并不能成为一个自为的存在,杜夫海纳这一思想的新颖之处在于他抛弃了再现的偏客体性特征,对再现世界做了现象学的还原,他是本着一种“描述”的态度揭示再现世界之所是。
二、表现的世界
从审美对象的显现方式上来讲,杜夫海纳处理再现与表现问题的新颖之处在于他推平了再现和表现的位置,它们不再是一种表现置于再现之上的关系,两者是平行的,并且是反置的,再现的对象通过表现的对象而出现,这是因为杜夫海纳始终处于“观赏者”的视角来看待审美对象,这一视角对于理解杜夫海纳和其他美学家如何看待该问题的不同之处相当重要。现象学强调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要想使审美对象的研究更具有普遍性就需要将它的视域转向观赏者,因为艺术作品总是置于观赏者的面前,即使是艺术家本人,当一件作品被创作出来,他也只能是这件作品的观赏者。传统美学对再现与表现问题的思考,之所以将再现理解为偏客观的,将表现理解为偏主观的,就是由于其视角是创作者的视角,他们在谈论再现的时候是创作论意义上的,回答的是艺术家基于什么而创作的问题,在谈论表现的时候,回答的是艺术家创作了什么的问题,这就往往会使表现陷入极端的主观性的情感宣泄论。
基于观赏者的视角,在审美对象的再现世界之中还不能见出一个独特的审美世界,再现再具有自己的品格也是基于对现实世界的描摹与构想,再现再具有想象和虚幻的特征,其深度也不能与表现相比,总之,再现的世界就是为了表现的世界。
杜夫海纳认为,再现的世界不是自足的、完整的、具有确定性的世界,但这也并不影响再现的世界称之为世界,“这种不确定性无疑是世界的本性:世界永远是躲躲闪闪的、无法综合的东西,因而有不断进步或像西绪弗斯那样不停地劳作的可能。”[2]212但审美对象作为各种对象中较为特别的一种,它能被我们真实可感且具备完整的意义就必须拥有一种确定性,否则无法捕捉,所以它在这种认识中如何获取自身的确定性或统一性成了必须面对的问题。在审美对象中,现实的、再现的、表现的东西都混在一起,但对于感知者来讲,再现的印象和表现的情感总有所不同,一个静物摄影作品所再现的历史或自然的场面,通过它的用光、构图、阴影、光圈、景深等一些列手段,成为表现的东西,或是高古卓绝的历史感,或是清新亮丽的自然感,表现的世界借以某种感性统一为世界,这种统一不是时间的,不是空间的,不是数量的,“它来自仅仅服从情感逻辑的内部凝聚力。”[2]216审美对象及其再现的世界通过自身的表现被认识,表现自身依靠情感来集拢,情感不是简单的反应行为,它具有自身的逻辑,是一种智性活动,但这种智性行为又不同于理性思考,情感虽然只能作为理性思考才能不至于让知觉停留在呈现层面,理性思考使感觉成为意识,但同时,理性思考也是对情感的麻痹,学识渊博的人感觉不是最灵敏的,而艺术则是为感情丰富的人存在的。情感介于生理反应和理性思考之间,它将表现推入一种透明的,毫无隐蔽的境遇,并把表现世界交付于我。
审美对象刚把自己交付于欣赏者时,欣赏者对它的知觉是混乱的,但它已经是一种感觉,它是即时性的,是获得的,“理解停止在外观,对外观进行整理和解释。感觉在超越外观行使思维功能时实际把握的是表现。”[2]418外观不能决定物的存在,但决定我们对物的把握,因为它是一种符号,自身不创造任何东西,如同物一样,它仅仅是其所是的东西,它具有一种完全暴露的外在性,所谓的物之隐蔽的东西不过是对我来说隐蔽的东西,它自己并不隐藏任何东西,这样表现就具有了它的领域。表现与外观相反,它是内在性的,属于主体的,它本身不是符号,而是发出符号,同时其意义又是内在于符号的,发出符号本身也就是发出意义。外观本身就是外在的,而表现是将自身外在化。从这种意义上讲,表现就是某东西的表现,或表现某东西。
表现的世界如同一种“气氛”,它可以延伸到其他对象身上,它在某种深度里开放,这种开放并非外延的开放,而是内涵的开放,因此,表现的时间、空间并不明确,它不像再现的世界那样可以见诸表象,以体验世界的时间和空间。表现得到不到完满的现实化,它自身潜在的那些不确定性不能穷尽,这是因为表现自身深不可测,表现不像再现那样拥有它的对象,表现的世界没有对象存在,它是先于对象而存在的,“它仿佛是破晓时刻,对象将在这个时刻出现,一切对这曙光有感觉的对象,或者如果愿意这样说的话,一切能在这种气氛中展开的对象,都降在这个时刻出现。”[2]218因此,审美对象的表现世界不是按时间和空间构成的,同它是潜在对象一样,它也是潜在的时间和空间,这种时空体验在作品所能再现的客观性中得以体现。再现的时间和表现的时间,如同再现的世界和表现的世界一样,再现的总是表述的、显现的,未经时间化的时间,而表现则是被经历的,时间化了时间。审美对象要有活力,自身就必须时间化,而不仅仅只停留在客观时间之中,审美对象的时间化以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建立一个表现的世界。这一点在音乐艺术中可以很容易辨识。音乐中的审美对象的客观时间停留在它的音符上面,演奏时的快慢、停顿和节奏都是对客观时间的讲述,这种客观时间总在某个历史时间之中,对于欣赏者体验的时间,即欣赏者体验的作品所要体现的时间,它不受历史时间的限制,它凝固在审美对象身上不动,它使欣赏者在接触审美对象的时候就感受到了审美对象的存在,而不是感受到它在说什么,这种时间性被杜夫海纳称作审美对象身上“真正的时间”,因为它在经历中根本上和存在联系在一起。另一位音乐美学家汉斯立克(Eduard Hanslick)却说:“玫瑰发出芳香,但它不以‘芳香的表现’为它的内容的;森林散布阴凉,但它并不‘表现阴凉’。我特别反对‘表现’概念。”[5]13他所反对的其实也正是表现所说的:音符不是事物的表现,而是事物本身,表现所做的事情是巧妙地将我和事物联系在一起。
总之,杜夫海纳所说的表现即具有超越的性质,又具有现实的一面。一方面,表现自身其实就是超越。审美对象就是对存在的超越,没有超越或者表现,审美对象无法获得意义。另一方面,艺术家内在于审美对象,使得表现能够从再现那里获得其现实性,因为再现也是一种对现实之物的模仿,它们保证了表现在艺术作品中可以被理解。表现的世界就是这样一个即和再现世界发生关系,又具有超越性的世界,表现世界确认再现世界的客观存在,同时又将再现世界作为自身存在的根据,并将自身开放。
三、再现和表现世界的区分
在杜氏美学中,审美对象具备再现和表现两个世界,前者是后者的现实性,后者是前者的可能性,两者互为基础,表现因再现构成一个统一世界,再现因表现成为一个活力世界,再现和表现的问题是艺术哲学的根本问题之一,北京大学曹文轩教授提出艺术并非既是“再现”又是“表现”的,艺术仅是“表现”的,这种看法与学术界对康德“物自体”以及叔术华“世界是我的表象”的理论批判分不开,曹文轩教授认为他们并不否定客观存在,而是强调主客体的统一,“大脑中的世界不是本体世界,而是一种非物质性的关于客观世界的映象”,艺术“它不可能是本体再现,而只能是现象的映象”。[6]偏重于艺术的表现方面是比较常见的一种观点,现代西方美学如表现主义、形式主义及符号论美学常有这样的见地,克罗齐认为“美学只有一种,就是直觉(或表现的知识)的科学。这种知识就是审美的或艺术的事实。”[7]19贝尔在他的第一假说中认为“一件艺术品的根本性质是有意味的形式”,即“意味”或“审美情感”来自于纯形式,同时形式又是审美情感的物化形式,两者互证,当贝尔对这一假说感觉到不满的时候又提出了第二假说,即“有意味的形式是对某种特殊的现实之情感的表现”,[8]67只是贝尔的“表现”概念最终走向了神秘主义。朗格基于符号学的认识,认为艺术作品是具有高度表现力的符号,“符号的重要认识价值就在于它们能表现那些超越了创作者过去经验的理念。”[9]452艺术是表象世界的表象,是第二次表象,它不等于客观世界,它只能是对客观世界的主观表现,人是出于一种情感动机委身于艺术。但这种表现性的情感论很容易遭到反驳,因其会使艺术堕入情感宣泄的泥沼,丧失其存在基础,审美对象必须避免观念论或实在论的陷阱,因此,杜夫海纳试图借助意向性理论来消除这一矛盾。
在杜夫海纳看来,再现在一般对象身上只是说明了它的世界,它是非构成性的,表现的艺术是被构成的艺术,表现与再现的不同在于表现是感性的表现。在表现之中审美对象超越自身为我们而存在,同时又自律地确定为自身,使对象被看(为我们),审美对象的这种矛盾违背了海德格尔存在论,它成为一种即不是主观或自我觉察到的那种内在于时间的存在,也不显示为此在于自由中的绝对特征,而是胡塞尔现象学的意向性中的“作为目的的主体和作为显象的客体即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东西,因为“客体既通过主体存在,同时又在主体面前存在。”[10]405在这种意向性理论的影响下,审美对象的主观性具有被知觉的和表现的双重性质,知觉在于观众的主观性,表现在于创作者的主观性;审美对象的客观性也具备自身独立的品格,它是将意义与显现同一为整体的自为的存在。“表现物和再现物之间的关系可以比作先验和后验之间的关系。表现物可以说是再现物的可能性,再现物可以说是表现物的现实性。它二者一起并连同给与它们形体的风格构成审美对象的世界。”[2]222总之,再现和表现相互奠基,再现的世界和表现的世界不是截然分开的两个世界。
一般意义上,表现需要再现才能成为表现,因为审美对象的表现是再现完成并成为符号的时候成为表现,再现已经把自己的所有意义都捐献出去,交给表现来处理。同时,如同表现需要再现一样,再现同样需要表现。在杜夫海纳看来,表现首先引起再现的对象,譬如,音乐中不再现什么东西,它的表现也不是由再现产生,但音乐在表现时又引起一些表象,它能在欣赏者的身上唤起一些组成这个世界的许多形象,音乐作品本身并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只是欣赏者的想象不耐音乐的诱惑,带领着他们从表现中生出一些再现以作为对表现的世界的补充,这种转换仿佛是一种外化。但是,外在不同于外化,单纯的外在只是应该被看见的东西,而通过外化则是看见的东西,外化关键在于它能获得一种自律,这种自律是外在在内在中构成自己并将自己外化得到的,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对音乐再现世界的推断,而表现同自为关系密切,自为是一种将自我外化的存在,表现显示的就是这样一个自为。
就表现物和再现物而言,表现物始终处于优先地位,它能改变再现物的面貌,并赋予其意义。再现物从表现那里获得的意义,不同于现实之物的意义,譬如一只老农的手,我们在乡下亲眼见到的这只现实的手,它和被一位优秀的摄影师反映到照片里的那只手是有差别的,那只现实的手可能在我们匆匆走过之后就再也不会出现了,但被一位摄影师所拍摄,它那清晰的皮肤纹路,突起的青筋,涌动的血液,粘在指缝里肥沃的泥土,加上片子的锐度,极好的曝光和背景处理,精彩的构图,它们身上全都浸透着情感,这幅作品比起那只现实的手来更容易让人心动,在这个再现物上它既有现实之物的那双劳动的手,又有表现物所传达的勤劳、沧桑、厚实和淳朴,再现就被表现笼罩在这样一种气氛下。
总之,“表现世界犹如再现世界的灵魂,再现世界犹如表现世界的躯体。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使它们形影不离。它们共同构成审美对象的世界,因而审美对象具有一种深度。”[2]226
[1] 倪梁康.现象学哲学概念通释[M].北京:三联书店, 2007.
[2] 米盖尔·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M].韩树站, 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6.
[3] 布洛克.美学新解[M].滕守尧, 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4] 张永清.现象学审美对象论——审美对象从胡塞尔到当代的发展[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6.
[5] 爱德华·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M].杨业治, 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2.
[6] 曹文轩.哲学:对再现论的全盘否定[J].百家, 1989(3).
[7] 克罗齐.美学原理;美学纲要[M].朱光潜, 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8] 克莱夫·贝尔.艺术[M].周金环, 马钟元, 译.北京: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 1984.
[9] 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M].刘大基,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10] Mikel Dufrenne.Intentionality and aesthetics[J].Man and World, 1978, 11(3-4):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