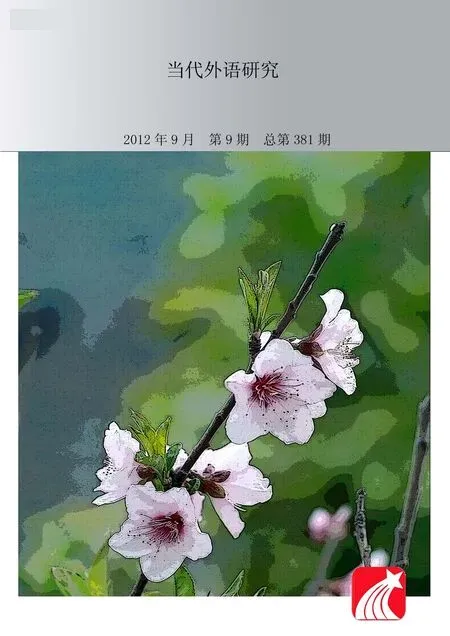富贵于我如浮云
刘宓庆
常言道“四十而不惑”。四十以后,伴随似水流年,人生感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对我来说,四十以后的近三十多年,感悟最深的是两句话,“做人要实在,做学问也要实在”。这两句话,可以引申为以下四点。
1. “翻译的实力就是翻译”
这句话是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吴兴华老师(1921~1966,诗人,北大教授)常常对学生们说的。这第一个“翻译”是指“译者”,第二个“翻译”是指“翻译的功夫”。吴老师解释说,“比如当木工。你连一根木条都刨不直,还当什么木工呢?”这两句话实际上影响了我一生。后来很多事情证明“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个“萧何”,对翻译而言,就是翻译实力。可以说,我一生特别注意练的功不是理论辩证,而是注重翻译的实在功夫,并从中引出理论体验——努力把“每一根木条”刨得溜溜光光、笔笔直直再说。
1996年的暑假很长。我在报上见到有欧盟总部人力资源局从布鲁塞尔发出的一则广告,征聘汉译英的临时译员,翻译“特快急件”——当时欧洲急于了解中国和打开中国市场。经初步联系,我启程前往欧盟总部所在的比利时面试。那天一共有十来个人应试,三名“面试官”是两位英国教授和一位垂垂老矣的侨居比利时的台胞,听说是布鲁塞尔大学资深汉学教授。两位英国人跟我谈话以后,那位台胞老教授先在一块小白板上写了句话,然后把小白板交给我,问道:“‘仕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是司马迁说的吗?能把司马迁说的原文翻成英文吗?”我仔细看了看,回答说,这是西汉刘向在《战国策》里说的。西汉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的话原句应该是“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老汉学家听了频频点头,似乎很高兴,就让我译成英文,并说“不急不急,给你三分钟”。我想了想,说:“可以这样翻吧:A gentleman is always ready to serve anyone who knows him well enough. A woman is always ready to make herself up for a man who truly loves her.”然后遵照老汉学家的要求把英文句子写在小白板上,他看完就交给了那两位英国人,然后问我为什么要加上“well enough”和“truly”两个原文中并没有的字。我回答说:“翻译中这叫‘诠释性添加’,我想司马迁的话有这个深层涵义。”老汉学家听了会心地点了点头。当天下午大约两点多,他们来电话说我被聘用了,请我尽快去签约。
我很“感激”司马迁,当然更感激我的老师吴兴华教授,是他那两句话让我领悟到翻译实践的重要性。套用当时的流行语就是:“只要翻好外国话,走遍天下都不怕!”
2. 坚持理念,默默耕耘
“理念”是一个人的基本信念,研究理论最重要的是要恪守基本理念。有了这个基本理念,就很难被杂念、时势、境遇、或所谓权威“屈打成招”!
我研究翻译的基本理念只有四个字:“为了中国”。据史载,中国从公元前174年起就与匈奴有外交、军事交手,贾谊就向朝廷提出过有关国策。至公元前末年匈奴降服来朝。试想想,如果当时没有口笔译,这种“交手”、“来朝”怎么可能进行?很显然,到东汉(25~220)和三国时代(220-265),我国的口笔译翻译(尤其是口译、公文和商务翻译活动)已是国事常规,先于佛经翻译。但经书翻译后来居上,有朝廷支持,有更广泛的民间基础,才有了关于支谦这些翻译高手纵谈“美言”与“信言”之类“翻译美学专业命题”的记载。隋初(607),日本特使小野来华,609年中国与波斯、西域各国建立了商务及外交关系,比盛唐贞观之治(629~649)早了大约半个世纪。13至15世纪,我国更与南洋各国广泛交往,海陆相通,科技翻译已很有规模,始有徐光启的“会通”(“通会”)之说。可见我国译学源远流长,今天我们必须坚持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的历时继承性和共时发展观,有我们自己的“中国气派”——应当学习西方之长,但也不应盲目跟风西方潮流。1987年我跟卞之琳先生在香港大学一起开会,谈到这个观点,卞之琳打趣地对我说,“小刘,咱们是‘老小英雄所见略同’了,你要深入研究,谨慎立论,为了中国译学!”卞先生这个鼓励与我在北大时的前辈老师的叮嘱如出一辙,更加强了我的信念。
默默耕耘必须有莽林拓荒之志,有百屈不懈之心,有破浪乘风之勇。我不敢说我都能做到,但我知道这中间无非是汗水加心血。比如,《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我写了三年多;《翻译与语言哲学》整整写了五年,几乎看完了当时香港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所有相关的中西著作,真可以说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文化翻译论纲》这本书更使我付出了“破记录”的艰辛,前前后后竟然写了十年(1988~1998)。1988年初我接受了唐瑾女士的约稿,不久去了法国巴黎和马塞,总之1989年和1990年我音讯缈无,唐瑾以为我是个飘到了北极圈的“断线风筝”。其实这期间我在“中西文化”思考的苦旅中煎熬,已经四易其稿,直到1998年我才勉强将它“杀青”,告慰唐瑾。唐瑾说“你仙游十年,今负笈还乡,不负我望,可喜可贺!”。其实,我哪里有花前月下的仙游雅兴。我是在都柏林大学的人文阅览室边写文章边啃干面包、喝黑啤酒,常常到晚上十一点半。偌大的阅览室原来只剩我一个人。管理员小姐必须关门闭馆时,才轻轻走过来,温柔地问我:“Sir,are you through(先生,你写完了吗)”?我感到很是歉然,常常急忙收拾东西,望着她说,“Sorry. I didn’t know it’s so very late(对不起,我不知道已经这么晚了)”。
其实,我当时正如清代马荣祖在《文颂·神思》里说的那样“冥冥濛濛,忽忽梦梦,沉沉脉脉,吟吟诵诵”地抽思理绪,为《文化翻译论纲》修辞酌句,梳理篇章。这一切,大概可以叫做:“默—默—耕—耘”吧。
3. 把握整体,深化认知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听说前辈翻译家袁可嘉(1921~2008)谈过一次美国人文理论研究的特点,他提到西方人研究人文理论热衷于“局部精彩”和“在微观突破中的个人陶醉”,至于国家社会的急需、理论体系的格局、学科宏观架构的构建、学科发展的愿景等等整体性整合研究,他们都是“恕我无暇”或“兴趣缺缺”的。这个点睛之评,我很赞成,也大受启发。当然我认为人文理论研究的一孔之见、一得之功也是可贵的,但完全置全局于不顾就欠妥了!一个人若是对“偏”、“陋”、“奇”、“诡”(语出清代杰出学者顾炎武)的课题研究走火入魔,就难免影响自己的理论品位和前程!
翻译学建设是个庞大工程,必须密切关注宏观架构建设的系统。宏观微观兼顾,以宏观决定体系格局,以微观富集体系内涵,这是中国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很忌讳“杂述散捬,不见经纶”(刘知几《史通·杂述》)。我们的观点是应该是辩证的:“无杂述则无以集经纶,无经纶则无以存杂述”。我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翻译界有人批评中国人只懂“术”,不讲“理”,这种论断近乎污蔑,根本不符合事实。以经学为核心的汉代学术、以儒道佛三学汇通的隋唐晋学术、以探求义理为核心的宋元学术、以心智理学和考证诠释之学为盛的明清学术,都是中国人讲“理”的精华。到外国学了一点点西论皮毛,最好回来先充充“国学”之电,有点底气了再去“登高疾呼”骂中国人只懂“术”。我感觉,中国不少学人一是疏于把握整体,二是疏于深化认知,浮华不实,心躁神虚,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实在令人担忧!
西方诸国许多翻译研究所我都去过,与他们的主管们交流过。他们其实也都在集中注意力于翻译理论一般规范的“本土化”、实务的“科学化”,外国的研究成果对他们来说都只是借鉴,几无例外。因此我一直主张重视翻译理论的“中国价值”,这应当是中国翻译界基本的“集体认知”。有了这个基本认知,才好深化译学的各领域研究。例如谈到译学的“文化研究”,现在很多人还是念念不忘洋人提出的所谓“归化”和“异化”。译界对“文化”的认识很浅薄,基本上停留在“文化现象学”层面,停留在物质文化、行为文化甚至时尚文化层面,最重要的精神文化(例如价值观问题)在中国似乎是“禁区”。这是不正常的,学术探索应该以提升学术为重,不可有所畏惧。
4. “富贵于我如浮云”
此话引自杜甫《丹青引赠曹霸将军》中的诗句:“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这句诗的精神境界至高至纯、至净至美,一直是我的座右铭。我认为搞学问,应该与功利心绝缘,所以我从不关心什么职称、级别、职衔、头衔,亦从未想要什么职位、依附任何团体、组织,我行我素,因此近三十年来辜负、得罪了很多人,心中着实抱歉。我写十二本书时,从未想过向国家和港府申请一分钱研究经费。我喜欢父亲的两句话:“两袖清风无牵挂,来去无踪不留尘”,因为功利心只能诱发冲动型、占有性欲念纠结,不可能激起持久性、频发性智能爆发。引起智能爆发的主要因素是某种历久不衰的、炽烈的科学或道德理念,绝非功利心。
以色列国家科学院以一种十分巧妙的方式对100名诺贝尔物理、化学、医学奖获得者作过一次正式的分析调查。结果表明,出于某种功利心驱动投入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奖者,“在100人中只有三个半人”。波兰化学家、被公认为“贫穷而美丽”的玛丽·斯克罗多夫斯卡·居里(Marie Sklodowska Curie,1867~1934)就是超乎功利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学者的楷模。当然,诺贝尔奖也常常涉及同业或跨国的激烈竞争,但竞争性的本质一般都与职业或国家的成就感荣誉感有关,与个人利欲之念没什么关系。
其实,杜甫这句诗受了庄子的“无待”(无所期待,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思想的点化。《中国哲学史》一书是这样解释“无待”的:
庄子在《逍遥游》中说,大鹏的飞翔要靠大风和长翅膀,走远路的人要带许多干粮,这都是有所“待”,因为没有大风、长翅膀、干粮等条件,就飞不了,走不成……真正的自由是一切条件都不需要依靠,一切限制都没有,在无穷的天地之间自由地行动,这就叫做“无待”。这是讲的要摆脱外界的条件和束缚。同样,受自己的肉体和精神的限制和束缚,也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各种主观条件也要摆脱,以达到“无己”。庄子理想中的最高尚的人,都是能做到“无己”的。例如,庄子在《大宗师》中描写的“真人”的情况是:睡觉时不做梦,醒来时无忧虑,……对生不感到特别喜欢,对死也不感到特别厌恶。总之,他们是自然而生,自然而死,也就是说,一切听任自然,毫不计较个人得失。这就叫做“无己”,(这样就)可以得到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北大哲学系2005:66-67)
用今天的话来说,“无待”、“无己”就是摆脱功利心。其实,西方也有很多人——哲学家、文学家、诗人都笃信这一点。带着功利心去搞学问,其后果无异于“一无所得的徒劳”(“out and out thankless effort”,见Franz Kafka 1915TheMetamorphosis)。他可能获得昙花一现的一点荣誉,取得梦寐以求的一点钱财,但荣誉和财富的陶醉感最终将断送他的“身后名”、他的理论研究的真值和道德分量。因为,这中间,始终有一个看不见却又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最高裁判官——历史。
悠悠五千年,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我想,今天的中国学者确实都得好好想想:在这个浮躁的、功名高于道德的年代,我们该如何自珍、自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