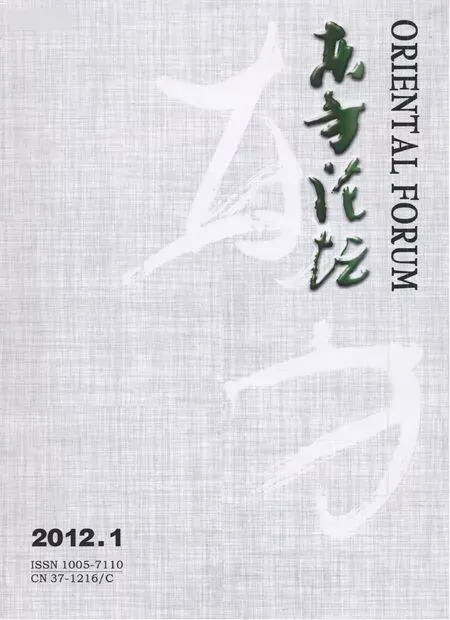政府市场经济的困境和路径选择
黄 建
政府市场经济的困境和路径选择
黄 建12
(1.中央党校, 北京 100091; 2.河南广播电视大学,河南 郑州 450053)
当政府在经济的运行中扮演主要角色时,市场经济体现出浓厚的政府主导色彩。政府市场经济的困境是指由于政府在市场行为中的作用,使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提升一国经济指标总量的同时,并没有给国民带来富足和福利。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一则是因为政府市场经济中干预的主观和逐利,二则是官民对市场规则的漠视。只有破除基于GDP主义的官员评价体系,完善行政审批制度,加大对权力寻租的惩罚,充分发挥公民的参与监督制度,市场经济才能良性发展,经济发展的成果才能真正为人民共享。
市场主义;官员经济;GDP主义;政治参与
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国进民退,经济总量和居民个人收入没有同比增长,有时甚至背道而驰,已不是一个什么新鲜的话题。根源于计划思维的市场经济,尽管在初期弥补计划经济造成的大面积空白上一度带来很好的效果,但随之便产生很多问题。市场自身的缺陷没有因为干预得以避免,市场优势却因为干预得不到体现,甚至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产生的GDP主义造成整个国民道德体系的解体。
经济活动是靠市场调节还是政府调节,或者说主要是靠市场调节还是政府调节,是判断市场经济性质的主要标准。政府市场经济就是政府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扮演主要角色,具体表现为官员按照自己对经济活动的理解制定规则和政策,并主导市场运行。根据公共选择理论,政治家、官员和普通人一样都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最基本的动机,亦即假定人都有经济人的特点。“当个人由市场中买者或卖者转为政治过程中的投票者、纳税人、受益者、政治家或官员时,他们的品行不会发生变化”[1] (P341)当经济活动被政治家或官员主导和控制时,经济规律和公共利益不总是他们制定和执行政策的首要考量,个人利益最大化,如升迁、寻租,无疑成为直接的影响因素。
一、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
市场经济,简言之就是通过市场供给和需求配置资源的经济,它起源于人类最早的自由贸易活动。显而易见的是这种自由贸易活动的发展只有在财产权和合同履约能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才能发展到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这类保证,最终只有由国家出面提供,才有可能达到最优规模。政府和社会的互动以及政府通过制定规则对贸易的推动,对市场经济的产生、发展和完善非常重要。因此,政府应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扮演一定角色,这是人们认可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也不例外。始于自发的贸易活动,随着商人阶层的兴起而得到发展和规则化。当国家意识到商业对国家强大的作用时,“重商主义”便产生了。应该说17、18世纪的欧洲国家的普遍政策倾向却都是“重商主义”的。著名经济学家希克斯教授在《经济史理论》指出,“重商主义”标志着一种发现,即经济成长可以用来为国家的利益服务。他说,当君主们开始认识到可以把商人用来当作为他们的非商业的目的服务的工具时,他们变成“重商主义”者。[2](P152)
“重商主义”的发展引起了一些经济学家和政治思想家的担忧。他们鼓吹市场秩序一旦建立,政府就应该退出对市场的干预。亚当·斯密坚决批判“重商主义”,他在《国富论》一书中,主张市场在一些状况下,将能自然的调节自身的问题,并且能产生比饱受管制的市场更为有效的状态,并把政府的职能限制在三个方面:保护社会,使其不受其他社会侵犯,即建立国防体系;保护个人,使其不受他人侵害与压迫,即建立司法机关;建设维持公共事业与公共设施。[3](P252)哈耶克也说,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一种“自发扩展的秩序”。[4](P58)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基本上不起什么作用,或者毋宁说,国家起不到什么正面的作用。
从洛克阐述有限政府学说,到亚当·斯密对“重商主义”的驳斥,发展古典经济学以来,思想家不断发展这种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减少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给经济和社会以更大的空间,似乎已是学者和民众的共识。虽然二战以来,倡导国家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在思想界产生重要影响,但这种思潮无非是为了克服市场过度自由带来的弊端,缓解社会矛盾的一种福利制度意识形态,它是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和社会事务日益复杂化的必然结果。这种国家干预只是宏观的调节,不会涉及具体的运作层面,和我们心目中的干预概念相去甚远。虽然很多发展中国家已实现从集权主义到权威主义的转型,但它们奉行的依然是一种政府全面干预的政策,市场经济不过是全面干预政策积弊愈深时的一种自我调节。但无论如何,这种自我调节已成为大势。市场经济总不停歇的试图挣脱政府的干预。
二、权力思维和政府市场经济的困境
市场是个好东西,无数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证明。然而在权力思维依然根深蒂固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的运行在给国民带来福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人不愿意看到的,有些甚至是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引起了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质疑。为什么在一国能良好运行的制度在另一国度却往往很难有效运行?市场经济是理性和法治经济,当人们在经济活动中遇到困惑或问题时,把本可诉诸市场解决的问题却渴望诉诸政府解决时,而他们绝大部分时间又不得不这样,市场经济就无疑成为大家在公开场合的台词,而台下谁也不愿意提及的词语。市场和政府本身应该是边界清晰的,当边界模糊,甚至经常重合时,我们在正面看到就是市场经济,背面却是政府经济、官员经济。
完整的市场概念包括市场自身的运行规律与它和政府之间关系两个部分。如果市场没有按照自身规律去运行,或者说它和政府边界模糊,那么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提升一国经济指标总量的同时,可能会使社会中多数成员生活质量下降,他们得不到市场经济带给他们的富足,享受不到政府带来的福利,这就是政府市场经济的困境。我们在谈论市场时,不能不谈到政府在其中的作用。一个优良的社会状态,市场的两面性和政府的两面性应该是互补的,政府应介入市场失灵部分,其自身的失灵应该交给市场和非政府组织解决。如果政府介入市场有效范围之内,而没有去关注自身和市场的失灵,那么社会多见的是两者的弊端,而不是优势。
著名法学家伯尔曼说过:法律只有具备了精神上的效力才能发挥作用。[5]市场机制也不例外。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市场观念首先发源于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思想家在展开的关于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的争论,这种争论使人们,不仅包括普通公民,也包括政府官员,明白了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以及各自的角色是什么,他们愿意按照,也希望别人按照这种规则做事。我国的市场经济观念的形成来自于政治权威的推动,而缺乏这种思想的启蒙,人们都知道发展经济是硬道理,但对市场的规则,尤其是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知之不多。可以说,这种推动缺乏民众思想认知基础,尤其是没有政府官员们从内心接受。从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市场经济正式提出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国民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仅次于美国,但是经济发展的成果并没有为全民共享,部分人群生活质量并没有得到提高,甚至有所下降。究其原因,问题就在于我国的市场经济是政府推动的经济,这种推动是按照官员们自己对市场化的理解来进行的,是建立在数字和工程项目基础上的,它没有按照市场的自有规律进行。在不该市场化的公共服务或公共产品领域,如教育、医疗和公共住房,推行市场化,在本该市场的领域,如一些垄断行业,不愿市场化。
三、解决政府市场经济困境的路径选择
(一) 破除基于GDP主义的官员评价体系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增长以GDP来衡量,GDP主义也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最主要政策根源。GDP主义是指政府刺激经济发展的一整套政策。政府确立了一个量化的发展目标,再把这个目标“科学地”分解,落实到各级官员。很自然,GDP的增长成了官员升迁的最主要的指标。
新加坡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郑永年认为,GDP主义的核心就是促成所有事物的货币化,或者如马克思所说的“商品化”。货币化导致了从“以人为本”到“以钱为本”的转型,钱变成了衡量人的价值的唯一标准。强烈的GDP增长冲动使各级政府迫不及待的摧毁了旧的社会保障机制,而没有建立起新的社会保障体制,使得社会成员全身赤裸裸地暴露在一个不确定的市场社会中去。官员们为了获得更大的控制权和财富积累,在生产领域尤其是国有企业领域的私有化上以意识形态为理由不愿推进,而在包括医疗、教育、住房等几乎所有的社会领域(政府本该承担更大的责任)却大搞市场化。可以想象,在GDP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发展,必然会出现如下两种情况,一方面经济增长率和经济总量增长很快,另一方面老百姓生活水平日渐下降。在出卖廉价的劳动力不足以维持生计和生存的情况下,人们不得不出卖其他一切可以出卖的东西,包括身体自身。[6]
实际上,在GDP主义的政治环境中,人们很难指责各级官员,因为GDP指标是这些官员生活其中的政治体系运作的内在部分。对各级官员来说,GDP不仅有政治利益,而且也有经济利益。盛行多年之后,GDP主义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一种牢不可破的意识形态。在GDP主义影响下,任何惠民政策都很难取得应有的效果。
从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的成就上分析,GDP主义无疑是最主要的推动力。今天,中国以经济总量为核心的综合国力已居世界前列,这个时候,该重新评价传统把GDP增长作为官员评价唯一标准了。亚里士多德曾说:“对于民主政体和寡头政体同样适用的真正上策不是那种能确保民主和寡头本身最大限度膨胀的政策,而是能确保它们最长久地延续寿命的政策。”[7](P20)管理学的发展历史也告诉我们,虽然其早期的理论和实践都以强调效率为主,但随着效率的提高,对公平的强调越来越势不可挡,并总能在与效率的博弈中占据主导地位。结合我国实际,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是不是该让位“兼顾效率和公平”,或者“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呢?
效率是可以通过数字量化的,而公平则更多是一种态度和评价。那么谁对公平最有发言权呢?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因此,转变传统的GDP主义,就是要真正把辖区公民对政府的评价作为对官员考核的主要标准之一。民主社会中,态度和评价是通过选票体现的。因此,扩大基层政府的直接选举范围,落实差额选举制度,是最行之有效,也最可行的办法。
(二)改革行政审批制度
行政审批是行政部门拥有的对个人、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从事或不从事某种活动的许可。在我国,几乎所有的部门都是有审批权的,这也是它们致力于维护和追求的。由于作为政治代理人的官僚机构拥有明显的信息优势,导致官僚自主性和权威扩展的自然性在很多时候可以影响甚至超越政治家的控制。有学者称中国是“处长治国”,就是说很多政策和法规都是由各主管部门处长们制定,然后层层报批,最后以权威部门名义公开发布。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之所有受到多方阻挠,与官僚机构对部门利益的维护有直接关系。
当前,微观经济主体从事任何经济活动,几乎都需要得到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从事卫生医药的经营要得到卫生主管部门的审批,从事环保的经营要得到环保部门的批准,哪怕是自治性的非盈利组织也要得到民政部门的批准。凡此种种,中国经济的审批范围是如此之广,审批项目又是如此之多,因此,中国的经济体制又可以称为审批制经济。审批制经济直接导致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并由政府或者说政府官员牢牢掌握和控制市场的运作和方向,这是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矛盾的,市场经济要求尽量少的行政干预。审批制下的政府市场经济必然会带来经济资源的浪费,增加市场的运营成本,这些最后都要直接转嫁到消费者,也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头上。
改革行政审批制度,首先要正确认识基于部门利益的官僚机构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不然总停留在减少审批项目、简化审批程序的说辞上,只能解决表面问题,治标不治本。在这方面,中央政府要付得起责任,要借助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际通行规则和市场的力量冲破来自部门利益的阻挠。正如李景鹏教授所说:“在市场与行政权力的博弈中,中央是站在市场一边的,是‘替天行道’的,而各级国家机关则主要站在体现旧体制与政策的行政权利一边的。正是因为中央与各级国家机关在改革政策上的博弈是行政部门权力与市场之间的更大的博弈的反映,所以中央在推行改革政策、冲破各级国家机关对改革政策的抵制和反对时,借助于市场的力量是完全应该的,这恐怕也是中央能借助的唯一的力量源泉了。”[8](P11)
(三)加大对官员寻租行为的监督和惩罚
解决市场主义的悖论,首先需要政治权威基于清晰认知上对市场的引导,这种认知应该是遵奉市场规则的理性判断,这种判断是稳定的、可预测的,而不是主观随意的。对市场的引导不仅包括政府自身的约束和教育,关键是要对官员试图从市场中寻租的行为进行监督和惩罚。
布坎南认为,政府的寻租行为来源于“寻求租金”。“寻求租金”不是指地主收取地租,而是指人们凭借政府保护进行的寻求财富转移而造成的浪费资源的活动,其本质在于获得更大的利润。他认为:“租金是支付给资源所有者的款项中超过那些资源在任何可替代的用途中所能得到的款项的一部分。”[9](P112)由于政府的各项经济决策往往以某种公共利益需要为解释为某些利益集团服务,这些集团为谋取政府保护,逃避市场竞争,实现高额利润,往往进行各种寻租活动,于是政府寻租行为就产生了。
对于政府寻租行为的监督,往往会由于政府官员垄断或封闭决策信息,或者由于监督者主观的原因,导致实践中无法或没有有效进行。这种情况常常会进一步加剧政府的寻租行为,进而导致政府权力滥用、行政受贿和资源浪费现象日益普遍。对于市场化初期产生的政府寻租行为,市场化本身不能解决问题。在我国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中,政府应该对市场规则的培育负有责任,并对违反规则的市场主体和其他组织给予惩罚,包括其自身。
中国当前自上而下的行政模式在监督体制完备时会使监督更加有效。在这种体制下,中央政府的决心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还是始终站在一定政治高度,把握大局,强力推动着经济秩序的有序化和规范化。尽管在实践中,这种干预遭产生了很多问题,但是它却能扮演着推动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强大动力。从2004年党中央颁布《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到2009年5月中纪委通过加强纪委书记的政治地位,增加纪委编制和提供办公保障等一系列手段对县级纪委的权力强化,都显示出中央政府层面对自身监督的加强。这种决心,加上不断完善的监督机制,以官员寻租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腐败必然会受到越来越多的惩罚。
(四)培育并呵护普通公众的表达参与机制
尽管我国最高决策层正在日益加大对官员腐败的惩罚力度,显现出很强的决心,但是自上而下的官场文化却让置身于其中的官员独善其身。“在官员眼中,一个清廉的异端远比一个腐败的同党危险。他们最重要的事情是铲除异己,而不是清除腐败。”[10]这种官场文化有其生存的土壤,或者说特定的环境滋生出特定的文化。因此,对官员寻租行为的揭露和惩罚,仅仅依靠中央政府的决心和制度是不够的。决心会因为决策者的更换和情绪而变化,制度会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被打折或忽视。寻租行为不能产生于真空之中,寻租行为带来的后果不可能不被利害相关人知晓,因此重视来自他们的声音表达无疑是遏制寻租行为的一条有效途径。众所周知,我国民间一直存在宁愿蒙冤也不告状的底层文化,他们的表达往往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行为。这种表达可能有夸大其辞和扭曲事实之嫌,但其真实性比起好大喜功的报表显然更具价值。
无需认真分析准确数字,随意的搜索都能带来一串因为百姓上访、媒体报道和网络曝光近年来被曝光并受到惩罚的官员的例子。制度有时并不能使官员害怕,这种无处不在的监督可能才是他们最后一根稻草。就像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曾说过一句很透彻的话,“牛栏关猫,进出自如”。[10]对上了一定级别的领导来说,监督只是形式而已。他完全可以随意进出,畅通无阻。
基于表达的参与是一种监督,这种自上而下的监督是自上而下监督体制的有益补充,并且应该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十七大报告把监督权的行使看做是人们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并且明确提出要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对于公民的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政府应该制度化容纳,而不能予以压制。
[1] 布坎南. 宪法经济学[M]. 三联书店,1996.
[2] 希克斯. 经济史理论[M]. 商务印书馆,1987.
[3] 亚当·斯密. 国富论[M] . 商务印书馆,1996.
[4] 哈耶克. 法律、立法和自由[M] .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
[5] 刘澎. 中国学者对话伯尔曼:法的背后是什么?[N]. 南方周末,2007-11-21.
[6] 郑永年. 中国的GDP主义及其道德体系的解体[N]. 联合早报,2009-12-29.
[7] 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王冠华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8] 王浦劬,徐湘林. 经济体制转型中的政府作用论文集[C].新华出版社,2000.
[9] 布坎南. 寻求租金和寻求利润[M]. 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
[10] 反腐学者.“反腐不可过头,重在制度科学” [N]. 南方周末,2009-6-25.
责任编辑:潘文竹
The Dilemma of the Governmental Market Economy and Its Solution
HUANG Jian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Beijing 100091, China)
When the government plays an important pole in economic operation,the market economy embodies a strong element of governmental leadership. The predicament of governmental market economy refers to the fact that because of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market behavior,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enhanced the total of economic indicators without bringing people prosperity and welfare. The first reason is that the government is subjective and profit-seeking in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market economy; the second is that the officials and common people ignore market rules. Only by breaking through the official evalua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GDP principle,perfecting the system of administrative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punishing more severely power rent and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system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and supervision,can market economy develop in a healthy way,and can economic development really benefit the people.
marketism; economy based on officials; GDP-orientati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F123
A
1005-7110(2012)01-0099-05
2011-12-18
黄建(1975-),男,汉族,河南淮滨人,河南广播电视大学讲师,中央党校政治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政治发展和政府管理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