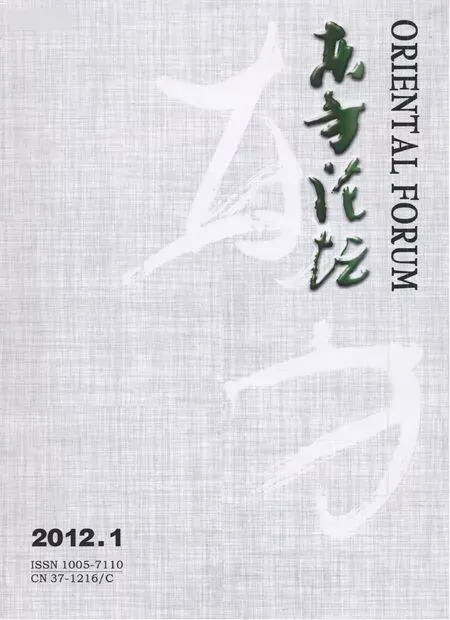关于中国海洋文化遗产的几个问题
曲 金 良
关于中国海洋文化遗产的几个问题
曲 金 良
(中国海洋大学 海洋文化研究所, 山东 青岛 266071)
中国海洋文化遗产是一个巨量文化遗产存在,内涵丰富,价值重大,存在状况堪忧,保护任务艰巨。一直以来,人们对 “海上丝绸之路”重视有加,但“海上丝绸之路”不是孤立的遗产存在,而是中国海洋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研究重视、保护开发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将其放置于中国海洋文化遗产的整体视野之中是必要的。这一方面有利于对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整体认知,也有利于对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整体的“生态保护”和整体的价值利用。
海洋文化遗产; 环中国海; 汉文化圈; 海上文化线路
一、中国海洋文化遗产的丰富内涵
中国海洋文化遗产的主要存在空间,是“环中国海”。
“环中国海”与“中国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国海”即环绕中国的广大海域,包括(由北到南)渤海、黄海、东海、台湾海峡及台湾东部近海、南海凡五大海区;国际上多将渤、黄、东海统称为“东中国海”(East China Sea),将南海称为“南中国海”(South China Sea),而将台湾海峡和台湾东部近海作为“东中国海”与“南中国海”的中间地带。“环中国海”,则是指环绕中国海与中国海共同构成海-陆一体的东亚“泛中国海”地区——“环中国海”的内缘,是中国大陆沿海地区及其近海岛屿;“环中国海”的外缘即外围,是(由北到南)东北亚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琉球群岛,和东南亚的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文莱、泰国、越南等国家和地区。
所谓“海洋文化遗产”,内涵十分丰富。历史上的人类海洋活动、涉海活动及由此而形成的思想意识、社会制度、科技创造、物质生活、民俗风情等的文化遗存,都是海洋文化遗产。历史上的人类海洋活动,主要是“渔盐之利、舟楫之便”,其中“舟楫之便”即航海活动的文化遗存,从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角度而言,一是港,一是船舶,一是船货,一是围绕着这三者人类进行的精神的、社会的、科技的、物质的、民俗的相关活动。这一“类”以“舟楫之便”为中心的海洋文化遗产,遗存空间广泛,历史累积的数量巨大,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含量也极为丰富,因而较之于“渔盐之利”的文化遗存,更为人们关注。
通过航海活动所形成的海洋文化遗产,主要是呈“线性”的“海上文化线路遗产”,一端是海洋的此岸,另一端是海洋的彼岸;中国的海洋文化遗产也是同样,一端在海内,一端在海外。因此,中国海洋文化遗产的空间范围,不仅包括“环中国海”的内缘的海洋文化遗产,而且也包括“环中国海”外缘的海洋文化遗产。也就是说,中国海洋文化遗产的整体空间边界,是由“环中国海”的内缘和外缘共同构成的海-陆空间范围的海洋文化遗产。中国海洋文化遗产的整体内涵边界,就是环绕中国海这一海洋空间,中华民族在与海外民族跨海互动中作为文化主体利用海洋所创造和积淀下来的文化存在。
在这一“环中国海”海-陆空间内,在长期的历史时期,中国一直是最大的内陆文明大国和海洋文明大国,一直对“环中国海”外缘周边国家产生着巨大的辐射影响力,并由此不但在政治上构成了历史上东亚世界直到近代才解体的以中国政治为中心的庞大的中外朝贡政体,而且也在文化上形成了“环中国海”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庞大的“中国文化圈”(亦称为“汉文化圈”或“儒家文化圈”)、在经济上形成了“环中国海”(并由此连通了“环印度洋”和“环地中海”)以中国经济为中心、以中国商品为大宗的庞大的中外“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网络。这种“环中国海”中外之间的政治互动、经济互连、文化互通,都是通过长期历史上一直梯航不断的中外海上往来实现的。而无容置疑的是,这种长期历史上中外之间的政治互动、经济互连、文化互通,一方面从质(内涵性质)上都是以中国大陆历代中原王朝为主导、按照中国大陆历代中原王朝的对外经略政策和中外宗藩体制及其朝贡制度而施行的;另一方面,由于“环中国海”长期历史上的中外航海一直以中国为“轴心”,由于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大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遍布沿海的港口和辽阔的幅员腹地,因此从量(无论是历时的还是共时的)而言,中外航海文化的主体是中国航海文化,以此为主要构成的中外线性海洋文化遗产,即“海上文化线路遗产”,主体上也是中国海洋文化遗产。也就是说,环中国海海洋文化历史的中心是中国,环中国海海洋文化遗产的主体属于中国。
航海的目的是载人载物;以载人为主的主要是政治、文化往来,以载物为主的主要是海上贸易。历史上长期的中外海上贸易,从中国源源不断地运走的大宗的“船货”主要是丝绸、陶瓷、茶叶,由此才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但丝绸、陶瓷、茶叶从来不产自海上,而是产自陆地,因此航海文化从来不是“纯粹的”海洋文化,而是具有海-陆一体性的海洋文化存在。而无论是中外航海政治联系、文化往来,还是海内外航海贸易,包括国内南北方海域之间的国家航海漕运,由于海洋环境复杂多变,桀骛难驯,往往难以“一帆风顺”,间或会有意外,造成海难。海洋文化遗产中的“水下文化遗产”,就是那些因间或发生意外而不幸葬身海底的难船。由于“环中国海”之间中外航海历史悠久,不幸葬身海底的难船经日积月累,“沉积”即多,加之一些人为的“海难”,如海盗劫杀、两军海战,从而导致沉船量极大,作为海洋文化遗产内涵丰富,因后世难以打捞出水而极度“稀缺”,从而弥足珍贵,如“南海一号”即有“海上敦煌”之称。但这些海底难船作为海洋“水下文化遗产”,只是全部航海文化遗产中的“冰山一角”(更是全部海洋文化遗产的“冰山一角”),更为大量、更为丰富的环中国海的航海文化遗产,是那些历史港湾、历史航道、历史码头、历史灯塔、造船遗址、港口海岸弃船、国家和民间用为海洋信仰祭祀的岸上庙宇、海商社会的岸上会馆、船民社会的造船与行船风俗、中外航海人集散的港口馆舍、相关人口社会聚居的港口城市遗产。它们是中国航海文化世代传承发展历史的内涵主体,也是现代社会条件下极易遭到破坏、大面积濒临灭绝、须加大力度保护的中国海洋文化遗产的主体。
环中国海的中国航海文化遗产,包括水下遗产和岸上遗产,在中国海洋文化遗产序列中无疑并非是海洋活动、涉海活动遗产的“大端”。其“大端”者,则是海洋活动中的“渔盐之利”遗产及其相关遗产、涉海活动中海疆管理、海岸治理、海防海战、滨海游赏等相关遗产。数千年来历代政府进行海疆管理和治理的一系列设施遗存,历代兴建万里海塘、万顷潮田、万座海防设施(如烽火炮台、军镇卫所建筑)等大型海事工程,沿海地区占大量人口比例的渔业社会、盐业社会所遗留下来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海洋文化遗产,其量之大,其内涵之丰富,其对中国社会、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所起的作用,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例如一个“渔盐之利”的“渔”字,就至少有如下内涵:历史上渔民社会的聚落主要是渔村;其打渔的海域是渔场;其渔业组织是渔行渔会;其渔产交易买卖的集散地是渔埠,通过行商遍及全国四面八方的销售场所是大大小小的集市与店铺;其干、鲜渔虾海产消费的终端是遍及全国百姓的餐桌;政府对其管理的衙门是渔政,渔民、渔产行商和坐商们向地方和中央缴纳的是民五花八门的税、费;渔业社会信仰祭祀的场所是山巅、海口的海神庙、龙王庙;其娱乐和审美的文化空间是节庆庙会;其出海打渔的渔场海域往往没有“国界”,因而其进行“国际文化交流”是家常便饭。再如一个“盐”字:环中国海历史上的盐业社会,仅就中国本土而言,就一直是一个庞大的海洋社会存在,他们分布在南北蜿蜒漫长的海岸线上,经营着或煮或晒的官办盐场,自先秦时期就是国家“官山海”的主要产业大军,历代国家财政往往“半出于盐”甚至更多,历代盐政是中国的一大行政部门,历代盐官是中国官员队伍的一大序列,历代盐商是中国“红顶商人”的一大群体,历代盐神是中国官府正祀和民间淫祀的一大景观——中国海盐一直占据着中国盐产的大半壁江山,充分显示着海洋对于中国的极端重要价值——其历史文化遗产,无疑是中国海洋文化遗产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内涵。
二、中国海洋文化遗产的存在状况
中国海洋文化遗产具有如上多方面的重要价值,广泛分布在环中国海的广大海-陆空间内,但其“生存”状况却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威胁、破坏乃至大量损灭,其整体现状令人堪忧。
一是危险来自环中国海的外围。随着新世纪“海洋时代”的来临和全球性海洋竞争白热化态势的出现,我国的海洋权益的维护包括海洋文化遗产安全的保护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挑战。由于作为环中国海海洋文化遗产的中心和主体的中国海洋文化遗产广泛、大量分布在一些与环中国海周边国家存在主权和权益争议的岛屿和海域,而这些岛屿和海域大多已被周边国家和地区实际控制,他们一方面作为政府行为,为了“证明”其“主权”和其他“权益”的归属及其“存在”,遮蔽中国海洋文化遗产的历史存在,故意破坏、铲除具有中国属性的海洋文化遗产,建筑他们自己的现代海洋实施,或改头换面为他们“自己的”海洋“遗产”,从而导致中国海洋文化遗产的损灭;一方面由于其遗产法规体系和管理制度的不够完善,也由于中国属性海洋文化遗产的“价值连城”,作为其政府行为,往往与国际上“先进的”海底捞宝公司“合作”藉以分赃获利;作为民间行为,则肆意偷盗、抢挖破坏和贩卖中国海洋文化遗产,从而导致中国海洋文化遗产的损灭。
二是危险来自环中国海内缘和外缘普遍的快速度城市化、工业化和经济全球化乃至不同程度的“文化全球化”所导致的“建设”性破坏。环中国海东亚世界作为“中国文化圈”或曰“汉文化圈”、“儒家文化圈”的传统的改变始自近代:中国自鸦片战争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日本自明治维新“转身”为“脱亚入欧”的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其他环中国海东亚地区大多被西方或日本部分殖民甚至完全殖民。东亚世界的这种近代历史虽然早已结束,但其“后遗症”却至今不乏端倪,其在文化上的显现,即是自近代以来对传统文化程度不同的外力破坏和自身自觉不自觉破坏。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人们为了“赶英超美”,不惜将传统文化遗产夷为平地,而代之以比西方还高的高楼、比西方还大还多的林立城市;人们为了工业化,不惜抛弃传统的作业方式和生活方式,为的是在经济数字包括GDP数字和诸多“指数”上竞相排名。这在我国也是同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国沿海是最先对外开放、城市和经济发展最快、现代化程度相对最高的地区,同时也是对海洋文化遗产遗存造成最为直接、最为严重的破坏的地带——既包括海滨海岸港口遗产、海湾航道遗产、涉海建筑遗产、岸上和水下航海文物与遗址等海洋物质文化遗产,也包括海洋社会信仰、海洋社会风俗、海洋社会艺术等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建设”性破坏的主要威胁方式,仅就“合法的”而言,就有大规模“旧城改造”(包括“旧街区”、“旧民居”、“旧港口”、“旧建筑”等“改造”)的“破旧立新”工程;有“城区”空间不断拓展、不断将“边区”古港古码头古渔村铲平而建设为新城区甚至城市中心的“大城市化”乃至“大都市化”工程;有“围海造地”向海滩要地、向海湾要地的“大炼油”、“大化工”工程;有以现代化陆源污染为主的海洋污染和海洋沉积导致的对海滨海岸和水下文化遗产的大面积“覆盖”与侵蚀“工程”;等等。如何对我国18000公里大陆海岸线上、6500多个大小岛屿上、300多万平方公里管辖海域中大量重要的海洋文化遗产进行有效保护利用,并对数百万平方公里管辖外海域及其岛屿、海岸中具有中国属性的海洋文化遗产进行有效监护,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十分严峻的课题。目前我国正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然会带来文化观念的转变,我们抱有极大乐观,但又深知任重道远。
三是危险来自国内沿海民间社会对岸上和水下海洋文化遗产的非法行为。这表现在多个方面。其一是沿海地区不少工程企业或为抢赶工程进度、或为抢占土地和海域,不经文物部门勘探批准就施工挖掘,甚至瞒天过海,故意掩埋、破坏海洋文物遗产;其二是一些沿海地方的旅游部门、旅游企业为“吸引”游客而肆意改造、“重建”海洋文化遗产景观,造成了对遗产本身乃至其生态的肆意侵略甚至严重破坏;其三是沿海一些渔民非法进行水下文物打捞,对海底船货文物非法侵占、买卖,并对水下船体本身造成破坏,还有的与内陆、与海外相互勾结进行海洋文物走私,造成文化遗产的大量流失;等等。有的海上盗宝者甚至组成“公司”,在对海洋水下遗产的非法盗窃中,有的负责“勘探”,有的负责打捞,有的负责“侦察”和“保安”,有的负责非法贩卖乃至国际走私。我国政府对水下文化遗产的考古打捞,实际上都是被动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如“南海一号”、“华光礁一号”、“腕礁一号”、“南澳一号”等“一号工程”,用我国水下考古工作者的话说,实际上是被国际国内的非法打捞盗窃行为“逼”的,是“迫于文物破坏和流失的严峻形势”的“不得不为”。由于政府组织的或经文物部门批准的正轨考古打捞行动一直较少,对岸上尤其是水下文化遗产的存在状况并不全盘掌握,这种非法盗窃打捞的民间行为如若得不到彻底治理,则海洋文化遗产尤其是水下文化遗产受到的威胁和损灭无法估量。
四是危险来自全球性气候变化带来的海平面上升和海洋灾害频发所导致的海洋文化遗产被淹没、侵蚀等慢性蚕食与突发灾难性破坏。这对海滨海岸文化遗产造成的威胁尤大尤多。我国目前海洋部门和海洋科学界对海洋环境所进行的研究监测与技术治理,尚未顾及对海洋文化遗产的保护。
五是危险来自政府对海洋文化遗产的管理尚不到位。我国政府对海洋文化遗产尤其是水下文化遗产重视较早,且多有强调,但一是由于相关法规尚不够完善(如对1989年发布实施的国家《水下文物管理条例》,尽管对其修改的呼声一直很高,但至今尚未行动);二是政府管理条块分割,海洋水下文物及遗址遗迹等遗产的“存在”环境状态极其复杂,只靠文物部门难以济事——由于我国“文化遗产”整体理论、整体观念缺失,导致“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国是分头管理,即文物部门只管“物质”而文化部门只管“非物质”(在我国政府部门序列中,尽管文物部门“属于”文化部门,但实际上只是“级别”和官职系列的“属于”,而在“管什么”上是分开的),文化部门几乎对文物遗迹遗址等“物质”遗产不加过问,而文物部门则几乎对附着在文物上、作为文物自身内涵的“非物质”遗产也不“越权”,因此对本是一种海洋文化遗产,比如对妈祖文化遗产,就呈现为文物部门只管妈祖庙宇,而对以妈祖庙宇为载体、与妈祖庙宇不可分割的妈祖庙会,则由文化部门及其虽然“同级”却领导着它的宣传部门来管——如同海洋局只管海水海域,而海水中的鱼虾则由农业部管,海水上的船由交通部管,海水的环境由环境部门管(或与环境部门分管),至于海水之上、之下的文化遗产则同样不管(不分管);三是近几十年来“经济”二字趾高气扬,其他往往被迫让位,每遇经济发展与文物保护冲突,文物保护往往难以招架“经济发展”的至高无上,给文物管理和执法带来极大难度。
六是危险来自国民海洋文化意识和遗产保护意识的淡漠和缺失。没有意识,就没有自觉。尽管近些年来情形已大为改观,但尚未普遍。全体国民海洋文化意识得到普遍提升、海洋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得到普遍强化之日,才是海洋文化遗产得以全面保护、海洋文化精神得以全面弘扬、当代海洋文化得以全面繁荣之时。
三、中国海洋文化遗产作为“海上文化线路”遗产的保护
中国海洋文化遗产的系统研究与保护,极为迫切,势在必行。这既基于环中国海中国海洋文化遗产的广泛、大量分布及其重大价值,更基于其面临的令人堪忧的存在状态。
自1994年于西班牙马德里召开的“文化线路遗产”专家会议上第一次正式提出“文化线路”这一新概念并予以重视和研讨,至2008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16次大会通过《文化线路宪章》,“文化线路”作为一种新的大型遗产类型被正式纳入《世界遗产名录》范畴以来,世界各国以“文化线路”类型申报世界遗产已经成为一种备受重视的新趋势。
目前,世界范围内被纳入《世界文化线路遗产名录》的“文化线路”已有西班牙圣地亚哥朝圣之路、法国米迪运河、荷兰阿姆斯特丹防御战线、奥地利塞默林铁路、印度大吉岭铁路、阿曼乳香之路、日本纪伊山脉圣地和朝圣之路、以色列香料之路等;被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确认以备推荐给世界遗产委员会的“文化线路”已有30多条,中国的京杭大运河、丝绸之路(中国段)都在其中;另有茶马古道、古蜀道等也都已排上了中国申遗的议事日程。
“海上文化线路”遗产,就是人类跨越海洋实现文化传播、交流和融汇的历史形成的线性文化遗产。海上“文化线路”遗产的存在空间,就是人类历史上的海上航线;“海上文化线路”遗产的历史内涵广泛而丰富,远远超越人们所熟悉的海上“丝绸之路”以海上贸易为中心视域的历史遗产内涵。
中国作为世界上拥有悠久航海历史的大国,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琉球群岛、东南亚、印度洋沿岸乃至非洲、欧洲之间,不但自古航海交流不断,而且自先秦滥觞,自秦汉时代就逐渐形成了跨越东亚海域以环中国海为中心的“汉文化圈”:环中国海“汉文化圈”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也就是环中国海区域以中国为中心跨海互动、梯航不断的航海历史;“汉文化圈”的空间结构,实际上就是中国与环中国海区域包括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琉球群岛、东南亚地区之间跨海连结的一条条海上“文化线路”编织而成的。例如历史上中国中原王朝通过山东半岛(主线经辽东半岛、支线横渡黄海)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连结为一体的主要海上通道——“登州海道”,自先秦时代即已开通,唐前称“莱州海道”,唐析莱州设登州后多称“登州海道”,宋元明清一直沿用,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开通历史最早、延续历史最长、使用频率最高、内涵最为丰富的一条重要中外海上通道。中国本土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构成的东亚环中国海重心区域之所以成为世界文明史上重要的环海文明区域之一,中国文化之所以在这一区域成为主导文化并成为历史悠久、幅员辽阔、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汉文化圈”的主要区域,主要就是通过连结这一区域的海上网络中的“登州海道”这条“主干道”,即中国本土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之间历史上梯航不断,政治互动、经济互连、文化互通的海上“文化线路”实现的。“登州海道”这一 “海上文化线路”的全面内涵、历史过程、整体面貌是怎样的?其历代港口、航线节点都有哪些?其在长达几千年的中外跨海交流史上发挥了哪些功能与作用,具有什么样的历史地位?其沿线大量的古港码头、候风岛屿、祷神庙宇、沉船与船货、金石碑刻等相关遗迹与文物等遗产的具体分布点、线、面及其现今遗存情况具体如何?其在当代中、日、韩各国的发掘发现和研究保护与开发利用现状具体怎样?如何才能使其作为中国和日、韩等东亚世界共同的文化遗产受到中日韩的共同保护,充分发挥其在当代“东亚共同体”和海洋和平世界建构中见证历史、连结当代、启示和激励中日韩共同构建和平友好未来的作用?这些都是应该受到中日韩学界乃至政界和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
重视研究和保护中国与环中国海区域包括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琉球群岛、东南亚地区之间跨海连结的一条条海上“文化线路”,对于丰富世人关于“中国文化”既包括中国内陆文化也包括中国海洋文化的历史内涵的了解和认同,认知中国海洋文化在中国文化对外跨海交流、对外辐射影响和构建东亚中国文化圈中的作用,强化国人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中既重视内陆文化遗产保护也重视海洋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和理念,切实加强我国文化遗产的全面系统保护包括跨国合作保护与价值利用,都具有不容忽视、不可替代的意义。
总之,中国海洋文化遗产价值重大,中国海洋文化遗产现状堪忧,中国海洋文化遗产需要从整体上进行系统研究和系统保护与利用,这既是中国文化遗产包括海洋文化遗产整体研究、整体保护利用的学术需要和实践需要,也是服务于国家文化战略、海洋战略的多方面国家战略需要。为此,学界刻不容缓的当下使命,是在“文化线路”遗产及其保护的新理念、新视野下,将以“海上文化线路”遗产为主要遗产内涵的中国海洋文化遗产的丰富内涵整体系统地复原、揭示出来,进而为如何实施国家保护和跨国保护与利用提供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战略对策方案,并使之尽快上升为国家战略行动。
责任编辑:郭泮溪
Some Questions about the Chinese Marine Cultural Heritage
QU Jin-liang
(Marine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The Chinese marine cultural heritage is plentiful,with rich meanings and great value. However,its current situation is worrying and its protection arduous. Much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Sea Silk Road,but 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hinese marine cultural heritage rather than an isolated existence. 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study,develop and protect the Chinese Sea Silk Road and view it as part of the entire Chinese marine cultural heritage. It contributes not only to the whole cognition of the Chinese Sea Silk Road,but also to its comprehensive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the overall application of its value.
marine cultural heritage; seas surrounding China; Chinese culture circle; sea cultural route
G04
A
1005-7110(2012)01-0015-05
2012-01-08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世界“文化线路遗产”视野下的我国“海上文化线路遗产”及其跨国保护与利用研究(11YJA850017)阶段性成果。
曲金良(1956-),男,山东东营人,中国海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所长,博士生导师。
——围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