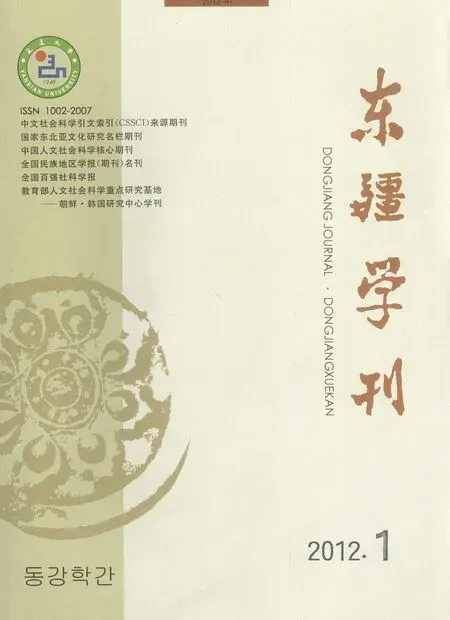《董妃行状》考证
于春海,赵乐
《董妃行状》考证
于春海1,赵乐2
《董妃行状》是清代文学中著名的悼亡古文。由顺治亲作,并以此纪念爱妃董鄂氏,笔意隐微,致使董鄂妃的来历与董小宛的去向迷离恍惚,历来多有疑者。通过对《董妃行状》作伪手法的揭示,可以对董鄂妃的来历和董小宛的去向进行新的探讨。
《董妃行状》;董鄂妃;董小宛;作伪
顺治十七年(1660),与顺治相伴仅仅4个春秋的董鄂妃与世长辞。顺治心痛不已,亲作4500字的《董妃行状》来纪念董鄂妃。《董妃行状》是我国文学史上悼亡文学的名篇,也是一篇备受关注的具有一定文史研究价值的文学作品。然而,对于这篇作品内容的研究,尤其是文中所述董鄂妃的身世描述惝恍迷离,令研究者莫衷一是。由于董鄂妃的身世,与明末“南京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之妾董小宛的死因与去向联系在一起,成为谜中之谜,历来文史大家如孟森、陈垣、钱仲联等皆有专文论述,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因此,对《董妃行状》一文以及与其有关之文献加以进一步的探讨,是很有必要的。
董鄂妃入宫、封妃之事扑朔迷离,疑信参半,在顺治当时便有许多蛛丝马迹,给后人留下了破绽。
一、对《董妃行状》的历史考辩
这里有两件事值得深入考辨。
先谈其一。据《清实录》载,顺治先有两位皇后,帝、后感情不合。第一位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系孝庄皇太后之侄女,大婚之后仅两年,顺治便以这位皇后“因亲定婚,未经选择,自册立伊始,即与朕意志不协,宫阃参商。”[1](51)为理由,废降为静妃,改居侧宫。第二位皇后为前皇后的从侄女。这两位皇后都是蒙古科尔沁女,是孝庄皇太后的娘家人。如果说册立第一位皇后时,顺治年仅十四岁,是出于政治目的,为多尔衮和皇太后所包办,那么第二次选立皇后,则是顺治亲自选中的。可是大婚不久,便又与皇后发生龃龉,对她加以冷落。甚至命礼部收回册宝,停止对她应行的各种礼仪,不准她到慈宁宫给皇太后请安。这是什么原因呢?西洋传教士汤若望所写的《回忆录》中有一段记载,为我们提供了寻根究源的启示。他说:“顺治皇帝,对于一位满藉军人之夫人,起了一种火热爱恋,当这军人因此申斥他的夫人时,竟被对于他这申斥有所闻知的天子,亲手打了一个极怪异的耳掴,这位军人于是乃因愤致死,或许竟是自杀而死。皇帝遂即将这位军人的未亡人收入宫中,封为贵妃。这位贵妃,于一千六百五十七年产生一子,是皇帝要规定他为将来的皇太子的。但是数星期之后,这位皇子竟而去世,而其母于其后不久亦薨逝……”[2](90)
据著名史学家陈垣考证,这位被顺治夺去其妻的“军人”,乃是顺治的弟弟襄亲王:“所谓满籍军人者,究为何人?其夫人能接近皇帝,则非疏逖
史载所谓顺治自撰《董妃行状》(即《御制孝献皇后行状》,以下简称《行状》),违背事实之破绽甚多,请择要辨析之。
其一,《行状》在述说董妃崩逝后,紧接着言道:“唯后制行纯备,足垂范后世,顾过来壶仪邃密,非朕为表著,曷由知之?是用其平生懿行,次之为状。”[7](357)可见,顺治写此《行状》,显然是别有一番用意。顺治自谓是为了“表著”这位董鄂妃的生平行操,不要因为“壶仪邃密”而使人们不能了解或产生误会。这愿望自然是好的,不过人们不禁要问:后宫内廷之事,诸如选妃、大婚、封典之类,朝廷大臣均当知之,何必非为“表著”不可?如欲为表其内阃细行,有此必要吗?终清之世,后妃众多,为什么唯有这名董妃需要特加表著呢?所以,我以为《行状》之撰别有用意。
复二,《行状》开篇,特首书曰:“后董氏,满州人也。”[7](357)这句话出自清朝皇帝之口,不仅有多余之嫌,且显为著意伪饰之破绽。何以知之?由史实知之也——清朝开国之初,有满汉禁止通婚之令,严禁汉女入宫。生当清季、官至侍读的吴士鉴撰《清宫词》八十四首,“或出于官书之记载,或采自私家之纂述”,诗之内容,为“有清一代宫禁旧事”。[8](1)其第四首注云:“顺治初年,孝庄皇后谕:有以缠足女子入宫者斩,此旨旧悬于神武门内。”[8](4)可见,清初禁止汉女入宫原来是一条十分严厉的法令。故终清之世,清史所载,后妃中没有一个汉人。既然如此,假若董妃果真是鄂硕的女儿,顺治的《董妃行状》只需写作“后,董鄂氏”足矣,何必开篇即大书特书“满州人也”呢?所以我认为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伪饰之辞。这种作伪,朝廷内外即有知之者,慑于皇权之威,谁敢啧有烦言?但可怜襄亲王却死得不明不白。若非有汤若望的亲历亲见作证,仅凭正史,这位年轻王子的死因,谁能知之?之臣可知。故有疑此为顺治之弟,名为博穆博果尔,顺治十二年十二月封襄亲王者,太宗之第十一子也。博穆博果尔顺治十三年七月初三日卒,年十六,二十七日服满,即为八月,故董妃以八月册贤妃,其时日适符也。”“其为董妃无疑。”[3](134)陈垣先生素以治学精湛刻实著称,其考证当是可信的。
又,现代学者邓之诚以“以诗证史”为宗旨,著《清诗纪事初编》,其卷五述李天馥云:“其诗体格清俊,自注时事,足为参考之资。别有古宫词百首,盖为董鄂妃作。自序昭阳殿里,八百无双,长信宫中,三千第一。愁地茫茫,情天漠漠,泪珠事业,梦蝶生涯,在昔同伤,于今共悼。语意甚显。词中‘日高睡足犹未起,薄命曾嫌富贵家’,明言董鄂先入庄邸。”[4](3555)李天馥为顺治十由检讨历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乃为时之人,其所讽咏时事,亦应可信。
复次,汤若望的《回忆录》亦具有史料价值,不可与稗乘野史同语。这望不仅是一位受宠于清朝廷的西洋是一位有真才实学的科学家。他于明(公元l623年)来华至京,因其通晓徐光启所器重,入清后复受清廷宠眷,在顺治朝先后被加官为钦天监掌印、太常寺卿,又诰封光禄大夫,恩赏祖先三代一品封典。顺治尝以“玛法”(汉语“爷爷”之意)称之,可见恩眷之隆。由于汤若望对清廷的忠诚和顺治对汤若望异常的宠信,故使两者之间相处关系之密切远远超出了所有朝廷大臣。据记载,汤若望奏事可以免循常例,可以随时径入内庭;顺治也经常到汤若望的寓所,不拘君臣礼节,“欢洽有如家人父子。”[5](296)尤可注意者,汤若望终顺治朝十八年间,一直是处在与顺治这种不同寻常的密切关系之中,他为了感激顺治知遇之恩,每每“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国家大事有关系安危者,必直言以诤之。”[6](297)由此可见,汤若望并非那种曲体情伪、无中生有之人。因此,汤若望具有了解顺治生活内幕的特殊条件,他的记载自然是可信的。然而,顺治自撰《董妃行状》所载董妃来历,却与汤若望《回忆录》所记大相径庭。《行状》云:“后董氏,满州人也。父内大臣鄂硕,以积勋封至伯,殁赠候爵,谥刚毅。后幼颖慧过人,及长娴女工,修谨自饬,进止有序,有母仪之度,姻党称之。年十八,以德选入掖庭……”[7](357)在这里,顺治说的和汤若望的记载有两点截然不同之处:一、汤只说是“一位满藉军人之夫人”,顺治则对此一字未提;二、汤说顺治皇帝“将这位军人的未亡人收入宫中,封为贵妃”,顺治则说“年十八,以德选入掖庭”。那么,这种互相矛盾的记载,当作何解释呢?回答应当是:此乃《董妃行状》作伪使然。
二、《董妃行状》疑点
董妃其实并不是“以德选入掖廷”的鄂硕的女儿。所谓董妃为鄂硕之女,只不过是顺治的《董妃行状》和依据《行状》由清廷官修的史书中的记载,不能作为信史的依据。因为清廷官修史书如《清世祖实录》,是经过了雍正至乾隆年间特意重修和校订的,而雍正是一个对乃祖顺治的不光采之事极尽包庇的皇帝。举一事为例:董妃死时,顺治将三十多名宫女赐死,为董妃殉葬。而雍正为了掩饰这一不道德的事实,在后来的御旨中却说:“我朝并无以人殉葬之事!”[2](92)这种明目张胆为尊者讳而篡改历史的做法,便使得多次“修改”后的《清实录》的史料价值越来越低。因而,其真相是不可能载入清史之中的。此乃情理中事。
董妃不仅不是鄂硕的女儿,而且也不是满藉人,而是一名汉女!有何为证?
三、对董妃身份的考证
顺治十年,清王朝曾为顺治举行过一次选妃活动,谕令“在内满州官民女子,在外蒙古王、贝勒以下,大臣以上女子”[1](52-53)都要参加应选。这是清王朝举行的第一次选妃活动,这次选中的却是科尔沁蒙古镇国公绰尔济的女儿博尔济吉特氏,而不是董鄂氏。
所以,董鄂妃应是汉女。
清初有严律,汉女不准入宫,何能成为皇后?其实并非尽然。清初虽有严禁满汉通婚、不准缠足女子入宫之令,但凡是被皇帝看中的女人,无论满、汉,照常可以在偷偷摸摸中进入宫内,甚至可以封妃封后。终清之世,这种情况并非绝无仅有。如康熙的生母孝康皇后,便是汉军之女,姓佟,入宫后改姓满族佟佳氏,一变而为满人了。又据近人考证,姓叶赫那拉氏的慈禧皇后,也是汉女,原藉山西长治县,本名宋龄娥。慈禧的五世侄孙和侄甥联名向当地史志办公室首次披露了这一前所未闻的秘史,并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这一新说,虽未可定论,却足以发人深思。可见,在“汉女不准入宫”的堂皇的禁令下,并不能禁住颁发禁令的皇帝本人。只要是皇帝(或王子王孙)看中的女人,是完全可以用改变族藉姓氏甚至伪造历史的办法来达到其目的!试想,如果本是汉女的董妃入宫后被皇帝赐姓“董鄂氏”,并落在鄂硕的名下作为一名女儿,朝廷内外臣民有谁敢去查皇妃的族谱?即便有人风闻内幕,又有谁敢在当时写作的文字中留下半句真实消息的记载去招惹杀身灭门之祸?历史的真实被伪造,伪造的历史留了下来,这完全是应当被承认的历史现象。《清实录》中传抄本与所谓“正本”记事就多有不同之处,蒋良骐先生的《东华录》与王先谦先生的《东华录》亦有差异。由于清王朝对国史的不断删改“修定”和伪造——将不光彩的隐讳之事消除之,把显宗耀祖之事光大之,故愈是“修定”后的“正本”,其史料价值便愈低。清朝开国史事和“文字狱”等记载的失实,即是显例。董鄂妃来历之作伪,不过是伪史中的一个小小情节而已!此亦可作为“尽信书不如无书”之一注脚也。
四、《董妃行状》作伪
如果我们没有理由不承认汤若望的记载是真实的,董鄂妃的确曾是襄亲王的妻室,而这位女人又是汉女而不是满人,那么,《董妃行状》之不足据,自不待言。可是顺治为什么偏偏要在《行状》中显赫地写上“后董氏,满洲人也”[7](357)这七个字呢?又为什么文辞写得有声有色,迷惑史坛达三百年之久呢?欲破迷雾,当先从《行状》撰写过程的真相说起。
原来所谓顺治御制《董妃行状》,其实并非顺治自撰,乃是出自内院大学士金之俊之手,为金之俊受顺治嘱意撰写而经顺治寓目托为“御制”者。何以知之?由金之俊《奉敕撰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传》(下简称《后传》)与《董妃行状》比较可知。细读《后传》和《行状》,即不难发觉,两者不仅文气相同,命意相同,直至大段文字也相同。简直如出一人之手。对于历时三百年的董鄂妃来历之疑,发覆者有之,考实者有之,然而对于《后传》和《行状》这两篇“奇文”却未有加以考辨者。笔者有憾于此,所以不惮烦琐,在此摘要加以比较,以利辨析:
A.记董妃禅悦事。
《后传》文:
后素不信浮屠氏,上流览经史,博极群书,尝以其余研心内典,契甚深义。因为后解释《心经》,遂信向禅学,参究宗旨,上偶一拈提,辄有省……[9](135)
《行状》文:
后素不信佛,朕时以内典禅宗喻之,且为解《心经》奥义,由是崇敬三宝,栖心禅学,参一口气不来向何处安身立命语,每见朕,即举之……[7](360)
B.记董妃卧病状态。
《后传》文:
自婴病后,从未偃卧,但凭椅榻,息心静坐。及病笃,犹忆上拈提之语,时为举似。故大渐时,言动如常,一心不乱,唯持念佛号。端然嘘气而化。崩数日后,颜貌整洁,犹无异生前……[9](135)
《行状》文:
自婴病后,但凭几倚榻,曾未偃卧。及病渐危,犹究前说,不废提持。故崩时言动不乱,端坐呼佛号,嘘气而化,颜貌安整,俨如平时……[7](360)
C.记董妃丧葬从俭事。
《后传》文:
后复谓上曰:“妾亡,度诸王等必来致赙,妾思人生世间,身外皆长物,死复何用?陛下诚念妾,与其虚糜无益,孰若施诸贫乏为善也。”已又嘱左右曰:“慎勿以绮丽束我体,崇上敦崇俭朴,不以玉食万方,稍移奉其身,如用诸华丽物,殊违上意,亦非我素心也。盍以我所遗者广行善事,庶有利益耳。”故殓具悉从俭约,上更以赙金二万余赈施贫乏,盖一一从后语也……[9](136)
《行状》文:
既,复谓朕曰:“妾亡,意诸王等且必皆致赙,妾一身所用几何?陛下诚念妾,与其虚糜无用,孰若施诸贫乏为善也。”复嘱左右曰:“我逝后,束体者甚勿以华美,皇上崇俭约,如用诸珍丽物,违上意,亦非我素也。曷若以我所遗者,为奉佛诵经需,殊有利益耳。”故今殓具,朕重逆后意,概以俭素,更以赙二万余金施诸贫乏,皆从后意也……[7](360-361)
D.记宫人殉葬事。
《后传》文:
后天性慈惠,平日宫中人均被赐予,感怀其仁,故哀痛甚笃,愿以身殉者多……[9](138)
《行状》文:
后天性慈惠,凡朕所赐赉,必推施群下,无所惜。故今宫中人哀痛甚笃,至欲身殉者数人。[7](359)
上引除称谓语气的转换外,其含义毫无二致,甚至语句文字完全雷同。当然我们不排除顺治在爱妃死后痛定思痛,为董妃写一篇《行状》的可能,但值得怀疑的是,二十几岁的少年天子,即便他的汉语文字水平能够写得出这种文绉绉的汉语文章,可是董妃死后,他一直处在一种异常哀痛甚至发狂的极不正常的精神状态之中,此时行文命笔,实难设想。所以当此之际,顺治命他所宠信的大学士金之俊,按照圣上旨意,先草撰《行状》,经顺治过目同意后,又命金之俊按照同一个内容再写一篇董妃的传记,才是情理中事。理由很简单,若不是顺治专门特意嘱托,文内那些董妃的言动细节、闱榻密语,作为朝臣的金之俊何能得知?且知之如此细微周详?若非出于一人之手,《后传》和《行状》的文辞情节又为何如此雷同?其实,草《行状》,写《后传》,这个捉刀的任务落在汉臣金之俊的头上,并非偶然。金之俊在历史上是被列入了《贰臣传》的,可见他在政治上是有一套上下其手的本领。他是明朝万历进士,在明为兵部右侍郎,入清后先官原职,后因向清廷献策有功,屡承恩眷,累官至内院大学士要职,“效力于满清凡十有八年,开国方略,咸出其手”。[10](2)时人曾送他一句大不敬的话,谓“从明从贼又从清,三朝元老大忠臣”。[10](2)对于金之俊来说,受命撰写皇帝爱妃的《行状》和《后传》文,实乃莫大之荣幸,理当受宠若惊。至于内容真实与否,何必多劳思虑?只要圣上怎么交代就怎么写得了!于是乎,传世不朽并为正史所本的“御制”《董妃行状》便这样出台了!因为是皇帝的“御制”,谁敢对其产生怀疑?当然是最“信”的“信史”了。殊不知顺治按照自己的意图命金之俊撰写的这篇“奇文”,却是一篇名符其实的“欺世杰作”!其中谎言连篇,不胜枚举。当道者如为尊者讳而奉为“史”,尚有情可原;如治史学者,亦甘心为其蒙蔽,则迂矣。今举数事辨析其内容之荒谬如下:
(一)上引董妃丧葬从俭事
《行状》谓:“故今殓具,朕重逆后意,概以俭素。”[7](361)这是谎言。按世祖《遗诏》谓:“仰奉慈纶,追念贤淑,丧祭典礼,过从优厚,不能以礼止情,诸事逾滥不经。”[9](136)现在所见世祖《遗诏》,据孟森考证,是由孝庄太后改定,并不是世祖临崩前所见的原草。顺治生前,凡对与董妃有关之“逾滥不经”的情事,大多采取隐瞒态度,临死前是不会将隐之唯恐不秘的事情如实说出来的。皇太后改《遗诏》,也可证孝庄对顺治与董妃的这段姻缘是怀有成见,对董妃入宫心怀怨意。皇太后所以要如实明确地指出顺治这种与董妃的“逾滥不经”之过,其意一则是为了表达她在顺治生前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二则作为一种鉴诫,好让下一代的皇帝接受教训。所以遗诏中所言,必是事实。
究竟董妃的丧葬“过从优厚”到什么程度,汤若望《回忆录》中有一段比较详细的记载,可资参考:“为殡葬事务,曾耗费极巨的国帑,两座装饰得辉煌的宫殿,专供自远地招来的僧徒做馆舍,按照满州习俗,皇妃的尸体连同棺椁,并那两宫殿,连同其中珍贵陈设,俱都被焚烧”。[1](53)这种惊人的糜费和场面,正好与吴梅村《清凉山咏佛诗》中的描述“殊方初云献,知破万家室,瑟瑟大秦珠,珊瑚高八尺,割割施精蓝,千佛庄严饰,持来付一炬,泉路谁能识?红颜尚焦土,百万无容惜”[11](724-725)的内容完全吻合。难道这就是丧葬“概以从俭”吗?《行状》之作伪,以至于此,董妃来历,岂能无疑?
(二)关于殉葬:
《行状》谓:“至欲身殉者数人”[7](359),意即是说,由于董妃的德行感人,以至于数名宫女愿意殉死。这种含糊其辞的文字,使人觉得似乎殉葬并未成为事实,只是“欲”殉而已。这又是伪造!其实际情况是:贵妃薨逝,“皇帝陡为哀痛所致,竟致寻死觅活,不顾一切,人们不得不尽夜看守着他,使他不得自杀,太监与宫中女官共三十名,悉行赐死!”[1](53)殉死者三十名,是强行“赐”死,而不是自愿“欲”死!一字之差,便致黑白颠倒,《行状》的伪造笔法,可以说相当巧妙。清初皇家殉葬之事,本来并不十分忌讳,如顺治年间,肃王豪格、豫王多铎、睿亲王多尔衮等,死后均有妃妾殉葬,一至三人不等。只是董鄂妃的殉葬,无论在当时抑或是顺治崩逝以后,似乎都有点敏感,甚而
讳莫如深。直至数十年后的雍正胤祯,还在谕旨中不遗余力地为此事辩护:“玉林弟子……作《侍香记略》,荒唐诞妄之处不可胜举,如云端敬皇后崩,茆溪森于宫中奉旨开堂,劝朝廷免殉葬多人之死等语,我朝并无以人殉葬之事,不知此语从何而来?”[12](91-92)这位在历史上以残忍和玩弄权术著称的皇帝,其所以为乃祖辩护,可能是因为他发觉汤若望、茆溪森等这些曾在顺治身边生活过的教徒们所发表的亲历亲见的记载,有损于大清王朝的尊严,或者说触及了其乃祖顺治的一段甚不光彩的隐秘,所以便以皇帝之尊出来“辟谣”。但这样一来,不但不能正视听于后世,反而给人留下了怀疑的破绽,正如陈垣先生早就说过的那样,实乃“欲盖弥彰而已!”
(三)虚构董鄂妃来历:
《行状》作伪的大破绽,是隐去了董妃入宫的时间,而又标明“后董氏,满州人也”[7](357)这句话。这正是少年天子掩人耳目之语。一篇长达四千余言的《行状》,对于董妃的闱闼私语,一言一颦,不惮烦琐,靡不备述,极尽摹绘之能事,唯于入宫之经过,却一语带过。
孟森先生曾著《董小宛考》,认为将董小宛比附董鄂妃是不根之谈,详引《忆语》中冒襄所述小宛生活经历,以证小宛未曾被清兵掠去、小宛死后坟墓葬在影梅庵、顺治与小宛年龄相差甚多不可能被纳为妃等情节,对此一疑案完全予以否定。孟氏考核翔实,多为史学界所服膺。然而既然《忆语》不能做历史看,引《忆语》以证史事,说服力便失其大半。以下就汉女能否入宫为妃问题和因年龄差距问题再加论析:
清室入主中原以后,首禁满汉通婚,著为甲令,实际并未严格实行。顺治选纳汉女石氏入宫便是显例。据王士祯《池北偶谈·谈异五》:“世祖皇帝恪妃石氏,滦州人,户部侍郎申之女也。”[13](591)《永平府志》也记载:“石申,字仲生,滦州人……先是世祖章皇帝稽古制选汉宫女备六宫,申女及笄,承恩赐居永寿宫,敕召申妻赵淑人乘肩舆入西华门,至右门下舆入宫行家人礼,赐重宴。"[14](87-88)又夏云虎《清宫词》云:“通婚满汉始章皇,入选蛾眉许汉妆,金谷园中好春色,弓弯云髻拜昭阳。”[14](87)注云:“世祖初欲以汉女备六宫,选滦州侍郎石申女入居永寿宫,后为太后所阻。”[14](87)《永平府志》与《清宫词》所记稍异,前者谓承恩赐居永寿宫已成事实,后者则谓为太后所阻。实际情形当是太后阻而未成,石氏入宫当真。不然何以康熙朝追封为妃?由此推知,董鄂妃是汉女入宫。
孟森先生以为,顺治与小宛年龄相距如此之大,决无缔婚之理。据张明弼《冒姬董小宛传》,董小宛死时二十七岁,时当顺治辛卯八年,顺治为十五岁,确是两者年龄相差甚远。但世间“少夫而娶老妻者”并非“未闻”之事,即万乘之尊而娶老妻,亦非仅见。明宪宗朱见深之娶万贵妃便是明显一例。万氏原是宪宗祖母的侍女,成化二年,万氏被宪宗宠幸而册封贵妃,时宪宗20岁,万氏37岁。万妃比明宪宗大17岁,董妃比顺治大12岁,两者相较,后者犹小巫耳!——后宫嫔妃众多,宫女如云,宪宗却偏偏看中了这位比自己大17岁且出身寒微的万氏,以至于专房异宠,封为贵妃,势胜皇后。无独有偶的是,当万贵妃死时,宪宗也是与顺治那样,伤心得“痛不欲生”,“长叹曰:‘万侍长去了,我亦将去矣!’于是悒悒无聊,日以不豫,至于上宾。情之所钟,遂甘弃臣民不复顾。”[15](84)可见男女感情一事,本极复杂,有不可以常理度之者。请看明宪宗与万妃同清世祖与董妃之所为,不是如出一辙吗?怎能说顺治与董妃,年龄相差,决无缔婚之理呢?臆断之词,不足为据。
或曰:《董妃行状》载董鄂妃年十八入宫庭,而张明弼《冒姬董小宛传》则谓小宛年二十七,以劳瘁病卒。如果说冒襄是将小宛被掠入京的日期作为“长逝”之日,那么两处所载年龄则不符合。这将如何解释?笔者以为张明弼所记二十七岁为真,顺治所说十八岁为假。如前所述,顺治既可把汉女伪改为满女,怎不能把二十七岁虚拟为十八岁呢?只是需明悉的是张明弼的《董小宛传》,它是据冒襄《影梅庵忆语》和《董姬哀辞》写成,大体一如《忆语》,好像是张明弼受辟疆之托而写成。不然传中述小宛言动声貌,有如亲历,如非辟疆口授,怎能逼肖到这种地步?顺治授意金之俊撰《董妃传》,是为了维护“御制”《董妃行状》的“权威性”,以欺世人耳目;冒襄委托张明弼写《董小宛传》,则是为了羽翼《影梅庵忆语》的“可信性”,以消弭社会流言,免遭爱妻被辱之耻。《行状》与《忆语》,《董妃传》与《小宛传》,两相映照,不谋而成趣。
五、结论
通过对《御制董妃行状》的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所谓《御制董妃行状》,不是顺治亲笔所撰,而是金之俊受命所为,其所述董鄂妃的来历,多是作伪之言,并非“信史”。
(二)董鄂妃不是满人,而是汉女。汉改满籍,托为满大臣鄂硕的女儿。
(三)董小宛被掠,辗转入宫一事,三百年来代代相传,影响深远,虽因无直接史料可征,董鄂妃是否董小宛,难成定论,但可疑之处依然存在。而对《御制董妃行状》这一重要文献的研究,则有助于这一疑案的深入探讨。
[1]万依,王树卿,刘潞:《清代宫廷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版,1990。
[2]陈垣:《陈垣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4]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上海:上海古藉出版社,1984。
[5]费赖之:《入华耶苏会士列传》,清史编委会,《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
[6]魏裔介:《贺汤若望七秩寿文》,《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7]徐珂:《世祖自撰董妃行状》,《清俾类钞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8]钱唐九钟主人:《清宫词》,北京:北京古藉出版社,1986年。
[9]钱仲联:《梦苕庵专著二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10]《清朝野史大观第二册——清朝史料》,上海:上海书店,1981年。
[11]程穆衡:《吴梅村诗集笺注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12]黄夏年: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陈垣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13]王士祯:《池北偶谈》,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14]刘潞选注:《清宫词选》,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5年。
[15]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I207.41
A
1002-2007(2012)01-0037-06
2011-09-10
1.于春海,男,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2.赵乐,女,延边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作家作品研究。(延吉133002)
[责任编辑 全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