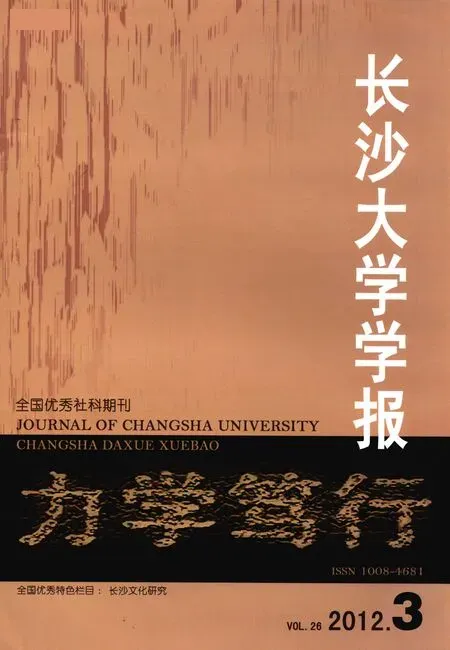论本雅明翻译思想对传统翻译忠实观的消解*
——以《论语》多种英译本为例
章亚琼
(遵义医学院外国语学院,贵州遵义 563003)
论本雅明翻译思想对传统翻译忠实观的消解*
——以《论语》多种英译本为例
章亚琼
(遵义医学院外国语学院,贵州遵义 563003)
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一文里提出来世说,他赋予原文以生命,认为艺术作品的生命包含前世、今生和来世,而翻译的出现是因为原文的生命在演变。以《论语》多种英译本为例,发现作为翻译原文的《论语》并非恒定不变,而是在不断发展变化,因此其英译本也不可能忠于原文。至此,传统翻译理论信奉的翻译忠实观遭到了消解。
本雅明;翻译忠实观;消解;《论语》英译本
一 传统的翻译忠实观
各种语言都是相通的,而对等词自然而然存在于各种语言之间[1]。作为两种语言间的翻译在过去就是“简单比附或对照原文译文……所得的结论不外是译文是否忠于原著,又或是译者怎样解决原文文本所出现的翻译难题”[2]。此种忠实的翻译观在中西传统翻译理论中比比皆是。比如,我国三国时期支谦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后秦高僧鸠摩罗什对“虽得大意,殊隔文体”的批评,近代严复的“信、达、雅”,再比如古罗马圣·杰罗姆的“有时意译,有时直译”,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奈达的“动态对等”。法国修辞学家梅纳日(Menage)甚至用“不忠的美人”(les belles infideles)指称翻译。一语以蔽之,传统的翻译理论始终纠缠于原文与译文的对等问题,是一种忠实的翻译观。
二 本雅明的翻译思想
瓦尔特·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1892-1940)是20世纪初德国最重要的思想家和文艺批评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文学翻译家。他的翻译思想,主要体现在1923年发表的《译者的任务》(Die Aufgabe des Bbersetzers)一文中。在文中本雅明针对语言、翻译、译者以及原文与译文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一些颇为独到和令人震撼的看法,诸如纯语言(pure language)、来世(afterlife)以及花瓶的碎片(fragments of a vase)和切线(tangent)等意象。《译者的任务》因此被奉为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经典,本雅明本人也被尊为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奠基人。尤其是他提出的来世(afterlife)说,更是有助于消解传统翻译理论始终纠缠不休的原文与译文的对等问题。
在《译者的任务》一文里,本雅明赋予原文以生命。“生命并不限于肉体存在。对于艺术作品的生命与来世之观念,我们应从一个全然客观而非隐喻的角度去看……只有当我们把生命赋予一切拥有自己的历史而非仅仅构成历史场景的事物,我们才算是对生命的概念有了一个交代。”本雅明说“伟大艺术作品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些作品的渊源,它们在艺术家的生活时代里实现,以及它们在后世里的潜在的永生。这种潜在永生的具体表现叫做名声”[3]。可见所谓原文的生命也就是原文的历史。显然,在本雅明看来,作为与译文相对应而出现的概念,原文的生命包含前世(作品的渊源)、今生(在艺术家的生活时代里实现)和来世(或名声,其在后世里的潜在的永生)。
名声起,则翻译生。译文的生成是由于原文的演变,由于原文进入了其生命的第三个历史时期——来世。如果一部译作不仅仅是传递题材内容,那么它的面世标志着一部作品进入了它生命延续的享誉阶段。所以译文并不源于原文,而是源自其来世。本雅明把原文与译文的关系比作生活的现象与生活的表白之间的关系。“正如生活的表白虽与生活的现象密切相关却对之不构成任何重要性,译作也由原作生发出来。不过它由以生发出来的不是原作的生命,而是原作的来世。翻译总是晚于原作,世界文学的重要作品也从未在问世之际就有选定的译者,因而它们的译本标志着它们生命的延续。”[3]
译文标志着原文生命的延续,换言之,翻译的出现是由于原文的生命在演变。既然原文都在演变,又怎能以之为基础,要求译文忠实于原文?甚至指责其为“不忠的美人(les belles infideles)”?所以,本雅明会说“如果译作的终极本质仅仅是挣扎着向原作看齐,那么就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译作。原作在他的来世里必须经历其生命中活生生的东西的改变和更新,否则就不成其来世。即使意义明确的字句也会经历一个成熟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流逝,某个作者文学作品中的明显倾向会逐渐凋萎,而其文学创作的内在倾向则会逐渐抬头。此时听上去令人耳目一新的辞藻彼时或许会变成老生常谈,曾经风靡一时的语句日后或许会显得陈旧不堪。”[3]
至此,传统翻译理论中的翻译忠实观遭到消解。传统翻译理论通常认为原文决定译文,译文应该忠实于原文,并在此基础上求信、求达、求雅。翻译的终极使命就是要追求原文与译文的对等,译者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克服原文文本所出现的翻译难题,无论他是否“有时意译,有时直译”。他所孜孜以求的就是某种“相同的美学体验”或者说“语言结构/动态对等”。显然,传统翻译理论所倡导的这种“翻译忠实观”有一个前提——原文必须是一恒定不变的中心。然而,它所假定的这个中心真的能岿然不动吗?由此而引出的忠实真的可能吗?本雅明很明白地告诉我们,原文并不是一个恒定不变的中心,而是有其前世、今生和来世。而正是在译文中,原文的生命之花“得到了最新的也是最繁盛的绽放。”可见原文并不能决定译文,决定译文的是原文的来世。因为译文并不源于原文而是源自其来世。而由于原文在他的来世里必须经历“其生命中活生生的东西的改变和更新”,译文也就不可能总是向原文看齐,不可能忠实于原文,甚至以此为基础求信、求达、求雅。正因为这个原因,像梅纳日之流的传统翻译理论家用“不忠的美人”来指称翻译是没有道理和依据的。
三 作为翻译原文的《论语》
《汉书·艺文志》云:《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撰,故谓之《论语》。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论语》一书并不是孔子亲笔书写,因而也就没有作者的权威来保证其恒定不变。他只是夫子言行的记录,是孔门众弟子对夫子和自己、夫子与当时之人,以及被夫子听到的众弟子之间的对话所做的记载。这些记载在孔夫子去世之后,由众门人经过讨论、遴选,最后编纂成册。《论语》这部儒家经典的生成并不是某个人的智慧,而是众人的劳动成果。他的编撰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一个过程。这一编撰成书的过程正如本雅明所言是“伟大艺术作品的历史”,而《论语》一书正是“在艺术家的生活时代里实现”。显然,翻译中作为原文的《论语》并不像传统翻译理论以为的那样恒定不变、岿然不动而是自有其生命的。
著名学者钱穆说“《论语》自西汉以来,为中国识字人一部人人必读书。读《论语》必兼读注。历代诸儒注释不绝,最著有三书。一、何宴《集解》,网罗汉儒旧义。又有皇侃《义疏》,广辑自魏迄梁诸家。两书相配,可谓《论语》古注之渊薮。二、朱熹《集注》,宋儒理学家言,大体具是。三、刘宝楠《论语正义》,为清代考据家言一结集。”[4]当译者翻译《论语》时,作为翻译原文的就不仅限于《论语》一书,古往今来的若干注解都是译者翻译时的原文。这些注解正如本雅明所言是《论语》这一伟大艺术作品“在后世里的潜在的永生”,是《论语》生命持续的演变。
四 众多英译者眼中的《论语》
《论语》虽然很早就传入朝鲜、日本,但直到1593年利玛窦把《四书》译为拉丁文寄回意大利,《论语》才为欧洲人知晓。《论语》的英译虽然在17世纪末期就已经开始,而正式的英文译本却要等到19世纪初期才出现。据王勇(2006)所言,《论语》的英译本至少有20多种[5]。英译《论语》的既有中国人(如辜鸿铭、黄继忠等),又有外国人(如理雅各、苏慧廉等)。考察不同英译的译者序言、致谢等材料,可以发现作为原文的《论语》在众多译者眼中究竟是如同传统翻译理论所说的是一恒定不变的中心,还是恰如本雅明所言“自有其生命,有其前世、今生和来世”。
潘富恩和温少霞于1993年推出了《论语今译》。在书中“英译说明”一章,作者谈到“由于《论语》的特殊历史地位,历代都有大批的《论语》研究者和注释者。在古代,最经典的注本是朱熹的《论语集注》;在当代,较权威的注本为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如今,吴树平又在杨氏译注的基础上加以修订……正是为了弥补这个不足,我们以吴树平修订的今译本为根据将《论语》译成英文,同时兼採国外的《论语》研究成果,参考了 James Legge的 Confucian Analects,Leonard A.Lyall的 The Sayigns of Confucius和 Arthur Waley的 The Anelects of Confucius等译本”[6]。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两位译者翻译时,作为原文的《论语》并不像传统翻译理论以为的那样恒定不变。“吴树平修订的今译本”,“国外的《论语》研究成果”乃至“James Legge的Confucian Analects,Leonard A.Lyall的 The Sayigns of Confucius和 Arthur Waley的 The Anelects of Confucius等译本”都是本雅明所谓的原文之“来世”,原文“在后世里的潜在的永生”,都是《论语》一书“在他的来世里必须经历的生命中活生生的东西的改变和更新”。
美籍华人黄继忠在他的译作的致谢部分里说“经过十年的研究、写作和修改,我将这本《论语》新译交付印刷。我不敢将本书看做我个人的功劳。因为促成本书完成的还有古今中外的众多学者。首先,我要特别感谢从汉至今的众多《论语》注释者,因为他们的作品极大加深了我对文本的理解并提高了翻译的忠实度。我还要感谢翻译这本巨著的一些先行者,例如理雅各、亚瑟·威利、刘殿爵、魏鲁男以及雷蒙·道森。他们译作中的优点和不足都使我在翻译时受益匪浅。”[7]照黄继忠的话来看,显然“古今中外的众多学者”对该书所作的注释以及“理雅各、亚瑟·威利、刘殿爵、魏鲁男以及雷蒙·道森”等翻译先行者的译本都对他的翻译具有参考价值,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也都可以看作黄继忠翻译时的原文。显然作为原文的《论语》在黄继忠的翻译过程中并不像传统翻译理论以为的那样恒定不变。相反,正如本雅明所言,《论语》也有生命,会在古今中外众多注释家和翻译家的手中不断发展演变,“在他的来世里必须经历其生命中活生生的东西的改变和更新”。
五 以术语“仁”的翻译为例
《论语》本身有生命,一直在演变,其中的术语自然也是如此,也会有生命的演变,以术语“仁”为例。《说文》曰,小篆“仁”,从“人”,从“二”。“仁”是二人合而为一,乃亲如一体也。杨伯峻在《论语译注》中说它在书中出现的次数多达109次。例如,在《颜渊第十二篇》的第一章就有这样一句:
颜渊问仁。
尽管术语“仁”出现在“颜渊问仁”这样相同的语境当中,他的翻译在不同译本中却不尽相同。现将笔者收集到的理雅各、威利、刘殿爵三人对该章的翻译列举如下:
1)Yen Yuan asked about perfect virtue.[8]
2)Yen Hui asked about Goodness.[9]
3)Yen Yuan asked about benevolence.[10]
理雅各将“仁”译作“perfect virtue”(完美的德行);威利译作“Goodness”(善心);而在刘殿爵的译本中“仁”被译成“benevolence”(仁慈)。之所以出现上述差异,除了译者的主观因素以外,还与古今中外众多学者对术语“仁”所作的不同注解有关。这些注解使得术语“仁”的生命持续发展演变,而非像传统翻译理论以为的那样恒定不变。
作为基督教传教士,理雅各进行翻译实践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传教。然而在他看来要实现这个目的就意味着他首先必须了解并接受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为此他开始学习并陆续翻译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因此在他的译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历代诸儒的影响。比如在此句的翻译中,他将“仁”译为“perfect virtue”,很明显是受宋代理学大师朱熹的影响。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里说:“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11]显然在朱熹看来,“仁”乃本心之德。受其影响,理雅各也认为这里的术语“仁”应该指示儒家所提倡的完美的德行,因此将之译作“perfect virtue”。
英国汉学家威利的《论语》译本出版于1937年。他把此处的术语“仁”译作“Goodness”,指示为儒家所推崇的一种道德标准。他的译文很明显是受《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的影响。北宋初年著名经学家邢昺在此处的注疏中说道:“此章論仁者必直言正色。其若好其言語,令善其色,欲令人說愛之者,少能有仁也。”[12]换言之,具有“善心”的人必定直言正色。如果一味用甜言蜜语谄媚他人,这样的人,应该没有什么善心。显然在邢昺看来此处的术语“仁”应该指示“善心”。受其影响,威利将“仁”译作“Goodness”。
香港学者刘殿爵的《论语》英译本于1992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作为现代华人学者,他的译文明显深受当代大陆学者的影响。杨伯峻在1980年出版的《论语译注》中对此处的注解是:孔子说:“花言巧语,伪善的面貌,这种人,‘仁德’是不会多的。”[13]杨伯峻认为此处的术语“仁”指示“仁德”,即仁慈的品德。受其影响,刘殿爵在翻译此处时才会将术语“仁”译为“benevolence”。
显然作为原文的术语“仁”并不像传统翻译理论以为的那样岿然不动。恰如本雅明所言,诸如“perfect virtue”“Goodness”和“benevolence”之类的翻译都是作为原文的术语“仁”经由朱熹、邢昺、杨伯峻之手进入其生命的第三个历史时期——来世时所绽放的最新的也是最繁盛的花朵。
六 结语
传统翻译理论始终纠缠于原文与译文的对等问题,认为忠实是翻译不变的圭臬,追求译文尽可能准确地传达原文的意义和形式。这种翻译忠实观本质上是一种静止的形而上学思维。本雅明的来世说对此提出了强烈质疑和挑战。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一文里赋予原文以生命,认为艺术作品的生命包含前世、今生和来世(又叫名声)。换言之,翻译的出现是因为原文的生命在演变。这无疑是一辩证的思维,与传统翻译理论的静止的翻译忠实观截然相反。以翻译原文的《论语》及其术语为例,都具有本雅明所谓的生命历程,又怎么能强求其英译本忠实于原文呢?至此,传统翻译理论信奉的翻译忠实观遭到了有力消解。
[1]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M].北京:三联书店,2002.
[2]王宏志.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3]汉娜·阿伦特.启迪:本雅明文选[M].张旭东,王斑,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
[4]钱穆.论语新解·序[M].北京:三联书店,2002.
[5]王勇.20 年来的《论语》英译研究[J].求索,2006,(5).
[6]潘富恩,温少霞.论语今译[M].济南:齐鲁书社,1993.
[7]Confucius.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M].Chichung Huang,tran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8]Confucius.The Four Books[M].James Legge,trans.Shanghai:The Chinese Book Company,1930.
[9]Confucius.The Analects[M].Arthur Waley,trans.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1998.
[10]Confucius.The Analects[M].Lau D C,trans.Hong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92.
[1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2]阮元.十三经注疏附校堪记·论语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3]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H159
A
1008-4681(2012)03-0089-03
2012-01-08
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青年项目“基于《论语》多种英译本的瓦尔特·本雅明翻译思想研究”,编号:11GZQN25。
章亚琼(1979-),女,重庆人,遵义医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翻译研究与文化。
(责任编校:陈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