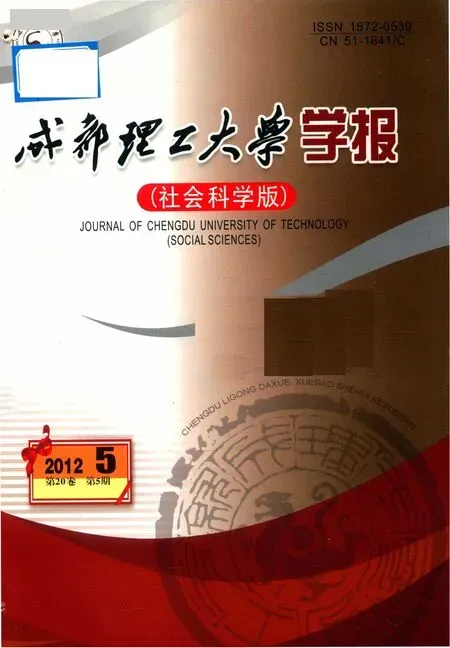置于主流话语意识下的女性关照
——论郭沫若的历史剧
李正红
(安徽滁州学院 文学院,安徽滁州 239000)
置于主流话语意识下的女性关照
——论郭沫若的历史剧
李正红
(安徽滁州学院 文学院,安徽滁州 239000)
在历史剧创作中,郭沫若将女性观照放置在主流话语意识下,塑造出的女性具有不同的时代质感。20世纪20年代的女性在“五四”个性解放意识浸染下最具叛逆意识,20世纪40年代的女性意识更多凸显的是左翼斗争意识,20世纪60年代的女性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更强调实践主体功能。相应地,郭沫若女性观照的价值取向也带有权力话语意识。
郭沫若;历史剧;女性意识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郭沫若可以算是一个女性主义意识强烈的男性作家。“我们如果要救济中国,不得不彻底解放女性”[1]137,20世纪20年代的郭沫若已是女性主义的有力呐喊助威者。“女性之受束缚,女性之受蹂躏,女性之受歧视,象我们中国一样的,在全世界上恐怕是要数一数二的”[1]137。对女性深怀同情之心的郭沫若,运用浪漫主义手法,借助于一系列古美人形象,公然抨击男性道德中心的不合理现象。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主张变革社会,建设思想,所以他们就有相似的左翼倾向和理想主义色彩。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郭沫若,打通女性解放和社会解放之路,结合不同时代和斗争的需要,给历史上实有其人或虚构的女性“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2],在20世纪革命这个主流话语意识的引导或调适下,使塑造出来的女性形象呈现出不同的时代质感,预设着现代女性解放之路。
一、20世纪20年代:弱势状态下的女性叛逆
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价值标准体系中,女人只是附属品,没有经济和政治基础,从而就失去了话语权,女人的名字就是弱者。“女人在精神上的遭劫已经有了几千年,现在是她们觉醒的时候了呢。她们觉醒转来,要要求她们天赋的人权,要要求男女的彻底的对等,这是当然而然的道理”[1]134,但当男权与女权这一对强弱者之间的对抗累积到一定限度时,一旦有了新思想、新动力注入时,便会出现狂风暴雨般的呐喊。卓文君说:“你们男子们制下的旧礼制,你们老人们维持着的旧礼制,是范围我们觉悟了的青年不得,范围我们觉悟了的女子不得!”。卓文君是一个有才情、有思想的女性,但在她的那个时代,她还不太可能具有这样的觉悟。但在郭沫若所赋予的“五四”个性主义解放思想的主流话语意识浸染下,自由、自主、叛逆代表了沉睡几千年女性的共同心声。女性观照更直接地体现为与男性的分庭抗礼,全面否定男权至上的神话,争取做人的尊严和资格。“我以前是以女儿和媳妇的资格对待你们,我现在是以人的资格对待你们了”。卓文君敢于打破常规,敢于做“在家不必从父”标本,敢于顺应人性发展的合理需要私奔相如,就性别斗争而言,她是具有非常强烈的革命性的。
在“五四”话语意识的干预下,王昭君被塑造成了一个中国版的叛逆出走的娜拉。“你的权力可以生人,可以杀人,你今天不喜欢我,你可以把我拿去投荒,你明天喜欢了我,你又可以把我来供你的淫乐,把不足供你淫乐的女子又拿去投荒。……豺狼没有你丑,你居住的宫廷比豺狼的巢穴还要腥臭!啊,我是一刻不能忍耐了”,我要“到沙漠里去”。出身低微的王昭君却拥有高贵的人格,藐视权钱交易,无视皇权圣威,不愿做男人的玩偶,即使被男人许愿当皇后也不行,自愿下嫁塞外,虽然不知道等待自己的下一个男人会是什么样,但在那一刻,她保有了一个女人难能可贵的尊严。
在“五四”思想大爆炸时期,作为多血质的激情奔放的郭沫若,狂飙突进地喊出了女权运动的宣言。和后来的女性形象相比,郭沫若20世纪20年代历史剧中的女性意识最为强烈,但人物过于扁平,艺术感染力不足。20世纪20年代中期,随着革命文学的兴起,郭沫若的思想也发生很大变化,带有一定的左翼色彩。原先酝酿很久的第三个叛逆女性由蔡文姬改写成聂嫈,一个很重要的因由是,“五卅惨案”的现实触发“我时常对人说:没有‘五卅惨案’的时候,我的《聂嫈》的悲剧不会产生的,但这是怎样的一个血淋淋的纪念品呦”[1]146。在革命视阈中,作者赋予聂嫈更宽广的天地,跳出了个人斗争的私语的狭小圈子,为了更多人的自由和解放,投入社会斗争洪流中,以女人的鲜血祭奠正义革命。
二、20世纪40年代:斗争状态下的女性意识回归
随着斗争逐渐进入白热化和残酷化,左翼思想主宰主流话语意识,此时的郭沫若更注重文学的政治宣传功能和服务现实斗争功能。在郭沫若三个时期的历史剧创作中,20世纪20年代和60年代涉及女性的剧本全是以女性为主角,并直接以女性名字命名,20世纪40年代的剧本,女性全退位于男性做配角,女性意识让位于左翼主流话语意识,斗争、正义、民族团结是这一时期主导词。这一时期的人物形象分为男人与女人,男人又划分为代表正义的光明形象和代表丑恶的黑暗形象。对于丑恶男人形象,女性角色极力抨击,女性意识高涨;对于光明男人形象,女性角色极力爱慕,女性意识消退。造成女性这一矛盾形象的最重要原因是左翼斗争意识对女性意识的驾驭。女性意识让位于残酷的社会革命。
其中最具代表的是如姬和婵娟。如姬是最富有胆识也是女性意识最强的一个。作为魏王的宠妃,如姬深知自己的处境,只是男人的“马儿”、“玩具”,并不具有人的主体地位。所以她倔强地说到:“像国王那样的人,实在连我都不高兴他”“连他的儿女我也绝对不要。他那样的人决不会有好的儿女”。作为女人,如姬有自己爱人的标准,只爱仁爱、尊重自己的男子。中国古老信条里,“女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母以子贵”,为国王生下儿子,是女人争宠的重要手段,也是女人赖于更好存活的重要资源。而这些,如姬弃之如敝履,就连死,也不愿用暴戾者的手来伤害自己,而是自己解放自己。同样是男人,面对“就是维持公道和正义”的信陵君,如姬却体现出的是女人的情深义重和深深敬仰。信陵君“把人当成人”的人本主义理念,如姬信仰着;信陵君“抗秦救赵”的政治主张,如姬积极支持着。当信陵君请求她帮忙窃符救赵时,明知这是一条不归路,深明大义的她欣然接受,运用自己的智慧,巧妙完成任务。如姬对信陵君虽然建立在爱怜与爱慕的基础上,但这是单向度的,最终极体现的是女性意识的消退和左翼斗争意识的凸显。作为女人,如姬是有见地的:“根本是没有把人当成人,假使世间有那么一天,人把人当成人的时候,那就好了”,但这“做人的勇气”是来自于男人信陵君的“光辉”的。如姬把信陵君看作是“太阳”,一方面不敢“走近了他的身边”,怕“会焦死”,另一方面怕“会要遮掩了他的光”。甘愿当自己“是一颗小星星,躲在阴暗的夜里,远远地把他望着”。“我也实在是想去呀,我是怎样得渴望着再能够见他一面呀!”,如姬“这样的人对于人人所敬爱的信陵君,不会说没有情愫”[3]。在左翼革命斗争意识视阈中,女人的柔情被阉割了。信陵君始终是至善至勇的代表,对儿女情长没有表现出半点意念,如姬虽暗含情愫,但却为了维护信陵君的道德和斗争形象,不能因自己而给他“蒙上了污秽”,最后自刎于父亲墓前。
同样的,作为“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儿”,婵娟“知道了做人的责任”,是受了屈原的“感化”。对把自己当成嫡亲女儿看待的屈原,婵娟朝夕近前服侍着;当自己心中的“楚国的栋梁”、“柱石”屈原遭到陷害后,婵娟不顾一切地前去营救。“使屈原得到安慰而继续奋斗到死的唯一力量”的“诗之魂”婵娟[4],可以说是屈原的一根肋骨。在屈原面前,她“安详得就像一只鸽子”。“如果你死,婵娟也要跟着你一道死!”离开了屈原就失去了生存的意义。最后,在东皇太一庙误饮了郑詹尹的毒酒代屈原而死,“我把我这微弱的生命,代替了你这样可宝贵的存在”,婵娟感到“是多么地幸运啊!”。而对奴性十足、没有“灵魂”的子兰和宋玉,婵娟是特别的恨,面对子兰的利诱,决不“苟且偷生”,誓死捍卫自己做人的尊严。
相对而言,郭沫若20世纪40年代创造的女性是最充满矛盾的:她们一方面有鲜明的女性意识,婵娟抗拒子兰让自己侍奉他从而挽救自己生命的诱惑,如姬对不尊重自己的魏王非常不高兴;但另一方面,她们又能为自己心中的精神楷模而甘愿牺牲自己。婵娟代屈原而死,如姬为保全信陵君而自杀。在充满血腥的残酷斗争时期,女性意识让位于社会斗争意识,女性解放汇入社会解放洪流中。
三、20世纪60年代:建设状态下的和谐意识追求
天地之间,阴阳互补。没有女人的男人世界和离了男人的女人世界都是没有色彩的世界。两性之间,犹如拉链,互补互充才能取得和谐。到了百废待新的社会主义新时期,如何更好发挥建设功能是时代需要的主流话语意识。女性意识不能仅局限于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认可,更要争取的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身份认同。文姬归汉贡献文治事业,武则天任人唯贤、广开言路、革新图强,就实践才能而言其并不逊色于任何男人。但郭沫若在处理时并没有过分强调女人的优越感和对男权意识的凌驾,而是注重强调女人的实践功能以及女人具有的柔性因素。
蔡文姬的身世是凄凉的,幼年成了孤儿,婚后不久又成了寡妇,接着又被胡人掳到塞外。幸好左贤王搭救,并结为夫妇,共同生活12年,生了一双儿女。当曹操平定中原花重金赎她归汉续修《汉书》时,蔡文姬陷入极度矛盾处境中。一方面,回归魂牵梦萦故土继承父业贡献自己的才智,这是实现女人社会身份认同的机会。但另一方面,作为母亲,别夫离子的伤痛深深撕裂着她的心。文姬一度消沉,后在使者董祀的开导下,决心摆脱个人的伤感,而要“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立志为国效力。但在归汉途中,文姬如泣如诉的《胡笳十八拍》深含着儿女情长和母子情深,具有非常强的感染力。
一向被斥为盗权窃国的红颜祸水一代女皇武则天,被郭沫若翻案成具有卓越才华的开明君主。她能体察民间疾苦,提出了“建言十二事”的开明政治主张;“外举不避仇”,用人唯才,敢于打击豪门贵族。与传统女人的优柔、多情有别,武则天是坚定的、刚毅的、机敏的,是胸怀苍生的,可以说是成为了“男性以上的人”。连贵为天子的唐高宗受武则天的影响而改变人生想法,“这就是受了你的影响嘛。你不是鼓励过大家读老子的《道德经》吗?”,“…如果没有你母亲,老早就没有我,还有你做太子的份?”。对追求“生动有为”人生的武则天,作家没有让其女性主义意识过度膨胀,而是追求男女间对等的和谐。太子东宫私藏兵器,在讯问和处理上官婉儿和太子贤时,武则天没有专权,也没有颐指气使,而是安排皇帝唐高宗在侧,不断征询他的意见,关心他的健康。这一笔的添置为过于刚性的武则天增添了一点女人味。
四、郭沫若女性关照的价值取向
与女性作家不同,作为男性作家的郭沫若在观照女性时带有明显的男性立场,在权力话语意识的驾驭下,将女性革命和时代革命交织在一起,在私人话语与公共话语、情感与理智的狭缝中寻求平衡,塑造出前卫与传统相融合的女性形象。女权主义的诉求之一就是获取与男人平等的性意识,大胆追求浪漫爱情。但在郭沫若的意识中,特别是40年代的历史剧中,这部分要求作了主流话语意识的陪衬。对于不把人当成人看的丈夫,如姬带有先锋姿态,敢恨敢叛逆;但对自己爱慕的信陵君,如姬却不敢爱了。不是说没感情,而是为了保全男人的信誉以能更好地发挥斗争作用,如姬理智地掐灭了爱情火焰。这种凄美举动是让人敬佩的,但也是女性自由发展的一种悲剧。无论何时代的女人,要想争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必须要具备一些价值追求元素。
(一)要有介入现实的时代使命感
几千年来的礼制社会给女人规定好了角色分工,“男主外,女主内”,女人的任务就是生儿育女,服侍丈夫,家庭就是女人的舞台和天地。郭沫若在自己的历史剧的艺术空间中,为女人开启了融入时代情境这扇门。“天下兴亡,匹妇有责”,游离于时代之外也就远离了权力话语中心。“我想把故事写成剧本,差不多是20年前的事,但因为如姬的事迹太简略,没有本领赋予血肉生命,因而也就不敢动手”[3],作为历史剧创作,人物的事迹太过简略带来创作上的难度,但同时也给想象力的充分发挥留下了宽广的空间。当然,这种虚构要在一定的限度内。事实上,在20世纪40年代历史剧中,如姬形象是最富功力和感染力的。如姬的识见、品格以及内心的矛盾纠缠都体现出了她的非同一般。把如姬写成既是出于报恩,又因为对合纵抗秦的政治主张有一种思想上的共鸣才冒死帮助信陵君,类似这样的描写都是“想当然的事”[5]。知恩图报是传统美德,出于这样的目的,如姬窃符救赵帮助信陵君,足以让人信服,作者却冒着违背历史事实的风险额外为如姬添上深知“唇亡齿寒”道理是深含用意的,赋予了女人关注现实、积极介入现实乃至奋不顾身的现代意识。
(二)要有勇于抗争的非凡能力
男女之间的对等不仅是性别意识、性意识的平等,更应该是权力的对等。但在男性道德价值中心社会里,女性是被构造的,没有自己选择的权力,也没有自己的话语权。作为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主体,女性的价值往往也是不被承认的。女性对极端恶劣的观念和暴力行经只有通过有力抗争才有改变的可能。在男人眼里,武则天主管政事是不合常规的,是混乱秩序的:“他们反对我,说我‘牝鸡司晨’,说我不应该管理朝政”。但她具有不信邪的抗争意识,“为了天下人都能够安居乐业,我不敢有一日的偷闲”,励精图治、心系苍生,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追求自我的价值表现,挖掘女性内在潜力,以实际举动争取到女性的话语权。
郭沫若历史剧的女性表达,“不再限于表达被压迫、被玩弄、被出卖者的怨憎。她们走出了这个‘弱者’的阶段,成长为没有任何软弱、非牺牲品,不需要拯救和等待施舍等附带意味的纯粹的女人,成长为有能力、有才智去以女人身份在男性世界里站稳脚跟的女人”[6]。郭沫若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历史剧的创作史,也可以被视作女性解放运动史。20世纪20年代,可以说是女性最初的性别意识的觉醒时期。卓文君开始“不相信男子可以重婚,女子便不能再嫁”,王昭君敢于反抗夫权、王权,主动出塞,挣脱套在身上的枷锁,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作为女人,她们开始有了主体意识的复活。20世纪40年代,可以说是女人社会身份认同意识的觉醒时期。对“一说到稍微重要一点的事情上来,他立刻就要说:没有你们女人的事;‘牝鸡司晨,维家之索’。”的魏王,如姬“真是不高兴他呢”。如姬也有把自己“和宫中的女官们也放到行伍中去工作”的想法,只是在女性失语的男权社会没有实现的可能。身为女儿身的聂嫈,为自己不是男子,不能和弟弟一道去做有益的事而深感悲哀,后为传播弟弟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英雄精神以激励后人,毅然赴死。女人有了与男子投身社会、拥有社会实践价值的自觉意识,但因历史条件的制约还只能做男人的配角,用鲜血来祭奠这一重要的转变。20世纪60年代,可以说是女人实现实践话语权力意识的时期。女性开始由边缘回归到中心,从话语权的缺席者向在场者转变。“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皇帝要我管,我只好管。只要我管得好,天下人不反对我,我就得管下去”。武则天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励精图治、劝课农桑、选拔贤良、和谐万邦,施于普天之下的女性关怀和道德关怀。
[1]郭沫若.写在《三个叛逆女性》的后面[G]//郭沫若文集·文学编(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137-146.
[2]郭沫若.《孤竹君之二子》幕前序话[G]//郭沫若.郭沫若剧作全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78.
[3]郭沫若.写作缘起[G]//郭沫若.郭沫若文集·文学编(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550.
[4]郭沫若.屈原与厘雅王[G]//郭沫若.郭沫若文集·文学编(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410.
[5]郭沫若.郭沫若论创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414.
[6]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的地表: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研究[M].台北: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1993:295.
The Sense of Women in the Main Current Words Consciousness:On the Chronicle Plays by Guo Mouruo
LI Zheng-ho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Chuzhou College,Chuzhou Anhui 239000,China)
Guo Mouruo developed many women with the different times corrent under the main current words in his chronicle plays.In the 1920s,women had the spirit of rebellion in the most under May Fourth Movement individual liberation consciousness,in the 1940s,Guo Mouruo had prominented the spirit of left-wing strugglement consciousness and had emphasized the main functionality of the practice during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in the 1960sabout women consciousness.Accordingly,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Guo Mouruo’s women sense had placed extra emphasis on the Power discourse discourse ideology.
Guo Mouruo;chronicle plays;women consciousness
book=5,ebook=17
I206
A
1672-0539(2012)05-0047-04
责任编辑:刘玉邦
2012-03-03
李正红(1973-),女,安徽来安人,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艺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