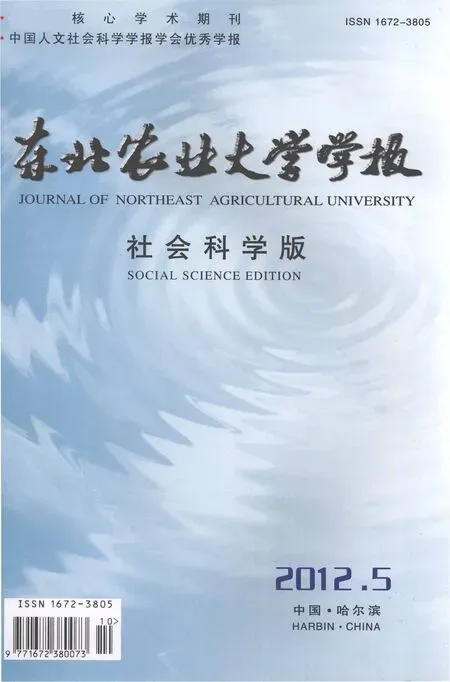浅议美国华裔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与传承
乔 程 弥 沙
(1.黑龙江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2.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哈尔滨 150030)
“美国华裔文学”是华裔美国人用英语创作的文学作品。这个界定有两点需要明确:第一,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主要是用英文创作的,而美国华人文学通常是用中文创作,是世界华文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美国华人文学与美国华裔文学在本质上是不同的;第二,“华裔美国人”是指那些出生于美国本土的华人后裔或已经申请加入美国国籍的华人。这两部分人在国籍上讲是被“美国化”的中国人了,特别是身处转折、繁荣期的美国华裔作家多数都是在美国出生或者长大,他们从小生活在美国文化圈中,接受的是美式教育,他们将自己在美国的生活体验和经历结合中国的文化符号反映在作品中。由此,我们应该意识到,美国华裔文学是美国文学的一部分。
一、美国华裔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与传承
从华裔文学的主要发展历程来看,华裔文学作家对中国文化经历了从开创阶段的极度留恋到转折觉醒阶段的极度排斥,再到最后繁荣时期的融合这样一个过程。纵观美国华裔文学的三个发展阶段,尤其是后两个发展时期的作品,会发现其中有两个明显相反的趋势:一个是断裂,一个是传承。笔者着重探讨了这一时期美国华裔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1.美国华裔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
美国华裔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出现断裂现象有其深刻的理论根源,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是导致华裔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出现断裂的一个重要因素。“东方主义理论”是“建立在关于‘东方’与‘西方’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区分基础上的一种思维方式”,东方主义“将西方人置于与东方所可能发生的关系的整体系列之中,使其永远不会失去相对优势的地位”,体现出西方对东方的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而且“东方主义”理论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批评色彩,比较全面地揭露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统辖东方的野心。当今比较有影响的华裔作家,大都出生在20世纪的美国本土,“东方主义理论”对这些华裔作家产生的消极影响较重。在此理论作用下,身兼双重身份的美国华裔作家倍感困惑,他们想尽力摆脱华人身份以及中国文化对他们产生的束缚和影响,他们渴望得到美国主流文化的认可。因此,这些华裔作家在文学创作和思维方式上总会自觉与不自觉地用“美国式”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父母、中国以及中国文化,从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的作品建构了“东方主义”的画面,从而导致了美国华裔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例如,华裔作家汤婷婷的代表作《女勇士》便带有严重的“东方主义”印记,她向西方读者描绘的是一个文化腐朽,思想愚昧,社会动荡不安的中国。在这个国度重男轻女思想严重,生男孩是天大的喜事,父母要为之大操大办庆贺一番;“养闺女还不如喂只鸟”,因为生了女儿往往被认为是“赔钱货”;他们笔下的女人淫荡无度,无名姑妈与村上不明身份的男人通奸;他们把中国人的人性描绘的非常残忍,母亲用刀子割断女儿的脐带;鬼怪横行,闹得有房子也无人敢居住等等。西方读者读到这些作品往往会瞠目结舌,他们也深深地“了解”了什么是中国文化,因为“东方人”自己创作的文学作品,它们应该是真实的,这也正好印证了西方读者头脑中对中国人固有的形象。对此,美国华裔文学评论家马胜美一针见血地指出:“汤婷婷有意识地歪曲中国文化”,以点带面地向西方展示了中国人/中国文化传统的男权主义歧视妇女的落后现象,有迎合白人读者之嫌,从而割裂了美国华裔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融。
此外,华裔族群的特殊身份是美国华裔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出现断裂现象的另一因素。从汤婷婷、谭恩美等美国华裔作家的经历来看,华裔族群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疏离感,汤、谭等人可以说是对中国历史文化了解少之又少甚至是一无所知的一代。这些人从小生活在美国,接受的是西式的教育,他们自幼只知道自己是“美国人”。这些人对自己家族的历史所知甚少,平时他们不会用中文来进行交流。因为,对于这些人来讲,中国并不是他们的祖国,而是一个文化上的“他者”。这种认识也充分地体现在他们的作品上。例如,谭恩美的成名作《喜福会》,小说通过叙述四位华人移民母亲和她们在美国出生的女儿之间的故事,表现了中国母亲和美国女儿间的情感纠结。母亲既希望女儿能保持中国的血缘身份,又希望女儿实现自己未曾实现的“美国梦”。小说展现了中美文化的对立和冲突,强调了华裔族群因特殊的身份承载着太多的经济和精神层面的历史负担,在难以承受的文化之重中艰难跋涉、步履蹒跚,甚至是割裂了文化之根,在不能承受的文化之轻中飘忽无着、偏离正轨。
2.美国华裔文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
简单地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文明历史长河中的文化积淀。具体包括中国人在历史上特有的宇宙观、道德观、价值观,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认知方式、生活方式与风俗习惯等。几千年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华夏儿女的影响极为深远,华人无论身处何处都力图保持中国文化传统,重视对子女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美国华裔作家,作为炎黄子孙也通过各种方式了解和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与教育,所以在他们的作品中也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现象,包含着浓厚的中国文化意义和强烈的人文意识。这也表明了美国华裔文学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这种传承表现出美国华裔文学发展的不同时期有着各自独特的特点。
在华裔文学开创阶段,许多华裔作家国学基础深厚,初出国门,在陌生的国度,他们对美国文化难以接受,对中国传统文化极度留恋,在文学创作时,两种文化在他们思想深处撞击和冲突,他们力求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融为一体。如,黎锦扬在《花鼓歌》中成功塑造的典型形象——王老爷的儿子王三就充分表现出他的中西合璧的思想。从小在美国长大的王三自幼在学校接受美国教育,13岁时已经完全融入美国社会,被美国文化同化,他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吃西餐,穿牛仔,甚至都不太会讲中国话了。可以说王三已变成一个黄皮白心的“香蕉人”,他的父亲竟然还妄图他能够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责令他学习孔孟之道,背诵四书五经等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而王三已经对孔孟之道难以接受,并且很厌烦,甚至抱怨说“对那些废话一窍不通”。王老爷空有一腔热望,力图用中国传统文化感化王三,希望将其从“堕落的危险”中解救出来,但结果却是徒劳。事实上,王老爷根本无法填平中美文化冲突横亘于其父子间的沟壑。
在华裔文学的转折、觉醒阶段,这些华裔作家,在种族歧视盛行的社会环境中长大,他们为自己的双重身份感到迷茫困惑,摆脱中国文化和华人身份的束缚,融入主流文化中,是这一群体所希望的。这一希望也投射在他们这一时期的作品中。作为这一时期代表作家的汤婷婷和谭恩美小说中的主人公尤其是第二代移民,已经渐渐远离了中国文化,而融入当地主流文化的愿望显得尤为强烈。可是随着时代的推进,女权运动逐步兴起和发展,使得这一作家群体深刻感受到了民族强大的重要性,进而在自己的作品中竭力维护华人形象,大力弘扬正宗的中国文化经典以此对西方的“东方主义”话语进行解构。这些作家逐渐意识到如果华裔完全抛弃自身的民族文化属性,将很难获得幸福。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这一语境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华裔作家们对中国流露出好奇和兴趣。如《喜福会》中的第二代的女儿们对标榜有中国特色的东西产生了浓厚兴趣,她们开始明白:在不刻意否定以及逃避自身民族属性和文化根源的前提下,自己才能更好地融入美国主流文化。这一转变也就促成了美国华裔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进一步融合。
华裔文学处于繁荣阶段这一时期,世界出现了经济全球化和思想文化多元化的特征,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日益提高,所以这一阶段的美国华裔作家身上早已没有因文化身份而苦苦挣扎、备受煎熬的感觉。抛掉这种束缚后他们能以较为轻松的心态,用诙谐、幽默、反讽的笔调对美国主流社会对少数族裔的歧视与偏见加以批判,并对民族平等及文化认同等问题加以探讨。如任碧莲在其代表作《典型美国人》中,对华人族裔是如何看待及解决在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国主流文化中的自我身份认同和自我建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提倡建立“‘美国色拉碗’式的多元文化”这一概念,客观上推动了中美文化的互相认可与融合。
二、结束语
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文明的冲突便产生了。它时强时弱,此起彼伏,但始终没有中断。人类文明也正是在不断的冲突中相互磨合,并催生出文化新枝。在今天的文明格局中,西方文明由于种种历史缘由而处在“文化施动者”的地位,非西方文明则不同程度地处于“文化受动者”的地位。但这种施动与受动都是相对而言的,文化传播从来不可能是单向的,总是存在着互动。且历史上文明的融合或生成从来就是在冲突中展开的。美国华裔文学作家身处中美文化接触的前沿地带,对不同文明而衍生出的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冲突与交融有着最切身的体会。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美国华裔作家开始超越族裔文化身份,逐渐从文化夹缝与身份政治当中解脱出来,以一种全球的新视野思考着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与交融。许多看似对立、冲突文化的自我与他者的界限在悄悄地、不知不觉地消解,从那些跨文化的情缘中,我们更能体会到异质文化的零距离接触对中美文化融合所起到的示范作用。
[1] 郭英剑.命名·主题·认同——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6):32.
[2] 吴冰.关于华裔美国文学研究的思考[J].外国文学评论,2008(2):15.
[3] 刘胥.关于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中的三个争议[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0(6):240.
[4] 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3-4,8.
[5] 弥沙.“新冒现的文学”—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综述[J].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