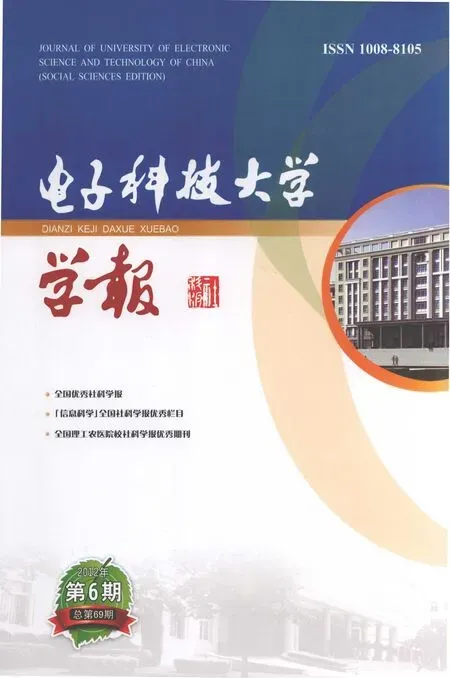苏轼与程颐在性情论上的分歧
□胡金旺 [宜宾学院 宜宾 644000]
在讨论苏轼与程颐的性情论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澄清一个问题,即我们讨论他们的性情关系中的性、情到底是在什么层面上的性、情,因为苏轼与程颐的性都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就程颐而言,他所论之性分作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天命之性具有超验的性质,而气质之性是属于经验的范畴,喜怒哀乐爱恶欲等七情也是如此。而苏轼的性也包括超验的本体之性与经验范畴的自然之性,情也有自然之情和人情之情两层含义。所以,我们在讨论他们的性情关系时,就要做具体的分殊,指明清楚。这是在讨论之前必须先交代清楚的问题,以免行文之中造成头绪不清。
一、性在他们哲学中的定位
在苏轼的哲学体系中,其最高哲学范畴为道,而这个最高本体之道,在他看来是不可见的。他说:“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未达也,无以异于眇。”[1]1981在《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中,他写道:“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曰‘以无所得故而得’。舍利弗得阿罗汉道,亦曰‘以无所得故而得’。……以吾之所知,推至其所不知,婴儿生而导之言,稍长而教之书,口必至于忘声而后能言,手必至于忘笔而后能书,此吾之所知也。口不能忘声,则语言难于属文,手不能忘笔,则字画难于刻琱。及其相忘之至也,则形容心术,酬酢万物之变,忽然而不自知也。自不能者而观之,其神智妙达,不既超然与如来同乎!故《金刚经》曰: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以是为技,则技疑神,以是为道,则道疑圣。古之人与人皆学,而独至于是,其必有道矣。”[1]390
道虽然难以认识、不可言说,但是道的境界是可以体验到的。如果用物娴熟得自己都忘记了在做这件事情,即到了一种游刃有余、完全自由的境地,用苏轼的话讲就是“相忘之至”、“不自知”的“神智妙达”的境界,则我们就体验到了道的境界。这个境界的最大特点就是无。所以苏轼用《金刚经》“皆以无为法”的看法来总结这种境界。但道很显然又不是无,否则道就是可以认识的了。道的特点是无,因而要体认道的境界,我们就要做到“无我”、无心。所以,苏轼说:“得道者无物无我,未得者固将先我而后物。夫苟得道,则我有余而物自足,岂固先之耶?”[1]176~177
道难以认识和不可见,而与道相关联的易却是可以认识的,在易以万物的面目呈现以后又是可见的。苏轼通过对道与易关系的阐述①为我们开启了一扇间接言说道的法门。他说:“相因而有谓之‘生生’,夫苟不生,则无得无丧,无吉无凶,方是之时,易存乎其中而人莫见,故谓之道,而不谓之易。有生有物,……方是之时,道行乎其间而人不知,故谓之易,而不谓之道。”[2]362道与易的关系实际上可以分作两个阶段来认识,即物未生成的阶段和物生成的阶段。当宇宙空无一物之时,我们可以说宇宙是空无的,从此时是无的特点与道的特点也是无的相同来看,所以“谓之道,而不谓之易”。易虽然也可以表现为无,但是作为生生之易的本质是物质的转化,因此,它终究要在宇宙中实现其自身显现为物。于是万物得以产生。万物产生以后,世界总的特点表现为“有”,与易的特点为“有”相同,所以此时“谓之易,而不谓之道”。但是两个阶段我们都可以说通过易来体认道,在未生物阶段是通过“无”(这个“无”是“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与道的特点“无”不同)来体认无,而在生物以后是通过有来体认道之特点无。在前者,我们有所谓的静坐之类来体认道,在后者我们通过我们的所经所历来体认无。
道在易中,在万物产生之后,我们只有通过应生生之易中流转的万物而达到无心的境界才能体认到易背后隐藏的道。但要达到无心的境界,光凭对自己有意识的这样做还不够,因为我们想要如此做到和能如此做到还是两回事。因此,要想做到娴熟得如鱼得水、自然而然的程度还必须经过在实践中反复磨练方能实现。所以,苏轼说:“犹器之于手,不如手之自用,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性至于是,则谓之命。”[2]142
通过易方能体认到道,就人性而言,就是体认到了性。所以苏轼才说“性至于是,则谓之命”,这个意义上的性与道都具有超验的性质,都是本体论性质的概念。前文说到苏轼论性也是从两个层面上来讨论的,即超验性质的本体之性和经验层面的自然之性。很显然,苏轼论述的与道处于同一个层次的性是指本体之性。本体之性与道一样其特点都是无。苏轼从两种意义上来论性从他的著作来看是非常明了的事,但是目前学界多是从自然之性来讨论苏轼的人性论,这就无法揭示出他的人性论的本来面目。
程颐哲学中,道与天命之性的关系如同苏轼哲学中的道与本体之性的关系是一样的,也是处在相同层次的范畴。程颐的最高哲学范畴是天理,也称之为道。他说:“性即是理。”[3]204“又问:‘性如何?’曰:‘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3]209又说;“称性之道谓之善,道与性一也。”[3]318道或者理有四种含义:即天道、物理、性理、义理,其中性理和义理是他的哲学关注的中心。由于本文主要是议论性情关系,因此着重讨论与性情相关的性理这一层含义。对于性理的理解,陈来说:“性理指人的道德本质,程颐后来提出‘性即理’,认为人性是禀受的天地之理,后来理学家普遍接受这种看法。”[4]
二、苏轼的性情论
上文我们说到苏轼的哲学体系是用道与易的关系来建构的,而道与易的关系反映在人性论上就是性与情的关系。由于道是不可言说和难以认识的,相应地,道在人性上的体现之性也就是不可言说和难以认识的。苏轼以为要体认道就必须通过表现在外的易方能实现,所以要体认人性、张扬人性,就必须通过自然而然地表现人情来做到。苏轼性情关系论与当时程颐保守的性情论针锋相对。因此,苏轼的性情论对于那个理学思想还没有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有其特别的意义。再加上苏轼的性情论在学界的认识还有不尽人意之处,而对程颐性情论的阐述又较为充分。所以在对苏轼与程颐在性情论上的分歧进行讨论之前,我们对苏轼性情论的探讨有其必要性。
苏轼对人性的认识有着明显的阶段差异,在早期主要是从自然之性的角度来认识人性的,而在后期主要是从本体之性的角度来认识人性②。苏轼在26岁那年所作的《扬雄论》中说:“人生而莫不有饥寒之患,牝牡之欲,今告乎人曰:饥而食,渴而饮,男女之欲,不出于人之性也,可乎?是天下知其不可也。……由此观之,则夫善恶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1]111
饮食男女这种人之欲望在苏轼看来也是性,这个意义上的性就是自然之性。后期苏轼在完成于元丰四年前后的《苏氏易传》中对性的看法有了新的发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前期性论的否定,而是其性的内涵又多了一层意思[1]1380。这时已年届知天命的苏轼,已开始从善恶根源的角度探讨人性的真谛。其所指性是本体之性,从其“性至于是,而谓之命”来看,也可以谓之性命之性。
苏轼的性情论中的性有两层含义,所以我们在讨论其性情关系时,必须清楚苏轼是从性的哪层含义来讨论性情论,这样才不至于误解他的思想。但是仅仅对其人性的含义有正确的认识还不够,其实苏轼对情的认识也有两层含义,一为自然之情,一为人情之情,而这一点学界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论述③。当然,我们似乎可以互不相干地论述苏轼情的这两层含义,但是当性情合在一起进行论述的时候,就有必要将情这两层含义分殊清楚,否则,对其性情论的阐述就会出现缴绕不通之处。因而对其性情论就难有一个全面正确的理解。
从我所要表达的情来看,我们应当将情自然、真实而不做作地表达出来。而要做到这一点,其根源就是要克服自我的不足,恢复到本真的状态,而这就是本体之性的状态,因此与这种情相对应的是本体之性。从这种情应当表现为自然而然、旷达潇洒,没有丝毫虚伪和做作来看,这种情可以称之为自然之情、旷达之情。本体之性的特征是“无”,所以当这种性发之于情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让任何私念和各种成见影响情的表达。苏轼在《思堂记》中说:“思虑之贼人也,微而无间。隐者之言,有会于余心,余行之。且夫不思之乐,不可名也。虚而明,一而通,安而不懈,不处不静,不饮酒而醉,不闭目而睡。”[1]363本体之性应当是澄明无染的,不会有私心杂念来扰乱自我的心情,因而表现在外也是自然而然、旷达潇洒。苏轼这种显露在外潇洒自然的感情在他许多的诗词中都有尽情的表达,尤其在他的传诵千古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其旷达之情彰显得淋漓尽致。
当然苏轼主张要尽情地表达自己的感情,而不是抑制自己的感情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违反封建礼教。在那个时代,作为封建士大夫的苏轼不可能提出这种叛逆的主张,他认为自然而然的表达自我之情与对封建礼教五常的遵守并不冲突。如果我们的自然之情违反了五常,则就不是自然之情,而是受到了私念的影响。所以他说:“夫岂独吾病之,天下之匹夫匹妇,莫不病之也,苟为病之,则是其势将必至于磬折而百拜。”[1]62如果违反了五常,则必然遭到人们的反对,因而人们就会放弃这种违反了五常的情。
怎样将情表达得自然而然,当然要使其本体之性充分地彰显出来,也就是说人不能拘泥于自我的本性而使本体之性受到遮蔽。这种差别用佛教的话说,就是不要用假我遮蔽了真我。只有这种真我彰显出来了,其自然之情才能在根源上得以自然而然地表达。这是保证自然之情得以畅达的一个方面的因素,已如上言。另外一点就是苏轼在道与易关系中所说到的要体认道的境界就要反复地在实践中训练,直到熟能生巧而达到一个“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的境界。而对于此处的性情关系而言,就是要不断地在现实中锤炼而能做到自然而然地表达自我之情,直到这种表达做到了不自知,才可谓体认到了本体之性。例如在人际关系中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不是想要应付自如就能应付自如,而是要经过锻炼方能如此。所以,我们说苏轼性情这个方面的关系是其道与易关系在人性论上的体现。苏轼的哲学体系的总体构想是通过易来体认道,而道与易的关系反映在人性论上,就是通过自然之情来体认本体之性。
苏洵与苏辙都重视“以情为本”或“情本论”的思想,苏轼也不例外,这一点可谓具有家学渊源。但这种意义上的情为人情之情,而不是以上所说到的自然之情的含义。
苏轼在《中庸论中》中说:“君子之欲诚也,莫若以明。夫圣人之道,自本而观之,则皆出于人情。不循其本,而逆观之于其末,则以为圣人有所勉强力行,而非人情之所乐者,夫如是,则虽欲诚之,其道无由。”[1]61他在《东坡书传》中也说:“饮酒,人情所不免。禁而绝之,虽圣人有所不能。”[5]这些看法都是指人的实际需求,是人的自然之性表现在外的必然反映。所以,苏轼当用“情”来指人的实际情况时,是针对人的自然之性而言。“以情为本”说到底就是以人之自然之性为本,表明苏轼非常重视人之生存之自然需求,而这又往往为封建卫道士所轻视。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苏轼性情论思想的价值。有人以为苏轼是一个具有平民意识的思想家,从此而言是非常中肯的意见。
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反复陈述要顾及众人之情,只有顺众人之情才能政通人和,他说:“唯商鞅变法,不顾人言,虽能骤致富强,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虽得天下,旋踵而失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果敢自用而不危者也。”[1]730苏轼针对王安石变法告诫神宗皇帝要顾及大多数人的实际处境,即大多数人的人情,要关心体贴民情,这样才能长治久安。
苏轼的情的两个层面的含义虽然都落在了经验的范围内,但是其内涵的差异是很明显的,因而区分它们非常有必要。只有做了这样的区分,才能准确把握他的性情论。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情的两层含义所针对的对象也是不一样的。将内心的情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通常是针对自我;而要重视民情通常针对的是全体百姓。前者侧重的是个体及其情感表达,后者侧重的是群体及其现实需求。有了这样的区分,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找到情所以要如此的根源,从而更好地做到表达自然之情、体察人情之情。
三、苏轼与程颐在性情论上的争锋
程颐认为天理是至善无恶的,因为“性即理”,所以人性从本质上讲也具有至善性。他说:“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3]292人的恶行主要是由于后天气质之性中含有的浊气所导致的,气禀清者表现为善行,气禀浊者表现为恶行。程颐说:“此只是言气质之性。……此言性者,生之谓性也。”“……生之谓性,论其所禀也。”[3]207又说:“才禀于气,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3]204所以人要杜绝自己的恶行关键在于抑制自己的浊气。怎样最大限度地抑制浊气,就等于将天理和至善之性最大程度地外显出来而不至于被覆盖。程颐也称人之恶为人欲,他说:“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3]312
去人欲的目的是存天理,如果情遵循至善无恶的天理,则情自然就是合理的。所以去人欲并不是完全要将情排除在外,而是要将不合理的情排除在外。二程提出情要“正”的说法就表明他们认可合理的情,二程说:“……‘故者以利为本’,只是顺利处为性,若情则须是正也。”[3]33存天理、去人欲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程颐的这个衡量情是否合理性的标准比起苏轼来要简单得多,但是却表现为僵化、一层不变的特点。因为程颐天理的内容实际上是封建道德的五常,而五常又是永恒的道德规范,是固定不变的。
苏轼、程颐对人性本质规定上的差异导致了对合理性的情认识的不同,因而在如下三个方面形成了尖锐对立。第一,程颐的性情论的特点是用道德理性来规范情。但是人的感情世界是丰富多彩的,除了要遵循道德理性的要求以外,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需要。如果将人的情感只是限制在道德的领域,而忽视情感的其他需要,就滑向了以道德理性主义为纲,用道德主义来观照万物的泥潭。对年轻的皇帝游园无意中的折枝行为,程颐都用道德的尺度提出严肃的批评,这种做法遭到人们的反感和厌恨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而苏轼性情论与程颐最大的不同就是不仅仅以善恶来认识性情关系。他以为,我们只有通过对万有包括情的实践而达到了一种不自知的境界才能体验到性之无的特点,这也就达到了无心的境界。显然,这种无心并非是什么也不做,而是要遵循无私念的标准做到应物而无累。因此,在此标准下的情必然并不是只要遵循一种道德主义的标准,而是要符合人的多方面情感的需要。我们只有做到了理性地满足情这些需要而不自知,才可能做到真正的无心,这才是通过情体认了性。苏轼重视情感自由畅快表达的满足,性外显为放旷自然的情,这些都是他的性情论的写照。这种思想与程颐用道德理性来规范情的旨趣大相径庭。第二,以道德理性主义为纲,就必然会表现出对仁义道德的过分信奉与崇拜,甚至会认为进行这些方面的修养会产生神奇的力量,从而愈加对情进行限制和抑制,最终成为禁欲主义的忠实信徒。有学者与程颐对话道:“问:‘至诚可以蹈水火,有此理否?’曰:‘有。’”[3]189这种对至诚效果的无限夸大会转化为对情更严格的压制。程颐还将寿夭与气禀联系在一起,从而迫使人们沉迷于他的禁欲主义学说。他说:“更如尧、舜之民,何故仁寿?桀、纣之民,何故鄙夭?才仁便寿,才鄙便夭。寿夭乃是善恶之气所致。仁则善气也,所感者亦寿。善气所生,安得不寿?鄙则恶气也,所感者亦恶。恶气所生,安得不夭?”[3]224
第三,程颐好用古礼,这是由于他只是遵循礼的最严格的规范,而不会随着形式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因此其标准是僵化不变的,表现出保守主义的特色。而苏轼的情本论是与时俱进的,因此,反对用古礼,主张礼要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变化。《资治通鉴后编》谓“程颐在经筵,多用古礼。苏轼谓其不近人情,深疾之,每加玩侮。方司马光之卒也,明堂降赦,臣僚称贺讫,两省官欲往奠光,颐不可,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坐客有难之者曰:‘孔子言哭则不歌,不言歌则不哭。’轼曰:‘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众皆大笑,遂成嫌隙。”[6]这次事件使得他们的关系愈加僵化。
第四,为了更有效地遵循天理的至善性,程颐提出了“敬”的修养方式。这种对外在行为规范中规中矩的严格恪守与苏轼主张性情自由洒脱的展现形成尖锐的冲突,因而苏轼对程颐的“敬”尤为反感,对之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和抨击。据《二程外书》记载:“朱公掞(光庭)为御史,端笏正立,严毅不可犯,班列肃然。苏子瞻语人曰:‘何时打破这敬字?’”[3]414苏轼毫不掩饰对程颐、朱光庭等人道貌岸然的假道学模样的愤恨。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苏轼、程颐在性情论上的差异根源在于在他们各自的哲学体系中性的内涵和实现方式不同。苏轼是通过情的多方面理性的满足来实现性,而程颐是用性的至善性来规范情,从而使得情打上了道德理性主义的色彩,限制了人的性情多方面的发展与满足。
四、结论
性情论自从隋唐时期佛教思想将性定位静、情定位染以后,儒家知识分子受此影响,就从善恶的角度来讨论性情关系。自从李翱提出性善情恶说以后,儒家学者在讨论性情关系时,大多没有逃脱这个窠臼。只是到了宋朝的苏氏父子手里始提出情本论的学说,尤其是在苏轼手里建构起他的哲学体系以后,才不只是将性情关系限制在善恶的角度来讨论。从此角度而言,苏轼的性情论在性情论发展史上有其截断众流的意义。另外,自从孔子提出仁的学说以后,历代学者总是从道德理性的角度来理解仁,因而仁作为最高本体和最高人生境界来讲,总是与道德修养联系在一起,结果就容易将道德理性当做人性的全部。而苏轼提出性之无的特点是通过人性的全部发展和满足后人所处的生活状态和生命境界的,因而,苏轼的性情论从中国文化发展史的角度讲也是一种对道德主义范式的突破。
但是哲学学派的影响与这种学派理论的价值往往不是对应的。虽然程颐的理论看起来有很大程度上的不合理性,但是理学学派的发展和影响在蜀学与理学争锋中却逐渐占据了上风,以至取得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形式。程颐提出“去人欲、存天理”,而天理与人欲没有一个客观的界线,在对类似宗教教义的天理的无限崇拜氛围中,容易将正当的欲望也视作人欲。而这种特点恰好适合中国古代统治阶级专制统治的需要,因而使得这种学说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注释
① 对苏轼有关道与易关系的详细论述请参见笔者另一篇拙文《道在易中:苏轼哲学体系略论》,《中州学刊》2012年第3期。
② 对有关苏轼人性二重含义的详细论述请参见拙文《道在易中:苏轼哲学体系略论》,《中州学刊》2012年第3期。
③ 学界专门探讨苏轼的人情论的文章有冷成金的《从<东坡易传>看苏轼的情本论思想》,《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叶平的《三苏蜀学的“人情为本”论》,《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但是这两篇文章都是从苏轼所论之情的人们的“实际处境”来论述,即是论述人情之情,对其相对于本体之性而显露在外的自然之情、旷达之情没有进行讨论,因而学界对苏轼的情的讨论是一方面大加讨论他的自然之情,另一方面又是热烈讨论他的人情之情,对情的这两层含义进行互不相干式的讨论,而没有对其进行通盘的考察,因而对苏轼的性情论之情就难以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从而也影响了对其性情论思想的认识与把握。
[1]苏轼.苏轼文集[C].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2]曾枣庄,舒大刚.三苏全书·苏氏易传(第1册)[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
[3]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4]陈来.宋明理学[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04:61.
[5]曾枣庄,舒大刚.三苏全书·东坡书传(第2册)[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121.
[6]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M].四库全书本:卷八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