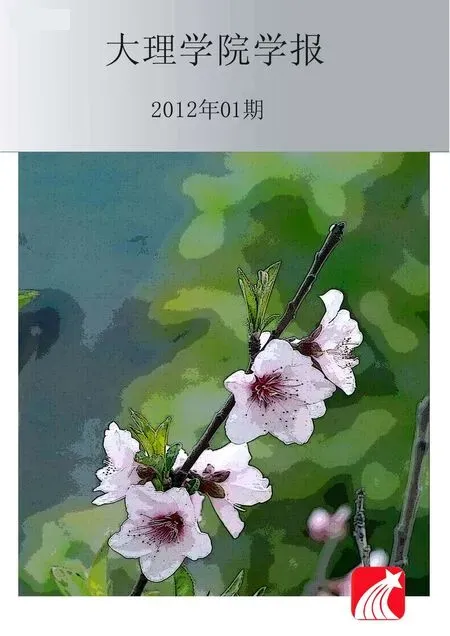李根源西使滇西根本动因分析
张根生,吴道显
(云南中医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部,昆明 650500)
李根源西使滇西根本动因分析
张根生,吴道显
(云南中医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部,昆明 650500)
云南重九光复后,出人意料的是发生了腾越、大理两地革命军队的冲突,这让正致力于稳定社会秩序的省军政府骤感压力,乃遣李根源西巡迤西,解决该冲突。学界公认的原因是李根源为腾冲人,又是同盟会云南支部的领导人,腾永的革命者等多为其旧部,故以李前往尤为适宜。但笔者认为这仅是表面的原因,事实上,滇军政府内部的纷争才是李西巡迤西的根本动因。
李根源;内部纷争;腾榆冲突;平川固滇
为响应武昌起义,云南革命志士张文光、彭蓂、李学诗等于1911年10月27日在腾越率先革命,成立云南第一个革命军政府——滇西第一军都督府。而后挥兵北上,直指大理。时昆明重九起义已经胜利,大理亦宣布光复。但由于信息不畅,而使腾、榆之间以及腾、榆两地与省军政府之间都缺乏必要的沟通,加之腾越方统帅陈云龙意气用事,不服从张文光的指挥,致使发生两地革命军之间的武力冲突。事发后,省军政府颇感事态严重,讨论解决对策,最后决定由李根源前往迤西解决此一棘手问题。那么,李根源到底愿不愿意出巡迤西呢?对此一问题,余师谢本书先生曾在早期所著的《李根源传》中有所论及:“因滇西乃李根源桑梓之地,张文光等又为昔日战友杨振鸿的继承者,所以李根源感到迅速将迤西军队治安整理完毕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另外,李根源内心还有一个目的,即准备将迤西的子弟兵略事整顿后率领由滇西出川,‘俾使有用武之地’,以达……‘平蜀固滇’的战略目标。”但先生在其近著《民国元老:李根源》一书中,却淡化了这一看法,看来先生对此一问题持保留态度。而李根源自己对于西巡一事也没有表现出其个人的态度倾向,在自编年录中,他是这样说的:“群议出任西事,十月初十任陆军第二师师长兼国民军总统,节制文武官吏自楚雄以上六府三直隶厅,共三十五州县悉属于余,不为遥制”〔1〕。不过,从内容上看,李本人似乎并没有欣然前往的意思。
实际上,出巡迤西并不是李根源的本意,李根源此时并没有西巡的准备和打算。迤西腾榆冲突发生后,引起了省都督府的高度重视,蔡锷、李根源等十分关注事态的发展,以至于发往迤西的电报一日数封。1911年11月25日,李根源曾致电张文光,探寻张的态度及协商解决问题的方法,在电文中李根源谈到了其当时的想法:“根源本欲亲赴军前,一图良晤,缘省中之事,蔡都督虽主军政,一切之事均由源主持。又拟与吕志伊同往鄂中一行,共商组织中央政府事宜,因此不克分身,良深歉仄”〔2〕65。可见,李根源根本没有前往迤西的打算,前往武昌参加组织政府的会议则是其高度关注点。不过奇怪的是,省都督府在同一天,也有一封致永昌的电报,内有“现复商派军政部长李印泉西上,与诸君接洽一切,不日即发”〔2〕54。这封电报由张文光的部下彭蓂从永昌转发而来,按《滇复先事录》的编辑体例来看,此电似乎要早于李致张文光电。如果此推测属实的话,李根源之离省赴迤西一事就颇值得玩味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李根源出使迤西呢?
云南军政府成立之后,军政府内部是否也像两湖黔桂等省内部存在纷争与冲突呢?众所周知,在重九起义之前,革命党人曾围绕革命领导权这一问题有过较为激烈的争论,形成以李根源、罗佩金、殷承瓛等和以唐继尧、李鸿祥、谢汝冀、雷飚、沈汪度等的对垒双方,李、罗、殷等人提倡“云南革命由云南人领导”,其实乃是想把革命置于同盟会领导之下,以期确保革命的彻底性。而后者主张以非同盟会员的蔡锷领导,其目标是以革命的成功为第一要义。鉴于此,李、罗、殷等从大局出发,放弃了其主张。但问题的关键在于,革命成功之后,云南军政府内部有没有分歧呢?还存不存在纷争和冲突呢?
对上述问题的肯定回答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军政府内部在权力的分配问题上还是引发了不小的冲突。这种纷争首先起始于跻身军政府内部的部分立宪派和旧官僚等人士,他们打着“云南为云南人的所有”的旗号,以最大限度地谋取权力。这在英驻云南总领事额必廉给驻华公使朱尔典的报告中已有所体现。额氏在电报中说:“云南为云南人所有的思想占支配地位的,因此在领导者中间发生了意见分歧。云南政府的首领是一位湖南人(指蔡锷—引者),因为库存中缺少现银,他正在失去权力”〔3〕68。这个敌视中国革命的英国人显然把革命军政府内部的纷争无限地放大了。其在随后上报给英国外交大臣格雷信函中,再次强化了这种认识:“尽管王先生向我保证说,革命军政府的成员们都是很好的朋友,在行政工作中绝对团结一致,但是我有一切理由相信,事实是相反的。有一次,由于激烈争吵的结果,湖南籍的都督坚持把主管职责交给云南籍的二号人物李根源。李根源尽力主持工作只有三天的时间,后来便请求蔡锷卸去他的重任”〔3〕284。这段记载颇出乎我们的意料,但这是其给外交大臣提供决策的汇报,显然可以排除杜撰的可能。不过,额氏不是云南省军政府的当事人,道听途说的可能性很大,因此他在一定程度上去事实真相甚远。但额氏还是执著地强化这一认识,在1912年2月上报给格雷的信函仍坚持这一看法:“某些有权势的云南人因蔡锷都督系湖南人而提出反对意见,一度很可能导致严重骚乱,而蔡锷本人明白表示想要离开云南府前往湖南原籍,这些都幸亏没有成为事实。他仍然是云南的独裁者;在他的指挥下,四川和贵州两省已处于隶属本省省城的附庸地位”〔3〕507。
事实上,从作为军政府核心成员李鸿祥后来的回忆看,军政府高层内部的矛盾还是很大的:“光复后,清朝官吏纷纷逃逸,军都督府成立伊始,需要人才甚亟,复以我与谢幼臣(指谢汝冀—引者)急须出发援川,蔡锷乃委殷(指殷承瓛—引者)充任参谋部长,罗(指罗佩金—引者)充任军政部长。二人尚能尽职,使援川军无后顾之忧。援川回师后,二人虽免职,但甫阅数月,蔡即保举罗任民政长……李根源于光复后因罗下蒙自而代罗任军政部长一星期有余。以李办理不善,调罗回任,派李率兵一营赴迤西,仍以办理不善被免职,嗣后蔡锷始终未再用李根源”〔4〕。李鸿祥的回忆显然不合乎历史事实,这固然是由于时间久远记忆有误,是可以理解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其整篇文章都充满着对殷、罗、李的偏见,尤其对李根源甚至可以说是敌意。雷飙对李、罗等同样不客气:“蔡公于辛亥年九月一日约同志刘云峰、刘存厚、唐继尧、沈石泉、韩凤楼、殷承瓛及飙等歃血为盟(罗佩金标统颇畏惧,事先运动赴河口接收军械,二十四标〈有误,应为七十四标—引者〉事由蔡兼摄,直接主持一切,更为便利)”〔5〕410。这同样与历史有较大的出入。李、雷等固然有些意气用事,但恐怕我们还不能不承认:革命前存在的纷争,在革命成功后还在某种程度上存在,随着革命的深入甚至还有恶化的趋势。
云南军政府在革命初期的巨大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其间的纷争乃至冲突,而事实上,这种纷争和冲突不仅仅是表现在本土派与非本土派、革命派与立宪派、旧官僚派之间的权力争夺,而且在同盟会派内部之间也有纷争,当然这些都和以李根源为首的同盟会与以蔡锷为首的非同盟会势力的矛盾复合交织在一起,这恐怕就是额氏所说的云南军政府内部争斗吧。由于军政府成立伊始,革命派内部的纷争要隐含得多,因而额氏显然将军政府间的冲突简单化地归结为本土和非本土的冲突。那么真实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杨琼在《李印泉先生传》有这样的记述:“方事之初……尤莫难于用人。时故官吏皆潜匿,乡之人长者,或不出,喜事者,又不足用。先生察其贤否,量材能,从人望,虚意延纳,任以事皆办。其后,人冗进,皆觊权柄,新旧争于廷,主客攻于下,用人者多嫌疑。先生独持议以谓:‘今日争省界,忘国之原,宜先去此见,乃可谋国。犹患旧人不知更张,新者不习为治,今宜取旧人有学问、新进有经验者,别其操行短长用之,亦何所嫌疑。’闻者皆服,以是为新旧主客之辩者不起,人皆尽其用,先生力也”〔2〕277。这段记述颇为翔实公允,可见军政府的确引入大量旧人、外省人等。现就时在军都督府就职的人员来看,旧人不少,然外省籍之人也占有一定的比例,诸如秘书处秘书张一鹏为江苏人、熊铁崖为黔人,军务部长韩建铎是豫人,军务次长(后为部长)沈汪度是湘人,军政部参事郑溱和民政司长杨福璋都是浙江人,外交司长周沆和参议院参事刘显治皆为贵州人,甄录处长刘锐恒为四川人,造币处副处长李佛育是鄂人,云南银行副经理刘辉祖为赣人,在军队及地方府州任职的还有刘云峰(河北)、李凤楼(河北)、曲同丰(山东)、韩凤楼(河南)、雷飚(湖南)、刘存厚(四川)等不一而足。而民政部各司司长及参事诸如吴琨、陈价、席聘臣、陈度、赵蕃、李增、段宇清、孙光庭、袁嘉谷、赵鲸、陈均、朱朝瑛等大都接受的是旧式教育,多为举人、进士出身,大都做过前清官吏,甚至朱家宝、王人文等前清有名的官吏也被引入参议院,以备顾问。二者相加在军都督府内部确占据半壁江山。不过,三部一院之长大都为同盟会员所占据,军政部长为李根源,次长为李曰垓、唐继尧,参谋部长是殷承瓛,次长为谢汝冀、唐继尧,参议院院长为李根源,此皆为同盟会会员,只有军务部长韩建铎在革命前为非同盟会员,但次长为沈汪度,是同盟会会员,可见整个军政府的主导权皆掌握在同盟会手中,而作为同盟会云南支部长的李根源自然成为军政府的核心。正如谢先生所评论:“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名义上的二把手李根源却又变成了实际上的一把手”〔6〕,可谓中肯之至。李根源对此点也丝毫不加掩饰,他在致张文光的电文中说:“缘省中之事,蔡都督虽主军政,一切之事均由源主持”〔2〕65。由此以观,额必廉之说似可采信。
然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此,作为都督府的一把手蔡锷对此又心有何感呢?我们不得而知。如果仅从个人荣辱的角度来看待此事,未免侮辱了领导重九起义的革命先驱,但蔡锷之建国治省之思想主张是否有别于李根源等人呢?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尤其是在用人标准的取舍、援川援黔方略的制定以及对待中央政府的态度和国家结构模式的选择上,二者之间可能都有着不小的鸿沟。毫无疑问,蔡锷是革命的积极拥护者和实际领导者,他主张共和,献身革命事业,但正如曾业英所评论,蔡锷“由于长期受梁启超思想的影响,不能从根本上跳出改良派的轨道”〔7〕。雷飙回忆也足以说明此点:“蔡公旋即亲赴法领事谒李经曦请其出维大局,李以个人历史关系,不肯遽出,且滇中军人亦多不同意,恐生不测,遂不复相强”〔5〕411。在北洋高官王振畿被杀的问题上更能显示出蔡锷的思想倾向:“蔡锷闻讯之后,曾抱着王振畿的尸体大哭”〔5〕371。我们暂且把谁是谁非搁置一旁,党派倾向之争已在所难免。由于时局所需,军政府内部大量引进旧官僚、立宪派,其政治主见虽与蔡有一定的差距,但比之于李根源等来说还是要近得多。即便是一些饱学之士,其观点可能会与蔡更近些,比如才华横溢的周钟岳,虽为李将之引入政府,但周钟岳与蔡的关系更为亲密,这显然不是说蔡人缘优于李,实乃是思想相接近的缘故也。况且同盟会党组织本身就很涣散,内部又有原本就对李等持有偏见的人员(李鸿祥、雷飚等)存在,此时更认为李根源太过“飞扬跋扈”,权力纷争的天平已在不知不觉中偏向蔡一方,最终结果是李以极体面的方式走出权力中心——西巡迤西。
毫无疑问,李根源出巡迤西有优于他人的条件,比如是其桑梓之地,熟悉情况,才干卓著等等。但李此时正因过度劳累而致呕血,如此艰难之重任放在一个身体虚垮的人身上能说得过去吗?李不出使迤西也是合乎情理的。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李根源出巡呢?除去李鸿祥、谢汝冀、唐继尧、沈汪度、雷飚等人外,一些不得志的立宪派、旧官僚等更是不遗余力,而蔡锷恐怕也难脱嫌疑。他似有意联合同盟会云南支部的另一核心人物吕志伊,压李就范。吕志伊在《杜韩甫事略》中曾提及到这一点:“大理驻军亦多同志,闻昆明光复,即通电表示响应,但与腾永军消息隔阂,致生误会,几起冲突。志伊与蔡锷密商,派李根源率师西巡”〔2〕225。既然是密商,恐怕是背着李所做的决定了。吕志伊之所以同意李西巡,实有想成为滇省赴鄂首席代表的嫌疑,精明的蔡锷是看得很清楚的。
以此观之,李根源之出迤西确是无奈之举。大而言之,迤西腾榆冲突应该说不是一件小事,但腾越的张文光乃是以大局为重、光明磊落之豪杰,大理的赵蕃虽起始为曲同丰等一般投机革命的部分人士所蒙蔽,但也是饱经宦海风霜的精明之士,可见腾榆冲突之解决并非什么难事。省政府派人只不过是居中调解,化解误会,实现和解统一而已。断非必须是李根源,至于授予李为第二师师长之后又加委“总统迤西陆防各军,并节制迤西各属文武”,更令人生疑:本就是省都督府的二号人物有必要拥有这个头衔吗(即便是李争取来的,那么李为什么要这个头衔呢)?如果是蔡锷主动提出授予,虽有便利事情解决的考虑,但亦隐含了要李根源长期驻守迤西的目的。这一点李根源当时虽不甚明了,但至少有些模糊的认知或者说对蔡使之西巡的目的有所怀疑。所以李并没有长期驻守迤西的打算,其真正目的是盘算如何解决腾榆冲突。因为他深知,腾榆事件最难解决的是裁兵汰勇,而裁兵汰勇的最好方法就是略加淘汰,然后加以组织整顿,率师入川,谋求更大的发展,是以他在西巡的途中就在认真思考这一战略。所以,蔡、李随后在移师入川问题上产生了较大的冲突,究其实乃是二人在这一事件上目的有着明显的不同。1911年12月2日,李根源抱病由昆明出发,“师行,空城送焉,人或惜先生去军政部蚤,未究其用者”〔2〕277。这不仅是李根源在各级各界各阶层人士中威望的展现,而且间接地暗示了李根源必然离开军政府的原因。
〔1〕王云五.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第14辑〔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1:43.
〔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65.
〔3〕胡滨.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4.
〔4〕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委员会.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53.
〔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三〔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2.
〔6〕谢本书,李成森.民国元老:李根源〔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9:141.
〔7〕曾业英.蔡松坡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3.
(责任编辑 袁登学)
Analysis of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Li Genyuan's Going to Western Yunnan
ZHANG Gensheng,WU Daoxian
(Department of Ideology and Politics Education,Yunn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Kunming 650500,China)
After recovery of Yunnan in Spt.9,it has happened one thing that the revolutionary armed forces of Tengchong and Dali conflicted with each other.The thing was so unexpected that made the provincial military government suddenly feel the strange pressure.And then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decided to dispatch Li Genyuan to resolve the conflict.Why the candidate was Li and not others?Scholars considered prevalently that Li Genyuan was born in Tengchong,and he was the leader of Yunnan branch of the United League.He has leaded the revolutionary armed forces of Tengchong.On based of the reasons,Li was the best person selected. However,author of the article believes that it is only the surface reasons,and the real and fundamental cause is the internal dispute of the Yunnan armed forces.
Li Genyuan;internal dispute;conflict between Teng&Yu;pacifying Sichuan to consolidate Yunnan
K81.82
A
1672-2345(2012)01-0051-04
2011-09-26
张根生,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