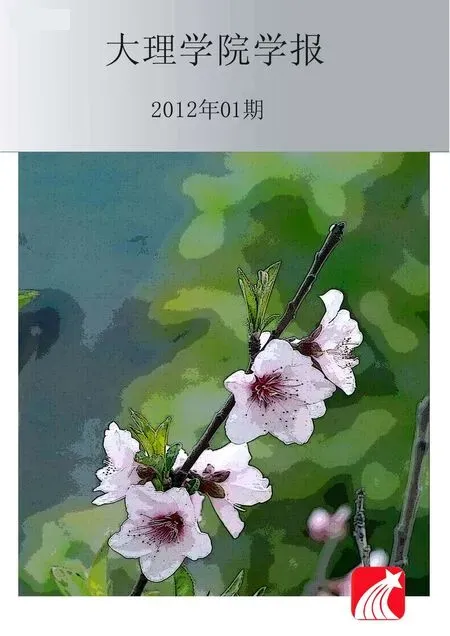民国凉山地区的保头制研究
朱映占,段红云
(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昆明 650091)
民国凉山地区的保头制研究
朱映占,段红云
(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昆明 650091)
保头制度是清末及民国时期流行于凉山地区的一种半官方、半民间的制度,其存在及运行与那个时代整个中国社会、凉山彝族社会性质和当地民族关系等紧密相关。此种制度通过保费把投保人和保头联系在一起,建立一种临时的或长久的合作关系,但在这种关系中投保人和保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因而其是一种畸形的社会制度。总体而言,其对地方社会和整个国家而言,消极作用是占主导的。然而这种制度却能够流行,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民国时期政府对彝族聚居地区治理的不善。
民国时期;凉山地区;保头制
清末及民国时期流行于大小凉山地区的保头制度,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清朝安抚凉山彝人的“包山保路”制度。清道光年间以来,朝廷对于凉山彝人的政策逐渐由“军事压服”转向“防夷”、“抚夷”。在此情形下,凉山汉彝杂居或交接地带,对于彝人,朝廷“若不能安之,则汉人之子女玉帛,房屋田产,时时有被其侵夺之可能。否则偷盗果麦,践踏禾苗,亦足以扰其生活。若此等夷人,无设官之资格,则给以年金,使其负责保护该地村庄,不得侵略汉人。此种制度,名为包山,其年金可由数两以致数百两。若此地为他支夷人所劫,则由彼代为清偿,然而包山夷人,果能赔偿之事,可谓极少。只求其不参加共同鱼肉汉人而已。至于通商大道之间,凡常为夷人出入所经者,亦请夷人保证,年给巨金,名曰保路钱。与包山制度相等”〔1〕73。
后来,民国政府的权威在凉山地区进一步衰落,原来的“包山保路”进一步演变成“保头制度”。至20世纪30年代,调查人员发现:“至于包山保路之制,沿自前清,迄无稍更。此种费用,多由地方筹集,仍能照常支应。而耕地不由夷人负责,则无法栽种。道路不由夷人保护,则无法通行。经营农商者,亦愿凑成此费。惟夷人之忠信礼仪,恒建筑于贪心之上,其欲望殆属无穷。若机缘凑合,亦可放弃其责任心,而为掳掠之举动。以政府本无威力以慑其后,无金钱以安其心,自不能完全满意。因此之故,居民除包山费外,常外加馈礼,以结好保头。每遇保头至家,尤须格外招待。而夷人遂得轮流转食,终年骚扰,无敢触怒者”〔1〕76。
对于此种保头制度,民国时期的调查者称:“所谓保头制,就是以适当的报酬,请黑夷首领(例如一家黑夷的家长)或其指定的代表,作为‘保头’(即保护者),护送过去。此种办法,大体与以前所谓‘保镖’,原则相同。报酬方式,商人以运货品的一定百分数,或按双方议定数目,送以若干银子。如系官方人士,黑夷多爱讲面子,因此所索不若对商人之奢。往往一半面子,一半实际,送一份相当重的礼物(盐布等)就够了。这样看来,所谓‘保头制’,实在也可说是一种保险制度”〔2〕130。
事实上,凉山地区的保头制度与古代的“保镖”制和近代的保险制度均有所区别,是流行在民间,得到官方默认的一种畸形的社会制度,其产生和存在是与清末民国时期凉山这一独特的时空联系在一起的。
一、保头制产生的背景
保头制的产生既有民国时期整个中国社会背景的原因,也有凉山地区社会内部的原因,更与民族间的矛盾和隔阂息息相关。
(一)保头制度是社会动荡的产物
清末及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急剧变革和动荡之中,位于川、康、滇三省接壤地带的大小凉山地区,在各种势力此消彼长无暇顾及的情况下,加之彝族奴隶主内部既相互斗争又相互联合,在此形成了与外界相对隔绝的社会,此区域遂被外国人称为“独立罗罗”。总体来看,民国时期,由于各级政府无力管辖,凉山地区劫掠横行,鸦片种植泛滥,社会秩序紊乱。然而,虽然社会动荡,凉山地区却有汉族所需的猎产品、畜产品、林产品和农产品等土产,同时彝人也需要从外引进铁器、食盐、针线、布匹、烧酒、装饰品等生产、生活用品,因此,彝汉之间的经济交流除了是一些商人谋利的手段外,更是日常生活所必需的,通常情况下是由汉商进入彝区交易,或在彝汉交接地区进行集市贸易。而在此过程中,汉商迫于生活压力,为了能够进入相对独立的凉山彝区做生意并顺利往返,就必须请黑彝首领做保了。并且,凉山彝区在一国之内形成独立于国家政权管辖之外,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情况。在导致该区域与外界交往的种种困难的同时,其更是成为谋求国家统一,民族统一的各界的忧心之所。因而,民国时期进入凉山地区考察和了解彝人情况是各界人士所期望的。然而,政府又无力保证进入凉山彝区考察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只能出资请彝人首领保护路途安全,也间接助长和延续了保头制度的存在。
(二)保头制是凉山彝族等级制度的一种延伸
民国时期,凉山彝族社会具有森严的等级制度,依据血缘、经济占有、人身权利等因素,全社会成员划分为兹伙(土司)、诺伙(黑彝)、曲伙(白彝)、阿甲(安家娃子)、呷西(锅庄娃子)5个等级。清末及民国以来,随着土司权威的衰落,这5个等级又可概括为两大阶级即“黑夷”或“黑骨头”,“白夷”或“白骨头”。黑彝阶级作为凉山地区的统治集团,其内部“由最亲近的血族关系人组成的一个小集团,通称之为‘房’。集若干同一血缘的‘房’组成一个较大的集团,称之为‘支’。再把血族的关系扩大组一个更大的集团,称之为‘家’。所谓家、支、房,便是罗罗的部落。故凉山部落组织,并无一定的统属性”〔3〕。但是互不统属的黑彝集团在整体上构成了奴隶主阶级,而白彝则构成了奴隶阶级。白彝作为被统治阶级,其人数虽超过黑彝,但其人身却隶属于黑彝阶级,由黑彝掳掠而来的汉人,战争中的俘虏,以及彝汉通婚的后裔等组成。
由于在凉山奴隶制社会下,汉人或从外掳掠而来的人都是作为奴隶阶级而存在的,加之凉山黑彝对凉山之外的世界了解有限。故而其把对待其辖地白夷和汉人的态度加之于外来汉人乃至外国人的身上,同样视他们为奴隶,不仅没有畏惧或平等相待之可能,而且还意图掠其为奴。因此,为求在凉山顺利通行,从外而来进入凉山的人,不得不出钱请保头保护。“今日凉山中有数十各自为姓氏,各不相统属的氏族部落,也便是凉山罗罗的支派。每一部落有固定之领域,有大至百余方里,而娃子多至四五千户。因此外人之入凉山者,欲行百里之地,便须逐步取保。若得不到某一房黑骨头之保护便通不过这一房领地也”〔3〕。
(三)保头制度是民族矛盾激化的反映
民国时期,凉山地区“社会秩序很乱,彝汉相互抢。经常见彝人被捆着,在凄厉的号声引导下,牵游田坝街,最后拉到小河子去杀。也常听说某某处的汉人被抢了”〔4〕。马长寿在凉山地区调查时,也看到了这样的情形:“余居雷波三月,逢罗彝入城屠杀汉人之事凡三期,远乡罗彝因杀人报官者又三起。析其原因多为复仇。或因汉诬彝杀人抵罪而复仇,或因汉欠彝债坐延不还而复仇,或因汉虏逃出而遭杀者,或因罗彝劫人而被杀者。至于掳劫之事,几二三日间必有一案。”还有“平时城厢汉人对罗彝之态度行动亦殊恶劣。罗彝妇女入城购物,滑商流氓喜乘间调戏之。猥亵之状,设汉女受之,行人裂眦。施于罗妇,则观者以为快。奸商交易,罗彝售皮、鬃、毛、药以大秤大斗入,买布、盐则以小尺小秤出。罗彝受此屈,纵太息流涕,官府亦不之直。若纠众来索,必相互动武,邻舍行人且助奸商而亏罗彝。故在城厢滋事,罗彝未有不失败者也”〔5〕。由于长期的冲突和隔阂,致使汉族具有“见蛮不打,三分有罪”的观念,而在彝族人中则有“石头不能当枕头,汉人不能做朋友”的观念。在此情形下,“汉人入倮区若无保头保护,即有生命之虞;倮胞到汉地须扯路单,胆小的倮胞一到汉地即备鸡拜当地有势力的汉人做干爸爸,以资保护”〔6〕。
二、保头制的构成和运行
保头制是保头和投保人通过一定的财物联系起来,并得到地方政府默认的一种区域性的民间制度,在其运转过程中,保头、投保人及保费缺一不可。
(一)保头及其保护对象
“‘保头’一词系边民用以表示黑夷的首领,一个有力黑夷能够保卫他的族人以及族内的娃子和财产,即可为保头。汉人投在黑夷保证之下以生存者,亦称黑夷为保头”〔7〕。可见,在凉山地区,并不是每个彝人都有资格和能力充当保头。要想做收取财物的保头,首先必须是黑彝首领;其次个人能力突出且往往家支势力强大。“在其辖境内,如有旅行者,经商者,或调查者通过,而担任保头时,能保证无其他不幸之事件发生,亦能限期令过犯者缴还,赔偿,或道歉”〔8〕。因此,在外人看来,“保头是一个酋长,他的权力支配一切……一个保头常管辖哇子或百余家,或数百家,与别个保头是各自为政的。且无论何人都不能独立,必投一个保头以讨生活,否则一定被人欺侮或掳杀的”〔9〕。
对于保头负责保护的对象,概括而言主要分为三类:一类是保护穿越凉山区域道路上的投保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一类是保护投保白彝生命、财产安全的同时,帮助白彝“打冤家”;一类是仅保护投保人耕种的土地不受侵犯。
(二)投保人和投保形式
投保人常见的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从外地到凉山地区做生意的行商;二是凉山地区的汉人或白彝居民;三是到凉山地区砍柴割草放牲畜的人。居住在凉山地区的汉人或白彝居民又分为家支集体投保和个人投保两种形式。民国时期,进入凉山地区考察的官员和研究人员也往往要请黑夷保头保护,形成一类比较特殊的投保人。如杨成志、中国西部科学院雷马峨屏考察团、马长寿、梁瓯第、川康科学考察团、林耀华等先后进入凉山地区考察的个人和团体都有请保头的经历。
(三)保头制的运行
保头制度的运行依靠的是投保人出保费给保头,保头负责保护投保人在凉山区域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其运行主要基于两个因素:一是投保人的保费,二是保头的能力和信用。
对于保费,清末时一部分由朝廷出资,民国以后则由地方筹集或个人出资。像居住在屏山、雷波等地彝区的汉人,每年均须向保证人缴纳钞米。而进入凉山做生意的汉人,通常其保费则为资本的十分之一。当然,由于地域和保头的不同,不同投保形式的保费是有差别的,“(甲)保商类。例如:A汉商入境凡通过各支地点,每支须请黑夷夷人为保头以资保护,保头请定以后不能更换。B汉商向每一保头应纳之保费,规定如下:布一綑(八十件),纳保费布一件。盐一口(约七八十斤),纳保费盐一斤。C已纳保费之汉商通过或居留其境内时,均应负保护安全之责,如发生抢劫应由保头负责将失物追回,否则照价赔偿。(乙)保护侨民类。例如:A汉民侨居夷地为安全计应找一黑夷为保头。B汉民向保头每年应纳布二件为保费。C保头有保护汉民安全之责任”〔10〕。而生活在凉山地区的曲伙与瓦加(阿甲)两个等级的人,每户对保头所履行的义务是:“过年送半个猪头的年礼;主人结婚送一锭银子或一只猪;嫁女送几斤酒;修房子等送几两银子或几斤酒;主人打冤家要参加,如双方皆系保头则可不去;赔命金时亦照三个财富级别来分摊负担;但在曲伙团结的情况下,主人虽派人前来索取,但大家都置之不理,则主人亦无可奈何。但从总的方面来看,这里的曲伙与瓦加受黑彝保头的压迫还是严重的”〔11〕。
通常“凡汉人入凉山,自来即须请凉山中一剽悍之夷人,或亲仁善邻,冤家稀少之夷人为保头,率领同去。保头剽悍,则莫之敢攫。保头亲仁,则左右逢源,困难自少”〔1〕8。而且,从外进入凉山的投保人,还往往与保头进行“椎牛盟誓”之礼,互相建立信任关系。如1929年9月,经多方联系之后,杨成志取得“大保头”禄呷呷的保护,与禄酋长行了椎牛之礼,之后在禄酋长的保护之下,杨成志途经么开、斯古、沙木箐、跑马坪等地,约200村落,800余里,深入凉山地区调查后并安全返回。然而,由于凉山地区黑彝家支林立,且互不统属,因此要经过凉山地区者,很难找到一个保头就能保证安全通过整个凉山地区。“势力强大,或者人缘很好的保头,往往一气可送三四跕,使旅客感觉方便。势力薄弱者,则有时只能送二三十里地,即需换保。此事一方面不胜其烦。另一方面,送换保头,所费代价,亦殊可观,换一次保头,就要一份保费”〔2〕130-131。即使这样,保头也不能绝对保证旅客安全,特别是出入凉山地区的汉商,有的出了保费请了保头,进入凉山保头辖区后,就被保头卖了当奴隶,显然保头的信用也没有可靠的保证。当然,对于到凉山地区考察的官员或知识分子等公务人员,彝人保头则比较不敢碰,因此民国期间到凉山考察者,均能够顺利返回。按理说,对于生活在凉山地区的曲伙和瓦加(阿甲),保头则“有责任‘保护’其生命、财产,曲伙与别人打冤家时,保头亦理应帮助,但在实际上却没有一个保头能对他的投保者做到这点。保头对保护投保者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帮助他们反抗外来的黑彝侵入方面都是徒具其名,旁观坐视,甚至助桀为虐,以达到他们进一步奴役白彝的实是普遍情况。所以,我们认为保头在此主要起着的是压迫曲伙、瓦加的作用,而不是什么‘保护’作用”〔11〕25-26。
总体而言,每个保头相对于整个凉山地区而言,其能力是有限的,能保证投保人安全的区域也是有限的。而保头的信用,则完全建立在财物的获取上,并且投保人与保头之间没有第三方或者法律制度来规约其权利和义务,投保人相对于保头处于完全信息不对称,地位不对等的状态,因此保头的信用的好坏,就只能取决于一时一地的情势及保头个人的好恶。显然保头制度下的保头,其信用很难有可靠的保障。
三、保头制的作用评价
在特殊时空条件下运行的保头制度,总体而言,其消极作用是占主导方面的。当然,其存在,又使得凉山彝区与外界交往成为可能,而不是完全隔绝。
(一)积极方面
其一,在政府管理不能有效达到的凉山地区,“保头制的施行,使凉山旅行,成为可能”〔2〕130。而且,保头制的存在也使得凉山彝区与外界有限的经济、文化交往得以艰难维系。
其二,由于保头制的存在,间接阻止了民国年间谋利的商人和大小军阀对凉山地区大肆盘剥的企图,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彝区居民的利益。凉山彝区“汉人根本不敢去,兵士亦非例外。同时少数武装队伍,亦无用处”〔2〕130。
(二)消极方面
保头制的存在阻碍了凉山彝区与外界在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正常交流,进而滞缓了凉山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如在小凉山的雷波县,就是由于无法忍受凉山彝人的劫掠和收保费,“多数商人,改行云南省地,交易中心,渐次移至井底,本地商务遂一落千丈”〔12〕216。随着商业贸易的减少,凉山地区的经济也日趋萧条。由于政府没有能力对凉山地区进行有效管理,使得家支林立的凉山地区的保头制度,成为在军事压服之外,政府及外部社会与凉山地区保持交流的唯一依靠,其不仅在民间流行,而且受到政府的间接支持,甚至有的地方政府还有专门的保头介绍给进入凉山地区的人员。这就使得凉山地区在民主共和时代却仍能维持人身不平等的奴隶制度。此外,凉山彝区没有使用通行的货币,一切交易均采取以物易物的形式,外来人员的保费也同样以布、盐、针线等物品支付,由于要顺利通过凉山,往往要请多个保头保护,这就需要随身带有大量物品以作保费,无疑大大增加了行人的负担和困难。且冒险进入凉山的汉商,“受保头的保护,在保头家里住下,名为商人,实同奴隶,背水推磨,都有他的份儿”〔13〕。在此情形下,如果不是走投无路或想一本万利做发财梦的人是不愿踏入凉山地区的,这就把凉山地区推入了孤立和与世隔绝的境地。
加深了各种矛盾和互不信任,助长了凉山彝人的“我族中心主义”,不利于“国内民族一切平等”目标的实现。如在雷波县,“现时境内人民,大多住居城镇附近,其距离稍远者,则请彝人保护。县城与黄琅交通亦时时为彝匪所阻碍,非有黑彝保护,不能通过。惟保护之制,不仅消耗保费,且无甚保障,如黄琅之羌海坝一带,彝人保地也,今年被彝人烧杀一空,箐口山上之商人百余名,亦被其保护之彝人捆去”〔12〕219。显然,保头制度不仅没有在投保人和保头之间建立良好的信用与合作关系,而且还加深了彼此间的偏见与仇恨。另外,由于除了居住在凉山地区的汉人须请黑彝做保头外,即使是从外进入凉山的客商、科研人员、政府官员,外国人等也都要请保头,才有进入凉山通行的可能。这无疑更加助长了凉山黑彝“夜郎自大”的心理,不利于此区域民族间平等关系的建立。
由于当保头有利可图,在凉山彝人内部,一个家支的保头位置被其他氏族家支的人夺走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因此时常引起氏族家支之间的械斗和战争。如民国二十八年梁瓯第在昭觉县府停留找保头时,彝人八溪拉木和诨名瞎子的黑彝就为了争当他们的保头而在梁瓯第和昭觉县长面前扭打起来,幸而被昭觉县长及时制止才防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
保头制度加重了当地居民的经济负担。在凉山彝区居住的汉人或白彝通常同时要投几个保头作为保护人。如在雷波县的上田坝,“曲伙与瓦加在这一带,一般都有两户以上的保头,最多的甚至达到六、七户”〔11〕26。并且,投保人除了要向保头缴纳保费外,如果保头上门,还要设酒食殷勤招待。更有甚者,保头家遇到年节、嫁娶等事,还会向投保人索要礼物,由于无法忍受,一些白彝不得不联合起来,拒绝保头的要求。他们对保头说:“保头太多了,你们都来要,我们无法了,只好迁走吧”〔11〕28!
清末民国时期凉山地区的保头制,是改土归流以来,土司制度衰落,土司权威丧失,流官制度虽然建立,但尚未发挥有效作用情况下,社会秩序混乱的产物,其存在一方面阻碍了凉山地区与外界的正常交往,也妨碍了凉山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得凉山地区民族关系更趋紧张,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和建构。这就说明从传统的王朝体系向现代民族国家体系转变过程中,要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现有效治理,不能仅从政治形式上进行改变,更不能期望一蹴而就解决问题。而具体到凉山地区,就需要从社会制度变革、少数民族治理方式和民族关系的转变等方面着手。在社会制度变革方面,如果凉山地区人分等级的奴隶制度不改变,其统治阶级就不能有与他人平等相待之可能,这就与当时整个中国社会谋求建立共和国家制度的历史趋势相违背,那么凉山彝区也就很难整合在民族国家之中;在少数民族治理方式方面,如何改变在武力征剿与高官厚禄安抚之间徘徊的传统治理模式,在平等相待的基础上,建立良好的法律制度,“以法律维系人心,不分汉夷,同等待遇,方能树永久之基础”〔1〕120-121,是政府实现对凉山地区长期有效管理的前提之一;在民族关系方面,改变传统的“华夷之辨”、“夷夏之防”观念,逐渐消除民族偏见和歧视,相互间建立同为一国之民的平等理念和平等关系,从而推动凉山彝区在各方面与外界广泛的交往,是凉山地区走出孤立与隔绝状态,主动参与到国家建设中来的必要条件之一。
〔1〕常隆庆,施怀仁,俞德浚.雷马峨屏调查记〔M〕.北平:大学出版社,1935.
〔2〕曾昭抡.大凉山夷区考察记〔M〕.上海:求真出版社,1947.
〔3〕李景汉.凉山罗罗的氏族组织:一个实地调查的介绍〔J〕.边政公论,1941:3-4.
〔4〕岭光电.忆往昔:一个彝族土司的自述〔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16.
〔5〕马长寿.凉山罗彝考察报告〔M〕.成都:巴蜀书社,2006:13-14.
〔6〕陆寿康.川康滇三省省边区:大小凉山区域边政问题的商榷〔D〕.武汉:国立武汉大学,1945:37.
〔7〕林耀华.凉山夷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15.
〔8〕徐益棠,雷波.小凉山之罗民〔M〕.南京: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44:55.
〔9〕施爱东.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与早期西南民族调查〔J〕.文化遗产,2008(3):46-57.
〔10〕庄学本.西康夷族调查报告〔M〕.雅安:西康省政府,1946:97-98.
〔11〕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四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县上田坝乡社会调查报告〔M〕.北京: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62.
〔12〕四川贵州彝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编辑组.四川贵州彝族社会历史调查〔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
〔13〕梁瓯第.我怎样通过大小凉山〔M〕.贵阳:文通书局,1944:38.
(责任编辑 袁登学)
Study on the System of Baotou in Liangshan Region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ZHU Yingzhan,DUAN Hongyun
(Insitute of Ethnic Cultures,Yunnan University,Kunming 650091,China)
During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the system of Baotou was a popular semi-official and semi-private system in Liangshan region.The existence of the system wa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whole Chinese society,the nature of Liangshan Yi society and the local ethnic relations at that time.Such a system associated with the insured and the Baotou by the insurance premiums,and established a temporary or long-term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In this relationship the status of the insured and the Baotou was inequality,which was a type of deformity of the social system.Overall,for the local community and the country as a whole,the negative effect of the system is dominant.However,the appearance and popularity of this system indicated from one angle that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an governace to Yi was bad.
Republic of China;Liangshan Region;the system of Baotou
C912
A
1672-2345(2012)01-0005-06
2011-11-10
朱映占,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西南民族历史、宗教与文化研究.
——与林刚先生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