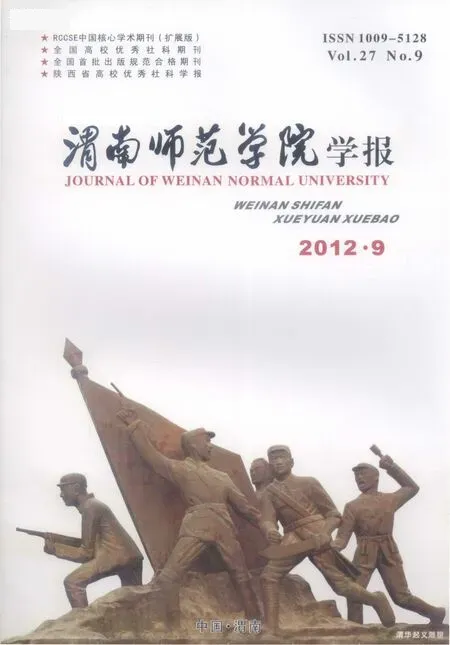论中国文学批评现状与出路
——以“笔耕文学研究小组”为例
孙新峰
(宝鸡文理学院中文系,陕西 宝鸡721013)
论中国文学批评现状与出路
——以“笔耕文学研究小组”为例
孙新峰
(宝鸡文理学院中文系,陕西 宝鸡721013)
当下中国文学批评深陷模仿和阐释他人的旧语境中;全媒体时代及“编辑文学”、多模态文学等现实存在,浅批评风行;缺乏问题意识和清醒判断力,无法克服刻板印象;精神低迷,状态不佳。而同样在中国文化沃土里成长起来的“笔耕组”却很好地规避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各种不足,坚持中国特色批评路线,得到了作家的认可和社会的肯定,成为中国文学批评领域有意味的品牌之一,为中国当下文学批评提供了思路,作出了示范。
中国文学批评;困境与出路;“笔耕组”;复制;创新
一、中国当下文学批评现状
无可否认,中国当下的文学批评深陷传播困境之中,批评的存在本来是为了播布中国的文学作品,却没有想到非但未把中国的文学推向世界,自己却深陷泥淖,处在尴尬和无为的境地。近20多年来,从“失语”、“缺信”和“缺位”、“缺德(缺乏个性体温、人文关怀)”到“真正透彻的批评为何总难出现?”“文艺批评的锋芒哪去了?”“全媒体时代文学批评何为”“文学批评死了”等关键词充分显示了当下文艺批评的现实尴尬和危机。其实这并不只是一个地区的问题。概言之,当下文艺批评成就可观,问题不少;虽有队伍,但各自为战,集体战斗力不强;评论家和作家关系缺乏默契,批评缺乏有效性;一些评论家缺乏骨格和审美品格,人格依附比较严重,口碑不高;批评对象不集中,随机性强,缺乏长期性、针对性;文人相轻在批评界仍有出现。批评无从用力、或用力不均、或力度高度效度不够。在新的文学语境和伦理秩序下,文学批评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之所以出现这么多不容乐观的状况,表面上看是方法论、审美品格或泛文化批评等问题,其实归根结蒂是批评精神问题。对此,评论家雷达《真正透彻的批评为何总难出现?》、李扬《对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回顾与反思》、饶先来《当代文学批评发展的困境与趋向》及中国作家网“今日批评家论坛”、近期《文艺报》等均有多文涉及。具体来说,处在当下中国文学批评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与挑战。可以说,批评界已经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暂时无力改变。汉语已成为国际语言,中国文学批评还深陷模仿和阐释他人理论旧语境,无法突破;这种困境主要表现在“无根”的理论困境、“无方法”实践困境、“无标准”评价困境、“无人”批评人格困境、“无群”批评队伍分化等。主体缺席;批评明星化、庸俗化、商业化、浮躁化等倾向明显;全媒体时代及“编辑文学”、多模态文学等现实存在,浅批评风行。缺乏问题意识和清醒判断力,无法克服刻板印象;精神低迷,状态不佳。呈现九多九少:名作家批评多,成长中作家关注少;男作家批评多,女作家批评少;表扬多,批评少;花样批评多,切中肯綮批评少;宏观印象批评多,精细文本批评少;自娱自乐多,责任批评少;知识搬家多,反思创新少;评论文章多,优质文章少;从业人员多,与大作家对等的大批评家少等。当下,国家品格、民族特色文学批评体系正在重建。“为何评?评什么?怎么评?”仍是学界普遍感到困惑和焦灼的问题,亟需固本培元,返本开新,砥砺创新批评精神。
二、“笔耕文学研究小组”:一个令人惊异的文学批评团体
30多年前,即1981年,全国第一个文学批评家团体——“笔耕文学研究小组”(以下简称“笔耕组”)在西安成立,由陕西当时一批中青年文艺评论家组成。组长是王愚、肖云儒,副组长兼秘书长为李星,其他成员有刘建军、刘建勋、李健民、畅广元、陈贤仲、蒙万夫、薛迪之、孙豹隐等,顾问为胡采、王丕祥。1982年扩大吸收陈孝英、李国平等,并由李国平担任秘书。“笔耕组”在陕西的文艺批评乃至全国的文艺批评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作为在全国成立最早的文学批评家团体,‘笔耕组’很快就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但得到了时任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的高度评价,更被相关媒体称为‘集体的别林斯基’;《红旗》杂志还专门刊发了经验文章。”[1]30 年来,“笔耕组”笔耕不辍,直接促成《小说评论》诞生、全国第一个文艺评论家协会在陕西成立。一定意义上讲,没有“笔耕组”,就没有后来中国文坛的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也就没有今天陕西文学辉煌夺目的成就。2011年底,陕西省文联为“笔耕组”颁发特别奖的授奖词是:“‘笔耕组’以自觉的文化责任感和担当意识,开创了陕西文艺批评‘精诚团结,辛勤笔耕,勇于探索,甘于奉献’的全新传统,其杰出的创新能力、追求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的精神,体现了批评家难得的才、胆、识、略。其必将成为陕西文艺批评薪火相传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从而推动后世的文艺批评。”[1]
谈到陕西文学批评,人们最先想到的就是1942年毛泽东“延安时期文艺讲话精神”的启蒙。而真正的开拓者,应该是郑伯奇、胡采、李若冰等人。郑伯奇,原名隆谨,陕西长安人。1926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学哲学科。1919年参加同盟会,1921年参加创造社,后历任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黄埔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官,上海创新社负责人,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教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常委,争自由大同盟成员,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编辑,《新小说》月刊主编,明星影片公司编辑,西安《救亡》周刊主编。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西北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干部,西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西北文学工作者协会主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副主席,陕西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文联第二、三届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二届理事。1920年开始发表作品。195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在十七年的秦地批评活动中,郑伯奇作为五四时期的老作家,和许多老作家一样,中止了创作而较多地从事文学批评和组织工作。他在本土常是以‘陕西新文艺’的先驱形象出现的,享有较高的威望。”[2]348有《郑伯奇文集》三卷本行世。“在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学批评活动中,胡采算得上是秦地批评界的权威。”[2]348胡采向来有“文坛巨匠”之誉。他从 20世纪40—90年代,就出版过《从生活到艺术》《胡采文学评论选》等十本评论集。他高举“革命现实主义理论旗帜”,以“生活真实在创作中的作用”为准绳,对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柯仲平、魏钢焰、李若冰,包括后来的陈忠实、路遥、贾平凹等作家予以评论和鼓励,极大地鼓舞了文学陕军的士气。1980年“笔耕组”成立时,胡采就是顾问。在胡采遗体告别仪式上,陈忠实说:“我认为胡采对文学、对作家的理解是深刻的,对青年作家的爱护是发自内心的。”贾平凹说:“我在文学上的一些想法和做法,不乏胡采的‘点化’之功。”中国西部作家研究中心主任刘卫平说:“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胡采都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在《讲话》后的文学发展历程中,胡采的投影是浓重而巨大的。杜鹏程曾写过一篇《历史的脚步》,而胡采的脚步也堪称陕西文学的脚步。”[3]李若冰主持陕西文联工作时期,文学陕军和评论陕军继续向纵深发展,保持了相当可贵的锐气和生气。加之李若冰本人也是作家,他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散文很出色,“大气清正,崇高坚实”。“自然、社会、生命糅合交织一起,构成李若冰散文的主题话语和精神向度”,其“以赤子情怀拥抱大自然、生活、生命的散文精神仍然是我们珍贵的思想财富,从‘写什么’这个意义上来说,李若冰散文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4]可以说,从郑伯奇到胡采再到李若冰,陕西文学批评组织圈始终保持良性健康发展局面,李若冰之后,陕西作家协会书记雷涛(包括省作协副主席、茅盾文学奖评委、小说评论现任主编李国平等)、一度担任陕西文联专职副主席的肖云儒(肖云儒期间或之后,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孙豹隐、李震等)自觉成为文学批评活动组织圈的灵魂人物。陕西文学批评事业薪火相传,自觉完成着“换代”和可持续发展的任务。
“笔耕组”成立伊始,其主要的评论对象便是陕西小说,这对陕西小说创作的促进作用是不可低估的。阎纲曾说:“陕西地面,人杰地灵,既有作家群,又有评论家群。少长咸集,群贤毕至,像笔耕小组这样一支批评劲旅,全国能数出几个!虽属地方选手,却打出了国家队的水平……我读过他们写的好文章,他们代表陕西小说评论的希望。”[2]350常年浸淫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笔耕组”成员都奠定了自己独特的理论批评地位。肖云儒有关西部文学的理论已经被学界广泛接受,其关于散文“形散而神不散”的理论至今演绎着不败神话;“敢言多思”的王愚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坚持探索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流变,始终挺立在潮头浪尖;精警大气、与时俱进的畅广元对文学主体论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探索,以及对中国文学批评文化转向的相关理论和陈忠实个案研究,至今无人能出其右;陈孝英的喜剧美学理论建树,开拓了喜剧批评的新的原野;“生拙老辣,意气纵横,有古君子之风”的费秉勋的《贾平凹论》,不仅成为新“贾学”研究的先声,而且得到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广泛认可。
30年的坚持,“笔耕组”成绩辉煌,但是随之也出现了一些图解政策、知识结构陈旧、批评态度拘谨、视野不够宏阔等负面声音。如杨乐生在肯定肖云儒“对视”书系的价值时说:“从肖提出‘散文的形散神不散’起,中经为现实主义文学正名、审美理想等的有益探索,‘西部美’的理论建构,一直到近数年有关‘长安文化’的深入研究,加之他对几乎所有艺术门类的探索的散文、随笔及小说的艺术实践,都使肖云儒成为研究当代文学、文化艺术乃至一部分当代学术领域绕不过去的一座山。……但是,其论著的缺陷和不足也明显地存在着的,我以为,除了肖本人原因外(也是主要原因),我们千万不可忽视时代、社会风气对肖的影响和制约,这个个案,也完全可以以中国当代学术、理论和批评的缩影目之。”[5]72-75韩鲁华也有相同认识:不论就“笔耕文艺评论小组”成员构成的理论素养,还是其文学批评实践,客观地讲,都不可能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本体文学批评,最少,批评的意识形态化的痕迹还是非常明显的。这是历史时代所限定的。但是,它难能可贵的是,在国家权力意志和意识形态话语下,尽力向着文学批评本体靠拢。也正因为如此,“笔耕文艺评论小组”对于陕西文学创作的批评,是切合实际的,极大地促进了陕西文学创作的发展与提升。特别是对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他们那一代作家的文学创作,给予了引导和指导性的评价。可以说,他们那代作家的创作从中获益颇多。当然,从今天来看,也有批评的不太妥的地方,比如对于贾平凹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厦屋婆”悼文》代表的一批作品的批评,就有失公允,最少是缺乏历史发展的前瞻性和敏锐性。虽然如此,其批评的态度则是严肃而认真、坦荡而真诚的[6]。不管怎么说,“笔耕组”建设性探索性批评对陕西文学繁荣做出了突出贡献。
可以说,通过30年批评实践,从中国文化沃土里诞生的“笔耕组”很好地解决了方法论等问题,得到了作家和社会的普遍认可,体现出了一定的中国精神和品格。已经成为中国文学批评领域一面旗帜,一个足金的品牌。“笔耕组”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一面镜子,其坚持审美个性和文化品格、坚持中西合璧、“别车杜”经验中国化、创新批评理念,坚持中国特色,用一个声音讲话,不断学习,积极跟进,重在建设,总结出了柳青道路、路遥经验、陈忠实视角、贾平凹现象、红柯笔墨等对全国都有借鉴意义的创作经验;突破了旧语境的桎梏,为当下文学批评创新提供了思路,做出了示范。
三、“笔耕文学研究小组”批评特色和贡献
“笔耕组”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领域都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个作家和文艺家群体。“是当代中国文学批评领域一个极具意味的现象。甚至可以说是当代文学批评体制史上的一种特异现象。严格地讲,这应当是一种带有极强的同仁性质的文学批评团体,而非严格意义上的体制化的文学批评组织机构。今天的‘陕西文学艺术评论家协会’、陕西省作家协会评论委员会,方是体制下的文学批评组织。‘笔耕文艺评论小组’具有着历史的超前性,更确切地讲,应当是在当代文学批评历史建构中,凸现着特异性。我甚至认为,这也是1980年初始全国思想解放,各种文化思想潮流所融会而成的改革大潮,所促成的文学批评上一个历史的幸运”[6]。韩鲁华此语可谓一语中的。
除了胡采、蒙万夫、王愚等已经过世的之外,“笔耕组”核心成员畅广元、李星、肖云儒、费秉勋等已经70多岁。一定意义上讲,其批评经验必须研究,而且研究就是抢救。众所周知,“笔耕组”吸取原苏联经验,走的却是有中国特色的批评路线。他们本着尊重创作,对视作家作品,理解作家的态度,持续介入,跟踪语境。开展认真的学理批评。其努力告诉我们:西方理论中国化的特色文学批评仍大有作为。与当下作家与评论家关系冷漠不同,“笔耕组”时期,确立了“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相结合”的持续介入批评精神和原则,作家和评论家建立起了难得的良性互动的关系,如陈忠实说“我是被蒙万夫老师骂出来的”;贾平凹也说“‘笔耕组’敢说实话,能点到穴位上”;作家叶广芩也说“我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作家,主要是李星等老师不断地‘砸’的结果”[1]。“笔耕组”30年的努力直接为当下“创作评论两张皮式”批评提供了启发和借鉴。纵览“笔耕组”30年批评实践,可谓成就辉煌,经验可贵。有一个事实已经引起大家的注意,也就是“笔耕组”成立时期,正是“西学东渐”之时。“笔耕组”的成功,一定意义上也是异域方法论在中国文学批评“软着陆”的成功。陈孝英的喜剧美学批评,薛迪之的比较文学视野,畅广元、李星、肖云儒等的文学文化批评都已经形成品牌。和中国当下活跃的老作家一样,陕西这些老批评家更多地吸收了原苏联的批评传统、批评精神。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批评理念烙印极深,“集体的别林斯基”并非虚妄之言。总揽“笔耕组”30年批评实践,坚持社会历史批评传统,坚持现实主义批评原则和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理念,高扬时代精神,以“尊重”、“对视”“理解”作家创作为关键词,不猥琐批评人格,从阶级性、人性、人民性等角度体察中国文学,在批评的文学性方面做了大量“去魅”和“还原”的工作,鞭挞假恶丑,弘扬真善美,批评充满着时代风格和个性体温。肖云儒的灵气,畅广元的大气,李星的率真深刻,都以鲜明的批评个性打开了局面。
20世纪80年代“笔耕组”才开始艰难起步,从陕西走向全国。1972年,陕西文艺创作研究室成立,以《延河》杂志1980—1981年连续两期刊发的“陕西中青年作家专号”,以及配发的曾镇南长篇评论文章为标志,全国第一个地域性作家群“陕西作家群”开始叫响文坛;同时,以《延河》《陕西文艺》等为平台,“文学评论陕军”初步形成;1981年“笔耕组”成立,集体向全国发出声音,就“写真实”等问题集中发表意见;1981年夏天,在秦岭深处太白县召开“太白会议”等,“笔耕组”成员集中向青年作家陈忠实、贾平凹、邹志安、李凤杰等对症“开炮”,指出创作问题和不足,力促其克服调整创作弱点,向全国一流作家看齐,“笔耕组”声名鹊起;从20世纪90年代,“笔耕组”成就杰出,这一阶段的成就主要表现在,“笔耕组”直接促成了“陕军东征”这个中国文坛重大事件,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程海、京夫、高建群等作家的长篇作品在文坛集中亮相,引起中国文坛注意;同时,正是在胡采和“笔耕组”努力下,“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相结合”成为陕西文艺工作的主要经验之一。2011年底,笔耕组背负着沉重的使命光荣谢幕。“笔耕组”已经成为历史的背影。
可以看到,“笔耕组”的魅力虽然是集体作战,一个声音讲话,却个性突出,10余人构成了十个人的文学批评史,形成了独特的个人批评魅力。“笔耕组”之品牌之所以成功,完全是在科学批评精神指导下,积极规避中国文学批评进程不利因素、坚持投身批评实践的结果;其不足亦是中国文学批评进程出现的不足;其成功经验可互补、参照、推动当下文学批评积极调整,突出重围,创新发展。地处陕西,自由、包容的学术环境和氛围,是“笔耕组”出现的基本条件;自觉的社会担当意识和主动献身文学的精神,使其能在中国文坛发出自己的声音,一坚持就是30年;“笔耕组”每个人的批评经历都是一部个人的文学批评史。总体开看,“笔耕组”的文学贡献主要在三方面:
其一是促成了“陕军东征”事件,凝聚了陕西作家。
“构成‘陕军东征’文学现象的代表性作品,除《白鹿原》和《废都》外,还应包括《最后一个匈奴》《八里情仇》《骚土》《热爱命运》《兰袍先生》等作品”。其“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市场经济的确立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对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撞击的结果,也是新时期文学发展进程中新旧交替不断演化的结果”[7]16。尽管对“陕军东征”这个提法还有争议,但是陕西有一大批潜力雄厚、实力强劲的作家已经成为文坛公认的事实。自此,散兵游勇的陕西作家有了榜样,有了归属感。商洛作家群、岐山籍作家群、陕北作家群、西安作家群,甚至出现“西北大学作家群”现象,可谓“异军”突起,群峰鼎立。他们遥相呼应,构成了陕西地域作家群的基本底色。文联和作协的凝聚力也显著增强,得到了作家和艺术家们的普遍认同,他们视文联和作协为“家”。如同李继凯所说:“对秦地小说家来说,能有这样一个‘家’,毕竟还是很幸运的,在这个‘家’的安慰鼓励和帮助下,小说家们多少会快一些走出秦地。”[2]359陕西文学响亮文坛,突出重围已指日可待。
其二是促成了《小说评论》杂志在陕西诞生。
正是在“笔耕组”努力下,1985年,全国唯一的《小说评论》杂志在陕西诞生,胡采、王愚、李星、李国平先后担任主编。经过20多年发展,已经成为中国文学评论主要平台;并一度入选全国中文核心期刊;2008年以来连续入选CSSCI核心数据库,办刊质量不断提升,学术影响力不断增强,实现了办刊的历史性突破。关于《小说评论》创刊,《小说评论》主编李国平这样说:
《小说评论》是“笔耕文艺评论小组”发展的合乎历史逻辑的一个结晶。也是进入后“笔耕文艺评论小组”时期的重要体征。就当时的情况看,“考虑到虽然有一支文学批评队伍,但是,没有阵地,难以巩固,难以发展,从1982年起,就有不断的呼吁创办一个专门性的理论批评刊物。1984年全国当代文学年会在西安召开,创办《小说评论》的欲望得到了与会专家、批评家的呼应和肯定。于是《小说评论》顺乎时势,应运而生”。[8]
韩鲁华也指出:
进入后“笔耕文艺评论小组”时期,“笔耕文艺评论小组”的个体成员,对于陕西文学评论新人给予了提携与培养,但是作为一种集体行为,其作用则是十分有限。这样,《小说评论》就历史地承担起凝聚陕西以及全国文学批评力量的责任,发挥了它的阵地优势。特别是,它以一个专门性的文学评论刊物,吸引了全国一大批从事文学评论,这里自然是指小说评论方面的专家学者,刊登了许多具有前沿性的探讨性的学理性的小说批评文章。这不仅在促进陕西的文学创作与批评,发挥了积极作用,就是对于促进全国的小说创作与批评,以及文学理论建设和发展,亦是发挥了积极作用。可以说,系统性阅读《小说评论》不仅可以看出新时期小说创作发展的历史路向,亦可把握文学批评及其理论建构的历史路向。[6]
李继凯这样评价:
多年的实践证明,《小说评论》的确是小说家(尤其是秦地小说家)的益友和诤友,她为秦地小说家提供了一面镜子,同时,在一定意义上讲,她也成了秦地小说家与评论家密切合作的一种象征。[2]351
其三,形成了“陕西特色”的“青创会”等创作评论研讨会议制度,锻造了一支在全国有竞争力的创作和评论新军。
和作家结朋友,“一对一”进行批评是“笔耕组”的传统。陈忠实对此颇有体会:“《笔耕》文学评论组的几位主笔,对陕西新时期冒出的几位青年作家一直关注其创作发展动向,却不知是有意分工或是各有偏爱,又都有各自研究的作家对象,关注并指点我的创作的是西北大学中文系的蒙万夫教授,写有专论。蒙老师不幸中年早逝,西安文理学院的王仲生教授又偏向于对我写作的关注。”[9]“笔耕组”进行批评的主要方式就是开文学讨论会。李继凯曾就新时期以来的秦地文学“会议文化”进行过考察。他说:
1978年12月25日,作协、《延河》编辑部举行座谈会,为杜鹏程及《保卫延安》平反;1979年5月24日,《延河》编辑部召开文学专题座谈会;1980年7月10日,《延河》编辑部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分析创作现状;1981年11月12日,作协、西北大学、陕西师大、省现代文学学会、《延河》编辑部联合召开《创业史》及农村题材创作研讨会;1982年2月10日,“笔耕组”召开贾平凹创作讨论会;1983年12月27日,“笔耕组”召开座谈会,讨论近年来的有影响的30余部中篇小说,包括路遥《人生》、贾平凹《二月杏》等;1984年3月22日,作协召开农村题材创作研讨会;1985年8月20日,省作协召开长篇小说创作促进座谈会。自1986年后,秦地文学界各类会议更有增加,仅长篇小说讨论会每年都要召开一次或多次了。……在秦地,文学讨论会大多是严肃的。……80年代的“笔耕组”成员大都深受传统的三秦文化的影响,仍能保持严肃慎重的批评风格……[2]354
其中20世纪80年代初陕西作协在太白县召开的“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可谓影响深远。“会上,王愚、肖云儒、李星、刘建军、蒙万夫等作家评论家,针对陈忠实、贾平凹、京夫、邹志安4位当时的青年作家进行了尖锐激烈的批评,这次会议让陕西文艺界至今难忘,是划时代的、里程碑式的会议。”[10]1984年,在陕西文联举办的相关评奖会议上,“笔耕组”和《延河》获得“陕西文艺开拓奖”中的“知音奖”;2011年12月30日,在陕西文联“第二届陕西文艺评论奖”颁奖会议上,“笔耕组”集体荣获“特别贡献奖”。在此,笔者还想强调有三次研讨会也应该载入史册。其一是1998年8月18日至20日,陕西省作家协会在秦岭主峰太白山下的眉县汤峪召开了专题研讨会,对当时创作比较活跃的六位中青年作家及其作品进行了讨论。这是继1997年在延安召开的全省青年作家会议之后,陕西召开的又一个主要以青年作家为对象的创作研讨会。50余名评论家、编辑参加,对王观胜、叶广岑、冯积歧、冷梦、红柯、寇挥六位作家进行研讨。其二是1999年9月2日,由陕西省作协、陕西省文联、宝鸡文理学院主办的“红柯作品研讨会”在西安召开。陕西及来自京津的40余位评论家及有关人士参加了研讨会。现在陕西文坛已经进入了“红柯代”。其三是,“2008年12月8日,陕西召开贾平凹获茅盾文学奖表彰暨陕西省青年文学创作会议,邀请了李星、梁向阳、周燕芬、常智奇、赵德利、畅广元、段建军、杨乐生、冯希哲、沈奇等十位评论家和贾平凹、冯积岐、张虹、红柯、冷梦、王观胜、朱虹、闫安等十位作家对寇挥、张金平、刘爱玲、林伦、黎峰、丁小村、高鸿、杨则伟、李小洛等十位青年作家进行了‘对文不对人’的认真细致的分析和评论”[10]。媒体称与“太白会议”不同,这种“二对一”即每位青年作家对应一位评论家和资深作家式批评方式独创,其实早在笔耕组主笔畅广元编辑《神秘黑箱的透视》一书时就采用过“青年评论家先发言,作家回应,老评论家再批评”的模式。陕西已经形成了召开研讨把脉诊疗作家创作的制度。可以说,陕西文学研讨会已经走向成熟,其有效性不言而喻。各种各样的研讨会成为“笔耕组”展现自我个性,促进陕西文学争先进位的当然的主要平台。在“笔耕组”影响下,陕西文人民间雅集文学沙龙蔚然成风。
正是长期不断地建设性批评,对陕西青年作家不间断地帮助、推进,《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秦腔》等先后获得茅盾文学奖。可以说,“笔耕组”及其为主体的评论界为陕西文艺崛起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正如畅广元所说:“陕西文学评论界有两个特点,一是团结;二是尊重作家。”[11]547尊重和团结并不是放弃原则,在“笔耕组”身上,找不到“月是故乡明”的小家子批评意识。热切关注不冷漠;实话实说不藏着;做作家知音,不做敌人;提前预警,雪中送炭;坚持思想的、历史的、审美的、艺术的、文学的标准,重在建设,而不是乱棒打死,再踩上一脚。针对作品不对人,名家普通作者都关注。全程“介入”创作过程,及时进行帮扶指导。在30年的批评实践中,“笔耕组”逐渐形成了鲜明的批评品牌:诸如“精诚协作、辛勤笔耕”的“笔耕组”共识;团结就是力量;骨气形成品格;敢言形成风格;坚持形成性格;深度介入创作等。笔者也完全认同韩鲁华教授指出的“笔耕文艺评论小组”的同仁性和本体性。他说:
“笔耕文艺评论小组”出现于80年代初,不可能脱离体制的约束,但是,就其发起的情形看,可以说,是陕西一批钟爱于文学批评的同仁,为了促进陕西乃至全国文学创作的繁荣与发展,而走在了一起。或者说,它是“一个民间文学研究团体”,“聚集了一批文学批评力量,在全国也造成了相当影响”。这是一种文学批评的自觉地行为,而非完全的体制文学批评行为。因而,也就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去非文学功利性的意义。[6]
“笔耕文艺评论小组”的文学批评史的价值和意义,是不可忽视的。甚至它在这方面的探索,仍然对于我们今天文学批评体制的建构与变革,可以提供极富历史意义的启迪。笔耕组有自己的评价标准,主要坚持历史的、审美的、文学的标准,针对作品不对人,全程介入。我以为笔耕组的批评关键词主要是尊重、理解、对视,尊重作家创造;理解作家心理,是对视而不是俯视、仰视、斜视。2000年9月,中国文坛发生“博士直谏陕西文坛事件”,陕西籍评论家李建军当面对陈忠实、贾平凹作品《白鹿原》《怀念狼》以及公认有成绩的陕西文学和批评界发难,指出陕西文学创作和批评存在重大问题,此后以《三秦都市报》为平台,学界、社会各界对此展开争鸣讨论,被称为“博士直谏陕西文坛事件”。2007年,在陕西召开“新时期陕西文学三十年研讨会”上,李建军在陈忠实、贾平凹因故缺席的情况下,发表了长篇演讲,主要指出陕西文学从创作到批评问题多多,不容原谅。其实面刺作家创作不足甚至失误一直是“笔耕组”坚持的风格,从一定意义上讲,从陕西文坛走向全国批评界的李建军是未进入“笔耕组”的“笔耕组”成员,该事件可以看作是“笔耕组”批评风格历史的回声。
毋庸讳言,“笔耕组”对陕西文学批评力量的换代和交接做出了贡献。韩鲁华指出:
《小说评论》,在后“笔耕文艺评论小组”时期,一方面可能仍然延续着“笔耕文艺评论小组”文学批评的传统或者历史责任。一个有力的证明就是,《小说评论》的编委会构成的基本成员,绝大部分是原来“笔耕文艺评论小组”的主将,一直承续到今天。最近一期(2011年第6期)《小说评论》编委会11位编委,其中8位是原“笔耕文艺评论小组”成员。另一方面,《小说评论》发扬光大了陕西文学批评,包括“笔耕文艺评论小组”的优良传统,并且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进入全国文学批评刊物的前列,甚至可以说,在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与评论领域,具有其不可替代性。特别是在发现培养文学批评新生力量方面,可以用功不可没来评价。在陕西文学评论界,80年代的青年,今天已步入中年的文学评论家,很少没有得到《小说评论》的扶持和提携。就是从全国而言,亦有后来知名的文学批评家,或者得到了《小说评论》的大力扶持,或者就是从《小说评论》走向文学评坛的。[6]
可以看到,“笔耕组”笔耕不辍,度过了波澜壮阔的30年。翻览30年的《人民日报》和《陕西日报》,“笔耕组”批评活动报道此伏彼起,基本从无间断。“笔耕小组的活动和声名,在全国文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活跃时期,《陕西日报》逢会必报;《人民日报》文艺版详细报道过如‘1982年贾平凹创作研讨会’等主要观点;中央报刊更是重点关注。约在1984年,时任中央研究室文艺组组长的陈涌来西安考察文艺工作时,在多种场合提到并肯定了笔耕小组。”[12]415在“笔耕组”示范带动下,作家理论水平提升很快,许多作家创作评论双丰收,如路遥的《早晨从中午开始》创作谈已经成为路遥研究“不动产”;作家红柯关于文学边疆精神的创作谈被《光明日报》发表,其《敬畏苍天》文集中许多创作谈也已成为研究西部文学不可或缺的资料;贾平凹的《平凹文论集》已经脱销。启发当下批评家,只要出于公心、大道,中国特色文学批评大有作为,路就在脚下;“笔耕组”相关创新批评经验可以复制、推广,其是陕西的,更是中国当下文学批评创新宝贵的民族经验、国家经验之一。
[1]笔耕组三十年笔谈[N].陕西日报,2012-01-09(6).
[2]李继凯.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
[3]王锋.文坛恸别胡采[N].华商报,2003-09-25(1).
[4]马平川.李若冰散文的当代意义[N].光明日报,2007-02-02(11).
[5]杨乐生.关于肖云儒“对视书系”答记者问[M]//选择的尴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6]韩鲁华.“笔耕文艺评论小组”与当代文学批评[EB/OL ]. http://blog. sina. com. cn/s/blog _4d34676601012cs2.html.
[7]陈传才,周忠厚.文坛西北风过耳——“陕军东征”文学现象透视与解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8]李国平,姜广平.本刊主编答姜广平先生问[J].小说评论,2009,(1):4 -10.
[9]陈忠实.《白鹿原》创作手记(下)[N].陕西日报,2009-07-31(8).
[10]若星,等.文学重镇春潮涌[N].文化艺术报,2008-12-27(7).
[11]畅广元.神秘黑箱的窥视[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12]陕西省委宣传部,等.陕西文艺三十年[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 朱正平】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Outlet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Taking Writing Literature Research Group as the Example
SUN Xin-feng
(Chinese Department,Baoj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Baoji 721013,China)
the present Chinese literature criticism and interpretation are in the context of imitation of others.The Media Age and Editing Literature and multi-modal literature exist,but lack of deepened criticism,such as shortage of problem awareness and sober judgment,incapability to overcome stereotypes,with low spirits and poor condition.But in the fertile soil of Chinese culture the Writing Group can well avoid the shortcomings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holding to Chinese characteristic criticism route,and has been recognized and affirmed by the community author.It becomes China’s literary criticism presenting the famous brand of being awareness,which offers the thinking way for the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and sets a model for it.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predicament and outlet;Writing Group;replication;innovation
I206
A
1009—5128(2012)09—0064—07
2012—05—05
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当代文学的新乡土叙事比较研究(11XZW019);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陕西“大学作家群”现象研究(11JK0253)
孙新峰(1972—),男,陕西洛南人,宝鸡文理学院中文系教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陕西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