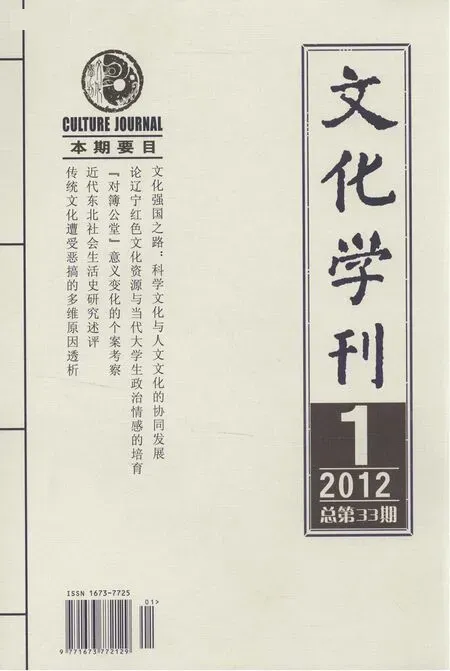重构中国文学“现代性”谱系的新声——读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
周仲强 张敏飞
曾几何时,沉溺于风花雪月的妓伶狎客,何其多情缱绻以至生死相随;游走于市井红楼的洋场才子,也曾佯装潇洒文雅风趣;穿梭于月球海底的冒险旅行,无不让人孜孜不倦心驰神往;而飘泊于江湖刀光剑影的侠客义士,却也到底难掩柔情似水儿女情长……晚清小说,恰似 “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神秘女子,究竟她的魅力何在?价值何在?启示何在?
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中,通过对以往的文学史书写进行回应和反思,苦苦追寻“被压抑的现代性”,拨开了“五四”革命与启蒙话语对晚清小说的遮蔽,挖掘并发抒新意,揭示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弊端,众声喧哗的多重线索和可能性。
一、现代与文学:穿越历史障蔽与时间迷雾
晚清小说的繁荣前人早已有所论及,阿英在其著名的《晚清小说史》开篇便彰明:“晚清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一个最繁荣的时代。”[1]而同样推崇晚清小说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的英文版于90年代中后期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与传统阐述和解析晚清小说的论调不同,作为“重写文学史”思考的一种实践,王德威的著作可以说拨开了革命与启蒙话语的重重缭绕,不仅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法进行了回应和反思,意欲重新整理和书写晚清小说及其现代性的谱系,而且在具体的考察中,作者也主要有感于“在中国叙事文学研究里,晚清小说一向不受重视”,即便在80、90年代晚清小说得到进一步研究,“仍不脱以往 ‘四大小说’(《官场现形记》、《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的窠臼;阿英、鲁迅、胡适等以‘五四’为视角的理论,依旧被奉为圭臬”。[2]因而以“现代性”为中心,重新回到世纪初小说发展的历史语境,为晚清小说重绘一个多声复义的现代性发展镜像,将晚清小说从传统古典文学的尾声提升到现代新文学的新声地位,重估之前一直都被视为只具有过渡意义的晚清小说,并且在此基础上阐明现代性并不是单线一元的发展格局,而应该有着多种展开的可能性,只有打破奉“五四”为中国现代文学圭臬的话语,真正折回近代晚清的历史语境,才能还原世纪之交中国文化和文学现代性无比壮观的涌动和喷发状态。“用晚清以来的文学和文化的现象,重新思考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以来,中国现代性流变的种种可能。 ”[3]
作者指出,晚清的现代因素与传统相比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吸收了诸多来自本土之外的发展要素,不再完全局限于古典和历史的窠臼,并且自觉而迫切地借助于西方的文化因素,在具体的发展过程中则表现出众声喧哗的多元性质,这样的论述明显有着巴赫金“复调”理论的色彩,而将“五四”标准的“厚障壁”推倒,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尝试和努力上溯到晚清,则显然受到了福柯“知识考古”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说,王德威是以后现代性的理论思维作为底子来追寻上世纪之交的现代性状况,颠覆了“五四”既定的话语规范,认为鲁迅、胡适等代表“五四”新文化阵营的文学家,主要以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为立场,来接受西方的现代思潮,力倡“为人生”的启蒙和现实关注,从而窒息了晚清小说难能可贵的丰富性,也窄化与压抑了晚清小说中彰显的多元现代性,“‘五四’作家急于切断与文学传统间的传承关系,骨子里其实以相当儒家的载道态度,接收了来自西方权威的现代性模式,视之为惟一典范,从而将已经在晚清乱象中萌芽的各种现代性式摒除于‘正统’的大门”。[4]这样的论断是否存在着将“五四”简单化和平面化的危险呢?然而事实并不仅仅停留于这个层面,不可忽视的却在于,正是 《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中对现代性发展和现代文学脉络的新的揭示,为文学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方法论的典范。袁进对此也说到:“中国文学发展到近代,好比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具有多种选择的可能,因此这也像先秦时期一样,成为中国思想史上最活跃的时期。”尽管关于历史事实与历史叙述之间的差异以及“压抑”与“被压抑”二元对立的视角为某些论者所诟病,[5]但是通过本书的整体视野和细部阐述,可以看到,作者所最终着眼的,并不仅仅在于“压抑”与“被压抑”本身,而是通过揭示和穿透以“五四”为圭臬的障蔽,拨开历史叙述与现代时间迷雾,在呈现出晚清小说所体现的多声复义的现代性图景的同时,也为文学史的认识视野与具体书写创造出多样可能性,从这个方面来说,本书是通过“拨正反乱”的手法打破文化和文学发展的单线一元格局,为现代文学的书写提供一种新的范型。
二、故事与叙述:揭示紊乱时代与交错话语
如果说前一部分王德威以现代性为旨归来重整现代中国文学谱系,揭示晚清小说的价值和启示的做法是本书一个总体理论纲领,那么接下来以题材为理路对晚清小说的分析则是详尽的细部阐述。书中第二、三、四章关于晚清小说的讨论可以说是沿用了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清代小说题材的分类,而第五章对“科幻奇谭”小说的概说和论述,不无对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以传统儒家观念出发而没有顾及的小说主题题材的一个反拨式的补充。并且在鲁迅对晚清小说考察的基础上更往前迈进一步,那就是以晚清小说的“现代性”为指归,探讨狎邪、侠义公案、丑怪谴责和科幻奇谭四类小说题材内部所包含的 “四种相互交错的话语:欲望、正义、价值、真理(知识)”,[6]并且指出这几种话语在晚清小说中已经显现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和文化发展路径的关键性标识。
狎邪小说向来为“五四”的文学规范所诟病和排斥,被视为“笔法粗糙”、品味低俗的“陈腔滥调”;但不可否认的是,狎邪小说对现代小说情爱一翼的发展有着突出的贡献,不仅继承了古典小说中的艳情和感伤的传统,而且以其深刻反映晚清特有的情、性风尚和积极吸收的外在因素,创造出了一系列全新的情感爱欲范畴。王德威在书中以陈森的《品花宝鉴》、魏子安的《花月痕》、张春帆的《九尾龟》、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曾朴的《孽海花》等晚清名噪一时的小说为例,阐述其中所表现的异性恋、同性恋等时代的性风俗,展现繁华都会的情仇色欲,揭示晚清小说中的“欲望”主题,并在此基础上指出这一类型的小说所代表的 “欲望叙事学”对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小说主题的深刻影响,其流波甚至触及了郁达夫、张爱玲等中国现代小说大家。
侠义公案小说所代表的“正义”主题同样在中国传统小说题材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晚清的同类小说所体现的“正义”却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内涵。书中以俞万春的《荡寇志》、石玉昆的《三侠五义》、文康的《儿女英雄传》、李伯元的《活地狱》为蓝本,对晚清的侠义公案小说所透露出来的时代气息和历史现实进行阐述,认为当中既显示了对皇权和法律的暧昧,在追求侠义和定夺公案的过程中所面临的错综复杂的时代处境,以及在实践公、义的具体行动中自身所倡导的精神与现实境况的相互龃龉,这都让晚清侠义公案小说所意欲表达的主题和精神经受难以逾越的危机,王德威在此也提出了一种怀疑,即在晚清那样一个不具备实现小说中所畅想和摹写的正义要素的时代,其所彰显的正义,最终会不会只是“虚张”的幻影?尽管如此,这场追求正义的想象,仍然凭借其藐视权威的勇气、扬善惩恶的正气以及许多深入人心的侠士仁人的叛逆、无私的豪气,成为世人耳熟能详的正义典范,晚清的侠义公案小说也成为了“中国现代大众文化的滥觞”。
晚期的丑怪谴责小说以嬉笑怒骂的方式,讽刺时局世事,揭示社会百态,通过丑化怪异的夸张,对政治黑暗和社会恶俗进行了尖酸无情的批判,书中以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为对象,指出其所摹写的虚拟迷幻的价值世界,以某种紊乱丑怪的笔法来展示和批判社会黑暗,并且在漫天的挖苦嘲笑中赢得市场的青睐;书中还以《官场维新记》、《糊涂世界》等小说为例,说明此类小说的喜剧、闹剧色彩,以戏谑的笔调描摹出人物和故事的荒唐;而李伯元的《文明小史》对士人阶层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批判,《市声》则揭露了一批商人、发明家和企业家的现实处境和道德选择;《市声》等丑怪谴责小说还以其浮露的“刺”锋和狂欢的嘲弄,成为了中国式的荒诞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品。尽管这往往只是无尽无休的插科打诨,但也正是这种虚无和近乎游戏似的文本运作,体现了晚清时期丑怪谴责小说本身就所具备的内在颠覆性,以及在无望社会中的自我调侃和解嘲。这种丑怪写实的风尚还影响到了张天翼、吴组缃、老舍和钱钟书等新文学家的创作。
最能体现晚清人们的想象体验和理想诉求的无疑是当时的科幻奇谭小说。无论是拥有奔雷车、参仙和乾元镜的“战争演义”《荡寇志》,还是捣乱时空,独创理想世界的《新石头记》,又或者是升天入地、畅游宇宙世界的《月球殖民地小说》和追寻未来、探索中华理想明天的《新中国未来记》,都体现了晚清科幻奇谭小说作者打破时空秩序、重理时间脉络的虚构精神和叙述技巧,在高邈的想象世界中,也体现出作者以及读者所面临的历史困境和现实诉求,在晚清特殊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也只有通过这样的突破时空的叙述策略,才能为自身所畅想的理想世界和未来国度设计出新的期待和希望。
通过对晚清狎邪小说、谴责小说、侠义公案小说以及科幻奇谭小说这四种最盛行的文类及其具体作品进行条分缕析的细致考察,作者从中抽象出了欲望、价值、正义、真理(知识)这四种交错互生的话语,指出这几种在晚清小说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话语在描绘出晚清纷繁复杂的现代性发展状况的同时,也在后来中国现代小说中得到更为深远的发展,并且作为现代性的内涵流变和叙述原型,在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谱系中体现出源头性的意义,从文学史意义上来说,可以说王德威通过这样的探索,重绘了一幅新的百年中国文学的图谱。
三、脉络与图景:追寻传统流变与叙事谱系
按照王德威的观点,在现代中国小说的发展历程中,晚清小说是具有源头意义的,这个开端鼎沸喧嚣,充满着“渴望、挑战、恐惧及困境”,后来中国现代小说之水既湍急又缓滞的流淌,有浅洼、有激流、有曲折、有回环……在或宽或窄的河流两岸,在或深或浅的河床内部,都将存留着源头的影子。袁进在《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中同样持此观点,“中国近代文学作出的选择,实际上决定了以后的文学发展,一直到现在,现当代文学碰到的问题,如文学的市场化问题,文学的雅俗问题,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作家面对各种潮流是否坚持自主意识问题,现实主义成为文学主流问题,中国文学吸收外来影响,中国文学对传统的继承与发扬问题,等等,一旦追根溯源都能追溯到近代”。[7]可以说袁进是从一个更为宏观的角度对中国近代文学发展的自身内部的变革及其对后世影响作出了论断,而晚清小说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晚清社会的短短几十年,其能量不单辐射到“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而且为中国当代小说的发展提供了某种原型式的选择。
在《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的最后一个部分,作者将触角伸及20世纪80、90年代的港台、大陆和海外的代表性小说作品,朱天文《世纪末的华丽》、李昂《迷园》、施叔青《维多利亚俱乐部》、《香港三部曲》、李碧华的《青蛇》、《霸王别姬》以及王安忆的“三恋”系列、苏童《我的帝王生涯》和贾平凹的《废都》,都明显地延续了晚清小说中所创生和繁盛的狎邪主题,其溶杂着身体、金钱、政治等因素,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新的欲望和颓废美学。“正义”的主题亦在当代小说中得以充分表现,从叶兆言、张大春、莫言等作家的作品中透露出了新的“正义”内涵,在这样一个英雄“殇逝”的时代,传统经典意义上的侠义被拆卸和重组,而种种拒绝英雄的姿态也正表现了作者借以对新的历史进行的考量和审视。丑怪谴责的强度通过新的表现手法,如黑色幽默、异形狂想等形式,在当代小说中得到进一步的加大,无论是刘震云、张洁的中长篇小说,还是余华、张大春等人的先锋探索,抑或王朔的横空出世,都以更为夸浮戏谑和怪诞乖张,以实现对秩序溃坏、价值崩坯的社会精神的思索和拷问。而《台海一九九九》、《台湾奇迹》、《浮城》、张系国《城》三部曲等作品,则延续了晚清科幻奇谭小说中对中国未来的遐想,同样通过想象和虚拟的方式,拓展出了理想国度和未来生活的疆界。
作者通过考察晚清和当代小说在主题题材方面的对话及其从中生长出来的历史现代性对接点,指出在流经近百年的现代中国文学的长河中,处于中下游位置的二十世纪末小说仍然流淌着源头——晚清小说的影子,在这种体现着深刻的历史相关性的作品题材中,似乎可以理出一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谱系。从晚清到二十世纪末期的现代中国文学,同样是“世纪末”,同样是多重现代性的复现和播散,在这里,历史被“重新讲述”,两个“世纪末”的文学现代性实现了互接和对话,那是由于晚清所绽放出来的现代性意义及其价值在历经近一个世纪之后,仍然光彩夺目,那属于晚清、属于中华民族的现代性穿越了历史的长空,重现光芒,这无疑便是王德威所企盼的现代中国文学“世纪末”之后褶褶发光的“新纪元”。
可以看出王德威不仅是要揭示众声喧哗的晚清小说创作状况,更重要的是打破“五四”权威,释放那被一元独尊的典范话语所压抑的文学谱系,打开被斥为“传统”、“前现代”的“过渡”时期的晚清历史大门,以福柯独具后现代意味的 “知识考古”的燃油,来点亮晚清小说中所体现的野火燎原式的现代性发展状况,烧断现代性单线发展的脉络,以照亮中国现代文学探索的多重线索和呈现出来的多种可能性,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 “现代”历史发展赋予某种具有史学意味的起源性的思考和揭示。但是话说回来,究竟王德威的最终目的何在?在他的想象史学思维中似乎也说得有些含混:“我试图描画现代性的播散而非其完成。”也许这将是一条永远“未完成”的道路,然而这种含混、混沌、隐而不彰和悬而未决的状态,不正是晚清小说、现代中国文学及其现代性本身的魅力所在吗?
[1]阿英.晚清小说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
[2][4][6]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情小说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4.23.
[3]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J].社会科学论坛,2006,(2).
[5]田祝,刘浪.被压抑与未被压抑的现代性——《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重新评价》质疑[J].中文自学指导,2005,(1).
[7]袁进.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