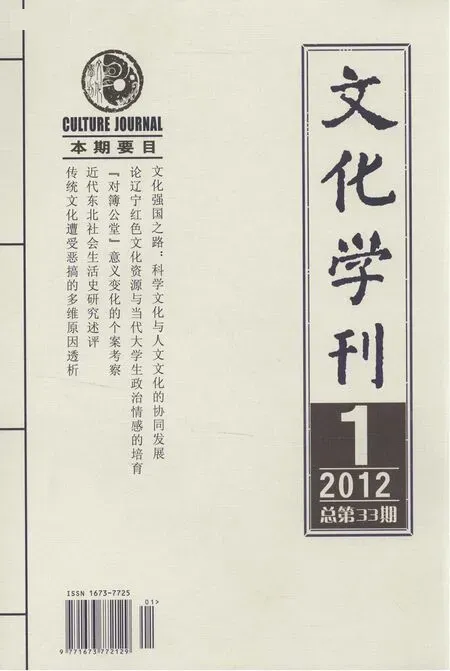何为通古斯——从比较视野看史禄国、凌纯声的通古斯人历史研究
李金花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北京 100732)
回顾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早期对于东北地区人群的研究,史禄国和凌纯声无疑是其中占有重要篇幅的两个人。前者作为俄罗斯学者,1905-1910年留学于法国巴黎大学,获得语文学博士学位,其后回国任职于俄国皇家科学院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在1912-1917年间对包括俄罗斯后贝加尔、蒙古、满洲在内的西伯利亚、远东地区被称之为“通古斯人”的人群进行了多次田野调查[1],之后因为俄国政治变革被迫滞留中国,参与到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早期进程中。后者作为中国学者,1926-1929年间同样留学于法国巴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于1930年左右前往中国东北的赫哲族进行民族志调查,成为早期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代表人物。这两位先后从法国巴黎大学毕业的人类学先驱,若从田野调查方面成果来说,则分别以《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和《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最为典型,前者是史禄国对于通古斯人调查最为详细而全面的著作,而后者则被中国人类学界奉为中国民族学史上破天荒之著作。[2]尽管史禄国的《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一书主要着重于对于被他称之为“北方通古斯”的通古斯人的社会组织的书写,而凌纯声则意图于对于赫哲族整体文化面貌的关注,但是两人却不约而同在两书之前对于通古斯人的历史起源问题有着重要篇幅的探讨,两人的不约而同并非偶然,而是有着其背后各自的原因。本文试图以两书中有关通古斯历史的讨论为桥梁,对于史、凌两人的通古斯研究作一番考察。①在此处,我将赫哲族纳入到通古斯人群当中,尽管史禄国认为称之为Goldi的人群可以视为是通古斯人的近邻,但是他亦不否认其同样有着通古斯人的来源。见史禄国:《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作者序言”,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年,124页。
一、史禄国有关通古斯人及赫哲族历史的思考
1929年史禄国的 《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一书以英文版形式在中国上海出版之后,同样亦为通古斯研究专家的I.A.Lopatin在当时的 《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有关此书的简短书评。在评论中,Lopatin说:
这本书中最引人入胜而同时又最具争议的章节是史禄国对于通古斯人的分类以及其形成及迁徙历史的分析。在通古斯人的起源问题上,存在着两种假设,其中一种为大多数学者所公认的:即将满洲视为是其发源地。然而,Drs.P.P.Schmidt和J.D.Talko-Hryncewicz这两位通古斯专家则主张蒙古西北部为其发源地的假设,Dr.Schmidt的理论极具价值,因为他将阿尔泰南部地区视为是突厥-蒙古-通古斯的共同发源之地。史禄国不同意以上两种观点,他主张最初的通古斯人是在更南部地区:如中国北部和中部,黄河及长江之间……[3]
Lopatin的这段话将史禄国对于通古斯人的历史起源及形成问题的主张鲜明地呈现出来,正是此一主张,成为了史禄国《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前三章得以形成的基础。在该书共八章的内容中,前面三章内容,分别是通古斯人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北方通古斯各集团的地理分布和分类及他们与邻族的关系、通古斯的氏族和通古斯的历史概述,后面五章则是如题目所言对于通古斯人包括氏族、家庭、婚姻、财产、社会习俗等社会组织的分析。前三章内容虽然包括有关自然环境的描述、北方通古斯地理分布现状等这些非历史的内容,然而实际上,却可以从后来史禄国对于这些材料的处理中看出,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地理分布、乃至于后五章中所谈及的氏族、社会习俗等,都成为了他论证通古斯人历史的材料的一部分,这其中甚至还不包括他所擅长的体质测量以及语言学材料的运用。纵观史禄国一生有关通古斯人的研究,其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部分①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史禄国这样出身于欧陆传统人类学学科思想熏陶和训练背景的人类学家来说,他同样对于体质、语言、考古等方面都有着深入的考察,尤其是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成为他后来在中国从事人类学研究的最为重要的田野工作,并因此写出了一系列的相关专著。对于通古斯语言研究,他同样在深谙通古斯语之时写出了有关通古斯语的专门文献。然而,就其影响来说,其对后来学者产生较大影响力的无疑是这三个方面。,社会组织研究②以其《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满族的社会组织》为代表。;萨满研究③以其《通古斯人的心理-心灵情结》(Psycho-mental Complex of the Tungus)为代表。;历史研究④以《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及文章“远东北方通古斯的迁移”为代表。。这同样可以从他在《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中所写的“序言”当中看出:
本书没有附上应有的结论,是出于以下考虑:即本书只是我的民族志学观察的一部分。如前所述,社会现象同其他文化现象有着密切关系,如果对通古斯民族志,其中包括通古斯人的思想体系和通常所谓的“宗教”,不做一般的全面论述的话,许多社会现象是不可能正确理解的。这个问题将在我的另几本书中探讨。至于通古斯人的形成及其历史,情况也是同样地,因此我决定在今后的著作中再对通古斯人的社会组织及其历史,作出一般结论。[4]
就如后来的众多学者所公认的,史禄国在上文中所说的有关结论的思考最后引申出了他首创出“ethnos”一词,开始了对于“民族”以及“民族性”等问题的思考。很明显的是,对于“ethnos”其内涵的思考,则不得不说是包含在他对于通古斯人历史、社会组织以及萨满的研究当中。
对于在西伯利亚、中国东北这片广阔地域上分布着的通古斯人来说,史禄国主张从语言学上来分成两类,北方通古斯和南方通古斯,前者以分布在后贝加尔、阿穆尔州、宾海洲以及呼伦贝尔等地方的通古斯人为代表,后者以满族为代表。前者按照其生计方式分类,又可分为饲养驯鹿的通古斯和游牧的通古斯,而后者则普遍以农业为主。夹杂在俄罗斯、蒙古、布里亚特、汉族之间的通古斯人,不管是生计方式、语言、体质还是文化特征,都呈现出纷繁多样的局面,从史禄国的观点看来,这种复杂多样性一方面是通古斯人为了适应自然环境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适应民族间外部关系的需要。正是此两种环境的影响,才使得通古斯人出现了二十世纪初期史禄国民族志调查时所反映出来的特征。
要如何理解所谓的通古斯人,也即他所说的“ethnos”,则需要建立在他的民族志调查基础之上。受俄罗斯、蒙古、汉三大强势势力挤压下的通古斯人,其生计方式逐渐在抛弃传统的驯鹿饲养,而纳入别的生计模式当中,其语言及风俗,亦在不断地忘旧纳新当中,乃至于其活动的地理范围,也日渐缩小。正是这一不断变化的通古斯人,才成为了史禄国所说的 “ethnos”:我在本书中所使用的“民族单位”一词,是指这样一种单位,在这个单位中民族志要素的变化过程及其向下一代的传递和生物学的过程正在进行。这些单位永远处于变化的过程中……[5]正是基于此一有关“ethnos”的论述,他对于通古斯人的历史所作的一番考察,将其重心放置在通古斯人的迁徙当中。由此而来的起源地的讨论,他反驳了施密特的北蒙古起源说和另外一种满洲起源说。首先,他反对北蒙古起源说,因为从他对于通古斯人的民族志调查中可以表明北方通古斯是起源于南方。这包括通古斯人的服饰不适宜西伯利亚寒冷气候、身体上的如眼睛对于雪地的不适应、以及心理上的如通古斯人不熟悉海洋。[6]其次,他反对满洲起源说,因为满洲地方气候寒冷、地域狭小,不适宜民族单位的形成。而只有华北和华中的低地和高原所形成的谷地、即黄河和长江的中游和部分下游地区,有着适宜的气候和宽广的地域。随后是中国汉人从西北部向黄河谷地的扩展,使得早期通古斯人开始向南或向北迁移。这在体质人类学上能够得到证据:北方通古斯人最普遍的伽玛型同样在华东、华北、甚至是华南能够看到。向北的通古斯人一方面与满洲的古亚细亚人相遇,发生融合,同时另一部分人继续向北迁移,直至西伯利亚。其后,通古斯人又发生了四次迁徙浪潮,史禄国以调查到的通古斯人的氏族名称以及传说故事为依据,对此四次迁徙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由此可以看出,史禄国心中所勾画的 “通古斯”,并非是一个静态的民族体,而是一个动态的变化体,在不断的外部环境的变化当中,其社会内部的社会组织、宗教心理、风俗习惯等不断改变以得以协调,达到平衡,似乎可以说,二十世纪上半期人类学界从拉德克利夫-布朗等结构功能论到后来利奇等人所不断完善的历史视野中的结构功能的努力早已经在史禄国的通古斯人研究中实现。史禄国的历史研究一方面应对了传统汉学研究中对于历史问题的关怀,更重要的是它成为了解释何谓“ethnos”的一部分。
如果说《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仍然是史禄国对于通古斯人社会组织关心的一个作品,那么,有关历史问题的论述他在另一篇长文中则表达得更为清楚。早在《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一书出版之前的1926年,史禄国在《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 会 杂 志 》 (theJournalof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发表了《远东北方通古斯的迁移》(Norther Tungus Migration in the Far East)一文,该文副标题是“果尔德和他们的民族关系”(GoldiandTheirEthnical Affinities),这里所说的“果尔德”,也即是凌纯声所调查的赫哲族。史禄国在文章前言中谈及,他的此篇文章本是为了回应Lopatin有关果尔德人的民族志研究而写,但是文章写成后却不仅仅成为了回应Lopatin的文章,反倒成为史禄国对于果尔德人乃至通古斯人历史研究思想的完整表达。[7]
Goldi在汉人的称呼中,经常被称之为“鱼皮鞑子”,而他们自称为“浩占”或“浩津”,在其邻近的比拉尔千及满族人中,他们被称呼为“赫哲”。史禄国认为虽然赫哲人与满族人这一南方通古斯有着亲密的关系,然而,他们的起源并不同,并且赫哲语言以及文化上都呈现出北方通古斯的一些特征。赫哲人主要聚集于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三大区域,因为地域的差异,其各自也呈现出不同的民族志特征。黑龙江流域的赫哲人受到了古亚细亚人、北方通古斯以及蒙古人的影响,乌苏里江流域的赫哲人主要受到了汉人的影响,松花江流域的赫哲人被认为是最具典型性的,甚至被认为是满族人的发源地。[8]尽管从文章标题看来其目的在于讨论北方通古斯人的迁移问题,然而,全篇却并未着眼于对历史迁移问题的回顾,史禄国更倾向于从赫哲人的民族志调查的材料中去比较在夹杂在北方通古斯、南方通古斯之间的赫哲族是怎样的民族志特征。他从赫哲人的生计方式——渔猎、善于用狗、主食为鱼肉、捕鱼方法、鱼皮服饰、定居生活、雪橇、氏族组织、婚俗、生育习俗、萨满、丧葬仪式等诸多方面,与北方通古斯人及满族人相比较,描绘一幅赫哲人与其他人群之间的文化关系图,与此同时,他还考察了赫哲人的语言、体质方面,从这些民族志特征,史禄国归纳出了北方通古斯人的四次迁徙波,在四次迁徙波之下的赫哲人,原初早期是北方的通古斯人群,甚至还饲养驯鹿,自称为鄂温克,其后受汉族以及俄罗斯人的强烈影响,到现今他们成为了包含汉、俄罗斯等文化特征在内的人群。
从比较起源于同一古老民族的不同人群的民族志特征,到根据这一比较来看民族志特征的地域分布,从而进行历史迁移过程的回溯,这一带有文化传播论倾向的解释在后来被一些学者所批评。史禄国的通古斯人的历史研究是从民族志调查为起点,去寻找历史的证据,而在历史证据之后,再思考研究对象本身的问题,尽管为后人所批评,但是不容置疑的是,他的这种大区域的视角无疑为我们今天的人类学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反思。[9]
二、凌纯声有关通古斯人及赫哲族历史的思考
相较于史禄国对于整个西伯利亚、远东地区以及中国东北地区的通古斯人人群的整体关注,凌纯声的通古斯人研究则集中于居住在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这一人群之上。对于赫哲族人的研究,他主要分为几个部分:历史;包括物质、精神、家庭、社会四方面在内的赫哲文化;语言以及传说故事。历史部分作为他开篇之章节,无疑有着重要的地位。
在《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的历史部分,凌纯声主要辨析了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通古斯非东胡民族,通古斯为东夷的一种,东北各民族名称的起源及其转变,赫哲与Goldi名称的来源,中国文献中记载的赫哲,现代的赫哲族及其地理的分布。凌纯声对于东北民族及赫哲族历史的考察,主要基于中国史书之记载。他并不关心如史禄国所作的南北通古斯之类的区分,他更在意的是:曾经在中国东北部存在过、在中国史籍当中记载着的各民族,到底应该归入哪个集团、或者说哪类人群当中。中国史籍当中曾明确区分了东夷、东胡的名称,他通过梳理史籍当中出现的被称为通古斯的各集团,认为通古斯人应该是“东夷”,而并非是如欧洲汉学家以及中国一些史学家所认为的 “东胡”,因为东胡应该与匈奴同种,是不吃猪肉的民族。而在中国东北地区,曾存在的古老人群有三类:古亚洲人、通古斯人、东胡人。尽管通古斯人为中国史籍当中的东夷人,但东夷人并不尽然全是通古斯人。凌纯声指出从古代到汉魏时期,中国东北地区的东夷应该是古亚洲族,而到隋唐之后,其主要民族才为通古斯人。有关通古斯人的起源,他亦提及了现存的三种说法,即满洲地起源说,中国北方起源说,蒙古起源说。他驳斥了史禄国的中国起源说,认为其分析并不可靠,更加认为从史禄国的研究中所推演出来的通古斯人或许和中国南方的部分人群如苗瑶在文化上有相似之处错误百出,不可相信。尽管他没有明确提出通古斯起源地在哪,但他推测认为通古斯人不可能是从中国本土向北迁徙而行,他认为通古斯人应该是从北部地区向南迁移的,这些北部地区可能包括史禄国所谈到的驯鹿通古斯所居住的后贝加尔地区,或者是蒙古北部地区。他的理由有三:其一是中国东北部及满洲地区已经有中国古籍上所记载的古亚洲族居住,其二是后来位于满洲地区的女真亦是北方而来,其三是北通古斯人的迁移方向同样是由北方而来。[10]有关赫哲族人历史的分析,凌纯声依据中国古籍文献梳理了从隋唐时期黑水靺鞨历经辽金以及明清时期的演变过程,很明显可以看出,他的这一做法就是众多后来学者所说带有“国族主义”观念色彩,将赫哲族纳入到中华民族的谱系当中,以此给这一人群以定位。而这一思想同样影响了他在对赫哲族其他方面研究时的取向。尽管《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的大量篇幅都是在对于他所调查到的赫哲族人的现状进行描述,然而,不然看出,在描述之后,他同样会将之与中国古籍当中记载的其他风俗相比较,尤其关注与汉人之间的异同,如赫哲人的饮酒方法,就与中国古代的饮酒法相似等。[11]尽管他不同意史禄国有关通古斯人起源中国本部说,但是他也借用了很多史禄国所谈及的通古斯人在中国东北受古亚洲人之影响的观点,如赫哲族的夏帽与日本人、汉人甚至马来群岛人的相似,认为是起源于古亚洲族,并受其影响。[12]
如果将凌纯声的赫哲族研究纳入到中国早期民族学、人类学的源流当中去思考,可以看到就如后人对他的评论一样,他的赫哲族研究是当时中国民族学研究当中“中央研究院”的“历史学派”的代表。[13]而这一流派后来直接进入台湾,影响了台湾很长一段时间内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
有关凌纯声的民族学与历史学的结合问题,我们一方面可以追溯到凌纯声本身在法国所受的欧陆传统的人类学的训练,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将之与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学术流派联系起来。正如诸多台湾学者早已关注[14],早期作为中国民族学南派代表的中央研究院,形成了用民族学理论与方法来运用历史的文献与材料以试图解决中国民族文化历史难题的倾向。[15]凌纯声即是其中重要代表之一,他融合了法国人类学莫斯以来的注重民族志材料细节的特征以及中央研究院关注历史以构建中华民族这一国族的目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就是建立在他自身扎实的田野调查以及蔡元培、傅斯年、李济等人的指导之下[16],而此三人正是当时中国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他们关注的正是如何在这些学科学术研究之下构建中华民族的问题。在此之下,对于凌纯声来说,“何为通古斯”的问题则迎刃而解:对于正在建构中的中华民族来说,作为通古斯人的赫哲人正是其中之一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凌纯声在其后期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当中,似乎转向了一种更为跨区域的尤其是对环太平洋文化的关注之上。他试图利用各地各人群的文化特质来证明其中国起源问题。他的这一倾向遭到了后人的诟病,认为是带有国族主义及传播论色彩的民族学研究。[17]然而,应该看到,凌纯声的环太平洋文化的研究已经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时的赫哲族研究存在差异,如果说后者有着国族主义的视角,那么前者更应该是一种文明的视野。他也似乎偏向了一种更为类似于史禄国所研究的路径。尽管史禄国在其后期主要侧重于从体质人类学上来解决这一问题,但两人却都是基于人群的迁移传播观点之上,试图将起源、族群文化以及历史过程联系起来,进行一种跨区域的研究,尽管凌纯声的落脚点在文明,而史禄国落脚点在他所说的“ethnos”。
时至今日,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界研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重新开始,早已经抛弃了如史禄国和凌纯声似的研究路径。尤其是结构主义的兴起,对历史问题的关注也开始从传统的史学方式的探讨走向结构与历史这样的主题,类如史禄国的“ethnos”的关注其重要性放置在族群、民族等词汇之上,或者与国族相关,或者与单个视为“文化孤岛”的族群有关,其已经大大偏离史禄国关注的意义。而跨区域的研究,则更加绝迹,社区研究方法已经深入中国人类学界。“何为通古斯”或者“何为赫哲族”的问题则已经失去了史、凌两人曾经赋予他们的视角和意义,或者说,凌纯声式的国族意义仍然在延续,然而却已转变得更为狭隘。
[1][4][5][6]史禄国.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1-11.8-9.11.223-224.
[2][14][15]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169.145-160.153.
[3]罗帕廷(I.A.Lopatin).书评,美国人类学家(33),1931.637-639.
[7][8]史禄国.远东北方通古斯的迁移[J].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杂志,1926,(57).123-183.
[9]李金花.从史禄国的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看人类学[J].西北民族研究,2010,(1).
[10][11][12][16]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M].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43-44.71.74.1.
[13]杜正胜.学术史与方法学的省思[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0.285-316.
[17]黄应贵.人类学与历史研究的结合:以台湾南岛民族研究为例[J].台大文史哲学报,2003,(59).
——“第十二届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负责人联席会议”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