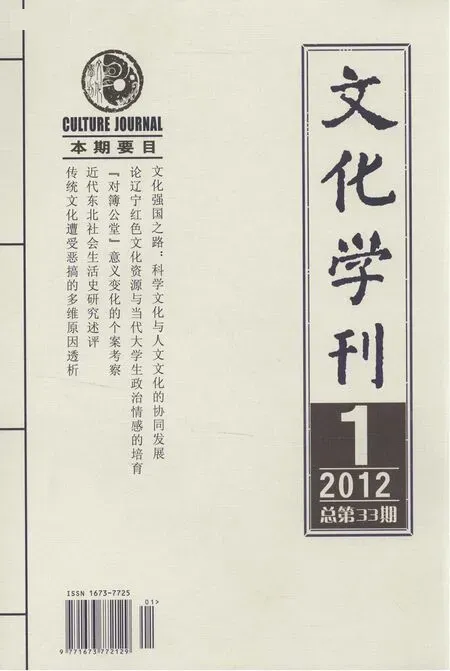凌纯声的赫哲族研究及其影响
姬广绪
(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1)
1930年春夏之际,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专任研究员凌纯声先生 (以下简称凌氏)带领商承祚先生前往今吉林省境内的松花江下游,对赫哲族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田野调查。这是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界意义相当深远的一次科学田野调查,被视为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对其意义和价值,学者们多从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角度论析,试图从现代中国提倡注重实地调查研究的学术背景来审视凌氏的这次田野调查。笔者认为,20世纪30年代开展的少数民族调查也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在当时复杂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下开展的。因此,本文首先将试图剖析此次凌氏赫哲族调查的社会背景以及此次调查学术研究之外的政治用意,同时,通过分析凌氏的赫哲族研究所体现的“中心”与“周边”的研究视角,来探讨此种理论倾向对于民族文化研究的意义。
一
无论是出于政治的考量还是出于文化研究的需要,对边疆民族考察在20世纪30年代是十分紧要且急迫的事。其缘由须从19世纪末帝国主义在全球加强资源争夺说起。当时支持帝国主义全球扩张的理论基础是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与民族国家(Nation State)概念。 社会达尔文主义将生物学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法则运用到人类社会演化中。民族(或国族)被视为一个个的生物体,演化程度高的民族被认为有掌握运用全球资源的权力。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列强争夺与瓜分中国及其周边地区资源的情况下,清末民初的中国知识分子逐渐从只求船坚炮利的自强运动中有了觉醒,感慨外人有“民族”能团结对外而中国则无,于是,他们开始呼吁并以行动筹建自己的民族国家。由于历史上汉与非汉在血缘、文化与历史记忆上有许多交汇,清帝国版图又及于蒙、藏、满洲与西南边疆,因此,在全球各国争夺土地与自然资源的背景下,此国家内的 “民族”包括清帝国统治下所有的汉与非汉人群逐渐成为当时许多中国政界与学界领袖们的共识。[1]东北研究的凸显与19世纪末期的中日关系格局的转变有着密切的关系,中日甲午海战改变了中日之间的政治格局,日本这个“东夷小国”竟然打败了“天朝大国”,这对中国人来说,惨败于日本比惨败于西方,所受的耻辱刺激更大、更沉重。1904年的日俄战争,日本再度打败另一个强大的帝国,其结果是韩国成为日本的“保护国”,日本确立其在东北的优越地位,开始了对东北的殖民。[2]“大陆政策”的成功实践也让日本的学术界大受鼓舞,相关的研究与论述逐渐增多。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教授矢野仁一自1920年代起,发表一系列“满蒙论”著作,强调所谓的“满蒙”地域之“特殊性”主张,即“满蒙非支那本来之领土论”。中国史学界以傅斯年为首的一批学者在国难当前,民族危亡之际,则提出“书生何以报国?”的问题对抗日本的“满蒙说”。[3]傅斯年在其撰写的《东北史纲》的前言部分说:
“中国之有东北问题数十年矣。欧战以前,日俄角逐,而我为鱼肉。俄国革命以后,在北京成立《中俄协定》,俄事交一面目,而日人之侵暴愈张。所谓‘大陆政策’,‘满蒙生命线’者,皆向我施其露骨的进攻之口号,而国人之酣梦如故也。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遂有沈阳之变。……国人不尽无耻之人,中国即非必亡之国!然而前途之斗争无限,知识之需要实殷,持东北事以问国人,每多不知其蕴,岂仅斯文之寡陋,亦大有系于国是者焉。吾等明知东北史事所关系于现局者远不逮经济政治之什一,然吾等皆仅有兴会于史学之人,亦但求尽其所能而已。己所不能,人其舍诸?此吾等写此编之第一动机也。”[4]
中国著名的东北史学家金毓黻在其撰写的《东北通史》的引言中表现出了同傅氏类似的学术目的,他说:“溯自逊清之际,国人怵于外患日亟,多喜谈边疆地理,……今日有一奇异之现象,即研究东北史之重心,不在吾国,而在日本,是也。姑无论其用意若何,所述有无牵强附会,而其搜材之富,立说之繁,著书之多,亦足令人惊叹。……以乙国人,叙甲国事,其观察之不密,判断之不公,本不待论。重以牵强附会,别有用意,入主出奴,积非成是,世界学者读之,应作如何感想。是其影响之钜,隐患之深,岂待今日而后见。由此吾国向无此类精详之专书,可供世界学者之考览,而国人忽略史事,研究不早,亦其一端也。”他同当时的傅斯年等人一样,怀揣着同样的忧国爱国之心开始致力于东北地方史的研究。他的目的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很简单,就是要“为主人者,自计其室中之藏,土田之籍,马牛蕃息之数。”以防“邻人或素昧平生之士,登其庭入其室,开其箧缄,一一而探索之,分类而晰载之,细大不捐,如数家珍,知其家之败可立待,且将辇其所藏以入于他人也。”[5]
傅氏同金氏之东北研究,字里行间都洋溢着斗士的风采,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爱国救亡意识。特别是中华民族的国土意识、民族意识、边疆意识和主权意识等,经过总结、宣传而不断普及和升华,鼓舞和激励了国人的斗争热情,顾颉刚将这些边疆史地研究称为“救国图存之学”。[6]
在边疆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边疆的稳定与民族关系的和谐成为20世纪30年代政治问题中一个重要的变量。由于边疆危机的加深,我国的学术界和政界对边疆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和整体的观念,部分的学术界爱国知识分子意识到:“强邻肆虐,侵略不已,同人谋以沿革地理之研究,裨补民族复光之工作,俾尽书生报国之志。”于是形成了当时边疆史地研究的热潮。
二
东北史撰写的热潮为当时民族学的东北民族研究提供了关注的目标,而以蔡元培为领导的中央研究院热心于提倡民族学的研究,在社会科学研究所中成立民族学组。当时中央研究院的学术风气是极力提倡实地搜集科学资料,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创刊号提到:“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明显了”。凌氏就是在蔡元培先生和社科所陶孟和先生的鼓励之下,到东北进行赫哲族的调查并撰写出了《黑龙江下游的赫哲族》。凌氏的松花江赫哲族的研究,连同当时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调查,如广西瑶族、台湾少数民族、湘西苗族等民族学调查揭开了中国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大幕。蔡元培积极组织民族学组展开的调查也是我国最早的一批关于少数民族情况的调查报告。
凌氏在法国留学师从莫斯,受到了良好的民族学训练。而适逢凌氏归国加盟中央研究院之时,全国知识界大行“科学”研究之风,傅斯年曾在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年年度报告书说:“中央研究院设置之意义,本为发达近代科学,非为提倡固有学术。如以历史语言之学,承固有之遗训,不欲新其工具,益其观念,以成为与自然科学同列之事业,即不应于中央研究院中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使之与天文地质物理化学等同伦。今者决意设置,正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此虽旧域,其命维新。”另外,在专业内部,中央研究院的民族学研究受到了当时中国人类学南派——“历史学派”的深刻影响,这让凌氏自开始民族研究以来一直秉持着“科学”研究“历史”的学术理念。在凌氏对赫哲族展开民族调查时,他运用了从老师莫斯那里习得的一套文明理论的框架,注重将文化间技术和知识的相互借用视为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我们可以从其民族志中发现他对于赫哲族文化中物质、精神、语言等方面的跨文化采借予以了充分的重视以及详细的阐述。凌氏的此种对待历史的科学态度使得其当时的赫哲族调查及其民族志《黑龙江下游的赫哲族》被李亦园称为“科学民族志”的开创者,“同时也是自 1922年 Malinowski出版Argonauts of Western Pacific之后至1935年间,全球文化人类学家致力于基本民族志资料搜集与著述期中,最重要的民族志书之一。”[7]
三
凌纯声的赫哲族调查是以专题民族志 《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的形式于1934年出版的。凌氏认为,民族学由描述的和比较的组成,描述的民族学可定义为“民族志”,而比较的民族学可以就称为“民族学”。就此而言他在“前言”中说自己的研究属于民族志的范畴。全书由3卷组成(图像卷、卷一和卷二),一共有333幅图片和694页。全书被分为4个部分:第一部分,东北的古代民族与赫哲族;第二部分,赫哲人的文化;第三部分,赫哲人的语言;第四部分:赫哲人的故事。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开始反思之前的田野调查,反思民族志写作中研究者与被调查对象间的互为主体性的问题,关注到了“人”在民族研究或族群研究中的存在感以及自我描述的重要性的话,如果将此种反思的视域投放到凌氏的赫哲族调查及其民族志中时,那么或许我们可以提问在当时的政治背景和历史语境中,凌氏是如何来“安排”他所研究的赫哲族人,他是如何处理赫哲族人同周边的族群的关系的?
凌氏在开篇第一部分 “东北的古代民族与赫哲族”中首先廓清了通古斯非东胡而东夷之一种的族源,而后又考察了东北各民族名称的起源及其转变,确定了赫哲族名称由“窝集”转变而来,但学术界对于这个特定的文化群体该如何称呼,争议颇多,凌氏认为Goldi一词已成为科学上的名称,然此词“远不如‘赫哲’的意义来得正确,可以代表黑龙江、松花江及乌苏里江所有的赫哲族,并且他们都以此自称。”[8]紧接着,凌氏很巧妙地以中国文献中记载的赫哲族为线索追溯了赫哲族从隋唐时期起在历代文献中的出现,从一个侧面标示出赫哲族自古就是生活在东北地区的一个民族,凸显了凌氏著撰此书的政治初衷——东北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虽強调“文化是人类应付生活环境而创造的文物和制度”[9],但全书描写物质、精神、家庭、社会四方面的描述,卻无法让人明确知道赫哲族的文化是在适应怎么样的生活环境下创造出來的。而凌氏似乎只关注如何利用该族资料解决中国上古史的宗教起源问题,这是一种“礼失求诸野”的态度与作法,将人类学、民族学所研究的“原始民族”,视为上古社会文化的“遗存”,而为印证及了解上古不解之谜的证据。而这种“溯源研究”及其背后的传播或演化论的学术典范,影响了近五十年来有关中国西南民族史的研究,使得描述异族的目的,往往是为了界定华夏民族自身的认同,而充滿了汉文化中心主义的观点。
综观全书,凌氏试图将赫哲族的族源追溯过程置放于一个更大的中国历史语境中,将赫哲族拉进了中国历史的长河,其中不免让读者心生赫哲族这个边疆民族在凌氏的论证下被纳入到了中国历史的“中心”上来,“从周边看中国文化”①“从周边看汉人的社会与文化”是已故的王崧兴先生的构想,但还未来得及实现先生就早逝了,之后人类学界的黄应贵、何翠萍、麻国庆等人均对此理论范式做出过细致的讨论,并有相关论文集出版。的理论企图似乎更加明显。
笔者认为,凌氏赫哲族的研究中对于“中心”与“周边”关系理论的建构, 主要是从文化的层面进行探讨,即关注赫哲族与汉及其周边民族的文化互动,以及作为汉族主流价值观的儒家文化对赫哲族的影响和渗入,这种理论建构的企图在其整部民族志中有很多的体现。在论述到赫哲族人的物质、家庭及社会生活的章节时,凌氏不止一次地提到赫哲族的文化与周边满蒙文化之间的借用现象,以及汉文化对于赫哲族文化的影响。例如,关于赫哲族的饮食中,凌氏说:“现代赫哲人煮物都用铁锅,在家里用的锅是在一方灶上加上一铁锅,与汉人无异。”[10]在论述到赫哲人的服饰时,凌氏又说:“赫哲人自与汉满俄诸民族接触后,即有面部输入代替鱼皮衣料。”[11]在论及到赫哲人的艺术时,凌氏说:“Laufer氏研究的结论是,在黑龙江流域诸民族间流行的图案艺术起源于中国,这句话我们可以相信无疑。”[12]在赫哲人的科学观方面,赫哲人“因与汉人接触,大都已习用中国历,他们对于天象的观察,知有七星(或称吉星),九星的分别。”[13]在精神生活的章节,任何在中国境内有类似资料的文献,又是无论古今,无论东南西北地域上的差距,都会被列入讨论或被引用、比较。[14]从凌氏的整部民族志我们能够比较清楚地把握其用意,他不单纯是要用三个月的调查所得材料撰写一部关于赫哲人的民族志,而是要将其更加富有挑战性的理论框架——从周边看中国汉人社会的文化——在赫哲人的群体上进行试验。同时从凌氏的此种“周边”与“中心”的理论框架中,笔者感受到更多的是他希望通过赫哲族这个周边文化与汉文化的互动及千丝万缕的联系来紧扣其研究当下的政治主题——东北历史上即为中国之一部分,进而对于日本的“满蒙论”予以文化驳斥。
四
凌氏的此种“从周边看中国社会的文化”的理论框架不仅体现在赫哲族的研究中,在其赴台后的研究中仍然清晰可见。在关于崖葬及犬祭的研究中,凌氏更是将比较的视野扩展至离开中国文化中心区更远的东南亚地区。用一种“礼失而求诸野”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化。
凌氏以后的学者,例如,王崧兴等人借鉴、吸收并发展了他的这套方法论,系统提出一套广泛应用于民族学、人类学中的研究少数民族的 “中心”和“周边”的理论图式。这些后凌氏时代的学者认为“中心”与“周边”这两个概念是互为建构的,是既对立又统一的,由此二者的界限也是历史动态的。
在人类学界,如台湾学者王明珂所著《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王崧兴的《龟山岛:汉人渔村社会之研究》、黄应贵和叶春荣主编的《从周边看汉人的社会与文化》以及日本学者末成道男主编的《中心和周边——人类学的田野视角》等等都运用“中心”与“周边”的理论图式对汉人社会进行文化研究。虽然这些学者都是在这一对概念上做文章,运用中心周边的方法来对各自的研究进行阐释,但是他们有各自对这对概念不同的理解。举例来说,王明珂在他的《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将族群边界的形成界定为是一个历史动态的不断演变的过程,他在书中所运用“中心”与“周边”的概念,在论述中国人的“族群内涵”时,采用了通过“族群边缘”的形成与变迁来解释“什么是中国人”。他用了一个比喻:“当我们在一张纸上画一个圆形时,事实上是它的 ‘边缘’让他看起来像一个圆形”。[15]我们从王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注重通过群对外的异己感所达到的“排斥”来勾勒出族群间的边缘,从而进一步完成对内的基本情感认同。而黄应贵在文集的前言中所论述的“中心”和“周边”的概念旨在通过周边族群的研究来完成对中心族群——汉族的观照,形成一种周边看中心的反思性效果,以达到一种类似儒家所谓“礼失而求诸于野”的文化审视。王崧兴的 “周边”概念并不局限于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 事实上涵盖了中国的台湾、香港以及日本、韩国、越南、冲绳等周边国家和地区。他特别强调,必须从汉人周围或汉人社会内部与汉民族有所接触和互动的异族之观点,来看汉民族的社会与文化。这一理念,对于更清楚地认识多元一体社会中的汉族,有着积极的意义。[16]
显然这些学者在研究民族文化中使用“周边”与“中心”这对概念时与凌氏相比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已经将此种“周边”与“中心”的话语表述转换为一套具有范式意义的方法论。“从周边看中心”的视角有利于东北文化研究者清楚地把握东北地区的民族文化在中华民族整体的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地位,这对于重新建立东北区域研究的学术范式都必将产生及其重要的学术意义。
此种研究的伦理观成为了当时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的主流,然而也就是在这条定位汉文化中心地位的路上,凌氏变得越来越民族中心主义。他坚持文化传播论,甚至认为环太平洋各民族的文化都起源于中国。凌氏此种做法和论断在当时虽能极大地满足国人的自尊心,但是却陷入了传播论的窠臼,反映出了其强烈的民族中心主义思想。
同时如果我们跳脱出凌氏调查的历史时代,用反思民族志的视角重新审视当时被提倡的 “科学”研究“历史”之范式,我们不难发现到凌氏当时所坚持的“纯粹客观史学”在运用到其赫哲族的调查中以及最终展现于其民族志中时所表现出的“文化代言人”特点。在凌氏的赫哲族调查及写作中,他以自己做认定的所谓科学的“客观标准”来定义赫哲族,而赫哲人的主观看法则完全被忽视,整本书中赫哲人始终处于失语的境地,无任何发声的机会,这样的民族志写作方式与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类学所提倡的反思型民族志中强调的民族志写作中调查者与调查对象之间的 “互为主体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这样一种民族研究的指导方法和民族志的写作方式影响着中国乃至台湾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早期发展,同时也成为后期此二学科方法论反思的重点。
[1]王明珂.历史变迁的微观过程——一个近代边疆民族考察的例子[N].南方都市报,2011-6-26.
[2][3][5]叶碧苓.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史学界对日本‘满蒙论’之驳斥——以<东北史纲>第一卷为中心之探讨 [J].国使馆学术集刊,2006,(11):108.105.2.
[4]欧阳哲生.傅斯年全集·第二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374.
[6]王海文.俾尽书生报国之志——追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边疆史地研究热[J].中国民族报,2009,(7).
[7]李亦园.人类的视野[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413.
[8][9][10][11][12][13]凌纯声.黑龙江下游的赫哲族[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51.63.65.72.197.199.
[14]徐正光,黄应贵.人类学在台湾:回顾与展望[M].台北:民族学研究所,1999.370.
[15]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3.
[16]麻国庆.作为方法的华南:中心和周边的时空转换[J].思想战线,2006,(4):2.
——“第十二届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负责人联席会议”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