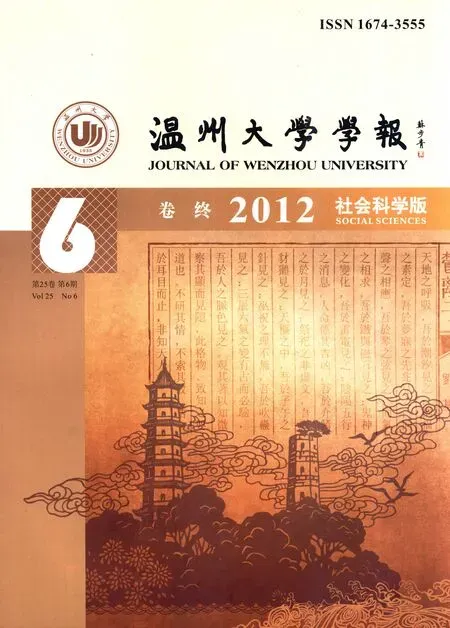元叙述的叙述功能
王正中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元叙述的叙述功能
王正中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元叙述是一种叙述策略。首先,它作为一种元语言必然具有元语言的某些功能。其次,元叙述手法无疑与正常叙述大异其趣,从而造成陌生化效果。第三,这种手法的采用,可以达到韦伯所说的“除魅”的效果,即去除文学魅力,同时,它还敞开了文本当中的意识形态。
元叙述;元小说;陌生化;意识形态
元叙述(metanarrative),这一概念最初是由热奈特于1972年在《叙事话语》①参见: 热拉尔•热奈特. 叙事话语[M]. 王文融,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中分析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②参见: 马塞尔•普鲁斯特. 追忆似水年华[M]. 徐和瑾,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0.时提出,他认为“元语言是一种在其中谈另一种语言的语言,所以元叙事应该是在其中讲述第二叙事的第一叙事”[1]。利奥塔于1979在《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③参见: Lyotard J F. La Condition Postmoderne: Rapport sur le Savoir [M]. Paris: Les Editions de Minuit, 1979.中提出了后现代的状况便是“元叙事的危机”。利奥塔所谓的元叙事是一种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它是知识建立的条件,而在后现代社会这种宏大叙事已不再可能,也就是热奈特所说的“第一叙事”出现了危机。因此,利奥塔所强调的元叙事是从其性质上而言的。利奥塔的元叙事与热奈特以及后来普林斯的元叙述的侧重点不同。1987年普林斯在其编著的《叙事学辞典》中对元叙述做了叙事学层面的解释,他认为“关于叙述,描绘叙述。元叙述是以叙述作为叙述的主题”[2]。本文主要采用普林斯的元叙述观点,认为元叙述是叙述的叙述,是在叙述过程之中暴露叙述自身的一种叙述手法。这种暴露自身的元叙述在文学作品中具体起到了以下功能。
一、类元语言功能
元叙述在很多方面与元语言具有共同性,在功能上也不例外。例如,元语言的使用可以导致正常语言的中断,元叙述的使用会使得正常的叙述出现中断,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分章采用了元叙述的这一特点。以下主要从元语言出发分析元叙述的两大功能,即解释补充功能和调节叙述节律功能。
(一)解释功能
元叙述的解释功能与元语言类似,因此,我们先从雅各布逊的元语言理论着手。雅各布逊对于元语言的论述仅有一段话,他说:“当说话者和受话者需要检查他们是否在使用同一代码时,它就扮演着元语言功能(例如,注释)。”[3]这里雅各布逊便指出了元语言的检查功能。它所起到的作用是检查交流双方是否共同享有或理解代码,以便使交流顺利进行。
与此类似,元叙述在文学作品也常起到这种解释补充的作用。格兰特•普林斯在其文章中也说:“但它们最显著、最重要的功能很可能是组织和解释功能。”[4]65与语言的交流沟通模式类似,在叙事文本中,也是一种沟通模式,查特曼在其《故事与话语》中曾给出了叙事交流图,“真实的作者……隐含的作者-(叙述者)-(叙述接受者)-隐含的读者……真实的读者。”[5]真实作者与真实读者身处文本之外,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则分别是作者和读者的化身,其实在文本之中就只有叙述者和叙述接受者才属于叙述层面的,在文本之中也就是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交流。这样,为了叙述者与叙述接受之间交流的顺利进行,便需要对其交流所凭借的代码进行检查,代码一致则交流顺利进行,代码不一致则交流受阻,需对其进行进一步的解释。如此,元叙述在文本中便起到了一种解释补充的作用,即“元叙述部分地展示了一个文本怎样被理解,它应该怎么被理解,它想要如何被理解”[4]65。
在文本中常见的元叙述,多数起到了这种解释补充的作用。例如,马原的《虚构》中的一句话:“细心的读者不会不发现我用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汉语词汇,可能。我想这一部分读者也许不会发现我为什么没用另外一个汉语动词,发生。我在别人用发生的位置上,用了一个单音汉语词,有。”[6]这便是叙述者对叙述语言作出的解释,即他为什么用了“可能”,而不是用了另外一个词“发生”,他是为了说明他所说的故事不一定是真实发生过的,是可能发生过,也可能是虚构的。
(二)调节叙述节奏
元叙述作品的特征之一便是叙述中断,也即故事所指滑向叙事能指并达到重合,而造成故事的断裂,也正因为这种断裂使得元叙述成为作家调节叙述节奏的一种手段。卡尔维诺把这种叙述中断称为:“离题”或“插叙”,他说:“劳伦斯•斯特恩的伟大发明便是他利用离题这一手法创作了一部小说,成为狄德罗效法的典范。离题或插叙,是推迟写结尾的一种策略,是在作品内部拖延时间,不停地进行躲避。”[7]358那么斯特恩是在躲避什么呢?卡尔维诺引用意大利作家卡尔洛•莱维话说“当然是躲避死亡”。而有趣的是作为元小说作家的卡尔维诺却说:“我并不崇尚插叙,也可以说我喜爱直线,希望直线能无限延长,好让读者捕捉不到我。”[7]359但不管卡尔维诺是否喜欢“插叙”或斯特恩是否喜欢“直线”,他们都是在尽力避免让读者看到故事结束。他们会采用某些叙述策略来放慢叙述节律,延迟故事结束时间点的到来。尽管如此,我们说卡尔维诺还是喜欢采用这种“插叙”的手法的,他的《寒冬夜行人》便是通过插入一个又一个的故事片段,来延迟他的男读者与女读者的结合,也就是延迟故事的结束。
格兰特•普林斯也认为:“元叙述有规律地放缓呈现新事件的步调,从而影响叙事的节奏。显然,它们在叙述时不会带来许多新信息,而是建构对旧有信息的解释。”[4]64-65元叙述在起到解释补充功能时,它往往是对旧信息或代码进行解释,这样它必然很少涉及到新的信息,因此也就延迟了新事件的出现,从而达到放慢叙述节奏的效果。这样调节叙述节奏便是元叙述的又一功能。
二、元叙述的陌生化
使用元叙述手法的小说与传统小说大异其趣,它们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都与传统小说迥然不同。这种内容与形式的不同,正是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所谓的“陌生化”和布莱希特所说的“间离效果”。
陌生化理论是由俄国形式主义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在其《作为手法的艺术》一文中提出。他说:“艺术的手法是事物的‘反常化’手法,是复杂化形式的手法,它增加了感受的难度和时延,既然艺术中的领悟过程是以自身为目的的,它就理应延长。”[8]自文学艺术诞生以来就一直是把自己当成一个世界,而作家则是这个世界中的上帝。人们在阅读的过程中只看到了“上帝”所创造的事物,却不知“上帝”如何创造了这个世界。而在元叙述作品中,“上帝”不再是深藏在事物之后,而是在创造世界的同时,向世人展示自己是如何创造的。这样的“世界”不再是传统的“世界”,传统阅读作品的认识方式被打破了,也就是读者在面对元叙述作品时,不得不去调整自己的认识方式,从而使得文本在读者面前呈现出一种“陌生感”。
元叙述的运用一方面使得文本的形式更加复杂化,不再仅仅是故事层在文本中呈现,而且叙述层也呈现在文本之中,并且这种故事层与叙述层的杂糅,使得故事情节放缓,从而“增加了感受的难度和时延”;另一方面,元叙述的使用也正好使得故事层也即是“被创造之物”在作品中显得“无足轻重”,而相反,该故事是如何被创造的却得以突显出来,让读者体验到了“事物之创造的方式”。这样的作品与传统的“陌生化”不同,传统的“陌生化”是把世界“陌生化”,恢复我们对世界的感受;而元叙述作品的“陌生化”它不仅仅是恢复对世界的感受,它还恢复了我们对文本的感受。什克洛夫斯基在谈到《项狄传》时说:“旧的世界感受,旧的小说结构,在他(斯特恩——笔者注)那里已成为戏拟的对象。他通过戏拟驱逐它们,并借助离奇的结构恢复强烈的艺术感受和品评新的生活的敏锐性。”[9]这样通过“戏拟”从而使得读者对于元叙述作品产生一种“陌生感”,进而恢复了对生活和小说的感受性。而对于文本的阅读来说,元叙述作品还体现了布莱希特所说的“间离效果”。
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与“陌生化”理论类似,都强调创造出一种距离感,使得熟悉的变得陌生,从而来重新获得对世界认识的机会。他强调“把事件或人物那些不言自明的,为人熟知的和一目了然的东西剥去,使人对之产生惊讶和好奇心”[10]。但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与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又不同,“陌生化使文学获得了文学性,并且由于陌生化突出了文学的艺术特征(审美特征),令读者专注于艺术特征本身而使文学成为不及物的自我目的物;而对于布莱希特,陌生化主要地则是为了艺术自身以外的目的,即认识和批判社会现实。”[11]114-115也就是说“陌生化”强调的是恢复人的“感受性”,而“间离效果”则是从认知角度来着手的,是以一定的距离来认识事物,也即“认识论方面的意义构成了布莱希特陌生化理论的核心”[11]116。这样元叙述作品的陌生化就可以同时从这两方面分析,即它不但恢复了读者对世界与文本的感受性,而且这种策略的使用还使得读者对作品的认知产生了某种距离,使作品得以冷静地呈现。
元叙述作品的这种“间离效果”是很明显的。元叙述作品的情节往往是断裂的,因为其中穿插了元叙述而中断了原先的故事叙事,这样也就使得读者很难完全沉浸在故事中,并且叙述者还站出来对叙述过程或其中人物进行评论,无疑使得读者必须不断地跳出故事来审视故事,参与评判。这样也就不可避免的造成了元叙述作品的这种“间离效果”。
三、敞开的意识形态
在后现代元叙述作品中,元叙述更多的关注于意识形态,如琳达•哈琴所提出的历史编撰元小说。历史编撰元小说是指这样一种小说,它们以历史为题材,但在叙述过程中指涉这些历史编撰本身的虚构性,也即“强烈意识到了其叙述过去的方式”[12]152,它们“质疑历史编写”,“它们都使用叙事、指涉、主体性的确立、文本性身份,甚至还有与意识形态的联系,却又对这些常规手段持怀疑态度”[12]142。这样,“所谓的‘真实’再现说和‘非真实’模仿说统统遭到了拒绝,艺术原创性的意义和历史指涉性的明晰性一律受到了强烈质疑。”[12]147
历史编撰元小说这种指涉自身的小说,它指涉的是小说本身而似乎与外界无关,那么它又是如何与意识形态关联起来,甚至被认为是意识形态的战场的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历史编撰元小说与语境的关系。从元小说的结构上看,历史编撰元小说确实是与外界无关的,它仅仅是通过元叙述来指涉与自身相关的事项,而不与外界发生联系。但我们知道“文学和文学理论均意识到了语言的意义实质上是靠语境产生,意识到了表明一切话语环境的重要性”[12]103。因此,不论是何种文学作品,不论它是如何的指涉自身,它都是无法脱离语境的。而历史编撰元小说,按照哈琴的分析,它的意义还不仅仅是来自语言自身的语境,而是来自重新的语境化,即通过元叙述来打破传统一统化的、孤立的语境,而赋予文本以后现代语境。
哈琴强调两个方面的重新语境化:第一,“表达行为”的语境,也即文本、制作者和接受者这三者构成的作品内部语境;第二,这一“表达行为”所隐含的更广泛的历史、社会和政治(以及互文)语境[12]103。也就是说,在历史编撰元小说中,因其对自身的指涉,而这种指涉自身的行为却恰恰暴露了小说的语境,即它的文本、制作者和接受者。“我们要被迫使正视这样一种现象,语境赋予语言以意义,由说话者(听者/读者)、地点、时间、原因赋予语言以意义。”[12]103也就是说,在历史编撰元小说中,通过元叙述的运用,它展示了谁在叙述,怎样叙述,选择什么来叙述,又掩盖了些什么东西?等等。这样,就将叙述与文化权力、意识形态的关系凸显了。
同时,在这一文本、制作者和接受者的暴露过程中,社会、历史语境已不可避免地“无意识地”融入其中了。“即曾经遭受压抑的整个表达行为的语境和‘被置于特定位置’的话语的语境,这种话语没有忽视理解行为的社会、历史或者意识形态维度,也就是詹明信所谓的与历史一道遭受压抑的‘真正的意识’。”[12]111
第二,历史编撰元小说文本中的意识形态。哈琴认为,后现代小说与传统小说不同,传统小说是尽可能地树立一种权威,而其它意识形态都为这一权威所“同化”,后现代小说质疑这种权威,但并不就此树立另一种权威,因为那样仍然是一个意识形态笼罩着整个文本,相反,“后现代主义……正视虚构/历史再现、具体/一般、现在/过去的矛盾。这一正视行为本身就自相矛盾,因为它拒绝复原或者消解两个对立面的任何一方,而且更愿意对两者都加以利用。”[12]134也即是说“历史元小说奉行多元的和承认差异的后现代意识形态”[12]153。在历史元小说中,那种传统的典型性或一元性的意识形态无法存在,因为它们始终处于被指涉的地位,也就是“被嘲讽和被削弱”的状态,它们必然奉行的是多元的且具有差异性的意识形态。因此,在历史元小说中它的意识形态并不是单一的,而是相互对立的,通过元叙述来质疑已树立的意识形态,而呈现出另一种意识形态,这两种意识形态以相互指责的形式出现,共存于文本之中。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权威与质疑并不一定是先后的关系或者权威的树立就是故事中的权威,而质疑的产生就是元叙述的质疑。相反,权威与质疑在具体作品中往往都是水乳交融的,而权威也可以是通过元叙述来树立的,用虚构的故事来质疑它。
第三,后现代主义与自由人文主义的交锋。权威与质疑的这两种意识形态是文本内部呈现出来的,其中还更隐含了不同历史时期之间意识形态的交锋,这便是哈琴所说的后现代主义与人文主义意识形态的交锋。
首先,这一交锋体现在小说的体裁上。“小说这一体裁已经变成了一个战场,用来肯定、质疑自由人文主义对艺术的地位与身份所持有的信念。”[12]243也即是说,在传统人文主义的观念中,他们相信通过小说这一体裁可以创造出一片纯净的世界,这里没有政治及权利。历史元小说通过元叙述的自我意识,来质疑其所树立的权威,也就是在小说内部包含着的两种意识形态的对抗。而这种对抗还隐含着后现代主义对自由人文主义的“战争”,自由人文主义的那种“通过小说这个体裁来说服其读者相信某种特定的阐释世界的方式正确无误”的观念,在后现代主义这里受到了强烈的质疑。
其次,这一交锋还体现在小说的语言上。小说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它必须凭借语言方能存在。而自由人文主义对语言的看法则过于天真,他们相信语言的确定性,即通过对语言的运用可以确切地表达想要表达的东西。“人文主义相信语言、相信语言再现过去的或现在的、历史的或虚构的主体或‘真相’的能力”,而“为了对抗这种信念”“后现代主义”则把“语言与政治、修辞与压制”关联起来[12]253。也即“人文主义相信语言的力量”而“历史元小说常常告诉我们:语言有很多用处,也有很多误用”[12]248。那么,这种语言又是如何和意识形态关联起来的呢?哈琴以伊恩•沃森的小说《镶嵌》为例说:“在这部小说里,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列维•施特劳斯的人类学结构主义、马克思的政治学观点共同详细说明和理论阐释了叙事是如何展现这些含义(有关人类的思维过程、文化行为、社会组织)的。所有这些理论都显示了这些都是人为构建之物,其运作符合政治势力以及‘公正客观’知识的利益:它们全都是潜在的操纵话语。”也即“语言不可避免地受制于社会和意识形态。”[12]249如同哈琴的论述,这些“潜在的操纵话语”正是通过在小说中引入的各种理论来“阐释了叙事是如何展现这些含义的”才反映出来的,也就是通过元叙述话语的引入,才将这些“潜在的操纵话语”表现出来。
再次,通过在作品中引入元叙述的后现代小说还在内容上质疑了人文主义的意识形态。有趣的是哈琴虽然有意地强调了后现代艺术对人文主义的质疑,但她同时还认为“后现代艺术与理论……同时又承认它们不可避免地(如果说不情愿的话)也是这一传统的组成部分”[12]253。但不论后现代小说是质疑还是从属于这种人文主义的意识形态,它都通过元叙述来展现了这两种意识形态。那么自由人文主义中哪种思想内容,在历史元小说中受到了质疑呢?“对于今天的很多人来讲,遭受质疑的正是我们自由人文主义传统中‘合理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思想。”[12]253
总之,由于后现代主义的时代特征,即权威的解体、思想的多元化、对普遍成规的质疑,在小说中通过元叙述的运用从三个方面敞开了文学中的意识形态。其一、通过元叙述的运用,对作品隐含的语境进行了再语境化,即通过元叙述将作品潜在的语境拉入文本之中,使得读者对作品的语境有重新的认识,从而明晰文本中包含的权利关系。其二、在后现代多数小说中,一方面用传统叙述方式树立了一种声音,另一方面又通过元叙述对这种声音进行质疑,即后现代小说往往通过元叙述手法的运用包含了两种或多种相互质疑的声音,这也隐喻了后现代的时代特征。最后,通过元叙述的运用,后现代主义小说还在体裁、语言和内容三个方面表现出与自由人文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交锋。
四、结 语
元叙述作为一种叙述策略,它并不仅仅是在进入后现代社会才诞生的,它的存在要早得多。据刘恪在其《先锋小说技巧讲堂》中所论,最早的元叙述作品诞生在中国,“唐代文言小说《枕中记》、《任氏传》、《李娃传》均是”[13]。这样,元叙述的功能是在不断地发展的。可以说元叙述的类元语言功能及其陌生化和间离效果广泛存在于元叙述的运用过程中,但对于利用元叙述来揭示文本中的意识形态则主要是在后现代主义小说中才出现的。
[1] 热拉尔•热奈特. 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M]. 王文融,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158.
[2] Prince G. A Dictionary of Narratology [M].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7: 51.
[3] Jakobson R. Closing Statement: Linguistics and Poetics [C] // Sebeok. Style in Language. Cambridge: MIT Press, 1960: 356.
[4] Prince G. Metanarrative Signs [C] // Currie M. Metafiction. New York: Longman Publishing, 1995.
[5] Chatman S. Story and Discourse: Narrative Structure in Fiction and Film [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8: 151.
[6] 马原. 虚构[C] // 马原. 马原文集: 卷一.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7: 2.
[7] 伊塔洛•卡尔维诺. 美国讲稿[C] // 伊塔洛•卡尔维诺. 卡尔维诺文集. 萧天佑,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2.
[8] 维•什克洛夫斯基. 作为手法的艺术[C] // 维•什克洛夫斯基. 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 方珊,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 6.
[9] 维•什克洛夫斯基. 散文理论[M]. 刘宗次, 译.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7: 243.
[10] 贝•布莱希特. 布莱希特论戏剧[M]. 刘国彬, 金雄晖, 译.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0: 92.
[11] 马大康. 生命的沉醉: 文学的审美本性和功能[M]. 南京: 南京出版社, 1993.
[12] 琳达•哈琴. 后现代主义诗学[M]. 李杨, 李锋,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13] 刘恪. 先锋小说技巧讲堂[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7: 139.
Narrative Function of Metanarrative
WANG Zhengzh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 325035)
Metanarrative is a narrative strategy. Firstly, as a kind of metalanguage, metanarrative is bound to have some of its functions. Secondly, metanarrative is undoubtedly very different from normal narrative, which causes the effect of defamiliarization. Thirdly, the adoption of this approach can achieve the effect of“disenchantment”, i.e. removal of literary charm, which is said by Weber,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opens up the ideology of a text.
Metanarrative; Metafiction; Defamiliarization; Ideology
I207.4
A
1674-3555(2012)06-0044-06
10.3875/j.issn.1674-3555.2012.06.008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编辑:付昌玲)
2011-11-16
王正中(1985- ),男,安徽无为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