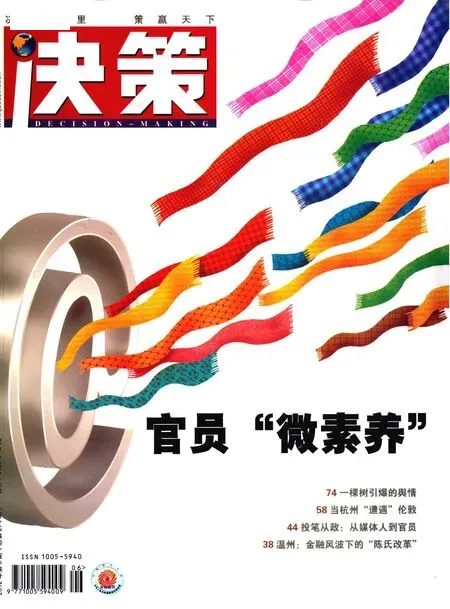浙江“小城市试点”探路
■蔡新祥
浙江小城市培育工作压力是浙江小城镇发展困境,基础则是浙江已经领先一步的“强镇扩权”。

温州小城镇的发展在中国小城镇发展中具有很高的享誉度,人口数量、城镇规模、经济发展比我国中西部的绝大多数县级市都要高,一些个别强镇实际上已经具备中等城市的雏形。
2012年初,《2012年全省小城市培育试点和中心镇发展改革工作要点》由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下发。这项源于2010年的试点工作进入了第三年。
2011年,浙江小城市培育的27个试点镇,面积仅占浙江全省3.9%,地区生产总值已占全省的5.8%,成效显著。
浙江省副省长陈加元表示,今年浙江小城市培育工作将紧扣由“镇”向“城”跨越主线,着力在城市形态、有效投入、发展速度、人口集聚、服务水平和改革创新上,突出做好“好、大、快、多、高、强”六字文章。
这预示着,“小城市试点”将成为浙江新一轮区域经济增长点。
“强镇扩权”升级
浙江小城市培育工作压力是浙江小城镇发展困境,基础则是浙江已经领先一步的“强镇扩权”。
近年来,浙江省小城镇发展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2007年浙江省就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中心镇培育工程的若干意见》,在全国率先对经济发达的141个中心镇下放了部分县级经济管理权限,全面启动了中心镇培育工程,通过政府推动、政策扶持、体制创新、市场运作,力争使中心镇成为具有辐射和带动能力的小城镇。
而其中,温州小城镇的发展在中国小城镇发展中具有很高的美誉度,其实体形态已经不再是一个镇的概念了,人口数量、城镇规模、经济发展比我国中西部的绝大多数县级市都要高,一些个别强镇(柳市、龙港、瓯北)实际上已经具备中等城市的雏形。
因此,在2010年2月,时任温州市委书记邵占维在强镇党委书记座谈会上提出“镇级市”的设想,提出要把柳市、塘下、瓯北、鳌江、龙港这5个试点强镇建设成为镇级市。
但是随着邵的离任,温州在“镇级市”建设方面其实并无实质性的动作。而“镇级市”这一概念却在全国媒体上轰动一时,一些东部和中部的省份纷纷提出要建设“镇级市”。
当然,这些省份的小城镇与温州的小城镇无论在哪个方面都尚存在差距,另外,由于“镇级市”在国家法律层面没有得到认可,2010年11月17日民政部发文就明确否定了“镇级市”的提法,即《关于严格行政区划建制表述等有关问题的通知》(民函〔2010〕247 号)。因此,“镇级市”这一设想,也就无疾而终了。
但浙江方面认为,现有的乡镇管理体制,已成为阻碍小城镇向现代化小城市发展的瓶颈。在专家们看来,把一批强镇“蝶变”为小城市,这是必然趋势。因此,2010年,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成立了课题组,专门研究在“强镇扩权”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中心镇向小城市转变的相关问题。专家们认为浙江方面应该做好“变性、换壳、扩容、转制”四篇文章。
所谓“变性”,就是要明确把中心镇原来的大乡镇性质转变为小城市性质,这是一次质的提升和飞跃,明确把中心镇纳入城市建设发展和管理的范畴,也就是变农村区域为城市区域;
所谓“换壳”,是对生产关系和行政管理构架进行改革调整;
所谓“扩容”,就是要加快产业集聚、人口集聚,扩大农民进城的容量,扩大中心镇建设发展地域和辐射带动地区;
所谓“转制”,是推进城乡统筹的土地、户籍、住房、社保、集体经济产权和镇行政管理体制等改革。
但强镇走向城市的道路并非坦途,首先,镇级市涉及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架构调整,中央的默认或支持至关重要;其次,强镇所在的县是否愿意让渡利益非常重要。更为敏感的是,按照小城市建设后,现行财政体制如何调整,“乡财县管”的利益格局必将改变,其阻力可想而知。
因此,也有专家认为,镇级改革应该分类进行,有的乡镇可以作为县的派出机构,有的镇可以先行探索变为小城市,有的乡镇,特别是贫困地区乡镇,仍需要进行镇乡合并,便于资源集中,应通过探索来确定究竟适合哪类模式。
在综合考量各方面的因素和浙江省小城镇发展的实际情况下,2012年10月,浙江省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快中心镇发展和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将“开展小城市培育试点,构建城市化发展新平台”,作为加快“十二五”建设发展的四大任务之一。
是年12月,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出台《关于开展小城市培育试点的通知》(浙政办发〔2010〕162号)。在全国首创进行小城市培育试点的探索,称要探索走出一条具有浙江特色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新路子。
对于这些试点镇,浙江省政府明确规定,允许他们在核定的编制总数内统筹安排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县(市、区)政府部门派驻试点镇的机构,日常管理以试点镇为主,其负责人的任用、调整及工作人员的调动,要书面征得试点镇党委的同意。垂直管理部门可以在试点镇设派驻机构。
同时,根据试点镇的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生产要素流向,允许适度调整试点镇的行政区划,拓展发展空间,增强集聚辐射能力。鼓励金融机构到试点镇设立分支机构,支持有条件的试点镇设立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浙江省政府在发出的通知中指出,省政府将从2011年起建立每年10亿元的培育试点专项资金(暂定三年),用于试点镇的基础设施、社会事业、产业功能区、技术创新和人才集聚服务平台、公共服务平台等项目的补助。
鳌江范本
在接到入选浙江省《关于开展小城市培育试点的通知》27个小城市试点名单和政策后,各小城镇所在地动作很大,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纷纷出台各自的政策和方法,其中鳌江镇具有典型意义。
鳌江镇正式建镇于1933年,素有“百年商埠、瓯闽小上海”之美誉。鳌江镇是平阳县的经济、交通中心,2009年列为温州市首批强镇扩权试点镇,2010年列为浙江省首批小城市培育试点镇。
那么,小城市应该怎么建?
鳌江给出的答案是“一条主线”、“五五战略”、“三大定位”搭建科学的战略体系,全力建设宜居宜商宜创的“新鳌江”。
为此,2011年4月,经浙江省政府批准,温州市撤销钱仓、南麂、西湾、梅溪、梅源五个乡镇建制,并入鳌江镇。2011年5月,经温州市政府批准,成立鳌江新区功能区,实行“区镇合一”的管理模式。
在这些区划调整之外,除了温州赋予鳌江的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和部分县级行政管理权限外,温州市还探索将试点镇政府整体升格为副县级单位,并建立相应机构,适当扩大人员编制。同时,按照事权与财权统一原则,探索建立统一规范的县(市)、镇财政收支体制。
其次,平阳县按照省政府对小城市培育提出的“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建设发展要求,为进一步增强统筹协调,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确保三年内鳌江镇小城市培育试点工作取得实效。
经过一年试点,鳌江镇成绩显著,荣获温州市功能区(镇)考核一等奖。2011年全镇实现工农业总产值166.13亿元,同比增长21.43%;财政收入10.77亿元,同比增长47.74%。
找到“新蓝海”
经过一年实践,数据显示,2011年,浙江省27个试点镇实现了镇均“固定资产投资62.2%的增长、GDP17.6%的增速、财政26%的增收、城镇化2.7个百分点的提升”的超常发展态势。
另外,2011年浙江省城市化水平达到62.3%,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约12个百分点。这其中小城市试点功不可没。
浙江省的小城市培育试点属于全国首创,但是困惑也有不少。主要是中心镇规模大小不一,在27个小城市中,人口最多的龙港镇人口40多万,远多于一些普通的城市和县城,工业总产值最高的店口镇达到649亿元,财政税收最多的柳市镇28个亿,远超一般的县市,而像江山市贺村镇在浙江省实际上是个普通的镇,由于地市均衡和地理位置的关系,而跻身小城市培育行列,两者相比之下,相差巨大,但是政策上却一样对待。
另外,小城市至今没有国家法律上的支持,国内尚没有小城市的法定概念。浙江省虽然提出了一些定义,但并没有上升为立法层面。随着小城市培育建设工作的进一步推进,浙江省内必将出现更多的小城市,如何使之建设有序、管理有效、发展有力,就不能仅以文件的形式加以诠释,必须要将小城市建设纳入有法可依、依法可建和用法有度的体系中来。这样,既能使小城市推进工作呈现常态化、可复制化和可持续化,也能为“小城市”找到依据,减少出现政策下行的阻滞和效用递减现象。
最近,根据相关媒体,国家正在探索实行多元化设市途径,适度增加设市数量。“镇区常住人口5万的建制镇可直接设市”。按此标准,浙江省27个小城市均可设市,这也是对浙江小城市试点一个利好的消息。
此外,如何解决小城市的人口集聚也是一大难题。城市是承载人生活为主要功能的,没有了“人”这个重要要素,城市就无法称之为“城市”;而小城市之所以称之为“小”,主要一条就是集聚的人口要少于大中城市。面对大中城市对人的强势吸引力,如何“引人入小城”及而“留人居小城”是解决小城市发展的关键问题。
另一方面,如何使小城市的人口在“被市民化”的过程中,避免出现因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交易方式的重大改变,从而降低“幸福指数”而成为旁观者、甚至居于对立面,进而阻碍城市化推进的现象,实现真正的“人城互动”,进而由自觉而自发、使之成为推动小城市形成的核心力量,这才是决策者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最后,小城市的发展是需要“真金白银”投下去的,没有投入根本形不成“城”,而仅靠中心镇微薄的财政收入是无法在短期内建设满足小城市功能的相关软硬件设施,按照目前举债发展的模式虽然可能会在一定时期内形成某些城市功能设施,但明显是权宜之计、无法持续的。
特别是在当前同质化招商的机制下,小城市在吸引投资上并无相对的制度与体制优势,缺乏形成资本高地和资金洼地的基本条件;传统的城市经营模式在小城市发展中的复制只能带来地产的泡沫化,更是会造成“去原住民化”,并会因无法对冲新住民而使小城市成为“空城”。
因此,在小城市发展的顶层设计中,要充分考虑“造血功能”的培育,摆脱建城扩投资的简单发展思路,逐步打造发展的可持续性,走出一条发展的“蓝海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