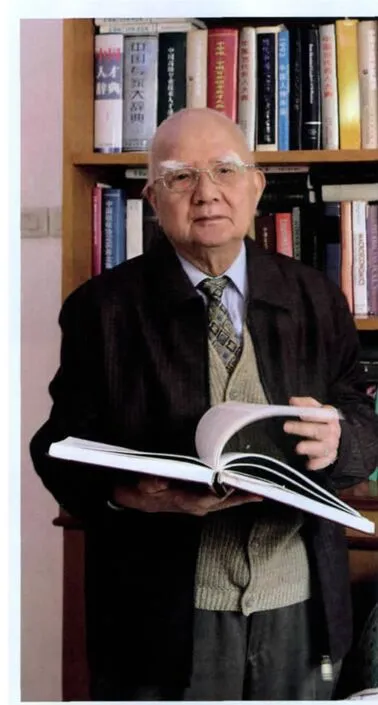吴良镛:倾心谋造“万家居”
文/王国平
吴良镛:倾心谋造“万家居”
文/王国平

20 12年2月14日,吴良镛从国家主席胡锦涛手中接过了“国家最高科技奖”。这位90岁看起来有些虚弱的老人,却用他身躯里蕴藏的巨大能量,为中国建筑求索不止。
毕生筑梦为民居
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为使命,不说空话,只做实事,是吴良镛一生的坚持。数十年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城市规划建设道路。
熟悉建筑界的人常说:“凡是到过北京的人,都曾亲身品读过吴良镛。”其实何止是北京?无论你是在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生机勃勃的改革开放前沿大都市,还是流连于苏州、桂林、丽江等古典与现代气息交融、自然与人文色彩竞艳的新兴城市,你肯定都曾亲身品读过吴良镛。从城市规划到建筑设计,从拜万人师到教书育人,吴良镛不知疲倦地奔忙着。
“与公共建筑相比,我更在意民居。”吴良镛常说,“民惟邦本,普通人的居住问题是建筑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
他经常告诫学生:“建筑学的意义不仅在于要盖房子,更要避免盖低劣的房子,不要以为在一个地方盖一座大房子就可以扬名,如果盖得不好,那就是历史的罪人。”在吴良镛的心中,创造良好的、与自然和谐的人居环境,让人们能诗情画意般地栖居在大地上是他一生不变的梦想。
作为中国建筑学与城市规划学的领军者,吴良镛非常重视科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不断探索着中国特色的建筑与城市理论的发展之路。他吸取中国文化、哲学的精华,融贯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创造性地提出“广义建筑学”理论,并在1989年出版了15万字同名专著,将建筑从单纯的“房子”概念走向“聚落”的概念。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邓卫告诉记者,这是我国第一部现代建筑学系统性理论著作,该书出版后,引起了中国建筑界的广泛关注,被推荐为“一本建筑师的必读书”。
在此基础上,吴良镛针对城市化日益加快的进程和建设事业大发展的格局,创建了“人居环境科学”体系。在这个宏大的体系中,吴良镛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城市规划、建筑与园林为核心,整合工程、社会、地理、生态等相关学科的发展模式。
北京菊儿胡同有一个41号院,原是一座寺庙衍生出的大杂院,也是菊儿胡同最破的地方。40多户人家共用一个水龙头、一个下水道,厕所在院外100米处。随着人口增加,院子里逐渐盖满了小棚小房,几乎没有转身之地,危房、积水、漏雨的问题一直困扰着这里的居民。
上世纪80年代,北京开始危旧房改造项目。但是,菊儿胡同又属于古都风貌的保护范围。由于许多改造方案与旧城风貌保护相冲突,改造项目一直停滞在规划层面。不仅如此,项目不大、费用不高,牵涉面却不少等问题,使得很多设计单位都不愿碰这类项目。后来,北京市房改办找到了吴良镛。出乎意料的是,吴良镛对于这个建筑面积仅2700多平方米、设计费用仅1万元的项目显示出极大热情。
“衣服破了一定要扔掉吗?是不是可以想想办法,例如打个漂亮点的补丁,或者绣上图案。”吴良镛一贯注重解决实际问题。
其实,早在1978年起,吴良镛就开始对北京旧城区中心地段的整治进行研究。他认为,北京旧城可以说是世界城市史上“无与伦比”的杰作,是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最后结晶”,因此,北京的旧城改造,不仅要满足现代生活的舒适要求,还要与原有的历史环境密切结合,要创造一种社会住宅。因此,他提出了“有机更新”理论和建造“类四合院”住房体系的构想。在这场“有备之战”中,吴良镛的理论在菊儿胡同四合院改造工程中得以充分展现。
据吴良镛的助手左川回忆,在菊儿胡同方案审批时费尽周折,前后审查了七次之多。但吴良镛不厌其烦、反复修改。到了施工图阶段,光图纸就出了95张。
如今,改造后的菊儿小区里,精心保留了原有的树木。一水儿的2层、3层小楼白墙黛瓦,与周边的老房子浑然一体,丝毫不觉得突兀。一进套一进的小院子,面积虽然不大,却并不觉得压抑。这样一座“类四合院”,完全没有高楼大厦那种冰冷、孤立的感觉,“大爷”“大妈”“叔叔”“阿姨”……邻里间出来进去的都打声招呼,有了困难也相互帮助,情境间,生活仿佛回到了过去的北京城。而这也恰恰体现出吴良镛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
相对于大拆大建,吴良镛倡导的“有机更新”理念,延续了城市原有的历史环境,对于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城市来说,可谓是探索了一条旧城更新和危房改造的新路子。1992年,菊儿胡同改造获得亚洲建筑师协会金质奖,1993年获得联合国“世界人居奖”。
“我们需要激情、力量和勇气,自觉思考21世纪建筑学的未来。”1999年6月下旬,在国际建协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上,时任大会科学委员会主席的吴良镛宣读了由他起草的《北京宪章》并获得通过,标志着“广义建筑学”与“人居环境”学说已为世界建筑师所普遍接受和推崇,从而扭转了长期以来西方建筑理论占主导地位的局面。作为国际建协成立50年来的首部宪章,它成为指导新世纪世界建筑发展的重要纲领性文献,并在2002年以中、英、法、西、俄5种语言出版。当时的国际建协主席V.Sgoutas表示,这是一部“学术贡献意义永存”的文献。英国著名建筑评论家Paul Hyett则评价说,吴教授以一种乐观和利他主义的姿态,提出了引导未来发展的“路线图”。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院士、世界人居学会主席……数不清的荣誉、成就,却没能让吴良镛停下前进的步伐。
战火中点燃建筑梦
已届九旬的吴良镛,现在可谓“随心所欲不逾矩”。是怎样的情怀,让这个耄耋老人呕心沥血成就这筑梦人生?我们得从吴老坎坷经历说起。
1922年春天,吴良镛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一个普通职员家庭。他自幼喜爱文学、美术,兴趣广泛,读书刻苦勤奋。在吴良镛出生与成长的南京门西地区,邻近“十里秦淮”。自古以来就是集文化、商业、服务业和专业化加工为一体的繁华地区,然而从民国初年开始大片衰落。吴良镛的家也没有逃过这悲惨的境遇。
少时的他,目睹了收账人揭走自家屋瓦。当时,妹妹正在发着高烧,无奈之下,一家人只好被迫告别祖居,遭受流离失所之痛楚。1937年南京沦陷前,吴良镛随兄长匆匆离开南京,先后到武汉、重庆求学。
“刚刚交完大学入学考试最后一科的考卷,就听到防空警报响起,日本人的战机突然来袭,”吴良镛回忆起1940年7月在母校重庆合川二中参加高考的情景,“当时我们赶紧躲到防空洞里,一时间地动山摇,火光冲天,瓦砾碎片、灰土不断在身边落下来,当我们从防空洞出来时,发现大街小巷狼藉一片,合川的大半座城都被大火吞噬。”在这场轰炸中,吴良镛非常敬重的江苏省首席国文教员戴劲沉父子不幸遇难。
流离失所、国破家亡的民族血泪,促使吴良镛在内心早早地树立了“谋万人居”的伟大理想。他悲伤地告别合川,临行前默默许下宏愿,“将来要从事建筑行业,重新修整惨遭蹂躏的城乡”。
1940年秋,吴良镛进入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学习,受教于鲍鼎、徐中、谭垣、杨廷宝、刘敦桢等我国诸位建筑教育先驱。在重庆中央大学图书馆的暗室里,吴良镛看到了一批越过“驼峰航线”运来的国外建筑杂志缩微胶卷。他惊讶地发现,同样饱受战乱侵扰的西方建筑界并未无所作为,而是信心百倍地放眼未来,致力于战后城市重建和住宅建设的研究。国破山河在,战后重建的美好愿景如同一道划破黑夜的闪电,照亮了吴良镛的心,而“重建”这个概念,也深深地印在了他的心中。
上大学期间,吴良镛在油印校刊《建筑》上发表了题为《释“阙”》的文章,被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看到,因欣赏他的才华,让他到身边协助工作。“在梁先生身边工作,有机会看到他从国外带来的建筑领域的最新资料,这让我开阔了眼界,积累了不少建筑学知识。”说到恩师梁思成,吴良镛充满感激之情。
抗战胜利后,刚毕业两年的吴良镛应梁思成之约,协助他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建系之初,梁思成赴美讲学,吴良镛和林徽因成为系里仅有的两名教员,自此,揭开了新中国建筑教育的新篇章。1948年夏天,梁思成推荐吴良镛到美国匡溪艺术学院建筑与城市设计系深造。在著名建筑师沙里宁的指导下,吴良镛开始探索中西交汇、古今结合的建筑新路,其间曾获罗马奖金建筑绘画雕塑设计竞赛荣誉奖,在美国建筑界崭露头角。

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给吴良镛寄去一封信。“百废待兴”这四个字,让吴良镛立刻做出了抉择。
1950年底,和那个时代许多充满赤子情怀的科学家、艺术家一样,吴良镛冲破重重阻挠,几经周折,毅然从美国绕道回国,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和教育事业。
回国后,吴良镛一直在清华大学任教,历任副系主任、系主任等职。1959年,他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1984年退休后,筹建了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并担任所长;1995年创办清华大学人居环境研究中心。
“年轻的时候,我曾在书本上了解到,西方城市有交通拥挤、住宅缺乏、失去自然等毛病,当时天真地认为,这些跟中国没什么关系。”吴良镛回忆说,“直到怀着满腔热情从海外回国参加建设时,我都依然认定所谓的‘城市病’只是资本主义的产物,社会主义中国不仅可以避免,而且还能建设得更好。”
然而,随着旧中国民生凋敝的影像在一批批拔地而起的新建筑、一座座百废俱兴的新城市身后渐渐淡去,吴良镛的心头却萦绕着日益浓密的困惑:现实和理想呈现出较大偏差。吴良镛认为,数十年间,中国城乡变化虽然巨大,却并没能绕开“城市病”。
吴良镛常说,西方建筑史是“石头的历史”,而中国古代建筑是“土木的历史”,因此,中国古建筑保护比西方更为不易。但让吴良镛感到揪心的是,城市文化建设面临着重重误区,有些城市呈现出不健康的规划格局:好的拆了,烂的更烂,古城毁损,新的凌乱。而且,城市同质化严重,千城一面现象尤为突出。
更让吴良镛愤慨的是,近年来国际上一批形形色色的建筑流派蜂拥而至,对我国城市建设产生了很大影响。“很多未经消化的舶来品,破坏了城市原有的文脉和肌理,导致有的城市成为外国建筑师标新立异的建筑设计实验场。”
“放弃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内涵探索,显然是一种误解与迷失,”吴良镛在很多场合都在强调,“不是不能借鉴西方建筑,但不能照搬照抄,拾人牙慧。”
许多城市管理者经常给吴良镛打电话,征求他对城市规划的意见,有的甚至直接找上门来。他对此总是不厌其烦、亲自接待。
“自古太守多诗人”,对于城市的管理者,吴良镛有话要说:“希望作为城市规划决策者的市长,都能具有诗人的情怀、旅行家的阅历、哲学家的思维、科学家的严格、史学家的渊博和革命家的情操。”

建筑大师缔造康复奇迹
“人们常说电影是遗憾的艺术,我觉得建筑更是遗憾的艺术,”吴良镛解释说,建筑完成后,修改的可能微乎其微,而且这个建筑可能要矗立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影响着这个城市,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因此,一定要力求做得更好,少留遗憾。
科学求真、人文求善、艺术求美,这幅吴良镛亲笔所写的书法作品,透露出他对事业尽善尽美的渴求。
“我豪情满怀地目睹了祖国半个多世纪的进步,每每扪心自问,我们将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交给子孙后代?”为了追寻这个问题的答案,他每天清晨就拖着装满资料的小车走到建筑馆工作,中午让家里送饭,然后在办公室里小睡一会儿,接着一直工作到晚上才离去。已经80多岁高龄的他不顾辛劳,经常亲自奔波在各个建筑工地上。直到2008年的夏天,86岁的吴良镛在南京金陵红楼梦博物馆工地视察时突发脑梗,一头栽倒在地上。
当时,所有人都以为吴良镛的工作至此就画上了句号,医生也判断他这辈子不可能再站起来。病痛并没有将他击垮,反而激发出更加顽强的拼搏精神。
面对脑梗造成的手脚不便,吴良镛开始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康复治疗。“别人一天练4个小时,我就练8小时,我告诉自己,必须尽早站起来,回到我热爱的建筑领域。”吴良镛暗下决心。
“当时,吴老的半边身体已经完全不能动了,在医院里,才刚刚清醒的他就招呼我到身边,询问北京奥运会的进展情况。”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朱文一回忆说:“在病床前,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党委书记边兰春问吴老有没有信心战胜病魔,吴老只淡淡地说了一句,我不但要站起来,还要能走路,还要恢复到能写字、能绘画。”
在医院里,医生都称吴良镛为“模范病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主任吴维佳说,吴老非常尊重科学,严格按照医生的指导方法锻炼,而且异常刻苦,很多小伙子都坚持不住的康复训练,吴老全都努力坚持下来。夏天屋里很热,很多患者都偷懒不愿锻炼。可是,吴老穿着个小背心,认真锻炼的身影每天都准时出现,一会儿,全身就已被汗水湿透。
正是因为有着远超常人的毅力,吴良镛很快就可以走路了,不听使唤的手也能握笔写字了。医生都啧啧称奇,认为这样的恢复效果太不可思议了。尽管这样,吴良镛仍不满意,他心里较着一股劲,一定要恢复到之前书法家的水平。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出院那天,吴良镛送给医院一幅亲笔所写的书法作品,苍劲有力的字迹,是给康复课程交出的最好答卷。医生们都说,他不仅给建筑界留下一个个令人惊叹的奇迹,在康复医学领域中也创造了一个奇迹。
“少有的刻苦、渊博,少有的对事业的激情,多年与困境抗争中表现出的少有的坚强。”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林徽因曾这样评价吴良镛。
出院后的吴良镛仍然闲不住,思维的活跃程度甚至超过年轻人,几乎每天都会有新想法、好创意迸发出来。在吴老枕边,总放着一支笔、一个本,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本子记录下新想到的问题,而且忙起来就一点也不顾及身体。“年纪大了,记性差了,所以只要想到了就必须马上记下来,否则很可能忘记,就错过了。”在接受采访时,吴良镛笑着说。
因为吴良镛的高强度工作,左川担心他身体吃不消,给他拟定了“八大注意”,其中一条就是不能激动。“通常是做不到的,喝口水都要人催着,有好多次,他讲着讲着就激动起来,还经常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真拿他没办法,”左川很是无奈。每次“批评”他,他还很“有理”,经常用梁思成的故事“堵”我们的嘴。
“梁思成脊椎有问题,不能打弯,但他每天仍坚持工作很长时间,经常用一个瓶子抵住下巴,在桌上画设计图,”每每讲起,吴良镛都无限感慨。
“言传身教,润物无声,”每一个当过吴良镛学生的人,对他的评价中从来少不了这一点。“吴教授从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告诉你必须怎样做,而是从点点滴滴处启发学生,”吴良镛的博士研究生郭璐说:“跟吴教授学习,不仅是学习的过程,还是思想境界不断升华的过程。”
吴良镛经常教育自己的学生:“建筑师与社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而每个时代又对建筑师的要求有所不同,但不管怎样改变,一定要牢记对人的关切,同时,建筑业需要具有赴汤蹈火的热情和无限的忠诚。”
“身体再好一点,能参加更多工作,”吴良镛平实的语言,表述出最质朴的愿望。满头银发,两道白眉,圆圆的脸上永远带着敦厚温和的笑容,就是这样一位老者,对工作仍充满了激情,没有丝毫减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