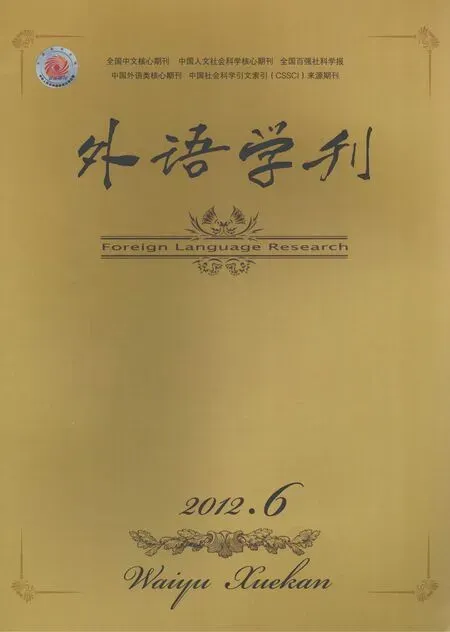梅列日科夫斯基创作中的彼得堡现代神话意蕴*
刘 锟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哈尔滨150080)
彼得堡作为俄国现代化和面向西欧文明的开端,作为与代表古老俄罗斯民族传统的莫斯科相对的年轻的都城,成为历代作家和人文学者关注的对象。“它从沼泽之中突兀崛起,把俄罗斯社会分成不可调和的两派:对于一些人来说,它是天堂和乐园,是通向欧洲的窗口;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它是预示末世论式的毁灭的深渊”。(Топоров 2003:1)普希金就曾“兴高采烈地讴歌年轻的俄罗斯的象征——彼得堡这北方明珠和军事重镇的出现”。(金亚娜1999)同时,还存在着另一种悖论。根据俄罗斯文化意识中的“第三罗马”的理念,莫斯科是东正教使命的中心,而彼得堡在民众的意识中则永远都是一个“天边的城市”,它陌生而冷漠,是建立在沼泽之中,建立在无数白骨之上的诡异的城市——在斯拉夫古代神话中,沼泽是不洁力量的住所,是神圣空间终结的象征。于是几百年来围绕彼得堡这个城市形成了种种神话。
1 俄罗斯文学中的彼得堡与现代神话
在现代哲学和文化学理论中,“神话”是一个使用得非常广泛的术语,其定义和阐释不下上百种之多,是人文学科中的一个时尚概念,但是,它的核心内容仍然是神秘的、难以把握的。传统的神话概念与宗教相联系,它的语义学内涵非常宽泛,词源学考证也争论不断,在这个过程中,这一概念也不断被学术界修正和扩展,现代神话理论因此得以产生和完善。20世纪俄罗斯著名哲学思想家А.Ф.洛谢夫从人类神话发展史和生活现实着眼系统地研究了神话的本质,他认为神话是“主客体之间活的交流,这种交流具有纯粹的真实性、可靠性、原则上的规律性和结构”(Лосев 1990:416),总之,神话是一个多层次的象征。现代神话本质上区别于古代神话,是因为现代神话创造的现实,不可避免地会和时代的日常观念发生关联,并且被作为不可思议现象的解释、象征性表述和潜意识的投射。(劳里·杭柯2006:58)俄罗斯文学中彼得堡神话的产生和发展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文化和民族心理机制。
彼得堡的建城历史及与之相关的种种传说作为文化的镜子和历史状况的结果,表征了它在文学叙事中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功能神话的必然性。彼得大帝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革虽然触及到贵族阶层的精英文化,实际上它并未使民间文化和民众素养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与这座城市的建立相伴而来的是政治的、宗教的、文化的种种传说和猜想的迷雾。作家们的创作为某些神话的产生和诠释提供了极好的载体。几百年来,关于彼得堡城市形象的文化、哲学阐释深刻而持久地体现在文学中,成为一个具有固定意义系统的文学象征形象:“迄今为止,很明显,不同种类的纯文学作品——历史书、指南、报纸甚至趣闻轶事——都已经为彼得堡神话的发展作出了贡献”。(Milcolm,Miller 2003:27)
应该说,俄罗斯文学中的彼得堡现代神话伴随着浪漫主义创作原则的兴起而逐渐形成。对彼得堡形象的阐释及其神话意义的思考已经成为俄罗斯文学的一个宏大传统。各时期的作家们都会被彼得堡这座城市在历史进程中的神奇意义和诡异传说激起无边的联想和幻觉。现代神话与古代神话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是集体无意识的产物,而现代神话带有强烈的作家个性精神特征。但是,俄罗斯文学中的彼得堡神话仍然体现了俄罗斯民众意识中关于这座城市的种种悖论。从普希金开始,以彼得堡为故事空间背景的俄国经典小说基本上从不同的视角挖掘和定型了这座城市的艺术形象,如普希金的《青铜骑士》从自然与人的意志、帝王权力与民众对立的角度揭示了彼得堡灾变和灭亡的主题;果戈理的《彼得堡故事》则把这座城市变成涵纳了诡异存在、卑微人性和无常命运的光怪陆离的空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突出了这座城市阴暗、丑恶、肮脏、非理性的一面……俄罗斯社会剧烈变动、社会思想空前活跃的19-20世纪之交,是俄罗斯精神文化历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被称为俄罗斯文化的“白银时代”。这一时期作家创作中的新神话意识特征明显增强,尼采宣称的非理性主义成为新神话意识出现的序幕,并且这种新神话意识在20世纪文化中扎根发展,成为时代意识的基本特征之一。例如安·别雷的《彼得堡》就以现代主义的方式渲染了彼得堡的不祥存在……彼得堡神话成为俄罗斯经典文学传递给现代文学的一个强大传统是有其内在必然性的,“在日常生活和作家的创作思维中经常起作用的是一种神话的逻辑,这种逻辑会创造一个不可能的可能世界,完成不可完成的事情,实现不可实现的东西——它的前提和结果只通过一个规律联系起来,即愿望或创作意志的绝对自由”。(Мосейко 2003:29)
20世纪俄罗斯文学和文化中的新神话意识凸显出人们对世界的感知中的非理性视野,进而各学科都广泛采用神话的意义结构或思维逻辑,致使古代传统神话和现代文化相互作用,互换位置,超现代的思想与神话的神秘主义相结合。而文学中的彼得堡文本及其神话也是这样一种不断的结合、互换和颠覆的产物,是一个复杂的研究对象,具有多层次多角度的阐释空间。白银时代作家德·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小说直接取材于俄国历史,不但具有浓厚的人文关怀、明显的宗教探索倾向和对民族精神的深刻思考,而且表现出对彼得堡这座城市复杂的情感和宗教神话体验。
2 梅列日科夫斯基创作中的彼得堡神话
梅列日科夫斯基1865年8月2日生于彼得堡市的一个旧式宫廷建筑中。在这样一个具有浓郁历史文化背景的成长环境中,他对彼得堡的体验是深刻而独特的。梅列日科夫斯基是“白银时代”俄罗斯“新宗教精神”运动的主要代表,重要的宗教哲学思想家和活动家,也是象征主义文学纲领的发起人。他不但是象征主义诗人,而且在历史小说创作方面的地位也不可取代。
梅列日科夫斯基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神秘直觉。不论是他的小说文本还是精神散文,都具有强烈的预言性和启示色彩。他在《彼得堡必将一片荒凉》(1908)一文中以种种印象强调了对这座俄罗斯新兴都城必然灭亡的预言。其实这种传说古已有之,而且在以后的作家作品中都有所体现。只是在梅列日科夫斯基这里被以极端化的形式呈现出来。那些被彼得大帝强行赶到这个“天堂”的俄罗斯人都相信这个神话,即这座城市将会被洪水卷走或沉入沼泽。梅列日科夫斯基认为,在彼得堡曾经发生过的一切都如同梦魇,在这座城市的面容中能够读到的只有两个字——“死亡”,只会引起恐怖和终结的感觉。虽然梅列日科夫斯基是对欧洲文化最为情有独钟的作家,但是他不喜欢彼得堡。彼得堡不是由本民族文化和历史积淀自然形成的,即使它是按照欧洲艺术典范由欧洲建筑师设计的,但它终究不是欧洲。莫斯科就完全不同,它是自然成长出来的,而彼得堡则是“被生长”,从地底下拖出来的,或者说简直就是“臆想”出来的。(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2000:328)彼得堡作为彼得大帝意志的产物,在这位思想家的意识中成为集现代文明和罪恶之城于一体的怪胎。
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彼得堡小说以历史为题材,承袭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彼得堡词典”和“彼得堡地图”式的叙事特点。作者仿佛带领读者亲历彼得堡的大街小巷、宫廷市井,游历和见证这座城市的往日今昔,小说每个情节发展和事件背景几乎都详细指明具体地点、周围环境或行动路线,全面清晰地展现了18-19世纪的彼得堡的市井风情。《彼得与阿历克塞》描写了彼得堡刚刚建立之初从皇室宫廷到山林乡野的俄国社会生活画面;《野兽王国三部曲》(包括长篇小说《亚历山大一世》、《12月14日》和剧本《保罗一世》)创作于1905年和1917年两次革命之间,这是俄国历史上的转折时期和极端时刻,这一时期作家的宗教哲学思索主要集中在俄罗斯未来的道路和历史意义等问题上,梅列日科夫斯基认为可以借助历史事件的启示性内涵进行探索。小说描写了发生在这座城市的社会动荡、政治阴谋及与此相联系的宗教传说和神学思考,借此探索俄国历史文化对于基督教的意义——继野兽王国的统治之后,俄罗斯以及全人类都在期待着的基督王国的到来。
2.1 反基督神话:“青铜骑士”
如果对于果戈理来说涅瓦大街是彼得堡和现代文明的缩影,那么对于梅列日科夫斯基来说,青铜骑士则是这座城市传奇历史的象征,是把彼得堡神话化的现实依据。“在使现实模式化的同时,神话类似于一种提喻(以部分喻整体),有时也会变成一种夸张(被神话化的客体被放大、变得醒目,类似宣传画的效果)”。(Хализев 2005:125)彼得堡市参政院广场上的青铜骑士塑像——骑在马上威风凛凛的彼得大帝就是这样一个被神话化了的形象,它似乎成为彼得堡现代神话的意义核心。这件建于18世纪末期法国大师法尔孔奈的杰出作品虽然只是一座雕像,却是彼得堡的象征符号,是俄国文明启蒙的缩影,是彼得一世的化身,它代表着彼得大帝“神明般的威力”。青铜骑士作为彼得大帝强大意志的延伸,仿佛随时都在参与这座城市的生活,上至帝王贵胄,下至市井百姓。普希金长诗中的“青铜骑士”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它仿佛随时可以从基座上跳下来奔驰在彼得堡的大街小巷,那清晰的马蹄声甚至时常会在受到这种意识影响的人耳边响起……这座雕像面向涅瓦河、背靠伊萨基辅教堂以及涅瓦大街,雄奇地注视着这里发生的一切,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往日与今昔,它仿佛诉说着彼得堡乃至整个俄国的奥秘与宿命。
梅列日科夫斯基在小说《彼得与阿列克塞》中把彼得塑造成一个半人半神,集种种矛盾于一身的超人形象。他丑陋,但又强大;他残暴,但又仁慈;他虔敬,但又渎神;他威力无边,但又渺小无助……这是一个带有偶然性的决定着俄国命运的形象,梅列日科夫斯基把他看作是人类历史阶梯上进行宗教精神探索的一个环节,是探索宗教真理的曲折道路上的一个否定性因素,因此作者在时间上后续的历史小说作品中会不时把彼得神秘化。
梅列日科夫斯基笔下的青铜骑士神话和俄国历史的政治传奇密切相关。他在几个世纪以来沙皇俄国统治者的王位更替、王权和教权的关系以及俄国宗教精神的发展道路之中既看到“野兽”统治的“反基督”性,也在其中寻找着未来宗教的启示,这种未来宗教是能够拯救俄国以及全人类的基督宗教,梅列日科夫斯基期待着“圣灵王国”的到来。《野兽王国三部曲》中的两位沙皇——保罗一世和亚历山大一世都是俄国历史上具有神秘传奇色彩的人物,前者命运离奇多舛最终死于非命,后者则以“王位上的演员”和“两面神”著称,他突然离奇的死亡以及后来盛传的隐居民间的传说更令人感到迷雾重重。
《保罗一世》是梅列日科夫斯基唯一的戏剧作品,2003年在彼得堡建城700周年之际,这个剧本被拍成电影《可怜啊,可怜的保罗!》。影片的名字来自剧本中保罗的一句独白。保罗一世这个俄国历史上最倒霉的皇帝,从出生就遭到母亲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冷落和厌恶,时刻害怕被人处死,在担惊受怕中战战兢兢地长大,但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却深得祖母喜爱。叶卡捷琳娜二世突然病故,没来得及宣昭,保罗一世意外当上皇帝,由长期的恐惧和憎恨到一夜之间君临天下的角色转换使这个心理扭曲的人变得乖戾残暴,穷兵黩武,引起人们的恐惧和不满,称他的统治是野兽的统治。梅列日科夫斯基在剧本中突出塑造心灵和人格几近分裂状态的保罗一世,他感觉自己就像是笼中的野兽,而皇冠就像荆冠,王位就像十字架,整个俄罗斯,整个欧洲命运的重负使他几近发疯。每当处于这样的状态,他就会想起一句话:“可怜啊!可怜的保罗!”这句话在剧中是保罗一世向自己的情人安娜讲起20年前在涅瓦河边的一幕而引出的:月亮照如白昼,保罗和库拉金走到参政院广场,库拉金落在后面,保罗“忽然感觉有人和他并排走着,我一看,这人高高的,穿着黑色披风,帽子压得很低,看不见脸,我问他是谁,这时他摘下帽子,我认出来他是彼得一世皇帝陛下,他长时间地看着我,苦楚而柔和地看着我,摇摇头,只说了两个词:‘可怜啊,可怜的保罗!’我倒下去,失去了知觉……”。(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1990b:70)
如同普希金笔下的青铜骑士离开基座飞跑起来一样,梅列日科夫斯基也运用非现实的手法强化这一神话意识,保罗一世渴望彼得大帝的庇佑和帮助,他反对母亲叶卡捷琳娜二世对自己的不公态度,继而反对她的所谓开明统治,他希望自己的才能和地位得到肯定。可是长期的压抑使他终日惶惶不安,为了自己的人身安全他命人修筑米哈伊尔城堡,并在城堡前建造了彼得大帝骑马征战的雕塑,尽管如此他仍然没有逃脱厄运,在住进城堡不久这里就成为他的葬身之地。在绝境中保罗一世总是不由自主地相信彼得大帝那神明一样的威力,但是青铜骑士只是一个象征符号,一个神话,一个强大的影子,彼得大帝已经主宰不了他身后俄国的一切。
《亚历山大一世》主要描写亚历山大一世在位的最后几个月,即从1824年3月11日到1825年11月20日,这期间人们都知道皇帝将死,作者对皇帝的病情也根据文献做了详细交待;《12月14日》围绕十二月党人起义事件展开,事件开始于1825年11月27日彼得堡人知道亚历山大一世去世,结束于1826年7月14日,即十二月党人被处决的第二天,在参政院广场举行安魂祝祷仪式。在小说创作中史实和史料作用的准确程度都得到强化,从人物到情节地点都有明确的现实依据,一些文献资料包括当时流行的笑话、格言俗语以及诗歌都被作者以人物话语或叙事语言引入文本,展现为当时彼得堡的社会风俗画,增加作品内容的时代感。随着亚历山大一世的去世,王位继承问题悬而未决,令民众感到俄国前途未卜,国家所有权像个私人物品被让来让去,国家的命运变成皇族的家事,这在接受过启蒙思想的十二月党人看来无疑是荒谬的。十二月党人虽然提出自己的纲领和主张,但是真正能把俄国引向何处,革命的意义在哪里,没有人能够确定;这一切的矛盾、徘徊、探索和思考都会被追溯到彼得堡的建城者——彼得大帝那里,而十二月政变事件正是发生在参政院广场,“彼得大帝”的眼前,在这种情况下作者更不可能不借助青铜骑士阐发自己的精神探索和事件的象征意义。
这两部小说的许多情节都通过瓦列里安·米哈依洛维奇·戈利岑公爵的视角和感受来加以呈现,他是十二月党人秘密协会成员之一,也是作者宗教思考的主要表达者。作者通过戈利岑的言行和思考赋予十二月革命宗教意义。在这位小说主人公眼里,彼得堡已经变成一个大坟墓,就像在《彼得与阿历克塞》中皇太子的预言一样。因为这里的专制统治、人工雕琢、上层社会的腐朽生活与建城之时以及后世在建筑工程中大批死去的工匠的阴魂给人以压抑和不详之感。
彼得堡腐朽的死气沉沉的生活正在期待着一场变革。戈利岑来到彼得堡后便投入紧张的密秘谋划工作之中,梅列日科夫斯基有意把每个活动地点都作了详细的交待,仿佛有意强调这里的每个建筑、每座小桥、每条运河和街道都在诉说着一个与俄罗斯命运相关的故事,都是正在发生的一切的见证者。小说中写道戈利岑和彼斯特尔“沿着新的海军部公园来到参政院广场,向青铜骑士雕塑走去”,“彼斯特尔绕过雕像,带着平静的好奇看着它,然后停下来,把脸贴向围栏,看着雕像的脸,就像看着一个活人的脸,沉默着,仿佛忘记了对方,最后用法语小声说:‘这里是一个深渊,如果马的前蹄落下,骑士就会万劫不复’……”;戈利岑说:“而马蹄下的蛇——就是叛乱、革命……”;彼斯特尔说:“而普希金说,俄国的革命从他(彼得大帝——引者注)开始”(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1990c:233-234)。这两个人物正在探讨彼得大帝对于俄国的意义。彼得当时根本无法预见到俄国以后发生的一切,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盲目的,但却富有某种神秘的启示和预言性。彼得大帝建城的意义不是一成不变的,西方也在进行着变化,不断发生着革命,涌动着革新的思潮,这是历史的必然,作为先进贵族阶级代表的十二月党人率先接受西方先进思想,看到俄国农奴制的弊端,希望改革立宪。在迷茫和焦虑之中,具有启蒙思想的十二月党成员下意识地相信在青铜骑士身上可能隐藏着关于俄国命运的预言。
2.2 大洪水神话:圣地一片荒凉
小说《彼得与阿列克塞》中,彼得从西方带来的文明和新鲜事物无不令民众和“长胡子的长老们”惶恐,那些散发着生命活力的异教神祗激发他们无穷的想像力,一时之间种种恐怖传闻到处流散。彼得是革新的沙皇,而他的儿子阿列克塞却是旧信仰的代表,那些两面派在彼得面前称彼得堡是一片乐土,背后对皇太子说这是“魔鬼的沼泽、鬼地方”。新旧思想、西方和俄国固有文化传统之间的斗争在各个领域都互不相让。作品开篇就描写1715年6月26日在彼得堡的夏园里安放从罗马运来的维纳斯雕像,庆祝“维纳斯节”的场景。彼得把这种庆典当作俄国的光荣,作为科学和艺术象征的女神维纳斯经过西方的文明之旅来到俄国,为俄罗斯开启启蒙和文明的进程。但是阿廖沙做的梦都和基督有关,他在梦中如同看到在红场和百姓一起庆祝基督进耶路撒冷的活动,又仿佛看到彼得的酗酒大联欢的队伍,仿佛他被人们遗弃,单独和基督在虫豸中间,被人践踏,圣地一片荒凉。圣母像一直是俄国最重要的圣物,会流泪的显灵圣母像正是俄国民众的骄傲和精神寄托,而彼得却在众目睽睽之下揭穿这只是个谎言,再一次挑战了人们的精神底线,引起更大的恐慌……而彼得堡大洪水仿佛印证了人们对于彼得种种“渎神”行为的传说,这种灾难被蒙上诡异的色彩。
彼得堡从开始建设起就饱受水灾之苦,300年来涅瓦河水患不断,差不多每5年左右就会发生一次。洪水成为与这座城市紧密相关的神话意象,它是人们潜意识里的一种隐痛,在具有迷信倾向的俄罗斯心智作用下笼上一种神秘气氛,而俄罗斯文学中彼得堡的大洪水也常常具有启示色彩。建城之初1703年的大洪水甚至卷走了准备修建彼得保罗要塞的建筑材料,给了雄心勃勃的彼得一世一个下马威,但就是这样仍然没有挫败他建立彼得堡的强大意志,因为他本人喜欢水,并且他“指望在这里能比任何地方更快地把自己的国民训练得熟谙水性”。(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1990a:130)普希金在《青铜骑士》中描写了1824年大洪水,把关于彼得堡的建城神话和神秘宿命推向极致。
梅列日科夫斯基在《彼得与阿历克赛》中描写了1715年11月的大洪水,也为关于彼得是反基督的种种可怕传说渲染恐怖气氛。“波涛席卷着破碎的平底船、倾覆的小船、原木、木板、房盖、整栋房架、连根拨起的大树和动物的尸体”。(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1990a:142)但在烘托彼得形象之中,在洪水肆虐的警示中,作者一方面描写彼得的暴戾强权性格,另一方面却突出彼得人格的复杂性,体现出梅列日科夫斯基式的二律背反的思想建构模式。“彼得一整夜没有休息,忙于从水中和火中救人。他像一个普通消防司令员那样钻进燃烧着的建筑物里,大火烧焦了他的头发,他险些没被倾落下来的大木头轧死。他帮助穷人从地下室的住宅里抢救不值钱的家当,站在没腰深的水里,冰凉刺骨,浑身直打哆嗦。他跟所有人共赴艰险,鼓舞了所有的人”。(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1990a:143)可以看出,尽管梅列日科夫斯基以自然主义的笔法描写彼得的种种怪异,他以自己的强硬统治几乎取消东正教会,但作者仍然认为彼得是影响俄国发展和宗教进程的超人——梅列日科夫斯基关注的是这位历史巨人对于俄国和世界宗教的意义,彼得对旧的历史基督教是一个否定因素,因此人们称他是反基督,但对于人类走向真正的宗教真理却是一个积极的因素。
大洪水在犹太教神话和希腊神话中都存在,都由神对人类罪恶的愤怒而起,因此大洪水是人类毁灭的象征,代表神的惩罚。而彼得不但以强大意志对抗“神意”,而且能够对普通百姓实施救赎——这个半人半神的形象在梅列日科夫斯基笔下的确是作为历史的超人出现的,他对于俄国和基督教的意义是潜在的。借助大洪水的神话,梅列日科夫斯基把彼得堡神话内涵与自己的宗教理念相结合,他认为,彼得堡的建立以及彼得大帝这一历史巨人的渎神性恰恰也是俄国新的基督教道路的开始,俄国将在对传统的腐朽的基督教的否定之后迎来真正的地上自由王国,这是一个未来基督的“圣灵王国”,它不但是俄罗斯所期待的,而且将是全人类的福音。
3 结束语
彼得堡自诞生之日起就充满神话和传奇,它的启示录和末世论色彩已经成为无数作家艺术直觉中的一个幻影。在长期的民族文化心理积淀和作家的创作意识的相互作用下,彼得堡已经成为一种特殊的俄罗斯精神文化符号。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创作赋予彼得堡神话以本体的意义,他不但雄辩地创造一种全新的认知超验实在的方法——神秘的历史辩证法,而且把彼得堡作为俄罗斯宗教精神之路的启示之城,挖掘、再现、发挥和重构与之相关的种种神话。他在小说文本的字里行间,借助彼得堡的现代神话阐明自己的文化理念和宗教哲学思考。
金亚娜.普希金文学遗产的普遍人类价值[J].外语学刊,1999(3).
劳里·杭柯.神话界定问题[A].阿兰·邓迪斯.西方神话学读本[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Milcolm V.Jones,Robin Feuer Miller.The Cambridge Compation to the Classic Russian Novel[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Лосев А.Ф.Диалектика мифа,из ранни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M].М.:《Правда》,1990.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Д.С.Петербуг быть пусту...[A].Исупов,К.Г.Москва-Петербург:Pro et contra.Диалог культур в истор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самосознания[C].СПб:Русского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2000.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Д.С.Собрание в четырёх томах,том 2[M].М.:《Правда》,1990a.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Д.С.Собрание в четырёх томах,том 3[M].М.:《Правда》,1990b.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Д.С.Собрание в четырёх томах,том 4[M].М.:《Правда》,1990c.
Мосейко,А.Н.Миф России:мифологические доминанты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йской ментальности[M].М.:Институт Африки РАН,2003.
Топоров В.Н.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текст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M].СПб.:“Искусство—СПБ”,2003.
Хализев,В.Е.Тео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M].М.:Высшая школа,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