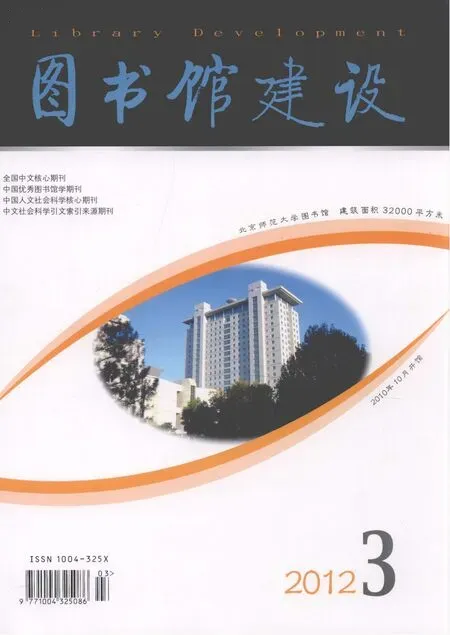文学作品导读中的“第二文本”发现
袁曦临 (东南大学情报科技研究所 江苏 南京 210096)
陈 霞 (东南大学图书馆 江苏 南京 211189)
巴特勒在《图书馆学导论》中指出,“图书是保存人类记忆的一种社会装置,图书馆是把它移入活的个人的意识的一种社会机构。”[1]图书或者其他载体形式的文本只是实现了人类文化的有效储存功能,为文化的继承和创造提供了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阅读是人类的一种认知过程,是其探索未知、创造自我的有效途径。因此,只有通过阅读,才能使文献的意义得以显现,并使文化的继承和创造成为可能。
导读是促进、推广阅读的一种方式,也是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是一个综合性的教育过程,也是一项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导读在我国图书馆工作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其理论基础是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宗旨的中国古代目录学。近代目录学家余嘉锡在其所著的《目录学发微》中写道:“目录学为读书引导之资。凡承学之士,皆不可不涉其藩篱。”[2]可见,古代学有所成的学者,无不得益于书目的指导。
西方阅读理论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迅猛,尤以接受阅读理论最为突出。沃夫尔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和汉斯·罗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在20世纪80年代创立了接受阅读理论,研究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接受和反应,并把目光转向了对文本与读者关系的研究[3]。
1 20世纪80年代阅读理论的发展
阅读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之所以得到巨大的发展,有其深刻的哲学背景,可以追溯到德国现代哲学解释家、解释学美学的创始人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年)[4]。他认为所谓理解的过程是文本世界与读者世界的融合过程,是创作实践与接受实践的融合过程[4]。早期的解释学只是针对圣经进行解释,认为文本的意义就是上帝的意旨。随着文艺复兴及人的理性意识的觉醒,解释学开始由对神学的阐释转向对作者的阐释,认为阅读就是重建或探究作者的创作原意或意图。
伽达默尔所开创的解释学对文学研究的非凡意义在于,为文学作品拓展出了一个全新的意义世界,即不同读者在面对同一部作品时,可以读出一个自己所理解的意义世界,因而极大地挖掘了作品意义的深度和广度,也为读者的阅读开拓出一个新的世界[5]。可以说,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对于我们今天认识阅读和导读的本质有着极为深刻的意义。作为伽达默尔的学生,姚斯和伊瑟尔认为文本和读者之间应是一种互动的关系[6]。读者以自己的审美经验创造性地理解文本,将文本转换为带有个人色彩的语意和形象,并在这一过程中获得阅读的快感,与此同时,文本也对读者施加了影响,帮助读者积累审美经验。因此可以说,阅读理解是一个创造性的转换过程,能够超越作者的本意。
在接受阅读理论中,有两个重要的概念,即“期待视野”和“召唤结构”。所谓“期待视野”,就是读者在阅读某一部作品之前原本就具备的生活体验、文化传统、审美经验及理解能力等;而“召唤结构”是作品向读者提示或暗示的东西,是作品给读者留下的联想和创造的空间。正是“召唤结构”促成了读者通过合理的主观想象去补充并完成作品的二度创作。
“召唤结构”在文学作品中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空白”和“空缺”。所谓“空白”,即指作品中没有明确写出来的或隐含、暗示的部分,类似于中国画中的“留白”;而“空缺”则是文学作品中另一种常见的表现形式,即读者阅读时发现作品在某些情节或人物的发展中显现出的一种缺失或断层,会给阅读造成某种程度的顿挫。相对于“空白”,“空缺”较难发现,它如同文本中的隐性结构,需要有阅读能力和文化素养的读者通过自身的体验和理解去“还原”和“显现”[7]。
接受阅读理论虽然来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社会,但其理念和思想方法并非仅为西方独有。事实上,早在宋代,洪迈在《容斋续笔》中就提出:“经典义理之说最为无穷,以故解释传统,自汉至今,不可概数,至有一字而数说者。”[8]自古以来,中国传统读书人的读书方法有两种:一是“我注六经”,二是“六经注我”。所谓“我注六经”,就是通过旁征博引求证经书的本义,以做到“无证不言,文本还原”;而“六经注我”,则是在前者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对原始经文加以深入挖掘,用六经来解释自己的思想,引申发挥,提出新的创见。因此从学理上讲,“六经注我”与西方的阅读接受理论相一致。
2 图书馆导读的4个要素
如果把阅读接受理论应用到图书馆导读领域并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图书馆导读涉及到4个要素:读者、阅读文本、导读工具与方法、导读者,这4个要素构成一个完整的阅读系统。本文将对其进行系统阐述。
2.1 读者
伽达默尔指出:“艺术作品的存在就是那种需要观赏者接受才能完成的游戏。”[4]从现象学角度看,文本的视角汇合点与读者的立足点都是虚在的,需要依靠读者的“结构化行为”(即阅读行为),才能将文本和读者实在化。所以,《小世界》的作者英国小说家戴维·洛奇才会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是一种游戏,一种至少需要两个人玩的游戏:一位读者,一位作者。”[9]这种比喻形象地阐述了作品和读者之间的关系,类似于棒球运动中投手和捕手的关系:投手负责“发送”,而捕手的责任是“接住”。至于如何发送和接住,则依赖球手的水平和玩法。“文本”就像棒球一样,是被投手(即“作者”)和捕手(即“读者”)双方所共有的,由一方开始,另一方终结。
2.2 阅读文本
“文本”(text)一词从概念定义上看,是指书写或印刷的文件或原文。但从词源学上看,可以发现它的词根“texere ”表示编织物、纺织品。可见“文本”原本就包含结构的涵义。
在接受阅读理论看来,一个作品一旦出版,虽然从文本形式上讲不再发生改变了,除非作者再次修订,但作品并不是封闭、固定不变的。从文本的内涵意义方面讲,其是一个面向读者开放的意义结构,其中包含着隐喻、不确定性,乃至空白点。这些“留白”、“言下之意”及春秋笔法,不断向读者发出召唤,呼唤着读者去聆听,去发现和填补,而有水平和能力的读者总会基于自身独特的视觉体验和视角,对文本的空白进行不同的填补,从而形成属于读者自己的独一无二的阅读文本,即相对于作家创作出的“第一文本”作品而言的“第二文本”。任何作品经读者阅读后都会在读者心中产生不同的理解。这种理解凝结了读者的心理、经历和体验。因此,“第二文本”是一种有别于第一文本的新的对象化的作品。
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要读经典作品?》中说:“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从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10]其原因就在于,经典作品留有足够多的“空白点”,而这些“空白点”向读者发出邀请,让他们运用自己的体会、经验、阅历乃至想象去解释和填补这些“空白点”,当这些“空白点”被填补后,文本便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因此可以说,每一部文学经典的身后,都拖着长长的影子。这重重叠影正是无数读者读出的“第二文本”。
2.3 导读工具与方法
书目是图书馆导读的重要工具。书目在文化过程中通过收录与编排文献来实现积累和保存文化的功能。例如,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就系统地整理评介了600余种西文图书,内容涉及政、经、史、社会、科技等多领域,用以传播西方的新思想和新知识,并在书目表中采用书前加圈的方式来说明某种图书的重要,劝导大家“择其要而读之,于世界蕃变之迹,国土迁异之原,可以粗有所闻矣”[11]。因此,书目是一种图书馆导读常用的方法,即通过编写内容提要或简洁说明,为读者指定读书范围,指明好的版本,指示读书方法,指点目录中所列图书之间的联系,引导读书的缓急先后。
长久以来,图书馆在开展导读工作时,最主要的导读工具与方式就是“导读书目”。但实践证明,“导读书目”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原因在于以下几种书目的大量存在。
(1)万金油式导读书目 范围过于宽泛,把公认的经典著作一一罗列,不考虑读者阅读需求和阅读基础的不同,也不考虑读者的性格、年龄与兴趣的差异,这一类型的导读书目虽然是由不同的图书馆提出的,但大多相似,千篇一律。
(2)深井式导读书目 不考虑读者的学科方向和知识积累,没有梯度,不分等级,并且所列书目过于专深,使读者尝试之后,感觉难度过大,遂望而却步。
(3)学者专家导读书目 有许多图书馆会邀请著名的教授、学者推荐导读书目。荐书者虽德高望重、学术成就斐然,但推荐的书目往往反映的是他们自己的关注点和志趣,对于大部分读者缺少实际的参考价值和吸引力。
笔者认为,在图书馆导读的实践中,普遍存在居高临下、忽视读者的倾向,因而导读效果并不理想。接受阅读理论对 “读者”的高度重视和重新发现,恰恰为图书馆导读的实践指明了调整和改进的方向,即将导读的重心转向读者对作品的阐述及读者之间阅读经验的交流和分享。
2.4 导读者
导读者具有两种类型。
(1)导师式 即导读者以其凌驾于读者之上的主观意识形态来指导读者阅读,读者在接受阅读指导的同时,也会接受导读者的意识和观点,或会受到导读者的意识影响;19世纪的图书馆服务理念带有强烈的“以图书和阅读教化社会”的理想主义色彩,认为好书和阅读可以净化人的心灵,提升思想和道德素质。这一阅读理想和导读理念直至今天依然是我国图书馆员进行导读教育和阅读促进活动的依据和出发点,因而这类导读馆员致力于筛选和推荐好书,培养读者的阅读习惯和能力。
(2)主持式 即导读者只是承担和负责阅读活动的组织,向读者提供尽可能广泛和全面的读本和选择,而把判断、选择阅读的权利交给读者。他们认为读者选择读什么或者怎么读是其的天赋权利。从本质上讲,这一类型的导读者受到的是西方自由主义理念、文化相对主义理念及阅读接受美学思想的影响,其在西方图书馆界居于主要位置[12]。
3 导读教育中的“第二文本”发现
冈特·格里姆(Gü nter Grimm)在《接受美学研究概论》中提出“第二文本”产生的理论前提为“S= A + R”。其中,S是指作品的意义,即文本的意义结构;A表示作者赋予的意义,由于作者一旦完成作品,即不能再在文本中开口发言,因此A的涵义是相对稳定的;R是指接受者所理解、领悟和发现的意义,由于不同读者的文化水平、阅历、眼界及领悟能力的不同,因此,R是存在差异和变化的,换言之,R的意义可以在读者的参与下得到无限延伸[13]。阅读同一作品的读者,他们面对的“第一文本”都是相同的,但阅读之后所产生的“第二文本”,则会因人而异。所以,从读者接受这个层面来看,“第二文本”的意义可能是无限的。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的是《易》,才子看见的是缠绵,革命家看见的是排满,流言家看见的是宫闱秘事[14]。读者眼光不同,看出的命意就各异,领悟到的意境更是各有千秋。面对同一文本,不同的接受主体可以有不同的“再创造”,使该作品具有不同的意义,也就有了“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说法。
读者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包含了两个阶段:(1)读者进入作品营造的环境和时代,在作者的引导下,对作家创造的人物和世界进行还原、经历和情感体验。(2)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保持理性和清醒,与作品进行交流,对作品进行填空、批评,甚至反驳。
由于每个人的文化观念、阅历、个人喜好等存在差异,其阅读经验和期待视野自然不同。读者阅读某一作品的过程,也就是读者自身的“期待视野”和文本相遇,进而开始读者和文本之间相互认识、彼此交流和沟通的过程。这一过程赋予了作品当代性和个体性,从而在交流中产生出新的意义。“第二文本”正是在读者期待视野和文本的召唤结构的互动中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作品需要读者创造性的诠释,唯其如此,其生命才可得以延续。
目前,国内图书馆开展的导读活动基本上采取“导师式”导读方法。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的会刊《今日阅读》正是这一类型导读的代表。其重点放在提倡读什么书,邀请学者和专家讲述怎么阅读及列出导读书目、推荐书目等,导读活动主要是围绕“第一文本”展开的。
众所周知,网络环境中信息传播和交流的最重要特点就是草根性、自主性和交互性,在Web2.0、Web3.0环境下成长的年轻群体,他们早已不满足于被告知和被动阅读,期待更多地参与信息的创造、传播和分享。
在此背景下,图书馆的导读服务如果仅仅强调“第一文本”显然是不够的,需要更重视“第二文本”的发现和开放性阅读,以读者之间相互交流的自己的体验和感受来促使阅读的推广。因此,图书馆的导读服务应该致力于发现阅读中的“第二文本”。
4 “第二文本”的边界
“第二文本”是属于个体的、私人的、非精英化的。在读者中心主义下, 文本的本意很有可能被读者的主观体验所掩盖,被再次建构、改变,容易削弱、曲解作者的本意,陷入解构主义的泥潭,使阅读失去根基,甚至可能产生“喜儿为什么不嫁黄世仁”这样离奇的疑问。对于经典作品来说,这种曲解降低了经典的价值。那么,“第二文本”的边界在哪里呢?如何找到文本对解读的限制和解读自由度之间的契合点呢?
对于这一点,伊瑟尔曾做过明确的说明:“不确定性与空白并不是文本中不存在的或可以由读者根据个人需要任意填补的东西, 而是文本的内在结构中通过某些描写方式省略掉的东西,它们虽然要由读者运用自己的经验和想象去填补,但填补的方式必须为文本自身的规定性所制约。”[15]因此,对于“第二文本”的强调,并不意味着读者可以凌驾于文本之上。如果以探寻“第二文本”为名,放弃、忽视文本无疑是错误的。
小说《玫瑰的名字》的作者、意大利符号学家安贝托·艾柯(Umberto Eco, 1932-),就对文本的泛滥无拘的诠释表示过忧虑。他认为开放性阅读一定是从作品出发的,它必须受到文本的制约,要有所规范[16]。他指出,对于文学的诠释不是无限的,丧失了鉴定的尺度必将导致诠释的失控,并且无限的衍义只能扰乱文本的解读,从而使作品陷入虚无[16]。
对于图书馆开展的阅读导读活动来说,在推动读者挖掘和发现“第二文本”的过程中,必须要遵守以下原则。
(1)必须围绕“作品的意图” 读者的解读不能将文本甚至文本中的片段孤立起来,以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态度加以阐释,造成对作品文本的曲解。
(2)承认诠释的客观真理性 即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应有相对确定的、为多数人接受的共同诠释。在读者进行“第二文本”的阅读过程中,要注意符合作品产生的时代、社会和民族,阐述和解读应与其他历史和社会的证据相吻合。
(3)强调作品的历史文化语境 历史文化语境不仅包含了作者创作当时的历史环境,也包含了作者所领悟和感知的所有过往历史的文化积淀。脱离语境,就不可能有作品的产生。因此可以说,语境是作者创作作品和读者阅读作品的依据和基础,作品的历史文化语境是作品人物、情节发展的内生环境和内在运行机制。
以上3点是图书馆进行开放式阅读导读必须遵守的原则和把握的尺度。反之,脱离了作品的原意、当时的文化价值观及语境,妄言“第二文本”的发掘和发现,就一定会陷入解读的泛滥和诠释的虚无,成为“戏说”。
5 结 语
阅读行为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阅读是人类诸多交流形式中,相对于写作行为维度不可或缺的另一维。阅读使得作者的写作、作品的意义得以实现。在作品的阅读感知活动中,没有人,文学作品形同黑夜。只有读者和作品之间对话式的感知交流活动,才照亮了作品文本;反过来,作品通过被感知和交流,又拓展和照亮了读者的阅读。面对信息社会中人们的阅读环境、阅读载体、阅读方式和阅读能力的巨变,图书馆必须要调整传统导读的内容与方式,并在此过程中寻找阅读理论和导读方式的创新和发展。这也是图书馆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标志之一。
[1]张大英.巴特勒《图书馆学导论》述评[J].图书馆, 2011(5):42-44.
[2]彭斐章.迎接信息时代的科学:目录学的现状与未来[J].图书与情报, 1989(4):1-6.
[3]潘智彪.读者·作品·召唤结构[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2):44-49.
[4]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阐释学的基本特征[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21l.
[5]王志强.从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原理看阅读的本质[J].语文学刊,2008 (2) : 57-60.
[6]金元浦.当代文艺心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32-235.
[7]伊塞尔.阅读活动:审美反应理论[M].金元浦, 周 宁,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215-220.
[8]曾祥芹.文章阅读学[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240.
[9]罗礼太,吴尔芬.故事的价值[J].当代文坛,2006(6):32-34.
[10]谭 帆,张福贵.大学语文:人文社科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09:281
[11]黄 涛.论梁启超《西学书目表》的目录学成就[J].学术界,2007(2):293-300.
[12]于良芝.图书馆学导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184.
[13]马新国.西方文论选讲[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500-520.
[14]鲁 迅.集外集拾遗补编[G]//林 非.鲁迅著作全编:第 3 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369.
[15]郭宏安,章国锋,王逢振.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327.
[16]艾 柯,柯里尼.诠释与过度诠释[M].王宇根,译.第2版.北京:三联书店,2005:24-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