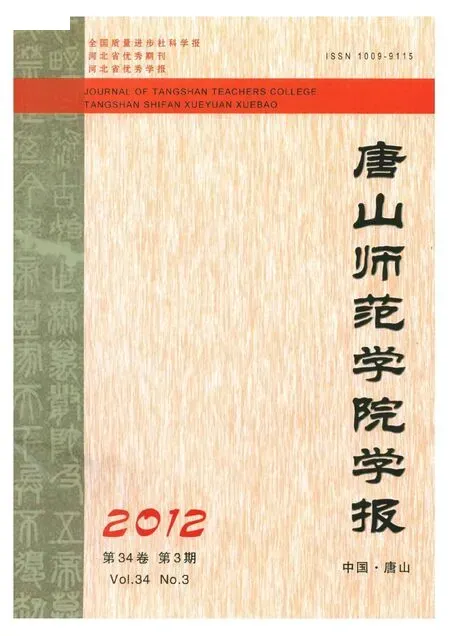论《道连·葛雷的画像》中的互文性和异质性
刁俊春
(嘉兴学院 外国语学院,浙江 嘉兴 314001)
论《道连·葛雷的画像》中的互文性和异质性
刁俊春
(嘉兴学院 外国语学院,浙江 嘉兴 314001)
从互文性和异质性两个方面解读小说的美学和伦理学意义,说明文本的多重声音和现代性特征。
道连·葛雷;画像;互文性;异质性;美学;伦理学
奥斯卡·王尔德(1854-1900)是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天才、思想巨匠。他短暂的一生为人类的精神宝库留下了珍贵的遗产。他的诗歌、戏剧、童话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他唯一的长篇小说《道连·葛雷的画像》(1891)从问世起就引发无数评论关注,至今不衰。评论的焦点往往都是集中在美与伦理两个方面,余光中先生对小说的评论是:“兼有美学与伦理的多重意义”[1]。本文试图从这部小说的互文性和异质性入手,说明奥斯卡·王尔德对经典文本的模仿与创新,进而深入探讨这部小说的美学和伦理学的多重意义。
一、互文性视角
互文性的概念是由法国学者克里斯蒂娃提出的,定义为:“互文性意味着任何单独文本都是许多其他文本的重新组合;在一个特定的文本空间里,来自其他文本的许多声音互相交叉、互相中和。”[2]
奥斯卡·王尔德天资过人,勤奋有加,在文学氛围浓厚的家庭中长大,又在著名学府受名师指点,古典文化造诣颇高。从上大学起,就广泛结交文学友人,同当时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的许多文学家、艺术家交往甚密。据维维安·贺兰(王尔德次子)所述:王尔德大多数严肃作品都在位于伦敦泰德街十六号的房子里写成,书房里的书桌原属于托马斯·卡莱尔,书房内满是书籍,“有希腊与拉丁文古籍,法国文学与当代欧洲知名作家亲自馈赠的作品”[1,p52-53]。以上事实表明:王尔德的创作离不开他的文本阅读和对经典的思索,所以,如果我们可以从《道连·葛雷的画像》中明显地看到其他作品的影子,听到“其他文本的声音”,就不会感到奇怪了。荣如德先生认为,究其渊源,《道连·葛雷的画像》的文本基础有巴尔扎克的《驴皮记》、戈蒂埃的《莫班小姐》以及《浮士德博士》等[3,p8]。笔者结合美学与伦理学,用另外三个文本来探讨《道连·葛雷的画像》中的互文性。
第一个文本来自凯尔特文学。王尔德研究专家彼得·阿克罗伊德在他的获奖作品《一个唯美主义者的遗言——奥斯卡·王尔德别传》中提起了这个文本:
凯尔特文学中有一个年轻的国度,叫做提尔南-奥格。这里既没有衰老也没有死亡;既没有眼泪也没有空洞的笑声。吟游诗人奥依森为了打探此地的奥秘,在黑暗的掩护下走到这里。他找到了这个迷人的国家,在那里生活了三百年。但他开始怀恋原来的生活,怀恋他出生的国家,最后沿着来的路回去了。他的脚一踏上故土,那三百年的生活立即成了他的重负。他的身体佝偻得无以复加,在这段漫长岁月里所发生的人世忧患也压到了他的身上。[4]
这一段文字似乎也暗示了人类对永恒和不朽的追求,以及因为这一追求给自身带来的痛苦与灾难。这一主题也契合了《道连·葛雷的画像》中道连·葛雷因为对永恒的年轻与美的追求而最终自我毁灭的人生历程。小说临结尾时,道连·葛雷幡然醒悟:
哎!当初他在虚荣和欲望的一时冲动下,祈求上苍让画像代他承受年龄的负担,使他自己永葆光华照人的青春。想不到那一刹那竟成千古恨……
正是他的美貌毁了他,正是他祈求来的美貌和青春葬送了他……事实上,他的美貌不过是一张面具,青春则成了笑柄。[3,p236]
第二个文本来自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以第十八首“能不能让我把你比作夏日”为例:
能不能让我把你比作夏日?/你可是更加可爱,更加温婉;/狂风会吹落五月里开的好花儿,/夏季租出的日子又未免太短暂:/有时候苍天的巨眼照得太灼热,/他那金彩的脸色也会被遮暗;/每一样美呀,总会离开美而凋落,/被时机或者自然的代谢所摧残;/但是你永久的夏天决不会凋枯,/你永远不会失去你美的形象;/死神夸不着你在他影子里踯躅,/你将在不朽的诗中与时间同长;/只要人类在呼吸,眼睛看的见,/我这诗就活着,使你的生命绵延。
莎士比亚在这首诗中探讨了自然美景的易逝,从而衬托艺术的永恒与不朽。在《道连·葛雷的画像》中自然的美景变成了道连·葛雷的青春,艺术的形式由诗变成了一张画像。小说中,道连·葛雷看着完工的画像,想起了青春的易逝:
是的,总有一天他的容颜会起皱、憔悴,他的眼睛会黯淡、褪色,他的体态会拱曲、变形。鲜红的色彩将从他的嘴唇上脱落,金黄的光泽将会从他的发丝上消失。生命本当造就他的灵魂,结果把他的肉身破坏了。他将变成一个毫无风度的丑八怪。[3,p29]
道连·葛雷感叹道:“太可悲了!我会变得又老又丑,可是这幅画像却能永葆青春。它永远不会比这六月的一天年龄稍大……”[3,p30]
同时,这首诗也涉及了男性的美以及男性之间的爱,这一点在莎士比亚一些其他的十四行诗里也有表现。而对男性的美以及男性之间的爱的描写相比较于含蓄的莎士比亚,王尔德就直白多了。
第三个文本来自柏拉图的《对话集》。柏拉图在《理想国》的第二卷中谈到了“正义和不正义的本质时”,讲了一个“随心所欲”的故事:一个牧羊人,无意之中得到一枚金戒指,获得了隐身的本领。于是,他想方设法谋到一个职位,当上了国王的使臣。到了国王身边,他勾引了王后,跟她同谋,杀掉了国王,夺取了王位。照这样来看,假定有两只这样的戒指,正义的人和不正义的人各戴一只,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想象,没有一个人能坚定不移,继续做正义的事,也不会有一个人能克制住不拿别人的财物,如果他能在市场里不用害怕,要什么就随便拿什么,能随意穿门越户,能随意调戏妇女,能随意杀人劫狱,总之能象全能的神一样,随心所欲行动的话,到这时候,两个人的行为就会一模一样。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证明没有人把正义当成是对自己的好事,心甘情愿去实行,做正义事是勉强的。在任何场合之下,一个人只要能干坏事,他总会去干的。大家一目了然,从不正义那里比从正义那里个人能得到更多的利益。
这个“随心所欲”的故事表明人如果能够做坏事而不会受到惩罚,多半会远离正义的。《道连·葛雷的画像》里,当道连·葛雷发现画像就是那枚“金戒指”时,他的堕落就注定开始了:
他觉得,现在确实到了必须作出抉择的时刻。也许,他的抉择已经做出了?是的,生活本身以及他自己对生活无限的好奇心已代他做了决定。永不憔悴的青春、无法满足的欲望、神秘奥妙的享受、如醉如狂的快乐和更加疯狂的堕落——一切都将为他所有。而他的耻辱的重荷将由肖像承担:就这么着了。[3,p113-114]
上述的三个文本都谈到了美和伦理,小说《道连·葛雷的画像》在文本中不时传出这三个文本的声音,不过小说更大的魅力来自其自身的一些异质的声音。
二、异质性解读
希利斯·米勒指出:“对文本最佳的解读就是对文本的异质性作出最好的解释,他展示出一组明确的可能的意义,这些意义系统地互相联系,有文本控制,但在逻辑上却是不协调的。”[5]《道连·葛雷的画像》中对美和道德伦理的论述就不是统一协调的,从而使文本系统的稳定性受到挑战,解释的多重可能性得以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尔德超越了维多利亚时期,正如加尼尔(Regenia Gagnier)在《王尔德与维多利亚人》(Wilde and the Victorians)中所说:“王尔德,一个充满悖论和矛盾的人,不但参与了现代价值的批判,同时也具有了后现代的视角。”[6]陆建德先生认为小说“体现了英国唯美主义运动和王尔德人生经历中的内在矛盾”。他在逝世前不久给自己想好了永久的称号:“声名狼藉的牛津圣奥斯卡、诗人、殉道者”[7]。乔治·伍德科克说他“在本质上是一种分裂型人格”:既是一个深刻的文艺思想家、“社会批判者”、预言家,又是一个故做姿态的美学小丑、“势利眼”、“纨绔子”[8]。以下,笔者就小说文本中王尔德在美与伦理道德两方面的悖论和矛盾来讨论小说的异质性。
正如托马斯·曼所说:“说到底,世界上只有两种基本态度或观念:审美的和道德的。”[7]那么,王尔德的态度到底是审美的还是道德的?笔者认为,对王尔德不能用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王尔德未必总是“唯美”,《道连·葛雷的画像》也不完全是一部道德寓言。王尔德多次说过:“悖论之道乃真理之道。”
王尔德在美的追求上体现的异质性是显而易见的,陈瑞红指出:王尔德,“兼有才子和庸人气质”,他的美学现象中存在着“先锋冲动与媚俗效应之间的矛盾对立”,他的唯美主义美学内部“蕴涵着崇美和媚俗的悖论。”[8]
王尔德崇美的态度在《道连·葛雷的画像》的“自序”中得到表明:“在美的作品中发现美的含义的人是有教养的。这种人有希望。认为美的作品仅仅意味美的人,才是精英中的精英。”[3,p3]多年以后,在王尔德控告昆斯伯里侯爵诽谤案的庭审现场,面对爱德华·卡森的询问,王尔德的回答也表明了他的崇美态度:
卡森: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按照你的观点,无论一本书的内容多么不道德,只要写得好,那就是好书?
王尔德:是的,如果写得好,自会产生一种美感,美感是人能够获得的最高感受。[9]
但是,王尔德这种崇美的态度首先从本质上就不是纯粹的,有其媚俗的成分,不总是“为了艺术而艺术”,而往往是“为了金钱而艺术”。例如,小说的第12章有大段文字描写“感官的崇拜”:香精、音乐、珠宝、绣品和挂毯等,这些描写主要还是为了迎合英国上层社会对奢侈的向往。文中大量新颖的似是而非的悖论说到底都有纨绔子弟式的哗众取宠之嫌[10]。其次,王尔德这种崇美的态度并不是一贯而终的。小说文本中就有大量的例子表明,美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高的。其中,小说的结尾处道连对美的反思最能说明这一点:
人是不是真的永远改变不了啦?他无限缅怀自己白璧无瑕的少年时代——亨利勋爵一度称之为白玫瑰般的少年时代。道连知道自己玷污了自己,腐蚀了心灵,毒化了想象;知道自己对别人产生了坏影响,而且从中获得了一种残忍的乐趣;知道自己结交的人中间禀性最纯洁、前途最光明的人都被他引入歧途而身败名裂。[3,p236]
最后他意识到“正是他的美貌毁了他”,“美貌不过是一张面具”[3,p236]。
同样,小说的异质性还体现在王尔德的伦理道德观上。王尔德在自序中写道:“书无所谓道德的或不道德的”,“艺术家没有伦理上的好恶。艺术家如在伦理上有所臧否,那是不可原谅的矫揉造作”,“一切艺术都是毫无用处的”[3,p3-4]。这些论述可以表明王尔德的非道德倾向。小说出版后,针对英国报业对小说“反道德”的指控,王尔德辩护道:“艺术的范畴与道德的范畴是截然不同的。”并声称:“从艺术的观点来看,坏人是非常吸引人的研究对象。”[1,p68-69]
但是,从一定程度上,小说也可以解读为道德寓言。陆建德指出:“虽然《道连·葛雷的画像》在出版后被认为不道德(该书序言为批评者提供了炮弹),现在读来,小说中的道德寓意是大致清晰的。”[7]雷纳·韦勒克认为,《道连·葛雷的画像》“展现了一幅道德败坏遂遭惩罚的寓意画,而非一篇为审美生活而作的辩护”[7]。
小说文本中伦理的声音不时通过画家贝泽尔·霍尔渥德传出,玩世不恭的亨利·沃登勋爵除了不时从道德上误导道连以外,自身并没有做过非常不道德的事,只有道连自己在画像这枚“金戒指”的掩护下,犯下累累罪行,而他最终的死亡也是作者对正义的伦理诉求。道连的内心一直是充满矛盾的,亨利·沃登勋爵和贝泽尔·霍尔渥德在他灵魂深处一刻不停地斗争着,表面上,前者占了上风,实际上,后者更加深入道连的内心。道连有一次对贝泽尔说:“我很喜欢亨利。不过我知道你比他好。”[3,p119]“亨利白天尽说不足信的话,晚上尽做不可能的事。这正是我喜欢的那种生活。不过,万一我遇到什么患难,我大概不会去找亨利。我多半会找你,贝泽尔。”[3,p125]
詹姆斯·韦恩的死最终让道连意识到了自己的罪恶,有了忏悔之心,于是对亨利勋爵宣布要重新做人。道连说道:“我一生作的孽太多了。以后我再也不干了。”[3,p214]小说临结尾时,他更是意识到自己“应该自首,应当为人所不齿,应当受到社会的制裁,这是他罪有应得。”[3,p238]然而,他最终还是道德感模糊了,他想毁掉画像——他的罪证,也是他的良心。毁掉了良心,也就毁掉了肉体。这一点似乎在讲一个寓言:人是无法离开道德而存在的;美也无法完全独立于道德。
三、小结
《道连·葛雷的画像》是建立在一些文学经典的基础上完成的,回应了古希腊柏拉图关于正义与善的思辨,呼应了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的美学思想,也顺应了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体现了文本的互文性。同时,小说中不同的美学思想、互为矛盾的伦理观念又使小说充满张力和异质性,从而具有了现代主义小说的特色。
[1] 维维安·贺兰.李芬芳,译王尔德[M].上海:百家出版社, 2001.
[2] 殷企平.重复[J].外国文学,2003(2):60-65.
[3] 奥斯卡·王尔德.荣如德,译.道连·葛雷的画像[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4] 彼得·阿克罗伊德.方柏林,译.一个唯美主义者的遗言——奥斯卡·王尔德别传[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129.
[5] 秦旭.希利斯·米勒文学解构的“异质性”维度[J].外语研究,2010(6):93-96.
[6] Regenia Gagnier. Wilde and Victorians[C]. Raby, Peter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Oscar Wilde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18-33.
[7] 陆建德.“声名狼藉的牛津圣奥斯卡”——纪念王尔德逝世100周年[J].外国文学评论,2000(2):76-85.
[8] 陈瑞红.媚俗:王尔德的一个美学困境[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4):98-102.
[9] 孙宜学.王尔德审判实录[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66-68.
[10] 周小仪.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王尔德的矛盾性及其社会意义[J].外国文学评论,1994(3):95-101.
(责任编辑、校对:任海生)
On Intertextuality and Heterogeneity in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DIAO Jun-chu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axing University, Jiaxing 314001, China)
This paper uses a new approach to analyze the novel’s aesthetic and ethical meani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textuality and heterogeneity, attempting to demonstrate the multiple voices in the text and its modernist features.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Intertexuality; heterogeneity; aesthetics; ethics
2011-11-15
刁俊春(1978-),男,安徽含山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英语文学、西方文论。
I106.4
A
1009-9115(2012)03-003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