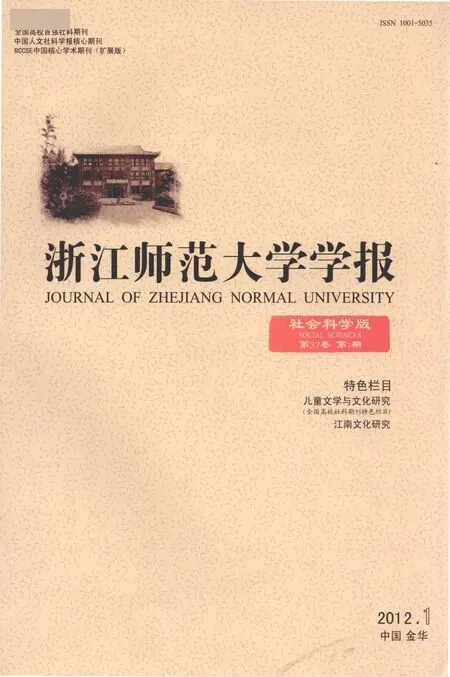受虐的身体与受控的主体
——论王小波小说的虐恋描写及其实质*
张川平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河北 石家庄 050051)
“虐恋”作为社会学术语源自潘光旦的译法,据李银河在《虐恋亚文化》一书中的介绍,“虐恋”这个词英文为sadomasochism,有时又简写为SM、S-M、S/M或S&M。她对“虐恋”的定义是这样的:“它是一种将快感与痛感联系在一起的性活动,或者说是一种通过痛感获得快感的性活动。”[1]6“是痛感与快感的结合”,痛感不仅指“肉体的痛苦”,也包括羞辱等引起的精神痛苦。社会学视域中的虐恋活动又被称为“成年人的游戏”,参与者有日渐增多的趋势(不排除潜在参与者不断曝光的因素),发展成为一种“神秘”而“有趣”的社会现象,它大大丰富了社会生活中人际关系的可能性和多样性。正如李银河所言:“虐恋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类性倾向,对于理解人类的性本质与性活动、对于理解和建立亲密而强烈的人际关系、对于理解社会结构中的权力关系、对于理解一般人性及人的肉体和精神状况,都颇具启发性。”[1]2这虽是一种社会学的界定和判断,但对于理解文学作品中的相关描写不无裨益,比如,有关“虐”的叙事,是仅仅围绕“性”还是最终指向“人”,是基于生理本能和自我选择的“性倾向”,还是被迫就范的“生存方式”,等等,就是有待我们仔细辨析的核心问题。
以“捆绑”和“鞭打”为主的虐恋表相
王小波小说中充满了具有明显“虐恋”特征的身体叙事,那些“导致心理与肉体痛苦的行为”的“虐恋”表相深隐内蕴着“统治与屈从关系”,作为“虐恋”活动最常见的两种形式——“捆绑”和“鞭打”——在小说中频繁出现,成为人物的生存常态,也是令读者应接不暇的视觉常景。
“捆绑”几乎是所有被囚被虐人物都会遭遇的肉体受惩科目。《黄金时代》出席“批斗会”的陈清扬、王二要被绳捆索绑(“绳子捆在她身上,好像一件紧身衣”)且被人“驾驶”着亮相。《2015》中的“小舅”先是被绑紧——“绑得像十字架上的基督——两手平伸,两腿并紧,左脚垫在右脚下”[2]180(这一造型是对“受难耶稣”的模拟和戏仿)——送去测智商,后又戴着手铐、脚镣押赴碱场劳动改造,在“习艺所”时为防他乱说乱动,给他嘴上贴上膏药,穿上紧身衣,自习室的桌上都带有“锁颈枷”,保证学员以统一的姿势和角度“躬腰面对桌面”。《大学四年级》、《黑铁公寓》和《黑铁时代》的房客每日戴着手铐上班、下班,定时放风、散步,公寓管理人员为免等待的麻烦,还会把他们锁铐在班车站点的铁柱上。《白银时代》中主人公永远也无法改好的小说《师生恋》里不断出现绑吊受刑的场景,在热力学老师的眼里,“我永远是写在墙上的一个符号‘X’。……在痛苦中拼命地伸展开来。”[2]12而在克利奥佩屈拉统治的沙漠里,“我”亦呈X形被“绑在四个铁环上”。《舅舅情人》中的女贼锁链加身,成为捕头任意处置的猎物,类似的情节在剧本《东宫·西宫》中演变为“黑衣衙役”、“刽子手”与“女贼”的关系,“捆绑”的描写更为直观和感性:“那条闪亮的链子扣在她脖子上,冷冰冰、沉甸甸,紧贴在肉上。然后它经过了敞开的领口,垂到了腰际,又紧紧地缠在她的手腕上。经过双手以后,绷紧了。”[3]211《东宫·西宫》是一部同性恋题材的剧本,但人物的性倾向和性经历中有着明显的虐恋色彩,“捆绑”情节不断出现在受虐者身上,如“公共汽车”戴着手铐被押上警车,警察小史审讯阿兰时给他戴上“背铐”。一种更加古老、也更具形式的“美感”的刑具——木枷,更是肉体被缚、精神受辱的古代囚徒出场时的必备道具,王小波常常将它们与柔弱的女囚之躯联在一起,而且木枷一经加身,便如孙悟空头上的金箍一样,万难去除,深植于肉体,生死相随,同步腐烂。戴枷过程的详细描摹仍发生在“女贼”身上,她的脖子、手和脚在施虐者的眼里都是“美丽的”,所以,要把它们“钉死在木枷里”。这样的情景也发生在《寻找无双》中的鱼玄机身上。此外,《万寿寺》中有模仿“捕猎婚姻”习俗的情节——薛嵩对红线实施捆绑式抢婚并痴迷于打造关押红线的“木枷”和“囚笼”,《红拂夜奔》中大隋朝的歌妓们遵照“领导上”的指示,“戴上手枷”“养指甲”,喝肥皂水催吐以巩固“缠细腰”的成果,忍受折断脚骨的痛苦来“缠小脚”,用训练出来的类似踩住鸡脖子的“啾啾”声说话,都是各式各样的“捆绑”变形,另外,还有《寻找无双》中的无双被缚高台,公开发卖,等等,这些都属显性的“捆绑”。
在显性“捆绑”的叙事中,“捆绑”工具十分引人注目,五花八门的工具衍生了、决定着“捆绑”造型的具体呈现,就种类而言,有紧身衣、绳索、铁链、手铐、脚镣、颈枷、手枷、木笼等;就材质而言,有木材、钢铁、球墨铸铁、铝合金,绳索有皮革、纤维、尼龙、麂皮等;就职能而言,这些工具都对“被缚者”造成了实质性的肉体伤害,也即,工具制造的痛感突破并深深嵌入受虐者的肉体,形成有形无形的创伤,再难拔除和愈合。相对于受虐一方而言,这是一种于不期然间强行闯入的伤害,非预先经过准备并渴望承受的肉体施虐,虽然,痛感在很多情况下也会转化或伴生着肉体的快感,比如,《2015》中的“小舅”伴随“智商测试器”的“电刑”一同袭来的是表现剧烈的“性高潮”,但这种生理反应并不能相应改变和削减精神上的屈辱感,当作家以高蹈的超越的笔触和姿态赋予受虐者“浑不吝”和“不在乎”的应对痛感和痛苦的策略时,其所产生的轻松、幽默的叙事效果,也不能改写和抵消痛感本身(作家的意图亦非如此)。痛感这一执着而鲜明、尖锐且实在的肉体烙印昭示了“捆绑”工具的性质——它是施虐的刑具而非“虐恋游戏”中的玩具、道具。
除了显性的“捆绑”,还有一种看不到绳索和镣铐的隐性“捆绑”,主要来自心理和精神的钳制,形成了诸多鲜明的肉体捆绑造型。比如,《似水流年》中的李先生在弥天漫地的尘沙以及尘沙样的懵懂包裹中,只有将自己蜷缩成一团,以酷似胎儿的睡姿,才能偷得片刻安眠。这是经历“文革”时期人情世故洗礼之后的自省和自觉,以自我“捆绑”、主动受虐满足施虐狂们的暴力宣泄。《革命时期的爱情》中受“帮教”的王二把自己拧成麻花样、团成拳头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柔韧性”变换着身体的形状以适应帮教者X海鹰的捏塑要求,而在X海鹰的家里,在完成了被X海鹰想象成阶级敌人的“强奸”考验的性交后,王二的身体仍然保持着一种秩序井然、不敢懈怠的疲惫,呈现一种无法释然的内在紧张。与之相反,当王二还处于“叉开了双腿,挺胸收腹”“雄赳赳的像只小叭狗”的自由状态时,另一种“捆绑”状做爱姿势给他留下的恶劣印象,使业已集结的性能量瞬间涣散,与女大学生的交往始终止步于“无性的性爱”,那恶劣印象来自米开朗琪罗的著名雕像《夜》的中国“炉筒子”版——女的背抵炉壁,“艰难地跷起腿来”,男的取“狗撒尿”式,近在咫尺的是一团“野屎”。这样的做爱场景早已攫住了王二的感知系统和神经中枢,与“凄惨”的心理反应相伴而来的是条件反射般的生理上的“早泄”,隐形“捆绑”导致了反向呈现的懈怠的身体病态。
“捆绑”的极端是将人塞入一个狭小密闭的容器内,使之便于携带和运输。这种受虐方式有主动和被动两种情况,即,将自我物化和自我被物化。《东宫·西宫》中阿兰对其心仪的男同学有一种完全交托出去的渴望,这是一种典型的具有受虐倾向的自我表达,也诉诸于身体的捆绑式献祭:“我可以钻到任何窄小的地方,壁柜里、箱子里。我可以蜷成一团,甚至可以折叠起来,随身携带……”[3]206当阿兰真正落入这样的境地并意识到“我不过是放在他窗外的一件东西罢了”时,他正因自我的“物化”而确证了生命的存在,从而产生一种悲欣交集的狂喜。阿兰选择放弃自我,将肉体置于极端酷虐的境地,透露出深刻而扭曲的自恋,“自恋主义的受虐倾向在面临不可避免的挫折时,当事人会通过表达控制能力来补救自我评价。他做不到对周围环境的控制,但是他可以做到使自己受苦,他可以通过受苦使自己从被动地位转到主动地位,他对自己说:‘没有人能摧毁我的意志,我自己摧毁自己,因为我喜欢这样做。’有受虐倾向的人因为自己能控制为自己制造痛苦的能力感到自豪,这是‘失败中的胜利’。”[1]186阿兰想象中的自我捆绑正是这种自恋心理的外现。
需要说明的是,《东宫·西宫》的叙事重心和主旨在于探究阿兰的自虐心理和受虐倾向的社会成因,而非孤立讨论同性恋和虐恋的生理和心理成因属正常还是病态,应该进行医学矫正和刑事处罚还是应该获得承认和起码尊重的问题,因此,它突破了单纯的性取向和性嗜好的范畴,而深入到自我确证、自我评价的主体疆域。也即,王小波在追究阿兰的同性恋性取向和受虐倾向的成因时是有所区分的,他根据对同性恋的调查和研究,认为同性恋性取向是一种客观的先天的存在,它不是畸形和病态,所以无矫正的必要,需要改变的是社会对这一客观存在的丑化和敌视、歧视、漠视。相对于前者的不可选择,虐恋以及虐恋中的受虐倾向则是一种可选择和被选择的生活方式,“虐恋不是一种病理现象,而是一种以文化为根源的现象,这一文化是在统治与屈从的基础上运作的。”[1]157这里突出了自愿原则和选择的自由,统治/屈从的关系框架是虐恋双方寻求快乐的借助途径,由双方认可和约定,且角色可以交换,总之,虐恋是一种游戏和戏剧演出,而阿兰的受虐倾向源于长期挣扎却无望得到承认甚或被剥夺了平等相待的权利,于是心理发生逆转,他将自我物化的主动选择根植于无法改变的被迫境遇,成长经历积聚的焦虑感、恐惧感及负罪感迫使他主动寻求痛苦和惩罚,并将肉体承担的消极后果视为享受和幸福。阿兰的经历很有典型意义,它清晰展示出社会一步步“造就”“受虐狂”的必要因素和不断施压的过程,最终,“受虐”成为“受虐狂”自认的天定命运,并深刻依恋施虐者,将肉体受惩和精神受辱的遭遇视为“爱”,警察小史称这种常人看来极度扭曲的心理是与生俱来、不可救药的“贱”,显然,二人关于“贱”与“爱”的争论主要围绕阿兰的“受虐”嗜好而非同性恋嗜好,两种嗜好的本质差别在于前者是可供“选择”的选项之一,却在环境的围剿压力下变成了不得不如此的唯一宿命。剧本的主旨及其人物形象的深刻性在于它呈现了一个事实:较之人们对客观存在的同性性取向的偏见,社会和他者的刚性压迫和束缚造成的视“虐”为“爱”的畸形心理和受虐现象的常态泛滥,是更严重的问题。在阿兰自行闭锁于“箱子”以供他人任意处置之前,来自身外的一股更形柔韧和强势的合力已先行将之绑紧并牢牢置于那样的被动境地。
《大学四年级》中的“秃头”一次次被装入“寄人的集装箱”发往天南海北时,作为“邮寄物品”,他已不再拥有“人”的感觉了,在此封闭装置中的身体不便只是作为“货物”的被寄者自己的事情,“邮寄业务”并不包括为之解除种种“不便”,邮寄者亦无此虑,他们之间的例行手续皆在于邮寄品的“安全”送达,使双方在这桩“生意”中得到满意的收益,所以,类似于警方运送交接犯人,不仅“填单子”、“打手印”、“照相片”、“留血样”,还要“用30天不褪色的荧光粉料在他额头、手背、前胸等部位盖了章,上面写着:‘邮寄物品,交回有奖,藏匿有罪。’”在此情势下,“自我被物化”的“秃头”较之“将自我物化”的阿兰,在更真切地体验到“容器”施之于身体的有形“挤压”之外,更有永难摆脱的无形的束缚和捆绑。
就其实质而言,“寄人的集装箱”是缩微的“黑铁公寓”,而且,对知识分子来说最为无奈的是“生在黑铁时代,不住在黑铁公寓,还想住在哪里”?因为某人一旦“被判定为专门人才,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他就“必须搬入一家领有执照的公寓,享受保护性的居住”,而之所以有这样的“必须”规定,皆因“他们太聪明”。这与《未来世界》里“训导员”的逻辑如出一辙:“知识分子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任重而道远”,故而“需要好好改造思想”,而“这将是个痛苦的过程”,王小波以“受虐”的“痛感”来模拟和再现此“过程”的实质。“受虐”是“黑铁时代”知识分子的现实宿命,由特殊的“身份政治”决定,此间的等级差异表现在与“虐”相关的“特殊待遇”上,“受虐”程度随“施虐”工具的“尊贵”与“华丽”不断升级。比如,《大学四年级》中那位35岁即获得信息科学最高奖项“图林奖”的“学长”,她所戴的是“一副铐人猿泰山都不过分、亮晶晶、黄灿灿的大手铐”,外镀“24K 金”,镌着四个大字——“国之瑰宝”,并注明“三部一局(指公安部、人事部、劳动部、技术监督局)监造”,这标示了戴手铐者的“政治待遇”。但所有的雕饰都无改于其作为“捆绑”之“刑具”的本质用途,这手铐唯一的特点就是无与伦比、无坚可摧的禁锢效果。《大学四年级》有这样的叙述:“据介绍,这手铐里还裹了贫化铀的芯子,这可是做穿甲弹的材料。万一钥匙丢了,用电焊气焊都打不开,用等离子束才能割开;或者到医院里去,先截肢,把手铐取下来,然后断手再植。铀的比重很大,所以那副手铐有20公斤重。”[3]277这一最高级别的“待遇”和“禁锢”落实于“身体”便引发或潜伏着血肉模糊的肢解危险。除此之外,“黑铁公寓”的所有房客身上都盖满归属之“章”,这种无形却镂刻于身心深处的“烙印”是最有力的绳索,甚至使其产生一种被驯化的温顺,一种至为顽固的自我禁忌、自我监管的潜意识,使之由内到外、从身到心时刻保持标准的“捆绑”造型。
“虐恋”的另一形式“鞭打”在王小波的小说中也十分常见。如果说,《黄金时代》中王二被击中腰部、痛得背过气去,《寻找无双》中的无双被“官媒”“掌嘴”,《似水流年》中的“李先生”遭造反派拳殴、在下放地被“偷粪”的农民用扁担痛殴等,尚属偶尔涉及的“非典型”“鞭打”,那么,在“青铜时代”、“白银时代”和“黑铁时代”的系列小说中,“鞭打”成为人物受虐的一种常态,“施虐/受虐”关系是“权力关系”的主要呈现方式,“受虐”是权力政治施之于“在下者”的规训科目,“黑铁公寓”中设有对房客执行“鞭刑”的专用房间,且设备专业、先进、齐全,由此观之,“身体”——或更直截称之为“肉体”——已成为双方关注和争夺的一大焦点。
为了达到精神羞辱和征服的目的,“裸露”的“鞭打”成为屡见不鲜的小说场景,《未来世界》、《2010》、《大学四年级》中的“鞭刑”都是在(部分)裸露私处的前提下进行的,作家直白的书写、不动声色的实录,把一幅幅难堪的身体特写推至读者眼前,充满了令人惊耸、厌恶的不雅和尴尬,然而,“执刑者”早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对他们而言,抡鞭抽人是件不轻的体力活,除了体力的消耗,他们唯余一份“职业”积累的漠然。所以,面对“秃头趴到板凳上,把胯部横担在凳面上,屁股撅得高高的,把浴巾解开,好像对方是个肛门科大夫”的场景,负责“打板子”的女孩确乎有一种医生的细致和镇定,在开始尽显“敬业”的“噼噼啪啪”之前,吐出一句“衷告”:“用手把阴囊兜住,别打坏了。”[3]275她的“作业”标准是将“秃头”的屁股打成一枚“苹果”的颜色。在《未来世界》中“掌刑”的“唐山女孩”也有类似的职业经验,她的刑前“动员”自具不容质疑的威严和事不关己的超脱,随着“谁先受帮助呀?”的质问到“照老规矩,女先男后”的建议再到“快点儿吧!你们后面还有别人哪!再说,早完了早回家呀!”的催促,“F”之一“背朝着我,脱下了制服裙子,露出了泡泡纱那种料子的内裤、宽广的臀部,还有两条粗壮的腿”,继而“M”之一“把白夏布的大裤衩脱到膝盖上,露出了半勃起的阴茎——那东西黑不溜秋,像个车轴”,直到呼啸的“藤条”向“我”抽来,留下“八道疼痛,道道分明”。“裸露”的“鞭打”把“羞辱”和“疼痛”深深植入“人”这一“身心共同体”,标出了(被“施”和所“受”之)“虐”的醒目刻度。
除此消极的侧面,在王小波笔下,“鞭打”也曾充当建构主体自觉的特殊途径,他主要借助“鞭打”带来的尖锐“痛感”来对抗“白银时代”一潭死水的麻木。对“我”这个患有抑郁症的人而言,“痛感”尤为珍贵,它是“我”还活着的一个佐证,但绝对均质的“银色”世界最大限度地消杀了“痛感”的来源,就连公共的“虚构”文本也至为“健康”、“清洁”,“我”只有转而致力于秘密写作,在作为私人秘籍的《师生恋》稿本中加入大量捆绑、鞭笞、吊打的场景,并进而展开更新奇怪异的制造“痛感”的想象,比如,《师生恋》中的“我”幻想经历“蚂蚁噬咬”、“骆驼舔食”等酷刑,并被训练有素的“行刑队”“处决”,“我”渴望“大粒的平头铅子弹带着火辣辣的疼痛,像飞翔的屎壳螂迎面而来”,视“挨上一下”为“惬意”的享受。《白银时代》中的“我”所设计的《师生恋》中的“我”之死依然不脱“鞭打”的想象——“钉死在十字架上”,在接受致命的最后一鞭——那颗利钉——之前,女王克利奥佩屈拉用“春蚕似的手指”给“我”“被晒得红肿的皮肤上带来了一道道的剧痛”。与之相比,设计这一切的“我”在“白银时代”的现实中所获得的“痛感”,除了可以期许的“枪毙”下属文稿后承受对方的重重一“踩”之外,尚有唯一一次不可期许的“吃痛”经历,那就是几个中学女生劫掠他的内裤时,刀尖很轻浅地扎到了他的大腿内侧。显然,最高级别的“痛感”只存在于“虚构中的虚构”人物的幻想世界,次之的“痛感”在虚构文本中成为“现实”,最小的“痛感”在小说主人公身上偶一闪烁,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他赋予“故事”的“寓意”却是“在剧痛之中死在沙漠里,也比迷失在白银世界里好得多”。由此推测,当“痛感”成为主体渴望确证自我的标志和克服“白银世界”死气沉沉的静寂的手段时,制造“痛感”的外界力量——包括“鞭打”——便不再是“施虐”的方式,而是促动主体更生的积极因素。这不同于“虐恋”活动中充当获取“(性)快感”媒介的“痛感”,它是激活个体生命的一剂良药,是主体意志“活着”的佐证。
总之,王小波的小说中不时出现“捆绑”和“鞭打”等“施虐”场景,特别是其间对身体不能承受之重的极限体验的描摹,与“虐恋”活动和“虐恋”文学中“肉体”负重的种种情形极具直观上的相似性,不独如此,王小波在人物关系设置上,也暗合“虐恋”角色扮演的常见模式,如主人/奴隶、教师/学生、警察/囚犯等,《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王二像一条狗一样被迫从属、服侍、追随X海鹰的情节,与“虐恋”中的主奴关系相较,便有几近乱真之效。《2015》中从如“电刑机”般的“智商测试器”里出来的“小舅”大叫“被电打很煽情”,他“在那个匣子里精液狂喷”的经验,酷似“虐恋”游戏中“受虐”一方借助“痛感”获取“快感”的典型效果,但是,二者的侧重点大为不同,“小舅”的逆转“痛感”为“快感”是反抗并战胜“施虐”者的途径和手段,以一种不屈服的姿态使“施虐”者的目的无以得逞从而将与其所施之“虐”引发的尖锐“痛感”很是相称的深刻的挫折感转嫁给对方,而自身并无以此种方式获取“快感”的生理和心理的需求与嗜好,“虐恋”中的“受虐者”恰恰相反,他们以身体承受压迫和折磨作为唤起“性快感”的必要条件,通常表现为“无比的温顺,驯服地接受所有加在自己身上的惩罚,从而证明其无效,通过谦卑的途径达到自己隐秘的目标”。[1]207显然,“小舅”的表面“驯服”,是对权力施诸的刑罚的蔑视,背后隐含着无穷的逆反张力。
施虐/受虐实质及其文化探源
王小波的文学作品中,施虐、受虐的场景随处可见,堪称一部集合了诸般“虐恋”表象和形式要素的交响乐,但却不是以表现“虐恋”为主旨的“色情作品”,而是以与“虐恋”游戏非常相似的狂欢化的写作心态,揭示现实权力关系架构和运作中施暴一方强加于受害一方的肉体痛苦和精神屈辱。
“施虐/受虐”关系与“虐恋”关系本质的不同,在于它不符合后者的一系列“共同特征”,其中最重要的一点,“虐恋”是基于特殊的身体和心理嗜好而在同好者之间展开的娱乐活动,有的将之发展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参与者是自愿的。这就是真正的暴力及其施暴者、受害者与虐恋关系的根本区别之所在。”[1]16“虐恋”遵循“事先约定”的原则,是以娱乐为目的的“成年人的游戏”,是有“剧本”作为规约和指导的“戏剧演出”,参与者有选择角色和更改所扮演的角色(通常情况下是角色互换)的自由,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由接受者(有受虐倾向者)而不是由施予者(有施虐倾向者)来安排和控制活动的内容和程度。”[1]18也即,“受虐”一方掌握主动,“是受虐者在控制着施虐者的手”,双方角色可以互换,但因“受虐”一方受益最大,是真正的“消费者”,故而,在有“虐恋”嗜好的人群中,“受虐者”明显多于扮演“服务方”的“施虐者”。最后,“虐恋”是建立在双方“极端亲密、了解和信赖”基础上的二人交往,它往往提供、构建了主体之间从肉体到情感到思想的深度交流的渠道,是一种自主和双赢的个人选择,表面看来,似乎属“性心理”极度扭曲、畸形的边缘、另类人群,但就其本质而言,“虐恋”是获得高度民主、自由的现代人才会有的交往方式和享乐方式,是富于建设性和积极意义的“人际关系”拓展途径。
显然,王小波所写不同于此,他笔下呈现的是与这些特征完全相反的真正的暴力施虐,它排除了“受虐”一方的一切选择和逃避的自由。但是,在“施虐/受虐”角色被权力格局派定和锁定的前提下,在彼此之间深刻的思想隔膜和仇恨情绪随肉体折磨而无限加剧的总体氛围中,王小波在展现主体“受虐”困境时,依然借助了“虐恋”的一些要素,比如,以幻想延伸或重构现实、狂欢化的激情表演、多重象征意味的呈现、仪式化的场景再现(主要是种种“刑罚”,包括“死刑”的场面)、“悬吊”内蕴的充满未知的悬念和目标实现的一再延宕,等等,这些具有“审美现代性”特征的精神体验通过身体语言表征出来,是王小波援引的解构权力规训和暴力压迫的有力武器。他的身体叙事洋溢着自我救赎和争取普遍自由的激情,在肉体的炼狱中喷吐着沛然莫御的精神欣快,这或可称为特殊的“虐恋”快感,肉体之“虐”成为权力规训和个体自我各自征服和利用的对象,它最终化为后者获取精神自由的特殊而有效的介质。
“施虐/受虐”关系常常被误解为“忠诚”和“爱”,特别是在这种关系建立的初始阶段,随着“忠诚”与“爱”无限升级,跨过了“理性”辨析的限度,“虐”的实质便愈加明显地暴露出来。“受虐现象尤其被视为表达爱的一种方式。为了另一个人完全否定自我,并把自己的权利与主张完全交给他,这被视为‘伟大的爱’的典型,为人所颂扬。似乎除牺牲和为所爱的人欣然放弃自我外再没有能证明‘爱’的更好证据了。”[4]110这里的“他”可以指特定的人,也可是人格化的集体、国家、信仰及其代理人等等,所谓“忠诚”与“爱”并不限于两性和两人的关系,而是一种更宽泛和更抽象的人际关系和主体交往的概括,但人们往往以两性之爱来对此做具体描述和分析,这种将论述对象“窄化”的做法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但也产生了一些误解,比如,以“虐恋”指称所有的“施虐/受虐”关系。
“施虐/受虐”关系中的“忠诚”乃是一种不得不如此、习惯成自然的“臣服”,而“爱”则是“施虐狂”的统治冲动与“受虐狂”的受虐依赖彼此纠结共构的假象,因为它缺乏“爱”所要求的平等和自由的基础,既非“热烈地肯定某个人的本质,积极主动地与之建立关系”,也非两者“在各自独立与完整基础上的结合”,而是“以其中一方的臣服与完整性的丧失为基础”,所以,以“爱”命名“施虐/受虐”关系是一种伪装,它忽视或掩饰了强权在其中所起的主导作用,将“施虐/受虐”的问题仅仅置于特殊的爱欲心理导致的人格建构的畸化和倒错等视域而单纯援引心理分析的模式加以解释是远远不够的。
王小波分别在杂文《弗洛伊德和受虐狂》和小说《革命时期的爱情》中提到弗洛伊德对“受虐狂”成因的解释,即:“人若落入一种无法摆脱的痛苦之中,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就会把这种痛苦看做是幸福,用这种方式来寻求解脱——这样一来,他的价值观就被逆转过来了。”[5]132这种“受虐狂”“起码是在表面上,不喜欢快乐,而喜欢痛苦,不喜欢体面和尊严,喜欢奴役与屈辱”。[5]132这是典型的受虐冲动,它的几种表现——“贬低自己”、“臣服于外在力量”、“伤害自己使自己受苦的倾向”——在王小波的小说中得到了印证,受虐冲动将主体导向一种“逃避自由的机制”,即“放弃个人自我的独立倾向,欲使自我与自身之外的某人或某物合为一体,以便获得个人自我所缺乏的力量”。[4]97-98
与受虐冲动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是施虐倾向,弗罗姆总结了纠缠在一起的“三种施虐倾向”:“一是让别人依赖自己,以绝对无限的权力统治他们,以便让他们仅仅成为自己手中的工具,像‘陶工手中的泥土’。二是不但有以这种绝对方式统治别人的冲动,而且还要剥削、利用、偷窃、蚕食别人,把别人吸净榨干,不但包括物质,而且还包括情感与智慧之类的精神方面。第三种施虐倾向是希望使别人受磨难,或看别人受磨难。磨难也可能是肉体上的,但多数是精神上的折磨。其目的是主动伤害、羞辱他们,让他们难堪,要看他们狼狈不堪的窘相。”[4]99据此观之,王小波揭示了一个事实:专制、特别是极权专制的实质是具有极端和综合施虐倾向的统治者向被统治者释放不断爆发和升级的施虐冲动的过程,在受虐群体中,知识分子是身心受到摧残最为酷烈的一个阶层,也是最具自我救赎和拯救他人能力的一个阶层,在受虐境遇中,他们首先质疑了作为受虐者的“依赖欲”和“受苦欲”,这导致他们针对施虐者的身心两方面的逃遁与抗争,因之,被专制者视为死敌和劲敌。从这个角度而言,王小波专注于书写知识分子的受虐和抗争对于探讨主体建构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
王小波描述、分析了“施虐狂”和“受虐狂”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赖和共生的关系,他特别指出,“受虐狂”的“无限雌伏”、“无限谄媚”的精神和彻底交出自己的无限被动的做派,直接造就了“施虐狂”,助长了施虐行为的无限升级。他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特别举了几个被“受虐狂”“招出来”的施虐例子:不加防护的俄国战舰、“被剃了大秃瓢,胸口戴着黄三角”的犹太人、被剃了“阴阳头”的“牛鬼蛇神”、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等等,其被动挨打的可欺和柔顺对“施虐狂”们的施虐、施暴秉性形成一种挑逗和诱惑,在此,他强调,正是受虐者的无条件屈从,召唤、巩固并加强了施虐者的施虐行为,受虐者“除掉自我”、“交托自我”等主动摧毁主体意识的消极做法恰恰应和了“施虐者欲把施虐对象变成手中一个无意志的工具”的主宰冲动。受虐者任人宰制、放弃反抗的应对态度对形成和维护这种不平等关系负有一定责任。当然,滋生并保障“施虐/受虐”关系秩序的力量不仅仅取决于或说不主要取决于受虐者的反应,文化形态、社会形态、意识形态等共同造就了这种关系的生成机制,并充当其保护伞,所以,王小波将“施虐/受虐”的成因解释为:“假如某人总中负彩,他就会变成受虐狂。假如某人总中正彩,他就会变成施虐狂。其他解释纯属多余。”[6]从量的积累到身份认同的渐趋稳定再到受虐自我本质化的结果,既包含了客观条件的设定和强化作用,也无法排除主体向角色的倾斜直至皈依。王小波甚至将中国的文化、历史和现实环境比作一座“S/M”的“密室”,因为两者之间有惊人的“形似”:“在密室里,有些masochist把自己叫做奴才,把sadist叫做主人。中国有把自己叫贱人、奴婢的,有把对方叫老爷的,意思差不多。有些M在密室里说自己是条虫子,称对方是太阳——中国人不说虫子,但有说自己是砖头和螺丝钉的,至于只说对方是太阳,那就太不够味儿,还要加上最红最红的前缀。”[5]91不仅“形似”,更兼“神似”,他借用辜鸿铭的说法加以描述:“华夏文化的精神,在于一种良民宗教,在于每个妇人都无私地绝对地忠诚其丈夫,忠诚的含义包括帮他纳妾;每个男人都无私地绝对地忠于其君主、国王或皇帝,无私的含义包括奉献出自己的屁股。”[5]91因此,这个解释不仅有助于弄清王小波小说中很多人物的关系实质,而且可以证之以中国历史上统治秩序中的“在上者”与“在下者”的主奴关系的生成和演化。
综合观之,在王小波所描述的主体受控状态中,身体叙事最为直接和直观地呈现了权力宰制的程序、特点、程度等,它印证了福柯的论述:“规训权力具有一种生命权力的形态,更多占领的是肉体而非心灵,它使肉体臣服于一种规范化强制。”[7]333“长恨此身非我有”、“身不由己”、“身心分离”、“心脑冲突”等体现了“身体政治”的一般规则,“生命不能承受的肉身之重和肉身之痛”、“身比心先老、心比身先死”等则是这些一般规则屡经变幻制造出的骇人景观。福柯有关“权力关系”落实于“肉体”的一些发现,比如:“权力关系中存在着充满规范内容的不对称性,而且,主要还不在于权力意志与强迫服从之间,而是在于权力过程与卷入这一过程的肉体之间。遭到虐待的总是肉体,肉体成了主权复仇的舞台;肉体受到规训,遭到机械力量的分解并被操纵……肉体的欲望既受到刺激,同时又遭到压制。”[7]335在王小波的笔下有一系列形象化的延展,在争夺“身体”主权的斗争中,主体的自主意愿和自由意志与肉体一起经历了诸多磨难,但在作家的主观意识中,这一斗志永不消歇、永难磨灭!
[1]李银河.虐恋亚文化[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
[2]王小波.白银时代[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7.
[3]王小波.东宫·西宫——调查报告与未竟稿精品集[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4]埃里希·弗罗姆.逃避自由[M].刘林海,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
[5]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6.
[6]王小波.黄金时代[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7]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