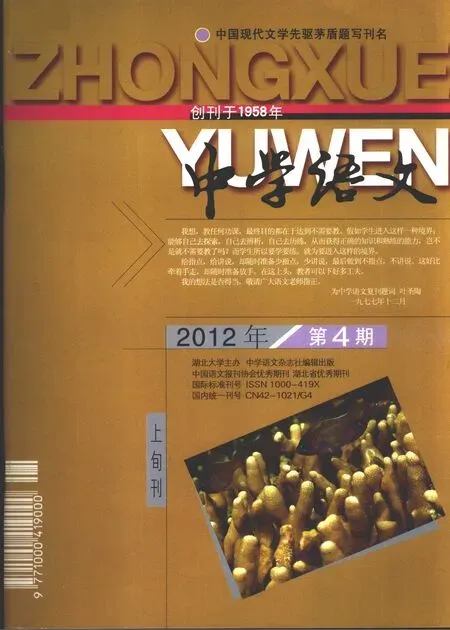辫子·称谓·偷
——鲁迅作品教学札记
葛德均
林纾《春觉斋论画》云:“名大家画,多在人不经意处格外经意。”文学亦然,文坛高手往往不需要惊天动地的事物,相反,他能够通过一些不为人注意的细微末节,精心着意,达至令人难以忘怀的艺术效果。鲁迅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作家,他在一些作品中,通过人物的“辫子”、“称谓”、“偷”等表面看来似乎微不足道的事物或言行,刻画出令人拍案叫绝、回味无穷的文学景象。我们在鲁迅作品教学中,如果抓住人物的“辫子”,聆听人物的“称谓”,审视人物的“偷”,均不失为一个很好的突破口,能收到“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的艺术效果。
一、内蕴丰富、不同凡响的“辫子”
鲁迅有一段人们熟悉的话:“要极俭省地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倘若画了全付的头发,即使细致逼真,也毫无意思。”我们理解这段话,切不要以为刻画人物只可画眼睛不可画头发,而是说要抓住人物最具特色的东西来写,该画眼睛则画眼睛,该画头发则画头发。辫子,本是那个社会中司空见惯的寻常之物,但一到鲁迅的神奇笔下,则神采飞扬。
解剖人物的刀子。《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有产物。他“先前跑上城里去进洋学堂,不知怎么又跑到东洋去了,半年之后他回到家里来,腿也直了,辫子也不见了”,后来又有了“一条假辫子”。可见,假洋鬼子的东洋留学,完全是时髦、镀金而已。至于剪去辫子,如果不是迫不得已,那就是以此捞点政治资本,因而回国后先装上假辫子,充当封建势力的爪牙。就是这样一个削尖了脑袋钻营的新型封建阔少,当“革命党已在夜间进了城”的消息一传来,马上又摇身一变,伪装革命,“已经留到了一尺多长的辫子都拆散披在肩背上,蓬头散发的像一个刘海仙”。可别以为假洋鬼子是革命者,他实在不是真心革命。尽管他买得一颗“银桃子”(革命党证章)挂在胸前,俨然以革命者自居,却又不准阿Q等贫苦人参加革命,甚至乘机残害人民,充分暴露他的反革命嘴脸。罗曼·罗兰说:“决不要满足于那皮相的混乱的表面运动的描写,要深入到灵魂里去。”辫子,可以说是一把解剖人物并深入到灵魂里去的锋利刀子。
透视现实的镜子。《风波》以辫子作为引起“风波”的导线,牵动了不同人物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不同表现:封建保守势力的代表赵七爷害怕革命,狡猾阴险。革命高潮时,他盘起辫子,收敛往日的凶狠,蒙混过关;复辟风吹来,他放下盘着的辫子,向人民反扑;复辟平息后,则重新盘起辫子,继续伺机报复。贫苦人民的代表七斤,有朴素的阶级意识,能够剪去辫子,说明他愿意接受革命主张,但又不完全理解革命,特别是“皇帝要辫子”时,他忧愁满腹,显然是不觉悟的表现。我们说,无论是赵七爷起先的盘辫子还是后来的放辫子,也无论是七斤当初的剪辫子,还是后来没有辫子时的心理负担,都可以看出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这次革命只是形式上赶跑了一个皇帝而已,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封建秩序,对七斤等广大人民群众只是剪去其辫子而已,并没有能够真正发动和组织并依靠人民进行革命,这正是辛亥革命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所以不妨这样说,一场“辫子”风波,便是当时社会现实的速写。列夫·托尔斯泰说,出色的作家“把所看见的生动的事物像用一块棱镜一样,集中在焦点上。”辫子,可以说是一块集中焦点、透视现实的镜子。
渗溢情感的管子。《藤野先生》篇首描写了“清国留学生”的生活情景,他们“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在这里,鲁迅含蓄地表达对那群游手好闲、不学无术的寄生虫以及他们那种浑浑噩噩、醉生梦死的生活态度的嘲讽。鲁迅到日本留学,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良方良药,是带着“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爱国之心和铮铮誓言而远离故土、只身异国的。他说:“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维新的信仰。”而当他到达日本东京时,那些留学的中国学生和他有着天壤之别,令他厌恶。可见,《藤野先生》开头有关“辫子”的描写,实际上反衬了鲁迅的爱国情怀。另外,辫子是中国民族受压迫的标志,鲁迅对它一直很反感。他到日本后就剪掉了辫子,表明他的革命志向。而那些“清国留学生”却在辫子上玩花样。鲁迅对此作了辛辣嘲讽,其中又寓含着他的革命激情。在谈到作家情感问题时,鲁迅说过:“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辫子,可以说是一道渗溢情感血液的管子。
二、致曲入细、心摹意匠的“称谓”
周振甫先生在《文章例话》一书中,以“称谓不一”为题专章论述,足见“称谓”在写作中的作用。钱钟书先生也十分赞赏“称谓”的妙用,他在《管锥编》中说:“夫私家寻常酬答,局外事后只传闻大略而已,乌能口角语脉以至称呼致曲入细如是?貌似‘记言’,实出史家之心摹意匠。”鲁迅作品中的“称谓”,深得其真谛。
故事情节的展示。小说《故乡》中闰土对“我”的称呼,由孩提时的“迅哥儿”到中年后的“老爷”,两声不同的称呼,带动了情节的发展。一声“迅哥儿”,那是昔日情景的形象注脚;一声“老爷”,则可以说是残酷现实的生动反映。从不同的称呼语中,我们看到生活的风霜,已使活泼天真的少年闺土变成了麻木呆滞的中年闺土;时间的波涛,冲去了儿时情谊,在好伙伴间筑起了无形的墙。这正是《故乡》中称呼语所包孕的情节内涵。
心理状态的透视。鲁迅笔下的阿Q,地位低下,贫困不堪,未庄豪绅赵太爷骂阿Q“浑小子”还不许他姓赵;赵秀才骂阿Q“忘八蛋”;赵白眼从不认阿Q是本家。可一旦阿Q“革命”了,赵太爷竟称呼起“老 Q”来了,赵秀才呼之不应时“只得直呼其名”,赵白眼还亲切地称“阿Q哥”。鲁迅通过变异了的称呼语,惟妙惟肖地表现出人物的阴暗心理:害怕革命,惶恐不安,见到“革命”的阿Q,便加“老”称“哥”,企图蒙混过关。
作者心声的呈现。高尔基说:“文学即人学”。在称谓中,作者的心声,也是会被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的。在《故乡》中,“我”把杨二嫂称为“瘦脚伶仃的圆规”,就颇生动地表达出“我”对杨二嫂这个市侩的厌恶。与之相反,“我”称闰土为“闰土哥”,则又真切地道出了“我”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同情和敬仰以及对隔膜了的儿时友谊的留恋。《社戏》中“我”(迅哥儿)称呼“双喜”、“阿发”等伙伴儿以及“六一公公”、“八公公”等长辈,其亲切的口吻,也透出对“平桥村”的喜爱,反衬出对世俗社会的厌恶。《阿Q正传》中称那个新型封建阔少是 “假洋鬼子”,《药》中称那个贪婪钱财的狱卒叫“红眼睛阿义”,称那个无所事事的茶客叫“驼背五少爷”,无不巧妙地表达了对这些人物的憎恨。《孔乙己》中称那个深受封建教育毒害的迂腐文人叫“孔乙己”,则在批判之余又寄予同情,所谓“怒其不争,哀其不幸”。尽管作品中的“我”决不等同于作者,但借“我”之口,传作者心声,这是毋庸置疑的。
三、异彩纷呈、各臻其妙的“偷”
我们不能简单地看待“偷”。有的人,偷得可憎,如《十五贯》中的娄阿鼠;有的人,偷得可怜,如《流浪者》中的小拉兹;有的人,偷得可爱,如《三盗九龙杯》中的杨香武;有的人,偷得可敬,如为正义事业而冒着生命危险去窃取敌方机密的地下尖兵。鲁迅笔下的偷,也是异彩纷呈、各臻其妙。
语言不同,“偷”出人物性格。鲁迅说过:好的人物语言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在他的笔下,同是“偷”,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语言,从而表现出各自不同的性格。孔乙己是一个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穷困潦倒的下层知识分子,他偷了人家的东西,但又自视清高,死要面子,不敢承认,先是“睁大眼睛”,继之 “涨红了脸”争辩,说什么:“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借此来掩盖自己,最后便说“君子固穷”或者“者乎”之类,引得众人哄笑。孔乙己对“偷”的自我解嘲与诡辩,正是他迂腐性格的表现。阿Q也偷,有一次到尼姑庵里偷萝卜,明明被人当场发现,竟还能厚着脸皮狡辩,先是矢口否认自己的“偷”,再就是耍无赖,以“你能叫得他答应你么”这蛮横无理的话来搪塞。这种赖皮语言,是非常切合阿Q“精神胜利法”性格的。与孔乙已、阿Q截然不同的,是《社戏》中一群农村孩子在看戏回家的路上,合伙“偷”罗汉豆吃时的语言。虽然是“偷”,但丝毫没有令人厌恶之感,相反却更见其纯朴、无邪。阿发把自家的豆当作“我们的”,招呼大家偷他家的豆,双喜及时提醒大家不要多摘,以免阿发娘伤心。可见,他们是多么的真诚热情,多么的体贴他人,他们不分你我,无间无隙,他们不讳“偷”这个字眼,这正是其心地纯洁、襟胸坦白、天真活泼的体现。
对象有别,“偷”出形象特征。孔乙己所偷,主要是丁举人这种读书人家的读书用品。或许当初丁举人也和孔乙己一样,但一旦金榜题名,则身价百倍,飞黄腾达。可悲的是,残酷的科举制度抛弃了孔乙己,而孔乙己却还是死抱着科举不放,他时刻梦想着能够顺着科举的道路爬上去,他不愿脱下那又脏又破的长衫,不愿放下读书人的架子,可见他受封建教育毒害之深。阿Q最典型的是到尼姑庵里偷萝卜。阿Q对赵太爷敢怒而不敢言,对假洋鬼子厌恶而不敢惹,这些高门大户家里有的是金钱衣食,但阿Q是不敢放肆半点的,他只能到尼姑庵里占便宜,这正体现了他的欺软怕硬。双喜、阿发等农村少年偷的是自己家的和六一公公家的罗汉豆,说明这群农村孩子的纯朴可爱,对于他们来说,只要能使大家感到快乐,自家的东西也就是大家的,可以拿来奉献给伙伴儿。至于偷六一公公的豆,则说明了孩子们的聪明活泼,他们知道,六一公公这位淳厚可亲的老人是不会责怪他们为招待客人而摘豆的。
性质差异,“偷”出社会环境。孔乙己本来有一副高大的身材,可以靠劳动为生,又“写得一笔好字”,能换一碗饭吃,但封建教育制度使他变成了一个既不会营生,又好喝懒做的废人,他终于走上了偷窃的道路。阿Q的偷,也是迫于生计。他本是一个样样活能干的农民,仅仅因为一次偶然地向财主女佣吴妈求婚,触犯了虚伪的封建伦理,从而被剥夺了靠自己的劳动而谋生的权利,他连出卖自己劳动力的主权也没有了,于是在饿了几顿肚子之后,实在感到“妈妈的”,只得铤而走险了。其实,孔乙己、阿Q所处社会本身就是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偷的世界,然而,“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这种极不公平的社会罪恶,从“偷”的这个聚光点上可反射出来。至于双喜、阿发等人的“偷”,偷得可爱,偷得可亲,他们不是真偷,而是在寻找乐趣。透过这种“偷”,我们可感受到乡村那纯朴的民风,正是乡村的纯朴民风熏陶了双喜、阿发这群孩子。另外,孩子们的纯真和乡村的纯朴,恰与那市侩气窒人的社会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我们在此又可反窥到整个社会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