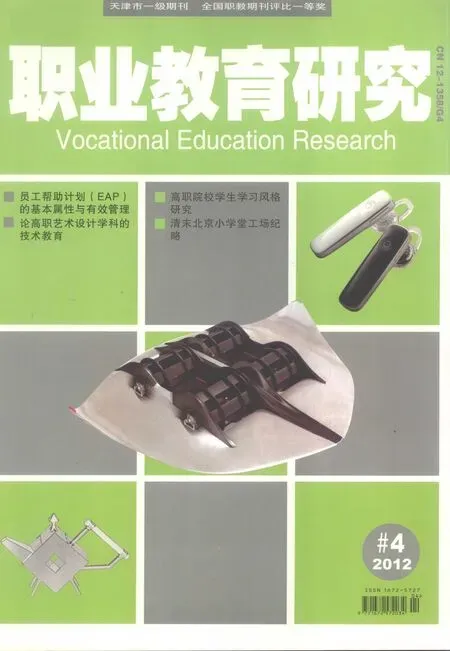清末北京小学堂工场记略
陈凯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300074)
清末北京小学堂工场记略
陈凯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300074)
清末推行“新政”期间,直隶当局于京师创建了两所“小学堂工场”(或称“工场小学堂”),将职业教育提前至小学阶段,既为解决贫民生计,也使为社会培养的劳动力“不致为无意识之工匠”,使之“具有学生性质”。不数年“工场”停办,“小学堂”仍在,其停办原因却尚未发现可资说明的史料。
清末;小学堂工场;开民智;兴民业;工学并逐;资裕贫民生计
清末,朝廷为维持其统治,挽救业已衰败的局面,提出并实施“新政”,一时确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所谓“新政”,基本内容就是振兴实业,操练新军,创建新式学堂。振兴实业,即发展工商业,是为强国家、裕民生的经济基础;操练新军,即引进新式操法、洋式装备,以保卫疆土;办新式学堂,则是取代科举和旧式私塾、书院,以近代文化科学知识广育人才的重大举措。
20世纪初,作为拱卫京师、都城门户的直隶,乃是全国督抚之首,而直隶总督正是从山东巡抚任上奉调而来的袁世凯。民国后,袁野心膨胀,因洪宪称帝而被世人所诟病,弄得众叛亲离,遗臭万年。但历史地看,当年袁世凯却也曾意气风发,在直隶大力推行“新政”,是颇有一番作为的,致使直隶被称为实施“新政”的“模范省”。其实,袁世凯早在山东巡抚任上,就曾倡导“开民智”,“崇实学”,十分重视推行近代教育。曾奏议朝廷,称“百年之计,莫如树人”。“作养人才,实为图治之本”①,而且于1901年,率先主持创建了山东大学堂。就任直隶总督后,其兴办近代教育的举措和力度有增无减。1905年,袁领衔联合五大臣,呈奏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并妥筹办法折》,痛陈科举之弊,称学校“乃以开通民智为主,使人人获有普及之教育,且有普通之知能,上知效忠于国家,下知自谋其生……”②并获得朝廷批准。袁诚聘曾任贵州学政,后又以创办天津南开系列学校而知名的严修执掌直隶学校司 (后称学务处)。在严氏及其后任的共同努力操持下,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直隶已建有北洋大学堂及工业、农业、医学高等学堂5所,初等农、工业工艺学堂及传习所,师范类学堂,中学、高小共二百余所,初小多达四千一百余所,另有武备、巡警等专业学堂数十所,不包括半日、半夜学堂,学生“总数不下十万人”。③
上述工艺类学堂在当年属于“实业教育”,即今天我们所说的职业教育。比较稀罕的是,当时曾创办了两所“从小抓起”的职业教育——“小学堂工场”(又称工场小学堂),而且就设在国都北京。迄今各类刊物已发表的文字中,大多只提到该“第一、二小学堂工场”之名,似少有具体论及。笔者依据史料文献,对此作一梳理,填补可能的空白。
直接提议创办小学堂工场的,正是直隶总督袁世凯,由周学熙任总办的直隶工艺总局承办。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初,一份《工艺总局会详学务处在京推广学堂工场文》呈报直督,文中写道,创设“工场并小学堂、半日学堂”是袁世凯“谕饬”,即系袁亲自下的指示;并颂扬袁“作育人才,轸念民生之至意,莫名敬佩”。周学熙等遵命与学务处会商,“拟将学堂、工场合办”,并“先试开一处”。继而报告在京已“觅得房屋”,“坐落北京前门内西城根,计大小六十余间”,且有空地,可供续建工场和体操场。并派工艺局提调赴京办理手续,“赶紧修理”;经费由“银元局拨款”。同时,建议邀聘京城光禄寺(朝廷后勤官署)、国子监各一名官员任“北洋驻京学务工业总董其学堂工场”,拟订《试办章程》,协助筹建。此外,《呈文》还提出,需恳请京城步军统领衙门(首都卫戍部队)、工巡总局(治安警察)、顺天府尹(地方首长)“转饬该地段员司一体实力保护”。同年九月初四日,袁世凯批示:“如详办理”。④
事隔一年,又一份 《开办第二工场学堂文》报呈袁督,称“(第一小学堂工场)开场开学,业已办有规模,亟应接办第二工场并第二小学”。且经“驻京总董”徐、李二员“会同觅得房屋一所”,位于北京内城西北毛家湾胡同一带,大小一百三十余间,“足敷工场、学堂之用”。袁于是年(1906年)二月二十六日批示:“据详已悉”,⑤准予办理。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工艺总局出版的《直隶工艺志初编》,对包括北京第一、第二小学堂工场在内的属下各单位逐一作了简要的总结。在《北京第一、二小学堂工场总志》篇中鲜明地指出:“考东西各国皆有工作学堂,凡习工艺者,必兼习普通学理,中国学界、工界两不相涉,以故工业窳败,日甚一日。”有鉴于此,需开设 “小学堂工场”,“每日课六小时”,“课毕入工场”,“俾工与学兼营,他日技成,工徒具有学生性质,不致为无意识之工匠矣”。同时,附设“半日学堂”。按当年的行政区划,北京属顺天府,归直隶管辖,但毕竟是国都所在,有“京师首善之区”的称谓,因此,有一种意见认为,京城内外,学堂、工场,官立、民立,各类设施及学生、工徒均为数众多,似不必由直隶出面在北京再设此类小学、工场。而袁世凯认为,“凡(直隶)所管辖之区,均有挈提之责,今虽小学工场,非大学堂、大工厂可比,然苟组织愈多,则推行愈广,教育愈行发达”。“即在异省,且不可有畛域之分,矧(音shen,况且意)在一省中,何地不当倡导而施教化所冀”。意思是说,即便是在其他省份,尚不能区分那么清楚,更何况北京同属直隶,我们怎能不去提倡呢?《初编》撰写者又对袁世凯和工艺局总办周学熙称颂一番,遂写道:“宫保与督办之志,热心任事,后先媲美,不徒津郡学务、工业蒸蒸日上,即北京之堂、若场,亦岂徒以第二为止境哉。”⑥就是说,将来可能还会有第三、第四……小学堂工场开办。总之,对未来发展和前景乐观地充满期待。
小学堂工场确定的“宗旨”,简要明确,即“学堂以开民智,工场以兴民业”,“以教养兼资裕贫民生计为宗旨”。同时,“附设半日学堂。即以学堂内学生,分早晚两班入工场习艺”。⑦这里有必要对当年的社会背景略加说明。20世纪初的清朝末年,中国基本上还是农耕社会,生产力低下,经济十分落后,近代工业起步不久,且多在军火制造方面。无地农民和城市无业游民众多,他们既无文化,又无技能,生计无着,已是重大的社会问题。直隶工艺总局于1905年即曾发布《劝兴工艺示文》,称“吾国幅员之广,生齿之繁,甲于环球,而财力则异常缺乏。此由实业不讲而游民滋多,……民穷财匮日甚一日”。因此,呼吁“城乡绅商士民”,“齐心协力,广设工场,以开生计而塞漏卮”。⑧使民众有业可就,有钱可赚,通过劳动得以谋生,乃是任何社会获得安定的必要条件,而要使劳动能创造价值,就需要使劳动者具有一定的文化和技能。因此,开办小学堂工场,如其“宗旨”所言:“学堂以开民智,工场以兴民业”,“以教养兼资裕贫民生计”,正是适时地、有针对性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据史料记载,第一小学堂工场(以下简称一小)时有讲堂、延接室、员司宿舍等用房55间,工场用罩棚、场棚50余间,另有库房等30余间,已具有相当规模。转年建立的第二小学堂工场(以下简称二小),从拥有房屋数量看,规模略大于一小,尤其是工场已由新建房屋55间取代了简易的 “罩棚”、“场棚”。⑨
小学堂、工场的教学及管理人员分列,一小学堂员司计有总董、监理、监学各1名,教习5名,收支、杂务各1名;工场员司包括总董、监理各1名,收支、杂务各1名,监工2名。二小人员配备大致相同。⑩
一小、二小经费均由官方拨付,又分开办经费与常年经费两类。一小开办费(1905年)由银元局拨银12000两,转年再拨“扩充经费”5675两。常年经费则分别拨给,学堂每月拨银260两,转年又增加50两;工场每月拨银165两,转年增至300两。⑪二小开办费由造币分厂(即原银元局)拨银15380两;常年经费学堂每月拨银320两,工场每月拨银400两。⑫一小、二小均有为数不多的自费生缴费收入。
学堂“教科”设有读经、修身、历史、地理、笔算、珠算、格致、国文、习字、作文、图画、手工、唱歌、体操等14门课。工场设“工科”,有织、染、木三科。以“织科”为例,又分打线络、打线穗、打线轴、轮线、掏综、入抒、上机、织布等“八班”。⑬一小、二小所设科目基本相同。
学生(工徒)分官费、自费两种。据1907年的统计,学堂高等一班有学生(工徒)50名;初等甲、乙、丙三班学生(工徒)120名。半日学堂有甲、乙两班学生(工徒)60名。学堂每日上课6小时,半日学堂上课3小时,“每一时分授一科,将各科以次轮教,周而复始”,“课毕入工场”。工场毕业生要求达到每日织布27尺,自费生上机4个月者达到每日织布20尺。每日一人能打络线10个,打轴线50~60个,打穗100个,每日二人能掏综入抒一份(因需二人配合操作),轮布线5匹,织布各生皆轮班上机。一小、二小情况基本相同。至1907年,毕业生一小先后有两批49名,二小有17名“均已请给凭单”(即毕业证书)。⑭
学堂置办书籍、器具有限,书籍各有一百余种;器具均为纺织用的织机、轮线架、掏综架、大小纺车等各二百余件。工场劳动的制成品有花布、被面、褥面、袍料、褥单、毛巾等多种。⑮
由于史料不足,尚有若干情况不明,如学生年龄、学制时间、毕业出路以及其后学堂的发展、演变等。我们只知道,不数年小学堂仍存在,而工场则已消失。
尽管如此,北京第一、第二小学堂工场的创办,在我国的职业教育史上,还是有可总结的经验和可吸取的教训。
第一,“学堂以开民智,工场以兴民业”,“以教养兼资裕贫民生计”的“宗旨”,既从实际出发,符合国情的需要,又适应了时代的潮流。为民众谋生计、为国家谋富强,是任何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的国家都需解决的第一要务。我们曾经有过的观念是,统治阶级从来不会关注民生,只是剥削、压榨,乃至希冀“从一条牛身上剥下两张皮”。这种片面、绝对的看法并不符合实际。试想,民众生计无着,就要起来造反,统治阶级岂能安生?中外历史已无数次地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工学并逐”,亦工亦学,手脑并用,理论联系实际,是当年周学熙办学所主张和强调的方针。当时,随着近代文明的传入,不少有识之士已认识到“中国学界、工界两不相涉”,彼此脱节,是造成“工业窳败,日甚一日”局面的根源。因此,特别强调工学结合,唯有如此,才能使工业得以振兴。第一、第二小学堂工场实行“工学并逐”、“工学兼营”,造就有一定文化和技能的劳动者,要求“工徒具有学生性质,不致为无意识工匠”,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三,充分运用有利条件,实现既定宗旨和方针。直隶选定在国都北京创办小学堂工场,是一种敢于担当的使命感和负责任精神的体现。而要把这种精神化为实际行动,实施确定的任务,从直隶总督到承办的工艺总局,运用了其所拥有的有利条件。如从组织人事上,借助京师的资源,聘请光禄寺、国子监有经验的官员出面主持筹建,协同安排各类事项。在经费上,由直隶银元局铸币所获得的余利(1902年至1907年3月,共获利达白银193万余两)⑯予以支持、保障。而在工场选定生产项目方面,纺织则是直隶的强项,更因其大多数工序均为手工操作,比较适合小学生工徒。
第四,创新精神和“试开”小学堂工场的创举应予肯定。直隶的职业教育多在青年人中实施,1904年在天津兴办的 “实习工场”,曾招收12~15岁“幼童”为工徒,后又取消。迄今似尚未发现从小学堂着手进行职业教育的。京师一小、二小可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创举。虽然“试开”未取得成功,半途而废,但这种敢于先试的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
如上所说,由于史料缺失,一小、二小何时结束,为何结束,均不得而知。笔者只能从其他文献——《京师督学局一览表》,即宣统元年(1910年)的统计中得知,当时列有“北洋官立第一小学堂、第二小学堂”或“直隶官立第一、第二小学堂”的记载,其学堂地址、成立时间、教职员和学生人数、课程设置等,基本与一小、二小一致,只是涉及“工场”的内容已不复存在。⑰
根据现有史料分析,小学堂工场之所以未能坚持始终的原因,其一是课业多,负担重,“课毕入工场”习工艺,要求过高,学生难以承受。其二是此种做法有使用童工之嫌,与近代文明背道而驰(当年小学生年龄约在7~15岁)。直隶当局用意虽好,却有揠苗助长、操之过急之弊,是不符合实际的;且前有“试开”之言,未能坚持,也就不足为怪了。其三也是重要的一点,常言“事在人为”,1907年,袁世凯奉调入京,升任外务部尚书,1908年,周学熙也应召入京,于农工商部主持开建京师自来水工程,二人均已不在直隶主政。可以说,直隶“新政”的黄金时期已过,应了“人去政息”的那句老话。
事虽如此,开办小学堂工场所提出的“学堂以开民智,工场以兴民业”,“以教养兼资裕贫民生计”,以及“工学并逐”,使“工徒具有学生性质,不致为无意识之工匠”等指导思想,仍是其精华所在,不失其在职业教育史上的重要价值。
注释:
①②③袁世凯:《袁世凯奏议》,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70,1187,1338页
④⑤⑥⑦⑨⑩⑪⑫⑬⑭⑮《直隶工艺志初编》,首都图书馆制网上版,第50-51,52,229-230,231,231-233,235-238,239-240,241-242,231,231-232,231页
⑧周学熙:《周学熙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124页
⑯《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下),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907页
⑰《京师督学局一览表》,首都图书馆制网上版,第36,97页
G718
A
1672-5727(2012)04-0177-02
陈凯(1936—),男,北京市人,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已退休),研究方向为天津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