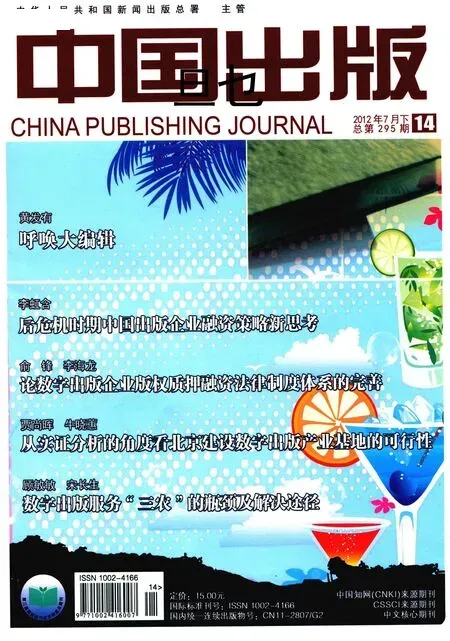《现代评论》与科学传播*
文/沈 毅
《现代评论》(周刊)(以下称周刊)创办于1924年12月,存续四年后于1928年12月终刊。它是以北京大学教授为主体的一份综合性周刊,标榜“精神是独立的,不主附和”,“态度是研究的,不尚攻讦”,“言论趋重实际问题,不尚空谈” 。[1]周刊是新文化运动之后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北京知识界一个很重要的媒体。周刊内容广泛,包括时评、政论、小说、剧本、新诗、科技以及人文学术等,很多题材旨在继承发扬《新青年》民主、科学精神。比较重要的撰稿人有胡适、徐志摩、闻一多、彭家沛、李四光、陶孟和、任鸿隽等。根据统计,周刊共发表与科学相关的文章约30篇,涉及的内容包括科学新知识、中国科学现状、科学研究的地位以及对中西医优劣的评价等。文章大多为国人所写,少数为译作。作者多为自然科学工作者,具有留学欧美、日本的经历。他们学识渊博,平日里学术活动、社会活动均很活跃。
一、对中国科学现状的认识
周刊的作者清醒地看到中国的科学发展水平的落后。如彭泽沛的连载文章《科学的流弊和中国》,介绍了大哲学家罗素对科学流弊的论述,作者不能原谅某些中国人借罗素批评欧洲科学流弊之机,兴奋地寻找反对科学在中国落地生根的理由。他认为,中国还没有资格去谈论科学的流弊,因为中国的现状是“没有科学文明”。“现今中国最大的害恶,是军阀的战争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不是中国科学文明发达的结果。”中国科学还很落后,不配伴着罗素的节拍起舞,任何拒绝科学的借口都是错误的。[2]
署名沧生的文章《中国的科学》细数了中国科学落后的种种表现。作者认为,首先,中国专门的科学研究机构的极度匮乏,大学虽然也开设“物理化学一类的课程”,但仅仅是“一种教书的机关”,“研究自然无从说起”。其次,是社会上虽然有一些科学机构并办有刊物,但数量很少,而且有一些还掌握在外国人手里。作者评论道,“我们虽然不敢附和说中国的科学还没有萌芽,但是我们也没有法子否认中国的科学程度,比人家差得还远”。第三,一些科技类刊物的内容往往不属于独立研究的成果,“拾人唾余”,“东拉西扯,凑成篇幅”。第四,物理、化学类基础学科的科研机构和刊物仍然阙如。[3]
科学的对立面是迷信,当时一般民众对迷信的热衷,反映出科学在中国的尴尬处境。杨幼炯在《民众思想与社会科学》一文中指出:一方面百姓为战乱和贫困生活所折磨,对未来没有信心,听天由命情绪泛滥;另一方面社会上的迷信组织如同善社、悟善社等又在传播迷信,“妖言惑众”,“报纸上关于‘降仙’、‘问卜’以及‘接神’、‘迎佛’的消息,差不多天天都有记载,甚而至于一省的长官,公然以命令行之”。作者感叹道:“我们更不得不疑是置身中古的黑暗时代了。”
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现代评论》刊登的文章在新形势下弘扬科学、扫除迷信,进一步揭示科学滞后、迷信猖獗的现实,对于警醒世人、认清社会改造的目标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对科学地位、科学精神的认识与呼吁
周刊的作者们从多个角度强调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国家和民族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杨幼炯指出,“现在要推翻一般民众的宗法思想,只有科学。因为科学是使人类思想进步的原动力,科学是研究物质实体,创造‘文明’;同时又利用这种系统的,创造新文化……我们就可以进而应用科学的法则,以解释一切社会现象,使民众对于环境生活有明白的认识。”作者对社会科学的社会改造功能表达得更为直接:“社会科学是根据科学的客观性,考察社会现象,用归纳的方法,综观社会现象之公律,而求结论的。所以社会科学是推倒一切封建社会中神秘性文化的利器。”[4]
周刊作者比较多地谈到了与科学精神有关的论断,尽管他们并没有直接使用“科学精神”的概念。陶孟和提出要正确地看待科学,科学是一个整体,不仅指自然科学,也应该包括社会科学。他认为时下片面为自然科学喝彩而冷落社会科学是很不正常的。他强调科学研究应“是指一切的科学研究,宇宙间一切的现象,自然的与人群的都包括在内”。他既否定传统文化对自然科学的轻视,也否定近代以来把国运不昌狭隘地归结为自然科学不发达。他在《社会科学的否运》认为“中国的前途,独立的,光明的前途仍然与社会科学同命运”。他指出,凡涉及中国几亿民众的社会组织、生产分配、权利义务,以及“实现社会的平和,与社会的公道”等问题,离开了社会科学是根本无法解决的。[5]
作者也探寻了中国科学长期落后、不成气候的原因。沧生认为除了社会不良外,还在于国人目光短浅,对科学事业的重要性认识不足。[6]陶孟和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论题,统治者是不希望社会科学真正发展的,“军阀的意志便是法律,枪刺的权威主持公道”。[7]“统治阶级所最希望的是人民的愚鲁,人民的驯服……他们所最不喜欢的是学生,尤其是学社会科学的学生”。陶孟和还指出,中国社会存在的浮躁风气妨碍了正确的科学观的建立。他感叹很多中国人热衷于表面上的大轰大嗡,满足于浅薄的写作,陶醉于廉价的吹捧。[8]任鸿隽同样感叹:“我们晓得在现在的社会中,要找飞扬浮躁的人才,可算是车载斗量,但是要找实心任事、不务虚名的人,却好似凤毛麟角。”[9]一个民族若不重视提倡和培养无条件的钻研精神,每一位个体若达不到以无条件钻研科学为乐趣的境界,真正的科学在这样的国度里是不会扎根的,属于全人类的创新和建树也与其无缘。中国自科举制度建立之后,读书人的行为就打上了功名的标签,对儒家思想的“信仰”也建立在功利基础之上,所读之书和科学也没什么关系。在这样的一种传统文化的氛围中若想培育起严谨、求真、心无旁骛的科学大树,谈何容易。
作者在撰文中提出了科学态度的问题。在他们看来,科学态度的树立对个体、对国家都是非常重要的。这种科学态度,就是老老实实,实事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夸大、讳言、矫饰是很突出的坏毛病,是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的死对头,如同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一针见血指出的:“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仪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10]胡适一向提倡讲老实话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新文化运动时期任鸿隽也强调科学的本质在于承认事实:“我们要晓得科学的本质,是事实不是文字。”[11]周刊对科学态度的宣传正与《新青年》精神一脉相承。杨幼炯在《民众思想与社会科学》中批评说,中国社会科学界存在的诸多问题的实质,多为不尊重事实,不重视实际,主观臆断,投机取巧。他说有的学者“抄袭外国材料,以外国学者片面的理论作根据”;还有的学者把社会科学“当做哲学研究,不从事社会实地调查,对于民众思想与社会现象,尤漠不关心,缺乏科学家实验的精神造成‘闭门造车’的谬误”。[12]
周刊刊载的文章有理有据,循循善诱,在揭示中国科学发展水平落后的基础上系统阐释科学地位、科学精神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其宗旨在于让国人充分认识科学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让国人摒弃妨碍科学发展的陈规陋见,推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比翼齐飞。
三、科学知识宣传与中西医对比
《现代评论》(周刊)传递了中国科学活动的信息和科学研究的动态。如1925年1月24日刊登了李四光(署名仲揆)的《中国地质学会开会纪略》,记述了中国地质学会第三次年会的情况。该文特别提及了几篇具有研究价值的、论述中国鄂西及甘肃、青海地质构造的论文,并特别指出科学论文能够引起“普通社会”对科学探索的兴趣,如古生物学与勘探的关系,《火星有人类居住么》等文章。[13]
对中西医争论是由署名西滢(本名陈源)的一篇《闲话》引发。该文对协和医院误诊梁启超病情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批评。由于在协和医院的误诊,梁启超在手术中被误切除一侧肾脏。陈源因此激烈地抨击西医。陈源是留学英国的博士,时为北京大学教授,大概是出于对他所崇拜的梁启超遭遇不应有的医疗事故的愤慨,行文之间表现出明显的情绪化。他认为协和医院在拿病人“做试验品”,“协和的医生,在美国,也许最多是二三流”,“疑心就是西洋医学也还在幼稚的时期,同中医相比,也许只有百步和五十步的差异”。[14]
此后,周刊发表了支持和批评的稿件。前者指责协和医院,言语之间激愤多于说理。后者指出所谓梁启超被无端地拔了七颗牙属于道听途说,不满意陈源作为热心“提倡科学的人”,居然对中医“大致其拳拳之意”。批评者希望国人能善待西医:“科学在中国方是萌芽时代,爱护,培养,鼓吹,提倡,很为必要,不当于其破绽处加以宣传,阻碍她的发展。”[15]
面对批评,陈源也做出了调整。陈源的变化显然也与梁启超本人对待协和医院及科学的一番高姿态表态有关。梁启超1926年6月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专门澄清了对西医的误会。他说,“协和这回对于我的病,实在很用心……我真是出于至诚的感谢他们。协和组织完善,研究精神及方法,都是最进步的,他对于我们中国医学的前途,负有极大的责任和希望……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16]
这场辩论的意义在于帮助人们理性地看待西医和科学。辩论的效果或许令刊物和编辑们始料不及,陈源批评文章的刊发对发起辩论显得有些仓促,险些演变成声讨科学的导火索。但对于提倡和捍卫科学这个大目标来说,这场辩论的结局还是理想的。
《现代评论》(周刊)的出版,在强化科学理念、营造科学氛围、丰富科学知识和培养科学情趣方面,扩大了科学观念的传播,对驱除社会上弥漫的反科学的雾霾产生了积极作用。从报刊业务的角度审视,有的文章偏于专业化倾向,抽象理论阐述偏多,不免枯燥。对科学内容的定位尚不成熟,未能很好地解决专业、科普和舆论导向三者的关系。文章的学科分布也有些不平衡,地质、天文、生命科学等偏多,其他学科显得薄弱。另外,周刊文章的轰动性少,没有形成必要的“热点”。相比之下,此前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存续不过一年半,在科学传播上曾发起过声势浩大的“科学玄学论战”,对捍卫科学的神圣地位作用卓著。
注释:
[1]现代评论(影印本)[M].长沙:岳麓书社,1999,第1卷,第1期,第2页
[2]现代评论(影印本) [M] .长沙:岳麓书社,1999,第4卷,第89期,第5页
[3]现代评论(影印本) [M] .长沙:岳麓书社,1999,第5卷,第118期,第4-6页
[4]现代评论(影印本) [M] .长沙:岳麓书社,1999,,第3卷,第63期,第9页
[5]现代评论(影印本) [M] .长沙:岳麓书社,1999,第4卷,第80期,第6页
[6]现代评论(影印本) [M] .长沙:岳麓书社,1999,第5卷,第118期,第6页
[7]现代评论(影印本) [M] .长沙:岳麓书社,1999,第4卷,第80期,第4页
[8]现代评论(影印本)[M] .长沙:岳麓书社,1999,第4卷,第80期,第6-7页
[9]现代评论(影印本)[M] .长沙:岳麓书社,1999,第6卷,第144期,第14页
[10]《胡适文集》(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76页
[11]袁伟时.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 373
[12]现代评论(影印本)[M].长沙:岳麓书社,1999,第3卷,第63期,第10页
[13]现代评论(影印本) [M] .长沙:岳麓书社,1999,第2卷,第47期,第18-19页
[14]现代评论(影印本)[M].长沙:岳麓书社,1999,第3卷,第75期,第9-10页
[15]现代评论(影印本)[M].长沙:岳麓书社,1999,第5卷,第114期,第18页
[16]夏晓红.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