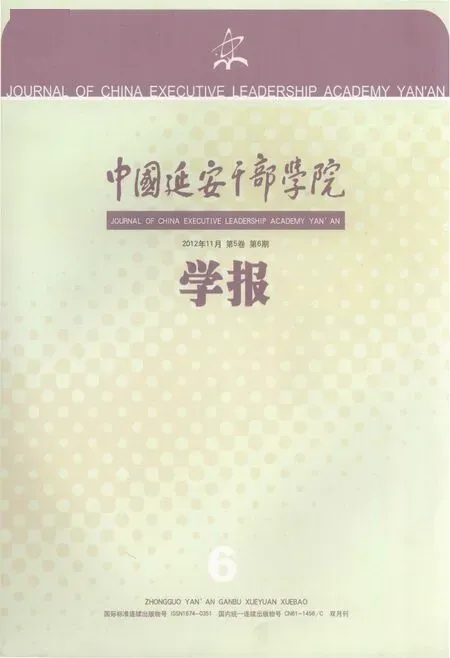中国政党制度创制得以成立的理论根据
孙 津,张 丽
(北京师范大学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海淀 100875)
中国政党制度创制得以成立的理论根据
孙 津,张 丽
(北京师范大学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海淀 100875)
中国的政党制度运作有效、成绩斐然,但却相对欠缺专门理论体系的根据支撑,而当今通行的(即所谓西方的)政治学又不能为这种理论根据提供准确理解和分类规范。针对这种情况,本文的分析论证表明,中国政党制度创制得以成立的理论根据,在于它具有范畴沟通及其应用的普适性、特色创制的合法性、以及道义为善的合理性;从学科意义上讲,这种创制的理论同样可以具有与通行政治学进行沟通和范畴应用的相应话语;中国政党制度的特殊性和普适性提供了政治学理论的创新内容,其主要含义在于创制与发展相同一的政治文明。基于这些认识,本文针对如何改变当前理论滞后于实践的情况、以及建构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范畴普适性的政党理论体系,提出了切合实际的思路。
中国政党制度;政党创制;政治发展;民主政治
一、问题的提出
所谓理论根据,是指反映和说明普遍联系的参照、范畴和方法,因此,虽然中国存在着真实的政党制度,中国也以白皮书的形式阐明了这个制度的性质和内容,[1]但这并不等于从理论上给出了这个制度的成立根据,而所谓理论滞后于实践的情况指的也就是这个意思。之所以这样说的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的现实:一方面,国内学术界对于中国政党制度的研究基本上是依据既定制度和相关文件所作的再阐释,所以还不能算是以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来给出这个制度得以成立的理论根据;另一方面,通行的(也就是所谓西方的)政治学并不能解释中国的政党制度,尤其是在它的政党制度分类中找不到适合中国的情况。
于是,问题提出的针对就在于,关于制度创制的理论必须在参照、范畴和方法等方面具有普适性,才能够支持这个制度及其创制特性的可理解性和真实性。但是,提出这种理论根据并不是说要以西方为标准,恰恰相反,它表明中国政党制度创制在理论上的普适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它应该具有能够和通行政治学关于政党分类标准相适应或相沟通的话语参照及认同;另一方面,它应该能够以其独特的创制弥补通行政治学的缺陷,或者说能够贡献出被认同的创新理论。如果只讲合法创制的特殊性而缺失学科分类的普适性,中国的政党制度可能就只是一种得不到理论认同、或者说缺失范畴应用功能的自说自话,即它可能是一种制度,但却很难说就是具有“政党”属性、或者“政党”这一概念规定性的制度,也无法仅靠自我宣称来证实这个制度具有道义为善的合理性。
从范畴的普适性来讲,政党制度得以成立的理论根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即基本参照的普适性、自身创制的合法性、具有道义为善的合理性。相对说来,基本参照的普适性是指在学科意义上普遍认同的、以及可作为范畴进行沟通应用的政党规定性,如果某种政党理论只能用来解释自己特定的现实,就很难说它具有了普适性;合法性指的是执政能力的有效性,并由此来保证政党和政党制度创制的特殊性;合理性指的是政党制度具有和体现了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并以此来表明相应的合法性具有道义为善的性质。必须说明的是,这三者相互关联,缺一不可,本文对它们作分别讨论仅仅是为了表述方便。
简括地说,中国政党制度创制的普适性主要在于现代国家运作的必须性,以及具有与通行政治学理论相一致或可沟通的政党分类规范和执政功能;合法性主要在于政治导向的选择性和有效执政的持续性;而它的合理性则体现为创制与发展相同一的、以及道义为善的政治文明。这些方面包括很多内容,不过就问题提出的针对性来讲,下面的讨论侧重于中国政党政治创制在理论上的普适性。换句话说,所谓理论根据在本文的讨论主要包括两层含义。其一,说明中国的创制不仅可以具有能够与通行政治学沟通的话语,并且可以相应地弥补它的理论缺陷;其二,说明中国政党制度在理论上的普适性、合法性和合理性主要是由创制和发展的同一性来提供和保证的。由此,我们的讨论大致包括三个主要方面,即能够和通行政治学相沟通并作范畴应用的理论普适性、自身创制所具有的合法性、以及由创制与发展相同一的政治文明所体现的合理性。
二、基本参照的普适性
在当今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是以政党为载体来运作政权和实施领导的,因此,作为中国政党制度创制合理性根据之一的现代国家运作的必须性,在此就没有必要讨论了。问题在于,不仅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政党制度,而且不同政党的政治属性也是有区别的,甚至是相对立的。因此,从理论上讲,判定政党和政党制度的规定性就需要某种具有普适性的基本参照,从而也才有可能将某种创制的理论和通行政治学相沟通并作范畴应用。
大致说来,政党制度的划分根据包括政党数量和是否具有政党竞争两类,不过就本文讨论的问题来讲,比较适合的类型针对有三种,在通行政治学中分别叫做极权(totalitarianism)、威权(authoritarianism)和民主(democracy)。其实,虽然这种分类的参照主要指是否具有政党竞争,但其含义指向应该是政权形式,因为任何政党制度都是对权力运作的安置和规范。因此,这仍是一种形式上的分类,其具有范畴作用的相关话语并未包括政党制度本身的政治导向性或价值观。比如,这种分类根据意识形态的强烈性和全面性,把希特勒时期的纳粹德国政权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政权都算作极权类型,全然不管这两种意识形态在政治导向和价值观方面的本质区别。同样,这种分类实际上是以“民主”为基准的,而这种民主的含义是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类型来确定的。因此,这种分类其实一方面自己已经确定了某种政治导向性或价值观,另一方面却在分类时假装形式上的价值中立。
由于上述状况,通行政治学的这种分类很难解释中国的政党制度。为了弥补这个缺陷,也就是避免违背“无遗漏包含”(inclusiveness)这项分类原则,创制话语的普适性参照就必须引进政治导向性或价值观这一考虑因素或维度。但是,在通行政治学中,“政党政治”专指通过议会或总统选举由获胜的政党执政或联合执政的政治制度,因此并不适用中国这种具有政治导向和价值观的政党制度。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政党制度以及政党政治本身都是一种创制,所以其理论根据并不能由创制本身来保证,换句话说,普适性的理论根据需要有某种基本的判断参照。
根据普遍存在的事实,可以认为这个基本参照就是政党的执政属性,因为无论从现代国家运作的必须还是从通行政治学对政党的理解来看,算不算政党的根本依据,在于它是否具有执政资格。在采取两党制或多党制的国家或地区,任何政党都具有执政资格,执政党与在野党或反对党的区别并不是指属性的执政与否,而是在于某届或某次选举的胜与否。但是,政党在中国却是有着执政和参政区分的,而八个民主党派的职能就被定为“参政”。因此,中国政党制度在其理论根据方面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参政党”这个创制的话语是否具有基本参照的普适性,也就是说,八个“参政”的民主党派算不算政党。从逻辑上讲,它们如果算是政党,中国就是创制了一种多党合作制;如果不是政党,中国就仍是一党制。但是,问题并未到此结束。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在谈到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的政党分类时认为,“一党制”是个错误的概念,因为“政党体系”的本意是指某种构成的复数,所以如果只有一个执政党,就应该叫做“党国制”、“党国体系”甚至“独裁制”。[2],[3]如果是这样,问题就不仅限于分类的普适性参照了,同时更涉及到合道义性或道义为善的问题,因为“党国制”和“独裁制”都有悖于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叫做不民主。
为了表述方便,我们先用通行政治学能够理解的话语,简括说明中国政党政治在新型政党概念上的五个主要创制内容。第一,以相同的政治属性建立合作联盟并以此作为复数政党成立的排他性原则;第二,执政和参政的地位及其职能是政党体系内部的法定区分;第三,体系内某些政党的成立不必以执政资格和要求为前提;第四,体系内某个政党可以放弃执政资格并自觉接受另一个政党的领导;第五,政党以体系的方式实施执政功能。通过这五个方面可以看出,中国政党制度创制的特殊性在于,所有政党都属于同一个政治性质,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政党的执政功能是以体系的形式来实现的。
上述创制及其话语至少在两个主要方面具有理论的普适性。首先是性质选择的普适性。对于任何政党来讲,政治信念和导向坚持都是一种选择,所以不管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还是别的什么主义,政治信念和导向坚持作为政党制度的政治特性,其普适性都在于选择的基本参照是由选择本身来提供和保证的。在这个意义上讲,两党制或多党制在政党对其政治属性选择方面的规定性,并不与中国政党对同一个政治属性的选择相矛盾。其次是执政形式的普适性。在这方面,中国创制了一种体系形态的执政形式。根据上述创制内容(尤其是第一和第五),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都是政党,因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民主党派的参政职能恰恰是复数的政党体系内部的法定分工,而民主党派一方面作为政党体系的构成部分,另一方面主要通过参加政权和政治协商等方式,与共产党共同承担和实现政党体系的执政功能。因此,这种政党制度基本参照的普适性就在于,它的性质选择和执政形式是高度统一的。
具体说来,合作型政党制度在基本参照上得以成立的理论根据,主要在于九个政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认同、以及体系内部的法定分工。这种根据之所以具有理论的普适性,在于它提供了与通行政治学沟通的同类话语,因为世界上的政党尽管政治属性不同,但也有以此话语为参照的情况。比如,两党制一般都具有相同或近似的政治理念、合伙或共同组阁必须依据至少是阶段性或协商性的体系内部的法定分工等。如果通行政治学把两党或多党的情况叫做政党的竞争类型,那么,依据这个逻辑恰恰并不存在排斥合作型政党制度的理由,因为多个政党的合作本身就有各种形式,包括它们对执政形式的选择。其实,就话语的使用来讲,中国的“多党合作制”本身就具有基本参照的普适性,因为表示政党类型的政党制的“制”在英语是“system”,其含义就是指政党类型的体系形态。尽管“制度”在英语是“institution”,表示具有法律形式的政权规范,但中文有时候也把“system”翻译为“制度”,其根据正在于制度也是具有体系形态的。
由于通行的政党理论看不到、或不愿承认中国政党政治对于合作型政党制度创制在基本参照上的普适性,同时在这种通行的理论框架内也不能正确理解并合理解释中国政党制度的特殊性和普适性,所以与中国合作型政党制度创制的相应理论就应该具有弥补通行政治学缺陷的意义,或者说应该是被认同的创新理论。撇开故意不予认同的偏见不谈,中国政党制度创制的基本参照具有理论普适性的另一个重要根据,就是作为分类原则之一的经验针对性。其实,这就是指现实存在的真实性和延续性。比如,萨托利曾针对所谓的一党制又细分出了“霸权党”的类型,包括波兰改革之前的意识形态型共产党和墨西哥的务实型制度革命党。但是,由于这两个党后来都不执政了,或者说具有原来特性的那两种政党都不存在了,所以萨托利本人和通行政治学都认为,此项分类已经由于缺失了经验的针对性而失去意义。比较说来,林兹(Juan Linz)在提出所谓军事威权型政党时,针对的也只是西班牙佛朗哥时期的情况,[4]但是,此项分类仍可以用来分析现在一些军事政变后的政党,所以仍然有效。在中国,不仅现实存在着有效的多党合作制,而且看不出可以预测它将被否弃的理由,因此,从创制话语的基本参照来讲,合作型政党制度的分类普适性也是得到经验针对性原则支持的。
但是,仅仅从形式分类的角度讲中国政党政治创制的普适性参照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现有的分类不过是一种分析框架,并不能保证将创制话语纳入普适性参照,更不能取代理论的解释。事实也正是如此,即现行政治学可以用它不明说出来的理由,否认中国政党政治创制的普适性。比如,它可以根据选举的方式、竞争的开放性、以及人权的状况等标准,认为中国的政党政治仍不具有民主性质,所以不能算是合作类型;或者认为,由九个政党构成的排他性政党体系违背了分类的“相互排斥”(exclusiveness)原则,所以合作型也不能成立,仍然应该属于极权型或威权型。其实,这种情况恰恰表明,通行的形式分类标准和话语本身就是有缺陷的,比如“民主”的含义在这种分类形式中就是先定的内容,并由此否定了新型民主的创制可能。因此,必须引入政治导向和价值观的维度,不过这些将结合后面两节的具体内容一并讨论。
三、特色创制的合法性
可以看出,以上关于具有普适性基本参照的创制话语讨论,主要侧重的是与通行政治学的学科沟通和范畴应用,所以省略了这种普适性的合法性支撑;同样,这一节的合法性侧重讨论中国政党制度创制的特殊性,但也并非等于这种创制没有相应的理论普适性。其实,合法性指的并不是有什么法律依据,而是指以法的效用行使权力的能力,包括制定什么样的法本身。因此,创制具有自身特色政党制度的合法性的主要理论根据,在于创制本身的有效性。但是,这种有效性或能力的理论根据也必须具有普适性,否则就可能只是某种粗俗的工具主义或胜者为王的霸权主义。由此,这一节主要针对新型政党创制的现实根据、代表性的逻辑根据、以及权威维持的过程根据等方面,分析特色创制的合法性所具有的范畴普适性。这三者虽然具有概念的递进关系,但作为合法性的基本构成方面也是互为表里、相互作用的,而与这种合法性相一致的合理性、也就是合法性在道义为善方面的理论支撑,将在下一节讨论。
首先,作为合法性,新型政党创制的现实根据不仅是历史形成的,而且是持续有效的。前面已经从基本参照的普适性角度,说明了新型政党创制可以被普遍认同的根据,但是,这在中国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就是共产党有一个经过武装夺权而进入和平掌权的变化。对此,一般的看法是说共产党有一个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问题。其实,这种看法并不准确,而且误解多多。当共产党自己这样说的时候,其含义在于如何针对新形势和新要求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执政能力。但是,这种说法在社会上、学术界、以及国外的看法却很混乱,并体现出两个主要的误解。其一,认为革命党和执政党是性质不同的政党概念;其二,认为执政党必须实施民主政治,所以应该进行民主化改革,包括逐步走向多党制。这些误解说穿了就是一个意思,即共产党如果仍然坚持它作为革命党的政治品格,包括仍然排斥多党制的可能,其制度创制的合法性就仍是不充分的,或者说是缺乏理论普适性的。
上述误解既不符合事实,也是对概念的偷换。共产党从干革命初期开始就以执政为核心目标,并且在有了井冈山这个根据地之后就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此后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共产党就在其所控制的地方建立政权并有效地执政,包括在半控制状态的游击区,也以武装拉锯或地下隐蔽等形式实施政权功能。事实上,中国革命的成功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军事胜利,而是共产党政权挤占、瓦解、并最终赶走国民党政权的过程。因此,不仅共产党历来就是执政党,而且其各种制度创制的针对也不是指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而是为了提高执政能力和实效。所谓偷换概念,就是把共产党所具有的革命品格当成了某种政党类型,不仅割裂了政党品格的延续性和发展性,而且抹杀了不同政党的政治特性。一般说来,作为政党类型的革命党有一个共同的分类参照,就是以夺取政权为核心目标,并且这个目标及其手段都是非法的,否则就不叫革命了。但是,这种分类本身并不涉及革命党品格的延续。从经验的针对性来讲,夺权任务完成后革命党就不存在了,但没有理由说革命品格不能延续和发展,也没有理由说这种延续和发展不能由原来作为革命党的那个政党实体来承载。恰恰相反,中国共产党对于新形势下提高自身执政能力和实效的要求,正是以保持和发扬其革命品格为前提和原则的。因此,在发展的同时,这些品格仍然真实地存在着,包括矢志信仰、忠于领袖、铁的纪律、秘密组织(指党内党外的区别)、廉洁操守、牺牲自我、甚至大义灭亲等。
其次,除了现实针对和普适参照,创制的合法性应该有其自身的逻辑根据,这就是共产党所宣称的,自己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及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但是,由于这种代表性(即“三个代表”)是排他的,即只有共产党具有这种宣称的唯一合法性,并由此在逻辑上排除了多党制可能,所以就有可能产生循环论证的问题,即仅靠自我宣称来论证逻辑根据。为了解决这个理论问题,逻辑根据的普适性至少应该具有两个方面的针对性,一个是比较,另一个是特性。
所谓比较,就是指不同政党的执政根据,也就是说,与形式分类不同,这种根据指的是政权合法性的自身逻辑。对于实行两党制和多党制的政权形式来讲,合法性的自身逻辑是“代议”,因为政党既不宣称、也没有资格代表什么,它只是许诺自己有能力把共同体(一般就是指国家)的公共事务做好。在这种逻辑中,政党和选民之间是一种“商议”权利的交易关系,选民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让渡给政党,政党以这种让渡本身作为获得执政权力的资格,并“代替”选民去执政。中国则不同,共产党不仅宣称自己具有上述三个方面的代表性,而且就以此作为自己执政的合法性根据。在这个逻辑中,“代表”和执政具有职能的同一性,即代表就是执政。因此,虽然各国都有选举,但中国的选举是形式,两党制或多党制的选举则就是内容本身。这种比较的普适性在于,“代议”和“代表”都没有可以用来否定对方不是在有效执政的根据。
所谓特性,主要是指政治属性的一致性。共产党从成立那天起就不隐瞒自己的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所以,“代表”的合法性从逻辑上讲是内在于共产党的政治品格的,否则这个政党就不能算是共产党了。可能的问题在于,其一,这种代表性为什么是排他的;其二,如果实效证明共产党没有履行好她所宣称的代表执政要求,是否意味着它应该失去代表或执政的资格和能力。其实,这两个问题所体现的普适性恰恰都是真实的逻辑根据,或者说,它们所回答的都是理论根据而不是现实状况。事实上,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哪个政党像共产党那样,宣称自己的成立根据和最终目标都旨在最终达到阶级、国家、以及政党本身的消亡,因此,作为合法性的排他性代表恰恰表明了政治属性的一致性,以及共产党对这种一致性的坚持。至于事实是否很好地实现了这种“代表”应该具有的职能要求,共产党的回答是她可以、并一直在以各种方式自觉纠正自己的失误。这种回答当然也是合法性的排他性的题中之义,但从理论上讲,更是和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相一致的,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已经主张并设置了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从方法论的角度讲,这种逻辑类似库恩的“范式”理论和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不仅自身发展可以以范式的方式进行,研究纲领更可以保证各种变化不会导致理论“内核”的失效。[5]因此,这种政治属性的一致性表明,内在逻辑作为政党创制的合法性根据可以具有相应的理论普适性。
第三,创制的合法性既然是一种权力运作的能力,政党本身必须具有权威的根据,并由此支持能力持续更新的过程。权威的形成因素很多,但问题在于是否、以及如何服从权威。自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并论述了科层制的问题以来,个人因素与职务规范的理论区分似乎已经瓦解了权威在政权运作中的合法性,而西方国家在运作中也宣称政治权威只在于法律或上帝。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不仅法的观念是属人的,法律更是人定的,只不过各主要政党如果不想改变政权的性质,权威的作用就不很重要,甚至个人权威还被认为是有悖民主原则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权威是内在于它的执政能力的,从历史事实来讲,这就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但是,民众是否服从这种权威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在许多西方学者看来,服从权威是中国人的传统,比如所罗门(Richard H.Solomon)通过他所谓的实证研究认为,中国人确实具有阿多尔诺(Theodore W.Adorno)所说的“权威型人格”。[6],[7]不过,所罗门也认为,他的研究表明毛泽东是反权威的,而且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中国人也不再盲从权威了。无论这种看法是否符合事实,有一个问题却是真实的,即权威持续的过程能否真实地支撑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其实,这个问题的理论普适性就在于“过程”本身,也就是什么时候、以及是否真的需要放弃权威。比如,资本主义政权开始是排斥政党政治的,后来不得已采取了竞争型的两党制或多党制,经过数百年政党社会化的历史,所有政党都不再担心权威问题了,而且事实上也几乎没有哪个政党能够真的树立起自己的权威。因此,权威提供的合法性是否具有理论的普适性,取决于权威持续的具体过程。根据同样的道理,对于有过长期武装夺权经历的政党来讲,具有权威必然是一个更长时期内都需要关注的问题,所以这恰恰表明了过程根据本身作为合法性的普适性,而不是权威需要维持与否的合理性。因此,无论通行政治学所谓的“威权型”政党,还是孙中山提出的所谓经由军政、训政到宪政的演进阶段,对于权威维持的过程根据来讲都是不得要领的。
四、创制与发展相同一的政治文明
上一节主要从有效性角度讨论了中国政党制度创制的合法性,但是,具有创制能力本身并不就能保证创制具有道义为善的合理性。所谓合理性,原意是指合乎理性(rational),所以实际使用时就包括有道理、有根据、有效性、正确性、以及科学性等多种含义,也包括前面说的话语沟通(包括分类标准、范畴应用、概念理解、方法规范等)的普适性。但是,当分析同一个事物或概念的时候,合法性主要指某种能力的特性,合理性则是指道义为善的特性,也就是符合普遍认同的价值观。比如,现在几乎所有政党政治都否定纳粹型政党,但这并不等于当时纳粹的政党制度不具有合法性,而是指它违背普遍的道义认同,所以不具有合理性。因此,在说明了创制话语所具有的范畴普适性、以及创制体现的合法性特征之后,这一节主要是把普适性、合法性和合理性结合起来,从范畴的可沟通和可应用角度说明,中国政党制度创制得以成立的理论根据主要是由创制和发展的同一性来提供和保证的。
对于中国政党制度来讲,创制和发展都具有鲜明的政治原则和导向,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很显然,“中国特色”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解释的概念,否则它将由于仅仅具有形容词的语义而失去范畴使用的功能。的确,从中共“十三大”以来,历届党代会都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含义表述,而且内容逐步丰富、旨向日益明朗,“十七大”更是明确指出,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8]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正在不断完善的理论建构,而且也是具体创制的实践过程。也许正因为如此,国外学术界在研究中国特色或者中国模式的“属性”时,使用的仍是具有范畴普适性的话语,比如国家资本主义、政府集中管理和计划的经济、务实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等。①出于同样的考虑,本节从范畴的可沟通和可应用角度,在把创制与发展的同一性作为中国政党制度创制的理论根据的合理性时,采用的是“政治文明”这一具有理论普适性的概念,表示创制和发展都具有道义为善的同一性质,而就对这种文明的核心含义的普遍认同来讲,主要指的就是民主政治。
事实上,任何政党制度都需要创制,资本主义政党政治及其政权的两党制和多党制原本都是一种创制。中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境况下建立社会主义的,所以它的政党制度更体现为一系列的创制。先是共产党自己建立革命政权以打倒反动政权,然后是联合各民主党派建立联合政府,直到形成比较完备的多党合作制度。就这些创制的合理性来讲,有一个道义为善的共同根据,就是现代化的必须。正是因为这个合理性,而不是出于政治理念或意识形态的考虑,现在中国才明确主张,各国都有选择它认为合适的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权利。因此,政党制度不仅只是形式,即前面讲过的既可以有竞争型政党制度也应该可以有合作型政党制度,而且作为内容的导向选择也可以具有同样的或相通的合理性,即现代化建设和竞争的需要。
但是,不同的现代化境况或程度有可能带来合理性在具体内容上的区别。现代化的真实含义,就是全球范围穷国追赶富国的竞争运动,[9]因此,一方面,现代化作为道义为善的合理性对于各种政党制度都是一样的和真实的;另一方面,由于在竞争上处于优势和劣势的差异,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政党制度合理性根据也是有区别的。比如,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不得以污染为代价,而穷国对于这个道义为善的主张也没有反对的理由,但实际上穷国要做到这一点其追赶富国的负担就必然加重。因此,道义为善的合理性就可能成为某些国家保持自己竞争优势、转嫁污染、采取双重标准等做法的根据,同时也成为加剧发展不平衡的制度原因。换句话说,尽管各国都主张不要搞“零和游戏”、应该在竞争中取得“双赢”,但是,由于合理性在具体内容上的区别,真实的情况只能是“零和转嫁游戏”,即“双赢”或“多赢”的游戏者们所获得的其实是没有参与进来的游戏者们所失去的。
正是由于上述合理性在具体内容上的区别,道义为善也就可能存在真伪之别和程度差异。在这方面,中国政党制度创制的合理性显得更为真实,其道义为善也具有更高的程度,因为这种创制是和发展相同一的。具体说来,在国际方面,中国坚持国家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与此相一致的政党关系原则,不仅承诺永远不搞霸权主义,而且主张不同政治属性政党的和谐对话;在国内,中国强调多党之间的互相监督,注重各政党的自身建设,要求党内民主和党际和谐。这些主张和做法表明,中国的政党制度既坚持政治理念的导向,也讲求灵活务实的效用,因此,政党创制和政治发展所体现的是一种内容和形式、目的和手段同一的政治文明。
比较看来,制度创制的合理性可以在现代化必须的意义上成立,但是政治发展的合理性就要依具体的政治理念和实际行为来判定了。在通行政治学的理论中,“政治发展”原本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提出来的,主要是指在不民主、或者欠民主制度中的政治应该如何发展。这种含义的成立有一个基本前提和立论指向,即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是民主国家了,所以政治发展的目标参照就是西方的民主制度和价值观。显然,这种含义如果作为普遍认同的政治学概念,其合理性的道义为善或者是片面的,或者是程度不高的,甚至由于其自我中心主义而成为虚假的。与此不同,政治发展在中国的含义主要指社会主义民主的创制,从机制层面讲,一是如何对待政治系统的结构分化,另一是如何应对社会的自主性。
就中国政党制度的创制来讲,政治发展在合理性方面的道义为善主要也是指政党政治的民主性,但这种民主具有明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导向,所以创制和发展才可能构成内容和形式、目的和手段相同一的政治文明。对于这种政治文明,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理解。比如,针对政治系统的结构分化以及社会对自主性的要求,于建嵘认为需要改变政治增压机制,提高政治治理的有效性,所以现阶段应该采取“法治式的威权政治”,最终达到实现宪政与民主的目标。[10]林尚立则认为,针对新的形势,中国共产党要在有序民主化的基础上有效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成长,就必须积极地将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有机结合,从而在政治上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长效动力。[11]还有的研究认为,中国社会稳定有序发展所需的宏观性政治功能主要都是由政党结构提供的,也就是政党政治的政治稳定功能、低代价政策优化功能、合法性功能和社会整合功能。[12]
尽管有不同看法,但这些观点所围绕的话题恰恰表明,政党创制与政治发展的同一的含义,主要是指这两方面在性质和功能的一致性,而其针对就是以民主政治为核心内容的政党政治文明。从合理性的普适性来讲,民主当然是一种普遍认同的价值观,而从政党政治来讲,主要是指保证人民对于政权合法拥有、共同治理、以及利益分享的权利。但是,就民主也是指国家形式来讲,各国的民主模式并不相同,所以通行政治学更多关注的是民主运作和实现的形式。至迟从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开始,民主的主要含义就是竞选,即通过选举和竞争来达到政治决策权的制度安排。[13]林兹也是这样认为的,不过可能出于对西班牙佛朗哥时期威权政体的担心,他更多关注和研究了自由竞争和社会结社的形式和作用。[14]根据这种对民主的理解,达尔(Robert A.Dahl)提出了民主政治的8项基本要求和标准,其核心问题是政治参与的扩大和政党竞争的开放,并将此称为一种理想的多元政体。[15]唐斯(Anthony Downs)不仅同意达尔的观点,而且从经济学的角度认为,民主就是指由选举产生公职人员和政党之间的公平竞争,因此,政党执政就像公司推销产品一样,即政党提出一些不同的政纲或政策以及职务候选人,让选民来投票。[16]
很显然,大概正是出于西方国家的这种政党实践,通行政治学就认为民主的内容是由形式来决定的。形式当然至关重要,尤其是程序民主对实质民主的保证作用,但是,这种理解也存在忽视内容的政治特性的偏向,因此其合理性的道义为善程度就不高。在中国,民主的价值观及其运作形式是同一的,目的和手段也是同一的,而且其运作形态十分丰富,包括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多党合作制度、政治体系内的民主集中制、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过程协商和终端票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区分与转化、政治生活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社会治理中民主与法治的结合、以及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等。
中国的这种民主模式已经在实践上证明是有效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实行的是一种实用或务实型(pragmatic)政党制度,而只是证明了一个理论性逻辑,即虽然不能说中国创制的政治文明就是所有民主模式的标准,但却说明它不必以西方的各种民主模式为合理性根据。在这方面,各国都有一个普适性的道义为善最低标准,就是减少政治浪费。尽管对于怎样的民主模式可以减少浪费,不同的政党制度可以有自己的判断,但事实上现在西方的选举几乎等于表演,既没有价值导向,也没有负责态度。一方面,政党的纲领、政策和意识形态都服从选举的成功,所以都可以随机改变;另一方面,选民尽管有选择倾向和意愿,但也都潜在地认为,因为有了形式民主的保证,被选出的代理人干不好把他换掉就是了。其实,不仅这些情况所反映的是一种不计政治成本的态度,而且各种选举不断、政党更换频仍、政策久议难决等实际状况,更是时刻都在增大政治成本。因此,相对说来,中国的政党创制,尤其是以内容与形式相同一的方式对待和设计选举,以及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等做法,确实更能够减少政治浪费。事实上,即使从程序民主的重要性来讲,内容和形式也是不可割裂的。比如,美国的政党制度和政治体制都被认为是高度民主的,但恰恰是为了减少形式民主造成的政治浪费,两大政党都没有关于决策的形式或组织载体,而是直接交由总统来主持决策会议,包括内阁会议和国家安全会议。奇怪的是,通行政治学只是将此作为民主模式在政体分类中的总统制,却不谈这种体制也具有威权体制的独断性(arbitrariness)因素。
五、简括的结论
针对“问题的提出”,上述分析讨论至少可以说明三点。第一,中国政党制度创制得以成立的理论根据,在于它具有范畴沟通及其应用的普适性、特色创制的合法性、以及道义为善的合理性;第二,从学科意义上讲,中国政党制度的创制可以具有与通行政治学进行沟通和范畴应用的相应话语;第三,中国政党制度的特殊性和普适性提供了政治学理论的创新内容,其主要含义在于创制与发展相同一的政治文明。
由于这三点,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党理论就是完全必要、非常适时、切实可行的;而对于这三点的重视和认识,也为改变当前理论滞后于实践的情况、以及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党理论体系提供了切合实际的思路。当然,这也只是指理论建构的可能,具体的理论建构和创新还很复杂艰难,因为作为一种既有自身特色、又能沟通应用的政党理论,其自身必然内涵某些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根据前面的论述,至少有两个重要的方面需要认真对待,即动员机制的道义性和可持续性、以及政党制度(包括合作制和多党制)与政党消亡的关系。
减少政治浪费是道义为善的做法,所以具有合理性,但它也是一种工具理性,所以其道义为善是不完整的,需要由所达到目的本身的属性来补充。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之一在于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而这样就需要依靠各种动员机制,甚至与此相伴的道义导向和意识形态很容易使动员成为某种政治常态。由此至少带来两个矛盾和问题,一是动员机制和民主形式的矛盾,即动员本身如何证明和保持它的道义为善性质;另一是动员机制与真心认同之间的一致性问题,即如何保证动员的持续和效用的真伪。这些矛盾和问题不解决,运动的常态就难以改变,甚至集权的可能也难以遏制。同样,多党合作制本身具有合法性,在分类意义上也具有普适性,但是,最终达到政党本身的消亡也是多党合作制的合理性所内涵的和特有的道义为善性质。由此至少也带来两个矛盾和问题。其一,如果特定的道义为善具有普适性,与不同政治属性政党的和谐共存就是一个矛盾。其二,不仅政党消亡只是一种逻辑推论,具体方式几乎无从设计,而且即使这个逻辑能够转换为现实,可以想见它也是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因此,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就在于,如何保证宣称具有这种道义属性的政党能够持续具有这种属性而不发生改变、包括将由哪种政党和政党制度来承担这种道义的引领。
从逻辑上讲,所有这些矛盾和问题的解决只能有赖于不断的创制,但这仅仅是理论根据的方向性原则,远不能替代理论体系本身的建构。正因为如此,现在就将这些矛盾和问题作为简括的结论提出来应该是合适的,否则就可能对前述理论根据的讨论分析产生误解,甚至可能陷入盲目性。
注释:
①这方面的研究日渐增多,为了方便了解,可参见比如《参考消息》2011年5月3日、11日、18日各“海外视角”(第12版)栏目中的相关文章。
[1]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政党制度[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7.
[2]G.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3]M.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政治学要素[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
[4]Juan Linz,An Authoritarian Regime:The Case of Spain(一种威权政体:西班牙的实例)[G]//Erik Allard and Stein Rokkan,eds.,Mass Politics:Studies in Political Sociology,New York:Free Press,1970.
[5]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6]Richard H.Solomon,Mao’s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毛的革命和中国的政治文化)[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
[7]Theodore W.Adorno,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权威型人格)[M].New York:Harper& Row,1950.
[8]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9]孙津.打开视域——比较现代化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10]于建嵘.共治威权与法治威权——中国政治发展的问题和出路[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8(4).
[11]林尚立.有序民主化:论政党在中国政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6).
[12]程竹汝,郭燕来.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研究综述[J].学术界,2010(5).
[13]Joseph A.Schumpeter,Capitalism,socialism,and Democracy(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M]//Geo.Allen & Unwin,London,1943.
[14]Juan Linz and Alfred Stepan,eds.,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民主的失灵)[M].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8.
[15]Robert A.Dahl,Polyarchy: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多元政体:参与和对立)[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1.
[16]Anthony Downs,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民主的经济理论)[M].New York:Harper& Row,1957.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Initiation of China’s Political Party System
SUN Jin,ZHANG Li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Haidian,Beijing 100875)
China’s political party system runs effectively and prolifically.However,the support from its basis of specialized theoretical system is relatively insufficient.The contemporary influential(i.e.the so called Western)political science can’t provide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r proper categorization for this type of theoretical basis.Aimed at this situation,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successful initiation of China’s political party system lies in its universality in conceptual communication and application,its legality in particular initiation,and its rationality in justice as virtues.From the view of academic fields,this initiated theory also has discourse corresponding to the prevailing political science for communication and conceptual application.The particularity and universality of China’s political party system provide new contents for political theory.It major implication lies in the political civilization of uniting initiation and development.Based on these understandings,this paper proposes practical ideas on how to change the current problem of theory lagging behind practice,and to construct a theoretical system with bo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ceptual universality on political parties.
China’s political party system;political party initiation;political development;democratic politics
[责任编辑 赵 春]
D05/D621
A
1674—0351(2012)06—0005—09
2012-09-30
孙津(1953— ),男,吉林省吉林市人,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丽(1985— ),女,河南信阳人,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