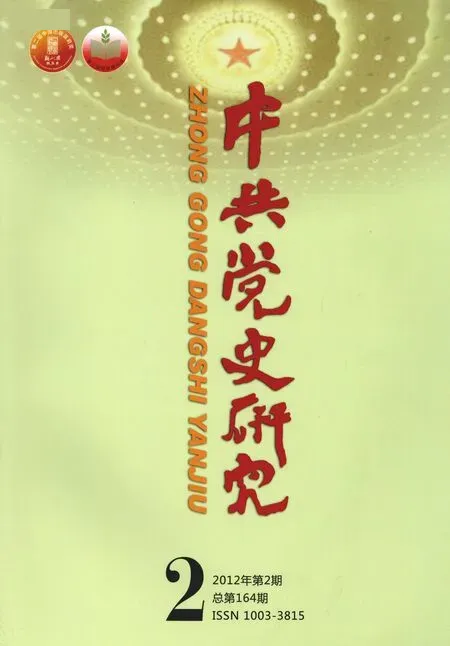从一则史料谈《内部参考》在国史研究中的利用
刘建平
《内部参考》是中共中央为了解社会动态,由新华社参考消息编辑组不定期编印的一本供党内高级干部阅读的内部刊物。如今,它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重要史料。最近笔者偶然读到《内部参考》1952年11月29日的一篇关于农村基层干部与天主教教徒发生冲突的报道,发现其中有失实之处,遂查阅了相关的原始档案资料加以匡正。如果仅就该事件本身而言,这是一个小问题,但倘若从《内部参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的史料运用的角度视之,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一、原始档案中的五帮村天主教徒与干部间的冲突事件
兴平县①经国务院批准,兴平县于1993年6月撤县设市,现已成为陕西省三个县级市之一。鉴于本文所涉及的内容均系新中国成立初期,所以笔者在行文中仍使用兴平县。是陕西省关中平原中部的一个农业大县,天主教传入的时间较晚,是在1756年(清乾隆二十一年)由本省高陵县通远坊传入县城以北的南市坡头村,以后逐渐发展到陈文村、来祁寨、五帮村、南于村,并以五帮村为教会重点继续发展,全县教务统归天主教周至主教区领导。民国时期教会活动比较兴盛。②兴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兴平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26页。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县计有天主教教徒2568人,神甫2人,教堂16处,主要分布于县内的二、四、五、六、七区,其中尤以第六区祝东区为最多。在县内,教会分为上、下两会,其中上会以第四区千丰区的陈文村为中心,下会以第六区第六乡的五帮村为中心。③《兴平县委关于贯彻省委“关于积极推进基督教、天主教运动的指示”的实施计划》 (1951年12月5日),兴平县档案馆藏,档案号2—1—139。教徒“绝大部分是农民”,“少数为教员和医生”;在经济来源上,兴平天主教会“解放前主要靠教会土地租剥削收入和高利贷剥削收入,还没靠外国接济”,解放后则是“由教徒捐助”;日常的宗教活动,每年大聚会有“大瞻礼”、“耶稣复活”、“圣母升天”、“耶稣圣诞”等,“每七天礼拜一次是经常的”,另外,“每天早晚教徒还各自在家念经或到教堂念经”。④《兴平宗教团体材料》(1952年8月22日),兴平县档案馆藏,档案号1—1—97。
作为兴平县天主教的中心地区之一,五帮村在行政规划上隶属于兴平县第六区(祝东区)第六乡(东曲乡)⑤兴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兴平县志》,第67页。。该村教会的历史至1949年前后已超过100年。最初,五帮村信仰天主教者为数不多,但在1929年(民国十八年)情况大变。是年,当地发生历史上罕见的大旱⑥当地老百姓习惯于称这场灾难为“民国十八年年馑”。,导致农民“生活极端贫困”,而天主教会对农民则多有施舍与救济,因此受到教会帮助而皈依天主教者“骤然增加”。至新中国成立时,全村共有村民143户、723人,其中教徒家庭有48户、329人,人数占全村居民的45.5%。⑦《兴平县五帮村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开展情况报告》(1954年),兴平县档案馆藏,档案号1—1—110。
本文涉及的五帮村天主教教徒与政府基层干部的冲突事件发生在1952年10月13日,事件起因于兴平县第六区第六乡召开的乡人民代表会议,其详细经过如下。
1952年10月,兴平县第六区第六乡决定于13日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因会议场地的需要,乡支部书记彭新亮遂于人代会前一天,即10月12日上午前往五帮村与该村教会协商,欲借用五帮村天主教教堂作为乡人民代表会议的会场。彭新亮到五帮村后,先找到该村驻堂神甫吴潜,谈明欲借用教堂开人代会一事,但吴以教堂由会长负责而推托,不愿借出教堂。支书彭新亮便只好去找该村教会的会长进行商议。结果,会长吴振南亦表示不愿借,并说借教堂“群众通不过”。鉴于此,支书彭新亮便只好回到乡政府,将事情经过转告乡长张世玺、民政助理员窦志伟。
眼看着第二天就要召开乡人民代表会议,而会场还没有着落,支书彭新亮、乡长张世玺和民政助理员窦志伟三人只能再次前往五帮村进行交涉。三人向神甫吴潜、会长吴振南以及其他教徒代表说明此行目的后,神甫吴潜仍不同意以教堂作为人代会的会场,称“你们开会不开会,由群众①此句为关中方言,意思是说由群众来决定。呢?”而会长吴振南则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即可以将与教堂一墙之隔的教会学校借给乡政府作为临时会场。这样既可以使教徒没任何意见,也能解乡政府开会的燃眉之急。但这一折中方案遭到乡长张世玺和民政助理员窦志伟的拒绝,他们坚持要在教堂内开会。张世玺态度强硬地说:“不叫开也要开,叫开也要开。”窦志伟表示,如果不在教堂开会的话,“恐怕把教民惯上去②“惯上去”,陕西关中地区的方言,意思是纵容某人,使其愈加嚣张。了”,学校就是条件好,也不去学校那边开会。最后,窦志伟与神甫吴潜议定当晚召开会长和教徒代表会议,对此事进行再次商议。但是,12日晚该区干部并没有赴会。
10月13日晨,窦志伟再次找到了驻该村教堂的神甫吴潜,要求召集教会代表来谈此事。吴说,教会的代表们“都到地里去了,等他们回来了,你去和他们研究开堂门”。此时,窦志伟有些着急,说:“眼看到了早饭时候,会场还没有布置好,代表来了咋办呢?”五帮村教会方面见到这种情况,作出让步。教徒吴国海向窦提出,此次会议可以在教堂里召开,但以后就不要在这里开会了。但窦却称:“这次开了,我们下去再研究。”民政助理员窦志伟的态度,开始引起部分教徒的不满,他们转而坚决反对在教堂里召开乡人民代表会议,说教堂门的钥匙不知道被谁拿着,找不到了。因此,双方形成僵局。之后,双方又有两次交涉,但均未达成共识。
早饭后,参加人代会的会议代表们陆续抵达五帮村,但会场仍然没有下落,更谈不上进行布置了。窦志伟再次向神甫吴潜询问教堂的钥匙,称“谁不给钥匙,会开不成,谁就负责”。教徒吴忍义说:“我负完全责任。”此时的气氛已经紧张起来,形成明显对峙。会议代表吴天申试图去强行打开教堂的锁子,但遭到教徒刘宗泽的阻拦。结果,乡长张世玺下令将刘宗泽叫到乡政府暂时拘留。这时支书彭新亮出来劝和,并叫代表们回教堂院里开会。当会议进行到报告阶段时,被激怒的教徒们闯入会场,并有部分教徒抬着五把铡刀。冲突事件由此发生。在双方的冲突中,支书彭新亮、乡长张世玺、民政助理员窦志伟及七名会议代表受伤,五帮村方面则有神甫吴潜受伤,教徒尹宣宣被代表推倒在地。③《兴平县六区六乡五帮村天主教徒与干部发生冲突事件调查报告》(1952年10月23日),兴平县档案馆藏,档案号1—1—110。
政府基层干部与教徒的冲突事件发生后,中共兴平县委高度重视此事。14日晨,兴平县委即派民政科科长雷明喆和宣传部的汤立前往五帮村进行调查,并于当天下午在县委会议上作了汇报和研究。15日,兴平县委派宣传部吴荣和民政科长雷明喆再次赴五帮村进一步了解情况。另外,兴平县公安局和检察局也各抽一名熟悉当地情况的人从侧面在群众中调查,同时还请兴平县天主教的代表前往五帮村进行安抚教徒的工作。①《报告兴平县六区五帮村天主教教民骚动事件的处理情形》(1952年10月31日),兴平县档案馆藏,档案号1—1—110。
经过政府多方缜密的调查和细致的了解,事情很快就有了结果。兴平县委认为此事的发生,“是由于区、乡干部政策观点薄弱,干部强迫命令所造成的恶果”,并对冲突事件作了妥善处理。兴平县委派民政科科长雷明喆在五帮村主持召开了“一家人”会议,支书彭新亮、乡长张世玺和民政助理员窦志伟均作了检讨,承认错误,并给予窦行政警告处分,教徒中动手打人者亦承认了错误。
对于这次冲突事件,中共咸阳地委也非常重视,多次向兴平县委询问事件发生的原因、经过以及处理情形。咸阳地委认为,此次事件“是由于某些区、乡干部政策观点薄弱以及工作作风上严重恶劣的强迫命令所造成的恶果”;对此次骚动事件,“窦志伟应负主要责任,在行政上应即予撤职处分”,“乡长张世玺借用教堂的态度也很强硬”,以蛮横态度对待教徒,致引起教民极端不满,又无理拘留教民刘宗泽,直接引起厮打等。因此,窦志伟、张世玺、彭新亮等三人应该“公开检讨,承认错误,收回政府的威信”,但同时也“向教民指明骚动行为是不对的,遇有问题应该尽量协商,达到合理解决问题”。②《中共咸阳地委致兴平县委函》(1952年11月10日),兴平县档案馆藏,档案号1—1—97。经过咸阳地委和兴平县委的迅速处理,五帮村天主教教徒与政府基层干部的冲突事件很快便被平息。据兴平县委的报告称,教徒“很满意,都说把官司打赢了”,纷纷反映说“如果不是搬铡子,我们就没有一点错,上边也不会批评我们的。”教徒普遍认为,相比较乡镇干部,“县上来的人总是讲道理”。③《报告兴平县六区五帮村天主教教民骚动事件的处理情形》(1952年10月31日),兴平县档案馆藏,档案号1—1—110。
至此,五帮村天主教教徒与政府基层干部的冲突事件被平息,兴平县委和咸阳地委正确的处理方式使五帮村的教徒们很满意。
二、《内部参考》对该事件的报道
对于陕西省兴平县第六区第六乡五帮村发生的天主教教徒和政府基层干部之间的冲突事件,新华社《内部参考》在1952年11月29日(第264号)以《陕西省兴平县六邦村天主教神甫煽惑教徒捣乱乡代会》为题,作了详细的报道。
报道称,陕西省兴平县六邦村天主教神甫吴潜、地主吴荣等“藉口不准借用教堂大厅(会前该乡干部已征得该堂神甫、会长的同意)于11月13日煽惑该村天主教徒扰乱正在该教堂大厅举行的乡人民代表会议。当时数十个教徒手执铡刀、爷头等武器闯入会场,撕毁毛主席画像和标语,打伤3个区、乡干部和7个乡人民代表”,最后“附近村庄民兵、群众闻讯自动集合准备反击捣乱者,恰逢该区区长赶到,教徒始散,事件始免扩大”。④《陕西省兴平县六邦村天主教神甫煽惑教徒捣乱乡代会》,《内部参考》264号,1952年11月29日,第361—362页。通读《内部参考》中的这篇报道,失实之处甚多,致使整篇报道距离事件的原貌太远。
首先是事件发生的时间不正确。《内部参考》的报道将这次事件发生的时间写为“11月13日”,而事实上,从当时咸阳地委和兴平县委对事件的诸多调查报告和处理意见中可知,冲突事件的时间应为“10月13日”,而非距离事件发生已过了整整一个月的“11月13日”。
其次是事件发生地的地名错误。在《内部参考》这篇报道中,天主教教徒和干部的冲突事件发生于“陕西兴平六邦村”。而笔者在档案资料的查找过程中发现,应为“兴平县六区六乡的五帮村”。五帮村的历史最早可上溯至明朝初年,当时该村有姓王的五百人居住在一起,故得名五百村。到明末时,王家已发展成五个自然村,遂取互相帮助之意,称五帮村。此名一直沿用到新中国成立以后。1958年,该村改名为五丰大队,取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望之意。1984年更名为五丰村,沿用至今。⑤参见兴平县地名办公室于1991年5月为该村所立的村碑的碑文。尽管村名正式更改为五丰村,但到现在为止,大家还是习惯于称其五帮村。
再次是事件发生的原因错误。五帮村的冲突事件发生后,兴平县委和中共咸阳地委都高度重视此事,多方派人调查了解此事发生的起因经过。经调查,兴平县委和中共咸阳地委都认为,此次事件“是由于某些区、乡干部政策观点薄弱以及工作作风上严重恶劣的强迫命令所造成的恶果”。所以,对事件中的几位干部均作了适当的处理。这样的结论显然是客观真实的,是符合冲突事件原貌的。但在《内部参考》的报道中却将事件发生的原因归于五帮村教徒群众的思想落后,认为“兴平全县的天主教徒绝大部分是地主、富农、中农”,“解放以来,这些教徒的思想根本没有得到改造,一贯抗拒各种群众运动和宗教革新运动”,加之“以上情形并未引起该县领导上的注意,以致发生这次捣乱事件。”这样来分析原因,不管是将冲突事件的责任,还是事件的性质,都颠倒过来了。
最后是事件发生经过的描述有误。这篇报道对整个事件发生过程的描述也有多处错误。比如在借用教堂作会场的问题上,乡支部书记彭新亮、乡长张世玺以及民政助理员窦志伟等人在会前并没有征得五帮村的神甫、会长以及教徒代表的同意,但报道却称“会前该乡干部已征得该堂神甫、会长的同意”。冲突事件的发生是因为彭新亮、张世玺以及窦志伟三人在借用教堂时的强硬态度,激起该村教徒的不满所致,完全是教徒们的自发行为,但报道中却写为“天主教神甫吴潜、地主吴荣等藉口不准借用教堂大厅”,“煽惑该村天主教徒扰乱正在该堂大厅举行的乡人民代表会议”,使整个冲突事件的性质明显发生变化。
因而,通过《内部参考》的这篇相关报道,我们已经难以清晰地了解冲突事件的历史原貌。
三、《内部参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的史料价值
匡正了《内部参考》对兴平县五帮村天主教教徒与政府基层干部冲突事件的错误报道以后,我们似有必要讨论一下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的史料价值以及研究者如何利用的问题。当然,笔者并无意因《内部参考》对上述事件的失实报道,而完全否认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的重要价值。与此相反,笔者依然认为《内部参考》是国史研究中极具价值的史料之一。
众所周知,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有着特殊的印行方式,它由遍布全国各地的新华社记者负责采写,“供给中央负责同志参考”。这些遍布全国的新华社记者具体采写的内容非常之庞杂,有“党的政策方针在各地贯彻执行中的情况和问题,特别是那些对领导机关有参考价值的实际工作中的困难、偏向、错误和缺点的情况”,也有“各阶层人民当前的政治思想情况,各阶层人民对国内外重大政治事件的意见,各阶层人民在生活和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难和对于领导机关的意见”,更有“不宜公开发表的重要情况”。①《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27—228页。因而,它往往比一般性的报纸、刊物更为真实,尤其是在反映1949年至1964年间中国社会的基层动态方面,更有着其他资料无法比拟的独特之处。诸如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四清等诸多运动在基层民众中的反映、成效以及遇到的问题,《内部参考》中均有过非常详细的报道。正因为如此,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学者们都非常重视这一史料,他们大都不辞辛劳,多方搜集,并尽可能地加以利用,以期能够窥探真实、客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然而,《内部参考》毕竟是由新华社驻各地记者采写而成的,属于一种报刊性质的资料,也就必然具有报刊资料的一般特点,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像前文所述报道失实的情况。1953年7月,中共中央就明确指出:《内部参考》虽然“曾大量地、及时地反映了各方面、各地区许多重要情况和问题”,但是“也有不少缺点”,例如“有些资料内容不够确实,有些诊断不适当或错误”,甚至“有些记者在采写过程中不尊重当地党委意见”,“干预当地工作”等。正因为新华社记者在编写过程中存有“不少缺点”,中共中央不得不明确要求在他们“写参考资料内容”时,“必须注意确实,力求客观全面,反对粗枝大叶,道听途说,并防止片面夸大”,新华社驻各地的记者们只需要“说明问题是什么时候发生和存在的,现在情况如何”,以及“说明资料的来源及其可靠性,以便领导机关对问题有较全面的正确的了解”,而且记者们在“写参考资料时,只负责客观真实地反映情况,不要对所反映的问题做出结论,也不要向有关方面提出处理的要求”。①《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5册,第227—228页。
尽管新华社的记者们在编写《内部参考》时存有“不少缺点”,“有些资料内容不够确实”,但我们绝不能因噎废食,不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中去利用。那么,这一重要史料又应如何去利用呢?笔者以为,《内部参考》资料和一手的原始档案资料的结合使用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正如本文案例中所采用的。众所周知,原始档案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最为宝贵和重要。所以,我们在国史的研究中应该高度重视原始档案,尽可能地以第一手的档案资料为基础,并以它去匡正其他资料的错讹之处。只有将《内部参考》的相关资料和原始档案资料结合起来使用,才能相得益彰,使共和国史的研究既真实客观,又生动形象。当然,笔者并不盲信、盲从一手的档案资料,而是倡导运用一种正确的思维和研究方法去对一手的档案资料进行鉴别和分析,尤其是对国史研究中的档案资料,更需仔细甄别。
《内部参考》资料在使用过程中,与口述史料的结合亦不应忽视。《内部参考》中的绝大部分内容都可归于当时社会各阶层对党和国家各项政策的反应,而且这些反应一般都应该有较为深刻的历史记忆。而口述史恰恰是重视下层民众历史的产物,它通过调查、采访等直接手段,从特定主题的当事人或相关人那里去了解历史。这种下层民众的历史正好可以去对照《内部参考》中的相关内容,从而既可互相纠谬,也可探究历史当事人或相关人如何进行历史记忆。
由此看来,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中利用《内部参考》这一重要历史资料时,需取一种谨慎的态度,研究者必须要有史识的修养和眼光,同时尽可能地借助多方面的材料,尤其是原始档案资料和口述史料,对所取内容进行小心的鉴别和判断,去伪存真。这样方能扬长避短,发挥《内部参考》这一重要史料在国史研究中的真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