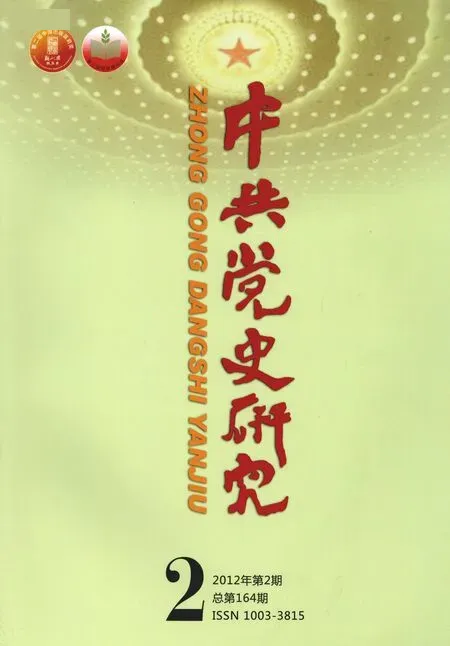南方谈话·历史经验·顶层设计
郑 谦
南方谈话·历史经验·顶层设计
郑 谦
一
细考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背景、内容及巨大的历史作用,联系到20世纪50年代党的八大及其之后发生的重大变化,给人许多深刻的启示。
1956年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全党上下精神振奋,急切地想做出一番新的伟大的事业。1956年间,以毛泽东在 《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一系列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方针为标志,党中央先后正确地判定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提出 “向现代科学进军”和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发展文化、科学的方针,在经济建设方面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等等。在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上,根据对国内外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党中央提出了今后的根本任务。八大指出,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我国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所以,党和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主要矛盾。以此为基础,八大在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方面,作出一系列重要决策。例如: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探索改进经济管理的方针政策;强调扩大人民民主,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加强执政党建设、发展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等等。八大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提出的许多新方针和设想是富于创造精神的。八大之后,以1957年毛泽东发表的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为代表,党又进行了一些重要的、正确的探索。如果中国后来能够沿着八大路线发展,“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及至 “文化大革命”都是可以避免的。
但历史容不得假设。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起,距离八大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八大所郑重确立的许多重要原则、方针相继被否定和改变:阶级斗争重新被认定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建设方针受到严厉指责;农业合作社中一些适合当时农村生产力水平的有益探索受到严厉批判;重新放开一点私营经济的新设想被弃置;知识分子重新被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个人崇拜又受到赞赏,党内民主被家长制、一言堂取代,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成为明日黄花;“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形同虚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变成 “两家争鸣”;民主法制建设成为一纸空文…… “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实际上违背了八大的路线,这一‘左’,直到一九七六年,时间之长,差不多整整二十年。”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3—254页。之所以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发生如此大的转变,一则是从革命到建设转变的深刻性、复杂性;一则是党在巨大的转变时缺乏经验,思想准备不足。此后,党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开始。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在科学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的基础上,开创性地系统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进一步明确了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制定了加快建设和深化改革的蓝图。可以说,在党的历史上,十三大与八大的历史贡献、意义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正如邓小平所高度评价的:十三大报告是一个很好的报告,解答了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能够持久地延续下去②参见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页。。但对十三大路线来说,也还存在一个问题,即能否坚持下去,会不会出现八大后那样的反复。这点邓小平也考虑到了:“也还有风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但我们必须走改革这条道路,有问题要及时妥善解决,不能停滞,停滞是没有出路的。”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0页。
十三大后,中国的改革在进一步深入发展的同时,也遇到了一些难以避免的曲折。1989年,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作用下,我国发生了 “六四风波”。在风波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未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改革趋于停滞,对十三大的质疑之声渐起,市场导向被指责为资本主义,改革被认为是 “和平演变”,中国的经济也因此陷入困境。此时,人民大众忧虑彷徨,改革精英忧心忡忡。中国会不会重演1957年的 “大转弯”?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在屏气敛声地注视着。
所幸,1957年的 “大转弯”及其之后20年的 “左”倾错误没有重演。这是因为中国有了邓小平,因为改革开放是人心所向,因为有了1957年的经验教训,因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不断科学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中走向成熟。
1992年年初,在党和国家发展的重要关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途中,就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发表了极为重要的谈话,明确回答了改革开放以来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他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371页。根据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党中央立即作出一系列部署,中国大地迅速掀起了加快改革和发展的新一轮热潮。
1957年与1992年、八大与十三大的结果如此迥异不是偶然的。除了邓小平个人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权威,除了中国改革大势难以逆转等等因素外,党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中所积累的经验教训的警醒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面对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外的形势和党的任务,邓小平在深广思索中自然而然地想到了1957年及其之后的曲折。他是这一段历史的亲历者,也是这一段历史教训的科学总结者。对他来说,这段历史已不仅仅是一种书本上得来的知识,而是一段刻骨铭心的亲身经历,由此形成的认识是他指导改革的重要思想资源和独特优势。这种经历使他时时高度警惕改革偏离经济建设中心的危险。他反复告诫全党:“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过去二十多年,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太沉痛了。”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0页。他指出:近三十年来,经过几次波折,始终没有把我们的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这方面来。“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9页。当他在南方谈话中斩钉截铁地强调十三大报告 “一个字都不能动”,“十三大制定的路线不能改变,谁改谁垮台”时,几乎可以肯定地是,此时他想到的一定是要避免1957年对八大政治路线的逆转。历史经验就是这样在关键时刻指导着改革,发挥着巨大的现实作用。
什么叫 “通古今之变”?什么叫历史经验、历史智慧?什么叫以史鉴今?什么叫资政育人?重温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及其伟大历史作用,会有一番新的感受。
二
重温南方谈话,至今仍令人心潮难平,除了其中贯穿历史的洞见、尖锐犀利的分析和化繁为简的哲思,还有那种高屋建瓴、一往无前的气势,以及由高度责任感凝积而成的深切忧患意识。这种思想方法和精神状态正是当前中国改革的 “顶层设计”所必须的,是我们今天纪念南方谈话20周年所应大力倡导和弘扬的。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当我们面对诸如 “中国速度”、“中国模式”、“北京共识”、“中国震撼”、“经济奇迹”等美誉时,必须清醒地看到面临着的诸多新问题、新挑战。中国的渐进改革经历了前期的大推进并取得巨大成就后,由于其自身的发展逻辑,目前已进入无法逾越的攻坚阶段。这种先易后难、逐步过渡的改革意味着由于问题的累积,发展中的阻力正不断增加。例如:改革初期一些举措已成为新一轮改革的对象,一些共识又被新的思想解放所突破;改革对象已发生很大的变化,改革动力非往昔可比;改革初期意识形态领域中改革与保守的区分,多半已被不同利益诉求取代;一些在改革中获得最大利益的群体本能地希望改革就此止步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利益分化减少了以往的改革共识,增加了统一思想的难度,等等。改革进程中出现的道德滑坡、诚信缺失、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改革动力弱化、官场腐败、权力崇拜、市场畸形、城乡差别、利益分化、深入社会肌肤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不断发展起来的利益集团对中国发展的影响和牵制,一些不断挑战民众容忍底线的恶性事件及其所激发的种种民粹主义思潮,都严重地威胁着改革的正确方向和持久发展的动力。还有一系列高难度的两难选择需要进一步破解。例如:稳定与发展,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公平与效率,强势政府与民众监督,市场原则与社会原则,一些领域的市场化不足与一些领域的过度市场化、商业化,在保证转型期必要的强势政府的前提下限制公权、遏制腐败,依靠政府,政党一元化的、集中的、强力领导造就一个精神多元、利益多元、决策多元的市场经济,如此等等。
在众多困难中,最为突出的恐怕还是存在于上层建筑领域之中。现在的问题早已不是政治体制方面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而是这种改革能不能与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总量迅速增长同步的问题。或者说,是 “四位一体”能否均衡发展的问题。依赖强势政府权力和权威实现的社会转型在取得巨大绩效的同时,也必然面临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没有强势的、有权威的政府和政党,转型的成本将高得无法承受。而没有对权力的有效限制与监督,这种成本同样高得无法承受,一切有关道德重建、消除腐败、规范市场、公平正义的讨论也都势必不得要领。不少人认为,强势政府与有效监督本身似乎就是一个难以两全的问题。但在整个社会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的背景下,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已成为当今众多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如果进一步的改革不能明晰权力与市场的界限,不能约束权力向市场的扩张,不能阻止没有边界的市场和没有边界的权力的结合,不能消除官本位体制背景下权力的骄横和贪婪,以往改革的成果将难以保持。面对这些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躲不开、绕不过的体制机制障碍,欲使改革不致成为时髦的套话、空话,必须凸显改革所具有的 “新的伟大革命”的意义,必须继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
总之,中国的改革远未 “大功告成”,它还在探索前进的路上。当前,改革又面临新的关口,难度空前增加。改革需要加大力度,加快速度。而此时在一些人群中弥漫的改革冷漠症、改革焦虑症、种种畏难情绪以及改革 “定型论”等,正可怕地吞噬着改革的动力和激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的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 ‘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等话语不能不使人击节赞叹,倍感亲切鼓舞。这种魄力和气势应成为进一步改革的 “顶层设计”中不可或缺的精髓和灵魂,这是细节的完善和精致永远无法替代的。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北京 100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