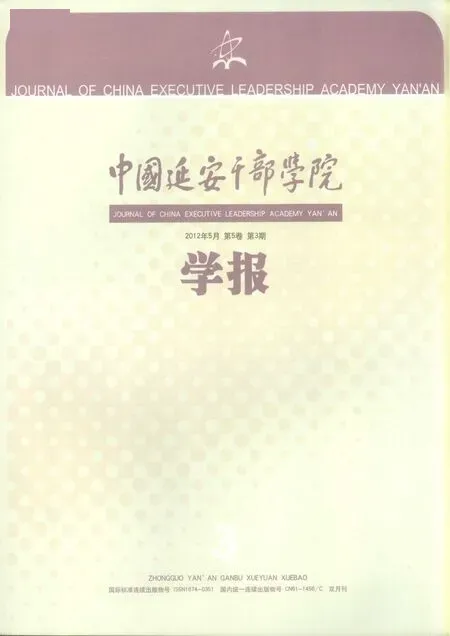如何认识当前的国际经济危机——兼评外国学者的各种见解
陈文通
(中共中央党校 经济学教研部,北京 海淀 100091)
如何认识当前的国际经济危机
——兼评外国学者的各种见解
陈文通
(中共中央党校 经济学教研部,北京 海淀 100091)
当前仍在持续的国际性经济危机,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这次危机不仅使传统资本主义模式难以为继,也宣告了新自由资本主义的破产。但资本主义制度不会就此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将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通过深刻的变革而实现模式转型。中国作为新兴的市场经济大国,已经不可避免地处于国际性的经济危机之中了,其内因是基本的。为此,必须深刻总结30多年来改革发展的经验教训,适当转变改革思路和发展方式,走一条既符合一般规律又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国际经济危机;资本主义模式;改革思路;发展方式;中国道路
如何认识和应对当前国际性的经济危机,是全世界共同而又迫切的任务。国际社会不少学者(理论家,政治家,媒体人)对此发表了见解,这对于我们深刻认识这个问题和走好自己的路子,很有帮助。但我们必须加以分析和鉴别,从中得出更加科学的结论。
一、关于当前危机的性质
(一)外国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危机的性质
自2008年开始的国际性经济危机到底属于什么性质,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不过,对危机性质关注的程度远不如对危机产生的原因、对策和前景那么高。一般的说法是,这是一次“百年一遇(或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问题是:第一,这次危机是否仅仅是“金融危机”而不是经济危机,是否仅仅是经济危机而不是政治危机,是否仅仅是市场经济的危机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第二,这次危机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第三,这次危机是致命性的还是可以解决的?到目前为止,专门谈论危机性质的学者屈指可数。
法国经济学家热拉尔·迪梅尼尔认为,当前的危机是新自由主义社会秩序的危机。他说,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阶段,其特点是,资产阶级通过与精英阶层、特别是与社会高官和金融部门的联盟来巩固权力。但随着新自由主义新社会秩序的建立,资本主义的运转发生了根本改变。当前危机是19世纪末以来资本主义经历的四大结构性危机之一。“当前的危机不是简单的金融危机,而是新自由主义这一不可持续的社会秩序的危机。”在西方国家,下述两种机制融合在了一起:一是,在疯狂追求利润和拒绝监管的思想驱使下,金融化和全球化造成所有新自由主义国家的脆弱性,美国的中央银行失去了对利率的控制和引导宏观经济政策的能力;二是,危机是美国经济失衡的结果。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特性是群众被排除在各政党和团体的游戏之外,他们能做的只剩下街头斗争了。[1]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马丁·雅克认为,这场危机既是深重的经济危机也是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危机。他指出,财富分配的不公和两极分化愈演愈烈,在美国尤为如此。因此,“目前面临的不止是一场深重的经济危机,也是曾经风靡一时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危机。”[2]
日本综合研究所理事长寺岛实郎认为,这场危机是不同于以往的美国式金融资本主义的危机。他指出:“这是一场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资本主义危机”,“是极度膨胀的金融和实体经济背离引发的危机”,即“金融资本主义危机”。在实体经济中,人们通过生产制造、提供服务等经济活动获取报酬;但在金融游戏中,“获利模式就是钱生钱”。由此,产生了所谓“贫富分化的资本主义”。冷战结束20年来,“美国式金融资本主义”风行全球,所谓“全球化”,“其实质是华尔街的‘金钱游戏’全球化”。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式金融资本主义已经病入膏肓”。[3]
概括地说,学者们对当前危机性质的认识,主要有三种观点:(1)美国式金融危机论。认为这是美国式金融资本主义的危机。(2)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双重危机论。认为这既是深重的经济危机,也是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危机。(3)金融危机和社会危机双重危机论。认为这不是单纯的金融危机,而是新自由主义导致的社会危机。其共同点是:一方面,他们都把这场危机和新自由主义联系起来;另一方面,他们都不认为是单纯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二)政治经济学应当对危机的性质作出科学的判断
学者们对这次危机性质的认识不尽一致,而且显然有较大的局限性。尽管如此,总体的认识水平还是有前所未有的提高。
1.把危机和“资本主义”联系起来是理论上的重大进步
上个世纪先后在中南美洲和亚洲爆发的金融危机,并没有引起国际社会应有的重视,更没有被看作是经济危机的表现,好像这两次金融危机和资本主义没有关系。但学者的上述认识表明,自从这一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理论认识有了前所未有的转变。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这次危机和“新自由主义”或“美国式金融资本主义”、“华尔街资本主义”、“贪婪的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这是理论认识上划时代的重大进步。不过,他们的认识仍有明显的局限性(首先是阶级局限性,他们大都是资产阶级的理论家),都没有把这次危机定性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危机。
2.当前的危机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
应当指出,现代社会任何经济危机都必然表现为信用危机或金融危机,并会加剧或引起新的经济危机;任何经济危机都与比例失调和结构失衡有关,因而都可以说成是“结构性危机”;任何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都有可能转化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但是,理论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层次和表现形式上,而必须触及问题的根本和实质。其实,当前的危机就其本质来说,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区别在于,这场危机的确发生在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阶段上。后面的分析将进一步表明,危机从哪里发生,导火线是什么,可以具有偶然性,但这次危机的发生本身具有必然性。危机是否具有致命性,不完全在于这次危机的严重程度,而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否完成了历史使命。对危机性质更深刻的理解,取决于对危机根源的认识。
二、关于当前危机的根源
(一)外国学者对危机根源的认识逐步深化
人们已经清楚地知道,这次危机是怎样爆发和一步步发展的,但它产生的经济社会根源是什么,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认识差距很大。但总体而言,人们的认识在逐步深化。
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本·穆罕默德认为,欧洲的债务危机是经济泡沫破裂和国家破产的结果。在他看来,债务危机之所以会发生在欧洲,其主要原因是:第一,民主和社会主义迫使欧洲国家引进各种福利,减少工作时间和增加报酬。更高的薪酬和福利需求很快蔓延到较高级别的职工,再到高管——即使他们失败也能保证拿到。因此,产品和服务变得非常昂贵,生活成本越来越高。第二,东方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迅速工业化和低成本高品质的产品,几乎将所有的西方制成品挤出百货公司的货架。面临生活水平可能降低的威胁,西方创造出了金融市场。无形产品被发明出来,供其投机和赌博,至少有钱人和精于此道的专家们凭借金融市场大发其财;他们没有将更多的资金投入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实体产业。然后,他们变得更贪婪,通过印制钞票来资助他们的赌博。最终泡沫破裂。第三,希腊靠借来的钱享受高质量的生活。少工作、高收入、更好的社会福利吃光了政府财政收入。于是,政府用借债的办法去填充国家财政预算的窟窿。事实上这个国家已经破产,而最终会导致欧洲银行破产。从根本上说,欧洲国家已经失败了。[4]
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萨默斯认为,危机起因是经济的控制系统出了问题,而根源在于技术进步。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停滞和失业率居高不下,不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缺陷”造成的,而是凯恩斯所说的“磁电机”出了问题。“问题的根源在于技术进步”。与此同时,与工业化时代的早期一样,社会结构的大错位以及规模生产能力的提高使得少数的幸运儿获得了巨大财富。问题在于工资相对于住房、医疗、食品、能源和教育等价格显得停滞不前,甚至下降。[5]
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亚洲项目的负责人凯利·布朗博士认为,美欧的危机是债务水平急剧上升和过度消费所致。他说,在美国和欧洲爆发的危机,和个人与公共债务以及消费过度有关。从核心上说,目前的危机是因为过去10年中债务水平的急剧上升导致的。[2]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马丁·雅克认为,这次危机是自由市场主义和私有化政策造成的系统性危机。他说,从上世纪30年代以来,“所有主要的经济危机都是人为造成的”,这和经济的周期和结构有关,但“首先是一种系统性危机”。危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末的撒切尔-里根时代,当时的自由市场主义和私有化政策为现在的危机埋下了祸根。尤其是在金融领域,这些政策导致违规操作成为一种常态。现在“银行家们成为新的上帝。政治家和媒体都成了金融利益的俘虏,这是一种堕落的表现。”[2]
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汉斯-乌尔里希·韦勒认为,没有治理的金融业是真正的根本问题。他说:“没有治理的金融业是当前资本主义危机中存在的真正的根本问题。”“金融行业完全摆脱了法律法规框架的束缚,解放,自由,没有法规”。[6]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国际经济危机是欧美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主义成分的产物。他说,2008年开始的国际经济危机的根源主要是发达国家,即欧洲和美国。其中,“欧洲国家主要是社会福利制度的危机,社会福利推动着政府债务危机。”而在美国,“金融危机也是美国政府一再提高社会主义成分的产物。”美国政府想利用市场机制解决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结果由于放松了对金融体系的管制而出了问题。他进一步认为,“西方今天正面临着两大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即金融资本主义和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以及民主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两大矛盾既是危机的根源,也使得西方难以挣脱危机,更使得新危机不断发生。一方面,西方国家已经从工业资本主义过渡到“金融资本主义”。但金融不再是为实体经济融资,而是“用钱来套取更多的钱”。当今的金融资本主义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也已经有了质的变化。实体经济仍然依赖于金融经济,但后者不必依赖前者。在金融成为当今资本主义的绝对核心之后,当代金融资本主义明显出现三大趋势:第一,金融资本挟持了政府,甚至整个经济。金融资本已经“大到不能倒”。第二,当代金融业不产生就业。当代金融业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而是用货币炒作货币。第三,当代金融业迫使世界上所有一切都货币化或者商品化。另一方面,在西方民主从精英民主转型成为大众民主之后,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并且是质的变化。西方经济从赤裸裸的原始资本主义转型为“福利资本主义”。政府必须以比较中立的立场,调节资本和劳动者之间的利益。而且,既然政权的基础不再局限于财富,而是选民的选票,那么,政治人物必须把选票作为优先的考量。于是,民主往往成为福利政策的拍卖会。在经济体不能创造庞大的财富来支撑福利和公共开支,而国家又无法增加税收的时候,西方政府就走上了借债度日的赤字财政,向人民借钱、向国外借钱、向未来借钱。这就是欧美等国家债务危机的根源。[7]
日本综合研究所理事长寺岛实郎认为,金融危机的根源是金融产业的急速变异。他说,以往金融产业的主要功能是以银行为代表的借贷活动,为实业提供资金,从实业成果中获得利息等回报。但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金融产业出现急速变异,不是从投资实业中获利,而是试图通过管理风险获利,典型模式就是对冲基金,后来还涌现出风险更高的金融工具。一旦出现破绽,就波及各个领域。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导致的危机,宣告这种“华尔街模式的美国金融资本主义已经进入死胡同。”他同时认为,美国陷入危机的基础性原因是军事和消费开支超出实体经济的实力。之所以能做到这点,就是因为利用了“金融”活动,华尔街“赌场”效应吸引的资金支撑了美国的财政开支和消费。这也是如今美国陷入迷失的本质原因。[3]
埃及前外长助理、阿拉伯投资者联盟主席贾迈勒·卜尤米认为,危机的原因是自由资本主义无法控制自由资本产生的黑洞。他说,2009年以来,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继而引发欧债危机和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和市场崩溃,美国这一自由资本主义的最大实体恰恰印证了自由资本主义的失败。现在资本已经转移到寡头和垄断者的手里,而大多数民众却获利甚少,这就是最根本的问题。[8]
墨西哥前驻华大使塞尔希奥·雷·洛佩斯认为,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缺乏约束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他说,目前的经济危机是政治危机的必然产物,从根本上说是缺乏约束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所造成的。资本主义的盲目自信也导致了经济危机的出现。事实证明,完全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是错误的理论。这场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过去几十年美国对市场疏于监管以及银行家贪得无厌的结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表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无限发展的趋势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这一矛盾的表现形式。资本主义制度在一段时间内可以带来经济繁荣和利润扩大,但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终将导致经济危机爆发。缺乏约束的资本主义制度必将走向衰落。[9]
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胡安·索马维亚认为,危机的原因很复杂,而结果则是极为严重并不断加剧的不平等现象。他说:“资本主义曾经经历过多次存在危机,而现在这次却是前所未有的。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但结果却很简单:不平等现象极为严重并不断加剧。目前全球有6100万人掌握着相当于35亿人所拥有的财富。”解决的办法是推行一种更有效的惠及多数人的发展模式。[10]
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认为,消费者和投资者每个人都是资本主义危机的共犯。他说,将资本主义危机归咎于全球金融和高得离谱的高管薪酬实在太简单了。既然我们大部分人都兼属消费者和投资者、劳动者和公民这四种角色,那么真正的危机集中在: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时,我们越来越容易达成划算的买卖,而作为劳动者和公民时,我们让自己的声音获得重视的能力则越来越弱。然而,这些划算买卖的代价是我们的就业和薪酬,以及日益扩大的社会不平等,还有对环境的破坏性影响和违背社会风化等。但迄今仍没有任何人找到让资本主义回归平衡的方式。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指责全球金融和全世界的企业,但应当把一些指责留给那些贪得无厌的消费者和投资者,这些人“每个人都是共犯”。[11]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认为,危机根源于西方资本主义犯下的三个错误。他说,资本主义本身并没有陷入危机,陷入危机的是西方资本主义。西方犯下的三个错误是:一是把资本主义视为一种意识形态,而不是一种用来改善人类福祉的实用工具。正因为如此,格林斯潘认为没有必要对市场严加监管。更为糟糕的是,西方还产生了一个庞大的金融服务业,这个行业根本不创造任何实际价值。二是忘记了欧洲资本家从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威胁中学到的教训——要使资本主义制度存续下去,各个阶级都必须从中受益。这就造成,不平等现象大大加剧,失业率不断上升。三是在向第三世界宣扬资本主义优点的同时,没有让其本国人民清楚“创造性毁灭”,并必须学习新的技能。由于存在种种缺陷,资本主义是一种不完美的制度。它要求政府认真监管。而亚洲则与此不同,它们处处都有宝贵的经验值得西方学习。[12]
概括地说,学者们对危机根源的认识,主要有下述几种观点:(1)基本矛盾论。认为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无限发展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的基本矛盾。(2)民主和社会主义压力论。认为危机根源于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压力导致内部关系和政策的变化。(3)经济和社会双重矛盾论。认为危机根源于金融资本和实体经济、民主与资本主义的双重矛盾。(4)失控自由资本主义论。认为危机根源于失去控制的自由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主义)、私有化政策和脱离法规约束的金融业。(5)西方资本主义犯错论。认为危机根源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三大错误,而这些错误在亚洲国家并没有发生。(6)债务消费超经济能力论。认为危机根源于公共债务、军事开支和消费支出超出实体经济的实力。(7)技术进步论。认为危机根源于技术进步导致社会结构的错位和财富分配不合理。(8)人们的贪得无厌论。认为危机根源于消费者和投资者的贪得无厌。从这些观点可以看到,学者们找出的根源属于不同的层次,都有助于说明危机的产生。其中有三点值得重视和肯定:一是多数学者从自由资本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寻找根源,这个方向是正确的;二是有些学者从分析经济社会矛盾出发,这个分析方法同样是正确的;三是个别学者已经把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但是,同样有三点是不能成立的。第一,公共支出和消费支出过多显然不是危机的根源;甚至相反,会弱化或者减缓危机。它们只是导致赤字财政的直接原因。有待于证明的是,是什么原因导致支出过多。第二,技术进步肯定不属于危机的经济根源,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演变的物质技术基础。危机不能归咎于技术进步;实际上,是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和局限。第三,消费者和投资者的贪得无厌,不会成为当前经济危机的根源。贪得无厌用在投资者(即资本所有者,他们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身上是恰当的,但不能用在消费者身上。危机当然和资本的贪得无厌有关,但问题不在贪得无厌本身。如果不去考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本身,不去考察资本扭曲和变异的原因,就什么问题都说明不了。
(二)危机的根源只能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的本性中去寻找
虽然大多数学者对于危机的根源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但总体而言,他们大都局限在西方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视野和框架内。他们没有从“新自由资本主义”、“美国式资本主义”中抽象出“资本主义”,也没有从“资本主义”中进一步上升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因为如此,他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关系,没有搞清楚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关系,没有搞清楚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的关系。正因为如此,在他们看来,在亚洲或者东方国家,似乎本身不存在危机。根据马克思科学的经济理论,特别是他的危机理论,危机的根源以及这次危机的特殊性,只能到现实的经济关系中去寻找,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和资本的本性中去寻找。
1.必须充分认识这次危机形成和发生的特殊性
这次危机的形成和发生,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规律,危机仍然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特别是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积累规律的作用。但是,和早期的危机(包括30年代的大危机)相比,有很大的特殊性。第一,国际经济关系的特殊性——经济和金融的全球化。经济(生产和流通)全球化的趋势早就开始了,但只是在上个世纪后期,经济全球化才真正建立在金融全球化的基础上。这时候,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一开始就具有世界性质。而且,危机一旦发生,几乎所有国家都不能置之度外。第二,货币体系的特殊性——取消黄金的货币地位。从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开始,美元取得了等同于黄金的特殊地位,为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奠定了基础。后来,在美元危机(由于美元的国际信用不断下降,各国纷纷抛售美元储备和抢购黄金)的频繁冲击下,197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接受了美国提出的“黄金非货币化”的建议。从此,纸币完全代替了真正的货币,为滥发纸币(特别是作为储备货币的美元)大开方便之门,为持续实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提供了条件。黄金货币的取消,不仅掩盖了当前的危机,也孕育了未来更大的危机。第三,资本本身的特殊性——资本本身的扭曲和变异。借贷资本的出现和信用制度的形成,出现了作为资本所有权证书的虚拟资本。但是,自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美欧国家为了保持虚假的繁荣和满足资本贪婪的欲望,放纵虚拟资本脱离实体经济而泛滥,资本本身发生了相当程度的扭曲和变异,为直接“以钱生钱”创造了条件。不仅如此,政府还用保护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的方式防止金融危机的扩大和蔓延,从而更加深化了金融危机。第四,政府干预的特殊性——政府以经济政策应对经济危机。早期的危机都是自然地发生和缓解的,从而形成有规律的经济周期,危机也为资本主义经济提供了起死回生的机会。但是,自“凯恩斯革命”以来,西方国家持续地用扩大货币供给和政府投资的方式“创造”需求,以应对生产过剩的危机。在资本主义内在基本矛盾照样存在的情况下,单纯着眼于缓解当前危机的做法不过是饮鸩止渴,所有“创造”需求的方式,都必然地带来通货膨胀、保护落后、产能过剩的负面后果,因此,危机本身反而更加深化了,资本主义经济愈益病入膏肓了。第五,应对社会矛盾方式的特殊性——以政府负债的方式解决资本主义本身带来的问题。政府不仅承担了干预经济的职能,而且承担了救世主的职能。贫困、两极分化、不公平和失业等问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在外部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内选民的双重压力下,西欧国家率先走上了“福利国家”的道路。但是,在社会基本分配关系不能改变的情况下,政府力图以负债的方式缓解这些矛盾,最终到了不堪重负和国家破产的地步。把上述种种特殊性集中起来主要是,资本扭曲变异和政府超能力执行职能。
2.经济危机的一般和基础性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经济危机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造成的生产相对过剩、从而经济停滞的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在商品生产普遍化的前提下,劳动采取了雇佣劳动的形式,生产资料采取了资本的形式,生产的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的关系发生了颠倒——物支配人,而不是人支配物,整个社会生产由盲目的自然规律——价值规律——调节;二是生产的直接目的是剩余价值。[13]995-998资本总有一定的物质载体,而且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但资本本质上是一种特定的经济关系,其本性就是无止境地追求剩余价值,使自身不断增殖。资本运动的基本规律是剩余价值规律。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包含着资本和雇佣劳动、资本家阶级和雇佣劳动者阶级(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工人的消费和资本积累的对立。由于这种对立,一方面,必然产生雇佣劳动者阶级的失业、贫困(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和两极分化;另一方面,必然造成生产能力的相对过剩。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始终包含着这样一个基本矛盾:以剩余价值为目的和以提高劳动生产力为手段的矛盾,工人阶级缺乏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和生产能力过剩的矛盾。这个基本矛盾必然使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地陷入危机之中。生产过剩导致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指出,经济危机是资本和劳动两种对抗因素发生冲突的周期性表现。[13]277经济危机基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和手段的矛盾,即资本增殖和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生产力的矛盾。[13]278或者说,根源于生产力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的矛盾。[13]272-273“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13]548在马克思那个时代,经济危机的主要表现和特点是:“交易停顿,市场盈溢,产品大量滞销积压,银根奇紧,信用停止,工厂停工,工人群众因为他们生产的生活资料过多而缺乏生活资料,破产相继发生,拍卖纷至沓来。”[14]626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同样决定了,经济危机是周期性的。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总是要经过一定的周期性循环。它要经过消沉、逐渐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和停滞等阶段。”[15]91“在周期性的危机中,营业要依次通过松弛、中等活跃、急剧上升和危机这几个时期。……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16]207一百多年来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具体形态的变化,并没有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经济危机在生产领域的基本表现依然如故。无论是金融危机还是政府(主权)债务危机,都是经济危机进一步传导的表现。如果说金融危机是经济危机在金融领域的表现,那么,政府债务危机不过是经济危机在政府财政上的表现。因此,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没有过时。由于受到扩张性经济政策的干扰,在比较短的时期内,经济危机的周期性没有充分地表现出来,但周期性循环的规律本身是不可能人为地取消的。
3.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是获得剩余价值的方式发展演变的结果
直接地说,这次金融危机是金融资本的质变和政府监管缺失造成的,是新自由主义的恶果,是诸多人为因素(华尔街的金融大鳄,政府机构的当事人,新自由主义的倡导者等等)造成的。但是,所有的人为因素都是在更基础得多的经济原因的基础上产生的。金融资本的质变和政府监管的缺失并不是根本原因,而这里涉及到的人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和资本的代表者和保护者。从唯物主义历史观出发,更加根本的原因来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经济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发展演变、从而取得剩余价值的方式发展演变的必然产物。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的发展演变,又是生产力、交换方式不断发展的结果。整个发展变化经历了一系列过程。
首先发生的变化是,越来越多的资本涌向不创造价值的非生产领域直接捞取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始终是商品价值的一部分,新获得的剩余价值始终是新创造的交换价值的一部分。剩余价值的源泉只有一个,就是生产商品的雇佣劳动者的活劳动(在存在职能分工的生产体系(企业)中必然是“总体结合劳动”)。但是,剩余价值的获得和创造是不能等同的。个别资本获得剩余价值的方式和途径是多种多样的,资本所有者获得剩余价值,完全不必成为产业资本家(实业家)。剩余价值最初由执行职能的产业资本家占有,但是,随着再生产过程各种职能的分离,资本所有权和再生产过程的分离,在资本运动的各个环节(购买,生产,出售)和资本的各种形式(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银行资本)上,都可以按照平均利润率规律获得和资本份额相当的剩余价值。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极大提高和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产业结构一步一步发生重大变化,资本和劳动越来越多地从工业和农业转移到所谓“服务业”中来,相应地,个别资本取得剩余价值的领域和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服务业包含完全不同性质的“产业”。有些服务业照样提供具有一定使用价值的商品,只不过商品只是一种服务活动,服务的生产过程同时就是买卖过程和消费过程;有些服务实际上是生产过程在流通过程中的继续(如运输业、仓储业以及分装等等),这种服务虽然不增加新的使用价值,但可以在这一过程中保存现有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从而起到增加价值的作用。然而,有些服务既不提供任何使用价值和商品,也不参与价值的创造,是根本不属于产业的“产业”。这些服务中涉及到的工资(劳动报酬)和利润(剩余价值),只是对已经创造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扣除。其中,有的服务执行的是纯粹流通过程的职能(买卖活动),这种职能虽然不创造价值,但却是商品社会再生产过程不可或缺的,因此,这个过程的劳动同样是必要劳动;有些服务则是纯消极的、不利于文明进步的。例如,为挥霍浪费的消费行为和腐朽堕落的生活方式提供帮助,政府(官僚机构或与劳动人民相对立的政府)强加于人的“服务”,等等。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通过雇佣工人的劳动,从已经创造的剩余价值中,为自己(资本家和工人)创造出一定的份额。总之,不管服务的性质如何,都可以成为一个特殊的投资领域。即使在既不创造使用价值和价值也不创造剩余价值的服务领域,甚至在不利于文明进步的服务领域,资本所有者和经营者同样可以借助雇佣劳动者之手,从社会已经创造的总剩余价值中为自己“创造”出一定的份额。这是资本开始出现腐朽的征兆和表现。
接下来发生的变化是,越来越多的资本通过制造价值泡沫和投机诈骗以钱生钱。价值泡沫是不包含真实价值的虚假价值表现。本来,价值不过是抽象一般劳动的特殊社会形式,价格不过是价值的货币表现。超出这个范围的价值表现,都是虚假的。因此,一旦价值表现脱离和超过了价值(劳动量)本身,就必然大打折扣。至于投机诈骗,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贱买贵卖,不是通过商品流通取得“让度利润”了,而是利用商品流通、货币流通和虚拟资本运动的形式骗取金钱。本性贪婪的资本的监护人(人格化的资本),不仅不满足于经营实业,也不满足于经营一般“服务业”(例如纯粹的商业服务),从而从已经创造的剩余价值中分得一杯羹,而是通过制造价值泡沫和投机诈骗,从中牟取暴利,直接以钱生钱。
价值泡沫的形成主要有两个要素:一是货币的超量供给;二是大规模炒买炒卖。价值泡沫是政府、金融机构、资本所有者制造出来的,主要的形式有:(1)滥发纸币,导致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2)以虚拟资本(所有权证书,现实资本的纸制复本)做抵押取代贷款,制造新的虚拟资本,导致信用膨胀和流动性过剩;(3)炒买炒卖,通过囤积和垄断商品制造供不应求的假象,达到哄抬商品(包括住房,股票等等)价格的目的;(4)在“金融创新”的名义下制造金融衍生产品,掩盖和转嫁金融风险,制造虚假的所有权证书。如果说制造价值泡沫为以钱生钱提供了基础条件,那么,投机诈骗就是以钱生钱的主要手段了。再生产过程以外以钱生钱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一是在商品流通领域投机。资本所有者不是从事商品流通,而是借助商品流通投机钻营。房地产和大宗可储存商品等等都可以成为囤积居奇、炒买炒卖的对象。其二是利用社会资本放高利贷。在生产过剩、银根吃紧的时期,货币资本成为最紧缺的资源,于是,高利贷生意就乘机大发横财了。但贷款大量的不是来自自由资本,而是吸收聚集社会居民的资金。其三是在特殊的商品市场——证券市场、期货市场、贵金属市场等等——呼风唤雨、兴风作浪,反复地拉高价格和抛售。其四是以提供金融服务的方式制造虚拟资本和发售各种金融衍生产品。如此等等。在这些不同形式的以钱生钱的投机活动中,都少不了两个主要当事者:资本所有者和金融机构。这里所说的资本所有者,是那些集中了大量财富和资本、而并不进入再生产过程的纯粹投机者。现在,越来越多的资本所有者既不投资于工农业生产,也不投资于广义的实业,而是以金融机构为核心,在各种形式的流通领域(商品流通,货币流通,资本流通,虚拟资本流通)做投机生意,直接以钱生钱。金融机构要么是整个投机活动的主角(策划者和主宰者),要么是主要的合伙者或同谋者。现在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重点不是充当金融的中介人,为企业融资提供服务,而是在流通领域做投机生意。如果说资本的总公式是G-W-Gˊ的话,那么,在借贷资本的场合,已经简化成G-Gˊ的关系了。现在,在金融机构和资本所有者那里,G-Gˊ关系已经变得更加赤裸裸的了,就像变戏法一样了。但是,价值泡沫毕竟是虚假的价值,虚拟资本毕竟不是现实资本,一旦价值泡沫破裂,所有权证书不能兑现,金融危机就要发生了。
资本的上述变化,并不纯粹是人为的,归根到底是一定生产力和经济关系的产物。第一,随着商品生产的普遍化和价值形式的发展,一切使用价值趋向商品化、价值化,人与人之间的一切交往关系都变成交易关系或买卖关系。既然货币(金钱)是财富的最一般、最抽象的形式,那么,对交换价值的追求也就自然变成对货币的追求,货币便被社会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第二,随着生产的进一步社会化和全球化,资本的货币形式(货币资本)成为最重要的资本形式,货币资本的运动成为社会经济体的神经系统和血液循环系统,信用制度和金融业不仅空前发展,而且越来越独立于实业和凌驾于实业之上,金融资本越来越成为社会再生产的支配者、主宰者。第三,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作为资本所有权证书的虚拟资本的运动和交易也随之发展起来。这时候,虚拟资本不再是由现实资本决定并服务于现实资本,而是人为创造虚拟资本和价值泡沫。作为融资场所的证券市场,越来越成为资本所有者赌博和直接捞钱的场所。第四,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以及为了应对经济危机而持续实施的扩张性经济政策,进一步确立了金融资本的统治地位和救世主地位。第五,信用的进一步扩张,要求突破和改变传统的货币和资本形态。首先是以作为单纯价值符号的纸币取代了商品的一般等价物的金属货币,从而取消了真正的货币,这就为银行创造货币(购买力)提供了可能,也为政府滥发纸币大开方便之门;其次是虚拟资本不仅和现实资本完全分离,而且获得了空前的独立发展,这就使资本发生进一步的变异,从而为资本直接“以钱生钱”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由上可见,金融资本的变异是必然要发生的。变异的物质技术基础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业结构的变化、生产的社会化和全球化,而变异的驱动力完全来自资本的本性。人们有足够的理由追究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责任人,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金融危机的直接责任人(首先是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大亨们)不过是变异了的资本的人格化,而政府的不合理行为不过是满足了资本的这种贪婪的欲望和要求。
4.欧盟债务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深化的必然结果
直接地说,以希腊为典型的欧盟主权债务危机主要与如下三个因素有关:政府财政赤字过大,债务负担过重;政府债务和金融机构相关联;欧盟国家采取统一的货币形式。但债务危机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如前所说,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一方面导致雇佣劳动阶级的贫困(发达国家主要表现为相对贫困)和两极分化;另一方面导致商品市场的盈溢和生产能力的全面过剩。这二者都会导致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对民选政府产生了极大的压力。欧盟国家的政府自然不会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而是力图通过政府的职能和政策缓解、推迟和掩盖经济危机。一方面,以宏观经济调控者的身份,通过实施凯恩斯的扩张性经济政策创造虚假的社会需求(如果有可能,还会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通过发动战争扩大需求),甚至还要出资挽救一部分陷入困境的企业,或者国有化。另一方面,以“社会正式代表”的身份,通过扩大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政策,安抚工人阶级和弱势群体,以缓解阶级矛盾。其典型形式是所谓“福利国家”。“福利国家”的实质是政府力图利用再分配手段(转移支付)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造成的问题,这是注定要失败的。上述这两个方面,都会大幅度增加政府的财政支出,而财源却不能相应扩大(赋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限制),就只有靠举债维持财政收支的平衡了,并且必然是不断地以新债还旧债,这在有些国家已经成为一种常态。结果必然是政府债台高筑直至不堪重负。如果政府不能偿还到期的债务,从而政府已经失去信用,债务危机就首先在有关国家发生了。如果这些国家通过金融机构发行了大量国债,债务危机就会殃及相关的金融机构乃至有关国家。目前,由于欧盟采用同一的货币,各国的金融机构已经形成一个具有紧密联系的体系,个别国家的债务危机就会成为整个欧盟的危机。在经济层面上,必然加剧已经存在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由此可见,尽管欧债危机有一些具体的原因和发展过程,但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欧债危机不过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延伸和深化。
5.危机的根源不应当仅仅从美欧国家并孤立地去寻找
自这次危机发生以来,人们大都分别地谈论源自美国的金融危机和源自希腊等欧盟国家的债务危机,好像这二者都不是经济危机的表现,好像这二者之间没有关系,好像危机的形成和其他国家(首先是新兴工业化国家)也没有关系,好像其他国家只是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这两个危机的“影响和冲击”。这种认识是不符合实际的。第一,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和欧盟的债务危机不是孤立的两件事,而是同一件事的两种不同表现。事实上,它们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造成的结果,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资本自身和政府为了摆脱困境和应对危机,而采取的各种措施必然导致的结果。资本力图以金融资本扩张的形式创造需求、掩盖危机和投机取利;政府则力图以增加财政支出的形式创造需求和弱化危机造成的后果。其实,没有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为基础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就不会发生。第二,在直接的形式上,欧美以外其他国家似乎和两个危机的形成没有关系,但它们只要同样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都参与到“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之中来,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形成就都与它们有关。在所有这些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是同样的,但在发展程度、资本化程度、经济制度、经济政策不同的国家,有不尽相同的表现。
在老牌的欧美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发展到了高峰,到了转折点,开始走下坡路。它们在技术和管理方面仍然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它们的高科技产品不仅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而且表现为更大的国际价值。但是,一般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由于劳动力成本大大提高而失去竞争力,并逐步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这样一来,一方面,经济增长率显著下降;另一方面,失业率不断攀升。美国把希望寄托于一箭双雕的房地产业——既可以解决中低收入居民的住房问题,又可以拉动经济增长(增加经济总量)和降低失业率。但它依靠的是扩张性的经济政策,是消费信贷制造的无力偿还的虚假购买力。结果,内在的经济危机必然地转化为外部的次贷危机。现在,欧美国家一方面不能不继续维持已经大大提高了的(包含泡沫的)工资水平和社会福利;另一方面又在高失业率面前无计可施。于是,就只好靠借债过日子了,内在的经济危机必然以债务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可见,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和欧盟的债务危机,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框架内,资本和政府应对经济危机必然带来的结果。
在新兴工业化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处在青壮年时代,而且,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存在一定的差异——或者更多地采取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或者国家是社会经济的主导者,有的则是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例如中国)。它们的平均工资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而剩余价值率却显著地高于发达国家,资本积累的速度更快。它们通过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首先在一般制造业领域取得了不可比拟的竞争优势。但是,除了个别经济以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成为它们的基本形式,这就必然造成这样的结果:第一,它们经过或长或短的时间,贫富差距往往比发达国家还要大;第二,它们有很高的资本积累率和投资率,而消费率显著偏低;第三,在国内消费需求受到压抑的情况下,它们更多地依赖于国外市场,首先是欧美国家的市场。因此,即使在不发生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也会经常存在产能过剩和产品过剩的问题。但是,一方面,这些国家的经济体制不同于西方国家,资本化和市场化程度低;另一方面,政府往往会通过实施更大力度的扩张性的经济政策为过剩的产能和产品开辟道路和创造市场。因此,在一般情况下,潜在的危机(经济危机以及金融危机和财政危机)不会显著地表现出来。但是,一旦出现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单靠这种扩张性政策就无能为力了,更何况,反复使用这种政策不仅得不偿失,而且会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因此,新兴工业化国家不能把这次危机看成是欧美国家的事情,而是应当看成全球化体系中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的事情。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就警告过当时洋洋得意的德国人:《资本论》中的经济事实虽然主要来自英国,但德国绝不应当“伪善地耸耸肩膀”,相反,“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这是因为,“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7]8马克思的警告同样适用于今天表面上“处于危机之外”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所有发展中国家。必须明确地认识到,在所有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国家,都会发生经济危机,它们是危机的共同制造者,而又互相影响,只是表现形式和严重程度不同。
三、关于应对当前危机的思路和对策
(一)外国学者从不同方面和不同层次提出了应对危机的思路和对策
此次危机已经持续3年多,受影响最大的首先是西方国家。美国经济的复苏仍然困难重重,西欧在债务危机中依然难以自拔。人们希望的所谓“后危机时代”迟迟没有到来。如何应对和克服危机,人们有不同的认识和思路。
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本·穆罕默德认为,欧洲必须承认像发展中国家一样穷。他指出,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失败了,许多欧洲国家包括美国在内也失败了。欧洲必须承认自己已经失败了。他们的一切努力都将失败。穷人必须活得像穷人样。他们必须放弃奖金、股权、福利、高收入和少工作之类的待遇。金融市场上的投机赌博也必须停止。他们必须回去工作,拿更低的工资去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他们必须卖掉自己的大部分资产。印钞票和填写支票毫无帮助。[4]马哈蒂尔还认为,西方有必要重归资本主义根本,欧洲必须向东方寻求危机的解决办法。他说,几个世纪的霸权让他们相信,他们的价值观要被接受为普世价值观;亚洲的价值观却被视为无关紧要。因此他建议,应该召开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会议,贫穷国家应该得到充分代表。新的货币体系应该考虑设立一种以黄金为基础的交易货币,而其他货币应根据这一货币确定汇率。银行应该受到更严格的监管。世界不可能恢复原状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时代实际上一去不复返了,欧洲必须向东方寻求危机的解决办法。[18]
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萨默斯认为,走出目前的困境只需要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他说,对市场资本主义的幻灭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取决于如何对下述两个关键问题作出回答:今天的问题,到底是目前这种形式的市场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呢,还是有更加直接的方法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经济停滞和失业率居高不下,不是资本主义本身存在问题,而是凯恩斯所说的“磁电机”出现了问题。因此,解决的办法是采取适当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而不是对资本主义本身进行大规模结构性调整。他断言,如果适当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当前的许多担忧就将烟消云散。萨默斯还认为,一个越来越富有的社会需要减少一些社会保障。这种见解和韦勒的见解(见后文)几乎相反。他说,资本主义是非常成功的,历史上,只要是采取了市场资本主义的就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资本主义的成功不能被当做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最需要改革的并非当代经济中资本主义特色最强的部分,而是资本主义特色最弱的部分,即那些与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相关的领域。[5]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马丁·雅克认为,克服危机需要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进行重大转变。他说,欧洲在危机面前软弱无力和束手无策,几乎没有任何新的思路。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原有的方式早就被证明无效。西方市场不大可能在短期内复苏。要克服这次危机需要很长时间,需要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进行重大转变。[2]
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汉斯-乌尔里希·韦勒认为,危机唯一的解决方法是银行信贷和投资银行分离。他赞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意见,唯一的解决方法是将银行信贷业务与投行的投机行为分离。如果某个投行破产了,就让它破产,国家不需要因担心发生连锁反应而不得不拿出上千亿美元的资金援助。但他注意到,这种做法在美国遇到很大阻力。韦勒还认为,应当寻找务实的资本主义道路。他说,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模式,在确保相对自由的资本主义同时,国家承担社会责任,为每个人提供社会保障;但在美国,4200万人没有保险。在实行社会国家政策的欧洲国家中,没有工资保障、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这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他认为,更聪明的方式是,寻找务实的道路,即相对的自由资本主义与社会国家、社会保障相结合。他相信,资本主义制度是弹性灵活、具有存活能力的,能够从危机中走出来。[6]韦勒和萨默斯观点的不同,明显体现了美国自由市场经济和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区别。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资本的错误只有依靠社会力量来解决。他说,“资本自己不会纠正自己的错误,政府无能或者无力纠正错误,那么社会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了。”最近发生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具有指标性意义。他认为,从历史上看,不管是社会危机还是经济危机,最终必然转化成政治危机。同时,也可能出现强人政治来应对危机和解决问题。无论什么制度,经过一定时间发展必然要出现转型。西方的资本主义体制现在面临着双重转型,一个是民主的转型,一个是经济的转型。不过,即使是转型或者改革,没有强人政治和强人政府是无法办到的。[7]
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认为,应对挑战需要新的方式和新的模式。他说,当前形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再适合当今世界,我们正处在一场大变革当中。今天的挑战只能靠国际社会来共同解决,而处置这些挑战需要新的方式,因为将我们带入危机的旧制度早已过时。为更好地应对突飞猛进的变革,我们需要新的思维模式。我们需要领袖人物以新的领导方式来应对变革。[19]
概括地说,学者们提出的应对危机的思路,主要有以下几种:(1)回归资本主义根本论。认为应当重归资本主义根本,向东方学习。(2)双重转型论。认为应当针对两大结构性矛盾,实现双重转型。(3)创新资本主义模式论。认为应当以新的方式和新的模式取代过时的旧制度。(4)政治思想转变论。认为需要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重大转变。(5)更新宏观经济政策论。认为应当制定新的宏观经济政策。(6)金融职能分离论。认为应当实行银行信贷和投资银行的分离。克服危机的思路和对危机本身的性质及其根源的认识密切相关。大多数专家的意见都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和战略性的,都有不同程度的启发性,有的有重要价值。但是,资本主义的“根本”是什么,回归根本就能够避免危机吗?如果回归根本就能够避免危机,那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不会发生危机。所谓“双重转型”有一个转型的性质和界限问题——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转型,还是转向另一种社会形式?“资本主义模式”是有可能创新的,但如何创新,创新后的模式能够解决什么问题,不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政治思想的转变”的确很重要,但这种转变毕竟不能脱离经济基础。其他的观点对于应对这次危机可能都有意义,但都停留在表面上。问题的关键是,国际社会应当和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在既定的经济前提下能够解决什么问题。
(二)应对危机的思路和对策必须以现阶段的经济关系为基础
“应对危机”本身就是一个包含不同认识和判断的模糊概念。具体的思路固然重要,但思路必须同现阶段的经济关系相适应。各国政府只应当做那些现阶段应当做和可以做的事情。
1.应对危机只能提出切合现阶段经济关系的要求和目标
应对危机首先有一个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和目标的问题。有两种极端的认识是不切实际的,甚至是有害的。一种是保守的一端,应对危机的目标只是为资本(同时也为主要是为资本服务的政府)解困,或者说挽救资本;另一种是激进的一端,即在现阶段就力图通过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而一劳永逸地避免危机。
单纯以挽救资本为目标的政府救市不过是饮鸩止渴。面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府债务危机,各国纷纷采取应对措施。对外主要是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转嫁危机;对内主要是采取“救市”措施。“救市”的重点和核心是救资本。一是政府直接向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和产业公司注资,直至实行国有化;二是放松银根,增加纸币供给和银行贷款(包括消费信贷),增加货币的流动性;三是增加政府对公共事业和公共工程方面的投资,为过剩的商品提供市场。这些措施可能有助于缓解眼前的困境,但对解决产能过剩不仅没有任何帮助,反而必定带来以下问题:一是进一步增加政府财政赤字和债务负担;二是导致通货膨胀、纸币贬值和增大金融风险;三是由于扩充产能而制造新的危机;四是由于为拉动经济增长而投资造成资源浪费;五是不利于淘汰和提升落后的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必须充分认识到,危机的发生并不是因为缺少货币,而是缺乏劳动者消费需求的购买力。因此,所有通过增加货币供给而扩大的需求,都不能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比例,而是一方面制造新的生产过剩,一方面制造价值泡沫。这样一来,经济危机(从而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就会恶性循环。总之,在危机面前,一个对社会负责的政府可以有所作为,但任何违背经济规律而旨在缓解和推迟经济危机爆发的办法,不过是饮鸩止渴,从而把一个个较小的、间隔时间较短的危机累积为百年一遇的特大危机。
现阶段还不具备建立起一劳永逸地消除危机的经济制度的条件。提出应对和克服已经发生的经济危机,并不意味着现在就有可能避免危机。因此,那种现在就力图避免或者消除经济危机的要求和思路,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判断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否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不能单纯看这次危机严重的程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暴露出来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看现在是否能够出现可以取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新制度。一批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实践(一部分回归资本主义道路,另一部分放弃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经济形式)充分证明,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走一条特殊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成功的典范),但不可能以劳动者联合的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实践同样证明,资本主义经济的潜力还远未全部发挥出来,至少在包括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因此,由这种生产方式必然带来的经济危机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现在还谈不上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和资本主义制度相对立的新制度、新方式、新模式。我们只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谈论“新制度、新方式、新模式”。
国家主导的亚洲发展模式不可能避免危机。前面关于危机根源的分析已经指出,当前的危机是纳入全球化体系的所有国家共同造成的,并且都毫无例外地处在危机之中,可谓“人人有份”。总结世界各国不同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经验可以发现,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确有值得学习借鉴的东西。但是,如果以为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发展模式可以避免危机,并因此而提出向它们学习,是极大的误解,在理论上也是不正确的。第一,不要以为亚洲国家乃至发展中国家就不会发生经济危机,中南美洲和亚洲在上个世纪都已经发生过金融危机了。第二,不要以为政府主导和管制的发展模式就可以避免危机。政府的主导和管制有两重性:一是有可能防止资本的变异,弱化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二是有可能助纣为虐,加剧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就前一重性质来说,有可能避免严重的经济危机;就后一重性质来说,政府至多可以掩盖矛盾和危机。如果政府主导和管制的结果不仅不能解决产能过剩和过度依赖外国市场的问题,危机反而比西方国家更严重;如果在政府主导和管制下实施更具扩张性的经济政策,从而带来更大的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那么危机至少已经在形成过程中了。应当明确,这次经济危机之所以没有从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爆发,主要不是因为它们是政府主导和管制的模式,而是因为它们现在大都还处在资本主义较低的发展阶段上。一方面,资本还不可能像欧美国家那样发生变异,另一方面,高报酬、高福利、高消费的状况还不可能发生。
2.避免严重的金融危机须摈弃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制度
我们确认目前不可能以新的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意味着资本可以按其本性为所欲为,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接受“新自由主义”。越来越多的学者从这次危机中得出正确的结论:要避免严重的金融危机须摈弃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制度。
新自由主义的实质是放任资本的恶性扭曲和变异。一般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凯恩斯主义失败后对古典自由资本主义的回归,是作为凯恩斯主义的对立物出现的,其基本观点是认为市场万能、私有万能、政府失败、政策无效,因而主张最大限度地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这些认识和概括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但并没有更深刻地揭示出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和要害。新自由主义是庸俗经济学的最新版本。新自由主义的问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题中应有之义。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和要害在于,要求社会放任资本职能和获得剩余价值方式的极度扭曲和恶性变异(畸变)。前面已经指出,资本的扭曲和变异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新自由主义起到了理论诱导和推波助澜的作用。资本扭曲和变异的主要表现是:作为价值符号的纸币完全脱离并取代了货币(黄金)本身,从而使纸币的发行成为任意的事情,这就意味着政府的货币当局可以创造“货币”;个别国家(首先是美国)的纸币成了作为“硬通货”的国际货币和储备货币,从而成为统治世界的力量;资本越来越脱离再生产过程而滞留在市场(包括虚拟的市场),专门进行投机、赌博和诈骗;作为资本所有权证书的虚拟资本,不是作为现实资本的纸制复本并服务于现实资本,而是越来越脱离现实资本,并凌驾于现实资本之上,成为投机和制造泡沫的工具;金融界的精英以“金融创新”的名义,通过制造光怪陆离的金融衍生产品和金融杠杆化,不断制造、掩盖、转嫁金融风险;从此,越来越多的资本不是通过执行自己在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获得平均利润,而是通过为所欲为地制造价值泡沫和投机诈骗而获取暴利。
新自由主义几乎把资本推上了自我毁灭的绝路。这次危机证明,新自由主义所导致的资本的扭曲和变异,不仅酿成了空前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而且已经危及到资本本身的健康发展。如果说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那么,资本绝不能离开一定的物质条件和经济关系。第一,资本本身必须有价值(社会一般劳动),必须以商品和货币作为它的物质承担者;第二,资本必须在再生产过程中执行一定的职能,剥削能够创造价值的雇佣劳动者。如果资本既脱离物质载体,又不剥削雇佣劳动,资本就不再是资本,或者说资本本身就不存在了。新自由主义正是把资本变成了虚无的东西,几乎把资本推上了自我毁灭的绝路。新自由主义对于资本的关系,就像癌症和毒品对于人的关系一样。因此,批判和摈弃新自由主义,不仅是应对危机的要求,而且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生存和发展的要求。我们必须把资本主义和新自由资本主义区别开来。批判和摈弃新自由主义,并不意味着现在就要摈弃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并不是要根本否定同资本的职能相适应的金融资本和虚拟资本的积极作用,而是把扭曲、变异、畸变的资本再矫正过来,割除长在资本上的毒瘤,使资本在社会的强制下“戒毒”。
新自由主义在潜在经济危机的基础上制造了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从金融资本反映出来的问题(这一次危机是金融资本存在问题的集中表现),是资本扭曲和变异的表现。资本是一种历史性的生产关系,它的产生、发展、消逝都不过是在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资本的扭曲和变异固然与资本贪婪的本性有关,但并不是“资本的错误”,而是资本的政治代表和理论代表的错误。作为资本政治代表的国家及其政府,以及作为资本理论代表的理论家(首先是经济学家),对资本的本性及其历史性质的认识,对危机根源和应对危机思路的认识,都可以犯错误,事实上已经不断地犯错误。起初,有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不会发生生产过剩的危机,听任危机自然发生又自然复苏。后来,虽然有人认识到有可能发生危机,但又认为危机根源于受心理预期影响的有效需求不足,要求政府承担起创造需求的重任。再后来,政府“创造”需求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于是新自由主义就作为前者对立面粉墨登场了,在他们看来,危机是资本被限制、资本主义制度被弱化的结果。自从资本的两方面代表充分发挥能动性以来,他们犯的最大的错误有两个:一个是连续地实施扩张性的经济政策,用导致新的产能过剩的方法缓解眼前的产能过剩,使经济运行恶性循环,从而埋下了发生严重危机的祸根;二是放任资本的贪婪本性恶性发展,致使资本严重扭曲和变异——资本越来越脱离再生产职能,越来越通过制造泡沫和投机诈骗取得剩余价值。变异的金融资本就像癌细胞一样到处扩散,以至于成为破坏生产力的因素。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就是资本的代表连续犯的两个错误造成的。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曾经以政府创造的需求暂时缓解了危机的话,那么,新自由主义也曾经以扭曲变异的资本创造的虚假繁荣暂时掩盖了危机。正因为如此,这次危机是前所未有的。没有第二个错误,危机也会爆发,但只是第二个错误,才使危机直接以国际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才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导致的经济危机不可避免,但是,由资本的政治代表和理论代表的错误导致的严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因而是可以消除和避免的。
摈弃新自由主义必须抓住问题的关键。摈弃新自由主义需要集思广益,并从各方面入手。学者们开出的药方,如果给以适当的解读,还是有用的。所谓“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重大转变”,就是摈弃新自由主义,但不是让政府取代资本本身的作用,不是重新恢复凯恩斯主义的统治地位。所谓“重归资本主义根本”,就是让资本回归到自己的职能上来,而不是走邪门歪道。所谓“双重转型”,无非是把变异的金融资本再转变过来,放弃以政府负债的方式解决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矛盾。但必须抓住问题的关键:第一,资本不能脱离商品和货币。资本是价值物,商品和货币是资本的基础和前提。资本脱离商品和货币,就像人的灵魂脱离肉体一样,变成一缕轻烟。因此,资本必须以货币和商品的形式表现自己,价值符号只应当作为真实货币的表现,而不能代替货币。虚拟资本必须限制在为现实资本服务的范围内。有鉴于此,必须在实际上重新确立能够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到目前为止只能是黄金)作为真实货币的地位;不能容许虚拟资本成为资本增殖的手段;不能放任投机资本的恶性发展。第二,资本必须回归社会再生产过程(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资本不过是生产的一种特殊社会形式,资本必须在再生产过程中执行自己的职能,必须通过支配雇佣劳动创造价值和取得剩余价值。个别资本有可能靠赌博、投机和诈骗取得剩余价值,但就总资本而言,这就如同变戏法一样。第三,资本不能无限制地任意进入一切领域。资本进入的领域,应当是充分竞争的领域。在个别资本特别是超大个别资本有可能垄断的领域,必须加以限制。或者限制其进入,由国家代表社会直接经营;或者限制其利润率,使它们不能不冒任何风险地获得高额利润。对于已经获得的高额利润,必须通过税收形式收归国家。至于在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领域,对资本的限制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3.避免政府债务危机必须正确规定政府的职能
政府的债务危机源于政府持续的财政赤字,而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则不得不向国内外借债,当到期债务不能偿还的时候,债务危机就发生了。政府债务危机的形成有两种可能:一是财政收入不足以支付政府执行社会赋予它的必要职能;二是政府承担的社会职能超出了社会容许的最大限度的财政收入。在前者那里,政府的职能定位是合理的,但财政收入没有给予保障;在后者那里,财政收入是合理的,但政府的职能定位过宽。在现代社会中,政府职能的合理定位和财政收入的合理界限,都是在既定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中反复实践的结果。一般地说,所谓“合理”就在于,更有利于经济发展、阶级和谐、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在西方国家,就财政收入来说,现在仍有增加的余地,该收的赋税没有全部收上来,但是受到大资产阶级、高收入阶层的强烈抵制(通过议会)。在竞争性的制造业领域,资本利润率比较适当;但在某些领域(例如金融领域,房地产领域),资本利润率明显偏高。所得税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形式,但仍有缺陷,没有起到抽肥补瘦、遏制贫富悬殊的作用。就政府职能来说,有些方面已经明显超出了合理的范围。一是用于颠覆他国的侵略性军事开支过多(美国是这方面的典型);二是和资本主义制度相矛盾的“福利国家”制度造成过度支出(西欧一些国家是这方面的典型);三是为应对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救市”)而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为了避免政府的债务危机再度发生,首先必须合理界定政府的职能,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必须免除用于维护霸权的军费开支;必须放弃“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制度;必须放弃饮鸩止渴和徒劳无益的政府救市。其次必须保持一定经济周期内的财政收支平衡,赤字财政在实践上是有害无益的,在理论上是不科学的。
应当指出,社会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例如教育,医疗,住房),建立起码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济制度)范围内也是可行的。这既是实现公平竞争和抑制贫富差距过大的必要前提,也是资本本身生存(它的生存一方面依赖于能力和素质不断提高的雇佣劳动者;一方面依赖于雇佣劳动者起码的购买力)的要求。因此,社会不能放任公共产品领域的资本化。强化公共产品领域的资本主义关系,不仅不会避免危机,而且只会适得其反。但是,社会不可能通过政府财政的转移支付和再分配手段,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必然带来的所有问题——主要是失业和两极分化等问题,而只是将其限制在资本和劳动都能够接受的范围内。实践证明,一个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政府,不应当也不可能解决这种生产方式本身的问题。政府只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解决应当和能够解决的问题。超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的政府职能,必定同仍然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矛盾。
4.危机有可能降低的程度取决于劳动者收入和消费的比重
如前所说,经济危机的基础性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劳动者报酬在新价值中的比例偏低,他们的消费能力无力吸收强大的生产能力生产的产品和服务。不仅就个别国家说是如此,就国际社会说也是如此。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然是先进生产力的主要承担者时,它内在的基本矛盾不可能消除。但是,由于资本的过分贪婪和变异造成的劳动者报酬和消费能力过分低下的状况,社会应当而且有可能改变。这种状况的改变,既不是靠政府的“施舍”,也不是靠滥发纸币,而是通过抑制资本的贪婪和变异,调整资本利润和劳动者报酬之间的比例关系。这就要求,每个国家和国际社会必须阻止和扭转资本的恶性扭曲和变异,必须限制资本在关系国计民生的流通领域投机,必须限制资本在虚拟资本领域的投机和诈骗,必须取消单纯通过投机和诈骗获得的暴利,必须尽力保护雇佣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劳动者报酬,就业,社会保障)。在这方面,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应当做得更好。
四、当前危机的前景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命运
(一)外国学者对危机前景和资本主义制度命运的认识见仁见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肯尼斯·罗戈夫认为,金融危机并不标志资本主义的终结,而是将以其他形式取代英美模式。他说,所有现行的资本主义形式归根到底都是过渡性质的。现代资本主义的众多缺陷(五大缺陷)——无法给公共产品有效定价;在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导致了异乎寻常的贫富分化;医疗保健的提供和分配不符合确保经济效率的价格机制的要求;大幅低估了后代人的福利需求;金融世界的技术创新增加了风险——也会日益彰显出来。但是,全球金融危机并不标志着现代资本主义的终结已初露端倪。至少在现在,只有其他形式的资本主义才可能真正取代当今居主导地位的英美模式。尽管资本主义灭亡的话题可能十分时髦,但其可能性似乎很渺茫。[20]
乌拉圭国际问题专家劳尔·西韦奇认为,资本主义将被“反体系”力量所摧毁,但不会一蹴而就。他说,当前的危机让世界不同的地区支离破碎,使世界体系越来越接近于脱节。世界正在向后资本主义时代过渡。在制定全球战略的进程中有两个因素在产生影响。一方面,资本主义既不会落空,也不会彻底崩溃,而是会被“反体系”力量所摧毁,这种力量既包括底层的社会运动,也包括存在等级差别的政党和抱有反资本主义意愿的政府。另一方面,向一种新社会的转型不会一蹴而就,不会在几十年内就发生。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过渡都需要数百年时间,其间人们不能不忍受巨大的痛苦。[21]
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戴维·皮林认为,陷入危机的资本主义同时也是亚洲通向繁荣的危险道路。他感到,“这个世界已经完全变了。”他援引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荣誉退休教授梅格纳德·德赛的话说:资本主义并没有陷入危机,陷入危机的只是步入老年的西方资本主义。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冲劲十足、勇于创新、只追求经济增长的资本主义——已经向东方转移。但是,他认为,亚洲国家那种妄自尊大的成就感只能到此为止;西方的资本主义危机对于东方来说也是一件深感不安的事情。他认为至少有三个相互关联的原因:第一,许多国家在筹划一条通向未来繁荣的道路时,决定推行越来越“资本主义的”政策——放松国家对银行、利率以及货币走向的控制,从而面向市场力量开放其经济。但是那条通往繁荣的道路现在看上去再危险不过了,容易受到繁荣和衰退的交替循环以及金融灾难的影响。第二,尽管有关亚洲价值观的言论曾经风靡一时,但是没有一个亚洲国家能够提出一个前后连贯的制度来取代资本主义。第三,亚洲人不应该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危机感感到欢欣雀跃,因为他们的经济都在同一条世界大船上。西方资本主义危机给亚洲经济体怎样才能管理好经济提出了很多问题。总的主旨是:国家应该发挥多大的主动作用?资本主义危机留下的另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亚洲社会的不平等到底应该达到什么程度。但事实上,没有一个亚洲国家提出一个更好的模式。由于缺少一个更好的制度,希望提高人民收入的亚洲政府将不得不重新依靠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制度。对于他们来说,它还是那个可能最糟糕的经济制度——但却是所有制度中最好的。[22]
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亚洲项目的负责人凯利·布朗博士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中的主要问题是不公平,在欧洲和美国这都是现实,甚至在印度和中国也存在这样的问题。然而,目前缺乏如何解决这种不平等的思路,消除这种不公平感的政策缺位,政府在调节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2]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马丁·雅克认为,现在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榜样。他说,从1978年以来,中国在很多方面的表现都值得其他国家学习和借鉴。虽然说就此归纳出一种特殊的“中国模式”来或许并不完全正确,但是在中国的发展中,在经济政策方面肯定存在大量成功的经验和思路,这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都非常重要。现在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榜样,而“华盛顿共识”则已经被抛弃。[2]
埃及前外长助理、阿拉伯投资者联盟主席贾迈勒·卜尤米认为,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改变所有制,让资金不再掌握在少数金融巨头手中。这需要制定相应政策,改革货币政策工具,加强市场监管。[8]
墨西哥前驻华大使塞尔希奥·雷·洛佩斯认为,这场危机并不是新自由主义学说的坟墓。如果能够纠正错误,经济恢复是可能的。经过调整,更加完善的、有管理的资本主义制度是有生命力的。我不认为目前这场危机就是新自由主义学说的坟墓。[9]
美国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赖克认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要求在于建立一个免受金钱腐蚀的、干净的民主制度。他说,我同意“占领华尔街”运动是贫富悬殊不断扩大的结果的说法。我认为抗议者所表达的核心信息是:当收入和财富如此集中于少数人手中时,会不可避免地破坏民主,因为那些极少数富人有足够的金钱主宰民主。我不知道“占领华尔街”运动未来发展方向,但是我预期这个运动的要求将集中于建立一个免受金钱腐蚀的、干净的民主制度。[11]
国际工会联盟秘书长沙兰·伯罗认为,20世纪的资本主义已经过时。他说,20世纪的资本主义不再适合21世纪。资本主义没能带来安全的饭碗,也没能平均分配财富。[23]
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认为,当前形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再适合当今世界。他说,政治家不称职,我们大家也一样,因为我们作为社会允许金融体系恣意妄为。我们没有及时制定规则来避免制度腐败变质。人们绝对可以说,当前形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再适合当今世界。[19]
德国著名经济学家奥特马尔·伊辛认为,政府为防止金融体系崩溃而实施干预已经动摇了市场经济的基石。他说,虽然“现实的社会主义”在每一块试验田都以灾难收场,但历史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承诺实现平等的思想永远不会消失。为防止金融体系崩溃而实施干预的做法,不仅严重削弱了人们对金融市场的信心,也动摇了人们对整个市场经济的信心。金融机构“大到不能倒”的问题导致社会(更确切地说是纳税人)不得不为个别金融机构的生存买单。因此,这动摇了市场经济的基石。巩固市场经济和自由社会基石的挑战依然存在。历史永远不会终结。[24]
学者们提出的关于危机前景和资本主义制度命运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1)制度过渡论。认为经过这次危机,资本主义不会自动崩溃,而是将逐渐被反资本主义体系的各种力量所摧毁,但不会一蹴而就,不会现在就彻底崩溃,而是缓慢地向“后资本主义时代”过渡。(2)体制过时论。认为老年的资本主义、20世纪的资本主义、当前形式的资本主义、英美模式的资本主义已经过时。但这不是资本主义的终结,而是以新的形式取代过时的形式。因此,这次危机不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危机,而是资本主义过时形式的危机。(3)模式转变论。认为“华盛顿共识”已经被抛弃,现在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榜样。(4)体制调整论。这场危机并不是新自由主义学说的坟墓,但会进行调整。经过调整,更加完善的、有管理的资本主义制度还是有生命力的。(5)机制变革论。认为须在现有的基础上进行不同方面的变革:从解决社会不公平的问题出发,必须提出现在仍然没有的新的思路;从解决资金掌握在少数金融巨头手中的问题出发,必须改变所有制;从解决贫富悬殊不断扩大的问题出发,必须建立一个免受金钱腐蚀的民主制度;从解决政府为应对危机而实施的不当干预的问题出发,必须改变政府不当的行为和做法。这些观点虽有很大差异,但都是积极的和建设性的。其中,“过渡论”无疑包含了一种正确的思想,因为新的生产方式总是在旧的生产方式内部逐渐孕育和成长起来的。但问题是,现在是否已经开始了“向后资本主义时代过渡”的进程,其标志是什么?“过时论”总体上也是正确的,西方国家老旧的资本主义模式的确已经过时,但新的资本主义形式是什么,二者质的区别是什么?新的形式能不能避免危机?“转变论”乍一看具有革命的性质,实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在亚洲或东方国家显示了当年在西方国家曾经显示的生命力,但是,这是资本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别,还是不同模式的差别?类似中国的模式能够成为西方国家的替代模式吗?“调整论”并不认为新自由主义本身有什么问题,而只是认为不够完善。这是不切实际的,在新自由主义框架内,不可能纠正资本扭曲和变异的问题。“变革论”中的各种建议也是积极的,甚至是现在就可以着手做的,但基本上没有涉及深层次的问题,因此,能够产生多大的效果还有待实践证明。
(二)当前的危机并不是资本主义终结的征兆
如何认识当前危机的前景和资本主义的命运,是一个实践性和理论性都很强的问题,不能作出简单草率的结论。这里只是提出以下原则性的看法。
1.世界经济不可能永久处于持续衰退的状态
早在2009年,即美国金融危机发生的第二年,我国就有学者谈论“后危机时代”。当时在他们看来,这次危机已经大势已去。实践证明,这是误判。就是现在,谈论“后危机时代”还为时尚早。我们必须充分认识这次危机的特殊性和严重程度,必须充分认识美欧和国际社会应对危机的方式。可以肯定,这次积累了很久的严重危机不会很快结束,经济低迷状态还会继续,债务危机不会轻而易举地解决,欧美国家的高失业率将成为常态,劳动和资本、居民和政府之间的斗争导致的社会动荡不可避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从此世界经济永久地处于持续衰退的状态,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将从此走向坟墓。可以预料,只要是把人为扭曲和变异的资本再扭转过来,只要是容许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然规律起作用,只要是在危机中能够淘汰落后的产能、技术、生产方式、生产要素等等,深受危机困扰的国家就会起死回生,世界经济就会走出衰退的状态。
2.发达经济体在经济全球化中陷入困境是不可避免的
经济(贸易、生产、金融)的全球化具有双重性,是一把双刃剑。率先发生工业革命并超前发展起来的西欧和美国,通过占领殖民地,通过输出商品和资本,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传播到资本所能到达的每一个角落,从而开始了全球化的进程。随着现代金融资本的发展,经济的全球化迅速发展。在发展中国家的商品生产还没有普遍化、资本主义经济还没有充分发展以前,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但是,进入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不仅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发展,而且,放弃传统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或者回归资本主义道路,或者走上特殊的社会主义道路,经济也快速发展。它们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在“市场经济”的名义下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二是通过对外开放吸引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当它们先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真正成为全球化经济的一员。它们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和国内的自然资源,很快在一般制造业中取得了相对优势。它们也像当年的欧美国家一样,把商品输出到世界各地,而数量最大的是发达国家。这时候,发达国家的一般制造业不得不逐渐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开始是“四小龙”,后来是“四小虎”,再后来就是“金砖四国”)。这种情况直接影响到发达国家的就业。这个进程并没有到此为止。很快,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高技术产品也获得了发展,并同样输出到世界各地。这时候,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被挤压在更加高端的高科技领域。但是,一方面,这个产业层次过分狭窄,不能解决大多数普通劳动者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它们实行限制高技术产品出口的政策,出口市场的扩大受到了限制。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新兴工业化国家和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方兴未艾的时候,发达国家却陷入困境。在发达国家,受到打击的不仅是蓝领工人,而且还包括白领工人和职业经理。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中产阶级都受到了全球化的威胁,发达国家本身也感到走投无路。现在,发达国家的一部分工人开始反对全球化了。当年全球化的鼓吹者现在却成了反全球化的力量。或者说,它们只希望有利于它们的片面的、单向的全球化。它们除了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反倾销,提高进口产品的技术标准,要求出口国的货币升值),别无他法。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性是改变不了的。如果说资本主义的兴旺发达是从欧美国家开始的话,那么,资本主义的衰败也必将首先从发达国家开始。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发达国家已经积累起来的货币财富和技术知识,以及相应的军事能力,足以使它们支撑相当长的时间。
3.资本主义还远未到退出历史舞台的地步
这次危机暴露出来的问题,的确足够严重,令全世界都为之惊恐。它既暴露了在新自由主义理论指导下资本扭曲和变异的问题,也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问题。但是,我们还不足以认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总体上已经过时。对于老欧洲国家来说,资本主义制度可能已经到了晚期,郑永年所说的“两大矛盾”——金融资本主义和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民主与资本主义的矛盾——缠身而难以解脱。但是,社会只要是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在一定限度内这两个矛盾都可以自行调节。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然是现阶段先进生产力的主要承担者,那么,它就会要求各方面的经济关系乃至政治上层建筑,必须与之相适应,扭曲和变异的关系必须矫正过来。金融(借贷资本和信用制度)本来就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如果金融独立于实体经济之外并为所欲为,资本增殖就会变成无源之水,利润就会成为虚幻的假象(泡沫),这时候,变异的金融制度就需要变革了。民主作为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同样是为经济制度服务的,如果以民主形式产生的议会和政府成为资本的对立物,从而危及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那么,这种民主形式就需要变革了。对于所有发展中国家来说,甚至对于美国和新欧洲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然是先进生产力的主要承担者。在世界的大多数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普遍发展只不过几十年的时间,还处在青壮年阶段,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这种生产方式仍然具有相当的活力。问题还在于,如果断言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到了穷途末路,那就必须有新的形式取而代之。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的实践证明,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不可能为共产主义生产方式所取代。这次危机暴露出来的问题,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中的问题——扭曲和变异。因此,现在还不能说世界正在“向后资本主义时代过渡”,过渡的进程还没有开始。
4.资本主义制度将适应生产力的要求而变革发展模式
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未到退出历史舞台的地步,并不意味着可以任凭扭曲和变异的资本主义形式继续下去。资本的扭曲和变异自然有其内在的因素,归根到底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的贪婪本性,而华尔街的金融大鳄、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政府的代表人物等等,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但是,既然这种扭曲和变异的形式已经危及到资本本身的生存、发展,那就一定有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得到适当的纠正。这种纠正包含双重涵义:在一定意义上是回归资本的本性(资本的历史使命就是以对立的形式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另外一种意义上又是对扭曲和变异关系的扬弃。对扭曲和变异的资本的纠正,意味着变革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模式。资本本身必然会提出如下变革要求:第一,重新确立真实货币的地位。资本作为价值物,必须表现在真实的商品和货币上,而货币是商品的一般代表和抽象财富。纸币(无论是美元、欧元还是人民币)是价值符号,它本身不是价值物,因而也不可能是资本。超出了同生产和流通相适应的货币额的纸币,更不可能是资本。现在,真实的货币只能是黄金。第二,恢复金融机构融资的基本职能。为社会正常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融资是金融机构的基本职能。金融机构本身不能成为投机诈骗、盗窃社会财富的毒瘤,不能以此目的制造所谓的金融衍生产品。第三,限制资本纯粹的投机活动。首先是限制巨额资本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商品(例如粮食,住房,石油等等)的垄断和在流通领域纯粹的投机;其次是限制资本所有者在虚拟资本形式上纯粹的投机活动。证券市场的存在,主要在于有利于资本的合理流动,资源的合理配置,淘汰落后的企业。但是,纯粹的投机活动所起的作用几乎相反。证券市场不能成为投机者轻而易举地盗取社会财富的场所。第四,放弃为掩盖危机和挽救陷入困境的资本而救市。对有可能陷于瘫痪的金融体系社会不能袖手旁观,在这个限度内自然可以谈论“救市”。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生命力在于充分竞争,而危机则加剧这种竞争,加速优胜劣汰。社会不应当为掩盖危机和保护落后而救市。因此,为此目的而采取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创造”需求而进行的得不偿失的投资,都应当废止。第五,政府财政收支必须实现平衡。赤字财政是债务危机的直接原因,这种情况不能持续下去。一方面,政府的财政收入必须同必须执行的职能相适应;另一方面,政府执行的职能必须限制在可能的财政收入之内。
5.我国必须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步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在经济制度和经济形式方面已经发生了重大的(甚至是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在经济制度方面,我国已经确立了公有资产占优势、国家控制经济命脉、公私并存、社资兼有、劳资两利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在交换方式和经济形式方面,我国已经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进入市场经济体系的市场主体,无论资产的法律所有权如何不同,生产方式大都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生产的直接目的都是为了实现资本增殖(剩余价值)。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系列经济规律,都会在我国现阶段不同程度地起作用。因此,由这些规律的作用导致的生产相对过剩、相对贫困、失业现象等等不可避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同样不可避免。而且,在我国深深地加入到全球化体系之后,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都无不具有世界性质。在这次发端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中,我国绝不是仅仅受到了“外部冲击”,而是在这种“外部冲击”下,充分暴露了我国已经孕育着的经济危机,只是表现形式和特点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罢了。如果说,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会被这次百年一遇的危机所击垮,那么,我国就不仅必须应对当前的这一次危机,而且必须应对今后还会发生的经济危机——首先是一般的周期性危机;如果西方国家难以实现资本主义模式转变的话,那么,还必须准备应对类似当前这样严重的危机。国际社会的问题,中国也有责任,但必须在国际社会形成共识的基础上一起努力解决。我国自身的问题,只能靠我们自己解决。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在传统的发展方式中,完全有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危机。一方面,从经济关系上来说,我国目前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劳动者报酬和资本利润的关系)、居民和政府的关系(居民收入和政府收入的关系),处于显著不合理的状态,产能严重过剩和社会两极分化就是这种不合理状态的两大表现。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和国有银行潜在的金融风险已经不可忽视。多年以来,我们不断地以扩张性的经济政策支持和制造高速增长的奇迹,但同时带来了越来越严重的比例失调、结构扭曲、城乡差距扩大、价值泡沫(通货膨胀,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资源环境恶化、贫富悬殊等等问题。在问题恶化到不得不改而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情况下,诸多行业产能过剩、地方财政危机和金融风险很快凸现出来。特别是在外需减少、出口下降的情况下,便会是祸不单行和雪上加霜。但是,价值泡沫一旦破裂,势必威胁到资本集团和政府的利益。因此,我们又以同样(甚至更大力度的)扩张性的经济政策来解决由这种政策本身带来的问题。这样一来,我们就完全依赖于扩张性的政策了,而且陷入恶性循环了。正如有的外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不应当有任何盲目乐观和侥幸心理。摆脱这种政策依赖和避免恶性循环的关键是,我国必须痛下决心,尽快转变传统的发展方式,真正走上科学发展之路。传统发展方式的要害是以速度为中心,但以速度为中心这种不合理的发展方式,来自我国特有的经济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两个定位”不够合理:一是国有经济的定位不够合理。国家资本不适当地进入了盈利性、竞争性的产业,并且借助官商结合的关系处于垄断地位和被保护的地位;二是政府的职能定位不合理。政府不适当地进入了市场本身能够解决好的领域,而市场无能为力且无利可图的领域,又任其商品化、市场化和资本化。这两个不合理的定位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公有制为主体”的名义下形成的。其实,不管主观愿望多么好,就其内容和效果来说,恰恰是对社会主义和公有制的异化。我们必须深刻总结30多年来我国改革发展的经验教训,转变改革思路和发展方式,走一条既合乎中国国情又遵循一般规律的发展道路。
[1]世界已进入危机的第二阶段[N].西班牙起义报,2012-01-15. 转引自参考消息,2012-01-29(3).
[2]新自由市场主义埋下祸根·资本主义危机纵横谈(上)[N].参考消息,2012-01-18(11).
[3]美式金融资本主义已病入膏肓·资本主义危机纵横谈(下)[N].参考消息,2012-01-20(11).
[4]马哈蒂尔·本·穆罕默德.失败的国家[N].脸谱网站马哈蒂尔主页[2011-11-11].转引自参考消息,2011-12-11(3).
[5]劳伦斯·萨默斯.目前的困境要的是智慧的新创造而非破坏[N].英国金融时报,2012-01-09.转引自参考消息,2012-01-25(10).
[6]金融业监管缺失导致资本主义危机[N].参考消息,2012-01-18(11).
[7]当代资本主义面临两大结构性矛盾·资本主义危机纵横谈(中)[N].参考消息,2012-01-19(11).
[8]美欧危机印证自由资本主义失败·资本主义危机纵横谈(下)[N].参考消息,2012-01-20(11).
[9]资本主义已经进入调整阶段·资本主义危机纵横谈(下)[N].参考消息,2012-01-20(11).
[10]胡安·索马维亚.从国际劳工组织角度看资本主义危机与不平等[N].西班牙起义报,2012-01-29.转引自参考消息,2012-01-31(10).
[11]罗伯特·赖克.贪得无厌的消费者正在破坏民主制度[N].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012-02-01].转引自参考消息,2012-02-20(10).
[12]马凯硕.到亚洲的工厂看看资本主义的教训[N].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012-02-20].转引自参考消息,2012-03-07(10).
[1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6]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8]马哈蒂尔·本·穆罕默德.西方有必要重归资本主义根本[N].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012-01-11].转引自参考消息,2012-01-25(10).
[19]克劳斯·施瓦布.资本主义制度不再适合世界[N].德国金融时报,2012-01-25.转引自参考消息,2012-01-26(10).
[20]肯尼斯·罗戈夫.现代资本主义是可持续的吗?[N].新加坡海峡时报网站[2011-12-06].转引自参考消息,2011-12-12(10).
[21]劳尔·西韦奇.左派和资本主义的终结[N].西班牙起义报,2012-01-14.转引自参考消息,2012-01-27(10).
[22]戴维·皮林.陷入危机的资本主义:通向繁荣的危险道路[N].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012-01-16].转引自参考消息,2012-01-26(10).
[23]沙兰·伯罗.世界经济如何发展……[N].德国世界报网站[2012-01-25]. 转引自参考消息,2012-01-27(1).
[24]奥特马尔·伊辛.资本主义绝非历史终点[N].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012-01-31]. 转引自参考消息,2012-02-02(10).
How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risis:Also on Various Views of Foreign Scholars
CHEN Wentong
(College of Economics,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Haidian,Beijing 100091)
The ongoi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risis is in essence a crisis of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This crisis not only makes the traditional capitalist model hardly sustainable,but also proclaims the bankruptcy of the neo-liberal capitalism.However,the capitalist system will not therefore step off the stage of history.Instead,it will realize model transformation inside the scope of capitalist system.As a rising power of market economy,China has been inevitably involved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risis due to fundamental internal reasons.Therefore,experience and lessons in the past 30 plus years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must be profoundly summed up.The approach for reform and mode of development should be properly adjusted for a developmental path that conforms to both the general laws and Chinese domestic condition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risis;capitalist model;approach for reform;mode of development;Chinese path
F039/D033.3
A
1674—0351(2012)03—0005—20
2012-03-19
陈文通(1941— ),男,河北乐亭人,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郭彦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