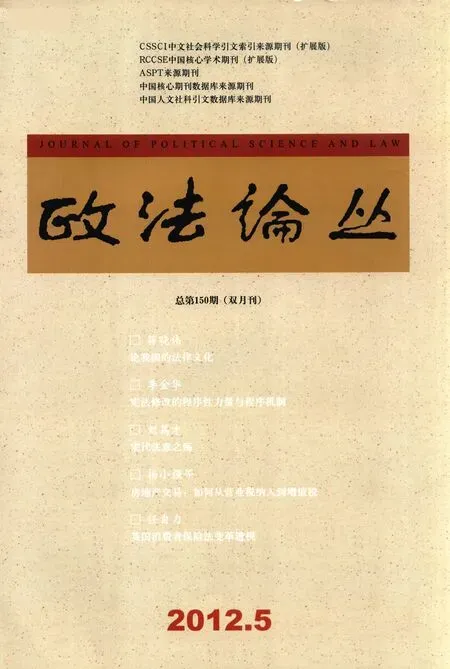自崇礼到重法*(下)
——以先秦士阶层“得君行道”观念为视角
李启成
(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100871)
四、法家“得君”观念下的“法治”思想
在荀子那里,还力图在“得君”和“行道”之间维持一种脆弱的平衡;但在荀子同时甚至之前,即有诸多“士”将价值的天平放在“得君”上,导致学术迎合权力,成为专制权力的帮凶和辩护者。如果说这时已呈现出此一演变趋势,到韩非及其所处时代,则成为士阶层压倒性的抉择。与此相应,社会治理的规范也完全从礼、法并存到绝对排斥礼的“以法为治”。从思想主体而言,这一转变之最终完成,是法家学派及其思想主导下的结果。
(一)法家所主张的“势”尊于“道”
和儒、墨、道等其他诸子不同,法家是先有实际的政治革新运动,后才有较为系统的理论出现。既然是政治革新运动,那自然要得到国君的支持才有推行之可能。因此,诸侯国君的“势”自然就具有首要地位,法家借助君主的力量进行革新,实际上是在“得君”的前提下“行道”,离开了“得君”,“行道”自是空谈。换言之,没有“得君”,“行道”本身不具独立价值。如此,“势”尊于“道”自有其逻辑上的必然。战国中晚期时势之演变,“六国诸侯,谿异谷别,水绝山隔,各治其境内,守其分地,握其权柄,擅其政令,下无方伯,上无天子,力征争取,胜者为右”,(《淮南子·要略》)更助成了法家这种注重现实之学说得势。所以,有学者富有洞见地指出,这一时期之政治思想,“以法家思想为主流,而以兵家思想为辅流,儒、道、墨三家思想在当世虽也是显学,但只是逆流,名家和阴阳家思想,不过是各为一种旁流而已。”(31)
在早、中期的法家思想里,对君主之“势”既有经验层面上的深刻体认,亦有理论上的阐发,尤其是慎到的相关论述,更是把“势”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慎到重点是在论述君主之“势”的重要性和特征,但对君主如何用“势”以治国则谈得不够。也就是说,他仅论及君主以循名责实和争取民心等方法来保证君主真有其“势”。尽管君主之安全是其治国之前提,但光有君主之安全还不足以治国。韩非在这个方面对“势”理论作了很大的推进。
韩非在荀子性恶论的基础上,认定人之本性完全在于其自为心。秉承法家将人分为君、臣、民的三分法,断定君臣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利害关系,儒家所肯定的君臣之间的伦理关系,在韩非看来,即便观察得到,那也是一种假相,其背后的实质仍是双方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所谓“上下一日百战”(32)是也。对握有“势”的君而言,威胁最大的是臣。故君主先要在心理上防备臣下,不能受儒家之蛊惑,相信君应按照伦理标准来对待臣下。君仅在心理上破除伦理障碍是不够的,还要采取积极措施来防患于未然。在这一点上,韩非给君主献策如下:君主要明确赏罚权的重要性。君主“身之至贵,位之至尊”,能保持这种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是实现富国强兵之前提。保持之道,就是要善于运用赏罚权。如何才算善于运用呢?首先国君一定要将赏罚权操在自己手中而不能假人行之;其次,要循名责实进行赏罚;再次,国君要做到不将好恶形之于外,让臣下无从窥测赏罚之所自。这后两点就是韩非所讲的法和术之运用。
韩非根据历史经验,认为绝大多数的君主都只是“上不及尧舜,下不及桀纣”的中材,君主对“势”的运用办法必须根据其中材资质来设计。韩非认为,“势”本身是一个中性的东西,“便治而利乱者也”,关键是看君主如何运用它了,故慎到所讲“自然之势”的不足就显示出来了,遂代之以“人设之势”。何谓“人设之势”呢?简言之,就是“抱法处势”。(《韩非子·难势》)
既然君臣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利害关系,君用臣是用臣之能,臣有能当然亦可反过来制其君,“任人者,使有势也。智士者未必信也,为多其智,因惑其信也。以智士之计,处乘势之资而为其私急,则君必欺焉。”如君主有此顾虑而不敢用能臣,则只好用德臣,但德臣又容易坏事,“任修士者,使断事也。修士者未必智,为洁其身,因惑其智;以愚人之所惛,处治事之官而为其所然,则事必乱矣。”(《韩非子·八说》)在韩非看来,这都是君主不用术、不善于用术所造成的。如果君主善于用术,那不管是能臣还是德臣,皆可用起来得心应手。因此君主需要术来探测臣下言行之真伪,保证办事之效率。
在韩非学说中,“势”既是如此重要,那“道”又如何呢?韩非又是不是“行道”甚坚呢?姚蒸民在陈启天、陈奇猷等学者考证的基础上,以“问田”篇所载韩非与堂谿公之晤谈,认为韩非绝不枉道求容,是一个忠于谋国而拙于谋身的政治家。[14]P45单纯从韩非所说分析,(33)确实能得出这个结论。但问题在于,即便我们认定此真乃韩非所言,可知韩非所认为的“道”是“立法术、设度数”,其最终目标是“利民萌,便度数”,但法由君主所立,术乃君主独用,怎么能够保证韩非之道真能达到“利民萌,便度数”之效果呢?那就要君主充分克制私欲。能充分克制私欲,使一己之言行符合君主个人之长远利益,也就是国家利益的,恐非常人所能做到。君主处至尊之位,诱惑很多,完全克制私欲难乎其难。诚如熊十力先生富有洞见所指出的那般,韩非所谓能“抱法处势”的“中材”,“虽才德不敢望圣人,而必为贤者无疑也。虽不及尧舜,而必能希尧舜而无疑也。”[15]P54很明显,这种合格之君主亦属非常难得,故在通常情况下韩非的“道”会被扭曲,“行道”与“得君”在韩非这里通常不能获得统一。韩非大谈游说之术,且认为其道易行,殉道之机会不大;他基于功利主义之立场,排斥仁义道德,那他话中所透露的这种“殉道”的道德词句又能有几分真实?即便我们退而认同姚先生关于韩非殉道勇气之肯定,那这也仅是韩非个体之选择。就整个法家学派而言,这种“帝王之学”(34)流风所及,且缺乏无道时卷而怀之的人生价值选择以自足,自然是“得君”重于“行道”了,“势”尊于“道”已是非常明显。与韩非师出一门之李斯,即是一例,为“得君”而上督责书,尚有何“行道”之可言?(35)
(二)法家之“法”
法家既认为“势”尊于“道”,“势”就是君主的权力,而君主制度又是从前此“周文”的宗法封建制下蜕变而来。在那个制度变革的转型期,君主权力的强化必然要对宗法封建制有所扬弃。具体而言,一方面要借助封建制下诸侯国君对于包括卿大夫在内的各级贵族和平民之权威,另一方面要打破封建制。双管齐下,最终实现国君的大权独揽。如何才能做到这后一点,那就是寻求法术之士的支持来打击逼君之贵族,以生于君之法代替源于俗之礼。在这种形势下,对法术之士而言,就是要游说国君,让国君坚信,惟有他们所操之法术能帮助国君大权独揽,亦能使其诸侯国救亡图存或一统天下。
春秋时期,尽管王权衰微,诸侯争霸,但在各诸侯国内政外交诸活动之中,礼仍是主要的社会规范。降及战国,经法术之士积极参与,各诸侯国君与之密切合作,展开了一系列的政治革新运动,遂至形势大变,法逐渐代替礼,成为指导各国内政的重要规范。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法术之士所秉持的思想观念起了很大作用。
法术之士多比较现实,且在战国中晚期那种大环境中认识到了君权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没有君权,其针对现实的学说就失去了落脚点,导致其本身也会沦落为他们所讥讽的“空谈”,所以不论是从自身之干禄求进还是学说得用,都要获取国君的信任。从这个意义上讲,徐道邻先生对法术之士之认识可谓深刻,“法家乃政治家而非法律家。这些法家的著作,其全部的内容,无不是在说明如何取得国王的信任,如何把国家弄得安定富强,如何治国第一必须重用法律,而不是对一些实质的法律问题,有任何深刻的探讨。他们是一群政治家,法律哲学家,而不是法律家;至少他们的书,是讲权术的政治学,间或略带一点法律哲学,而不是法律学。‘法家’(Legists)并不就是‘法律家’(Jurists)。”[16]P4明白此点,即可进而对法术之士所谈的法有较为准确的定性。
在法术之士这里,法是君主所用的治国之具,是一种以威慑为后盾,以赏罚为动力的外在规范。它和礼有什么区别呢?本来,在西周封建制下,“礼”与“法”,如龚自珍所论断,和“书”一样,都是在官府,也就是在贵族内部掌握的一种原理、原则性的治国方略。到孔子那里,情况有所变化:他纳仁入礼,赋予其内在精神,从而把“礼”和“仪”区别开来。此一时期,随着成文法公布,由于它以刑罚制裁为主要特征,所以在治国方略上,孔子是把“刑”作为“礼”的对立面来立论的。随着法家革新运动渐次兴起,其主要治国之具是“法”,是以外在赏罚为主要内容且平等适用于除王之外的所有人,故“法”在多数情况下成为“刑”的同义词。故“法治”就是为国以法、为国以刑,从而与为国以礼的“礼治”构成一组对立的治道概念。
到荀子那里,已经部分割断了孔、孟关于礼与内在道德自觉之间的联系,将礼的根据外在化,从而凸显了礼的外在规范特征,拉近了与法的距离。尽管如此,但礼与法仍然存在很大的差别。到战国中晚期,这种差别仍然非常明显,主要表现在:(1)从产生来看,礼生于俗,生于习惯;法生于国君。尽管有周公制礼作乐之说,这是否完全可信尚存问题。即便可信,但周公亦非凭空制作,而是在周族长期习惯的基础上择其精要和大纲,将之系统化。即便圣如周公、孔子,既不能随便废弃积习相沿之旧“礼”,亦不能随意创造新“礼”。法则由国君制定,本质上是因权力而生,故君主完全可以推陈出新。(2)从特征上言,礼注重等级性,法讲求平等性。礼所自生的习俗来自于宗法封建社会,宗法封建社会的特征就在于社会的等级性,所以礼必强调等级之间的差别,要求诸等级之人们各守其礼来维护秩序,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就是这种特征的概括性说明。“法”观念之产生虽在春秋时期,但其确立是在战国末叶,[14]P170-171这一阶段正是封建制遭到毁灭性打击的时期,故各等级之间的界限逐渐拉平。为了适应君主集权需要,反对等级特权、强调平等性的法应之而生。(3)从表现形式上看,礼是一种秘密规范,为特权等级的贵族所掌握,只是到用的时候才在内部讨论,所谓“断事以制”;而法是要公布出来为众人所知的明确规范。礼作为秘密规范,随着春秋时期成文法的公布而能取信于民,受到很大冲击。
礼法区别之存在从逻辑上并不足以构成礼、法非要互相取代之态势,但不论是礼还是法,本质上互相之间皆具有较强的排他性。礼在封建制下发挥着“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左传·隐公十一年》)之重大功能,虽能部分容纳法之强制性,但绝不容许法来与之分享此种安邦定国之道;法对礼的排斥就更不待言。二者既明显相区别,且当时又不能调和于其间,那新兴的法取代礼,在逻辑上就可以成立了。
法在战国末期即开始了取代礼承担安邦定国功能这一过程,随秦帝国之建立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完成。其原因固然取决于社会演变之大趋势,但法术之士的推动作用亦是完成此一转变的重要力量。
自战国中期,游士逐渐得势,钱穆先生将他们按照出仕态度之差别分为劳作派、不仕派、禄仕派、义仕派和退隐派,申韩不与焉,而将韩非视为战国晚期裁抑游士的三个代表性人物之一。[17]P107-112此说大致不差,但韩非之裁抑游士,在理论上是以取得国君绝对信任的独“仕”方式来实现的。在政治上绝对排斥各家,在法家是有传统的,如商鞅之在秦,即在得势后下令焚诗书以明法令。(36)
既然要取得君主的绝对信任,那就要取代国君原先的近臣、大臣和重臣。这些臣下都是由各级贵族担任,君臣原不甚相悬隔。既然要取代他们,那就要废除世卿世禄的封建制,要创设新制度让君主来选拔臣僚。这个新制度之精神就是“食有劳而禄有功”,(《说苑·政理》)造成“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之结果。如何保证已废除的封建制度不再死灰复燃,就不能再用保障等级特权的“礼”,而应代之以富有平等色彩、对全国臣民能一视同仁之“法”来治国。
君主亦是人,法术之士一时获得君主的绝对信任并不能保证君主对其的长期信任,那应怎么办呢?法家从两个方面入手:第一、要让君主有自安之道,那就是君主运用法、术两种东西以固势,防止“奸劫弑臣”,保证其绝对权力和权威。(37)第二、让君主安于明主之称。法家虽反对儒家以道德为准据之明主圣王,但却不反对明主圣王本身,而是认那些能定法、守法、善用术之君主为明主圣王。如此一来,法术之士就能在“尊君”的基础上,辅助国君恰当运用法、术,在实现富国强兵的同时亦能为自己建功立业。这就是法家法治之内涵和实质所在。
整个中国社会在先秦时期的治理规范从礼到法转变之完成,是与法术之士的出仕观念紧密相关的:法术之士重“得君”甚于“行道”,亦即是“势”尊于“道”,从而能够获得君主的信任,得以辅佐君主,由君主制定的平等性、公开性的法,取代了生于习俗、具有等级性和秘密性的礼,成为社会主要的治理手段。
法既已取代了礼,成为新的治国之具,法术之士所理想中的道未必能实现,但有了法术之士所提供的帮助,尊君却成为既成事实:中国第一次社会大转型在政治领域最重要的表现是君主专制制度代替了之前的封建制度。之后,具有绝对权威的君主反过来综合利用法术之士所教导并加以正当化的法、术、势,就非常容易对付那些少数持道较坚的法术之士。结果,法家所希望实行的“道”势必落空,其所主张的“法治”遂成为君主“治”臣下和民众之工具,当然倡导“法治”的法术之士也属于被“治”的对象。
结语
自东周以降,礼崩乐坏,产生了士阶层,导致君、师分离。在此种情况下,“尊师重道”和“得君行道”观念因之而生。早期较有影响的士,以儒家孔、孟为代表,认定道尊于势,不能得君,则以明道自任,道即为赋予礼以内在道德上的根据,彰显其仁心,以保持等级社会的开放和活力,故其治道重在为治以“礼”。到战国中晚期,士多君少的现实导致“势”观念勃兴,尊君思想张扬,作为儒家此期代表之荀子则在“道”与“势”之间游移,因要“得君”,故亦须迎合时代思潮而尊君,遂将礼外在规范化,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法的一本同源之物,故在治道上礼、法并重。降及战国末期,尊君之思潮愈烈,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成为思想界的主流,将尊君推到一空前之高度,一方面因得君之切而牺牲了行道之实,另一方面因尊君而尚法,其法治沦为君主“治”臣下和民众的工具。士阶层在“得君行道”观念上的侧重点从“行道”逐渐向“得君”的转移,与相应的治道从“重礼”向“尚法”之演变能大体保持一致。进而言之,传统中国“法治”观念的张扬,是与君主专制的强化同步发生的。这种“法治”,实际上是“治法”,是君主“治”臣民之“法”。(38)“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管子·任法》)一语即道出了此种“法治”的真谛。(39)
及至秦帝国一统天下,君主专制政体完全确立。之所以得以确立,离不开士阶层对君主的大力支持,尤其是法术之士,不仅为尊君提供理论依据,更为君主提供了尊君之办法。其在“得君行道”上完全将“得君”作为首要考虑,不计后果地尊君,乐观地相信中材之君即可行其法治之道,造成以后中国的“士”在整体上依附于君,不能充分保有其独立性的大结局。朱熹窥之甚准:“黄仁卿问:‘自秦始皇变法之后,后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曰:‘秦之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且如三皇称皇,五帝称帝,三王称王,秦则兼皇帝之号。只此一事,后世如何肯变?’”[18]P3218
帝制自秦建立以后,经过汉初的探索,逐步建立了援法入儒,以儒为尊的“外儒内法”之思想大一统体系,帝制得以稳固下来,完成了第一次社会大转型。帝国有了自己的统治思想,不再允许新的民间学说来“惑乱黔首”,胡萝卜和大棒双管齐下,作为思想主体的“士”渐渐也就思不出其位了,不再有以自创一家之言来改革一代政教的气魄和能力,遂转移聪明才智于自娱自乐之途,两汉之后个人诗文集繁兴即是士大夫政法思想萎缩的重要表现之一。其实,景帝时辕固生和黄生之间的论争即暗示了此一结局:
(辕固生)与黄生争论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40)
到班固所撰之《汉书》,尽管抄录了《史记》中的这段记述,但却将其所引起的后果“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一句删除,(41)于此可见儒家之“士”在君权已固、统治思想已具的背景下主动自我约束。(42)随着察举、九品中正和科举等官员选拔制度的建立和逐渐完善,“士”所追求的“得君行道”有了常规渠道,先秦“士”靠以一家之言来游说君王“得君行道”的做法,在整个帝制中国成为绝响。先秦时期和帝制中国不同,治道无常,行道亦无常轨;而在帝制中国,治道已定于一,即外儒内法;行道亦有定制。详言之,治道已定,“士”所做的主要是阐发,而非创造,尽管可以寓创造于阐发之中,但毕竟空间有限;超越限度,即有被归入“伪学”、“异端”之危险。行道之主流就是力争做官,但官僚系统本身的习性足以扼杀任何行道之可能。“士”要越过官僚制度之常轨,争取在庙堂行道之机会,即只能冀望于君。在这样的情形下,对治道起关键作用的不再是“士”,而变成了“君”。到明清,随着君权之极端强化,社会治乱取决于个体君主之贤能与否的趋势越发明显,一批明智之“士”从庙堂转身直接进入基层社会,以家族和乡里为中心,创造出义庄、祠堂、祭田、乡约等制度以“觉民行道”。(43)这种相对撇开君权,注重“觉民行道”之做法,在君权笼罩一切的大环境下,其成效整体来说并不显著,尽管有其深远的思想影响。
自先秦所争鸣的“得君行道”以尊君、重法而告终,形塑了随后整个帝制中国的以外儒内法为核心的治道,以及皇帝握有治道之秉的现实。这无疑只是一种霸道,以士为尊、道尊于势、以民为贵的王道始终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44)历代大儒对此亦只能空自感慨现实是“牵补挂漏”、“圣学日远”。(45)近代前夜,龚自珍即对这种霸道进行了激烈批评,云:“昔者霸天下之氏,称祖之庙,其力强,其志武,其聪明上,其财多,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大都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19]P20“一夫为刚,万夫为柔”就是帝制中国在治道为一的前提下,“得君行道”观念的实践后果,追溯其源,先秦诸子所倡导的“尊君”和“尚法”难辞其咎。先秦诸子之所以倡导“尊君”和“尚法”,实乃其“得君行道”之念过于迫切的必然归宿。“士”之立说与出处,岂能说无关乎治道?可不慎哉!
(全文完)
注释:
(31)参见陈启天:《中国政治哲学概论》,转引自姚蒸民:《韩非子通论》,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9年版,第58页。
(32)此乃韩非托黄帝言以增加其权威性,可视为韩非自说自话,载《韩非子·扬权》。
(33)韩非曰:“夫治天下之柄,齐民萌之度,甚未易处也。然所以废先王之教,而行贱臣之所取者,窃以为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故不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必思以齐民萌之资利者,仁智之行也。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夫身而不见民萌之资利者,贪鄙之为也。臣不忍向贪鄙之为,不敢伤仁智之行。先王(生)有幸臣之意,然有大伤臣之实。”(《韩非子·问田》)
(34)对韩非及法家学说多从正面肯定其现代价值的姚蒸民先生即如此定性,载氏著《韩非子通论》,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9年版,第97页。
(35)李斯在《督责书》中言:“俭节仁义之人立于朝,则荒肆之乐辍矣;谏说论理之臣闻于侧,则流漫之志诎矣;烈士死节之行显于世,则淫康之虞废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独操主术以制听从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势重也。凡贤主者,必将能拂世摩俗,而废其所恶,立其所欲,故生则有尊重之势,死则有贤明之谥也。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史记·李斯列传》)
(36)《韩非子·和氏》。关于商鞅是否真下令焚诗书,历代学者有过怀疑。但诚如王先慎转引王应麟氏之《困学纪闻》所载“《史记·商君传》不言‘燔诗书’,盖诗书之道废,与李斯之焚书无异也”,(王先慎撰:《韩非子直解》,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97页。)商君是否真下令与否并无关紧要,关键在法家是否有强烈排斥百家之传统。
(37)韩非说得特别明白:“主用术,则大臣不得擅断,近习不敢卖重;官行法,则浮萌趋于耕农,而游士危于战陈,则法术者乃群臣士民之所祸也。”(《韩非子·和氏》)
(38)韩非子所主张的明主或圣人“治吏不治民”并不是就字面意思而言只治吏、不治民,而是因为吏乃“民之本纲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从治吏入手,就能纲举目张;反之,从治民入手,则劳而无功。故它只是一个方式方法问题,其最终目的还是要臣民皆受“治”。
(39)作为大儒的韩愈不仅接受并加以强化,且大力宣扬这一观点,云“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参见“原道”,载《韩愈集》,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46页。
(40)《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第六十一”,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册,第3122-3123页。
(41)《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第五十八”,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册,第3612页。
(42)近代学者黄节指出,“申桀纣而屈汤武,孝景知其非,然犹曰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则吾国对君主之界亦亡矣。呜呼!国界亡则无学,无学则何以有国也。”(“‘国粹学报’序”,载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二卷上册,第42-43页。)
(43)“觉民行道”一语是余英时先生对明代士大夫之政治思想取向所发生变动所归纳出来的概念。他认为宋、明两代理学之间的断裂远过于延续。盖明太祖虽深知“治天下”不能不靠士阶层的支持,但绝不承认士为政治主体,更不肯接受儒家理论对君权的约束。所以从王阳明开始即走上了“觉民行道”之路。在余英时先生看来,王阳明最大收获是他找到了“行道”的新路线,即“觉民行道”。故“觉民行道”是十六世纪以来文化、社会大变动的一个有机部分,与“觉民行道”运动同时的还有小说和戏文的流行、民间新宗教的创立、印刷市场的扩大、宗族组织的加强、乡约制度的再兴等等。参见余英时:《史学研究经验谈》,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74、75、185页。
(44)明代理学家吕坤在《呻吟语》中深刻阐释了皇帝所握有的“势”和儒家士大夫所秉持的“理”(也就是“道”)之间的理想关系:“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焉,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故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然则理也者,又势之所恃以为存亡者也。以莫大之权无僭窃之禁,此儒者之所不辞而敢于任斯道之南面也。”(参见:《吕坤全集》(中册),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46页。)实际上,尽管历代帝王并非对“理”(道)毫无顾忌,但在关键时候,以势夺理、强词夺理更是不绝于书。
(45)朱熹在与陈亮争辩王霸之时,沉痛指出,“若以其能建立国家,传世久远,便谓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败论是非,但取其获禽之多而不羞其诡遇之不出于正也。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牵补挂漏,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参见:“答陈同甫”,《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三十六卷,载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1册),安徽教育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2页。)王阳明亦指陈:“既其久也,斗争劫夺,不胜其祸,斯人沦于禽兽、夷狄,而霸术亦有所不能行矣……圣学既远,霸术之传,积渍已深。虽在贤知,皆不免于习染,其所以讲明修饰,以求宣畅光复于世者,仅可以增霸者之藩篱,而圣学之门墙,遂不复可覩。”参见王守仁:《阳明先生集要》(上册),施邦曜辑评,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24页。
[14]姚蒸民.韩非子通论[M].台北: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9.
[15]熊十力.韩非子评论[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16]徐道邻.中国法制史论略[M].台北:台湾正中书局,1953.
[17]钱穆.国史大纲(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18]黎靖德.朱子语类(第八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9]龚自珍全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