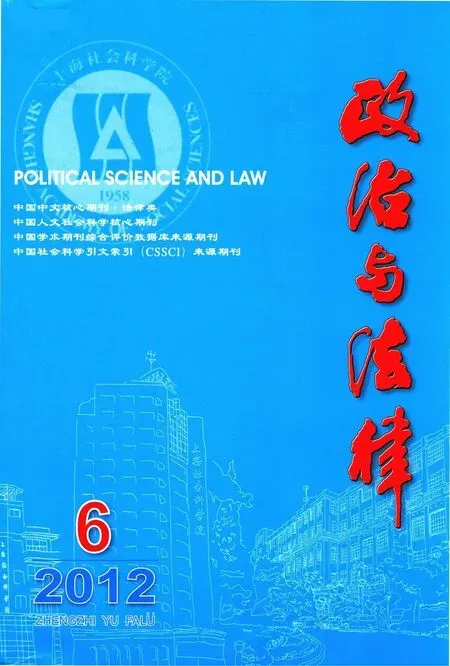当前港澳基本法热点问题研究论香港高等法院对“菲佣居港权”案的判决
——兼论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的法律效力
董立坤 陈 虹
(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广东深圳 518060)
当前港澳基本法热点问题研究论香港高等法院对“菲佣居港权”案的判决
——兼论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的法律效力
董立坤 陈 虹
(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广东深圳 518060)
编者按:近期,香港、澳门在社会生活和政治领域内发生了不少事件,其中有许多涉及基本法实施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引致公众和学界的热议。香港社会对“庄丰源案”和“菲佣案”两起“居港权”案特别关注,本刊特选取两篇对案件进行分析与检讨的文章,希望对香港法院有所启示。在香港政治领域内,关于政府法案修正案的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并数度引起宪制性争议。本刊特邀专家对其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以求这个问题得到完满解决。在澳门,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释法与作出“关于两个产生办法的决定”标志着澳门处理政制发展的工作已经进入“五步曲”中的第三步,这个步骤需要坚实的理论准备,因此我们邀请澳门学者来讨论行政长官产生办法修改的法律边界问题,以确保国家对澳门既定的基本方针政策以及基本法的有关规定得到落实。
香港高等法院原讼庭在“菲佣居港权案”中,以所谓的普通法的解释方法,判决香港《入境条例》有关条款抵触了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4项的规定。香港法院的判决涉及中央与香港关系中的若干重要的法律问题:一是香港法院解释基本法刻意偏离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在有关的“释法”中明示的基本法的解释方法,香港法院片面地强调依所谓字面解释方法解释基本法也偏离了普通法惯用的对宪法性法律采用的目的解释方法;二是香港法院对基本法第24条中有关“通常居住”的理解也是错误的,非中国籍人无法凭藉香港高等法院原讼庭的判决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三是应当正确解读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的法律性质和法律效力,只有根据基本法的规定,才能建立起全国人大常委会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释法方面的良性互动关系。
“菲佣居港权”案;基本法解释方法;居留权;释法效力
一、案件由来及香港高等法院判决
“菲佣居港权”案是香港高等法院受理的一件司法复核案。提起本案的申请人是在港从事家庭佣工的菲律宾人瓦耶荷丝(Evangel ine Banao Val lejos)。瓦1986年来港,25年来一直为同一雇主服务。2008年4月,她向香港入境处申请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但香港入境处根据香港《入境条例》第2条第4款第a(vi)项拒绝其申请。同年12月,瓦向香港人事登记事务处申请再度被拒,遂向香港人事登记审裁处提出上诉。2010年6月审裁处驳回她的上诉请求。2010年12月,瓦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核,香港高等法院接受了她的司法复核申请。1该院于2011年8月下旬开庭审理此案。
自菲佣提出居港权的司法复核后,香港社会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据“估计今次案件政府一旦败诉,10万合资格外佣将带同30万子女涌港,在香港享受房屋、教育福利,冲击社会安定”。2各种报纸评论均指,在这起司法复核案中,“港府输硬”。据2011年8月15日香港《太阳报》报道:“政府已不停向建制派放风,指司法覆核案政府败诉机会高达八成。”3于是香港各界均为香港特区政府可能面临的败诉提出了各种应对意见,其中最主要的主张有:在政府终审败诉后请求人大释法,继前律政司司长、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梁爱诗表态主张人大常委会释法解决菲佣居港权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原香港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亦开腔认同梁爱诗讲法”,“而民建联核心则认为,外佣居港权官司在终审败诉后,释法是无可避免”。4为反对外佣有居港权,“连日来,不少团体举办签名运动,甚至示威行动”。5确如大众所预料,2011年9月30日香港高等法院原讼庭作出判决:“本庭的结论是,基于普通法的解释方法,‘非难条款’(即香港《入境条例》第2条第4款第a(vi)项——笔者注)抵触了第24条第2款第4项。”6若依此判决,香港《入境条例》第2条第4款第a(vi)项规定的“受雇为外来家庭佣工(指来自香港以外地方者)而留在香港”的“不得被视为通常居住于香港”的规定因抵触《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4项而被宣布无效,换言之,外佣在香港工作期间的居住,为可获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的“通常居住”,从而为在港工作的数十万的非中国籍家庭佣工可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打开法律大门。
本案判决后,香港特区政府已依法律程序向香港高等法院上诉庭提起上诉,上诉庭已于2012年2月21日至23日开庭审理,并于3月28日作出判决。上诉庭回避了原讼庭的判决理由,以香港特区政府有权根据基本法的规定行使入境管理权限而判决香港特区政府胜诉。依香港法律程序,此案还可能上诉至香港终审法院。笔者认为,香港高等法院原讼庭判决涉及中央与香港关系中的若干重要法律问题,并将影响到香港终审法院的最终判决,上诉庭的判决回避了有关问题,因此,从理论和法律上深入分析香港高等法院原讼庭判决对于解决以后可能发生的若干类似案件具有重要意义。
二、基本法的解释方法
正如香港高等法院判决书指出的那样,本案的焦点在于:以什么方法解释基本法,是采用香港终审法院在庄丰源案中所确立的解释基本法的方法,还是根据中国法律惯用的根据立法原意解释基本法。这是本案涉及的关键问题。
(一)香港终审法院在庄丰源案中所确立的解释基本法的方法
香港高等法院在2010年124号案的判决中强调,法院是以普通法的方法解释基本法的,即根据香港首席大法官李国能在庄丰源案中所确立的解释基本法的方法。李国能在庄丰源案的判决书中强调:“法院根据普通法解释法律的文本所采用的字句,以确定这些字句所表达的原意,法院的工作并非仅是确定立法者的原意,法院的职责是要确定所用字句的含义,并使这些字句所表达的立法原意得以落实。法例文本才是法律。”7在庄丰源案中确定的解释基本法的方法为以后香港法院所遵循。在谈雅然案和普莱姆·辛格案中,香港法院也以普通法解释方法解释基本法。因此,在香港高等法院2010年124号案的判决中法院尽管也确认,有多种证据证明,香港《入境条例》第2条第4款第a(vi)项的制定是有充分根据的,也符合基本法的立法原意,但是“本庭的结论是:基于普通法的解释方法,非难条款抵触了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4项”。
(二)中国有关解释基本法的方法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宪法和法律就法律解释问题有多项规定。1954年宪法第31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法律;1975年宪法保留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也予以同样规定,并增加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的权力;1979年制定、1983年修订的《法院组织法》第33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55年和1981年先后两次就法律解释问题做出了专门决议,特别是1981年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对中国的法律解释工作作出了全面的规定。根据该决议,中国法律解释体制,从主体上可以分为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行政解释;从形式上可以分为对法律的解释、对行政法规的解释、对地方法规的解释和对规章的解释;从内容上可以分为对法律条文本身的解释和对法律如何应用的解释。8
中国法律应用何种解释方法,似乎法律并没有明文的规定,但理论和实践中,多采用以立法原意的解释方法解释法律。“立法原意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它是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条文时的真实想法”;当“争议双方对法律条文的字句有不同解释时”,“要按照最符合立法原意的意思来解释”。依立法原意解释法律是成文法体系国家传统的解释法律的方法,其起源于1804年法国的《拿破仑法典》第1156条:“在契约中,应探求契约当事人的共同意思,而不应停留于字句的文字意思。”1937年《瑞士债务法典》第18条第1款更是明确规定:“为了判断一个契约的方式和条款,须探求各当事人真正的和共同的意思,而不停留于其可能由于错误或为了掩盖契约的真正性质而使用的不正确的词语或名称。”依立法原意解释法律可保证制定法的稳定和准确地实施法律。9
我国不但是个传统上实行成文法的国家,更重要的是,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立法原意解释法律,可以保证宪法所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所享有的各项权利,保证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在解释和实施过程中真正体现立法原意的人民意志得到贯彻和落实。2000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对“解释法律”作了专章规定。《立法法》第42条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律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一)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二)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由此可见,《立法法》规范了中国的法律解释制度:中国的法律解释权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其目的是要进一步明确其原来制定法律条文的真正含义,中国的法律解释目的在于探求立法者原来立法的真正立法原意,使被解释的法律条文与其相关的法律保持一致,以此保证法律的稳定性,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可见,《立法法》所确定的法律解释体制和解释方法与中国1949年以来所实行的法律解释制度是完全一致的,即与绝大部分成文法系国家法律解释体制和解释方法是一致的。
(三)普通法对宪法性法律采用的目的解释方法与中国法律的“立法原意”解释方法没有本质的区别
应当承认,中国依立法原意的方法解释法律同香港的普通法的解释方法有所不同,但两者也非完全对立。在普通法解释方法中,也常考虑到被解释法律的立法原意。在普通法法律解释制度中,主要的法律解释规则有文义规则(literal rule)、金色规则(golden rule)、补救规则(mischief rule),还有适用于宪法性法律解释的“目的规则”。
文义规则是指如果条文本身十分明确及确定,法官在适用时须按照条文本身的自然或通常的含义解释法律。金色规则是指如果根据法律条文含义解释将会导致荒谬后果或与法律其他部分明显不符,则不应该采纳该含义。因为这样的荒谬后果不符合或不可能是立法者的原意。补救规则是为挽救文义规则和金色规则产生的缺陷而制定的,是指法官在解释成文法时既不能机械地拘泥于法律条文的表面的含义,也不应该为顾及法律解释的后果而轻易的放弃对法律条文含义的理解,而应该首先理解该法律制定前的普通法的规定,再分析制定该成文法时的立法宗旨及其提供的补救措施来解释法律,使其解释真正符合法律制定的宗旨,体现立法者的意思。目的规则主要用于较为原则和弹性的宪法性法律的解释,其规则强调在解释相关法律条文时,不应该拘泥于条文的表面的含义,而应该根据条文制定的目的和宗旨解释条文。目的规则和根据立法原意解释法律的方法基本是一致的。
从以上对普通法有关法律解释方法的介绍中可以看出,各种法律解释规则不是绝对的。无论以何种方法解释,都应当顾及被解释法律制定的目的。也就是说,解释法律不能违背法律制定的意图,如果违背了有关法律制定者的意图,法官有责任以其他方法予以补救,尤其在涉及宪法性法律解释时,应该充分考虑到立法者制定有关法律条文的目的和宗旨。《香港基本法》是香港宪制性法律,香港法院甚至将其称为香港的宪法,而香港法院在解释基本法这样的宪制性法律时应更多考虑的是目的性解释方法,即应认真考虑立法者制定相关法律条文的目的和宗旨,也就是应考虑被解释法律的立法原意。但香港法院却将文义解释和目的解释对立起来,片面强调文义解释,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明确指出的应依立法原意解释基本法的意见视为异端,是难以理解的。其实,根据普通法的法律解释规则,香港法院在涉及基本法的解释时,完全可以协调普通法的目的解释方法与中国法律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已明确的以立法原意解释方法的关系,在顾及基本法的立法目的和立法原意中,对基本法相关条文作出解释。
(四)应依立法原意解释基本法
依什么方法解释《香港基本法》,自基本法制定和实施以来,在理论与实务上都存在争论。有人认为基本法明确规定了“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故应依中国法律解释方法解释之;也有人认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已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本法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和“本法的其他条款”进行解释,作为一个“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的法院,应依普通法的解释方法解释基本法。香港法院正是依据这个思路对菲佣居港权案作出判决的。如果不对这个问题辨别清楚,同样的麻烦和争论还会不断地继续下去。到底是依普通法的方法解释基本法,还是依立法原意的方法解释基本法,其判断标准就是有关解释方法是否符合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规定。根据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规定,应依基本法的立法原意解释基本法的相关条文。
第一,基本法是全国性法律,应依中国法律解释方法解释之,不能由香港法院法官依普通法解释方法“改造”基本法。基本法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中国宪法和“一国两制”原则制定的,是国家法律体系中仅次于宪法地位的国家的基本法律,不仅体现了香港居民的意志,也体现了全国人民的意志;不仅在香港实施,也在全国实施。无论根据宪法还是基本法的规定,基本法的解释权都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既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基本法的解释权,那么毫无疑问,在解释基本法时,也只能根据中国法律解释方法解释基本法的相关条文,以使基本法的解释与基本法的立法原意相一致。如果基本法依香港普通法的解释方法,由香港法院的法官仅考虑“条文的字面意思”即所谓“通常”或“自然”的含义,却拒绝考虑法律条文的真实意思去解释基本法,那么,在这种解释方法下,基本法要通过法官的解释进行一种“转换”,才能成为法律规则加以适用。这样,基本法可能出现普通法下的新的规则,变成“法官”所“改造”后的“基本法”,并按其“遵循先例”的原则,使这种普通法成为特区法律中起决定性和依据性的部分,其结果是体现全体中国人民共同意志的基本法被“转换”和“隔离”了,基本法将可能不成为其原来制定时的法律了。10
第二,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解释基本法的相关条款,明确了基本法的解释方法,香港法院应无条件地依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规定行使基本法的解释权。1999年6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应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请求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和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解释》序言说明了《解释》的起因:“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提请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和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的议案》。国务院的议案是应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四十三条和第四十八条第(二)项的有关规定提交的报告提出的。鉴于议案中提出的问题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1999年1月29日的判决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有关条款的解释……而终审法院的解释又不符合立法原意。”故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宪法和基本法的规定,阐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2条第4款和第24条第2款第3项规定的立法原意。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对基本法的解释,有重要的意义。这次解释明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的基本方法:依立法原意解释基本法;同时,《解释》也指明了香港法院也应当依基本法的立法原意解释基本法,香港终审法院的解释之所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重新解释,是因为它的解释“不符合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如果说,基本法第158条明确规定了基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那么,此后在有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相关条文的解释中,更明确了根据基本法的立法原意解释基本法的方法。
第三,香港终审法院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的声明。1999年2月26日香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宣读终审法院5名法官一致的《澄清判词》:“特区法院的司法管辖权来自《基本法》。《基本法》第158(1)条说明基本法解释权属全国人大常委会。”《澄清判词》进而强调:“我等接受这个解释权是不容质疑的。”“如果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作出解释时,特区法院必须要以此为根据。”也就是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释法中确立的依立法原意解释基本法,特区法院也应当以此方法解释基本法。
三、“非难条款”与基本法相关规定不抵触
(一)关于“菲佣居港权案”争议的焦点
香港《入境条例》第2条为“释义”,对该条例涉及的相关法律概念作出界定。第2条第4款规定:“就本条例而言,任何人在下述期间内不得视为通常居住于香港。”其a项(vi)规定,“在任何期间内”,“受雇为外来家庭佣工(指来自香港以外地方者)而留在香港”,“不得被视为通常居于香港”。
根据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4项规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持有效证件进入香港,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7年以上并以香港为永久居住地的非中国籍的人”可以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香港高等法院在审理菲佣案的过程中,反复论证香港《入境条例》第2条第4款第a(vi)项的有关“通常居住”是否符合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4项中的“通常居住”的“通常”“自然”的含义,如果不符合,香港《入境条例》的规定就抵触了基本法,菲佣即可藉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4项之规定,可以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获得在香港的居留权。笔者认为香港高等法院片面理解了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4项的规定,该案的关键问题不在于基本法和香港《入境条例》中的“通常居住”的含义是否符合普通法中有关“通常居住”的“通常”“自然”的含义,而在于菲佣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是否符合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4项设定的非中国籍人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的条件。香港高等法院应当也是清楚的,判决书中明确表明:“本案要解决的问题是:一位外籍家庭佣工是否可藉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4项之规定获得香港的居留权。”11为此,为了解决该案所要解决的问题,不能从通常居住的字面去理解“通常居住”,而应该从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4项所设定的非中国籍人要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的条件去理解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4项的真正含义,理解其中“通常居住”的真正含义。
(二)香港基本法中“通常居住”的立法原意
需要指出的是,基本法中使用的居住、通常居住、永久性居住地和居留权等法律概念来源于英国法律,是在香港回归过程中为适应香港法律地位的变化而采用的法律制度。香港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4项以及第24条第3款中有关居住、连续通常居住、住所、永久居住地和居留权等概念同普通法国家相关概念是基本一致的。
第一,为因应香港回归,基本法主要以住所和居留权界定香港居民的身份。
“九七”回归前,香港受英国的殖民统治,英国人为加强对香港的控制,主要根据英国的国籍法界定香港居民的身份。“国籍是指一个人,作为一个特定国家的成员而隶属于这个国家的一种法律上的身份”。12“国籍是以依附、生活和情感的真正联系的社会事实以及相互权利和义务为基础的法律纽带”。13为了加强英国与香港居民的这种以依附、生活和情感联系的法律纽带,英国在1841年占领香港时就曾发表公告称:“一切居住在香港的本地居民必须了解他们已是英王的臣民,因此对于女王及女王的官员必须尽责及服从。”之后,英国的国籍法进行了多次修订,但香港的居民依英国的国籍法界定其身份的规定没有改变。
“九七”回归后,对于香港居民而言,再用国籍来界定香港居民的法律身份已不合适。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中首次使用了“香港居民”的这个概念。之后,在1990年基本法中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简称香港居民,包括永久性居民和非永久性居民。”该法还规定,香港永久性居民“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居留权”;“香港特别行政区非永久性居民,有资格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取得香港居民身份证,但没有居留权”。是否有居留权成了区分香港永久性居民和非永久性居民最重要的标准。
应当说,香港居民并不是一个国籍概念。国籍不是决定香港居民身份的唯一条件。无论是中国国籍、英国国籍或其他国家国籍,只要符合香港法律的一定条件,任何自然人都可称“香港居民”。从某种意义上说,香港居民这个概念同住所有某种联系。住所就是一个人的经常居住地,是一个人与主要居住地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在普通法国家,认为“构成住所的概念的根基就是永久的家”。14借用住所这个概念,香港永久性居民就是以香港为经常居住地,由香港法律决定其权利与义务,与香港形成固定法律关系的人。或者说,以香港为永久的家的人就是香港永久性居民。
当然,住所与居留权是密切相关的。一般而言,在一个国家或地区有住所的人,他在这个国家或地区有居留权。享有居留权的人,也会在其居留地有住所。故基本法中把是否在香港享有居留权作为区分香港永久性居民和非永久性居民的唯一标准。
居留权这个概念也是在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中首次使用的法律概念。居留权与居留权利是有联系又有重要区别的两个法律概念。依照基本法以及根据基本法修订的香港《入境条例》的规定,居留权是指在香港享有“入境权;不会被施加任何逗留在香港的条件,而任何向他施加的逗留条件均属无效;不得向他发出递解离境令;不得向他发出遣送离境令”的权利。15只有完整享有以上全部四项权利的人,才能称之为享有居留权的人。因为住所是居住者永久的家,你不能把他一个人从其永久的家的地方递解或遣送到任何其他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说,居留权与住所是不可分离的。
居留权利,是有条件的居留权,经批准,他可以合法进入他所居留的地区,也有合法逗留的权利,但他随时有可能被递解离境或遣送离境。在一定意义上说,居留权利是与居所密切相关的。
第二,通常居住不是取得住所的决定性条件,居住者的意图才是取得住所的最重要的条件。
住所是指一个自然人永久的家,居住者的长住事实和久住意图是获得住所最重要的条件,有久住的意图无长住的事实,或有长住的事实无久住的意图,都难以获得一个新的住所。但是英国法学家在居住事实和久住意图方面,更强调:“作为一个法律问题,没有必要要求居住的时间而言是长久的……居住时间的长短本身并不重要,它只有作为居住意图证据时,才是重要的。”16“一个新住所直到有在某个其他国家建立永久居所的固定的意图,而且直到这个意图已被在那里的实际居所实现时,才会获得。没有意图的居住是不够的,这已通过许多案例显示出来,在这些案例中,居所显然已被建立,而且在这些案例中,结果只是取决于被提名者是否有必要的意图这个问题。”17
当然,强调居住者的意图是取得住所的重要性时,应当注意,长住的事实也是取得住所的重要的条件。认定居住事实时,多以居住者在居住地通常居住的时间为依据。
“通常居住”一词在英国的一系列法规中有所使用,包括1971年英国的移民法案,以及英国1948年和1981年的《国籍法》。“通常居住”也用于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提供的教育或其他社会服务的资格标准。移民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自然人是否具有“通常居住”作为是否可以取得移民资格的决定性因素。
“通常居住”一词与传统的“住所”是有区别的,区别的关键之处在于“通常居住”不要求在一国或一个区域有永久居住的意图,它仅是一个居住的事实。“通常居住”通常与居留权是没有关系的,不能凭“通常居住”而获得有关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而住所必须要有永久居住的意图,获得永久住所的人一般都享有居住地的居留权。
“通常居住”与通常的居所或“出现”居留地也有区别。“通常居住”应是合法的居住。通常非法入境者,违反逗留期限的居住,或以难民身份的居住;被法院判处监禁或被依法羁留;或由居住地政府明令禁止移民的人群而获得的居住都不能视为“通常居住”。
正常合法的“通常居住”,应被视为久住事实的一个证据,大部分国家或地区的法律都规定,经一定时间的连续性的“通常居住”是取得住所的一个必要条件。
第三,1996年全国人大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作出的《关于实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的意见》,阐明了基本法第24条第2款中“通常居住”的立法原意。
根据国际上一般有关自然人取得住所的条件,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4项对非中国籍人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即住所)的条件作出了规定,即“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持有效证件进入香港,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七年以上并以香港为永久性居住地的非中国籍的人”可以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永久性居民,并在香港有居留权。很显然,这是一条关于非中国籍的人取得香港永久性住所的条件。此项的前半部分是指非中国籍人要取得香港的住所,必须持有效证件进入香港,并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七年以上。这是所谓长住的事实。此项的后半部分是指要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即住所)除前半部分长住的事实外,还须“以香港为永久性居住地”,即必须有久住的意图。
为了阐明基本法有关条款中的“通常居住”的法律含义,1996年8月10日全国人大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通过了《关于实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2项和第4项涉及的“通常居住”作出解释和说明。《意见》第2条规定:下列情况不被视为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2项和第4项规定的在香港“通常居住”:(1)非法入境者或非法入境后获入境处处长准许留在香港;(2)在违反逗留期限或其他条件下留在香港;(3)以难民身份留在香港;(4)在香港依法羁留或被法院判处监禁;(5)根据政府的专项政策获准留在香港。《意见》第3条还特别规定: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4项规定的非中国籍人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七年”的计算方法,应为紧接其申请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之前的连续七年。这说明可以作为取得永久性身份的“通常居住”连续七年,必须是合法的,并以进入香港之时开始,就有明确的以香港为永久的家的居住意图。违反以上规定的所谓“通常居住”均非基本法第24条所指的“通常居住”。
为了贯彻《意见》,1997年4月13日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发表谈话全面介绍1997年7月1日后有关香港居民国籍和居留权问题的政策,其中在谈到六类人士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享有香港居留权时,专门谈到何为“通常居住”,并特别指出在“某些情况下”,在香港居住的人不属于“通常居住”,例如非法入境者、被法庭判决在港监禁或拘留的人、外籍劳工或外籍家庭佣工等。
特别重要的是,1999年6月26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解释》特别指出,本解释所阐明的立法原意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4条第2款其他各项的立法原意,已体现在1996年8月1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意见》中。
从乾隆晚期开始,有些地方就出现了“财政亏空”,即地方政府财政入不敷出,不得不负债经营。到了嘉庆年间,这已经成了各地的普遍现象,几乎每省每县,都出现了财政亏空……
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到国家主管港澳工作的最高行政机构,都明确了基本法第24条中所指的“通常居住”的立法原意,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有关条款的解释中以非常明确清晰的语言,指出了基本法第24条中“通常居住”的立法原意。以上国家权威机构的意见,已经以十分明确的语言说明了基本法第24条第2款中有关“通常居住”的立法原意。
(三)香港《入境条例》第2条第4款第a(vi)项的规定不抵触基本法相关条款的规定,也符合普通法国家的一般规则
首先,香港对《入境条例》的修订符合基本法的规定。
基本法第154条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依照法律给持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的中国公民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给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其他合法居留者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其他旅行证件。上述护照和证件,前往各国和各地区有效,并载明持有人有返回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权利。对世界各国或各地区的人入境、逗留和离境,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可实行出入境管制。”为此,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根据基本法第24条第2款和1996年8月10日全国人大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的《意见》,以及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讨论同意给若干类人可以作为专项政策留在香港的意见,对《入境条例》有关条款进行了修订,以使其与基本法的规定相一致。具体地说,香港《入境条例》的内容作了以下修订。
其一,明确了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的条件。任何人作为香港《入境条例》附表1第1条第2(c)段所指的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身份,只可藉以下条件确立:(a)发予他的有效证件和同样发予他并且附加于该旅行证件上的有效居留权的证明书;或(b)发予他的特区护照;或(c)发予他的有效永久性居民身份证。
其二,明确了居留权和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关系。修订前香港《入境条例》早在1987年前已有居留权的规定。永久居留权是指居住者在香港享有不受条件限制的居留权。随着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基本法在香港实施,基本法第24条明确规定,只有在香港取得永久性居民资格的人才可享有香港的居留权。《入境条例》第2A(1)条规定:香港永久性居民享有香港居留权:(a)在香港入境;(b)不会被施加任何逗留在香港的条件,而任何向他施加的逗留条件,均属无效;(c)不得向他发出递解离境令;及(d)不得向他发出遣送离境令。
其三,明确了居留权与居留权利、永久性居民与非永久性居民的关系。根据基本法第24条的规定,居留权是专属于香港永久性居民的权利。那么,对于香港非永久性居民在香港也享有居留的权利,对于“任何人如:(a)在紧接1997年7月1日之前并不根据当时有效的本条例享有香港居留权;(b)并非有效特区护照或有效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的持有人”等非永久性香港居民可享有居留权证明书;获准在香港居留的非永久性香港居民可享有香港入境权及合法的居留权利;但不享有永久居留权的其他两项权利:不得向他发出递解离境令,不得向他发出遣送离境令。也就是说,非永久性居民在香港的居留权利完全根据法律或合约的规定,任何违反法律或合约,或不符合香港实际需要的人,都可能随时被递解或遣送出香港。
其四,界定了居住、通常居住、住所与香港居民身份的关系,把“通常居住”与取得香港的永久居留权(住所)的条件相连接。其真正的目的在于:规定了一个非中国籍人在香港可以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的条件,也就是说,一个非中国籍人可在香港获得永久住所或永久居留权的条件。
香港《入境条例》第2条第4款明确规定:“就本条例而言,任何人在下述期间内不得视为“通常居住”于香港,包括:(i)于非法入境后不论是否得到处长授权而留在香港;或(ii)在违反任何逗留条件的情况下留在香港;或(iii)以难民身份留在香港;或(iv)被羁留在香港;或(v)在政府输入雇员计划下受雇为外来合约工人(指来自香港以外地方者)而留在香港;或(vi)受雇为外来家庭佣工(指来自香港以外地方者)而留在香港;或(vii)以《领事关系条例》(第557章)所指的领馆人员身份留在香港;或(viii)以香港驻军成员身份留在香港;或(ix)以订明的中央人民政府旅行证件持有人身份留在香港;(x)任何期间内,依据法院判处或命令被监禁或羁留。”《入境条例》的规定,与全国人大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的《意见》完全一致。
由此可见,《入境条例》第2条第4款第a项之第(v)至(ix)段人员应是《意见》第2条第5款所指的“根据政府的专项政策获准留在香港”的人员。无疑,香港《入境条例》第2条第4款第a项对有关人员,其中包括第a项第(vi)段受雇为外来佣工的非中国籍人在香港的居住不被视为基本法第24条中所指的“通常居住”,不能依此获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的规定,是同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4项以及1996年8月10日全国人大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的《意见》的规定是一致的,是符合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4项的立法原意的。
其次,家庭佣工在受雇国的工作居留不被视为可获得住所所需要的“通常居住”,符合英国普通法的理论与实践,也符合国际的惯例。
香港高等法院在判决中,对香港工作的外来家庭佣工可根据普通法的有关“通常居住”“自然”“通常”的含义,可在香港取得永久性居留权,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这个观点不符合英国有关住所的理论和实践,也不符合国际法律惯例。无论在英国或是其他国家,外来(籍)的家庭佣工工作居留多不被视为可获得住所所需的“通常居住”。在一般的情况下,佣工都难以在受雇国家或地区取得住所。
其一,根据住所的理论,“人人都应有一个住所”,同时“谁也不能同时为了同样的目的有两个以上的住所”。18“人人都应有一个住所”,是建立在把个人与某个法律联系起来的实际需要基础之上的。当一个人实际上没有家时,就会根据人人应有住所的原则,从与他最有密切关系的地区给予他一个住所。根据“一个人不能同时为了同样的目的有两个以上的住所”的原则,一个人必须在放弃原来住所的条件下,才能获得新的住所。在英国有关住所的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广泛讨论获得住所的条件,并对诸如“犯人;可依法驱逐的人;难民和逃亡者;伤病员;武装部队成员、雇工、外交官”等特殊类的人员在相关国家的居留的事实和意图与获得住所的关系。19在有关理论和事实的讨论中,一个基本的意见是:一个以工作为目的的雇工在被雇佣地的居留是不应被视为可获得住所的“通常居住”的。雇工一般是难以获得雇佣地的国家或地区的住所的。英国有关的权威著作还专门列举了有关的案例予以说明:“××的住所在英格兰,在一个雇佣合同之下,他接受了在新西兰的雇佣,依该合同,他将要在新西兰呆10年,他因而把全家及行李带到新西兰并在那里建了房子,意图10年之后返回英格兰。尽管他的家目前在新西兰,但他继续在英格兰有住所。”20
其二,被雇家庭佣工在被雇工作期间不能获得住所,也是国际法律关系实践中的事实。菲佣遍布世界很多国家,现在还没有一个国家法律明确规定,菲佣可以在其所工作的国家可以获得住所。因为根据住所的理论,菲佣前往有关国家或地区是为了工作,而非移民。同时菲佣到其他国家或地区工作时,他的永久的居住地(他的永久的家)仍然在菲律宾。
综上,香港《入境条例》第2条第4款第a(vi)项,根据基本法规定,将“受雇为外来家庭佣工而留在香港”“不得被视为通常居住于香港”,不能因此获得香港的永久居留权,符合普通法对有关人员获得住所的理论与实践的规定,也符合国际法律的一般惯例。
再次,香港高等法院对“沙阿”案的理解是错误的。
“菲佣居港权”案原讼庭法官不断地强调在香港的若干起案件中都采用了沙阿诉伦敦巴尼特自治市(Reg v Barnet London Borough Council,Ex p Shah)(下称沙阿案)一案给出的解释“通常居住”一词的方法,即按其自然、通常的含义来解释,并认为鉴于沙阿案方法在香港相似背景下的用法已经确立,本案也应适用该方法。但笔者认为,香港高等法院对沙阿案理解是错误的,沙阿案说明的是要根据居住者的意图确立“通常居住”的“自然”“通常”的含义。
沙阿案是涉及以“通常居住在英国”来确定必修学生获得当地政府奖学金资格标准的案件,该案是五起同类案件经由不同的区域法庭判决后上诉到上议院的。案件中的五个学生都是移民身份,依据1971年的移民法第3(1)条的许可进入英国,都没有获得英国的居留权,其中四名学生具有限制逗留身份,而沙阿(Ni lish Shah)与父母一起以定居的目的居住在英国并获得了无限制逗留身份。该案中,斯卡曼勋爵认为下级法院以移民法语境中的通常居住的判断标准来解释教育法背景下的通常居住的含义,以入境身份上的限制,即强调在英国定居取得无限制逗留身份才是“通常居住在英国”,来判决沙阿有资格获得政府奖学金,而其余四名学生没有资格获得政府奖学金,这是不正确的。斯卡曼勋爵认为应以上议院两个税金案作指引,应以通常居住的自然、通常的含义来理解,居住的目的可以是学习、工作、经商等等,并提出入境身份仅仅是护照上载明的许可入境的条款,可以构成也可以不构成自然人在这个国家建立居所的意图的指引。以上这些观点在本案原讼庭法官的判决中都有提及。21原讼庭法官就是基于此而认为菲佣的入境身份、居留意图不构成通常居住的限制,并判决菲佣符合申请香港永久性居民条件。但是,该法官完全断章取义,没有细细研究斯卡曼勋爵提出这些观点的来龙去脉,没有遵循英国普通法、国际私法传统下通常居住的判断标准。
斯卡曼勋爵认为案件的关键是在教育法的目的背景下解释“通常居住在英国”的含义。22斯卡曼勋爵首先分析了教育法有关以“通常居住在英国”来确定必修学生获得当地政府奖学金资格标准的条款的历史发展。1944年的教育法案开始规定地方政府有义务给予必修学生奖学金,法案中没有出现“通常居住”这一概念,对学生没有国籍、种族、性别等限制;1962年教育法案中引入了“通常居住”这一术语,也没有给予任何的限制性条件23,尽管同期制定的1962年移民法案已经有来自联邦成员国的移民的区分,但没有使用“通常居住”的措辞,因此,斯卡曼勋爵认为教育法案中针对授予奖学金这一目的,制定法没有赋予“通常居住”特殊含义,同时,议会也不可能没有注意到移民的区别,英国议会也没有以移民法案来施加限制的意图。由于下级法院把1971年移民法案24的“通常居住”的含义适用于沙阿案,斯卡曼勋爵认为需要在此背景下进行分析。
这一问题又可以分成两个层面:第一,在申请人获得奖学金的权利的背景下,“通常居住在英国”的自然、通常的含义是什么;第二,与本法相关的法律的制定背景或当下的运行环境,特别是1971年移民法案,是否强加给“通常居住在英国”特殊的含义。
针对第一层面的问题,斯卡曼勋爵回顾了“通常居住”一词的发展历程,这个术语不是英国普通法中的术语,而是起源于十九世纪,议会频繁在制定法中使用的术语,是1806年税法法案的一个显著特征,随后在家事法、婚姻法、移民法中广泛使用。斯卡曼勋爵认为,“通常居住在英国”的自然、通常的含义体现在上议院的两个税金案中25,在税务专员诉莱萨特(Inland Revenue Commission v.Lysaght)案中,大法官萨姆纳子爵(Viscount Sumner)提出了“通常的反义就是异常,通常居住构成个人有序生活的一部分,是以定居为目的自愿采取的”论断;在莱文诉税务专员(Levene v.Inland Revenue Commission)案中,大法官卡弗子爵(Viscount Cave L.C)提出“通常居住应有某种程度的持续性,有别于偶然或临时出现在某地,在税法法案的目的下,通常居住没有任何特殊的含义,是一个人在某地有序地生活”。根据两个税金案的指引,斯卡曼勋爵认为通常居住一词的限定词“通常”(habitual ly)是非常重要,因为在那两个税金案中法官认为ordinary与habitual是同义的,所以,通常居住至少包括两个必要条件,即自愿采取和定居意图,同时提出了著名的关于通常居住的概念。
针对第二层面的问题,斯卡曼勋爵认为不能用后制定的1971年移民条例解释1962年的教育法案,就申请政府奖学金的目的而言,入境身份仅仅是在护照上载明的许可入境的条件,只是载明在这些限制性条件下学生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的指引,这里也没有规定学生不能取得政府奖学金,但是如果学生违反了这些身份限制条款,就不属于通常居住在英国26,为此,斯卡曼勋爵批评了下级法院法官在解释教育法时强调入境身份的做法,下级法官认为“我们要放弃传统的解释方法,应在1971年移民法案的入境身份背景下解释通常居住”;斯卡曼勋爵还强调,如果允许以1971年移民法案来作为解释1962年教育法案的辅助资料,教育法案采用通常居住要比移民法中居留权采用的限制要少,甚至比定居的限制还要少。通过以上层层推理,斯卡曼勋爵最终推翻了下级法院以移民法中的“通常居住”的含义解释教育法中的“通常居住”的错误判决,判决该案中的五名学生都有资格获得政府奖学金。
沙阿案给法庭的正确指引是在制定法没有明确指引、加以限制的情况下,在制定法的目的背景下,结合上下文,以其自然、通常的含义解释通常居住。因此,当英国的税法、教育法条款的上下文都没有对通常居住作出限定的情况下,在税法的目的及在教育法的目的下都不能以移民法中移民身份对通常居住的限制(如定居的意图、时间等)来决定通常居住的含义。反观“菲佣居留权”案,该案需要解释的恰恰是申请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条款,属于移民条款,遵照沙阿案的指引,在移民法的背景下,在基本法24条第2款第4项明确规定“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7年以上并以香港为永久居住地”的上下文中,通常居住恰恰加上了“以香港为永久居住地”这样一个限制性条件,因此,在该条中,通常居住赋予了不同的含义,移民身份的限制(即签证上的限制)构成对通常居住的限制,这一点也可以从沙阿案的下级法院的判决中得到印证。依据英国普通法、国际私法的传统,菲佣在港居住不属于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4项背景下的通常居住。
(四)菲佣不能藉该案的判决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
该案司法复核的申请人菲佣瓦耶荷丝“寻求推翻审裁处和人事登记处处长的决定”。她对第2条第4款第a(vi)项合宪性提出质疑,要求法院裁决《入境条例》这一条款违反基本法,因而是无效的。香港高等法院也已作出裁决:“本庭的结论是基于普通法解释方法,‘非难条款’抵触了第24条第2款第4项。”也就是说,菲佣在港工作期间的居留权可视为“通常居住”,但“本案要解决的问题是:一位外籍家庭佣工(以下简称‘外佣’)是否可以藉此条款获得香港居留权。”那么,根据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4项的规定,一个非中国籍的人要获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重要的是要有以香港为永久居住地的意图,“通常居住”并非是获得香港永久居留权的关键性的条件。根据基本法第24条的规定修订的香港《居籍条例》对各类人员获得香港的居籍(即住所)作了完整的规定,其中第二部“断定居籍”部分规定:“每名个人均有居籍;任何个人不得在同一时间为同一目的而多于一个居籍。”“任何个人于成年人时”要取得新的居籍,必须证明合法地“身处某国家或某地区,并且意图无限期的以某国家或地区为家”。可见,居住者意图仍然是决定取得香港住所最重要的因素,申请人并不能藉香港高等法院以香港《入境条例》中的“非难条款”抵触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4项中的“通常居住”的判决而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
四、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的效力
(一)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的效力关系到该案的判决
在菲佣案争议中,人大常委会的释法效力问题始终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在199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中,已非常明确地指出,应依立法原意解释基本法,并说明“本解释所阐明的立法原意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4条第2款其他各项的立法原意,已体现在1996年8月1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的意见》中”。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在庄丰源案中既不认同全国人大常委会确立的依立法原意解释基本法的方法,也不承认全国人大常委会在释法中已明确基本法第24条第2款各项立法原意的指引,并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意见视同普通法判决中的“附随意见”,拒绝承认其效力。199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的效力,没有得到全面的承认和执行,导致了今天菲佣案和香港高等法院的判决,可见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释法效力对菲佣案及以后可能发生的相关案件是个重要的问题。
(二)人大常委会的释法并非司法行为
香港终审法院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视为一份类似于香港法院的司法判决书,将其分为具有法律效力的部分(类似于判决书中“判决理由”)和不具有法律效力的部分(相当于判决书中的“附随意见”)。为此有人主张,人大释法是司法行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只能就香港法院在具体案件中提出的有关基本法的问题进行解释。笔者认为,根据中国宪法和基本法,人大常委会释法非司法行为,而是一项阐明立法原意的行为。
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国家的立法权,全国人大常委会还行使解释宪法和法律,监督宪法和法律的实施的权力,其与司法机关的性质有根本的区别,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释法行为视为司法行为,显然是不妥的。
第二,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并非限于法院的提请。司法行为包括司法中的法律解释行为,都发生于具体案件的诉讼过程中。虽然基本法第158条规定,香港终审法院在审理案件中,需要对基本法有关条款进行解释时,在对案件作出不可上诉的终局判决前,可由香港终审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有关条款进行解释。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不限于香港终审法院的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是全方位的,可被动解释,也可主动解释,可由香港终审法院提请解释,也可由国务院、特区政府等机构提请解释,还可以由人大常委会主动进行解释。把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行为定性为司法行为,是不够全面的。
第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释法是阐明立法原意的行为。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可否视为立法行为呢?笔者以为,这也是不够妥当的。“法律解释是立法的延伸,而不是立法本身,立法是创设新的行为规范的活动,而不是对现行规范的含义进行解释的活动。”27故我国《立法法》第42条非常明确地规定,法律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其一,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其具体含义的;其二,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由此可见,人大常委会释法就是阐明被解释的法律有关条款立法原意的行为。
(三)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应与基本法有同等效力
我国宪法第6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宪法、监督宪法和法律的实施。根据我国《立法法》第47条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根据基本法第158条规定,“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作出解释,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引用条款时,应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解释为准”。由此可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与被解释的法律和法律条款具有同等效力,应得到各方面包括香港法院的严格遵守。
(四)香港法院无权限制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释法效力,全国人大常委会与香港终审法院应根据基本法第158条的规定建立互动关系
香港终审法院在庄丰源案中将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分为有法律效力的部分和没有法律效力的部分,从而限制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释法效力。香港终审法院通过其判例限制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释法效力,显然是错误的。但是有人认为,对人大释法而言,它可以选择精确的“规范式”的语言来反向限定判决意见规则的适用空间,从而建立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和香港法院释法的互动空间。对此,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两方面建立全国人大常委会与香港终审法院的互动关系。
首先,建立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香港法院的释法互动关系应明确全国人大常委会与香港法院的法律地位。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是我国宪法赋予的权力,是由主权而产生的权力。香港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对某些特定的案件被授予释法权,是授权性的释法,不具有任何主权的特征。基本法第158条明确规定,香港法院的释法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解释,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引用该条款时,应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为准。基本法没有规定香港法院可监督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释法行为。由此可见,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与香港法院释法并非同一性质的释法,香港法院的释法应始终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
其次,应根据基本法的规定建立全国人大常委会与香港法院在释法中的良性互动关系。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需对基本法有关条款进行解释时,可依基本法规定的程序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当然,香港法院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基本法的相关释法有疑问时,亦可依法定程序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新的解释,或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进一步明确含义。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法院任何的释法请求,或明确其基本法解释含义的请求,应依法定程序快速准确作出答复,以共同维护基本法的权威。这里笔者要明确指出的是,若照某些人士主张的那样,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香港法院可寻找释法中漏洞,在判决中为其创设新的权力,然后中央再作新的释法,以限制香港法院的权力,这绝非是良性互动,而是地方向中央争权,是地方司法权挑战国家的主权。如果建立这样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与香港法院的互动关系,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有何权威、基本法还有何权威可言?如此,人大常委会释法更无权威可言。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相关条款的解释,香港法院应承认其效力,严格依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释法规定行使其司法权。
注:
1香港高等法院宪法及行政诉讼2010年第124号案。
2参见《拥居权菲人:不会死在香港》,《明报加西版(温哥华)》2011年8月14日,“港闻”版。
3《太阳报》2011年8月15日,A06版“港闻”。
4参见《评外佣居港权案范太认同释法解决》,《星岛日报》2011年8月15日,A16版“政治”。
5参见香港《文汇报》2011年8月15日,A13版“香港新闻”。
6See Evangel ine Banao Val lejos v.Commissioner of Regist ration and Registration of Persons Tribunal,HCAL 124/2010,para.177.
7参见“入境处处长诉庄丰源”案(FACV No.26 of 2000)中译本判案书,第87段。
8参见董立坤:《中国内地与香港地区的法律冲突与协调》,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79-80页。
9、27参见陈斯喜:《依法释法和决定保证基本法正确实施》,《中国法律》2007年6月号。
10参见蒋朝阳:《从香港法院的判决看基本法的解释》,《港澳研究》2007年夏季号。
11See Evangeline Banao Val lejos v.Commissioner of Regist ration and Regist ration of Persons Tribunal,HCAL 124/2010,para.1.
12参见李浩培:《国籍问题的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5页。
13参见[英]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一卷(第2分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291-293页。
14、16、17、18、19、20参见[英]J.H.C.莫里斯主编:《戴西和莫里斯论冲突法》,李双元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4页,第156页,第158页,第148页,第165-169页,第147页。
15参见香港《入境条例》第2A第1A部第一款。
21See Evangeline Banao Val lejos v.Commissioner of Regist ration and Regist ration of Persons Tribunal,HCAL 124/2010,para.148-154(原讼庭法官还提到了斯卡曼勋爵对“真实的家”,“通常居住与住所”的区别等观点).
22See Reg v Barnet London Borough Council,Ex p Shah[1983]2 AC 309,at 336-351(所有观点均来自斯卡曼勋爵的判词,笔者从中进行了提炼).
23该法案的相关条款原文为(转引自沙阿案):“(1)It shal l be the duty of every local education authority,subject to and in accordance with regulation made under this Act,to bestow awards on persons who-(a)are ordinari ly resident in the area of the authority,……(2)This section shal l apply to such ful l-time courses at universities……”
24该法案首次把“通常居住”引入移民法案中。
25这两个案件是解释“通常居住”一词的标志性案件,在众多案件中引用,菲佣案中也有所引用,见Evangel ine Banao Val lejos v.Commissioner of Regist ration and Regist ration of Persons Tribunal,HCAL 124/2010,para.104。
26香港高等法院原讼庭法官只引用沙阿案348 D-E部分,没有引用349 D-E部分,断章取义认为只要是合法进入,其他限制都可不考虑,事实上,移民需遵守移民身份上的条款,即菲佣需要遵守在其入境时限制其申请居留权的规定。
(责任编辑:姚 魏)
DF29
A
1005-9512(2012)06-0002-15
董立坤,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陈虹,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科研秘书。
——基于国有企业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