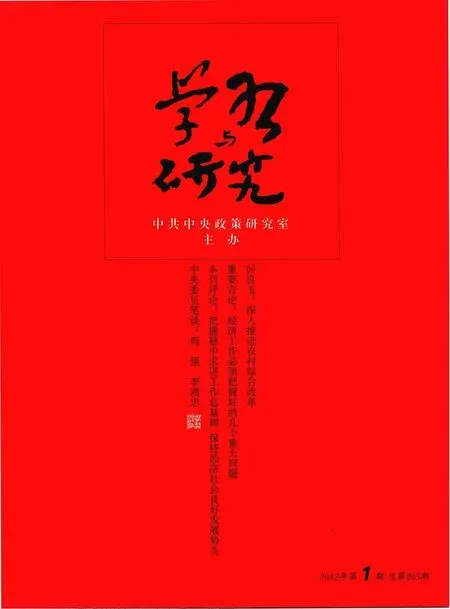论李二曲对宋明理学的总结
林乐昌
(陕西师范大学 政治经济学院哲学系,陕西 西安 710062)
明清之际,李二曲(1627-1705,姓李名顒,字中孚,学者称二曲先生)掘起于关中,与北方的孙夏峰(奇逢)、南方的黄梨洲(宗羲),“时论以为三大儒”。[1]当时诸大儒或着重从政治制度角度(黄梨洲),或着重从历史经验角度(王船山),或着重从理学得失角度(李二曲),分别对鼎革之变的惨痛教训做了深刻的总结。二曲总结宋明理学各派学说得失所涉甚广,本文仅选择其中三个方面略加探讨:一是依据宋明理学史上各派本体观念的实质性意涵,着重以“虚明寂定”四字加以全面概括;二是以“明体适用”为基准,特意提出兼顾体用知识的“知体”概念,弥补了程朱、陆王两大学派的缺失,是对两派学说的改铸和归并;三是重视经世思想的学理根基,从“明体适用”的高度重新思考传统的经世问题,提出以“明学术”、“醒人心”为中心的新的经世观念。
一、“虚明寂定”:对理学各派本体观念的总结
李二曲创建的“明体适用”学说正是以宋代理学的体用论为框架基础的。[2]二曲对宋明理学体用论的总结,集中见于他与顾亭林就“体用”加以论辩的三通书札。①二曲在致亭林书中提出:“如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则‘体’为真体,‘用’为实用。”“苟内不足以明道存心,外不足以经世宰物,则‘体’为虚体,‘用’为无用。”②在明清之际的哲人中,二曲最重本体论,他对形上本体的切己体验和精深论述均超乎同代学者之上。由于被时代剧变所引发的迫切现实问题所掩盖,二曲本体论的重要哲理意义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康熙七年,四十二岁的二曲对门徒口授《学髓》,以“虚明寂定”四字对“本体”观念做了独特的界定,提出:“虚若太空,明若秋月,寂若夜半,定若山岳。”[3]二曲这里的表述实质是熔虚、明、寂、定于一炉,用以形容本体的特征。这可以视作二曲对宋明理学本体观念的理论总结。此外,二曲在《四书反身录》中以“虚明定静”四字对本体观念做了类似的界定。[4]
第一,“虚”。作为对本体特征的概括,二曲所谓“虚”当直接源自北宋关学宗师张载(横渠)的“太虚”概念。张载提出:“由太虚,有天之名。”“太虚无形,气之本体。”[5]张载以道释儒,借道家的“太虚”概念提升儒家之“天”观的超越性意涵,视太虚(天)为气之本体。他所谓“太虚”,也省称“虚”。同时,张载强调“虚心”、“无心”、“大心”,提倡“变化气质与虚心相表里”,主张求心之要“只是欲平旷,熟后无心如天,简易不已。”[6]他还提出,“格物,外物也。外其物,则心无蔽。”“格去物,则心始虚明,见物可尽。”[7]这就把“太虚”本体与“虚心”功夫统一起来了。在宋明理学各个学派中,张载关学与阳明心学之间的联系历来被学界所轻忽。这两个学派之间的思想观念联系集中表现在,阳明晚年对张载“太虚”观念多有引述,以说明“太虚”与“良知”之间具有同一性,乃至认为“本体只是太虚”,“太虚”是宇宙的终极根源。这种理解深度,为理学其他各派学者所未达。嘉靖六年丁亥(1527),五十六岁的阳明自越入广之前,在答复门下两大弟子钱德洪和王畿关于良知本体有无之辨时说:
有只是你自有,良知本体原来无有,本体只是太虚。太虚之中,日月星辰,风雨露雷,阴霾饐气,何物不有?而又何一物得为太虚之障?人心本体亦复如是。太虚无形,一过而化,亦何费纤毫气力?德洪功夫须要如此,便是合得本体功夫。[8]
阳明论本体历来只言及良知,然而这次却强调“良知本体”或“人心本体”“原来无有”,必如太虚那样,对于万物无所不容,而又不为任何一物所障。其中,“太虚无形”原本就是张载《正蒙·太和篇》的用语。表面看来,阳明只是以“太虚”作为良知本体的比喻;但更深层地看,阳明是主张作为宇宙本体的太虚比作为“人心本体”的良知更具根源性。
此前一年,阳明致书关中籍弟子南元善曰:
夫惟有道之士,真有以见其良知之昭明灵觉,圆融洞澈,廓然与太虚而同体。太虚之中,何物不有?而无一物能为太虚之障碍。……故凡慕富贵,忧贫贱,欣戚得丧,爱憎取舍之类,皆足以蔽吾聪明睿知之体,而窒吾渊泉时出之用。……故凡有道之士,其于慕富贵,忧贫贱,欣戚得丧而取舍爱憎也,若洗目中之尘而拔耳中之楔。其于富贵、贫贱、得丧、爱憎之相,值若飘风浮霭之往来变化于太虚,而太虚之体,固常廓然其无碍也。
这里所说,除太虚对万物的包容性以及任何一物都不足以构成本体的障碍与前引阳明所说一样外,还强调了良知“廓然与太虚而同体”的观点。这表明,在阳明看来,太虚作为客观的并具有超越性的宇宙本体与主体的良知本体之间至少是具有同一性(“同体”)的。阳明晚年两次论及良知与太虚“同体”,甚至认为良知本体只是太虚,这或可视作阳明本体思想的新变。
二曲对于关中理学前辈张载的天人之学和事天之学都有真切的理解,他说:“事天之实,在念念存天理,言言循天理,事事合天理。小心翼翼,时顾天命,此方是真能事天。”[9]另外,二曲认为“心如太虚”[10],这表明他与阳明一样也赞成太虚与良知是“同体”的。
这里有必要指出,在阳明、二曲之后,真能深刻理解张载太虚与阳明良知之间关系者,似乎是日本儒者大盐平八郎(1794-1837,号中斋,又号洗心洞主人)。大盐平八郎信守“太虚”之说,显然受到了张载《正蒙》的影响。
或曰:“子动以心归乎太虚为言,自张子《正蒙》来否?”曰:“吾太虚之说,自致良知来,而不自《正蒙》来矣,然不能逃于《正蒙》。”[11]
对于太虚与良知的关系,大盐平八郎的认识相当深刻,他指出:
熟读玩味,数日卒业,乃掩卷叹曰:以孝贯万善,以良知贯孝,以太虚统良知,而天地圣人易简之道,于是偶获之焉。[12]
从“万善”、“孝”到“良知”,再到“太虚”,这四个词组或概念愈往后则愈具有根源性和统贯性。大盐平八郎还提出:“良知即是至善也。其良知之本,即天之太虚,无极之真耳。”[13]大盐平八郎以太虚为良知之本,以太虚统贯良知,比阳明论太虚与良知之间的关系显得更为明确和深刻。
第二,“明”。阳明喜用“昭明灵觉”说明良知本体,他还以赠弟子的诗句“悟后六经无一字,静馀孤月湛虚明”[14]形容良知本体。与阳明一致,二曲也喜以明镜、明月喻本体,他说:
胸次悠然,一味养虚,以心观心,务使一念不生。久之,自“虚室生白”,天趣流盎。彻首彻尾,涣然莹然。性如朗月,心若澄水,身体轻松,浑是虚灵。秦镜朗月,不足以喻其明;江汉秋阳,不足以拟其皜。[15]
明镜和明月都是光明的象征,故二曲常以其喻本体。二曲的另一个重要的明镜之喻是:“静默返照,要在性灵澄彻。性灵果彻,寐犹不寐,昼夜昭萤,如大圆镜。”[16]除用比喻之外,二曲也常常直接用“明”或“灵明”界说本体。有学生问“本体”,二曲答曰:本体“即个人心中知是知非,一念之灵明是也。此之谓天下之大本。”[17]二曲强调,光明本体的呈现必须依赖于修养功夫。一次,有人问“心体本然”的“养之之功奈何”?二曲回答道:“终日乾乾,收摄保任,屏缘熄虑,一切放下,令此心湛然若止水,朗然如明镜,则几矣。”[18]在二曲看来,《中庸》的“慎独”功夫也是使灵明本体呈现的有效途径。他指出,学者对于“慎独”,“不要引训诂,须反己实实体认。凡有对便非独,独则无对,即各人一念之灵明是也。”[19]二曲的意图是要求学者通过长期的功夫修为,最终达致“明无不烛”[20]的光明境界。
第三,“寂”。“寂”字义同于“静”,二曲后来在《四书反身录》中以四字总结本体使用的便是“静”字。北宋理学家受《易传》影响很大,喜以《易传·系辞》之“寂然不动”说本体。周敦颐说:“寂然不动者,诚也。”朱子解此句作:“本然而未发者,实理之体。”[21]周敦颐又说:“静无而动有,至正而明达也。”朱子解此句作:“以其未形,而谓之无耳。”“静无,则至正而已;动有,然后明与达者可见也。”[22]几乎与周敦颐同时,张载对“寂”或“静”的本体意涵和动静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阐论得更加深刻,他认为,太虚本体“至静无感,性之渊源”,但太虚又是“无所不感”的。[23]张载还指出:“静者善之本,虚者静之本。静犹对动,虚则至一。”[24]二曲主张“静极明生”,他指出:“吾人之学,不静极则不能超悟。”[25]虽然二曲与周敦颐、张载所论视角有所不同,但思想实质却相当一致。
第四,“定”。嘉祐四年(1059),程明道撰《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回答张载所问“定性”问题,故也被简称为《定性书》。明道解释说:“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事则定,定则明,明则尚何应物之为累哉?”[26]对此,二曲也曾略有论及,说:“张子患定性未能不动,就程子质问,程子告以定性之旨,‘廓然大公,物来顺应’是也。”[27]可以看出,明道和二曲所论及的“定性”都是就功夫而言的,并非是就本体而言的。由于与“虚”、“明”、“寂”这前三个字相比,二曲对“定”的论述比较少,故我们只好推断,“定”在本体意义上应当与上述“寂”或“静”的语义大体一致。
总之,“虚明寂定”四字既是二曲对宋明理学本体观念的总结,也能够体现二曲哲学本体论的重要特征。其一,“太虚”本体内、外之间的统一。如前所述,二曲是认同阳明太虚与良知“同体”的观点的,主张“心如太虚”。但总体看来,二曲似乎更强调本体的内在性,“心如太虚”主要是以“太虚”比喻内在的心性本体。其二,“虚明寂定”四字之间的统一,其中尤以“虚”与“明”、“明”与“静”之间的统一更加凸显。二曲不但同时用“虛明”界说本体,而且还将“常虚常明”作为实现本体的功夫途径。[28]其三,“虚明寂定”蕴涵了本体与功夫之间的统一。除以上提及的“虛明”本体与“常虚常明”功夫的统一之外,二曲还曾论及本体之“明”与“明性”工夫的统一。其四,“虚明寂定”四字在静、动关系之间的统一。二曲说:“水澂则珠自现,心澂则性自朗。故必以静坐为基,三炷为程,斋戒为功夫,虚明寂定为本面。静而虚明寂定,是谓‘未发之中’;动而虚明寂定,是谓‘中节之和’。时时返观,时时体验。一时如此,便是一时的圣人;一日如此,便是一日的圣人;一月如此,便是一月的圣人;终其身常常如此,缉熙不断,则全是圣人,与天为一矣。”[29]可以认为,二曲用“虚明寂定”四字把哲学本体、修养功夫与精神境界完全统一起来了。
二、“明体适用”:对程朱、陆王两派思想的总结
顺治十六年己亥(1659),二曲提出了“以‘明体适用’为经世实义”的学说。[30]此后,二曲对这一学说不断加以完善,并坚持了一生。对于二曲的“明体适用”学说,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观察视角:一是对儒家经世致用观念的发展进行全面总结的视角,二是以“明体适用”为标准对程朱、陆王两大学派的理学思想进行全面总结的视角。本节采用第二个视角。程朱、陆王是宋明理学诸多学派中影响最大的两个派别,这使二曲的总结具有了相当重要的学术史价值。对于二曲与程朱、陆王两派学术关系的问题,前人早有评断,清儒徐世昌和唐鉴都持“调和”、“兼取”说,只不过二者对二曲学在“调和”、“兼取”中以哪派为主的认识有所不同:前者认为二曲“论学虽兼取程朱,实以陆王为主体”[31],而后者则认为二曲学“确宗程朱家法”。[32]时贤对此问题的探讨和争辩,其实并未超出清儒(徐、唐等)眼界,思考方式也仍未脱离二曲对程朱或陆王加以取舍时究竟偏重于哪派的框限。本文的着眼点是,二曲所建构的“明体适用”之学,分别对程朱、陆王两大学派的缺失皆有所弥补,是对两派学说的批评和重铸,或者也可以说二曲之学的骨架是对程朱、陆王两派学说的“合并归一”。[33]因此,二曲学有其既不同于程朱学派,也不同于陆王学派的哲理特质和独立价值。
(一)二曲对程朱学派理论得失的总结。这里的论析,主要以朱熹为代表。由于总结将以“明体适用”为标准,故也需要从朱子学说中概括出一个在形式上类似的理论框架,这就是朱熹所谓“全体大用”。朱熹在为《大学》“格物”补《传》时说:
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34]
朱熹这里的“全体大用”说,主张以格物穷理为起点,通过经验知识的长期积累,最后“豁然贯通”,达到对本体(“天理”)的领悟。这是一条从知识论达到本体论的为学进路。
程朱学派的“性即理”,尤其是朱熹明确划分知识主体与知识对象,就已知之理求未知之理,将形上学和形下学都纳入知识范围,非但穷究吾心之本体,而且更要穷究宇宙万物之本体。由此,朱熹次第及于人理、事理和物理,以建构其“全体大用”之学的思想系统,这是朱熹在认识论上的一个重大贡献。然而,朱子学也有其缺失。朱熹主张“格物穷理”,认为必须在万物之自性中去认识天理,而且又要穷尽天下万物之理。从道德修养的要求看,其实这是一条很难走得通的路径,这是朱熹学说的缺失之一。朱子所建构的“大用”之学,其范围过于宽泛,漫无限制,以二曲“适用”的观点视之,未免有不切合实际之处,有的甚至窒碍难行,这就直接影响了经世事业的落实和实现,这是缺失之二。
(二)二曲对陆王学派理论得失的总结。这里的论析,主要以阳明为代表。由于总结将以“明体适用”为标准,故也需要从阳明学说中概括出一个在形式上类似的理论框架,这就是阳明所谓“立体”、“达用”。阳明晚年回答弟子“然则何以在‘亲民’乎”的提问时指出:“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而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35]陆王学派的贡献则在于,注重从个人践履的过程中去观照和体验“灵昭不昧”的本体,他们在这方面提出了许多深刻、透辟的见解,尤其是阳明把孔子的“仁”观发挥到“万物一体”的极致。此外,陆王都重视事功,二人在事功方面都有昭彰的业绩。在此基础上,陆王学派形成了一套体用兼备的哲学。但是,陆王学派在认识上过分强调“心即理”,以致将知识主体与知识对象相混淆,偏重道德价值,而对于实用知识的地位和作用未能给予充分的肯定,从而未能对实用知识进行专门的研究,阳明之学尤其如此。这是陆王学派的重大缺失。
为了弥补程朱、陆王两大学派的理论缺失,二曲特创“知体”一名,提出“知体”论。二曲对“知体”的界定,有两方面重要意涵。第一,“知体”之“知”是“灵原”之“知”。二曲在《学髓》中提出“灵原”这一重要概念,认为“灵原”亦即灵妙的根源性知识,它是对对象性知识的超越。[36]这是“知体”之“知”的首要涵义。第二,“知体”之“知”是体用之“全知”。二曲指出:“知体本全,不全不足以为知。”[37]可见,二曲所谓“知体”,不仅是就本体论而言的,而且还是就认识论或知识论而言的。二曲“知体”论所要强调的,是知识之“全”,就是说,他所谓知识必须涵括体与用,既包括本体知识,也包括实用知识,能够将各个层面的知识凝铸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在此意义上,“知体”也就是“明体适用”之“知”。总之,知体的内涵,包括道德的主体、灵原的智慧、知识的来源,并兼涵体与用等各个层面的知识。[38]
三、“明学术”、“醒人心”:对宋明理学经世观念的总结
李二曲总结儒家经世致用传统,提出新的经世观念,与他自己为学观念的转变有关。顺治十四年丁酉(1657)的夏秋之交,三十一岁的二曲,患病静摄,深有感于“默坐澄心”之说,于是一味切己自反,以心观心。久之,觉灵机天趣,流盎满前,彻首彻尾,本自光明。太息曰:“学所以明性而已,性明则见道,道见则心化,心化则物理俱融。跃鱼飞鸢,莫非天机;易简广大,本无欠缺;守约施博,无俟外索。若专靠闻见为活计,凭耳目作把柄,犹种树而不培根,枝枝叶叶外头寻,惑也久矣。”自是屏去一切,时时返观默识,涵养本源。[39]
与《年谱》以上记载相近,二曲在《圣学指南小引》中说:
余初茫不知学,泛滥于群籍,汲汲以撰述辩订为事,自励励人,以为学在是矣。三十以后,始悟其非,深悔从前自误误人,罪何可言?自此,鞭辟著里,与同人以返观默识相切砥,虽居恒不废群籍,而内外本末之辨,则晰之甚明,不敢以有用之精神,为无用之汲汲矣。[40]
这表明,二曲三十多岁时为学观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从“泛滥于群籍,汲汲以撰述辩订”为学,变为“学所以明性而已”,以“明性”为出发点,进而“见道”、“心化”,直至“物理俱融”,内外本末一贯。从此开始,二曲之为学便“屏去一切,时时返观默识,涵养本源”。为学观念的这一根本改变,对于二曲嗣后创立“明体适用”新说,确立新的经世思想,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顺治十六年己亥(1659),三十三岁的二曲提出了“以‘明体适用’为经世实义”的思想。[41]康熙八年己酉(1669),二曲四十三岁,由门人录其讲学答语成《体用全学》一书,使“明体适用”成为更加完整的学说。以“明体适用”作为经世的实质性意涵,从体、用关系的高度思考经世问题,是二曲经世观念的重要特质。可以说,这在清初主张经世致用的诸多学者中是相当突出的。
在此“明体适用”的基础上,二曲意在“匡时”、“用世”、“救世”的经世思想,主要体现于“明学术”、“正人心”的社会教化使命。康熙九年庚戌(1670),二曲四十四岁,因有感于友人言及时务,便郑重指出:“治乱生于人心,人心不正则致治无由,学术不明则人心不正。故今日急务,莫先于明学术,以提醒天下之人心。”[42]自此,“惟阐明学术、救正人心是务”。[43]二曲还进一步提出:“大丈夫无心于斯世则已,苟有心斯世,须从大根本、大肯綮处下手,则事半而功倍,不劳而易举。夫天下之大根本,莫过于人心;天下之大肯綮,莫过于提醒天下之人心。然欲醒人心,惟在明学术,此在今日为匡时第一要务。”[44]在二曲,落实此“匡时第一要务”的主要形式是从事民间讲学。在此,以“明学术”、“正人心”的社会教化为己任,表明二曲经世思想从以政治、民生为主要内容转变为以“明学术”、“醒人心”的社会教化为中心,这是二曲经世方向的新选择。
这里的问题在于,“明学术”、“醒人心”的社会教化事业能否与“经世”相联系?这涉及对儒家经世观念之完整内涵及其变迁的理解。“经世致用”是儒家的重要传统,二曲对此深有体会,他说:“吾儒之教,原以‘经世’为宗。”[45]但是,对于经世观念的完整内容和实施重点等问题,长期以来在不同学派或学者之间一直存在着歧解或争辩。站在总结历史经验并进行现代阐释的立场上来看,“经世”的最一般涵义,当指对世间亦即国家和社会一应实际事物的经略和治理。若对“经世”的内涵做更为完整的考察,似有必要将其区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制度或政治的层面,包括典章法制的沿革,政治准则的厘定,对国家、社会事务的掌管和治理;还包括对以上诸项的批评或重构等。这一层面,直接关乎国家和社会的治乱。第二,物质或经济的层面,亦即“开物成务”,诸如农工商贾、水利漕运、兵马钱粮等一应有关国计民生的实际事务都包括在内。这一层面,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强弱和社会的盛衰。第三,精神或文化的层面,其重心在于建构、完善和维护社会的精神文化价值系统,以范导和整合“世道人心”,它关系着社会各阶层道德水准的高低、精神气质的优劣、社会风气的好坏等等。上述三个层面,体现了儒家重建社会秩序的全面要求。二曲思想成熟期的经世观,主要指向第三个层面,亦即以“正人心”为重点的“倡道救世”事业,力图为社会重建精神文化价值系统。
然而,近世学者对于儒家的经世意识,大多只论及政治或经济层面,似乎精神或文化层面的事务并不包括在儒家的经世范围之内。其实,精神文化层面的社会教化事业本来也是儒家经世观的题中应有之义。从先秦到宋明,儒家之民间讲学,不仅具有社会教化的功能,而且也是推动儒教自身学理发展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儒教民间讲学还冲击了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官学格局,有效地维护了学术的独立性。故可以说,经常性的民间讲学活动,是儒学存在和发展必不可少的平台和途径。
从宋明新儒家经世事业的历史变迁来看,北宋的王安石变法把政治层面的经世事业推向了高潮。当时,以张载、二程为代表的民间讲学活动,主要着眼于人才培养和人心教化,但由于仅限于关、洛等地区,尚处于边缘状态。张载说:“今欲功及天下,故必多栽培学者,则道可传矣。”[46]可见,张载把讲学传道、培养学者视作“功及天下”的头等大事。王夫之在总结北宋真、仁朝的文教政策和兴教运动的影响时说:“嗣是而孙明复、胡安定起,师道立,学者兴,以成乎周、程、张、朱之盛。”[47]随着王安石变法的失败,至南宋尤其是明代以后,原先处于新儒家经世事业中心的政治改革,其地位才愈益被民间讲学所取代。这可以看作新儒家在政治领域受挫之后,经世观念发生转向,开始在精神或文化层面上施展其经世抱负。
二曲以“明学术”、“醒人心”为中心的新的经世观念,正是他总结宋明理学经世观的结果。由于阳明讲学一生,生平志业以社会教化为重心,故二曲尤其对其讲学事业推崇备至:
阳明先生自为驿丞,以至宰庐陵,抚江西,总督四省,所在以讲学为务,挺身号召,远迩云从。当秉钺临戎,而犹讲筵大启,指挥军令,与弟子答问齐宣,直指人心一念独知之微,以为是王霸、义利、人鬼关也,闻者莫不戚戚然有动于中。是时,士习灭裂于辞章记诵,安以为学。自先生倡,而天下始知立本于求心,始信人性之皆善,而尧舜之皆可为也。于是雨化风行,云蒸豹变,一时学术,如日中天。[48]
在二曲看来,阳明倾全力从事讲学事业,是力图在全社会范围内推动改善人心的道德教化运动,以实现天下之治。正是在总结宋明理学家讲学传统的基础上,二曲才格外强调讲学在儒学中的特殊位置。他说:
立人达人,全在讲学;移风易俗,全在讲学;拨乱返治,全在讲学;旋乾转坤,全在讲学。为上为德,为下为民,莫不由此。此生人之命脉,宇宙之元气,不可一日息焉者也。息则元气索而生机漓矣![49]
儒家的讲学传统源远流长。二曲不仅继承了这一传统,而且更加高扬了儒家的讲学精神。将讲学置于如此重要的地位,可以说这在儒学史上是颇为罕见的。
[注 释]
① 全祖望撰:《鮚埼亭集》卷十二《碑铭七·二曲先生窆石文》,《全祖望集汇校集注》,朱铸禹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37页。后来,梁启超也以李二曲为“清初大师”。参阅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朱维铮校注,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57页。
② 据《宋元学案》,北宋胡瑗“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参阅黄宗羲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一《安定学案·文昭胡安定先生瑗》,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页。
[1]李顒撰:《二曲集》卷十六《书一·答顾宁人先生》,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48-152页。
[2]李顒撰:《二曲集》卷十六《书一·答顾宁人先生》,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49-150页。
[3]李顒撰:《二曲集》卷二《学髓》,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1页。
[4]李顒撰:《二曲集》卷二十九《四书反身录·大学》,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403页。
[5]张载撰:《正蒙·太和篇第一》,《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9、7页。
[6]张载撰:《经学理窟·义理》、《经学理窟·气质》,《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74、269页。
[7]张载佚书《礼记说》辑本,第219条。
[8]王守仁撰:《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五《年谱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306页。
[9]《二曲集》附录三《二曲先生年谱》,第652页。
[10]李顒撰:《二曲集》卷十八《书三·柬惠含真四》,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04页。
[11]大盐平八郎撰:《洗心洞札记》,《大盐平八郎集》,收入上村胜弥編:《大日本思想全集》第16册,东京:《大日本思想全集》刊行会1932年版,第384页。
[12]大盐平八郎撰:《增补孝经汇注自序》,收入井上哲次郎,蟹江义丸合编:《日本伦理汇编》第3册,东京:育成会1901-1903年版,第549页。
[13]大盐平八郎撰:《古本大学刮目》,收入《日本伦理汇编》第3册,第214-215页。
[14]王守仁撰:《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外集》二《诗·送蔡希颜三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32页。
[15]李顒撰:《二曲集》卷十六《书一·答张澹庵四》,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45页。
[16]李顒撰:《二曲集》卷十六《书一·答张伯钦四》,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61页。
[17]李顒撰:《二曲集》卷四《靖江语要》,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4页。
[18]李顒撰:《二曲集》卷六《传心录》,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45页。
[19]李顒撰:《二曲集》卷四《靖江语要》,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5页。
[20]李顒撰:《二曲集》卷二《学髓》,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8页。
[21]周敦颐著:《周敦颐集》卷二《通书·圣第四》,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7页。
[22]周敦頤著:《周敦頤集》卷二《通书·诚下第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5页。
[23]张载撰:《正蒙·太和篇第一》,《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7页;《正蒙·乾称篇第十七》,《张载集》,第63页。
[24]《张子语录中》,《张载集》,第325页。
[25]李顒撰:《二曲集》卷一《悔过自新说》,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6页。
[26]程顥、程颐撰:《河南程氏文集》卷二《书记·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60、461页。
[27]李顒撰:《二曲集》卷三十《四书反身录·中庸》,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422页。
[28]李顒撰:《二曲集》卷四《靖江语要》,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6页。
[29]李顒撰:《二曲集》卷二《学髓》,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0-21页。
[30]李顒撰:《二曲集》附录三《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636页。
[31]徐世昌等编纂:《清儒学案》卷二十九《二曲学案》,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095页。
[32]唐鉴编纂:《国朝学案小识》卷四《翼道学案》,清道光年间刻本。
[33]参阅〔日〕荒木见悟著:《李二曲》,东京:明德出版社1989年版,第24页。
[34]朱熹撰:《大学章句》,《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7页。
[35]王守仁撰:《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大学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68页。
[36]对二曲“灵源”的解释,参阅〔日〕荒木见悟著:《李二曲》,东京:明德出版社1989年版,第48页。
[37]李顒撰:《二曲集》卷二《学髓》,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8页。
[38]参阅林继平著:《李二曲研究》,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4-253页。
[39]李顒撰:《二曲集》附录三《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634-635页。
[40]李顒撰:《二曲集》卷十九《题跋》,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25页。
[41]李顒撰:《二曲集》附錄三《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636页。
[42]李顒撰:《二曲集》附錄三《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651页。
[43]李顒撰:《二曲集》卷十二《匡时要务序》,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03页。
[44]李顒撰:《二曲集》卷十二《匡时要务》,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04页。
[45]李顒撰:《二曲集》卷十四《周至答问》,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22页。
[46]张载撰:《经学理窟·义理》,《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71页。
[47]王夫之撰:《宋论》卷三《真宗一》,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3页。
[48]李顒撰:《二曲集》卷十二《匡时要务》,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06页。
[49]同上,第1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