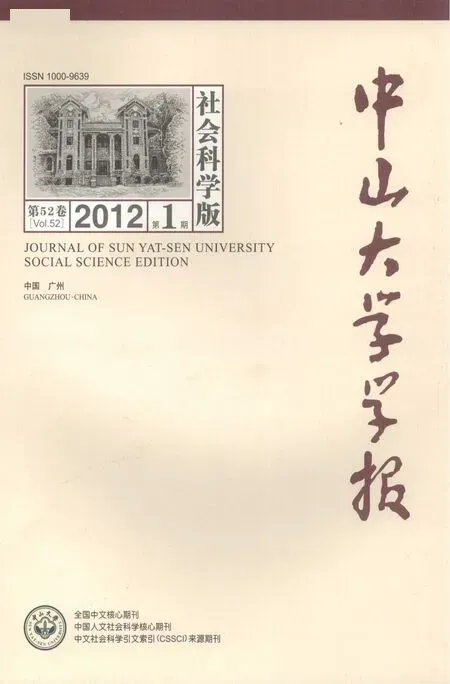再论马克思的“实践”概念*
——兼答刘林《新实践美学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误读》
张玉能
刘林的《新实践美学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误读》(《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4期,以下简称《误读》)认为,新实践美学误读了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和实践哲学。我们觉得,《误读》实际上是误读了新实践美学对“实践”概念和实践哲学的解释。为了促进当代中国美学的发展,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此予以澄清。针对《误读》所批评的新实践美学对实践的感性性、总体性、革命性的误读和错释,我们予以回答,以正视听。看来《误读》的作者并没有很仔细地阅读《新实践美学论》等新实践美学的代表论著,而是以意度之。请看《误读》对新实践美学的“实践”概念的三个质疑和批评。第一,新实践美学没有理解实践作为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新实践美学所理解的“感性”是一个与“理性”相对的概念,它是直接的、物质的、功利的和低级的,最终会被精神的、理性的、非功利的活动所替代。这样的“感性”仍然停留于传统哲学认识论的框架内。在这种对感性的理解基础上,新实践美学对“实践”概念的理解也仅在认识论层次上。这种对“实践”内涵的把握降低了实践的地位,没有真正理解实践的本体论意义。可以说,感性活动就是生命活动本身。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一种现实的感性活动超越了以往哲学中感性与理性、物质与精神、事实与价值的二元对立,从而生成了本体论意义上的“实践”概念。第二,新实践美学对于实践的不同层次的划分,破坏了实践本身的总体性内涵。这种对“实践”人为割裂的根本原因在于,新实践美学简单地把实践理解为人类适应自然、求得生存的手段,而忽视了实践的本体论意义。总体性的实践活动所创造的世界具有真正统一性的理想,即马克思所说的,人与自然矛盾的真正解决、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人自身矛盾的真正解决,这种统一性的理想就是人类的美学境界。第三,新实践美学没有理解马克思实践哲学的革命性意义,从而将审美活动重新陷入传统美学之中。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是对传统二元论哲学的超越,它使哲学不再以探寻永恒真理和世界的超验本质为目的,而是使哲学成为与人、与人的实践活动相关的人类学实践论。但是,新实践美学不但没有赋予实践哲学这种意义,相反,它使美学研究重新进入传统的对审美意识的研究。新实践美学沿着审美意识的思路,继续认为审美是与其他实践不同的自由实践的产物,审美关系是一种超越了实用的、认知的、伦理的、巫术宗教的功利目的的关系。这种观念使新实践美学不是建立在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基础之上,而更像是对近代康德美学的回归。更重要的是,新实践美学仍然抱守着美学本质主义不放,它将美的本质定义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事实上,即便出现了对象化的实践活动,审美也并不一定发生,尤其是在当代西方美学中,寻找美的本质问题早已被弃之不顾。当代美学关注的问题是:审美究竟在生活中的何种情境下发生以及艺术在文化中具有什么作用?新实践美学事实上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它使美学纠缠于早已废弃的美学问题,而遗忘了真正的美学问题。
以下,是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回应和澄清。
一、关于实践概念的感性性
的确,关于感性的含义,应该有认识论的意义和本体论的意义。所谓感性的认识论意义就是,凡是以感觉器官,即眼耳鼻舌身等五种感觉器官来获得的认识,就是感性认识,它是认识的初级阶段,还有待于发展为理性认识,即通过思维进行的抽象的认识。所谓感性的本体论意义就是,凡是人身体力行的直接的活动,就是感性的活动,它是人的存在方式的物质形式,有待于发展为人的存在方式的精神形式。因此,认识论意义上的感性是与理性相对的,而本体论意义上的感性是与精神相对的。实际上,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的实践概念既有认识论意义上的含义,也有本体论意义上的含义。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多次谈到实践的感性性。比如:“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gegenständliche]活动。因此,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做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9页。这一段话就是批评费尔巴哈和一切旧唯物主义哲学的主要缺点,这种缺点就是对“对象、现实、感性”的理解仅仅是认识论方面的,也就是把对象、现实、感性仅仅当作是认识或者理论的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而没有从“感性的人的活动”,即社会(人类)本体论的意义上来理解“感性”。由此可见,在马克思那里,感性概念既有认识论意义上的含义,也有本体论意义上的含义,而社会(人类)本体论意义上的含义是“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实践概念上的革命性变革。新实践美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实践概念的。众所周知,长期以来,苏联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就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本体论,只有认识论,而本体论不过是中世纪封建主义哲学和启蒙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固有特点。实践美学的早期代表人物李泽厚在20世纪80年代探讨美学的哲学基础时,就指出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这种错误理解,提出了所谓“人类学本体论”②我们不同意所谓“人类学本体论”的提法,因为人类学只是一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边缘科学,不具有哲学的高度,因而不能够成为作为研究存在的本原和存在的方式的哲学学问的本体论的定性尺度。作为存在,在地球上,除了自然的存在和社会的存在,就没有其他的存在了。因此,本体论就应该分为自然本体论和社会本体论两种,社会本体论直接与人类的存在相关,所以也可以称为“人类本体论”。详见张玉能:《试论20世纪美学的人类本体论转向》,《上海文化》2005年第3期。。然而,在关于实践概念的理解上,李泽厚却并没有真正从社会本体论或者人类本体论的意义上来理解实践作为“感性的人的活动”的全部含义,仍然仅仅把实践概念局限在物质生产的范围之内,那么,在物质生产的范围之内,“对象、现实、感性”仍然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概念,是脱离“实践”概念的,或者说是与实践概念相对立的概念。这主要反映在旧实践美学对“自然的人化”的理解上。在李泽厚那里,“自然的人化”是通过物质生产(实践)的改造,自然(对象、现实、感性)成为了人们“认识了”(把握了)的自然,这就是“人化的自然”。因此,这样的理解就必然招来这样的驳诘:人们没有直接加工改造过的“自然”,如太阳、星星等等,如何被认为是“自然的人化”和“人化的自然”呢?如果“认识了的”自然就是“人化的自然”,那么就很可能滑入唯心主义。这种认识论意义上的含义,只是把实践(物质生产或劳动)作为人类认识能力(感性、知性、理性)的一个前提,并没有把“感性”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实践之一种。正是从这样的历史状况出发,新实践美学才真正地、全面地从认识论意义和社会(人类)本体论意义上来理解感性和实践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美学的哲学基础的讨论中,笔者就坚决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仅有认识论,而且有本体论,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是一种社会本体论或者人类本体论,由于它把实践作为人的存在本原和存在方式,所以就是一种实践本体论。我们在刘纲纪教授明确提出“实践本体论”之后,一直到今天都是坚持“实践本体论”的。而且,我们在分析和阐发实践概念时,是非常强调从哲学的不同层次来进行的,所以我们既注意实践、感性等概念的认识论意义上的含义,也注意它们的本体论意义上的含义,甚至还注意它们的价值论意义上的含义。
简而言之,马克思突出实践的感性性,主要是为了凸显实践的人类主体性、能动性、革命性、批判性,也就是凸显实践作为人的存在本原和存在方式,指明了人的存在的本原和方式并不是精神性的、理论性的,而是实实在在的感性的存在。所以,马克思说:“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做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集,第501,501页。这样,就不是刘林所理解的感性就是“我们无限丰富的感觉过程,包含了人类活动的一切方面,它使人类本质的一切方面无一不构成实践的要素”。如果真是这样,“感性”概念,既仅仅成了“感觉过程”,又“包含了人类活动的一切方面”,势必陷入无法自拔的自我矛盾之中。殊不知,无论怎么无限丰富,感觉过程毕竟还是感觉过程,且不说这个“感觉过程”仍然是一个心理学和认识论的概念,感觉过程并不是实践的全部。也就是说,实践的感性性并不是实践概念的全部,而只是实践概念的一个方面;实践还是一个双向对象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现实的活动过程,还是一个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实践的感性性虽然是最直接、最生动的,也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基础,但是它绝不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全部。实践不仅要使人的认识从感性认识发展和深化为理性认识,而且还要使人的感性存在发展和生成为精神的存在,成为区别于一般的感性的动物的社会存在和社会生活。因此,“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集,第501,501页。。所以,感性概念在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之中,具有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多重意义,并不能把本体论与认识论对立起来,以一个概念的本体论意义否认它的认识论意义,也不能以这个概念的认识论意义否认它的本体论意义,更不能把感性概念与实践概念等同起来,须知感性只是马克思用来界定实践概念一个方面的概念。刘林用“感性活动”偷换了“感性”,因此就有了一系列的推论:“感性活动既是一种可观察的、能够对象化的活动,又具有某种主观性,凝聚着人的目的和理想,因此,感性活动自身就具有无限丰富性,它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统一,现实和理想的统一。可以说,感性活动是生命活动的最直接的方式,或者说,感性活动就是生命活动本身。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一种现实的感性活动超越了以往哲学中感性与理性、物质与精神、事实与价值的二元对立,从而生成了本体论意义上的‘实践’概念。”这种推论,仅仅是在谈论“感性活动”,还是在谈论“感性”概念本身?如果说是在谈论“感性活动”,还可以勉强说得通,因为这里的“感性活动”实际上就是“实践”的代名词;如果说是在谈论“感性”概念,那么这些推论就大成问题了。请问:“感性”概念本身“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统一,现实和理想的统一”吗?“感性”概念本身“是生命活动的最直接的方式”,或者“就是生命活动本身”吗?进一步讲,要知道并不是“一种现实的感性活动超越了以往哲学中感性与理性、物质与精神、事实与价值的二元对立,从而生成了本体论意义上的‘实践’概念”,而是人类的“实践”活动本身统一了以往哲学中感性与理性、物质与精神、事实与价值的二元对立,从而产生了本体论意义上的“实践”概念。这里的“感性”与“感性活动”是不能混淆的。如果刘林不是有意为之,那就是犯了概念混乱的逻辑错误。
二、关于实践概念的总体性
众所周知,“总体性”概念,无论是作为西方传统哲学和美学思想的概念,还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卢卡奇的概念,都遭到了利奥塔、福柯、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和美学家的猛烈攻击,被他们视为旧形而上学和本质主义的一个概念和观念。后现代主义哲学和美学解构确定性,张扬不确定性,利奥塔就大声疾呼:“让我们向统一的总体性(totality)开战”,即向西方传统哲学和美学思想追求的普遍性、统一性、整体性开战①参见朱立元主编:《西方美学名著提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导论”第2页。详见张玉能:《后现代主义与实践美学的回答》,《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告别或者解构“总体性”或“整体性”,已经成为了后现代主义哲学和美学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后现代主义告别了整体性和统一性,因为,以往那种维系语言结构、社会结构、知识结构和文化结构的统一性上的总体性的普遍逻辑已不奏效。过去,这种普遍有效逻辑建立在元叙事(Metanarrative)的基础之上,作为主流的思想,它们曾赋予整体性和统一性以合法化的依据。”②岛子:《后现代主义艺术系谱》,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74页。当然,我们并不完全同意后现代主义哲学和美学的这种观点。笔者在《后现代主义与实践美学的回答》和《后现代主义思潮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③《后现代主义思潮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是张玉能主持,张弓参加的一项2006年度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已经结项,并且发表了多篇文章论述关于后现代主义哲学和美学否定总体性的观点,如张玉能、张弓:《解构主义文论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9期),张弓:《崇高美学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之中,已经对后现代主义哲学和美学关于不确定性和总体性的论述进行了辨正和分析;但是,后现代主义哲学和美学关于总体性、整体性、统一性的反思和批判却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我们在论述一个事物或者一个概念时,既要看到事物和概念的多层次结构,也要看到事物和概念的组成要素必须是一个整体。正是这样两个方面的辩证统一才形成了该事物和该概念的多层次结构和意义,及其所形成的系统性和它的整体性、统一性、总体性和变化发展。换句话说,任何事物和任何概念都不可能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整体”,然而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们又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整体。所以,我们应该在整体和部分、系统和要素之间看到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们正是这样来看待和分析实践概念的:我们把实践概念在结构上分为物质交换层、意识作用层与价值评估层;在类型上分为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与话语生产;在功能上分为建构功能、转化功能与解构功能;在发展程度上分为获取性实践、创造性实践、自由(创造)性实践等等;并且实践在不同层次上与审美活动的不同方面发生着联系。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实践概念实际上就是具有这样的不同层次的含义,我们在研究它时也就必须如实地这样划分清楚,否则就会仅仅有一个混沌的、模糊的实践概念,就像新中国建立以后到新时期之前我们哲学界和美学界对待实践概念那样,缺乏分析,只是直观地、混沌地、模糊地运用实践概念,从而产生了模糊不清的概念运用。实践概念绝不是一个单一的、混沌的概念,不是类似于莱布尼茨的“单子”的那样一种实体概念。它是有结构的、分层次的,是由许多要素组成的“整体性”概念。因此,我们在不同的结构、不同的功能、不同的发展程度、不同的层次上来分析实践与美和审美及其艺术的关系,从而能够发现美和审美及其艺术并不是与实践的混沌整体发生模糊混沌的关系,而是自由创造性实践的产物和表现。它们不是一般的物质生产,而是一种精神生产和话语生产及其产物,物质生产不过是它们的最终决定因素。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即建构功能、转化功能或者解构功能。当然,在总体上,美和审美及其艺术是与实践发生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的,因此,在实践哲学和实践观点的哲学基础上建构的美学体系才称为“实践美学”,而不是其他的什么美学。在这个意义上,新实践美学既是在实践概念的总体性上建构起实践美学的,又是在实践的不同层次、不同功能、不同结构、不同发展程度之中来揭示实践与美和审美及其艺术之间的本体论关系、认识论关系、价值论关系和方法论关系。只有这样的分析才可能真正揭示出实践与美和审美及其艺术的真实关系和实际价值,不至于仅仅在混沌的、模糊的实践概念基础上模糊地、混沌地论述美和审美及其艺术,从而像旧实践美学那样在遭到后实践美学和其他一些美学流派的质疑和驳斥时,陷于无法自圆其说的窘境。其实,分层次、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来论述实践与美和审美及其艺术的关系,并不一定破坏实践概念的整体性、统一性、总体性,把整体性与结构性、整体与部分对立起来,悬设一个空洞的、整体的、一成不变的、单子式的“实践”实体概念,只能是一种西方传统哲学和美学的“形而上学”,是必须破除的。这也就是后现代主义哲学和美学所猛烈攻击的形而上学传统概念。这种不加分析的实践概念同时也是中国传统哲学和美学思想的整体性、直观性思维方式的的表现。它虽然有其优长之处,但是,如果把整体性与分析性对立起来,甚至排斥分析性,那就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片面的思维方法的表现。就像庄子所说的“浑沌”被凿七窍而死亡的寓言所坚持的那样的混沌性,就是一种片面的整体性,也是中国传统哲学和美学思想长于综合、直观,拙于分析、知性的一种表征。我们应该注意借鉴西方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的分析的、知性的思维方法,同时保持中国传统哲学和美学思想的综合的、直观的思维方法,才可能真正辩证地揭示实践与美和审美及其艺术的实际关系,才能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当代美学体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界和文论界为了医治所谓的“失语症”,许多学者提出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和文论思想以及美学范畴和文论范畴的“现代转型”。然而30年过去了,仍然没有见到有什么比较成功的经验和成果出现。其中原因当然非常复杂,但是,思维方式的转换和美学思想、文论思想的范畴概念的厘定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和文论思想是中国古代传统思维方式的产物,它的范畴概念大多是混沌的、模糊的、整体的、直观的,很难予以明确定义和确切解释,“意象”、“意境”等还是比较清晰的,像“神”、“大”、“美”、“形”、“质”、“意”、“言”等等很难确切阐释,几乎没有办法融入现代西方美学和文论的范畴概念体系,更不能直接移植,必须对其进行大量的分析、阐释才能够进行“现代转型”。不仅文言文的语言形式是个难以跨越的障碍,而且更艰难的是,这些混沌、模糊、直观、整体的范畴概念的确切含义不分析清楚就根本没有办法做到“现代转型”。正因为此,直到目前为止,中国当代美学界和文论界鲜有学者认真进行思维方式转换,结合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优长之处,克服它们各自的不足之处,对中国传统美学和文论的范畴概念进行分析和综合的改造和转换,所以在一定意义上,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和文论思想仍然处于“失语症”状态之中。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和文论思想无法与西方美学思想和文论思想进行交流对话,也没有办法直接面对中国当下的审美现实、文学艺术现实,更不能对中国当下文学艺术的现实状况进行评论解说。要改变这种状况就首先必须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混沌性、模糊性、总体性的误区之中解脱出来,把结构分析与系统整合结合起来,逐步完成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取长补短,逐渐形成与西方美学思想和文论思想相互融合的范畴概念体系。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不祛除类似《误读》所主张的“总体性”观念和思维方法,是绝对不能完成的。
至于我所说的“人类的实践是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生存而进行的处理人与自然、社会、他人之间关系的感性的、现实的活动”,是否破坏了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本体论意义,这是非常明显的事实。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也就是社会本体论或人类本体论问题。无论是从人的进化和生成,还是从人类的实际生存状态来看,人类的实践都是为了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也就是为了解决人类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而进行的。一个没有任何需要的死人是无需实践的。而且人类的实践也是按照人类的不同需要层次逐步发展起来的,而美和审美及其艺术就是人的审美需要的产物。审美需要的生成必须是在物质需要和认知需要、伦理需要等精神需要得到满足的基础上才能够达成的。这不仅仅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已经论证过了的心理学基本原理,而且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过了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得清清楚楚:“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集,第601页。离开了人的基本需要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所谓“总体性实践”就是一种虚无,哪来的什么“总体性的实践活动所创造的世界具有真正统一性的理想,即马克思所说的,人与自然矛盾的真正解决、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人自身矛盾的真正解决,这种统一性的理想就是人类的美学境界”?《误读》在这里引用的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那种统一性的理想是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一种描述。如果只有这种统一性的理想才是人类的美学境界,那么这种美学境界也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可是我们所谈论的是现实的实践所逐步生成的现实的美和审美及其艺术的美学境界。由此就可以看出,《误读》所说的“总体性”不过是一种类似于柏拉图的“理念”的传统形而上学概念,倒是应该被列入后现代主义所说的“宏大叙事”之列,理应抛弃!
三、关于实践概念的革命性
的确,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和实践概念是一种世界哲学和美学的革命性变革。这一点我们早在1990年11月出版的《美学要义》中就已经指出了。以后,我们反复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美学对世界美学的革命性变革。这种革命性变革主要表现在:其一,马克思主义美学把美学问题与人类社会实践联系起来。这实质上也就是实现了哲学和美学由认识论向社会本体论(人类本体论)的转向。其二,马克思主义美学把美学问题与人的本质联系起来。这实质上也就是在人类本体论意义上来研究美和审美及其艺术。其三,马克思主义美学唯物而辩证地解决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这实质上也就是实现了由实体本体论向关系本体论的转型②详见张玉能:《美学要义》,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9—13页。。我们不仅在理论上这样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革命性变革,而这种革命性变革的标志,就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以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和实践概念为哲学基础;而且我们在与后实践美学流派或者其他美学学人的辩论过程中,也是充分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和实践美学的基本观点,绝没有把实践概念重新放回到近代西方传统美学的认识论美学的框架之中。然而,《误读》却指责新实践美学“使美学研究重新进入传统的对审美意识的研究。审美意识是近代认识论哲学的产物,它使审美活动成为与认知活动、伦理活动不同的领域,在这一领域中,审美是一种与知识和道德无关而只与个人的感性愉快相关的无功利、无目的、无概念的对待事物的态度,审美意味着一种自由。现代西方美学早已对这种审美意识进行了反思,认为审美并不限于私人的审美意识中,而是与人的生活紧密相关的。新实践美学沿着审美意识的思路,继续认为审美是与其他实践不同的自由实践的产物,审美关系是一种超越了实用的、认知的、伦理的、巫术宗教的功利目的的关系”。这样的指责真是叫人匪夷所思。好像《误读》的作者连最起码的美学基本知识也还欠缺。难道美学研究审美意识就是重新回到传统认识论哲学和美学范围之内了?任何一种美学都应该包含着三个部分:审美客体的研究,即美的本质、美的形态、美的范畴的研究;审美主体的研究,即研究美感(广义的美感是指审美意识,狭义的美感是指审美感受)的产生和发展、美感的性质和特征、美感的心理因素;审美创造的研究,即研究技术美学、艺术哲学、审美教育(见《美学要义》第一章美学的对象)。我们是在审美关系的整体之下来分析美学研究对象的这三个方面的,我们认为,美学是以艺术为中心研究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科学。审美关系表现为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审美创造三个方面③张玉能:《美学要义》,第16—17页。,那么有什么根据可以说新实践美学研究审美意识就是回到传统认识论哲学和美学呢?如果真是这样,世界上就没有《误读》所谓的“现代美学”了,因为一切美学都必须研究审美意识,即广义的美感。还有更加令人莫名其妙的:《误读》认为认识论哲学和美学“使审美活动成为与认知活动、伦理活动不同的领域,在这一领域中,审美是一种与知识和道德无关而只与个人的感性愉快相关的无功利、无目的、无概念的对待事物的态度,审美意味着一种自由”。把审美活动与认知活动、伦理活动区别开来,恐怕并不是近代认识论哲学和美学的特殊贡献,好像中世纪的经院派美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就已经把美与善区别开来,把美归结为认识活动的对象,把善归结为欲念(伦理活动)的对象①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66—67页。。至于说“审美是一种与知识和道德无关而只与个人的感性愉快相关的无功利、无目的、无概念的对待事物的态度,审美意味着一种自由”,这是康德的说法。新实践美学并不完全同意康德的说法,我们从来都没有说过“审美是一种与知识和道德无关而只与个人的感性愉快相关的无功利、无目的、无概念的对待事物的态度”。我们从来就认为,审美活动是一个包含着认知、情感、意志的完整的心理活动过程,审美活动不可能“无功利、无目的、无概念”,而只是“超越了直接功利目的”,“积淀着理性认识(概念)”,“以情感为中介”的自由的实践活动②张玉能:《美学要义》,第42—61页。。审美活动是一种自由的实践活动,难道就不是实践活动了?而且,我们认为,美和审美及其艺术是人类社会实践达到一定自由程度所形成的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具体表现。换句话说,审美关系显现在审美客体上就是所谓的“美”,审美关系显现在审美主体上就是所谓的“美感”(广义的是指审美意识,狭义的是指审美感受),审美关系显现在审美创造上就是所谓的“艺术”。
至于《误读》指责新实践美学“仍然抱守着美学本质主义不放”,也是无的放矢。首先我们必须澄清“本质”的探讨与“本质主义”的区别。我们一直认为,本质的探讨与本质主义是两码事,不能把所有的关于本质的探讨都说成是所谓的“本质主义”。本质与现象是西方哲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对范畴。“本质和现象是反映客观事物的特性及其发展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的一对哲学范畴。人们通常把事物的普遍的、必然的和相对稳定的内部联系称为本质,而把事物的外部特性和特征称为现象。人类认识的目的就在于通过事物的现象而进到事物的本质,由浅近的本质进到深刻的本质。因此,自哲学产生之日起,本质和现象这一对范畴实际上也就提出来了。这对范畴本身也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③李武林、谭鑫田、龚兴主编:《欧洲哲学范畴简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76,508页。至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里,本质和现象这一对范畴还是行之有效的哲学范畴。“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地继承了哲学史上关于这对范畴的优秀思想,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这对范畴。”④李武林、谭鑫田、龚兴主编:《欧洲哲学范畴简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76,508页。所以,作为美学的一个主要问题,探讨美的本质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课题。《误读》一文本身在引用和论述过程中都多次出现了“本质”一词,也说明探讨本质问题是哲学和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回避不了的。研究本质问题与本质主义不是一回事,不能因为反对本质主义而拒绝探讨本质问题。所谓“本质主义”是指西方传统哲学和美学中主张有一种先在的、决定着事物性质的、固定不变的理性规定性的理论观点,如柏拉图的理念论就是这样一种本质主义的形而上学观点。它认为决定事物的性质的就是那先在于事物现象之后的一成不变的理性观念,即理念。这种本质主义的理论观点,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遭到了各种形式的质疑和颠覆;然而一直到19世纪末,本质主义传统也没有中止,许多哲学家都认为,一部欧洲哲学史就是在给柏拉图哲学作注释。到了19、20世纪之交,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的兴起才打起了“拒斥形而上学”的大旗,反对本质主义的哲学观点。最早明确地提出反对本质主义的应该是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他早期的《逻辑哲学论》(1922)认为,类似于美、善、“本质”之类的问题都是不可言说的问题,也就是一些必须对之保持沉默的问题。他明确地说:“凡是可以说的,就能明白地说,凡是不可以说的,对它就必须沉默。”⑤洪谦主编:《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252页。也就是要把探讨本质的问题逐出哲学领域。然而,到了他的晚期,维特根斯坦发觉美、善、“本质”之类的问题,是回避不了的,于是就提出了一个所谓“家族类似”的概念来取代“本质”。这实质上就等于是承认了事物的共性或本质是存在的,只是不要把它视为某种一成不变的、先在的、固定的规定性,而是要以多层次的开放的视角来探讨它。美国分析哲学家奎因也认为,虽然事物没有什么“本质”,但是哲学研究必须有“本体论的承诺”。因此,反本质主义的思潮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和。这似乎表明,本质的探讨还是应该而且可能进行的,不过,不应该以旧形而上学的那种柏拉图式的固定不变的、先在的、抽象的规定性来界定事物的本质。也就是说,事物或者概念的本质是存在的,也是应该研究的,但是事物和概念的本质是多层次的开放的整体。应该像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所说的,事物和概念应该有第一级本质,第二级本质,第三级本质……本质是离不开事物的存在现象的,所以,萨特才强调“存在先于本质”。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还认为,本质表现为现象是一个逐步展开的过程。因而,人们对于本质的认识也是随着事物的现象的不断展开而逐步深入,不断地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在实践中,人们完全可以通过现象来认识事物的本质”①李武林、谭鑫田、龚兴主编:《欧洲哲学范畴简史》,第509页。。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是反对本质主义的思维方法的,但是,却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来探讨美的本质问题。
我们关于美的本质的探讨是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的,把美的本质看作是多层次的开放的整体。因此,我们认为:从认识论角度来看,美是客观的属性;从本体论角度来看,美是一种社会属性和价值;从发生学角度来看,美是社会实践达到一定自由程度的产物;从现象学角度来看,美是附丽于感性形象之上的。整体言之就是:美是显现社会实践自由的形象的肯定价值②详见张玉能:《美学要义》,第126—142页。。把美的本质定义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美和审美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这种观点并不是李泽厚旧实践美学观点的继续,而是新实践美学的起点。这一观点是蒋孔阳先生在《美学新论》中明确提出来的。它虽然遭到批判,但却是完全可以自圆其说的。关于此,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人的本质力量与美》(《青岛科技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来回答那些否认“美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人们。事实上,只要出现了“自由的”对象化的实践活动,美和审美及其艺术就必然发生。而且,人的本质是分为层次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的本质可以是一个三层次的系统:人的需要即人的本质——自由自觉的活动(劳动)是人的类本质——在其现实性上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力量就是人类所具有的一切物质能力、精神能力、话语能力的总和。而美就是人的本质和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美是在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实践之中生成的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对象性显现;美也反过来作用于人,使人成为真正具有人的本质和人的本质力量的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人的本质力量,作为人类所具有的一切物质能力、精神能力、话语能力的总和,在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话语生产的社会实践之中凝定在对象之中,即对象化了;而且达到了一定的自由境界,于是在人与对象之间就生成了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这种凝结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了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就生成美的属性,或者说对象显现了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而人自己在体现了自己的本质力量,即自己所创造的对象世界之中直观到自己的本质力量所产生的快感,或者说人自己感到了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显现在自己身上所产生的快感就是美感(审美)。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美是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形象的肯定价值,美是显现实践自由的形象的肯定价值。这里的“对象化”的含义就是,在对象之上显现出来;这里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含义就是,人之所以为人应该具有的能力,体现了人的本质的能力,因此也就是达到实践自由的一定程度的人应该具有的能力,或者说就是自由自觉的、形象显现的社会能力。因而,虽然旧实践美学没有解决真正的美学问题,但是新实践美学确确实实、真真切切、明明白白地正在解决问题,而且也部分地解决了一些关键问题,诸如美的本质的初步界定、美学学科的定位问题、艺术的本质的初步界定、美和审美及其艺术的客观性和客体性问题、美和审美及其艺术与人的本质力量的关系问题、美和审美及其艺术在实践之中生成问题、新实践美学的价值论维度问题、实践美学的语言学维度问题、实践概念的含义问题……当然这些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及其真理性的程度,还需要社会实践的检验,不过,我们正在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探索着,比起那些仅仅破坏而不建构的学人应该是更加实在的。尽管在当代西方美学中,寻找美的本质问题早已被弃之不顾,但是美的本质问题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废弃不了的。再说,我们是要建设中国特色当代美学,为什么一定要唯西方美学马首是瞻?你跟着西方当代美学的屁股后面亦步亦趋,最后就是一个邯郸学步的下场,最好的结果也就是西方当代美学的“附录”。你不搞清楚美的本质究竟应该如何界定,连一个比较确定的界定都没有,你如何去回应当代美学关注的问题呢?“审美究竟在生活中的何种情境下发生以及艺术在文化中具有什么作用”这样一个所谓的“当代美学关注的问题”,早在马克思的实践美学之中就有了原则的答案,新实践美学正在进行更加深入细致、广泛现实的研究和探讨。新实践美学事实上并没有使美学纠缠于“美的本质问题”,“美的本质问题”是永远无法废弃的美学问题,而遗忘了“美的本质问题”就无法真正地触及真正的美学问题。我们还是扎扎实实地来学习研究,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和实践概念的真理,为构建中国特色当代美学而努力工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