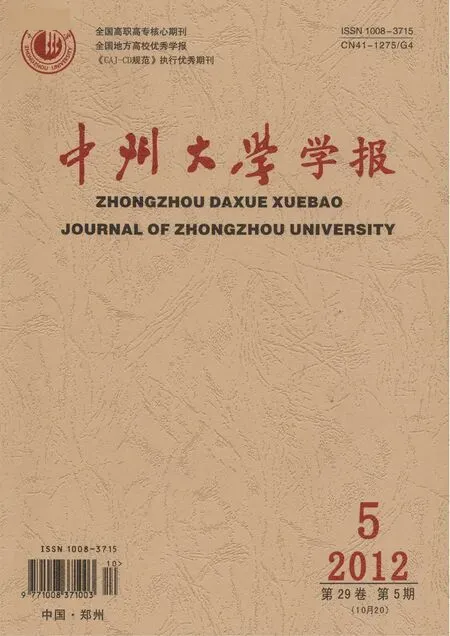论宋代艳情词中的寄托
陈丽丽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 开封475001)
词作为一种娱乐性质的音乐文学,花间尊前、男欢女爱是其主要表现内容,晚唐五代时便确立起绮罗婉媚的艳情本体特色。寄托,是中国古代诗文中极为常见的一种艺术手法,即作家们把内在真实的情感或心绪寄寓、托付在其他的人或事物之上。艳情与寄托,在中国传统文学创作中时常被联系起来。究其根源,可以上溯到《诗经》、《楚辞》中的比兴、象征。在历代诗歌中,借女子口吻或男女关系来托寓各种情怀的作品并不少见,比如文人们时常会借夫妇之情喻君臣之义,或以蛾眉遭妒代小人陷害,或以美人失宠指怀才不遇,或以节妇烈女表忠贞不二,屈原的《离骚》、张籍的《节妇吟》、朱庆馀的《近试上张籍水部》(一作《闺意上张水部》)皆为此中名篇。词为诗余,本是末技、小道,一向以抒写风月之情为主,然而随着文人对这种文体的接受,通过词来表达内心情志的现象越来越增多,寄托也逐渐与词体联系起来。历代创作及词论中,咏物词及咏古词中的寄托手法最受词学家们关注。对于词体最重要的主题——艳情词而言,其中同样蕴含着丰富的寄托手法,值得我们关注与探讨。
一、艳情词与寄托的关系
关于词中寄托,宋人即有清醒认识,例如鮦阳居士《复雅歌词》分析苏轼《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一阕,认为每句皆有寓意,并得出“与《考槃》诗极相似”[1]的结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评苏轼《贺新凉》“乳燕飞华屋”,认为是“冠绝古今,托意高远,宁为一娼而发耶”[1]182。到了清代,词论家们更加关注词中寄托,沈祥龙在《论词随笔》中指出:“屈、宋之作亦曰词,香草美人,惊采绝艳,后世倚声家所由祖也。”[1]4048直接把词与《楚辞》中的香草美人、比兴寄托联系起来。其实词体初创之时,大多用于花间、尊前娱宾,词作中所描绘的女子形象及所呈现出的“要眇宜修”风格,与《离骚》中的“香草美人”有着内在本质区别,前者仅是男人对美色、两性的态度,后者则蕴含着作者人生际遇和政治理想。北宋时期词体复兴,艳情词创作十分繁荣,但其中的寄托手法并不突出,比较常见的是文人在表达男女之情、相思离别时,自觉不自觉地把时光流逝的感伤、怀才不遇的苦闷以及羁旅漂泊的艰辛倾注其中。北宋艳情寄托之作比较典型的是晏殊的《山亭柳·赠歌者》,晏殊被誉为“北宋倚声家之初祖”,郑骞解读他这首词是“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磊之作”,并详细阐释为“此词云‘西秦’、‘咸京’,当是知永兴军时作,时同叔年逾六十,去国已久,难免抑郁”[2]。这首词从小序到内容皆围绕着一位歌妓,但实际上,曾经少年得志、富贵风流的晏殊是借歌妓年长色衰的悲哀来寄寓自己花甲罢相的失意以及“知音见采”的渴望。
随着文人的广泛创作以及词体地位的提升,词中所表达的内容和意趣越来越丰富,“不平则鸣”在词中也渐有体现。不少词人像屈原、宋玉等人一样,借鲜花美人、男女情感来传达自己内心的忧愁幽愤与难言情怀。清代浙西派创始人朱彝尊曾对艳词中的寄托有所分析,他在《红盐词序》中提出:“词虽小技,昔之通儒巨公往往为之,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辞愈微,而其旨益远。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3]朱彝尊认为善于填词者,往往借儿女之言抒发骚雅之义,尤其那些怀才不遇者,更适宜用“寄情”笔法。朱氏所谓的“寄情”,即把内在真实心态、情感志向通过闺阁幽思、儿女情长婉曲地表达出来。由于词体本身具有“绮罗香泽之态”,因此借艳情来表达情感志向,成为词中寄托的一种重要方式。这类富有寄托的艳情词与传统即席应景、赠妓、咏妓之类的艳情之作有所不同,尽管这些作品仍着眼于闺阁情怀、两性情感,但并没有单纯停留在伤春、怀人这些浅层的声色描绘上,词人填词目的并不是为了表现对美色的欣赏、迷恋,或者对情感的倾诉与追忆,而是借助男女间的悲欢离合、相思愁苦来倾诉内心深处因家国、政治、个人遭际等带来的幽隐情怀。可以说,“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1]1652是宋代艳情词名篇的一个显著特色。
南渡之后,出于对亡国之音的反思,不少词学家对词这种文体进行思考,纷纷从“比兴寄托”的角度来体悟前人作品。从具体创作来看,靖康之变带来的国破家亡之痛,定都临安后朝野上下的和、战之争,使得文人心中的情绪越来越丰富。尤其孝宗执政时,从强烈的中兴之志,到北伐失败、隆兴和议后的“无复新亭之泪”[4],国恨家仇、抗金大业淹没在轻歌曼舞、纸醉金迷中。淳熙年间,文人林升曾在临安邸题下一首诗:“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这首著名的政治讽刺诗,强烈地表达了士人们对于忘记国难、苟且偷安社会现实的嘲讽与不满,可以说是当时有识之士思想心态的典型写照。这种心态在词中也有显著体现,与北宋词人的身世之感相比,国势、政局赋予南宋词人更广阔的胸怀和更深刻的情志,因而这一时期词坛上集中出现了一批借艳情寄托家国情思之作。
二、稼轩词中的艳情寄托
辛弃疾是南宋、乃至整个宋代词坛的杰出代表。在稼轩词中,不仅有家国情怀、个人心志的直接抒发,也有借闺阁艳情委婉含蓄的寄托表达。辛派后劲刘克庄为稼轩文集作序时称:“世之知公者,诵其诗词,而以前辈谓有井水处皆倡柳词,余谓耆卿直留连光景歌咏太平尔;公所作大声鞺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其秾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5]可见辛弃疾不仅有横绝六合、豪放劲健的爱国之词,也有不亚于晏几道、秦观秾纤婉丽的艳情之作。综观稼轩所有词作,艳情所占比例并不大,共80余首,仅占其总数14%。然而在这些艳情词中,最著名的篇章几乎皆是有所寄托之作。
例如《摸鱼儿》“更能消”一阕,是辛弃疾词集中知名度最高,最受历代词选家、词论家关注的作品[6],也是一首典型的寄托之作。这首词上阕伤春,借春光流逝来表达年华虚度、国事无望的悲哀,下阕用陈皇后失宠及杨玉环、赵飞燕死于非命的典故,抒发自己被排挤、被打击的忧愁苦闷以及对当权小人得意猖獗的愤懑不满。从内容、风格上看,该词具有浓郁的艳词笔法,但小序“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为赋”,详细点出了填词的时间、地点、创作背景,使读者意识到作者的创作意图并非为了歌宴尊前的单纯娱乐,因而使全词比兴寄托之意格外突出。淳熙己亥即孝宗淳熙六年(1179),辛弃疾时年40岁,由湖北转运副使调任湖南,而在此之前,他已频繁转徙,均未能久任。辛弃疾本是位“壮岁旌旗拥万夫”的侠胆英雄,怀抱着一腔热血南渡归宋,然而却屡受压制,抗金志向一直未得实现,心中郁闷在所难免。他在同年七月上孝宗皇帝奏疏中自称“臣生平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顾恐言未脱口而祸不旋踵”[7],可见其当时处境与“娥眉曾有人妒”极为相仿,因而自然而然地借艳情来抒发郁结于心的压抑与苦闷。罗大经《鹤林玉露》记载:“辛幼安《晚春》词云:‘更能消、几番风雨……’词意殊怨。‘斜阳’、‘烟柳’之句,其与‘未须愁日暮,天际乍轻阴’者异矣。使在汉唐时,宁不贾种豆种桃之祸哉!愚闻寿皇见此词,颇不悦。然终不加罪,可谓至德也已。”[8]罗氏约生于宋宁宗庆元初年,距孝宗时代不远,他所提到寿皇(孝宗)见此词不悦,足可以看出辛弃疾虽以伤春及女子命运着笔,但词中所寄托的个人被排挤被冷落的忧愤以及对国事、对朝廷的批判极为明显,因此招致统治者大为不满。
辛弃疾《祝英台近》“宝钗分”,也是备受历代词选、词论者青睐的经典之作。这是一首典型的闺怨词,具有明显艳情色彩。词人在上阕以烟柳凄迷、片片飞红的春景来渲染男女之间的离情别绪,下阕则重笔写相思,无论是花卜归期还是梦中呜咽,都显得缠绵悱恻。宋人张端义《贵耳集》称该词是辛弃疾为去妾吕氏而作,但后代词论家皆不以为然,纷纷认为这首艳情词别有寄托,如谭献认为“断肠”三句“一波三过折”,末三句“托兴深切,亦非全用直笔”[9]。沈谦认为:“稼轩词以激扬奋厉为工,至‘宝钗分,桃叶渡’一曲,昵狎温柔,魂销意尽,才人伎俩,真不可测。”[1]630张惠言则臆测到:“此与德祐太学生二词用意相似,‘点点飞红’,伤君子之弃。‘流莺’,恶小人得志也。‘春带愁来’,其刺赵、张乎?”[1]1615黄苏《蓼园词评》分析得更为详尽:“按此闺怨词也。史称稼轩人材,大类温峤,陶侃。周益公等抑之,为之惜。此必有所托,而借闺怨以抒其志乎。言自与良人分钗后,一片烟雨迷离,落红已尽,而莺声未止,将奈之何乎。次阕,言问卜欲求会,而间阻实多,而忧愁之念将不能自已矣。意致凄婉,其志可悯。史称叶衡入相,荐弃疾有大略,召见,提刑江西,平剧盗,兼湖南安抚。盗起湖、湘,弃疾悉平之。后奏请于湖南设飞虎军,诏委以规画。时枢府有不乐者,数阻挠之。议者以聚敛闻,降御前金字牌停住。弃疾开陈本末,绘图缴进,上乃释然。词或作于此时乎。”[1]3060黄蓼园不仅指出辛弃疾在这首词中借闺怨以抒其志,而且以“知人论世”之法,从其人生经历来推断该词的写作时间。
辛弃疾《青玉案·元夕》一词同样寄托遥深,别有寓意。词人在下阕刻画了一位在热闹的元宵之夜却独自伫立于“灯火阑珊处”的佳人形象,这位不慕繁华、自守淡泊的清高女子,正是词人在政治上遭受冷遇后仍不愿同流合污的高洁人格的写照。梁启超认为该词有所寄托,并指出词人“自怜幽独,伤心人别有怀抱”[10]。
辛弃疾的艳情托寓之作,历来是后世词学家选编、评论的重点。尤其是清代,随着词学中兴,浙西词派与常州词派相继崛起,虽然这两派词学主张不尽相同,但都十分重视词中的寄托手法,从浙西派领袖朱彝尊,到常州词派盟主张惠言,再到周济、陈廷焯、谢章铤、谭献、况周颐等词论家,皆对辛弃疾等人作品中的艳情寄托颇为关注。
三、南宋其他词人作品中的艳情寄托
借艳情托寓身世、国事的笔法不仅在稼轩词中极为突出,在其他辛派爱国词人作品中也时有所见。例如陈亮《水龙吟》:“闹花深处层楼,画帘半卷东风软。春归翠陌,平莎茸嫩,垂杨金浅。迟日催花,淡云阁雨,轻寒轻暖。恨芳菲世界,游人未赏,都付与、莺和燕。寂寞凭高念远。向南楼、一声归雁。金钗斗草,青丝勒马,风流云散。罗绶分香,翠绡对泪,几多幽怨。正销魂,又是疏烟淡月,子规声断。”细腻地描写了闺中女子面对春景的寂寥落寞以及怀念远人的伤心幽怨,刘熙载点明该词的寄托之意:“‘恨芳菲世界,游人未赏,都付与,莺和燕’言近旨远,直有宗留守大呼渡河之意。”[1]3694张德瀛亦关注到陈亮词中寄托,称:“陈同甫幼有国士之目,孝宗淳熙五年,诣阙上书,于古今沿革政治得失,指事直陈,如龟之灼。然挥霍自恣,识者或以夸大少之。其发而为词,乃若天衣飞扬,满壁风动。惜其每有成议,辄招妒口,故肮脏不平之气,辄寓于长短句中。读其词,益悲其人之不遇已。”[1]4163可见龙川与稼轩一样,同样是借闺情来寄托故土沦丧、国事凋零的残酷以及词人心中引发的悲哀伤感之情。
与辛弃疾交善的韩玉,有一首《水调歌头》:
有美如花客,容饰尚中州。玉京杳渺际,与别几经秋。家在金河堤畔,身寄白蘋洲末,南北两悠悠。休苦话萍梗,清泪已难收。玉壶酒,倾潋滟,听君讴。伫云却月,新弄一曲洗人忧。同是天涯沦落,何必平生相识,相见且迟留。明日征帆发,风月为君愁。
该词序曰:“自广中出,过庐陵,赠歌姬段云卿”,可见这是一首赠妓之作。词人一开篇便点出这位名叫段云卿的歌妓有着如花美貌,然而接下来却没有丝毫艳词丽语描绘姿容媚态,而是写她崇尚中州容饰,并着力刻画这位歌妓离家别乡后漂泊寄寓、身如浮萍的悲苦。韩玉这首赠妓词与传统赠妓之作明显不同,洗却了脂粉与秾艳,以歌妓的命运来揭示靖康之变后的家国之悲。尤其下阕“同是天涯沦落,何必平生相识,相见且迟留”,与白居易的《琵琶行》如出一辙,借同命相怜的歌妓来寄寓自己内心深处的忧国悲愤。
南渡以后,不仅爱国词人多以艳情来寄寓家国之悲、不遇之叹,婉约一派也用寄托笔法来传递情绪。赵长卿是位宗室词人,其作品风格接近北宋,《天仙子》“眼色媚人娇欲度”、《瑞鹧鸪》“结丝千绪不胜愁”皆为传统艳情词,而词序却题为“寓意”,直接点明词人所作是有所寄托的。两首词的上阕皆以浓笔抒写歌妓的娇媚多情以及男女之间的缱绻情感,《天仙子》以“往事悠悠曾记否”转片,由艳情转向写景。黄鹂、百花皆为春天的典型物象,然而在词人眼中则是“忍听黄鹂啼锦树。啼声惊碎百花心”,显得无比凄哀,尤其全词结句“谁为主。落蕊飞红知甚处”,不免使人联想到南渡之后身心无依的悲戚;《瑞鹧鸪》的境界相对开阔,由歌女尊前“檀口未歌先揾泪,柳眉将半凝羞”的离别伤悲,写到送行酒后乘舟归去,末尾“待得名登天府后,归来茱菊映钗头”,传达出开阔向上的志向与意趣,寄寓了作者对前程对国事的信心和期望。这两首词皆以艳情着笔,但都超越了男欢女爱的狭窄范围。
客观来看,寄托手法在宋词中并不鲜见,从北宋词人的打并身世之感,到宋末移民词人的融入亡国之悲,词人们通过艳情、咏物、怀古等主题,寄托自己内心深处的幽隐情怀。就艳情这一词体最重要的题材而言,其中寄托遥深之作在整体数量上并不算多,但富有寄托的艳情词却是两宋词史上最突出且影响最深远的创作类型。从宋词发展来看,虽然寄托早在在北宋晏殊、苏轼等处便有所体现,但真正比较集中创作,并形成一定规模的,是在南渡以后。尤其是南宋中兴时期,以辛弃疾为代表的一批爱国词人,巧妙地用词体本色传统的闺情、绮语委婉地表达内心深处的家国之感、身世之悲,为通俗、轻浅的艳情词增添了几分深沉与蕴藉,并对后世推尊词体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
[1]唐圭璋.词话丛编[C].北京:中华书局,1986:60.
[2]叶嘉莹.唐宋词名家论稿[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48.
[3]朱彝尊.朱彝尊词集[M].屈兴国,袁李来,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405.
[4]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12.
[5]金启华,张惠民,等.唐宋词集序跋汇编[C].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173.
[6]王兆鹏.唐宋词史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110.
[7]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C]//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441-830.
[8]罗大经.鹤林玉露[M].王瑞来,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12.
[9]谭献.谭评词辨[M].清道光27年,刻本:卷二.
[10]梁令娴.艺衡馆词选[M].刘逸生,点校.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