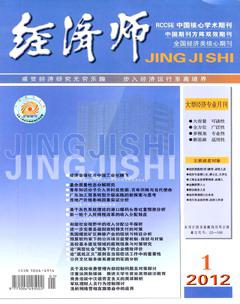施存统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研究综述
张舒
摘 要:施存统(1899-1970),浙江金华人。在中国现代史上,他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历史人物。作为中共创始人之一和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改组派”的理论家,抗战后中间路线思潮的领袖人物,他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对施存统的研究没有予以足够重视,这一课题基本上是一个冷门。文章从他对马克思主义论文的科学阐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精辟见解、在建团建党过程中的宣传组织工作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综述。
关键词:施存统 马克思主义传播 综述
中图分类号:A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12-045-02
建国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 史学界对施存统研究缺乏反映,除了几篇回忆文章外,论文论著基本阙如。80年代后期开始,状况有所改善,对施存统的研究渐渐增多。据统计,近年来,学术论文有21篇,传记有1部,而研究施存统对于马克思主义传播作用的文章主要有2篇。这些成果使对于施存统研究不断深入。无论在广度上或深度上,该课题研究都取得了新的成就。从横向上看,研究的范围日益广泛,涉及了政治、经济、学术、党建等多个领域。从纵向上来说,五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施存统都纳入了人们研究视野范围。而且学者们不但注意纯文本分析,也开始全面考察当时的历史现实、社会环境、研究对象的社会经历及其性格对施存统的影响。
一、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科学阐述
陶水木在《施存统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贡献》一文中认为,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虽然施存统的地位赶不上李大钊、李达、陈独秀等人,但他也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应予以肯定。施存统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即(1)宣传唯物史观。施存统的贡献首先在于:他从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内在联系出发,强调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说最重要的原理有三点,即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这三者中,“以唯物史观为根本,离开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和剩余价值都无法理解,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是以唯物史观为根底的,撇开唯物史观,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2)反击无政府主义,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自1919年始对马克思主义发起全面攻击,他们主张绝对自由,反对一切强权和国家,其要害是反对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以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为信号,与无政府主义者展开大规模论战。正在日本留学兼负责东京党小组工作的施存统积极参加了这场论战,先后发表了《经济组织与自由平等》、《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第四阶级独裁政治底研究》、《无产阶级专政与领袖变节》等文。施存统的反击极富自己的特色,他除了批驳无政府主义的绝对自由论外,还紧紧抓住无政府主义者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要害,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这方面,他比其它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更深刻、更彻底。(3)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4)明确提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如何改造社会?怎样进行中国革命?是五四时期一代知识分子始终孜孜探求的问题,在这方面也留下了施存统的足迹,他的长文《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堪称当时中国人探索中国革命的代表作。(5)科学地说明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区别, 阐述共产主义实现。①
王炯华在肯定了施存统上述类似贡献的同时,更进一步指出了施存统理论贡献的首创性和深度。他认为,施存统是中国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强调无产阶级、士兵和学生的革命联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人,也是明晰地理解和说明共产主义实现步骤的第一人。阐述实现共产主义的步骤。特别是,施存统在这篇文章中明确提出了既要遵守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又不必拘泥枝叶政策这个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他指出,“我以为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都是拿产业发达的国家底材料做根据的,所以他有些话,不能适用于产业幼稚的国家。但我以为我们研究一种学说一种主义,决不应当‘囫囵吞枣‘食古不化,应当把那种主义那种学说底精髓取出”。他以马克思唯物史观和经济学说的基本原理为例,说明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实在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底精髓,乃正是马克思主义精髓底应用”。他强调说,马克思主义本身“并不是一个死板板的模型。所以我以为我们只要遵守马克思主义底根本原则就是,至于枝叶政策,是不必拘泥的”。在这里,施存统从马克思主义精髓即基本原理的普遍适性和它的个别结论不适用于诸如中国这种产业落后的国家的正确判断出发,从马克思主义本身不是死板的模型即生硬的教条的命题出发,明确提出在中国应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既要遵守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又不必拘泥马克思主义的枝叶政策, 这正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很明显,这种科学态度对于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及其对于中国革命的正确指导是极其重要的。施存统在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明确提出这个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这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和革命史上的意义是重大的和深远的。②李俊和周军在《论五四时期施存统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提出,施存统不仅对于促进共产党人进一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 而且是当时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水平相对较高的一位。施存统认为,马克思主义使“社会主义才具备了科学的体系”,“马克思主义底特色,在于注重物质的条件”。但是“马克思主义底本身,并不是一个死板板的模型”,要注重同各国的实际情况相联系。至于具体的操作,“一定要参酌中国情形”。③其中,李俊则更加强调施存统在五四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研究,为此他在《五四时期施存统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研究》中阐述得比较具体。他指出,当时,施存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翻译日本社会主义学者的研究论著,二是自己撰文宣传马克思主义,然后将这些译文、专论寄回上海《民国日报》发表,以便国人及时了解马克思主义以及当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近况。施存统占据天时地利人和, 先后翻译了山川均的《劳动组合运动和阶级斗争》、河上肇的《见于“共产主义宣言”中底唯物史观》、《俄罗斯革命和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上所谓“过渡期”》、佐野学的《中间阶级的社会主义论》等论著。通过翻译这些文章,既加深了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与信仰,同时也使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断提高。在翻译日本社会主义学者论著的同时, 施存统也发表了大量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些文章重点介绍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和唯物史观,并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意义。④陈国庆认同李俊对施存统五四时期政治思想及其变化的分析,但他同时强调施存统五四时期政治思想变化是两个过程的统一,即施存统对无政府主义信仰、批判、抛弃的过程,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接触、信仰、运用的过程。⑤
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精辟见解
杜芳则重点考察了施存统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她认为施存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上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当代化”和“民族化”。“当代化”指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时代发展的特征和状况相结合,具有世界眼光。“民族化”指马克思主义必须和各自国家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施存统怎么认识20世纪20年代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特征呢?在谈及为什么要用共产主义改造中国时,施存统指出:“俄罗斯共产主义国家,已经替全世界无产阶级开一个新纪元了;从此各国无产阶级必然奋起猛进,推倒有产阶级,与俄罗斯同志们携手协力建设共产主义的世界。”施存统的这一认识建立在他对时代特征的准确把握基础上。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中国革命已经进入到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中国革命理应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施存统对时代特征与中国革命关系的分析为以后的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重要借鉴,即必须要具有世界眼光。施存统以俄国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为例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要求。施存统指出:“俄国之所以让步到国家资本主义,乃是为开发实业的一种手段,并非各国都要如此。如果在产业发达的国家实行共产主义,则此种国家资本主义当可免除。”在此,施存统已经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必须和各自国家的实际情形相结合。那么中国的现实情形是怎样的?施存统指出:“中国资本主义虽不发达,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底冲突,却仍不免。我们只要看失业劳动军如此之多,就可以明白。”这种冲突如何解决?施存统号召“一切被掠夺被压制的阶级一同起来”,向“一般军阀,官僚,政客,绅士,资本家,地主等”实行无妥协的“阶级斗争”。中国社会问题的最终解决必须靠实行社会主义,但实行社会主义必须具备“物质的条件”,那么中国是否具备“物质的条件”?施存统指出:“我们一面知道中国非实行社会主义不可,但一面又知道中国现在很缺乏这个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的条件;所以在现在中国要实行社会主义,真是难乎其难。⑥
陶水木也在《施存统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贡献》中提及,施存统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我国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之始,就力图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学术界一般认为,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最早提出了“相结合”思想。但陶水木以为:无沦从提法还是从含义看,李大钊在该文中对这一问题的阐述都不甚明确,最早明确阐述这一问题的应是施存统,他在《主义与遗产》、《马克思底共产主义》、《第四阶级独裁政治底研究》等文中对此都有精辟的论述。⑦
三、在建团建党活动中的宣传组织工作
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所著《青年时期的施存统——“日本小组”与中共建党过程》中提到,1920年6月20日,在戴季陶的资助下,施存统从上海乘船到日本学习和养病。在日本东京,施存统经常与上海的陈独秀、李达保持通信联系,商讨建党的有关问题。这一时期的施存统,在日本看到许多国内查禁的书籍,他广泛涉猎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日本共产主义研究者河上肇对他产生巨大的影响,施存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并开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他翻译的《资本论大纲》和《社会进化论》等,深受读者赞赏。中共“一大”后,旅日共产主义小组发展很快,成员发展到10多个人,这其中包括后来成为“农民王”的彭湃,该小组的组长依然是施存统。1921年8月,共产国际为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派张太雷来到了东京,由施存统介绍与日本共产党员取得了联系,可是很不幸,同年12月,施存统与部分日本共产党员一起被捕,在东京监狱里关了10多天后,1922年1月,施存统被日本驱逐出境,遣送回国。⑧
除此之外,倪兴祥在《五四时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中提到施存统周佛海和张申府以及周恩来等在日本东京和法国巴黎的中国留学生中也成立了党的早期组织。这些各地党的早期组织的主要发起人和组织者,包括这些党的早期组织的主要成员绝大多数都是五四时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正是经过他们共同的不懈努力,才迎来了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宣告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南的,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⑨
施存统从日本回国后,受命于负责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他对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宋亚文在这方面做了探讨。她在《施存统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贡献》一文中,将施存统的贡献归纳为四个方面:全力以赴恢复和发展青年团组织,积极引导青年学生运动,正确对待青年运动问题的论争,奠定青年团思想建设的基础。⑩
当然,这些研究也并非尽善尽美。首先是资料整理不够,作为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施存统无疑是浙江籍里比较重要的一位,但是对于他的生平以及政治活动却研究甚少,只有一部传记。连回忆文章都显得有些苍白无力,不能准确全面地反映施存统对于建党及其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其次,笔者目前尚未发现有任何施存统文集的问世,从而不能集中反映施存统的政治思想,对于施存统的研究极为不利。另外,对于一些具体问题,比如施存统对建团的贡献及其建国后的活动几乎没有涉及,更不要说系统深入的研究了。
总之,近年来对施存统对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研究有了一些发展,但还不尽如人意。这个课题仍然需要进一步探讨。
注释:
①陶水木.施存统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贡献.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1(4)
②王炯华.略论施存统在建党时期的理论贡献.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87(2)
③李俊,周军.试论五四时期施存统的马克思主义观.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4)
④李俊.五四时期施存统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3)
⑤陈国庆.论施复亮在五四前后的思想转变.青岛海洋大学学报,1997(3)
⑥杜芳.施存统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世纪桥,2010(21)
⑦陶水木.施存统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贡献.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1(4)
⑧石川祯浩,王士花.青年时期的施存统——“日本小组”与中共建党过程[J].中共党史研究室,1995(3)
⑨倪兴祥.五四时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东方论苑,2004(9)
{10}宋亚文.施存统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贡献.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3(4)
参考文献:
1.齐卫平.施复亮传——民主革命时期的英勇战士[M].华夏出版社,1991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扬州 225002)
(责编:吕尚)